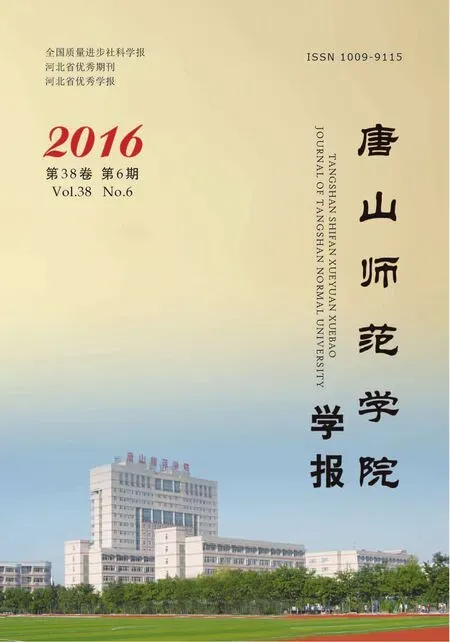汉字性质研究述论
包诗林
(商务印书馆 汉语编辑中心,北京 100710)
语言学研究
汉字性质研究述论
包诗林
(商务印书馆 汉语编辑中心,北京 100710)
汉字性质问题研究,贯穿整个20世纪,学者们从汉外比较、古今比较的角度,通过多个层面对汉字的性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方式论”与“单位论”之争的本质在于研究视角的不同,从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来看,“表意说”具有明显的缺失,“语素说”可以体现汉字的基本性质。
汉字性质;方式论;单位论;表意说;语素说
20世纪中国人的语言生活发生了三件大事:白话文运动、推广普通话、汉字改革。围绕汉字改革运动,从20年代到90年代初,学术界掀起了汉字性质问题的大讨论。在这场规模空前的讨论中,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采取多种标准,对汉字性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关于汉字的性质问题,虽然至今尚无定论,但在不少问题上还是取得了共识,这对汉字学自身的学科建设、比较文字学的创立和发展等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汉字性质问题研究的视角
客观事物的性质是共性与个性的结合。共性指的是客观事物发展变化所遵循的共同规律,通过对不同对象进行求同比较,可以得出关于对象的共性认识。个性指的是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多样性、独特性和特殊规律性,通过对不同对象或同一对象不同发展阶段进行求异比较,可以得出关于对象的特殊性认识。特殊性就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最根本的性质,所谓汉字的性质指的就是汉字区别于其他文字的最根本的属性。就汉字论汉字显然不能有效地认识汉字的性质,比较研究是探讨汉字性质问题的有效途径。
中国传统的文字研究,自许慎《说文解字》以来,始终围绕“六书”做文章。晚近以来,国门被打开,更多的国人有机会了解汉字以外的其他文字;西学东渐,国外的理论深深影响了我们的传统学术研究。另外,随着甲骨文的发现,古文字学的逐步建立,也给汉字研究提供了参照。
综观20世纪的汉字性质问题研究,学者摆脱了以往就汉字论汉字的单一视角局限,从比较角度审视汉字的性质。这种比较主要体现在汉外与古今两个方面。
(一)汉外比较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语言中的语素、词这些单位包括音和义两个方面,不论哪种文字,都是以不同的形体去记录语言中的各个成分的,即通过“形”记录语言的音和义,所以文字作为符号,本身有形、音、义三个部分。文字系统是在语言基础上产生并逐渐完善的,语言和记录它的文字之间虽然没有严格的对应性,但是任何一种文字必须适应自己所记录的语言的结构特点和语音特点[1,p186]。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具有一切文字的共性。与世界上的客观事物一样,汉字也是共性和个性的同一,要揭示汉字的性质,必须把汉字置于人类文字的体系内,进行汉字与非汉字间的比较。
在汉语言文字的研究史上,汉末魏晋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梵语以及记录梵语的拼音文字,曾给人们进一步认识汉语和汉字的性质提供了有效的参照,反切法的产生与完善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不过,受中国学术传统的影响,人们并没有就此深入研究下去。20世纪学者在研究汉字性质问题时,认识到了比较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立论、定性的依据。
从现有资料看,较早通过比较的方法给汉字定性并产生重大影响的是瑞士人索绪尔,他在1916年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说:“只有两种文字体系:(1)表意体系。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而这个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体系的古典例子就是汉字。(2)通常所说的,‘表音体系’。它的目的是要把一词中一连串连续的声音模写出来。表音文字有时是音节的,有时是字母的,即以言语中不能再缩减的要素为基础的。”[2,p50-51]索绪尔的定性是否合乎事实暂且不论,不过他对汉字的定性确实是通过比较而得出的。
在国内学者中,较早通过比较而给汉字定性的是沈兼士,20世纪20年代,他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字形义学》时说:“综考今日世界所用之文字,种类虽繁多,我们把它大别起来,可以总括为两类:(1)意符的文字,亦谓之意字。(2)音符的文字,亦谓之音字。意字的性质,不以声音为主而以表示形象为主,用文字来具体的或抽象的形容事物之状态,如文字画、楔形文字,中国的象形、指事、会意各字皆是;音字的性质以表示声音为主,大都是由意字转变来的,如欧美各国通用的拼音文字,中国的形声字皆是。”[3]
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比较文字学逐步建立,学者在研究汉字的性质时,自觉地把汉字置于整个人类文字的体系中加以探讨,比较的对象从记录屈折语的音素文字,扩大到记录黏着语的音节文字以及境内的少数民族文字,周有光、聂鸿音等在这方面多有建树。
(二)古今比较
古今汉字具有同质性,但差异也是比较明显的。伊斯特林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明确把古代汉字和现代汉字看成不同类型的文字[4,p32]。裘锡圭认为:“汉字在象形程度较高的早期阶段(大体上可以说是西周以前),基本上是使用意符和音符(严格说应该称为借音符)的一种文字体系;后来随着字形和语音、字义等方面的变华,逐渐演变成为使用意符(主要是义符)、音符和记号的一种文字体系(隶书的形成可以看作这种演变完成的标志)。如果一定要为这两个阶段的汉字分别安上名称的话,前者似乎可以称为意符音符文字,或者像有些文字学者那样把它简称为意音文字;后者似乎可以成为意符音符记号文字[5,p16]。
王凤阳在《汉字学》中明确指出,从篆书到隶书是文字体系由量变进入质变的标志,是记号表意文字取代象形表意文字的标志,是汉字新时代的到来[6,p489]。
王宁说:“汉字是表意文字。这样定性只是说,汉字是因义构形的。”[7]她后来在《汉字汉语基础》里则对古今汉字的表意性做了区别,认为早期的汉字是因义而构形的,这一点在小篆以前的古文字阶段表现得更为直接和明显[8,p78]。
王伯熙也提出过古今有别的观点:“古代汉字(小篆以前的汉字)是一种象形拼符表词文字;现代汉字(汉隶以后的文字)是一种方块拼符表词文字,或者也可以说现代汉字是一种方块拼符语素文字。”[9]
周有光从多个方面考察了汉字的性质,认为古今汉字在性质上有所不同,在古文字阶段的汉字是“语素+形意音+图符”文字,隶楷阶段的文字是“语素+意音区别+字符”文字。古文字阶段的汉字跟文字画的性质不同,文字画的性质应是“章句+形意+图符”文字[10]。
从以上可以看出,在古今汉字的划界标准上,各家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即小篆以前为古文字阶段,隶楷以后为现代汉字阶段。在古今文字的主要区别上,观点也基本差不多,即古今汉字的构形方式存在差别。在研究汉字性质时,这种区分还是必要的。单说古文字,或单说现代文字,甚至古今不分,有些问题会纠缠不清。学界对汉字性质之所以人言言殊,与古今不分是有一定关系的。
不同文字以及同一文字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构造方式和表达功能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研究汉字性质的众多学者也正是从这些角度加以阐发,进而导致多标准的研究格局。
二、判断的标准与汉字的定性
形、音、义是汉字符号本身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研究汉字的性质当然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记录语言是文字的主要功能,文字符号的性质与它所记录的语言的特点有一定的关系。所以,研究汉字的性质,又可以将汉字与汉语的关系作为切入点。汉字与汉语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汉字记录语言的方式和汉字记录语言的单位。切入点不同,会产生标准上的分歧,从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就判断汉字性质的标准而言,有人主张单一标准,有人主张双重标准,还有人主张多重标准。
(一)单一标准
1. 从汉字记录语言的方式看
(1)象形文字(衍形文字)
吴玉章1940年发表《新文字与新文化运动》认为,中国的汉字注重形体,表示一个物件的词,就是这个物件的图形,每一件事情也按照事情的意义表示出来,这种文字叫象形文字[11]。
云中1943在《真知学报》2卷6期上发表《中国文字与中国文字学》认为,“中国文字随着中国之特殊语言而构成‘衍形’文字,欧美诸国因语言多诘屈而形成‘拼音’文字。……中国文字无论如何衍形,不能脱离象形形式,此为中国文字之特殊性,与中国语言有密切之关系”[12,p3-4]。
蒋善国也曾从形的方面考察汉字的性质,他在《汉字的组成和性质·自序》中说:“汉字的本质是衍形的,在字形里面,反映了古代社会的生活。”[13]
(2)表意字
索绪尔的“表意文字”说,对我国的文字学界产生很大影响,沈兼士20世纪20年代在《文字形义学》中把汉字定性为“意字”,40年代张世禄在《文字学与文法学》里把这种“一方面保持着一些图画文字的遗迹,另一方面却又具有很丰富的表音成分”的中国现行汉字称为表意文字[14,p162]。
梁东汉在《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中也提出:“方块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15,p59]
曹先擢认为,现代汉字形声字的大量来源是以假借为声符再加义符造出,形声字的增加,从主要方面讲是大大加强了汉字的表意性,而不是相反。“汉字的表意性是汉字的命脉,表意性一旦受到根本性的破坏,汉字将难以有效地为社会服务。”[16]
王宁也认为,汉字因义构形,属表意文字[7]。陈淑梅对此做了进一步论证,她认为,研究汉字的性质只能从语音或语义入手,以此为标准,汉字是“根据语言的意义构拟形体”,因而可称为“构意文字”,即通常所说的表意文字[17]。
(3)表音文字
郭沫若1955年在《光明日报》上撰文,提出了对文字性质的看法,“汉字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基本上是保守着所谓‘象形文字’的体制的,但在实际上是走着音标化的道路的。特别在今天语汇的组成起了很大变化,很少用一个字来表示一个事物了。因此,汉字差不多已经成了纯粹的音标,就是表音的符号了”[18]。
真正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的是姚孝遂的“表音文字”说。《古文字研究》第一辑发表了署名为“吉林大学古文字研究室”的文章,对古代汉字是象形文字这一普遍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19],后来姚孝遂撰文对表音说做了论证。“就甲骨文字的整个体系来说,就它的发展阶段来说,就它的根本功能和作用来说,它的每一个符号都有固定的读音,完全是属于表音文字的体系,已经发展到了表音文字阶段。其根本功能不是通过这些符号形象本身来表达概念的,把它说成是表意文字是错误的。”[20]
(4)意音文字
“意音文字”说的主要依据是汉字中存在着大量的形声字。1931年徐来银在《夜光》第1卷第2期上撰文《中国文字的特性》,认为汉字“以不同性质之二种符号,配合成文。一者代表意义的符号,一者代表读音的符号。”“此音义之文字,为吾国文字之特性”[12,p2]。
20世纪50年代周有光、曹伯韩相继提出意音说。周有光从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出发,对意音文字做了系统的阐述,认为汉字还维持在意音制度上[21]。曹伯韩把世界上的文字类型分为意音文字和拼音文字两大类,认为汉字属意音文字[22]。
(5)形音文字
刘又辛从汉字的构形出发把现代汉字分为表形、表音和形音三大类,并据形声字占汉字的主流这一事实,认为汉字兼表形和表音两种功能,属形音文字[23]。
2. 从文字记录语言的单位看
(1)表词说
布龙菲尔德在《语言论》中说,表意文字这个名称容易使人产生汉字直接表示观念这一错误认识。因此,他认为最好把“表意文字”改为“表词文字”[24,p360]。
(2)语素(词素)文字
语素理论产生以后,国内外许多学者从汉语记录汉语的单位出发,探讨汉字性质问题。赵元任在1959年发表的《语言问题》演讲稿中,首次把汉字称为词素文字[25,p141-144]。
前苏联著名比较文字学家伊斯特林在1960年出版的《文字的产生和发展》一书中说:“很早以来就确定了文字体系分为三种类型的传统分法,这三种类型传统上称为‘图画文字’‘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但是,伊斯特林认为文字类型的这种三分法是不够严密的,“方法正确的文字分类法应该从符号的意义出发。既然文字是用来表达言语,所以书写符号和图形就应根据它们表达言语的何种要素来分成各种类型。文字类型的名称也应据此而来”。他的结论是,文字可分为句意字、表词字、词素字、音节字和语音字(音素字)五种类型,古汉字属表词字,现代汉字属词素字[4,p27-32]。
吕叔湘在《汉语文的特点和当前的语文问题》中,根据文字代表语言的单位,把世界上的文字分为三类,即音素文字、音节文字和语素文字,认为汉字是语素文字的代表[26]。
李荣也明确提出,汉字为语素文字[27]。史有为也说,汉字是世界上独特的文字系统,它最大的妙处是替人们把语素基本上分析出来了[28,p16]。
高明在《中国古文字学通论》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汉字不仅每个字各代表一个音节,而且还具备独立的词义,所以应该把它区别于一般的音节文字,而称之为“音节词字”[29,p48]。所谓“音节词字”,实际上也就是语素文字。
(3)音节—语素文字
由于汉语中存在着一些联绵词和外来词,单个音节没有意义,因此从文字记录语言的单位来看,汉字还有单纯记录音节的一面。叶蜚声和徐通锵在《语言学纲要》中认为汉字为语素—音节文字[30,p164],后来尹斌庸在《给汉字“正名”》一文中对此做了进一步阐释[31]。
(二)双重标准
裘锡圭多次谈到汉字的性质问题,在《汉字的性质》一文里,他先明确指出,一种文字的性质是这种文字所使用的符号的性质决定的,汉字不应该简单地称为语素文字,而应该称为语素—音节文字,不过他在做进一步讨论时,又倾向于意音文字说[32]。后来他在《文字学概要》中说,仅仅根据文字书写的基本单位所代表的语言成分的性质来给汉字体系定名,也是不妥的。因此,裘锡圭认为,考察汉字的性质,要从两个方面进行。第一方面是看文字使用什么字符。字符包括意符、音符和记号,在汉字象形程度较高的早期阶段,基本上是使用意符和音符的一种文字体系,后来随着字形和语音、字义等方面的变化,逐渐演变成为使用意符、音符和记号的一种文字体系。第二方面是看文字表达语言中的什么单位。从这一点看,汉字是语素—音节文字[5,p14-15]。
朱德熙认为,要弄清汉字的性质,应该区别两个不同的平面,一是汉字作为语言的符号,另外一个是汉字本身使用的符号,在分类与定性问题上基本同意裘锡圭的观点[33]。在讨论中,胡双宝认为汉字为语素/义素文字[34]。
苏培成在综合各家之说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汉字的不同定性是因为从不同角度去立论而得到的结果。从文字记录语言的基本单位着眼,汉字是语素文字;从汉字内部的结构看,汉字是意音文字。他还比较了两种定性的关系,认为二者不是并列关系,语素说为主,意音说为从[12,p25]。
张桂光把汉字分成两类,一类是纯粹的表意字,一类是形声字。纯表意字固然是表意文字,形声字就整体而言,仍属于表意字的范畴,他认为这是汉字性质的主要方面。另外,他又从汉字与汉语音节的对应关系的角度,认为汉字属语素文字,他说这是决定汉字性质的另一方面。“所以,汉字就汉字的整个符号系统而言,汉字应属于表意性质的文字,确切地说,汉字是音节的表意文字。”[35]
(三)多重标准
最早从多角度认识汉字性质的是姜亮夫,1933年他在《青年界》4卷4期上发表的《中国文字的特色及其在学术上的地位》一文中认为,中国文字的特色体现在“衍形”“单音缀”和“方整美观”三个方面[12,p3]。
高家莺认为,汉字从它记录的语言单位看是一种语素文字,从它记录语言单位的方式看是一种意音文字,从它的书写形体看是一种方块形平面汉字[36]。
王伯熙认为,讨论汉字的性质应该首先明确概念的逻辑范畴,概念范畴明确,才不至于互相混淆。从文字体制来看,它是表意文字;从记录语言单位来看,它是词素文字;从记录语音成分来看,它是表音节的文字;从构形来看,它是方块汉字[37]。
根据多重标准给汉字定性,影响较大的当属比较文字学家周有光。自1957年提出意音文字的观点后,他在1987年撰写的《文字类型学初探》一文中提出考察评判文字的“三相说”,即“符号相”“语段相”和“表达相”。根据“三相说”的标准,汉字在古文字阶段是“语素+形意音+图符”文字,隶楷阶段的文字是“语素+意音区别+字符”文字[10]。
三、“表意文字”说的局限
不同的标准,会产生不同的结论。汉字性质的讨论主要是围绕表意、意音和表音三种观点各抒己见。至于标准问题,主要集中在记录语言的方式(称之为“方式论”)与记录语言的单位(称之为“单位论”)两个方面。“方式论”者坚持汉字的自身的表意性,认为汉字是表意文字、意音文字。而“单位论”者认为,汉字是语素文字。两种标准孰优孰劣姑且不论,单从结论来看,“方式论”在研究汉字的性质,特别是在探讨现代汉字的性质时,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一)从表意与表音二分的基础看
综观20世纪,受西方文字学的文字发展观及文字优劣论的影响,与讨论汉字性质相纠缠的是汉字改革问题,学者对汉字改革的立场不同,会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对汉字性质的认识上。提倡汉字拼音化的钱玄同,在1923年发表的《汉字革命》一文中提出,“汉字的变迁,由象形而变为表意,由表意而变为表音。表音的假借字,和拼音文字只差一间”。他是用文字发展“象形→表意→表音”的规律来印证文字发展的“三段论”[38,p40],实际上是为汉字的拼音化寻找理论依据。
伊斯特林在谈到文字发展时曾特别指出,文字发展具有总的历史规律性,但根据这一点来判断某种类型文字的先进或落后,则是根本错误的。某种类型的书写体系,如果符合语言的特点和该体系使用的条件,如果它达到十分完善的境地,那么这种书写体系就可能是合理的[4,p556-557]。关于文字发展的阶段论,聂鸿音对此有过精当总结:“‘文字发展三段论’和‘语言发展三段论’(孤立语→黏着语→屈折语)可以说同样是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进行殖民扩张这一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随着比较语言学的发展,‘语言发展三段论’已于20世纪上半叶被人们抛弃,而‘文字发展三段论’却至今还有大量拥护者。”[39]
汉字拼音化,至少到目前为止,既无可能,也看不到必要。表意、表音之争显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更不具有语言学上的价值[40]。
(二)从“表意”自身的内涵看
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便指出,“表意文字”是一个很容易引起误会的名称[24,p360]。实际上,这种“误会”还是被布氏言中了。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说:“在中国,一如在埃及,文字不过是一种程式化了的、简单化了的图画系统。就是说,视觉符号直接表示概念,而不是通过口头的词去表达概念。”[41,p39]这种极端化了的“表意文字”,本质上与原始图画毫无二异。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内也有人在宣传类似的观点,并且认为这就是汉字的优越性所在。历史上“水之皮为‘波’”的说字法和当今“十分具体为‘真’”的切字法,已使汉字研究走上庸俗主义的歧途;无限制地扩大汉字的表意性,神化汉字的功能,势必把汉字研究引入客观唯心主义的泥淖。
关于汉字表意说,郑林曦曾做过一段发人深思的论述,他说:“汉字果然有一看形就知义的神力吗?真是那样的话,《甲骨文编》上所收的4 672个字该早已全部认识了,用不到古文字学家花上近百年的苦功夫,才认识了一千来个,还有三千多至今还千百遍看不知其义!”[42]语虽偏激,但不无道理。
(三)从汉字的构形方式看
传统的“六书”理论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常常被“方式论”者作为汉字表意说的立论根据,而象形、指事、会意又被看成是最具表意特点的构形方式。实际上,象形文字早在殷商时代已发展到极至,并逐渐丧失构成新字的能力。随着语言的发展,作为记录汉语书写符号的汉字,指事、会意等构形方式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
黄德宽对汉字构形方式系统进行了动态分析,结果表明,从殷商到宋代约2500年间,汉字经历了从古文字到近代文字的发展,汉字结构类型的分布比例发生了很大变化,指事类型的汉字分布从4.29%降到0.53%,象形类从28.28%降到2.07%,会意类从37.50%降到3.53%,而形声类从29.10%上升到93.87%。“西周以后,汉字构形方式总体上看再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形声构形方式的勃兴和表意构形方式的衰落,其时间之早是以往学者所未曾揭明的。由此看来,所谓汉字是‘表意文字’的说法显然不能从构形方式系统发展的角度得到有力的支持。”[43]
(四)从形声字的结构看
就发展过程而言,多数形声字是通过对假借字加注形符而形成的,并逐渐发展到加注声符和形、声直接组合等构成方式。一般认为,形声字的形符表示一定的意义,声符记录语音,而现代汉字形声字占90%左右,所以自然会得出汉字为“意音文字”的结论。
“意音文字”说的根据正是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形声字。那么现代汉字中形声字的表意、记音的实际状况究竟如何呢?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汉字整理研究室对《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中的7 000个通用汉字进行了定量研究,在一般认为的5 636个形声字中,声韵调完全相同的占形声结构的比例为40.54%,声韵调完全不同的占形声结构的比例为12.56%,还有近半数的形声字的声符只是近似地记录语音。声符的记音状况如此,形符的表意功能则更差,在所统计的使用频率最高的前10个形符中,完全表意的只有5个,完全不表意的199个[44]。所谓形符表意,也只是大致地揭示类义或特征,与所记录的语言中的词的意义并不是一回事。
既然现代汉字中的形声字既不能准确地标音,又不能充分地示意,不顾事实仍把它叫作“意音文字”,争议便在所难免。
另外,就整个汉字文化圈而言,同为方块形的汉字,在不同的系统里,其地位、性质与功能显然是不同的。日本官方1981年颁布《常用汉字表》和《人名用汉字别表》,两表共收汉字2 229个,韩国文教部1972年制订了1 800个教育用基础汉字。记录日语的汉字、记录韩语的汉字与记录汉语的汉字不属于同一语言文字系统的文字,同一个方块汉字,如果仅从形体结构上看,它在各自文字系统中的地位、性质以及功能是无法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的。
四、“语素文字”能够体现汉字的基本性质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文字符号的产生和发展是以语言的存在为前提的,语言符号有音和义两部分,而文字符号则是以形记录语言中的音,进而表示意义。因此,任何体系的文字都是由形、音、义三个部分组成的。片面强调表意或表音功能,不能完全理清汉字的性质问题。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其功能首先表现为工具性,所谓的审美功能、益智功能等都是其附属功能。因此,从记录语言的单位来讨论汉字的性质是一条可行的途径。
从记录语言的单位来讨论汉字的性质,具有标准的同一性,因而更具科学性。表意说与表音说是从文字发展的两极各自申述自己的理由,也就很难形成共识。从记录语言的单位看不同体系的文字,首先要找准文字与它所记录的语言间最小的结合点,文字是通过形体记录语言中的音,进而表达一定的意义,语音单位包括音节、音素(音位),根据文字与语言的结合点不同,即文字记录语言的单位不同,由此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认识文字的性质。
从记录语言的单位来讨论文字的性质,在称名上也更容易取得共识。文字与语言在某个单位上实现结合,便可称为某某文字。“书写符号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决不是它的形式,而是它的意义,即这些书写符号表达言语的哪些要素,文字分类就应该建立在这个特点的基础上。”[4,p28]文字与它所记录的语言在音素(音位)层面上实现结合,便可称为音素(音位)文字;文字与它所记录的语言在纯音节上实现结合,便可称为音节文字。单个汉字记录的是语言中的音节,汉语的音节绝大多数都表达意义,显然,汉字在语素层面上与汉语实现结合,所以汉字叫语素文字。
汉字为语素文字,语素所表达的是语言符号的意义。“方式论”者所谓的“表意”,指的是汉字形体所表达的造意,造意与语言义不在同一层面,而且即便是造意,从现代汉字的构形也不易辨识。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文字体系是为适应语言需要而逐步完善的,语言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文字特点。汉字首先是因为记录语素而表达意义,而不是相反。段玉裁在《广雅疏证》的序言中曾明确指出:“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而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45]此话说在200年前,今天来看也并不过时。
[1] 高名凯,石安石.语言学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3] 沈兼士.文字形义学[A].沈兼士学术论文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6:375-566.
[4] B. A.伊斯特林.左少光,译.文字的产生和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5]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6] 王凤阳.汉字学[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
[7] 王宁.论汉字简化的必然趋势及其优化的原则[J].语文建设, 1991(2):24-29.
[8] 王宁.汉字汉语基础[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
[9] 王伯熙.文字的分类和汉字的性质——兼与姚孝遂先生商榷[J].中国语文,1984(2):108-116.
[10] 周有光.文字类型学初探——文字“三相”说[J].民族语文, 1987(6):5-19.
[11] 吴玉章.新文字与新文化运动[A].文字改革文集[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8:27-88.
[12] 苏培成.二十世纪的现代汉字研究[M].太原:书海出版社, 2001.
[13] 蒋善国.汉字的组成和性质[M].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1980.
[14] 张世禄.文字学与文法学[A].陈望道,等.中国文法改革论丛[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61-167.
[15] 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59.
[16] 曹先擢.汉字的表意性和汉字的简化[A].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北京:语文出版社,1987:17-27.
[17] 陈淑梅.论判定汉字性质的标准及汉字的构意性质[J].语文建设,1998(8):27-30.
[18] 郭沫若.为中国文字的根本改革铺平道路——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1955-10-25(3).
[19] 吉林大学古文字研究室.古文字研究工作的现状及展望[J].古文字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80:12-22.
[20] 姚孝遂.古汉字的形体构造及其发展阶段[J].古文字研究(第四辑),中华书局,1980:7-40.
[21] 周有光.文字演进的一般规律[J].中国语文,1957(7):1-5.
[22] 曹伯韩.文字和文字学[J].中国语文,1958(7):322-324.
[23] 刘又辛.汉语汉字答问[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4] 布龙菲尔德.袁家骅,等译.语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
[25] 赵元任.语言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6] 吕叔湘.汉语文的特点和当前的语文问题[A].语文近著[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141-155.
[27] 李荣.汉字的演变与汉字的将来[J].中国语文,1986(5):321-333.
[28] 北京市语言学会.教学语法系列讲座[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7.
[29] 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30] 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1.
[31] 尹斌庸.给汉字“正名”[J].中国语文通讯,1983(6):13-14.
[32] 裘锡圭.汉字的性质[J].中国语文,1985(1):35-41.
[33] 朱德熙.在“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发言[A].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北京:语文出版社,1987:11-16.
[34] 胡双宝.关于汉字的性质和特点[A].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北京:语文出版社,1987:114-119.
[35] 张桂光.汉字学简论[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
[36] 高家莺.文字研究方法的改革趋向[A].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北京:语文出版社,1987:91-99.
[37] 王伯熙.汉字特性和文字改革[A].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北京:语文出版社,1987:204-213.
[38] 周有光.汉字改革概论[M].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79.
[39] 聂鸿音.从文字发展史看汉字的现状与前途[J].语文建设, 1993(5):12-15.
[40] 詹鄞鑫.20世纪汉字性质问题研究评述[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41-47.
[41] L. R. 帕默尔.语言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42] 郑林曦.有关汉字改革的两个语文问题[J].文字改革,1982 (2):27-31.
[43] 黄德宽.汉字构形方式的动态分析[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1-8.
[44] 李燕,康加深,魏励,等.现代汉语形声字研究[J].语言文字应用,1992(1):74-83.
[45] 王念孙.广雅疏证[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责任编辑、校对:郭万青)
A Synthetic Account of the Na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BAO Shi-lin
(Chinese Editing Centre, The Commercial Press, Beijing 100710, China)
Studies on the na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abound throughout the 20th century. Meaningful outcome had been made by comparing Chinese with foreign languages and by comparing ancient with modern Chinese. The debate on the mode theory and the unit theory actually comes out of different research perspectiv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characters, ideographic theory has obvious deficiency; while morphemic theory can reflect the na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 na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mode theory; unit theory; ideographic theory; morphemic theory
H12
A
1009-9115(2016)06-0010-06
10.3969/j.issn.1009-9115.2016.06.003
2016-05-25
包诗林(1967-),男,安徽舒城人,博士,副编审,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字学。
——针对对外汉语语素教学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