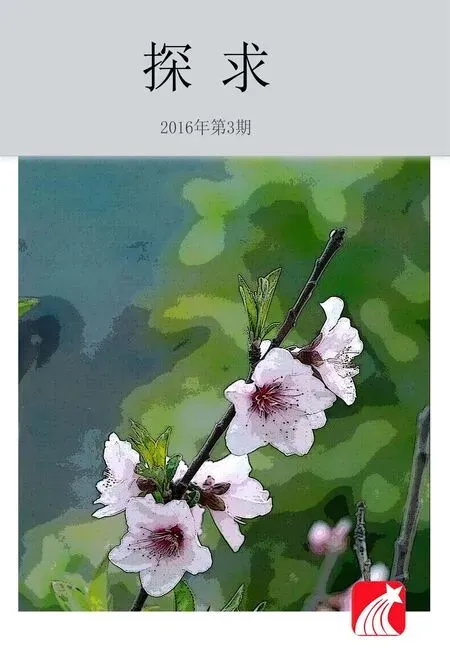试析《广州大典》对于广州文化认同的价值
□文远竹(广州日报报业集团 研究室,广东 广州510121)
试析《广州大典》对于广州文化认同的价值
□文远竹(广州日报报业集团 研究室,广东广州510121)
《广州大典》是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标志或文化符号,对于广州文化认同的价值,主要表现在历史渊源、群众基础、时代气息三个方面。《广州大典》是广州文化的集中体现和重要组成部分,蕴涵了广州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元素,具有开放性和跨文化性等特点,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申遗正走向世界。
广州大典;文化认同;价值
一地之文化有别于他地,最主要的是有其独特的文化标志或文化符号,能激起本地民众普遍的文化认同,产生一种文化的优越感和文化的归属感。《广州大典》之于广州文化,就是这种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标志或文化符号,地域性、时代性十分明显,也具有时空上的纵深感。《广州大典》对于广州文化认同的价值,主要表现在历史渊源、群众基础、时代气息等几个方面。
一、文化认同的历史渊源:《广州大典》浓缩了上千年的广州文献典籍,是广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州大典》是一部大型的历史文献丛书,旨在系统搜集整理和抢救保护广州文献典籍。《广州大典》对于广州文化认同的价值,首先表现在其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广州大典》浓缩了上千年的广州文献典籍,已成为广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州大典》依经、史、子、集、丛五部分类,收录历代4064种文献,编成520册。编纂完成后,相当于把广东历史上的文献典籍整理了70%,见证了广州作为广府文化发祥地和文化载体的这段历史,揭示千年古城根与魂。
仅举南海神庙庙会活动为例,《广州大典》以大量的典籍汇编,对南海神庙为载体的庙会文化活动进行了详尽的记载。南海神庙是我国古代有历朝官方拜祭的四大海神庙中唯一完整保存至今的最大、最古老的海神庙。相传由土人董昙始建于南朝梁武帝大同元年(535年)。[1]按官书记载,最迟于隋代已经建成。据《通典》记载:“于南海镇南并近海立祠。”[2]《隋书》中也有相同的记载,并明确了建祠的时间是“文帝开皇十四年(594年)闰十月”。[3]《广州大典》对此进行了分门别类的记载。在广州民间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波罗诞庙会活动,起源于何时众说纷纭。据《广州大典》记载,波罗诞相传始于唐代。当时,一位波罗国(今属印度)的使者乘船至广州,因故误了归船返航的时期,后来终老于广州。他把携来的波罗树种子植于南海神庙中,后化为神,当地人在庙中为他建一塑像,并尊其为“达奚司空”。[4]南海神庙因此又名“波罗庙”,南海神庙的庙会也称为波罗诞,诞期为每年农历二月十一至十三,正诞为农历二月十三。从宋代始,波罗诞已成为一个颇具规模和地方特色的庙会,南宋诗人刘克庄在他的《即事》诗“其一”、“其二”对当时波罗诞的盛况有过生动的记载:“香火万家市,烟花二月时。居人空巷出,去赛海神祠。东庙小儿队,南风大贾舟。不知今广市,何似古扬州。”明代以后,波罗诞活动盛极一时,南海神庙也成为全国有名的庙会胜地。清代许多史料和文人笔记、诗词中也有不少关于波罗诞的记载。嘉庆年间人崔弼在他写的《波罗外纪》中对波罗诞庙会的热闹情景有过十分生动的描述:“波罗庙每岁二月初旬,远近环集如市,楼船花艇,小舟大舸,连泊十余里,有不得就岸者,架长篙接木板作桥,越数十重船以渡,其船尾必竖进香灯笼,入夜明烛万艘与红波辉映,管弦呕哑,嘈杂竟十余夕。连声爆竹,起火通宵,登舻而望,真天宫海市不是过矣。至十三日,海神诞期,谒神者……络绎庙门填塞不能入庙……凡省会、佛山之所有日用器物玩好,闺阁之饰,儿童之乐,万货聚萃,陈列炫集,照耀人日……糊纸作鸡涂以金翠或为表鸾彩凤,大小不一,谓之波罗鸡,凡谒神者游剧者必买符及鸡以归,馈赠邻里,谓鸡比符为灵。”
《广州大典》记载了波罗诞庙会活动与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南海神庙和扶胥古镇的发展、历代皇帝对南海神庙的敕封、地方官吏的祭祀等活动。可以说,作为有形文化典籍的《广州大典》全程记录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无形文化遗产的波罗诞庙会与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的这段历史。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明代以后,南海神庙一带在环境和功能方面都出现重大变迁,唐代时作为全国最大对外贸易港的扶胥港商贸功能日渐衰落,最后遗迹都沉没在了今天庙头村的鱼塘底部。[4]在作为广州文化载体的许多史迹遭到毁坏、荡然无存之后,《广州大典》以经典的典籍记载,传承了这段逝去的文化,也勾起了人们对这段文化的记忆和认同。
二、文化认同的群众基础:《广州大典》蕴涵了广州最有代表性的本土文化元素,符合地方民众的文化心理需求
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需要广泛的群众基础,否则便是“空中楼阁”或“空谷幽兰”。《广州大典》蕴涵了广州最有代表性的本土文化元素,符合地方民众的文化心理需求,为广州文化认同打下了扎实的群众基础。《广州大典》详细记载了白云、越秀的传统醒狮,海珠、荔湾的咸水歌,南沙黄阁的麒麟舞,天河的猎德大鼓,番禺的龙舞、高桩醒狮,花都、增城的客家山歌,萝岗的貔貅舞,从化的猫头狮,粤曲大吼,粤北采茶戏等岭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渊源,甚至还有波罗粽、鸡仔饼、双皮奶等独特岭南特色的美食文化。
《广州大典》不仅仅是一部地方文化典籍百科全书,也为广大广州市民提供了充满广州文化元素的公共文化服务。《广州大典》记载了充满想像空间的“南海神传说”和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留下张九龄、苏东坡、陈白沙、林子觉等不少名人佳作的“章丘诗会”,诗歌、词赋、散文、楹联分门别类,吸引了各年龄段的市民对广州文化的浓厚兴趣。
文化认同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社会心理过程,并不是一朝一夕,或简单一两句口号就能形成。“文化认同的意义在于构筑人类精神与心理安全和稳定的基础。”[5]因而,一种区域文化要想得到广泛认同,一定得符合地方民众的文化心理需求。而作为广州文化经典大全的《广州大典》,正是极大地满足了广州市民对本土文化寻根的最原始的、最基本的心理需求。
在古代,广州等沿海地区远离中原,语言、习俗等与中原地区相差甚远,被视为“南蛮”之地。而《广州大典》却通过对祭祀、舞蹈、说唱等系列民俗活动的记载,实现了对本地区、本族群文化活动的记录。向年轻一代灌输、传播本地区、本族群文化的一般知识,并通过这种方式延续自己的文化,让后代了解自己的文化,增强本地区、本族群文化的自豪感和优越感,“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中,人们建立起对本文化的认识并与其强烈的认同,同时在这种认同中获得安全感和心理力量”[5]。《广州大典》主编、时任广州市市长陈建华指出,《广州大典》是有鲜明特色和弥足珍贵的“城市记忆”,也是“民族记忆”和“人类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构筑了广州学术研究的新平台。[6]
文化认同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需要有异质性,此文化非彼文化,能自立于文化之林。《广州大典》便恰恰具有这种特点,具有广州文化、岭南文化等显著特点,有别于内地其它地域的文化。
《广州大典》记录的广州文化还具有开放性和跨文化性的显著特点。在《广州大典》里记载的广州文化活动,从古至今都不是封闭式的,而是面朝大海、多元文化交融的开放式的文化活动,这与广州作为“海上丝路”的发祥地有关。生活在广州的民众大多是常海出海的渔民或经常与外商打交道的商人,他们见多识广,心胸开阔。广州本土文化活动与内地相对封闭式的中原文化有所不同,是富有岭南地域特色和异域风情的海洋文化。像南海神庙是有史可考的最古老的皇家祭海圣地及最早的对外通商口岸。在上千年的传承中,岭南地区形成了以祭祀南海神为主的独特的“洪圣文化”。岭南地区遍布300多座洪圣庙,远至香港、澳门地区也有洪圣庙。[6]南海神庙不仅是岭南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中国海事文化的发源地。“从海上丝绸之路目前可以查询到的资料来看,最早出发和到达的船都在这里,最早的通商口岸也在这里,闭关锁国的时候,这里没有关闭过,2000多年一直畅通。”[7]在《广州大典》的记载里,广州文化以开放姿态将彰显皇家气象的中原文化与放眼海疆、沟通异域的海洋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广州是多元文化实现跨文化交流的舞台。中原文化与海洋文化在这里交融,中华文明与异国文明在这里碰撞。《广州大典》记载的文化活动既有岭南地区海神、财神等神灵崇拜,也有中原皇家正统祭祀,还有源于异域的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及商业文化、“海丝”文化等多元文化的交融。《广州大典》客观地记载了广州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窗口的这段历史。
三、文化认同的时代气息:让现代人找到“乡愁”,带着“海丝”走向世界
《广州大典》的经典典籍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仍对广州文化认同具有极大的价值?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以深厚的文化积淀,唤醒了现代人对于原初时代的“童年记忆”,让现代人在城市森林中找到了“乡愁”;二是在“海上丝绸之路”申遗的热情之中,让广州人加深了对广州本土文化重要性的认识。
(一)《广州大典》正成为现代广州人挥之不去的“乡愁”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双重压力下,人际交往方式和信息传播方式得到了彻底的巅覆。现代人在城市化、信息化、国际化等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身份”焦虑,人们迫切需要找到可以得到文化身份认同和纾解文化“乡愁”的载体。“这个乡愁虽可能沾带有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中所说的‘家的意识形态’(ideology of home),但从根本上说,更与一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相关。说到底,一切的乡愁,都是对文化的乡愁。”[8]《广州大典》蕴涵了广州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元素,以典籍的方式记载着最原始、最纯正的广州文化、风俗习惯,其中又弥漫着远古神话、民间传说、异域风情等文化“兴奋剂”,正成为现代广州人挥之不去的“乡愁”。现代广州人在“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寻根、坚守中,不知不觉中完成了对广州文化的认同。
(二)“海丝”申遗必将在激发广州文化认同中发挥更大作用
近年来,以广州、泉州、北海、漳州、宁波、扬州等为代表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9城市,正积极推进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2013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曾为东西方交往作出巨大贡献的“海上丝绸之路”,再次被赋予深刻含义。《广州大典》也将“海丝”文化作为鲜明的特征和符号。作为“海丝”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广州大典》,在申遗中成为广州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载体,也必将在激发广州文化认同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陈建华主编认为:“《广州大典》的出版完成,标志着广州占据了另一个文化高地,是这座城市内心深处的文化自信,将有助于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9个城市中的牵头城市。”[9]
[1](清)仇池石.羊城古钞(八赉堂藏版)[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
[2](唐)杜佑.通典·礼六[M].北京:中华书局,1988.
[3]隋书·礼仪志(卷七)[Z].北京:中华书局,1997.
[4]王少冰、卢丽芬.广州扶胥港·南海神庙与“海上丝绸之路”浅析[C].洗庆彬主编.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香港: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7.186.
[5]时东陆.21世纪,寻找现代文化认同的中国[J/ OL].360doc个人图书馆.http://www.360doc.com/content/ 07/0805/08/9737_654095.shtml.
[6]《广州大典》出版座谈会隆重举行[J/OL].广东文化网,2015—5—5.http://www.gdwh.com.cn/whwnews/20-15/0505/article_25924.html.
[7]吴彤、周松.新八景要传承广州历史文脉[N].羊城晚报.2011—1—6.
[8]汪涌豪.中国文化中的乡土意识与情怀[N].文汇报,2010—4—18.
[9]张林、王秀全.《广州大典》编纂十年完成出版揭示千年古城根与魂[N].羊城晚报,2015—5—1.
□责任编辑:温朝霞
G237
A
1003—8744(2016)03—0021—04
2016—4—26
文远竹(1977—),男,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研究室主任、高级记者,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媒体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