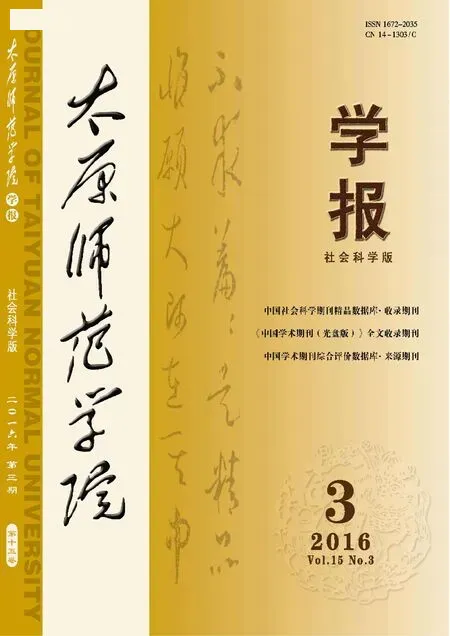《文心雕龙》“物”范畴的多层次内涵
吴建民,夏新秀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文学】
《文心雕龙》“物”范畴的多层次内涵
吴建民,夏新秀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徐州221116)
[摘要]“物”是古代文论的核心范畴,在古代文论建构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心雕龙》是古代最重视“物”范畴的文论著作,全书有二十篇文章运用“物”范畴阐释其理论观点。《文心雕龙》的“物”范畴涉及创作发生论、艺术想象论、艺术表现论等多方面理论,对其展开研究是把握古代文论“物”范畴丰富内涵的一把钥匙。
[关键词]文心雕龙;“物”范畴;古代文论
“物”是古代文论的核心范畴之一,具有极强的理论建构功能和衍生功能,形、象、景、境等都是与它相关或由它衍生出来的系列范畴。以“物”为词根,有“感物生情”、“神与物游”、“体物得神”、“借物抒情”、“以物观物”、“格物”、“物格”等理论命题,涉及创作发生、艺术想象、艺术表现、作品构成等多方面理论。“物”作为古代文论范畴萌芽于先秦,正式形成于汉代的《乐记》,之后历代文论家在阐述其文论思想时几乎都离不开“物”及与其相关范畴的运用。而在众多的古代文论著述中,对“物”范畴的重视莫过于《文心雕龙》。因为此书中使用“物”范畴多达五十九处,出现在二十篇文章中,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二。此外,还出现了一系列相关的范畴如“象”、“形”、“色”等,或准范畴如“貌”、“容”、“状”等,共计一百五十八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还专设《物色》篇,对“物”范畴展开专门探讨,这在古代文论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物”范畴专论。“物”范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有多方面理论内涵,涉及多方面理论。《文心雕龙》中“物”范畴的理论内涵主要有如下诸方面:
一、创作发生论内涵
《文心雕龙》“物”范畴的内涵首先体现在创作发生论中。刘勰认为,“物”是导致创作发生之根源。《原道》篇云:“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言立”之创作活动与“文明”之作品产生以作家“心生”为前提,而作家之“心生”又以“物”为前提。《文心雕龙》中这方面的论述很多,如《明诗》篇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诠赋》篇云:“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物色》篇云:“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物色相召,人谁获安?……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兴,辞以情发。”又云:“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这些论述表明,“辞以情发”的文学创作活动以“情”为关键。那么“情”从何而来?刘勰指出,情源于物,即“睹物兴情”、“情以物兴”。在刘勰看来,“七情”虽是人的天生禀赋,但这种天生禀赋必须依赖于外在之物的作用才能产生,即“应物斯感”。作家若不“应物”,亦无“斯感”。也就是说,若无对外物的感应,作家的“七情”是不会产生的。刘勰此论显然受《乐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的思想影响。刘勰与《乐记》的作者都认为,人有感应外物而产生种种对应感情的本然天性。外物作用于人,人必然要产生对应的感情。刘勰又认为,“应物斯感”和“感物吟志”都“莫非自然”,即作家“应物”而必然“斯感”,有感而必然“吟志”,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必然过程。
“感物”而“兴情”,情兴而辞发,文学创作的基本程序是物→情→文,文生于情,情源于物,外在之“物”是人之思想感情产生的根本所在,文学创作的最终根源只能是外在之“物”。将创作之根源确立在“视听之区”的形形色色的外物之上,体现了唯物主义的创作精神。至此,刘勰所论“物”范畴的意义和价值也体现了出来:“物”是文学创作之最终根源,作家创作必须率先“睹物”、“感物”,而不能面壁玄想,脱离外在之物,静坐书斋、闭门造车是无法产生审美感情的,也无法展开创作。作家创作必须以观物、感物为起点,大千世界才是作家创作的真正摇篮。作家只有走进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才能产生复杂微妙的思想感情,然后才能导致文学创作的发生和精美之文的产生。刘勰的这一观点不但揭示了古代作家的创作规律,而且当代作家创作也同样遵循这一规律,所以《文心雕龙》“物”范畴的创作发生论内涵在当代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二、艺术想象论内涵
文学创作离不开艺术想象,艺术想象离不开客体外物,因为想象之“象”根源于“物”。因而,“物”范畴具有艺术想象论内涵。这一内涵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其一,“物”是构成艺术想象的基本因素。刘勰在《神思》篇中指出:“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思”即艺术想象,是“神与物游”的过程。“神”指作家的主体精神,包括审美感情、理想志向、思想观点等因素;“物”是源于客体世界的“物象”,包括“珠玉之声”、“风云之色”等各种景物、景色、景象,即当代文艺心理学所说的“艺术表象”;“游”即“神”与“物”二因素相互融会贯通的心理运动。“神与物游”也就是主体之“神”与客体之“物”的自由运动。此命题揭示了艺术想象的实质:艺术想象既离不开创作主体的“神”,也离不开来自客体世界的“物”。也就是说,在“神思”想象的过程中,“神”与“物”即主体精神与艺术表象缺一不可,“物”是构成“神思”想象的基本因素之一。
其二,“物”为“神思”的展开提供了运思实体。艺术想象作为艺术思维活动,具有突出的形象化特点,所以,当代人又称艺术想象为“形象思维”,即以“形象”为基本因素和展开方式的思维形式。这种思维形式与以抽象概念为基本因素和展开方式的抽象思维最显著的不同在于,形象思维以具体的形象为基本因素,整个思维过程始终贯穿着具体的形象,作家通过对具体形象的取舍、改造、夸张、连缀、组合等而创造出新的形象,抽象的概念“极少”参与(“极少”而不是“绝无”);抽象思维以抽象的概念为基本因素,具体的形象参与不多(“不多”亦不是“绝无”)。因此,“神思”作为艺术想象,就离不开“形象”的参与。刘勰所说“神与物游”的“物”,实际上就是形象思维活动中的“形象”,或艺术想象中的艺术表象,而不是外在客体世界所存在的实物。《神思》篇说:“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物沿耳目”之“物”,实际上就是作家通过耳目感观所获得并积累在自己大脑皮层上的艺术表象。“沿耳目”进入大脑皮层的“物”,实际上是外物之“象”,当代文艺心理学称之为“艺术表象”,这些艺术表象是作家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观察各种自然景物、生活事件及人物活动而存储于作家的大脑皮层上的,当作家创作时,就会将其调动出来,以供想象构思使用。“神思”作为一种以“形象”为基本元素和展开方式的思维形式,当然离不开“物”,即离不开艺术表象。“物”作为艺术表象实际上构成了“神思”活动的“实体”,作家在“神思”想象时脑际总是充满各种各样的景物、事物、人物、场景、画面等,即刘勰所说的“万涂竞萌”、“卷舒风云之色”。
其三,“物”构成了主体之“神”的本源。“神思”想象以“神”为主,《神思》篇说:“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居于作家胸中的“神”即审美感情,在想象过程中具有主导作用,因为它制约着想象的进程,规定着想象的方向,推动着想象的发展。作家神思始于内在思想感情的冲动,作家胸中有强烈的思想感情,才可能去想象构思。但是,“统其关键”的“神”却来源于“沿耳目”的客体外物。因为作家只有“睹物”,才能“兴情”。若无客体之物,亦无主体之情,并且“情以物迁”,作家之情随“物”之变迁而变迁。就此而言,“神思”想象的最终根源只能是客体之“物”。
三、艺术表现论内涵
所谓“艺术表现”,就是作家将自己的审美情感、思想精神用适当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形诸文字,从而实现“言立而文明”之创作目的。那么,作家的审美感情、思想精神应该怎样表现?表现作家审美感情、思想精神的最佳形式是什么?刘勰对此作出了精彩的回答:“神用象通。”在刘勰看来,“象”是作家表现思想感情的最佳形式,是完成艺术表现的关键因素。“神用象通”是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末的赞文中提出的艺术表现论命题,云:“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神”即作家的内在精神,包括审美情感、理想志向、思想意趣及创作意图等因素,是作家主体精神的总和。“象”是由“物”衍生出来的同类范畴,指作品所描写的各种景物、景色、景象。“通”即疏通、沟通,可引申为表达、表现之义。“神用象通”就是作家借助于各种景物、景色、景象而将自己的审美感情、思想精神表现出来。所以,“神用象通”是一个关于艺术表现的理论命题,其内涵就是要求作家创作时必须借助于“象”来表现“神”,而不可让作家之“神”直截了当地坦露于作品,也就是当代文论家所要求的通过形象来表现作家的意图思想。“神用象通”体现了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因为形象性是文学的基本特征,没有形象性,文学也就失去了它的基本特征。形象性作为文学的基本特征,要求作家在艺术表现时必须通过“象”的创造来表现主体之情感精神。所以,“神用象通”实际上是古今中外作家在艺术表现时所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用“象”来通“神”,借“物”来达意,艺术表现离不开“物”。因而,“物”范畴具有艺术表现论内涵。
艺术表现之所以要“神用象通”,原因主要有四。其一,形象性是文学的基本属性,只有“神用象通”,才能保障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具有形象性。离开对“象”的描写,文学作品只能是“淡乎寡味”[1]24。马克思、恩格斯在批评拉萨尔的剧本《济金根》时曾强调作家创作必须“莎士比亚化”,反对“席勒式”,[2]574就是要求作家创作必须重视形象性描写。其二,“象”具有更好的达意功能。王弼论言意关系时明确指出,“意以象尽”,“尽意莫若象”,[3]773作家的意图意旨只有借助于“象”才能更好地表达出来。其三,从读者接受的角度看,富于形象美的作品才能使读者乐于接受。而文学作品五彩缤纷的形象美,正来自艺术表现的“神用象通”。其四,从作家主体精神的角度看,作家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是一种抽象的存在。这种抽象的观念性、意识性存在,其突出特点在于虚而无形,不可捉摸,如果仅仅以语言文字直接表述作家抽象的思想感情,这样的作品也就成了作家思想感情的直接宣泄,即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批评的“时代精神的单纯传声筒”[2]574。其作品必然是抽象的东西,也必然没有任何美感可言,晋代流行的玄言诗及被马克思、恩格斯所批评的拉萨尔的《济金根》都是此类作品的典型范例。
《文心雕龙》“物”范畴的艺术表现论内涵还体现在赋、比、兴三种表现方法方面。刘勰认为,赋、比、兴三种方法都离不开“物”。《文心雕龙》对“赋”与“物”之关系的论述虽不多,但很重要。《诠赋》篇云:“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此论是说,“赋”作为艺术表现方法,具有铺陈描写的功能,其特点是“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就是说“赋”这种方法离不开“体物”。所谓“体物”,王运熙先生注为“刻画物象”[4]60,“体物写志”,也就是通过“刻画物象”来抒写情志,是“赋”法的根本所在。“赋”之所以要“体物”,是因为作家“睹物兴情”后产生的审美感情和创作冲动,必须通过“体物”才能得到更好的表现,若直言情、志,则味同嚼蜡。钟嵘也有类似解释:“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1]39叶嘉莹女士认为“赋”为“直接叙写”,其特点为“即物即心”。[5]26即通过对“物”的叙写来表达主体之“心”。这样的形象化描写才会使作品富于美感特征。如果说“赋”是以“直言”的方式“体物写志”,那么“比兴”则是借助于“物”的“曲言”。刘勰在《比兴》篇中指出:“故比者,附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蓄愤以斥言……”又云:“何谓为比?盖写物以附意,拟言以切事者也。”“写物以附意”,是“比”的根本所在。其中,“意”是根本,“写物”的目的在于“附意”,“附意”以“写物”为手段,“比”的作用在于通过物的描写而把作家之“意”表现出来。刘勰在《比兴》篇末赞文中又以“拟容取心”来说明“比”这一方法,“拟容”也即“比拟事物的外貌”,[6]209“取心”是取作家之“心”寓于物之“容”中,也即“附意”或“附理”。作家在运用“比”这一方法进行“写物以附意”或“拟容以取心”时,必须“切类以指事”,并且“以至切为贵”,“切类以指事”是“比”这种方法的基本特点,而不是“比”的本质。所谓“切类以指事”,是说喻体和本体要切合、类似、贴切、吻合,并且贴切的程度越高越好。如何才能做到“切类”呢?刘勰又提出“触物圆览”的要求,就是要求作家要善于广泛观察生活中各种客观事物,因为“比”的运用离不开“物”的描写,作家只有“圆览”万物,积累丰富,在运用“比”这一方法“附意”“附理”时,才能得心应手地找到“切类”的喻体。“兴”与“比”有一定的联系,但比“比”更加复杂。《比兴》篇云:“兴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兴则环譬以托讽。”此论是说,“兴”是“起情”,“起情者,依微以拟议”,意思是说微小的事物能寄托深广的意蕴。宋代李仲蒙将其释为“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7]73朱熹说得更直接:“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8]65可见在“兴”这一艺术表现手法中,是先写物,后托意,由物及意,并且所写之物又有“环譬”之特征,即“兴”所写之“物”能构成一定的“譬喻”。所以,“物”是“兴”这种方法不可缺少的内容,无“物”也就谈不上“兴”这种方法。
以上分析表明,“物”范畴涉及古代文论的多方面理论,对古代文论之建构具有举足轻重之作用。而“物”范畴的多方面理论内涵在《文心雕龙》中都有所体现。因此,探索《文心雕龙》的“物”范畴不但有利于推进《文心雕龙》研究的深化,而且有利于推进古代文论研究的深化。
[参考文献]
[1]钟嵘(撰),曹旭(集注).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王弼(注),孔颖达(疏),余培德(点校).周易正义[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
[4]刘勰(著),王运熙、周锋(撰).文心雕龙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5]叶嘉莹.迦陵文集(第1册)[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6]刘勰(著),陆侃如、牟世金(译注).文心雕龙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1981.
[7]胡经之.中国古典文艺学丛编(第1册)[G].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8]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G].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责任编辑张琴】
Connotations of “wu” in The Literary Heart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WU Jian-min, XIA Xin-xiu
(School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JiangsuNormalUniversity,Xuzhou221116,China)
Abstract:“Wu”, a core concept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ism,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history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ism. It is highlighted in “The Literary Heart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in which the concept is interpreted in 20 essay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odern critics, the concept “wu” is related to creation occurrence, artistic imagination and art expression and some other aspects. Therefore the research on it will be serve as a key to understand rich connotation of “wu”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ism.
Key words:The Literary Heart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the concept of “wu”;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ism
[收稿日期]2015-12-25
[作者简介]吴建民(1955-),男,安徽亳州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夏新秀(1994-),女,江苏句容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
[文章编号]1672-2035(2016)03-0052-04[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