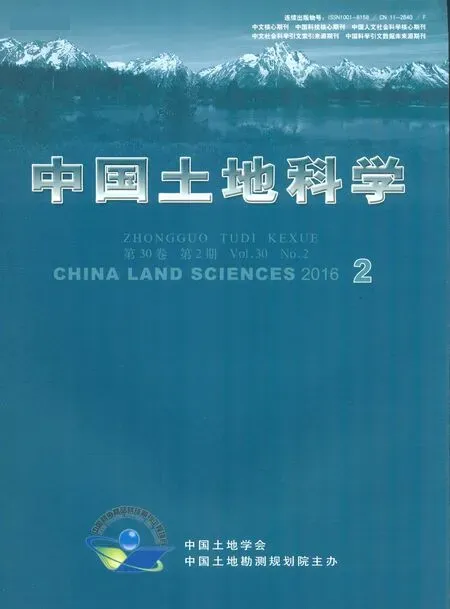中国土地整治转型发展战略导向研究
严金明,夏方舟,马 梅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872)
土地整治
中国土地整治转型发展战略导向研究
严金明,夏方舟,马 梅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872)
研究目的:立足国家战略发展的宏观背景,针对土地整治出现的突出问题,重新认知土地整治的本质和功能,进而探索土地整治转型发展的战略导向。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比较分析。研究结果:土地整治面临着新的转型背景和发展需求,亟需针对当前认知偏于狭仄、定位整体偏低、理念创新不足、协调统筹有限、模式趋于同化、社会参与缺乏等问题,界定其本质为“对人地关系的再调适”,分析其功能为“满足人的‘三生’提升诉求”,并进一步提出促进土地整治实现转型发展的“十大战略导向”。研究结论:土地整治的定位要从“土地本身”到“高位统筹”,理念要从“注重数量”到“四位一体”,阶段要从“粮食生产”到“永续发展”,核心要从“以地为本”到“以人为本”,目标要从“保护耕地”到“优化三生”,对象要从“单项推进”到“要素综合”,范畴要从“项目承载”到“全域协同”,模式要从“同质同化”到“差别整治”,路径要从“自上而下”到“上下结合”,资金要从“财政负担”到“多元共投”。只有如此,土地整治才能应时所需、切实成为新形势下统筹城乡发展、服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目标的有力抓手和重要平台。
土地整治;本质功能;战略导向;转型发展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土地整治不断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调整和完善。从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首次从政策层面要求“积极推进土地整理”,到1999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在法律层面首次明确提出“国家鼓励土地整理”;从200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进一步鼓励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到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大规模实施土地整治;从“十二五”《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1—2015年)》的实施,到“十三五”《全国整治规划(2016—2020年)》的编制,土地整治在范畴、目标、内涵和方式等各个方面都在不断创新和发展[1]。
近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和外需向内需转化期的“四期叠加”阶段,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但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2]。在此形势下,土地整治亟需立足国家战略发展的宏观背景,针对土地整治出现的突出问题,分析土地整治本质和功能的根本认知,进而开展土地整治转型发展战略导向研究。
1 中国土地整治战略转型背景
1.1经济新常态
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支撑中国高速发展的强大外需萎缩疲弱,国内传统人口红利的比较优势逐步减弱,资源环境限制影响不断提升,表明中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中国的GDP增速告别过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从2012年起开始回落,2013年、2014年和2015年增速分别为7.7%、7.3%和6.9%,面临经济增长动力与经济下行压力并存的局面,意味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速度上从高速转为中高速增长,在结构上不断优化产业升级,在动力上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在管理上简政放权、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3-4]。
1.2生态文明新要求
党的十八大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做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决策。当前中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环境污染、水土流失、土壤退化、景观破坏等问题日益突出:全国20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45.4%的地下水污染较严重、16.1%污染极严重,现有土壤侵蚀总面积294.91×104km2,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9.4%[5],中度以上生态脆弱区域占全国陆地国土空间的55%[6],约 60%村庄乡村景观风光一般或差,约80%的村庄街道和田间道路绿化不足、沟路林渠破损严重[7],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构成类型单一、格局混乱、覆被稀松,缺乏特色和空间层次感,人居舒适感下降[8]。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要求进一步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空间均衡”、“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等理念,构建起由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空间规划体系、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环境治理体系、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8项制度构成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进生态文明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1.3新型城镇化建设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2% 剧增到2014年的54.77%,在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下依然实现了平均每年递增1.02%的高速城镇化进程。然而随着城镇化率的迅速提高,农民工人数也在逐年激增,从2008年的2.25亿到2014的2.74亿,占全国总人口的20.03%,去除农民工城镇化率仅为34.74%,伪城镇化问题突出。同时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资源利用方式较为粗放,单位GDP能耗和地耗远高于发达国家,水资源产出率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60%左右,处于低效利用状态的城镇工矿建设用地约5000 km2,占全国城市建成区的11%,土地城镇化速度高于人口城镇化速度。亟需进一步以人为核心,以解决三个1亿人问题为着力点,促进一亿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有序稳妥落户,改造一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一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稳步提升城镇化水平和质量,优化城镇化布局,转向精细化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真正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健康发展[9]。
1.4新农村建设
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新农村,是构建和谐社会、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要求,也是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当前中国农业生产问题随着国内外环境条件变化和长期粗放式经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逐步显现,“十二连增”的背后显露出粮食增产潜力不断下降,由于耕地面积减少、质量偏低等生产条件的限制,再加上农村人口比率的不断减少,粮食需求的刚性增长,中国未来粮食供需平衡压力依然较为突出。同时,中国农地经营规模总体上呈现“小、散、碎”特征,农业组织化、市场化程度偏低,农业科技整体实力不强[10],导致国内粮食生产成本偏高、价格优势消失、生产效益下降,农业积极性下降;同时,当前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如医疗、教育、科技仍然存在极大不足,缺乏整体统一规划、人才供给也相对不足,无法解决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的突出问题,传统乡土文化正日益萎缩和消失,乡土文化在传承中出现断层,农民精神生活匮乏,亟需针对农民和农村的多元诉求,促进水、电、路、暖、气等基础设施和住房人居环境改善,健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关爱农村“三留守”群体、留住乡土文化和建设农村精神文明,推动“物的新农村”和“人的新农村”齐头并进。
1.5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目标
作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要针对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在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科学发展、深化改革、依法治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原则下,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已经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要求的基础上,努力实现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和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等新的目标要求。
2 中国土地整治现状问题分析
2.1土地整治认知偏于狭仄
中国开展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规模土地整治仅仅不到20年时间,对于土地整治本质和功能的基本认知依然不尽准确,多将土地整治认作是实施性的工程、技术或是任务,并未认识到土地整治的本质和功能是对人地关系的再调节,是对低效、空闲和不合理利用的城乡土地进行综合治理,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的各类土地整理、开发、复垦、修复等活动的统称,因而也影响了土地整治整体定位、创新理念、目标模式和实施路径等核心要素的根本认知,导致在整治过程中盲目性、功利性、过度工具化和行为短期化等问题造成的负面影响较为突出[11],影响了土地整治的整体效率和效益。
2.2土地整治定位整体偏低
当前土地整治的定位仍囿于土地本身,多关注“战术层面”而非“战略层面”,未能“跳出土地谈土地,跳出整治谈整治”,多强调土地整治在耕地保护和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而并未认识到土地整治不仅可以作为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关键措施,更是加强政府治理实践、助力推进精准扶贫的重要手段。此外,土地整治工程仅仅就整治谈整治,地位远不及高铁、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工程,未被视作是拉动内需的强大引擎,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目标的坚实保障。因此,土地整治整体定位和功能被相应低估,亟需重新从更高层次上定位土地整治。
2.3土地整治理念创新不足
当前的土地整治仍然将土地整治作为增加耕地和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手段,多针对于“用地不足”问题而非“用地不当”的问题,以“数量”作为核心理念,“重数量、轻质量;重面积、轻效益;重耕地、轻农民”,未能以人为核心,统筹兼顾对被整治土地相关权利人的多元需求,未将土地整治看做是挖掘结构潜力、优化空间布局、提升利用效率,协调促进土地“合理利用”的核心抓手,未能融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十三五”核心发展理念[12],难以体现出土地整治的质量创新性、三生协调性、绿色生态性、开放国际性和人文共享性,距离进入主要以提高生产质量、生活品质和生态环境为主要导向的可持续土地整治新阶段仍然任重道远[1]。
2.4土地整治目标过于单一
在“保发展、保红线”方针的指导下,为了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中国当前土地整治仍以增加耕地为首要任务,多偏重于农用地整治,重点关注耕地的调整、地块的规整和耕地改造等方面的内容,对“水、路、林、村、城”等对象的综合整治相对不足,忽视了对“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的生态保护[13]。事实上,长期以来中国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水平较低,生产、生活和生态的“三生”空间利用无序、布局散乱,生产用地空置闲置、管理失效等问题较为严重,人居生活环境质量偏低、基础设施不尽完善,生态环境污染严重、生物多样性减少,城镇、村落、农田、道路、河流水系、森林等景观要素之间的功能联系遭到破坏,亟需拓展土地整治的核心对象与目标,统筹城乡土地利用结构,改善“三生”空间布局。
2.5土地整治协调统筹有限
目前,土地整治实践主体往往局限于具体部门,整治客体通常依托于固定整治项目,“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全域化、综合化、系统化的前瞻规划和设计,各部门各自为政的问题也较为突出,缺乏国土、农林、水利等部门的配合协调统筹,资金使用分散和投入交叉重复现象比较普遍,导致各个整治项目难以实现彼此时空和功能上的联结衔接。在区域上,与“京津冀”一体化等区域发展战略协调力度相对不足,与“一路一带”等国际发展战略协同开放程度较低,距离全面实现土地整治工程“融进去”、“走出去”的发展目标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2.6土地整治模式趋于同化
在土地整治的过程中,不少地方未能充分尊重自然规律,而追求高品质设计,导致田间的路、沟、渠大量铺筑水泥,农田整治呈现混凝土化;部分历史久远、极具地方特色、蕴含文化遗产性质的自然风貌和建筑民居未能根据其自然禀赋和历史文化,进行分类整治、充分保护,导致乡土文化遭到破坏,自然景观趋向同质化,一些地方原有的青山绿水、民俗民风和生活形态未能得到保留,出现了“千镇一面”、“千村一面”等问题。因此,土地整治亟需针对田、村、镇等被整治区域的独有乡土元素,全面保护地方乡土特色、文化气息和人文特征。
2.7土地整治社会参与缺乏
中国土地整治往往是由政府“自上而下”确立的项目,缺乏民众自发“自下而上”的主动整治,是政府意志的体现而非是农民主体的需求,也因此容易导致整治中公众参与的程度较低,许多整治区域中的农户对整治目的、方向、权属调整方案等都缺乏了解,土地整治权属调整和利益分配的公平性仍显不足,难以体现“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同时就当前而言,中国土地整治项目只有非常少的资金来源于企业或个人,绝大多数来源于政府财政投入,而土地整治作为一项资金占用量大、投资回收期长的项目,从长远来看,只依赖财政有限的资金仍然远远不足,亟需寻找有效完备、可供推广的资金筹集方式。
3 中国土地整治本质和功能的再认知
在新形势下要实现土地整治转型发展,最核心、最基础的任务首先是准确认识土地整治的真正本质和关键功能,进而才能针对现存问题,对土地整治的定位、理念、阶段、核心、目标、对象、范畴、模式、路径和资金等要素进行转型分析,相应提出土地整治转型的关键战略导向。当前关于土地整治的规划、潜力、模式、效益等方面的研究关注较多,然而关于土地整治本质的研究极为匮乏[14],且在实践中多将土地整治看做是一项管理性、强制性、实施性的工程、技术或是任务,将其功能狭隘地看做是增加耕地或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目标仅在于保障粮食生产和土地财政收益,使得土地整治被认为是少数人群获益而非社会整体受益,因而导致群众整治动机不强、满意度较低。实际上,土地整治的本质是“对人地关系的再调适”:是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效益、保障国土资源永续利用、改善生态景观环境为主要目的[15],利用土地整理、土地开发、土地复垦、土地修复等一系列手段,通过“田水路林村城”土地综合整治提升人类生活和生产条件,通过“山水林田湖”国土空间整治保护人类生态空间,最终促进人与自然可持续协调发展的活动。
在人地协调的本质认知下,土地整治的功能也超越了单纯扩大耕地面积、提升耕地质量的意义[15],而更注重满足人们的核心需求。因此,土地整治的功能应是“三满足”:以人的切实需求出发,合理调整国土“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结构和布局,满足人们的生产发展诉求,满足人们的生活提升诉求,满足人们的生态保护诉求。应当指出的是,在不同的土地整治发展阶段,其功能的侧重点也应有所不同。如日本1945—1964年间土地整治主要侧重于生产发展功能,通过农地改革(1946—1949年)、《农地法》(1952年)、《农业基本法》(1961年)等一系列政策手段促进农业发展和粮食增产;1965—1984年,日本则通过《山村振兴法》(1965年)、《新都市计划法》(1968年)和《过疏地域振兴特别措置法》(1980年)侧重于推动土地整治的生活提升功能,整治建设生活环境,满足居住生活需求;1985年至今,日本土地整治则全面侧重于景观生态的永续发展功能,通过《集落地域整备法》(1987年)、《食料·农业·农村基本法》(1999年)和《景观法》(2004年)的出台,充分保护生态环境,推动人与自然协调发展[16]。相较于日本,中国地域更为辽阔、各地自然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也各不相同,因此土地整治也应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区域的不同阶段有的放矢地进行功能选择。
4 中国土地整治转型“十大战略导向”
4.1土地整治的定位要从“土地本身”到“高位统筹”
土地整治应总体定位为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抓手,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平台,实现生态文明的建设路径,提升民生福祉的发展动力,加强政府治理的突破窗口,保障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工具。“十三五”时期,土地整治还可具体定位为拉动内需的强大引擎,落实空间规划“多规合一”的实施单元,助力精准扶贫的重要手段,服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目标的切实保障。
4.2土地整治的理念要从“注重数量”到“四位一体”
土地整治转型理念应融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理念,树立“数量、质量、生态、人文”的四位一体土地整治理念,以理论、制度和科技等创新为土地整治内在动力,以促进城乡协调、区域协调、“三生”协调为土地整治关键目标,以环境污染治理与景观生态质量提升为土地整治核心导向,以改善民生条件、实施精准扶贫和维护乡土文化为土地整治根本核心,以统筹保障“一路一带”等国际国内重大战略的落地实施为土地整治重要任务。
4.3土地整治的核心要从“以地为本”到“以人为本”
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因此,土地整治应以明晰整治土地的产权界定为基础,维护整治涉及利益相关者的根本利益,在思想层面激励公民意识与公民本位的价值认同和主观意愿,在制度层面健全全维度公众参与的具体制度,在技术层面实施信息公开与交流回馈制度[1],在经济层面以提升人民收入水平、改善人民福祉为根本出发点,在社会层面突出体现乡风文明和特色人文情怀,保证整治过程公平、公正、公开,提升整治过程的公众满意度。
4.4土地整治的阶段要从“粮食生产”到“永续发展”
土地整治转型发展要以“永续发展”为发展导向,以生态、景观服务及休闲游憩功能为重点,提升土地整治环境污染治理能力,加强“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的整体修复[17],构建以“山为骨、水为脉、林为表、田为魂、湖为心”的国土生态安全体系,并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加强景观建设,增大农田、林地、绿化等生态用地空间占比[18],改善人居环境、建成都市生态屏障[19],协调资源的永续利用、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安居乐业、幸福美满。因此,通过开展永续发展型土地整治,使大地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生态世界和可持续利用的壮丽美景。
4.5土地整治的目标要从“保护耕地”到“优化三生”
土地整治转型发展要以“三生空间”为承载,兼顾保障粮食供给安全、城市发展安全、生态环境安全,通过在空间划定“耕地保护红线”作为“生产线”、划定“城市发展边界”作为“生活线”、“生态保护红线”作为“生态线”,实现在生产上进一步严格保护耕地,提升耕地质量,适度推进农业规模经营;在生活上进一步优化空间形态与建设用地结构,提升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城乡生活“人物”并进;在生态上要破解城乡生态空间萎缩、污染问题突出与景观破碎化的问题,通过建设绿色基础设施,强化生态化土地整治技术的应用,最终实现整个区域生态、生产和生活的同步重构。
4.6土地整治的对象要从“单项推进”到“要素综合”
土地整治的对象不应禁锢于单个耕地、集体建设用地等单个要素,要实现“山、水、田、路、林、村、城”7要素综合整治,即在整治区域中综合国土、农委、林业、水利、环保等各个部门合力,同步推进山体、水体、农田、道路、森林和城乡居民点、工矿用地等多种类型的整治,实现生产集约、生活提质、生态改善的“三生”目标。
4.7土地整治的范畴要从“项目承载”到“全域协同”
土地整治转型发展要转变以具体单个项目为整治范畴的固化思维,转向全域规划、全域设计和全域整治。根据地区间的区域差异、相互关联,围绕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促进区域间合理的分工与协作等目标,统筹各区域的土地利用发展,防止重复建设、产业结构趋同,促进区域经济、产业、人口发展与土地利用相协调。在更宏观层面上,通过树立国际化发展视野,土地整治通过分区域、分类别差别化重点整治,致力于保障“一路一带”、“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促进土地资源在都市圈、城市群和一体化区域的结构优化和空间协同化布局。
4.8土地整治的模式要从“同质同化”到“差别整治”
土地整治的模式设计要摆脱千篇一律、城乡雷同的同质化趋势,必须要转向差别化保护城乡景观特色和传承乡土文明。数千年的农耕文明使得中国的乡土文化源远流长,很大意义上代表了中华民族得以繁衍发展的精神寄托和智慧结晶,然而相对弱势的乡土文明在高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浪潮中极易被摧毁和遗忘。因此,土地整治中应高度重视保护历史沿革、民俗风情、古建遗存、村规民约、家族族谱、传统技艺、古树名木等诸多方面的乡土文化,大力鼓励土地整治以保护乡土文明为前提,创新性构建独特模式,构建具有地域特征的自然风貌、建筑民居和传统文化,留住以土地为载体的“乡愁”[20]。
4.9土地整治的路径要从“自上而下”到“上下结合”
土地整治的实施路径要从当前政府主导、指标分解的“自上而下”模式向群众自愿、政府引导的“上下结合”模式转变。在土地整治中应充分考虑被整治对象主客观状况的匹配程度,以市场需求为现实基础,以群众意愿为内在动力,以政府政策为外部引力[21],融合政府推动、市场配置与群众构想,实现“上下结合”综合治理路径,充分保障被整治对象主体地位、实施动力与权益权利,促进土地整治实施绩效最优化。
4.10土地整治的资金要从“财政负担”到“多元共投”
目前主要由政府财政作为土地整治资金的主要来源显然不可持续,在新时期土地整治应探索由政府、企业、个人等多元主体形成的外包式、股份式、私营式等不同结构的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资金支撑模式。在此模式下,政府和私人部门(企业或个人)可以依据项目特征、资金现状和发展预期设计融资方案,可以由政府全额出资企业承包部分工程(外包式),也可以制定各方资金比例和分配预期收益(股份式),或者由私人部门全额负责(私营式),从多种渠道满足土地整治资金诉求,从而多元共投,保障整治工作持续有序的推进。
5 结论与建议
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的重大变化、中国不断发展的经济社会转型需求和逐步深入的全面改革预期将为土地整治带来更多的机遇和挑战,亟需土地整治未雨绸缪、与时俱进地进行积极的转型发展探索。本文通过总结土地整治新形势下的转型背景,分析了土地整治当前的突出问题和发展需要,探究了土地整治本质和功能的根本认知,提出了土地整治在“四期叠加”时期要实现转型“十大战略导向”,如此才能应时所需、切实成为新形势下统筹城乡发展、服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目标实现的有力抓手和重要平台。
当然,土地整治转型发展战略也离不开强有力的实施保障,一是要对应土地整治的转型定位,进一步促进土地整治的法律地位提升,加紧提出《土地整治法》的立法建议,从根本上提升土地整治的权威性;二是要完善土地整治规划体系和引领效能,进一步强化转型发展导向下的规划定位、目标及任务,有效统筹资源、服务国家内外大战略的顺利开展;三是要强化提升土地整治转型发展的科技支撑,编制详细又具备地方弹性的新型整治技术标准和规程,提高土地整治功能化、模型化、信息化水平;四是要全面提升土地整治转型服务意识,界定明晰政府与私人部门的权责利,运用分层次、分区域、分类型、分单元等多种模式,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引导推进土地整治工作顺利转型发展。
(References):
[1] 严金明,夏方舟,李强.中国土地综合整治战略顶层设计[J] .农业工程学报,2012,28(14):1 - 9.
[2] 余斌. 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宏观调控政策取向[J] . 改革,2014,(11):17 - 25.
[3] 新华社.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N] .人民日报,2014 - 05 - 12(A01).
[4] 新华社.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N] .人民日报,2014 - 07 - 30(A01).
[5] 环境保护部. 2014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R] .北京:环境保护部,2015.
[6]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通知[EB/OL] . http://www.gov.cn/zwgk/2011-06/08/content_1879180.htm,2015 - 12 - 30.
[7] 郧文聚,宇振荣.中国农村土地整治生态景观建设策略[J] .农业工程学报,2011,27(4):1 - 6.
[8] 刘黎明,杨琳,李振鹏.中国乡村城市化过程中的景观生态学问题与对策研究[J] .生态经济,2006,15(1):202 - 206.
[9] 严金明,刘杰. 关于土地利用规划本质、功能和战略导向的思考[J] .中国土地科学,2012,26(2):4 - 9.
[10] 陈锡文.中国农业发展形势及面临的挑战[J] .农业经济,2015,(1):3 - 7.
[11] 信桂新,杨朝现,魏朝富,等. 人地协调的土地整治模式与实践[J] . 农业工程学报,2015,31(19):262 - 275.
[12] 新华社.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EB/OL] .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1/03/c_1117027676.htm,2015 - 11 - 03/2015 - 11 - 22.
[13] 龙花楼.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空间重构[J] .地理学报,2013,68(8):1019 - 1028.
[14] 吴次芳,费罗成,叶艳妹.土地整治发展的理论视野、理性范式和战略路径[J] .经济地理,2011,31(10):1718 - 1722.
[15] 冯广京.我国农地整理模式初步研究[J] .中国土地,1997,(6):13 - 20.
[16] Sorensen, Andre. Conflict, consensus or consent: implications of Japanese land readjustment practic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J] .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00, 24(1): 51 - 73.
[17] Forman, Richard T. T. Land Mosaic: the Ecology of Landscape and Regions[M]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8] 陈百明,谷晓冲,张正峰,等.土地生态化整治与景观设计[J] .中国土地科学,2011,25(6):10 - 14.
[19] Yan J., Xia F., Bao H. Strategic planning framework for land consolidation in China: A top-level design based on SWOT analysis [J] .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5, (48): 46 - 54.
[20] Taylor, J. The China dream is an urban dream: Assessing the CPC’s National New-Type Urbanization Plan[J] .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2015, 20(2): 107 - 120.
[21] 夏方舟,严金明,刘建生.农村居民点重构治理路径模式的研究[J] . 农业工程学报,2014,30(3):215 - 222.
(本文责编:陈美景)
Strategy Orientations of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Land Consolidation in the New Period of China
YAN Jin-ming, XIA Fang-zhou, MA Mei
(Department of Land Management,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Polic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identify the emerging issues and transformation requirements of land consolidation, to redefine its essence and functions, and then to figure out the strategic orientations of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macroscopic background of national strategy development.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are appl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currently, land consolidation is in a new period with transformation requirements. Against the new definition of its essence as “readjustment of human-earth interrelation” and functions as “satisfaction of individuals’improvement requirements in production, life and ecology”, ten strategic orientations are put forward in allusion to current problems such as cramped cognitive, low positioning, homogeneous pattern, and lack of innovative concepts, coordination as well as public participation. The conclusion is that land consolidation shouldbe changed from land-only to high-level integration in its position, from quantity-priority to quaternity in its concept,from grain production to landscape protection in its orientation, from land-oriented to people-oriented in its core, from protecting farmland to optimizing production, life and ecology in its target, from single implement to feature generalization in its object, from project-carrying to domain-coordinationin its scale, from homogeneity to differentiation in its pattern,from top-down to up-down in its path, from fiscal burden to multiple modelin its fund.With this ten strategy orientations,land consolidation can be regarded as the powerful gripper and important platform to balance urban-rural development and contribute to the new goal of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land consolidation; essence and functions; strategy orientations;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F301.2
A
1001-8158(2016)02-0003-08
10.11994/zgtdkx.20160129.145443
2015-12-20;
2016-01-18;修稿日期:2016-01-29
国土资源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课题(201511003-2);国土资源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课题(201511010-04);中央在京高校重大成果转化项目。
严金明(1965-),男,江苏南通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利用管理与城乡规划。E-mail: yanjinming@ruc.edu.cn
马梅(1981-),女,江苏徐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规划与利用。E-mail: meim@mail.mlr.gov.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