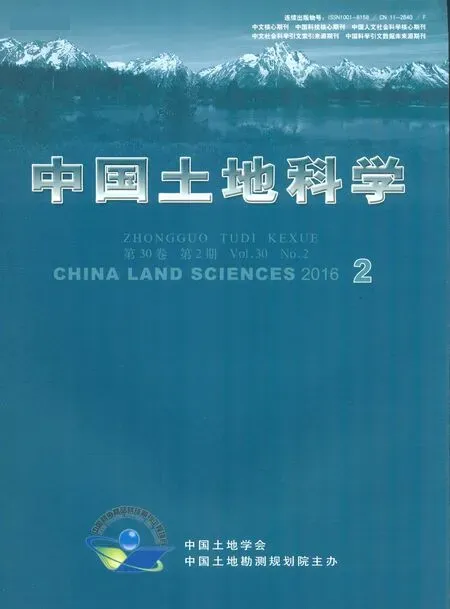县域批而未用土地的监测研究
裘双双,岳文泽
(浙江大学土地管理系,浙江 杭州 310029)
县域批而未用土地的监测研究
裘双双,岳文泽
(浙江大学土地管理系,浙江 杭州 310029)
研究目的:为研究如何从土地管理的时间维度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提供一个新的视角。研究方法:目视解译法、GIS空间分析、景观格局指数。研究结果:(1)研究区县域2006—2012年新增建设用地中共产生259宗批而未用土地,面积为515.47 hm2;(2)批而未用土地数目随时间变化波动增长,呈现集聚性、趋向性的空间分布特征;(3)市场不确定性、政策与规划调整以及土地管理脱节是产生批而未用土地的主要原因。研究结论:利用高分辨率影像目视监测批而未用土地的方法简单,对提高建设用地利用的时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土地管理;批而未用土地;监测;目视解译
1 前言
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均耕地少、耕地质量总体不高、耕地后备资源不足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建设用地供需矛盾仍很突出,耕保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仍须坚守[1]。面对如此严峻的土地资源基本国情,土地粗放浪费的现象却仍十分严重。根据2015年7月国家审计署的审计结果,22个省及2个中央部门存在资金沉淀和土地闲置问题,涉及资金564.47×108元、闲置土地3.6×104hm2,一些地方由于土地规划调整、融资等原因,闲置土地盘活较慢,有些政策实施和简政放权不到位,部分重点建设项目推进缓慢①http://news.xinhuanet.com/house/hz/2015-08-31/c_1116418288.htm。。土地闲置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而且会影响土地和房地产市场的正常运行和发展[2]。
中国在节约集约用地及闲置土地处置方面已出台众多政策,例如,2008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2012及2014年国土资源部分别颁布《闲置土地处置办法》与《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规定》。在土地管理实践中,各地政府以地均GDP、万元二三产业增加值用地量等绩效指标评价土地的投入产出效率,通过规定建筑密度或容积率提高土地利用的空间效率。科学研究则主要关注以下4个方面:一是评价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3-4],构建适用于各类用地的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将环境等指标列入评价[5]等;二是研究如何将节约集约用地理念融入土地利用规划[6-7];三是制度绩效评价及创新[8];四是探索该工作开展的方法、模式及经验[9-10]。然而,无论是管理实践还是科学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土地利用的时间效率。一宗土地经过审批、征收到供应进入市场需要较长时间,无论哪一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土地利用的时间效率,最终导致闲置土地的形成。
国内外针对闲置土地的研究较多,主要从其内涵、类型、成因、解决措施及监管手段等方面展开。现行法规对闲置土地的多项规定已难以适应实际需要[11],土地利用是否有产出或使用价值是否得到体现更应被关注[12-14]。王宏新[12]、叶晓敏[2]等讨论了闲置土地形成的内在机理,包括经济区位与区域非均衡、社会集聚、市场冲击与市场波动规律、政策干预与制度空隙、城市建设惯性与社会阻尼等机理。其现实成因可分为企业、政府和不可预计因素,企业因素包括开发商囤地、资金不足等,政府因素包括征地遇阻、为增值收益储备土地、规划调整等[2,12,14-16]。此外,已有研究发现公共政策对闲置土地的数量具有显著影响[17],闲置土地与城市边界扩展、人口变化、地方经济增长呈正相关[18]。监管技术上的国内进展包括:一是建设用地批后监管系统设计,结合3S、数据库建设技术、SOA理论等实现土地利用动态监管[19-22]以及用地异常信息的分级预警[23],主要服务于实际土地利用管理;二是闲置土地判别,采用计算机解译方法,利用光谱、植被指数、纹理、梯度、方差等特征识别新增建设用地中已建设的土地[24-25],间接判别出闲置土地。国外学者开始利用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目视判别,如采用遥感影像、航空影像、谷歌街景等识别人造地物、确定地块覆被情况及实际用途[26-28];提出多人多重高精度的照片解译法,在无需高超解译技巧的情况下仍可减少误差[29]。由此可见,先进的监测技术及高分辨率影像将使闲置土地的判别更便捷和精确。
本文研究的批而未用土地是闲置土地的一种类型,但专门针对批而未用土地的研究较少。根据《闲置土地处置办法》以及已有研究[13],一宗土地从批到用,存在一个正常利用周期,通常认为该周期的合理跨度为两年。因此,文中的批而未用土地指经批准两年后仍未利用的土地,包括批而未征、征而未供、供而未用土地。由于缺乏地块实地调查,其中的“用”仅指土地利用的初级集约[30]情况,即是否被平整硬化、是否存在建筑物,同时考虑从批到用的时间跨度,但不包括对地块次级集约[30]情况即实际利用效率(如投入产出比)的判断。
以中国经济发达的浙江省A县为例,借鉴国外闲置土地识别技术,运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结合已有地块的空间位置信息,使用目视判读方法,解译出批而未用、批而已用及其中的用而未尽等类型。在此基础上,分析批而未用土地的时空变化特征,进一步分析其形成原因,为从时间维度提高土地利用管理效率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2 数据与研究方法
2.1研究区概况
A县位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下辖4个街道、11个镇和3个乡。根据2013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该县土地总面积为183650.52 hm2,其中建设用地占8.83%。近年来,虽然该县建设用地投资效益有显著增加,但城乡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仍有待提高。
2.2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研究对2006—2012年间A县新增建设用地的批而未用情况进行目视解译。A县新增建设用地数据来源于期间农用地转用为建设用地(包括未利用地转用为建设用地)的矢量数据,新增建设用地通过审批的时间由项目批准文件确定。考虑两年的正常利用周期,研究采用2014年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分辨率为0.5 m),借助目视判读,解译新增建设用地的利用情况。此外,借助行政区划图、乡镇政府分布图、交通线路图等矢量数据和相关资料进行辅助分析。通过投影变换、数据转换、空间校正等操作,将遥感影像、新增建设用地矢量图斑统一至高斯-克吕格投影、1980西安坐标系及1985国家高程坐标系,并在ArcGIS 9.3中将两者叠置,如图1所示,白线即为新增建设用地矢量图斑。

图1 目视判读解译标准Fig.1 Visual interpretation standard
按照以地块覆被情况为主、同时考虑正常利用周期的解译标准,目视解译出新增建设用地在2014年的利用情况,具体解译标准如下:
(1)完全利用。首先,白线范围内2/3以上是建筑物或不透水路面的解译为完全利用,如图1(a),图左地块已被完全利用为学校;其次,地块位于偏远山区,规划用途为工矿仓储,白线范围内2/3以上无绿色植被覆盖,有采石采矿痕迹的也解译为完全利用,如图1(a),图右地块几乎无绿色植被覆盖,以裸露的地表及开采过的痕迹为主。
(2)完全未利用。白线范围内2/3以上由绿色植被覆盖的解译为完全未利用,如图1(b),地块内大部分为耕地,左上角小部分为林地,无建设痕迹。
(3)用而未尽。白线范围内大于1/3(根据城市建设各项用地对绿地率的规定确定)且小于2/3被植被覆盖或裸露、其余部分为建筑物或不透水路面的仍判定为利用,但认为是用而未尽,如图1(c),地块内约1/2是建筑物,仍有1/2被植被覆盖。
(4)周期内已利用与周期外未利用。白线范围内2/3以上无绿色植被覆盖,没有或仅有少量建筑物但有动工痕迹的地块可能处于动工开发阶段,考虑正常利用周期,开发时间过长的地块仍被认定为未利用。因此,将2011、2012年出现该情况的地块解译为周期内已利用,而将2011年以前的解译为周期外未利用。如图1(d),图左为2012年的地块,几乎无绿色植被,大部分由黄土覆盖,处于动工开发阶段,判断为周期内已利用,图右为2006年的地块,植被覆盖面积小于1/3,有动工痕迹,判断为周期外未利用。
因此,将批而未用土地分为完全未利用和周期外未利用,将批而已用土地分为完全利用、用而未尽和周期内已利用。
最后,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主要包括叠置分析、缓冲区分析等)对2006—2012年A县的批而未用土地进行时空特征分析;在空间特征分析中,利用Fragstats 3.3软件计算每年度批而未用土地的景观格局指数(斑块密度PD、散布与并列指数IJI)作为辅助,指数的空间分布意义和公式见表1。

表1 斑块类型指数及其生态学意义Tab.1 Patch class indices and their ecological meanings
3 结果与讨论
3.1批而未用土地的总体情况
2006—2012年该县共有1123宗新增建设用地,总面积为1759.47 hm2,其中864宗为批而已用土地,面积为1244.00 hm2;剩余259宗批而未用土地,面积为515.47 hm2。批而未用土地的数目和面积分别占新增建设用地的23.06%和29.30%,因此以2014年为判断时点,7年间A县约有1/4的新增建设用地存在闲置现象。批而未用土地中包括239宗完全未利用土地和20宗周期外未利用土地,面积分别占批而未用土地总面积的88.34%和11.66%;批而已用土地包括774宗完全利用土地、50宗用而未尽土地以及40宗周期内已利用土地,面积分别占批而已用土地总面积的82.33%、8.77%和8.90%。3.2批而未用土地的时间变化特征

表2 新增建设用地的利用情况统计表Tab.2 The utilization condition of incremental construction land
首先,总体上数量呈增加趋势。批而未用土地从2006年的3宗增长到2012年的82宗,平均每年存在37宗。2012年达到最大值,占总数的31.66%,且占该年新增建设用地的42.05%,也就是说,经过两年的正常利用周期,仍有将近一半的土地无法被及时利用,可见土地利用时间效率低下。由于周期外未利用土地仅指2011年以前审批至2014年仍处于动工开发阶段的土地,因此,2011和2012年不存在该类土地,其数目虽然较少,但总体上仍有所增加。而占将近90%的完全未利用土地,几乎代表了批而未用土地,其与总数一样呈增加趋势。

表3 批而未用土地年度变化情况(2006—2012年)Tab.3 The annual variation of approved but unused land from 2006 to 2012
其次,数量波动增长。如图2,2006—2008年期间,批而未用土地数目持续增加,其中2006—2007年出现迅猛增长,随后开始上下波动。2009和2011年是批而未用土地出现的低谷,而在2008、2010和2012年分别达到三个高峰,其中2012年的增幅最大,增长率达110%。批而未用土地数目随时间变化波动上升的趋势非常明显。从两类批而未用土地来看,完全未利用土地和总数的波动趋势几乎完全一致,而周期外未利用土地无论在数目还是在面积上,波动都更为剧烈,其中2007和2010年的面积要远远大于其余三个年份,是因为其中分别包含一宗面积大于20 hm2的港口码头用地和城镇用地。新增建设用地数目变化与批而未用土地相类似,需提及的是,它在2011年产生了爆炸式的增长,数目达381宗,其中223宗是作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移动基站,在全县范围内铺开,若排除该类用地的影响,新增建设用地数目的增长则较为平稳。

图2 批而未用土地波动趋势Fig.2 The fluctuation tendency of approved but unused land
再次,近期产生的批而未用土地较早期而言,更易被及时利用。利用2013年遥感影像目视解译2006—2011年间新增建设用地的利用情况,发现以2013年为判断时点,A县共有201宗批而未用土地,数目随时间变化波动增长。与2014年遥感影像目视解译结果对比后可知,2013—2014年共利用批而未用土地24宗,利用率为11.94%。经过一年的利用,2006—2011年每年的批而未用土地数目都有所减少,利用的数目从2006年的1宗逐渐增加至2011年的8宗,除去2006年,其余年份的利用率均在10%左右波动,且逐渐增长,2011年达到最大值17.02%。可见,近期的批而未用土地较早期而言,更易被及时利用。此外,经过两年的正常利用周期,2011、2012年分别产生47、82宗批而未用土地,占这两年新增建设用地数目的29.75%、42.05%(已剔除223宗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土地闲置情况加剧。

表4 2013—2014年期间批而未用土地的利用情况Tab.4 The utilization condition of approved but unused land from 2013 to 2014
3.3批而未用土地的空间变化特征
3.3.1空间集聚性 批而未用土地在县域内的空间分布情况如图3,主要集聚于A县的中部和北部地区,在各乡镇中分布不均,差异较大,分布最多的街道有40宗,而最少的乡镇则一宗也没有,标准差为12.21,离散程度较大。
该空间集聚性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中心城区范围内的大面积集聚,如图3中心的集聚圈所示,中心城区包括4个街道和一个镇,批而未用土地主要分布于街道、乡镇中心及其交界处;二是乡镇邻接处的集聚,如图3左下角的集聚圈所示,批而未用土地从一个乡镇跨行政界线蔓延至另一个,分布较为紧密;三是乡镇内部的小范围集聚,如图3上部和右下角的5个集聚圈所示。

图3 批而未用土地的空间分布特征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feature of approved but unused land
将批而未用土地的空间集聚性特征与该县的发展规划和产业布局相比较后发现,发展规划和产业布局所确定的重点发展区域与批而未用土地分布的空间区域具有高度一致性。“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重点发展的中部和北部同时集聚着较多的批而未用土地,工业和服务业的布局也恰与三种空间集聚类型及乡镇差异情况相吻合。中心城区范围内的集聚圈是A县科技园区所在区域,包括文具、汽车零部件及新型建材与家居等产业园;乡镇邻接处的集聚圈位于服务业空间布局中由两乡镇组成的一个节点;其余内部发生集聚的乡镇,均以开发区及产业园建设、工业及服务业发展为主,或是存在产业园,或是服务业空间布局的中心或节点,其中两个分别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乡镇在7年中将近有一半的新增建设用地被闲置。
此外,该空间集聚性还表现出时间差异特征。2006—2008年间,虽然批而未用土地数目逐渐增加,但每年分布都较为分散,在各乡镇、街道中均有分布;2009年数目虽略有减少,但却开始在中心城区范围内集聚;2010年,批而未用土地明显集聚于中心城区及北部乡镇,其中约1/3位于北部循环经济开发区;2011年集聚程度下降;2012年集聚程度回升,主要体现在中部及北部地区,其中约1/3用作温泉项目的批而未用土地集聚于一个西北部乡镇。散布与并列指数(IJI)较好地揭示了每年批而未用土地集聚与分离的特征,批而未用土地年度集聚区域与总体空间集聚情况相一致(图4)。随着“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的深入实施,中心城区的建设逐步加快,2010年集中供应了循环经济开发区及铁路工程所需土地,2012年集中供应了温泉项目所需土地,这种在某一年集中发展重点区域的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批而未用土地空间集聚的时间差异特征。

图4 景观格局指数变化图Fig.4 The variation of landscape pattern indices
3.3.2空间趋向性 批而未用土地的空间分布趋向于交通干线和乡镇中心。采用缓冲区分析法,对A县主要交通干线及各乡镇中心周围批而未用土地的分布情况进行分析。以2 km为间隔半径做多重缓冲区,批而未用土地分别分布于距交通干线10 km及距各乡镇中心8 km范围内,且距交通干线及乡镇中心越近,分布越密集。近70%的批而未用土地落在主要交通干线周围2 km范围内,近80%落在4 km范围内;虽然仅有约40%落在各乡镇中心2 km范围内,但各乡镇中心4 km范围内却包含了近90%的批而未用土地。
批而未用土地对不同类型交通干线的空间趋向性不同,相较于铁路,其更趋向于省道。A县的主要交通干线包括铁路、省道、国道及高速公路,其中主要为铁路和省道。对两者分别进行缓冲区分析,结果发现在铁路周围2 km及4 km范围内各有71宗和104宗批而未用土地,在省道周围2 km及4 km范围内各有134宗和176宗批而未用土地,因此批而未用土地在省道周围分布更多且更密集,这与省道在A县内分布更为广泛和完善有关。此外,该空间趋向性也具有乡镇差异,不同乡镇中心周围批而未用土地的集聚程度不同,根据统计结果,批而未用土地更趋向于行政地位较高、经济较发达的乡镇中心,例如中心城区的几个街道、北部较为发达的乡镇等,而在乡和以第一产业为主的镇等行政级别较低、经济较落后的乡镇中心周围则分布较少。
3.4批而未用土地的形成原因分析
宏观经济波动影响市场稳定,导致土地因供需失衡而闲置。宏观经济波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等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变,会改变区域市场需求,导致早期土地供应与现状市场需求不匹配,最终影响批而未用土地的产生。A县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对外贸易频繁,受到外资和政策的影响很大,因此经济波动剧烈,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2007年的12.8%降至2008年的-4.0%,而在2009年又增长至15.2%,出口总额于2009年下降9.8%,随即于2010年增长了45.2%。在经济波动中,土地和房地产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强,土地供应调整机制的不健全导致部分土地闲置的不可避免。
政策与规划调整是导致土地无法被及时供应或利用的另一个原因。首先,政府换届导致发展思路发生转变,而由于过去发展思路下的土地供应已成定局,区域开发重点的转移会最终导致土地闲置。其次,由于规划调整而形成闲置。地方政府常以发展经济和公益事业为名对既定规划方案进行调整修改[14],特别是一些基础设施规划项目,如路网调整[31]等,这使得根据原方案供应的部分土地无法被及时利用;当规划调整引起土地用途、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等变更时,建设项目需改变原设计方案,重新依据新用途和指标进行规划设计或直接转让土地[14],这就拉长了土地开发利用周期。第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规划未良好衔接[32],也会导致批而未用现象的出现。
土地管理脱节是导致批而未用土地形成的重要原因。第一,审批环节效率低下。审批程序复杂、材料繁多,需经审查、勘测、提交方案、会审等多个环节,最终还要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一宗土地最快也要一个月才能顺利通过审批,因而拉长了利用周期。第二,征地环节遭遇阻力。征地制度设计缺陷导致征地周期具有不确定性,常由于标准不统一等问题[14],导致“钉子户”频现。第三,供应环节也存在问题。由于以地生财的思维存在,地方政府会将一些开发条件不成熟的土地出让,导致开发商无法及时利用;另外,在土地收益驱动下,地方政府还存在拖延供地进度、变相闲置土地的行为。第四,利用环节监督不足、处置不力。由于供地后的反馈机制和监督系统并未建立起来,开发商囤积土地、待价而建的行为没能得到有效查处。据调查,A县批而未用土地中10%因工期拖延而闲置,批而已用土地中近9%用而未尽,且上述两类现象中工业用地居多,可见对工业用地的监管更是薄弱。
4 结论
本文利用2014年浙江省A县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目视解译出2006—2012年新增建设用地中的批而未用土地,并进行时空特征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成因。得出以下结论:
(1)以2014年为判断时点,考虑两年的正常利用周期,A县共有259宗批而未用土地,面积为515.47 hm2,根据不同解译标准,将其分为完全未利用和周期外未利用土地,分别占批而未用土地总量的92%和8%。此外,在864宗批而已用土地中存在50宗土地用而未尽。
(2)批而未用土地数目随时间变化波动增长,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空间集聚性及空间趋向性。空间集聚性包括中心城区范围内的大面积集聚、乡镇邻接处的集聚以及乡镇内部的小范围集聚这三种类型,并存在时间差异;空间趋向性指趋向于交通干线和乡镇中心,且更趋向于省道并具有乡镇差异。
(3)市场的不确定性、政策与规划的调整以及土地管理脱节均会影响批而未用土地的产生。相对于已有研究,本文的意义在于:提出了一种简单、高效的批而未用土地监测方法,即利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和已批土地的矢量数据,目视判读地块利用情况,并强调对监测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References):
[1] 张晏,周怀龙,程秀娟.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成果公布我国土地资源基本国情没有改变耕保红线粮食安全底线仍须坚守[J] .国土资源通讯,2014,(1):8.
[2] 叶晓敏.城市闲置土地的分布特征与形成机理研究[D] .杭州:浙江大学,2009.
[3] 林坚,张沛,刘诗毅.论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的技术体系与思路[J] .中国土地科学,2009,(4):4 - 10.
[4] 林胜.福清市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研究[D] .福州:福建农林大学,2010.
[5] 韩宇笛.基于GIS的长春市区域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状况评价研究[D] .吉林:吉林大学,2014.
[6] 李汉敏.基于节约集约用地理念的土地利用规划研究——以河南省商丘市为例[D] .开封:河南大学,2008.
[7] 陈常优,毋晓蕾,李汉敏.基于节约集约用地理念的土地利用规划研究[J]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09,(4):36 - 38,48.
[8] 冯应斌.重庆市节约集约用地制度创新研究[D] .重庆:西南大学,2009.
[9] 陈世权.浅析如何搞好节约集约用地工作[J] .中国西部科技,2011,(22):58 - 59.
[10] 何传新.城镇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路径选择——以泰安市为例[J]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10,(3):37 - 40,56.
[11] 赵小风,黄贤金,马文君,等.闲置土地的认定思路及处置建议[J] .中国土地科学,2011,(9):3 - 7.
[12] 王宏新,周拯.城市闲置土地的生成机理及治理[J] .城市问题,2012,(9):78 - 82.
[13] 陈璟.批而未用土地的治理对策研究——以福建省2009年批而未用土地专项清理工作为例[J] .海峡科学,2011,(12):13 - 15.
[14] 罗遥.江苏省城市闲置土地成因与处置研究[D] .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12.
[15] 李彤彤.昆明市闲置土地成因研究[D] .昆明:云南财经大学,2011.
[16] 郭秉晟.土地闲置问题及其解决对策[D] .苏州:苏州大学,2014.
[17] 蒋文娟,王继尧,阴江涛,等.征供一体化土地批后监管系统研建[J] .地理空间信息,2010,(3):96 - 99.
[18] 李茜.基于GIS的省级建设用地批后监管系统研究[J] .测绘通报,2013,(6):94 - 97.
[19] 耿衬.基于“一张图”的土地资源综合监管平台的设计与实现[D] .南昌: 江西理工大学,2013.
[20] 熊小超.建设用地动态监管系统研究与实现[D] .武汉: 华中农业大学,2012.
[21] 陆萃.城镇建设用地批后监管的利益博弈与对策[D] .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13.
[22] 张茜,刘顺喜,陈戈,等.面向新增建设用地发现的地块特征构建[J] .国土资源遥感,2013,(4):98 - 103.
[23] 杨冀红,郭蕾,孙家波,等.利用SPOT-6影像提取新增建设用地的方法研究[J] .地理信息世界,2014,(4):54 - 58.
[24] 郑新奇.集约用地的两个水平和五个阶段——节约集约用地基本理论问题探讨之三[J]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14,(7):4 - 6.
[25] 王伟.基于两型社会建设的长沙市闲置土地利用研究[D] .长沙:湖南农业大学,2010.
[26] 龙开胜,秦洁,陈利根.开发区闲置土地成因及其治理路径——以北方A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例[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1):126 - 131.
(本文责编:郎海鸥)
The Monitoring of Approved but Unused Land at County Level
QIU Shuang-shuang,YUE Wen-ze
(Department of Land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9, China)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improving land use efficiency from the time dimension of land management, by means of analyzing spatial-temporal patterns of approved but unused land and its causes. Methods employed were visual interpretation and GIS spatial analysis and landscape pattern indic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regarding 2014 as the judge point and considering two years’ normal use cycle, 259 parcels of approved but unused land are visually interpreted from the incremental construction land during 2006 to 2012. They cover 515.47 hectares and include two types of completely unused land and unused land beyond cycle; 2)the number of approved but unused land increases unsteadily over time,and it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clustering and tendency; 3)unstable market, adjustment in policy and planning, disjointed land management are all main reasons for such spatial-temporal pattern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method of interpreting approved but unused land visually by means of high resolution images is simple and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spatial-temporal efficiency of construction land utilization.
land management; approved but unused land; monitoring; visual interpretation
F301.2
A
1001-8158(2016)02-0031-10
10.11994/zgtdkx.20160307.152515
2015-09-12;
2015-10-1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4AZD124);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13YJA63012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裘双双(1992-),女,浙江奉化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利用管理。E-mail: ssqiu@zju.edu.cn
岳文泽(1977-),男,安徽凤台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利用变化与大数据应用。E-mail: wzyue@zj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