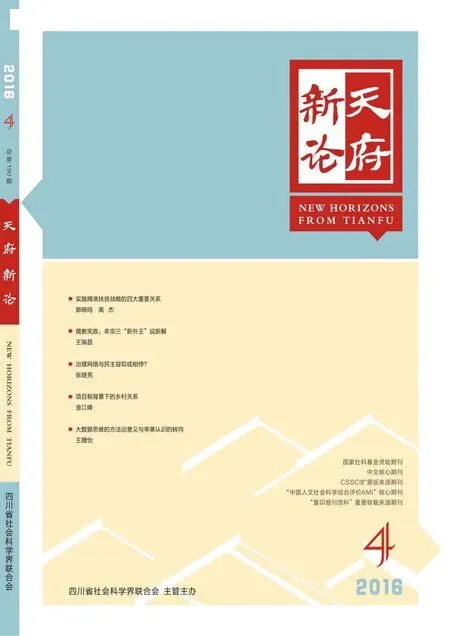儒教宪政:牟宗三“新外王”说新解
王瑞昌
儒教宪政:牟宗三“新外王”说新解
王瑞昌
摘要:论者一直普遍认为,牟宗三在其“新外王”说中的政治主张是“民主”。本文在广泛而深入地研究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新外王”说提出了新的解读:牟宗三真正的政治主张实际上是“儒教宪政”。“民主”与“宪政”有原则性区别,牟宗三本人和许多旁观者所意谓的“民主”,如果细加推究,实际上主要是“宪政”。而且他推扬宗教之价值,并主张儒教为一“宗教”,且认为应当立之为国教以指导政治。与西方自由主义者之政治主张不同,其“新外王”说实际上是某种“政教合一”说。
关键词:牟宗三 新外王 民主 宪政 儒教
近十数年来,在大陆儒学界,“儒教 (儒家)宪政”日渐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议题。“儒教宪政”之具体内容和形式,难免言人人殊。本文认为,一番政治论说,如果具足四个条件,即可称其为“儒教宪政”之说。第一,肯定“儒教”系一宗教性存在,而非只是一套世俗生活之说教;第二,肯定儒教是中华民族精神命脉之所寄,而非效忠皇权之意识形态;第三,支持政治上中国应走“宪政”之路,而非满足于传统之“致君尧舜”、“风生草偃”或现代的某种“专政”;第四,主张儒教与这种“宪政”有某种协同性、呼应性关联,而非斩然两橛,划然剖分。以此标准衡量近现代儒家前贤之政治思想,本文认为其中牟宗三先生的“新外王”说即是某种“儒教宪政”说,而非政治上的“西化民主”论。关于牟宗三先生的“儒教宪政”思想,时人鲜有正面论及者,本文尝试论之,或许可成一新解也。
一、“新外王”:与其说是“民主”,不如说是“宪政”
或者是因受“五四”以后“科学”与“民主”两大口号之熏染,或者是由于对“民主”与“宪政”之间的异同分合所做慎思、明辨功夫之未尽,牟宗三先生“新外王”之两项基本内容,不论其本人还是观者,皆以“科学”与“民主”两语称之,至今俨然若成定论。“科学”之称,存而不论。就其中之“民主”之称而言,本文认为实有“正名”之必要:与其称其为“民主”,不如称其为“宪政”尤为如实切当也。
或许有学者觉得:“宪政”即是“民主”,“民主”即是“宪政”,两者名异而实同,把牟先生之“新外王”正名为“宪政”乃无谓之举。浮泛地说,这种感觉不能算是严重错误。然而,从严格的学术角度出发以求称名之精审的话,则此“感觉”实为一种比较严重的混漫。“宪政”与“民主”,不论就其核心意义而论,还是就其历史渊源、诉求目标、客观效应等方面而论,都是非常不同的,甚至是截然对立的。
“宪政”之称和实践,是近代以来的事情①据哈罗德·J.伯尔曼说:“宪政”一词出现于十八世纪晚期或者十九世纪早期,主要指成文宪法高于制定法这一美国原理 (“The word‘constitutionalism’was invented in the late eighteenth or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to refer chiefly to the American doctrine of the Supremacy of the written constitution over enacted laws.”Harold J.Berman:Law and Revolution:The 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pp.394-395)。当然,宪政之观念会出现得更早,如英国 《大宪章》中即有其萌芽。。其本义,诚如当代匈牙利宪法学家安德拉什·绍约(András Sajó)所言,是“限制国家权力,保护公共和平。”②“Constitutionalism is the restriction of state power in the preservation of public peace”,András Sajó:Limiting Government:An Introduction to Constitutionalism,Budapest: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1999,p.9.另,麦基韦恩 (C.H.McIlwain)对宪政之历史演变作详密考察后得出结论说:“宪政,在其各个历史阶段中,都具有这样一个本质属性:某种对政府的法律制约;专断统治之反方;暴政——即凭意志而不是依法律进行统治——之对立面……真正的宪政之最古老、最强劲和最持久的核心内容,自其出现到现在,几乎仍然是老样子,即依法限制政府。”(“In all its successive phases,constitutionalism has one essential quality:it’s a legal limitation on government;it is the antithesis of arbitrary rule;its opposite is despotic government,the government of will instead of law……the most ancient,the most persistent and the most lasting essentials of true constitutionalism still remains what it has been almost from the beginning,the limitation of government by law.”C.H.McILwain:Constitutionalism,Ancient and Modern,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47,pp.21-22)亚里士多德说:“谁主张由法律来进行统治,可以说谁就是在主张完全由神祗和理性进行统治;谁主张人治,就是把禽兽的成分加了进来。”③“He who bids the law rule may be deemed to bid God and Reason alone rule,but he who bids man rule adds an element of the beast.”Aristotle,Politics,Book III,1187a,Jonathan Barnes ed.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vol.2,p.2042.同理,主张政治要由宪法来进行节制的宪政,当然也是一种理性之治。宪政诉求的核心价值是政治自由,其现实效应是秩序、和平。与“宪政”不同,“民主”之称与实践,古希腊即有充分表现。诚如政治学者所言:“就本来意义而言,民主是指多数人的统治,或叫人民的统治,即最终的政治决定权不依赖于个别人或少数人,而是特定人群或人民全体的多数。”〔1〕“民主”强调的是“参与”。美国学者柯恩给民主定义为:“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并言“此项定义中参与是具有关键性的概念。”〔2〕其诉求的核心目标是政治平等,甚至延伸至经济上的、社会地位上的平等。“人民的统治”也不必然是“理性的”。康德说:“民主政体在这个名词的严格意义上就必然是一种专制主义。”〔3〕至于托克维尔“多数人的专制”(tyranny of the majority)之说,更是广为人知。复次,民主之客观效应也不一定是秩序井然的和谐和平。麦迪逊说:“这些民主制度一向是骚乱与争斗之大观;从未看到它们曾与人身安全或财产权相容过;而且,总体而言,它们总是短命的,一如它们总是暴死的。”④“Such democracies have ever been spectacles of turbulence and contention;have ever been found incompatible with personal security,or the rights of property;and have,in general,been as short in their lives,as they have been violent in their deaths.”The Federalist Papers,No.10,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52.因此之故,当代政治学家萨托利 (Giovanni Sartori)说“民主与宪政并非是不可分的伙伴”⑤“Democracy and constitutionalism are not indivisible partners.”Giovanni Sartori:The Theory of Democracy Revisited,part one,Chatham House Publishers,Inc.1987,p.192.,安德拉士·绍约甚至说:“民主与宪政,在任何方面都不能被视为相同的。其相互关系至多可以近乎仇视的紧张来形容。”⑥“Democracy and constitutionalism cannot be considered in any way the same.At best,their relationship can be characterized as a tension bordering on animosity.”András Sajó:Limiting Government:An Introduction to Constitutionalism,Budapest: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1999,p.54.现代西方之政体实际上是这两个“近乎仇视”的事物之间的结合:即法治对民意进行“驯服”而形成的政体模式〔4〕。它是近代自由主义之结撰⑦萨托利说:“不论过去或现在,宪政制度事实上就是自由主义制度。可以说,自由主义政治即是宪政。”(“Constitutional systems,both past and present,are therefore in fact liberal systems.One might say that liberal politics is constitutionalism.”Giovanni Sartori:The Theory of Democracy Revisited,part two,Chatham House Publishers,Inc.1987,p.309),恰当的说法是“自由主义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或“宪政的民主”(constitutional democracy)或“民主的宪政”(democratic constitutionalism)。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宪政”是个纯粹政治、法律概念,而“民主”一概念,当今其指涉范围已经泛化到政治之外的经济、企业管理、家庭乃至社会各方面。
由于“民主”与“宪政”两概念有如此大之差异,则用之不可不慎。就牟先生之“新外王”而论,如果深入研究,就可明白以“宪政”称之比用“民主”概括之会更为合理而如实,名正而言顺。
牟先生的“新外王”是为了弥补“老外王”之短板,解决秦汉已降一直无法克服的,困惑着顾、黄、王等大儒的政治问题,而在近代西方自由主义启发下从儒家基本理念开出来的一套政治方案。牟先生认为,周代贵族政治逐渐解体之后,君、士、民皆从宗法血缘、井田等封建之制中脱离出来而得以初步客观化,从而形成秦汉“君主专制”之政治格局。此格局一直延续到清末才解体。君主专制解体后,政治应该顺应世界大势,走向现代化。此即戊戌变法所谋求的“立宪”、孙文 《建国大纲》追求的“宪政”。可以说,牟先生之“新外王”说所诉求的目标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诉求是一脉相承的。
为使政治现代化,必须对传统政治形态进行检讨,明其长短得失。对传统君主专制,牟先生没有全盘否定其价值和历史合理性。在儒家士人的努力下,在儒家思想的熏蒸下,传统君主专制在治道上表现为“圣君贤相”之治,因此并非一团漆黑①牟先生说:“说君主专制,则是那时的政治形态如此,而儒家的‘理性之作用表现’下的‘德化的治道’(再加上道家‘道化的治道’),却正是对于大皇帝的一种制衡作用。”(《政道与治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页53)。但是有其严重不足,其不足主要表现在无法解决王船山提出的三大难题:朝代更替问题、皇位继承问题和宰相之难问题。因此,两千年来,一治一乱,往复循环;篡弑争夺,朝廷不宁;宰相地位不稳,宗室外戚宦官集团辄酿内乱。牟先生认为,要解决这些难题,必须对君、士、民进行进一步客观化。“君”从封建制解脱出来后,成为无约束之无限体;“民”成为潜伏状态的、政治上被动存在的“臣民”,一盘散沙;“士”之“治权”没有客观的法律保障,被君以及依附于君之宗室、外戚、宦官等集团包围,在为“修齐治平”之理想奋斗中,往往成为悲剧性的“气节之士”。为使君、士、民进一步客观化,就得转出“理性之架构表现”,建立客观的政治架构,由此将其身份、地位予以贞定,形成“对列之局”,不相陵越。他说:
“使这三端充分地客观化,就是现代化民主政治所做的工作,也就是现代化民主政治的本质与理想之所在。在现代化的民主政治中,国家组织的建构,必须根据一个根本大法,即所谓宪法。在宪法规定下的民主政治,即所谓民主宪政,乃是一种制度化的民主政治。君、士、民在这种制度中,皆有一定的权限,皆不能够乱来,无一人是可以‘唯我独尊’的。”〔5〕
这里面含有其所谓对君、民的“两步限制之立法”:
“承秦大败天下之民之后,处于时代之问题性中,而唤醒人类理性之自觉,则必顺孔孟之第一义而转进至一个普遍文化运动,由道德教化、圣贤人格之精神主体,广披于政治社会而广度化,归复于一般人要求自立之精神主体上,做到两步限制之立法,而成为‘理性之内在表现’,方可说是一新转进。两步限制之立法:一为对于君之限制之立法,一为对于民之权利义务之承认 (亦含有限制)之立法。(不管其程度如何,能向此做,便走到政治形态矣,不只是吏治。)然而西汉儒者乘复古更化之时,不能向此用心,而转其形态为禅让论、五德终始论 (此亦为对于君之限制,可见总有此问题,责之以两步立法,非谓不可也),成为迂怪之超越表现,因而引出荒谬乖僻之王莽。此岂不可惜哉!”②《历史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页251。按:此段引文中的“理性之内在表现”非该书论及东汉光武帝时所谓“理性之内在表现”。其确切意思是:“表现而为事理之推求,此是理智之运用;表现而为人性之尊严、个性之尊严,此是意志之运用。”前者为科学之基础,后者为宪政之根基。参该书,页250。
以上引文是就汉代政治而发者,然从中可以窥见其宪政思想。牟先生认为:若欲实现代表政权之“君”、代表治权之“士”和代表民权之“民”之“客观化”,则须有授予并限制“君权”之立法和赋予并限制“民权”之立法。前者是关于“政权”者,后者是关于“民权”者,而此两者非他,正是现代意义之宪法之两项基本内容。“能向此做,便走到政治形态矣,不只是吏治”,意思是走入现代客观化、理性化的政治形态,不仅有“治道”,而且“政道”亦因之而奠基矣!这正是“新外王”之根本诉求,其用心聚焦在“宪政”而非“民主”,十分显明。③当然,由于“对于民之权利义务之承认”,民成为自觉的政治主体,一定程度的“民主”成分自然蕴含其中,但非诉求之直接目标。可惜西汉政治未能转至此境,“则中国两千年之历史即为如是之形态而永转不出矣”。(《历史哲学》,页252)
此外,当“民主”与“宪政”发生冲突时,牟先生明确说“参加竞选,即必须承认此一共同的宪法体制”,“对于这一架构本身则是不可争论置疑的,否则就是自我否定”〔6〕;“民主须通过法治一客观的规范轨道来运行”〔7〕。这其中蕴含有明显的“宪政”优先于“民主”之意。
通盘观察牟先生关于“新外王”的论说,可知在他的心目中,中国政治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是“分析的尽理精神”、“理性之架构表现”、“理性之外延表现”、“客观化”、“对列之局”、“政道”的开出,而其中一以贯之的则是“知性”。他认为,现代政治之所以先出现于西方,一是其有“概念的心灵”、“架构思考”的传统,二是由于其社会阶级对立比较突出。其中,“架构思考”是更为关键的,阶级对立只是现代政治产生的历史机缘。牟先生所说的“架构思考”,其实就是以逻辑数学为代表的“知性”之抽象思考。他认为,科学与现代政治成立的基础,都是“知性”,两者同根同源①牟先生说:“逻辑数学科学与近代意义的国家政治法律皆是理性之架构表现之成果,这都是些建筑物。”(《政道与治道》,页44)“此两系为同一层次者,而其背后之精神俱为‘分解的尽理之精神’。”(《历史哲学》,旧序一,页3)。牟先生精研康德哲学,深受其影响,这种看法与其康德哲学的思维方式有关。知性是科学知识成立之先验的形式条件,感性经验经过知性范畴之规范,形成知识,成立科学世界。在政治实践领域,知性通过抽象的架构思考,建立抽象的架构,以之规范各党派、各阶层、各群体的利益、权利、偏向等等内容方面的诉求,由之而形成现代政治。可以说,知性既是自然之立法者,也是政治社会之立法者之一②社会政治之另一更重要的立法者为道德理性。。牟先生说,现代政治“严格地说,即是一个实现人权的形式条件 (formal condition)”〔8〕。又说,中国传统政治,因缺乏“概念的心灵”,遂“流于漫荡而软疲”〔9〕。可见,客观的政治架构 (政道)在政治中的地位相当于知性范畴在科学知识中的地位。“政道”与“逻辑”虽然因其对应的领域不同,但是其本质都是“知性”、“形式”,都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而感性经验、政治利益,虽然有科学领域与政治领域之分别,但都只是“内容”、“质料”,在关键性、重要性方面,它们不及知性概念或政道架构这样的形式③这里的“形式”、“内容”,当依亚里士多德、康德哲学的思路来理解,这些形式更重要。萨托利在谈到“形式的自由”的重要性时说:“把我们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下享有的自由称为‘形式的’——同时把‘形式的’理解成‘不真实的’——这是对形式这一术语的法定含义的误解,并把问题弄得模糊不清……倘若自由主义带来的仅仅是空洞的形式上的自由,西方那些贬损形式上的自由的人为什么会只要他们的不真实的自由 (据他们声称)受到侵犯 (据他们声称)总会激烈地进行抗议呢?”(“To call formal the freedom that we enjoy in liberal-democratic systems—when formal is used in the sense of“unreal”—is to misconceive the juridical signification of the term form and to obfuscate the issue.……Had liberalism produced only an empty formal liberty,how is it that its Western detractors protest so vehemently whenever their unreal freedom(in their claim)is(in their claim)infringed upon?”Giovanni Sartori:The Theory of Democracy Revisited,part two,Chatham House Publishers,Inc.1987,p.391)。。牟先生甚至认为,中国儒家思想已经有“民主之内容”,所缺的是形式表现〔10〕。可见,现代政治之所以是“现代的”而不是“传统的”,关键在有没有某种“形式”。而牟先生之“新外王”之所以为“新”而不是“旧”,也是基于某种“形式”之建立。这种“形式”,其与“民主”观念的关联程度显然远不及其与“宪政”概念的关联度高。因为,“宪政”就是安排并限制国家权力、平衡民权和政府权力的一种“形式架构”。总之,从牟先生更强调其“新外王”中的“形式”因素而言,以“宪政”称之也远比以“民主”称之更为贴切。
牟先生在论说政治现代化时,对政体的安排、公民的自由、私有制等解说非常丰富,而对公民直接参与管理、多数决定、全民公决之类的典型“民主”内容强调不多。这也表明,他对“宪政”的强调远远大于其对“民主”的解说,虽然“民主”一词在他的论著中的出现频率远远高于“宪政”。
如前文所言,“宪政”是法律、政治上的概念,而“民主”则常用于政治之外。牟先生反对“泛政治主义”、“泛民主”,主张“教化的归于教化,学术的归于学术,政治的归于政治”〔11〕,也未闻其主张“经济民主”、“工业民主”、“社会民主”等等民主之泛化。出于这点考虑,也应该以“宪政”而不是“民主”来称其政治“新外王”。
牟先生的政治论说,旨在建立中国政治之“现代化”,而其言说的背景则有两个,一是秦汉以来之“君主专制”,一是当代之“极权政治”。④牟先生说:“政治的最高原则是就个体而‘顺成’。以前中国在政体上虽是君主专制,然于治道上,这个最高原则是无人能违背的。唯近代极权专制始以概念、主义把持天下,牵率人民,不就个体而‘顺成’,却倒转方向抹杀个体而‘逆提’。”(《政道与治道》,页103)君主专制的问题是君权没有理性架构的制约,“极权政治”的问题是“泛政治化”。要对治这两个古、今政治问题,最恰当的药方是“宪政”,而非“民主”。而且后者还有可能产生诸如“多数人的专政”、“群众专政”等严重的副作用。在厘清“民主”、“宪政”的分际并研究牟先生的具体论说和真实意图之后,可以说,其“新外王”是“宪政”,至多是“宪政民主”,而非单纯的“民主”。至于他本人经常用“民主”称之,乃是沿用俗说,未见谛当。
二、作为宗教之儒教:“新外王”之根源和动力
以上论牟先生所言政治上之“民主”何以更恰当地说是“宪政”,则其“儒教宪政”成立之第三项条件已经具备。兹略论其如何具足第一、第二项条件之情形。
要言之,牟先生认为,不论就人生层面而言还是就社会、国家层面而论,宗教之“教”皆不可无。不仅不可无,而且是笼罩性的首出庶物者。安心立命,使个体生命获得究极意义,贞定社会生活、人伦日用之“常规”,保障国家政治之不走失而悖于天理之公,根本上皆赖宗教之护持。所以他说“一个民族是不能没有教的”〔12〕,乃至认为宗教是“永恒的真理”①牟先生言:“我们今日当然既不能反宗教,亦不能反民主,亦不能反科学,这都是永恒的真理。”(《牟宗三先生晚期文集》,《全集》卷27,页19)。
宗教之成立,首先是基于其唯心论哲学。牟先生说:
“唯心论有各种不同的系统,有各层次各领域上的说法。从纯理过程上看,当然各有利弊,并必有不健全的地方,亦有令人生厌的地方。见仁见智,自可有所取舍。但是综起来看,唯心论有一个共同的意向与共同的主题,那便是想在纯然的科学世界科学知识以外,开辟并肯定价值世界,以‘意义’与‘价值’(维特根什坦所说的不在命题世界内的那个意义与价值)为主题,以说明与成立道德宗教为目的。”〔13〕
“由这样而开出的科学知识以外的境界的唯心论者 (理想主义者)正是古今中外学术大传统的所在:人道由此立,理想价值由此出,学术文化由此开,一切现实的实践都在这里得其方向,得其意义。繁兴人间一切正面的光明的大用,有百利而无一害。”〔14〕
牟先生甚至认为,西方只有观念论,“只有中国才有真正的唯心哲学”〔15〕。他说:
“我们根据中国的智慧方向消化康德,把康德所说的超越的理念论与经验实在论那个形态转成两层的存有论——‘执的存有论’和‘无执的存有论’。‘执的存有论’是识心;‘无执的存有论’就是智心,这就是彻底的唯心论。彻底的唯心论就从‘无执的存有论’透出来,这个在西方是透不出来的。”〔16〕
在此唯心论基础上成立的宗教,其重要性牟先生强调之不遗余力:
“宗教是一民族文化生命之最深处、最根源处之表现,亦是一文化生命之慧命之最高表现。”〔17〕
“关于道德宗教方面,吾人必须知这是‘人道之尊’之总根源,价值所从出之总根源。人性之尊严,人格之尊严,俱由此立。人间的理性与光明俱由此发。宗教不是外在的迷信,乃是人生向上之情,期有以超越其形限之私之不容已。而此不容已也就是人之‘内在道德性’之发见处。”〔18〕
牟先生还借助梯利希 (Paul Tillich)的“终极关切”说来阐明儒教之为宗教:“终极关心问题,就是不管你在社会上做什么事情,是什么地位,都必关心的问题。依西方文化来说,就是宗教的问题。在西方,宗教问题,自然是指自古犹太体系中衍生出来的基督教而说的;印度,则是印度教和佛教。中国以前虽然没有产生像这样类型的宗教,但是道家、儒家的学问,并也都有宗教的作用,故也可以称为一种宗教。因为,它们所要解决的都是宗教性的终极关心问题。”〔19〕
就中国文化而论,牟先生认为儒释道“三教”之一的儒教,并非如黑格尔等不少人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世俗的道德格言②黑格尔说:“(《论语》)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页119),而是有超越向度、丰富精神性的宗教,并且是高于其他宗教的“大中至正之大成圆教”〔20〕。
由于牟先生有儒教是“人文教”、具有“高度的宗教性”之类的说法③如说:儒教“自理方面看,它有高度的宗教性,而且是极圆成的宗教精神”。(《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页103),可能有学者便认为:既然儒教是“人文的”,因此就是否定超越存在的,因而也就不是真正的宗教④在西方语境中,“人文的”(human)经常与“神性的”(divine)相对而言,“人文主义”(humanism)有否定宗教之意思。“人文教”中之“人文”则与“神性”相通,如牟先生说:“古有‘人文化成’之成语,此可为儒家人文主义之确界。人文化成者,以人性通神性所定之理性化成天下也。”(《道德的理想主义》,页6)。这种联想是不正确的。“人文教”是说儒教之精神内在于人生社会伦常之中,不是“隔离的”宗教,并不是说儒教没有超越的神圣神秘的向度。儒教是内在而超越的。牟先生对此有明确说法:“孔子之人文教,从其文制为日常生活之轨道方面说,固不离人伦日用,然又岂只限于人伦日用纯为现实的而无超越理想耶?若诚如此,则中华民族早被淘汰矣,而尚能延续至今耶?从仁义之心之点醒方面说,体天道以立人道,则上下贯彻,通透而不隔,既超越而又内在,既内在而又超越,所谓‘肫肫其仁,渊源其渊,浩浩其天’,则生命之奋发、超越之理想、人间之光辉,固已函其中矣。”〔21〕
牟先生认为,以西方宗教为标准来衡定儒教是否为宗教,是不恰当的:“上帝是上帝,基督教是基督教,二者不可混同为一。上帝是普世的,是个公名,叫它道也可以,叫它天也可以。基督教不一定是普世的,它有历史文化的特殊性……把上帝人格化作为祈祷的对象,这是一个方便。本来同样是一个绝对性,却用种种形态表现出来:佛家是如来藏型,儒家是天道性命,道家是道心,基督教是上帝。这些不同只是教路的不同,上帝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绝对,都不能有排斥性。”①《时代与感受》,《全集》卷23,页205-206。引按:既然把“上帝”视为公名,则恰当地说“基督教是上帝”当作“基督教是耶和华”。可见,儒教是肯定某种超越的实体即“道”的存在的。牟先生当然也不否认“道”的神秘性:“天道茫茫,天命难测,天意难知”,“并非人的意识可以确定地知之而尽掌握于手中”,人并不能“把天道的全幅意义或无限的神秘全部体现出来”。〔22〕
此外,还可能有人认为:既然牟先生说儒教有“宗教性”,言下之意可能是儒教只是某个方面有宗教性,而其他方面则是非宗教性的,因而从整体上看,儒教不是宗教。此种联想也不见得恰当。由于在牟先生心目中宗教“是一民族文化生命之最深处、最根源处之表现”,而宗教又是关于“道”这样的“绝对存在”的,“道外无事,事外无道”,则“宗教性”必然是笼罩其他各方面的,而不可能是自我局限一隅而不渗透全体的。关此,当代美国儒教学者罗德尼·泰勒 (Rodney Taylor)的看法值得参考:
“不论是把儒教传统定性为一个宗教传统还是定性为具有宗教向度,一旦儒教的宗教能力被确认,它就不会是此传统的一个无足轻重的方面。事实上,我们可以证明:宗教只要出场,它就不会是第二性的。在这方面,这个传统所具有的宗教能力与此传统之政治的、经济的、社会学的或哲学的等面相是不一回事的。尽管所有这些因素或更多的其他因素都可以被确认和被讨论,但是,只要此传统之宗教向度被证成,此一向度就是根基性的。它就不会仅仅是其他诸多因素当中的一个;它会是一个决定着这个传统之本性的因素。”②原文:“Whether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can be defined in terms of a religious tradition or religious dimension,the religious capacity of Confucianism when identified is not an insignificant aspect of the tradition.In fact,one can argue that where religion is present,it is never secondary.In this respect the religious capacity of the tradition is not the same as the political,economic,sociological,or philosophical aspects of the tradition. While all of these factors and many more can be identified and discussed,if and when the religious dimension of the tradition is established,it is primary.It is not one factor among other factors;it is the factor that determines the nature of the tradition.”Rodney L.Taylor:Illustrated Encyclopedia of Confucianism,vol.1,Introduction,XIV New York:The Rosen Publishing Group,Inc.2005.
牟先生正是把中国文化当成一个儒教传统来看待的。他说:“一个文化不能没有它的最基本的内在心灵。这是创造文化的动力,也是使文化有独特性的存在。依我们的看法,这动力即是宗教,不管它是什么形态。依此,我们可说:文化生命之基本动力当在宗教。了解西方文化不能只通过科学与民主政治来了解,还要通过西方文化之基本动力——基督教来了解。了解中国文化也是同样,即要通过作为中国文化之动力之儒教来了解。”〔23〕“儒家在中国是个‘教’的地位,就好像西方基督的地位一样。”〔24〕儒教信仰者,是为“儒教徒”③牟先生“儒教徒”之称,见 《时代与感受》,《全集》卷23,页34。。
既然牟先生认为宗教是“一民族文化生命之最深处、最根源处之表现”,是“文化生命之基本动力”,则儒教之为其“新外王”之根源与动力,顺理成章。牟先生认为,虽然宪政先在西方出现,但它是“共法”,是人类“分解的尽理之精神”所成就者。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宪政,不是因为其与中华民族生命根本上不相容。相反,它是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生命的儒教之“内圣外王”、“公天下”、“成己成物”等理想所要求者。“家天下”并非究竟,宪政在中国历史上未出现,只是因为历史因缘未至、前儒一时思之未及而已①牟先生说:“以前的儒者一接触到这个问题,便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一、大皇帝根本不许谈这问题。你讲仁义、道德可以。讲这个问题就不行。‘免开尊口’,那是与他的君主专制绝对不相容的。二、凭空想出来一套政治架构并不是很容易的,且是很困难的。如果我们今天不是有西方近三百年演进而成的宪政民主系统为借镜,我们也不一定就能想得出来。”(《时代与感受》,《全集》卷23,页411)。“出现不出现完全是发展中的事,不是先天命定的事。”②《历史哲学》,页163;亦见 《牟宗三先生晚期文集》,《全集》卷27,页81。按:牟先生虽然是就逻辑数学而言的,但也适用于宪政民主。
牟先生认为,西方走上宪政之路,一是因其“分解的尽理之精神”之发露充分,二是因为西方历史上有阶级对立以为助缘③牟先生认为:“阶级对立是一个现实上的因缘,而分解的尽理之精神则是其本质上的条件。”(《牟宗三先生晚期文集》,《全集》卷27,页82)。由于中国社会、历史背景不同于西方,并无阶级对立,所以在中国要开出宪政,应结合中国国情,不可硬套西方阶级斗争的模式④牟先生认为,在西方,“阶级实是其民族生命中恶根浊根之表现”。(《政道与治道》,页111)。正途是通过道德本心之“坎陷”把理性之作用表现转为理性之架构表现,从而开出“对列之局”,并通过文化的力量、思想的自觉,使国人挺立起政治上的主体意识,成为一政治之主体,参与国家事务。由此而建立其现代化的“民主宪政”〔25〕。也就是说,中国之宪政建设是民族生命“自尽其性”中应有的事,是植根于本民族之民族生命的。西方之宪政所给与的启发只是外缘,中国宪政的义理基础是建立在自己的儒教之上的,不同于西方宪政,因后者是建立在基督教之上的。此义牟先生言之甚明:“新儒家认为西方之所以为西方,不在民主科学而在其宗教。民主科学要能定得住,须通过宗教,在中国,要通过儒家传统文化而来。若光讲科学民主,就是只有‘下’,而没有‘上’,只有‘外’,而没有‘内’,只有‘术’,而没有‘道’,若迎进了西方的基督宗教,而不知归本于自家文化传统的话,虽有‘道’实亦无‘道’,因为文化的‘道’,只能从自家开发,不能从外移植……而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道’,舍儒家之外别无可求。”〔26〕
又说:“科学民主为世界之共法,而在西方民主的精神依据在宗教。科学民主是‘术’,宗教精神是‘道’,外王是‘术’,内圣是‘道’。而我们的内圣、我们的神明就在儒家,所以当代新儒家认为要通过儒家来开出民主科学,就是通过‘道’来开出‘术’,来定住‘术’,否则只有‘术’而无‘道’,一定会错乱。当代新儒家面对的问题就是民主科学如何透过中国传统去生根、去成长,如何由透过内圣而开出外王,此内圣要在儒家。”〔27〕
常有学者反驳说,这是“中体西用”之翻版,而“中体”并不能开出“西用”。牟先生认为,此是因为不明白“体”的层次分际所产生的谬见。“体”有内在之体与超越之体两层之分:“内在之体是知识制度层,超越之体是精神理念层”。洋务、维新运动因不明两层之“体”之不同,欲以中学超越之“体”以求西学之用,此固不相应。但是如果我们能消化“西学内在之体”,便可引生西学器物之用〔28〕。牟先生所说的“内在之体”即是体现在逻辑数学中的“分解的尽理之精神”;超越之体,即道德宗教。牟先生称之为“两种定常之体”:“定常之体在两方面呈现,一在逻辑方面;另一在道德方面。”〔29〕逻辑,如牟先生所言“逻辑只有一个,亦如人类的‘根本理性是一’一样”〔30〕,则此“内在之体”完全可以由中华民族把握之以成就科学、宪政之“术”并免于西化之诮。因之,也无需通过打破“中体”来成就宪政、科学。不仅不可打破,此主要由儒教所表现的“中体”,还是中华民族自尽其性过程中所要求的以宪政为内容的“新外王”之根源和动力之所在。⑤牟先生认为:从君主专制转至宪政民主,“这是一民族自尽其性的本分事,不是西化的事”。(《生命的学问》,页53)
三、“人文化成”:“新外王”之为儒教宪政之义理根基
在牟先生的政治思想中,宪政之建构是被嵌置于由三个义理纲维所构成的理论框架之中来运思的。这三个纲维分别是:一、“依于仁”;二、“华族自尽其性”;三、“道揆法守”。而“人文化成”则是一以贯之于三者之间者,是“人文教”之落实。
(一)“依于仁”
宪政之架构,是理性主义之结撰。其内在的“形构之理”是“政道”。此外,其上尚有其“存在之理”或“实现之理”为其超越之根据⑥关于“形构之理”、“存在之理”之义,可参 《心体与性体》第一部第二章三、四节。。在儒家,此超越的“存在之理”即是仁体、道体。
西方之通过阶级斗争以宪政民主,实际上是逼出“形构之理”之外缘,不是其本质。这个可借助认识论来理解。牟先生承续康德哲学,认为认识由感性经验和先验的逻辑范畴构成,两者缺一不可,但其中逻辑范畴更根本,它们是理性的、恒定的、稳定的。牟先生不赞同对逻辑数学持“约定主义”立场①参牟先生 《认识心之批判》一书之序言。,认为逻辑数学是先验之理性。所以他说宪政是“超然的”:“自由、民主之所以是超然的,即是说,不论你信什么主义,民主政治乃是实现人权的一个条件,严格地说,即是一个实现人权的形式条件 (formal condition)。民主政治是个架子,超然而不可和任何特殊的政党、特殊的政策同一化。”〔31〕可见,在牟先生看来,政道是一个理性的事物,而不是经验的事物,也就是说,它不是阶级利益博弈过程中达成的一种方便的约定。如果纯是方便的约定,则不能稳定,也达不到克服“一治一乱”的目的。
由于宪政是个架子,是“超然的”,它当然具有某种“中立的”性质。西方一些自由主义者便因此倡导“国家中立”说。如果牟先生仅此而止,则其与自由主义者确实无根本差别。但是,牟先生思想不止如此。在此宪政的“形构之理”之上,牟先生极力主张“存在之理”:存在之理是形构之理之上的另一超越之理。此超越之理,就是“天道”、“仁体”,牟先生亦曰“根源的理性”②参 《政道与治道》,页92。按:自梁漱溟以来,现代儒家都有把“仁”称为“理性”之用法。此“理性”当然非逻辑理性、知性之理性,而是“由人性通神性所定之理性”:“此理性,儒家向往其为一普遍之理性。其向往也,非凭空之抽象的向往,乃由实践的证实而成之向往。依此,其向往转为超越之崇敬。此种理性的普遍性,不独限于人类之历史,且大之而为宇宙之原理,依此而成为儒家之形上学。此具有普遍性之原理,儒家名之曰‘仁’。”(《道德的理想主义》,页8)。
此“存在之理”,就宪政之健康运转来说,必不可少:“理性之外延表现在成科学知识与讲逻辑、数学上甚当行,无弊无病。在成民主政体上也当行,然不能裁断其理性之根,又须随时善讲、实讲、深讲此理性之根,而不能只将自然科学上的‘外延法’移来用于政治、社会,乃至历史、文化上,而化除那‘理性之根’。在自然科学上,顺外延表现而裁断其理性之根,尚不甚要紧,但在政治社会上亦如此做,则其弊甚大。”〔32〕又说,一方面肯定科学民主,同时以道德理性调节之,是“儒家特殊之用心”:“儒家历来不反智,故正德、利用、厚生三事并讲。德、智是人类理性的两翼,德智双修是儒者的理想规范。民主政治亦在德智合一中获得其理性中之根。随着时代条件的成熟,民主科学在中国扎根已成为我们理性中所必然有者,亦为今日儒者所应当首先正视而应予以理性的说明与肯定,并使之与道德理性相贯通而使之不失其范域。这是儒家思想家的特殊用心。”〔33〕
也就是说,在牟先生的运思中,有两层依次递进的超越与贞定:第一层是先验的形式理性对政党等经验性的政治力量、利益博弈的超越与贞定,由此而成“宪政”之对列之局和架构表现;第二层是儒教所宣示的“仁体”对作为架构表现的宪政之超越与贞定——由此而成就的只能是“儒教宪政”。如果牟先生只讲纯粹的“民主宪政”之架构,则与自由主义无本质差别;如果他虽然不仅讲宪政而且讲宪政之后、之上的超越的价值基础,那么所成就的则也可能是基督教或其他教之宪政。由于牟先生的宪政是以儒教而不是以基督教等教为其义理和价值之超越基础的,则其宪政不能不是儒教宪政。再者,由于牟先生认为作为“大成圆教”的儒教是优于作为“离教”的其他教的,则其儒教宪政不仅是优于自由主义宪政的,而且也是优于其他教的宪政的。因此,牟先生的“新外王”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宪政民主是不同的。它是本诸儒教的基本义理价值和儒家政治社会思想和理想,在西方自由主义宪政的启发之下,从自己民族文化生命中开出来的,其情景犹如两宋诸大儒在佛教哲学的刺激启发下本诸孔孟基本义理而构建“道德的形上学”一般。正如牟先生认为“阳儒阴释”之说是对宋明之学的诬妄之辞一样,他也不认为“民主宪政”便一定是“西化”③牟先生说:“谓之为阳儒阴释者,皆是浮光掠影无真实感者之肤谈,不负责任之妄语。”(《心体与性体》第一册,《全集》卷5,页268)又说:“科学、民主根本也是孔子所说仁义道德的必然要求。孔子若地下有知看到中国二千年来没法解决的政治、经济问题借着你引进的民主与科学解决了,他高兴感谢你还来不及哩!”(《时代与感受》,《全集》卷23,页429-430)。“新外王”之为儒教宪政,不可等之于西方自由主义政治思想,这一点从他下面一段话中可清楚地看出来:“我们当然不能说孔子或儒家是现在的所谓‘自由主义’,但他的确能表现自由主义的宽容的精神。自由主义只是一种态度,它本身无内容。来自西方近代的这个特定的自由主义,其提出是有它的特定背景的。它是在人权运动下产生的。它是对宗教信仰上的迫害而产生,对阶级制度而产生的,对专制暴君而产生。儒家传统所表现的宽容精神不是这样产生的……儒家所表现的宽容精神是根据克己、慎独、明明德而来的,是他们的道德修养所达到的一种通达的智慧与雅量与德量。不是从社会上对某一客观问题,如宗教、如阶级、如专制而发的一种运动。此其与西方近代所出现的自由主义不同之处。它是克己慎独的圣教所透射出的一种宽容的精神或敞开的精神。这是由克己慎独而来的智慧与德量,但却与从社会上对客观问题而发出的自由主义相契合,而且可以说这是更根本的、更真实的,比特定的自由主义更高一层。它可以使那从社会上而发出的自由主义更真实化、更充实化,更能提得住而站得住。”〔34〕牟先生此语虽然谈的是“自由主义精神”,但是同样也适用于“自由主义宪政”。可以说,牟先生的“新外王”吸纳了自由主义宪政思想,同时又“用儒家的精神理念来贞定民主与科学”〔35〕,使其“调适上遂”,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宪政,即“儒教宪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自由世界所肯定的人权、自由、平等都是在‘立于礼’的道德立场上派生出来的”〔36〕。
虽然牟先生对自由主义精神多有肯定,但是对当今的自由主义,它认为已经失去其“精神性”,需要儒家来引领时代。他说:“吾默察今日之自由主义已不复能作为领导时代之精神原则。在文艺复兴时,自由之实践具备其充分之精神性,因而下开近代之西方文明。然而演变至今日言自由,已具体化而为政治之民主制度,经济之资本主义,而今日之自由主义者其心思亦黏着于政治经济之范围而不能超拔。自由主义显然已失其精神性……自眼前言,自由主义有其应付现实之时效性,此俨若对付特殊问题之特殊思想。然特殊思想必有普遍原则作根据。其精神性之恢复,端赖此普遍原则之建立。此普遍原则即儒家学术所代表之推动社会之精神原则也。惟精神透露,自由主义始能恢复其精神性,变为可实践者。”〔37〕此可见,牟先生对“现代性”所带来的问题甚有警觉,而其所意谓的“精神性”,即是儒家之“仁”。在此“依于仁”之大原则下所开出的“新外王”,乃是“儒教宪政”,已非“自由主义宪政”。
(二)“华族自尽其性”
牟先生说:“我们如果单讲民主政治,不通文化生命,则国家建立不起来。”〔38〕“新外王”之为“儒教宪政”,不仅如上文所论,可从超越的“仁体”之落实这一角度来看出,也可从其“华族生命自尽其性”这一角度来透显。关此,上文已多有涉及,此处稍事补充。
“文化生命”是新儒家思想中的关键词之一。其含义,首先它是一民族的“集团的生命”,非单纯的个体生命。牟先生说:“生命的学问,可从两方面讲:一是个人主观方面的,一是客观的集团方面的。前者是个人修养之事,个人精神生活升进之事,如一切宗教之所讲。后者是一切人文世界的事,如国家、政治、法律、经济等方面的事,此也是生命上的事,生命之客观表现方面的事。”〔39〕其次,“文化生命”既非纯粹的生物生命,亦非纯粹的精神生命之自身,而是两者之综合:“严格言之,只是生物生命固然不是文化生命,就是隔离的宗教生命亦不是文化生命。文化生命等于超越的宗教生命与形而下的生物生命之综合。”这个综合,也就是“历史文化”,也就是孔子所说“文不在兹”之“文”〔40〕。
依此,关于宪政,牟先生有两项论断:第一,宪政是“华族生命自尽其性”;第二,宪政是“人文化成”之“文制”。
唐虞之“天下为公”尚矣,夏商及周,据宗法血缘原理而成之贵族封建之制臻于极至。此贵族政治之下,虽然具“亲亲尊尊”之义、“郁郁乎文哉”之美,然受血缘关系之拘牵,政治不能客观化,不可为华族文化生命之“尽性”之完成。经春秋战国至秦汉而铸成、垂两千余年而未变之君主专制政体,政治从血缘宗法封建制之束缚中解放出来后,在“圣君贤相”之格局中,颇有“文治政府”之风。然“皇帝是一个无限制的超越体,人民是纯被动的潜伏体”〔41〕,政治仍未能走上理性化之途,未能“立千年之人极”以免于“一治一乱”之局,民族文化生命因之不能畅通。辛亥革命后,内忧外患,政局不堪闻问。“在创造真正之人生中,是谓尽己之性;在建立自己之国家中,是谓尽民族之性。”〔42〕牟先生正是激于现实之弊,承续华族慧命以构建其“新外王”之说的①牟先生慨乎言之曰:“何吾华族上下五千年,皆为家天下之意识所笼罩,而不能冲破耶?抑非必无其他隙明也。尧舜禅让也,选贤与能也,亦示于家天下外尚有公天下之一说,而且置于历史之开端,视为理想之境界。何不就此理想而一深思耶?深思其所以实现之道耶?岂可尽推之于天而止耶?”(《历史哲学》,页200)。唐君毅先生谓“其所以取资于西方文化者,即以承昔先圣贤之志而解决中国文化历史中自身之问题,是孝子慈孙之用心”〔43〕。自此角度以观“新外王”,也有助于加深对“儒教宪政”之理解。
(三)“道揆法守”
牟先生说:“没有一个客观的文制为道揆法守,社会上日常的是非善恶的判断,未有不混乱的。”〔44〕“道揆法守”,即牟先生常称的“文制”,是“新外王”中之另一题目,从中尤可看出“新外王”之儒教宪政特色。牟先生说:“道德宗教,在其客观广度方面,有成为‘日常生活的轨道’(即文制)之意义,在其主观深度方面,有作为‘文化创造之动力’ 的意义。”〔45〕上文所论,可谓从“文化创造之动力”方面说的,即儒教宪政为此儒教、民族生命之“文化创造动力”因应时代而创造者。下面再从儒教之“文制”意义看儒教宪政。此可分两层次说:即从“宪政”架构本身说和从“日常生活轨道”说。
文制,即人文化成之制度,包括礼乐、习俗等“日常生活轨道”。但是,在牟先生思想中,“文制”也可以涵盖政治、法律等公共领域之制度,是政治上的“立于礼”。牟先生说:“道的表现而为礼乐,就是‘文’。拿‘道的表现’来成全人,就是拿‘文’来成全人:此即是‘人文化成’。文是道与器、天与人,内与外,本与末的综合表现。光说道,是分解的抽象的说法,这是立大本。说‘文’则是综合的,具体的表示。(合而为一,即为具体)。所以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这就表示孔子慨然以夏商周相传而大备于周的‘综合体的文’自任。”〔46〕可以说,“文制”就是孔子“文不在兹”之“文”,是“人文化成”之“综合体”,也就是牟先生所称“人文教”所化成之一切。犹如牟先生把西方的近代制度称为西方政治生活之“文制”一样〔47〕,他也把儒教开出的宪政称为政治生活之文制。他说:“孔孟立教,及后人继之而发展的儒家学术,其转为文制,只是日常生活的文制,始终未转出政治生活的文制。”〔48〕显然,他的“新外王”便是这种政治生活上的“文制”。此说蕴含的意思便是:“新外王”是一种儒教“人文化成”之常规,是传统“礼乐”之制推陈出新之转进,而非移花接木之变异①宪政制度下,虽然有党派、利益之斗争,但都是“文斗”而非“武斗”。竞选失败后,握手言欢,不失其和,此实合乎孔子“其争也君子”之义。因此,宪政之制亦含“礼”义,即政治上之“立于礼”。若参政者之个人备儒者之修养、具儒者之风范,则更是如此。。
从“日常生活轨道”说,则作为“日常生活轨道”之“文制”对宪政制度之健康运行具有保障性功能,同时也对宪政下的政治活动具有制约作用。牟先生认为,在人生和民族生命之“整全”中,政治并非“首出庶物”者,其上受宗教之笼罩,其下受“日常生活轨道”之支撑和制约。文制是一民族之日常生活经过圣贤教训和宗教教化之长期浸润而形成的礼俗。人们行之而安,习之以为定常,成为超自觉或不自觉的生活方式。人之生命、生活由此得以贞定,具有“为生民立命”之意义。“若只有政治上的民主,而没有生活上的轨道,则国本不立。”②《人文讲习录》,《全集》卷28,页4-5。牟先生还说:“中华民族之建国必有其国体,建国就是使一个国家有‘体’,有国体。国体有两层,一层是政治国体,一层是文化国体。宪法代表政治的国体;文化国体是民族的文化教养、生活的方式、生活的方向、生活的态度。”《时代与感受续编》,《全集》卷24,页424。按:此处所谓“国体”义通于“国本”。政治上,现代社会之人民固然应该从传统的“潜伏状态”中复苏,自觉成为一政治上的主体,意识到其对国家的权利和义务。但是,政治不是人生之全部,对大多数人而言,政治生活只是其“人生之全”中的一小部分。正如科学不能解决人生问题一样,宪政民主之下的自由、平等、人权等也不能解决人生的全部问题。政治之外的许多其他人生问题,需要由文制来解决。政治上的观念,包括宪政之下的政治民主、自由、人权、平等等观念,应该局限在政治领域,不可泛滥到日常生活领域③如牟先生说:“权利、义务、公民、国民等观念都是政治层面的观念,只应在政治上运用,不可以随便乱用、泛用;谈到道德、谈到家庭,就不需要这些东西。”(《时代与感受续编》,《全集》卷24,页263)。文制是生活之“常道”,不是某一特定的“学说”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更不是可以去取代的〔49〕。因此,牟先生极力反对政治、自由、民主等观念溢出自己的范围泛滥到日常生活领域而成为“泛政治”、“泛民主”、“泛自由”。不仅如此,教化被打破之后,不仅人生苦不堪言,而且也会影响宪政民主制度的健康运转。牟先生说:“从西方来的‘正视自由与民主制度’固有贡献于自由与文制,然而必须有人文教育以培养其理性生命,然后自由方能成其为自由,文制方能成其为文制,否则两方皆可以恶化而成为其自身之否定——自由恶化而为放纵无度,民主亦可以恶化而为暴民混乱……有健全的文化教养之国民,始有健全的国家之制度。”④《时代与感受续编》,《全集》卷24,页432-433。按:此中所言“文制”指民主宪政制度言。就中国而言,文制就是圣贤所造就之礼乐,是“人文教”之人文化成。牟先生认为政治不能侵犯它,等于说宪政民主不仅受儒教“於穆不已”之天道仁体等基本义理之统御,而且也受儒教在“人伦日用而不知”之社会生活层面的“人文化成”之经验“综合体”之制约①牟先生说:“中国所讲的圣人的教化,皆是不属政治管辖的。”(《时代与感受续编》,《全集》卷24,页287)。可以说,文制相当于儒教的仪式。虽然牟先生曾说“儒教不是普通所谓宗教,因它不具备普通宗教的仪式。它将宗教仪式转化而为日常生活轨道中之礼乐”②《中国哲学的特质》,页103。按:儒教祭天、祭孔未必不可视为儒教之宗教仪式,牟先生笼统说“不具备普通宗教的仪式”并不准确。,但这不一定构成对儒教仪式之否定,其意也可能是指儒教“即生活之轨道而为宗教仪式”。因此,护持日常生活轨道,具有护持儒教之意,也有限制自由、民主之泛化之意。“文制”之说是牟先生“新外王”之说的重要内容,从中也可以看出其宪政何以是“儒教宪政”之一斑。以下引牟先生之言以证之:
“道化的治道与德化的治道,自今日观之,实不是普通所谓政治的意义,而是超政治的教化意义,若说是政治,亦是高级的政治……在道化与德化中,人民在以前说为‘天民’,而不是国民,亦不是公民。国民、公民,与权利、义务同,都是政治意义中的概念。我们认为这一层是不可少的。这一层中的诸概念、诸意义之转出,统系于‘政道’之转出。但我们也认为政治的意义与教化的意义并不冲突对立。因此我们不能因为要转出政治的意义,必抹杀或否定教化一层的意义。我们认为天民、国民、公民,俱是价值观念的表示,无一可少。”〔50〕
按:由此可见,牟先生认为现代政治观念与传统之礼乐教化可以并行不悖,分属不同领域。
“凡可以成教而为人人所接受而不能悖者,必非某某主义与理论 (学说,theory),亦必足以为日常生活之轨道,由之以印证并肯定一真美善之‘神性之实’,即印证并肯定一使人向上而不陷溺之‘价值之源’。非某某主义与理论,此言其普遍性与定然性。即就人文教而言之,儒家所肯定而护持之人性、人道、人伦,并非一主义与理论。此是一定然之事实。即就其为定然之事实而言其普遍性与定然性。言其足以为日常生活之轨道云云,此明其与为政治生活之轨道之民主政治不同。此两者互不相碍,互不相代。”〔51〕
按:此益可见宪政民主之不能排斥儒教及其所教化而成之文制。
“人不能只有科学知识,即算完事。科学知识不是文制。吾人亦不能只有民主政治即算完事。因为民主政治只是政治生活的制度。人不能不有日常的生活。无论科学家、政治家、智、愚、贤、不肖,皆不能不有日常生活。依是,就不能不有日常生活的常轨 (文制)。在社会崩解的时候,道揆法守皆归绝丧,则人即无日常生活的常轨。个个皆拔根,皆落空,其苦自不待言。而且不只苦而已,且横冲直撞,泛滥决裂,生命即不能保。再茫然决裂下去,人类势必归于淘汰。‘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有江湖为其底子,则鱼可相忘而保其活命。有道术为其底子,则人可相忘而保其天年。日常生活的文制就是鱼的江湖,人的道术。圣贤学问、道德、宗教方面的教训之不容忽视,就在这里。”〔52〕
此言文制之为“道揆法守”。
“政治上轨道之后,儒家思想自能带动文化生活上轨道。这在以前就是所谓国教、礼乐生活。既为日常生活轨道作安排,又提升人的精神生活。《礼记》里有完整的一套,冠仪、婚仪、乡饮酒、丧仪……这一套现在说过时了,不适用了,这话是不通的。要用,它仍然适用。是用不用的问题,虽然尽可有损益,其实中国传统文化生活的安排是最合人道之常的。”〔53〕
此说俨然有儒教“文制”自古及今可以有其“自足”、“自治权”以与政治上之“现代化”相制衡之意。
综上所论,在“新外王”中,宪政是“仁教”义理之落实③牟先生时有“仁教”之称,参 《生命的学问》,页34、58。,是“华族自尽其性”之民族生命所生发。它是政治上的“立于礼”而成之新文制,同时与作为日常生活上的“道揆法守”的旧文制互相平衡制约,并行而不悖。可以说,“新外王”是涵泳在儒教“人文化成”之义海者,其宪政是“儒教文化中的宪政”。
四、“新外王”中的儒教宪政之基本制度设想
客观地说,牟先生之“新外王”说主要是基本义理上的开发与疏通,对于当下或未来的具体政体构建,未遑细论详说。但是从其著作言论中,可考见或推知其基本制度设想。
“新外王”因为吸纳融化了近代西方宪政制度,则宪政政体所本具之基本制度如有限政府、分权、保障基本人权、代议选举、市场经济等制度,自不待言。以下只论其能表现儒教宪政特色之制度设想。
(一)“以儒教领导社会并制衡政治”
黄宗羲 《明夷待访录·学校篇》曰:“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非谓班朝,布令,养老,恤孤,讯馘,大师旅则会将士,大狱讼则期吏民,大祭祀则享始祖,行之自辟雍也。盖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
牟先生论之曰:“(此篇)期予政治以制衡之作用。学校为教化之系统,其作用有三:一、司教,二、养士,三、议政。是非不独存于朝廷,亦且公诸天下,而由学校之是非以制衡天子之是非。君师殊途,二元骈行,自始即为儒者所力争。”〔54〕“是非”是一切政策之基础,而是非最容易言人人殊,莫衷一是。牟先生赞同黄宗羲之主张:是非折中于儒者。“君师殊途,二元骈行”,实际上说的是在是非对错问题上,儒师高于君主。
牟先生更就 《学校篇》之整体论之曰:“其所说者,大体皆可行或当行于今日,与 《原君》、《原法》等篇所说,皆有永恒之意义。其基本精神实欲以儒教领导社会并制衡政治。故在今日势必将儒家之‘教的精神’提炼而上之,以代其他国家之宗教地位。只有在此教之精神之提炼与弘扬上,始能培育名儒与大儒,以主持学宫……今日学校之弊正缺此主导之精神,故欲使学校能尽养士、议政、研究学术、司教以美风化之四责,则必恢复儒教之教的精神以为主导不可。”〔55〕当今倡导儒教宪政最力者蒋庆先生认为黄宗羲所论太学“最符合‘儒教宪政’的精神”〔56〕,而牟先生谓“以儒教领导社会并制衡政治”之原则具有永恒意义,则牟先生之“儒教宪政”于此可得有力佐证。
牟先生不仅主张以儒教来制衡政治,也用其别具一格的“多元价值”论来制衡政治。他说:“儒家不同于墨道法,它就人间肯定多元价值。它有四个标准,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天地、君、亲、师。天地代表超越的意识,亦可称曰天;君代表政府;亲代表家庭;师代表教育学术。在这多元的肯定中,家庭不能够化归于国家,社会也不能化归于政府。我们不能够以政治斗争的理由叫你回家斗争父母,也不能以政治斗争的缘故抹杀教育学术的独立。儒家以四个标准同时成立,这是墨、道、法不能讲的。现在□□□就一个标准,一切都唯政府,只有政府一个标准,其他都没有了,这是不行的。”①《时代与感受》,《全集》卷23,页134。按:牟先生在香港的家中悬有“天地圣亲师”一条幅,可见其用意之诚。可以看出,牟先生说的“天地君亲师”四个多元价值标准,实质上是儒教的标准,意在以儒教指导社会并制衡政治。
(二)儒教之国教化及其组织化
从前文所论,尤其从其“在今日势必将儒家之‘教的精神’提炼而上之,以代其他国家之宗教地位”之说中,即可见牟先生是主张把儒教立为国教的。以下再稍作补充。
牟先生赞成信仰自由,不反对公民个体信他教,但是非常强调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因而也极力强调儒教之在中国社会应居主导地位,而不是与其他教等量齐观,更反对以洋教压儒教。他说:“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中国文化是以儒家为主的一个生命方向与形态。假如这个文化动源的主位性保持不住,则其他那些民主、科学等都是假的。即使现代化了,此中亦无中国文化,亦只不过是个‘殖民地’的身份。”〔57〕“信仰自由是一回事,这是不能干涉的,然而生而为中国人,要自觉地去做一个中国人,存在地去做一个中国人,这则属自己抉择的问题,而不是信仰自由的问题。从自己抉择的立场看,我们即应念兹在兹,护持住儒家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有人骂我们这是‘本位主义’,然而这种本位主义有什么不好?每一个民族事实上都是本位主义,英国人以英国为本位,美国人以美国为本位,何以独不许我们中国人以中国为本位呢?若是这叫本位主义,又怎么能反对呢?”②《政道与治道》,新版序,页23-24。按:牟先生下面之说亦可引为参证:“在中国平面地单讲自由主义是不够的。有的人想以基督教的信仰来贬抑中国文化生命之主流。信仰自由,我们不反对任何宗教,但若想以基督教来压儒教,我们必反对。”(《时代与感受续编》,卷24,页173)按:牟先生此意实与蒋庆先生所说“历史文化合法性”相当。儒教代表中国之常道,牟先生既极力维持儒教相对于其他各教的优先地位、主体地位,同时又认为“一个政府有维持常道的义务”〔58〕,则立儒教为国教则必然是其思想中应有之义。
牟先生主张立儒教为国教,还可以从其为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极力辩护中看出。近人以为“独尊儒术”大悖思想自由,牟先生龂龂辩之曰:
“孔氏所承之文化系统固有其所以能一道同风之本质矣。一道同风之普遍性,能求之于申、韩、黄、老等家乎?能以之为立国之最高原则乎?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尧舜三代以来所积累之文化系统,具于五经中者,由孔氏删削而整理之,反省而抒其义,此固非一家之说,亦非一人一时之聪明所能杜撰。此一文化系统早已居于正统之地位,非待孔氏而成为正统,亦非待仲舒、汉武而成为正统也。其所以为正统,乃因其为吾华族之民族生命文化生命之贯通的发展之结晶,故能具有一道同风之普遍性与公共性,即以此而居于正统矣,而为吾华族发展之最高指导原则矣。经过一破败之时代而欲承接文化,不以此本有之主流文化系统为国教 (立国之常道),以谁乎?须知此乃国家居于综合立场、公共观点而为民族立一自肯也,其抑黜百家也,是立于为民族立一自肯上而黜之 (即国家不为之设博士,不以之为民族之指导原则而已),何碍于思想自由耶?”〔59〕
此段文字,慨乎言之,不仅是为董子辩护,亦可视为牟先生今日主张儒教为国教之慷慨陈词也。
牟先生还进一步讨论过儒教在现代社会之“组织化”问题。1954年牟先生创立“人文友会”,此举实有以现代社团方式建立儒教教会之用意。他说:“我们这人文友会,还有一大愿望,即关心我们这一民族国家的立国之本。我们主张使儒家成为人文教,并主张于未来成立人文教会以维持国脉。”还说:“我们要祭天,祭祖,并祭圣贤”。牟先生认为这“三祭”是儒教必不可少的,以前是靠皇帝,现在则需靠儒教社团。他说:“我们从教主讲,称‘孔教’;从内容讲,称‘人文教’。不过要成宗教,必须靠三祭——即祭天、祭祖、祭圣贤。这须靠国家来维持,社会上必须有教会来持载。过去靠皇帝,现在要靠社团。如要此一理想成为客观化,须通过宪法,此为吾人奋斗之目标。”〔60〕从建立组织化之儒教以“维持国脉”这样的主张中,可以明显感受到牟先生强烈的“国教”意识。至1961年,关于儒教教会建立问题,牟先生之设想有所调整,建议“提炼并护持儒教之为教,不别设教会,即以学校为凭借”①《政道与治道》,页153。按:据 《全集》编者说明,《政道与治道》初版于1961年,此语所从出之第九章系该书初版时牟先生新撰就者。。此一设想,盖终其一生而未变。虽然牟先生后来主张把儒教寄托于学校,但其主张国教之意思,则始终一贯。1990年底,年逾八十的牟先生在回答“儒教今天是否需要一套形式以确定自己并适应现代社会”这一问题时说:
“现在最重要的是建立有宪法基础的民主政治轨道,以此政治轨道来保障政治个体与社会生气,以及教育学术之独立,由此遂得以维持住文化的个体;同时文化个体依其所受于儒家之教而培养成的文化理想,反过来亦可以调节润泽政治个体以及种种学术研究。政治上轨道以后,儒家思想自能带动文化生活上轨道,这在以前就是所谓国教、礼乐生活。”〔61〕
虽然这里牟先生没有提“儒教教会”之事,但是在学术自由之中,有儒教之精神贯穿其中以为“调节润泽”,而且明确地把文化生活之轨道定在“国教、礼乐生活”上,则其对“国教”的肯定绝无可疑矣。虽然未再强调“儒教教会”,但他也未必一定排斥之,更何况“寄儒教于学校”,也是某种形式之组织化。也因此之故,虽然牟先生对康有为、陈献章之学术思想贬之甚力,但在“定孔教为国教”一事上,则称其具有“识大体的意识”②《生命的学问》,页86。按:牟先生评康有为有“康圣人讲 《公羊春秋》,讲 《大同书》,讲得乱七八糟”等说法。参 《时代与感受续编》,《全集》卷24,页481。。
牟先生还把儒教与英国之国教相提并论,说:“西方讲自由讲科学,但是基督教不也还在维持那个社会的定常吗?讲自由民主的老祖宗是英国人,但国教还是国教,并没什么受影响。中国人素来讲三祭:祭天、祭祖、祭圣人。如果你连三祭都不愿意保存,那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提升你的生命呢?”〔62〕
(三)祭孔、读经制度化
关于祭孔、读经,牟先生认为,这不仅是应该的,而且应该形成“文制”,即上升为国家之定制。其 《祀孔与读经》一文,言之深切而著明。他说:“一个民族尊崇他的圣人是应该的。政府代表民族国家,从文制上来尊崇也是应该的:既是它的权利,也是它的义务。”〔63〕牟先生认为,一个民族国家必须有由其共同的信念所构成之纲维以维持国本,必须有其“文制”以为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民众生活之“常道”,而在中国只有儒教、儒家学术能提供这个纲维,具有成为“文制”之资格①牟先生说:“凡是文制都是表示现实生活上的一个常规:有普遍性、有一般性。民主政治是政治生活的一个常规,所以民主政治也是今日的一个文制。西方除科学外,惟赖有民主政治与宗教这两个文制,才能维持他们生活的常规。宗教是政治生活外的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文制。这不能由民主政治来代替,也不能由科学来代替的 (科学不是一个文制)。我们也不能拿西方的宗教来代替。”(《祀孔与读经》,载王兴国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牟宗三卷》,页415)。《五经》所代表的圣人之教是普遍的、一般的不可须臾离的常道,不是诸子百家之“学说”,更不是一时兴起的某种特殊的“主义”或理论。“孔子是圣人,圣人是没有什么学说的”〔64〕。
牟先生论汉代以来之尊孔曰:“这不能完全是统治者的自私,统治者的利用。因为尊崇维护五伦之教,不会单是自私,单是利用。就是动机是自私,结果也是公。就是利用,也是上上下下,大家都要利用,不光是单有利于某一人。因为这是上上下下的一套生活方式,所必共由之道。”〔65〕
针对清末民国以来知识分子罢科举、废读经之声,牟先生诘之曰:“清末民初以来的智识分子,个个都是空前绝后,不识大体,不知谋国以忠之义,所以才不了解儒学的文制意义,也不知道文制的重要。自清末废科举兴学校以来,随着来的就是废除读经……为甚么有了学校就得废除读经?当时废除读经尊孔的理由是:孔孟之学在汉代以前只是诸子之一,我们现在没有定尊它的必要,应当还它原来之旧,让学人自由去研究。这一方面倡导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其理由好像很正大,可是另一面,就是拿‘个人的思想理论’的观点来看一切学术,这一个观点是害事的,就是不识大体的。当然,如果学校是研究学术的机关,自然须让学人自由研究,人的精力有限,研究其一,不必研究其他。但是学校与研究,不是唯一的标准。如果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认识到立国之本,出之以‘谋国以忠’的态度,则学人研究虽可自由,而普遍读经不可废除。纵使退一步,大学废除,中小学亦当有个办法 (这不是关乎懂不懂的问题,凡是关乎这类性质的事,都不必一定要懂。念佛的人不一定能懂佛理。‘尔爱其羊,我爱其理’。同样,尔爱其懂,我爱其习)。再退一步,纵使整个学校废除读经,政府以及有识之士,立于国家之立场,也当该认识儒学文制的意义而有一个尊孔护持的办法,这才是谋国以忠,顾及千秋万世的用心。可是当时领导社会的思想家、教育家,却只是拿‘个人的思想理论’的观点来看一切学术,以诸子百家的态度来看儒家及孔子,遂轻轻把含有文制意义的儒学,维持华族生命已经数千年的忠信观念,一笔勾销了。这个无识不忠的罪孽,遗害不浅。”②《祀孔与读经》,载王兴国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牟宗三卷》,页414。按:正因废除读经,所以牟先生对蔡元培颇有微词:“这个人并不是任何一面都可以称赞的”,因为他也参加了“把中华民族的常道拉掉的行列”。又说:“民国以来的知识分子大都是有罪的。”(《时代与感受》,《全集》卷23,页369,372)关于“打倒孔家店”之说,牟先生反驳说:“他们根本不知‘孔家’根本没有一个‘店’,孔子仁义道德的教训只是把人人心中所固有的知忠知孝、能忠能孝的道德心指点出来而已。”〔66〕
(四)有限的政教合一
牟先生之“新外王”说不赞同国家中立、把道德信仰纯个人化私人化等西方自由主义者的主张③牟先生对现代“一切学术思想都只有个人的思想理论,道德宗教无其客观文制上的意义,只缩而为个人的”这种情况深致悲哀。参《时代与感受续编》,《全集》卷24,页84。,而是主张某种形式的“政教合一”。
首先,道高于政,道统高于政统,政治应该受到儒教之制衡;其次,政府代表民族国家,有权利和义务尊崇作为国教的儒教,应该把“祀孔读经”制度化为“文制”;第三,国家和政府对社会负有以儒教之基本人伦来教化国民之责。关于前两项,前文论之已详,以下对政府与教化之关系再作补充性论述。
在牟先生看来,如果仅有民主宪政、自由人权而无教化,则可能导致人的“物化”,甚至民主宪政也会因失其国本而朽坏。他说:“人无文化教养必物化,古人叫做‘化于物’。软性的物化,就是奢靡;硬性的物化,就是暴戾。一个有远见、有责任感的政府,在谋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就应该注意以文化‘教养’为主,使人民免于物化的文化建设了。”这里的“文化建设”当然不只是普通的知识技能上的教育工作,而主要是指道德人伦方面的教养,即几千年来“人文化成”、“化民成俗”意义上的“教化”。牟先生接着说:“孟子所说舜在禹平定洪水之后命契为司徒,行五伦之教,使民‘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而免于禽兽化 (即物化),便是我国历史上中央政府第一次有计划有目的的文化建设。”牟先生认为,现在的政府也应该承担起这种教化之责:“今天的问题,同样也是如此,中央政府的文化建设仍是要用这五伦之教来使人民从奢靡与暴戾的物化陷溺中解放出来回归到做人的本位上。也就是古人所说‘复人道之正’。”〔67〕
牟先生在主张政府膺有教化之任的同时,又对政府在教化上的职权范围和执行方式作了明确的限定。这些限定大致可归三项:一先富后教,二教以基本的人伦,三不能“君师合一”。“先富后教”是孔子明言,自不待论。①牟先生认为,“先富后教”中之“先后”是“着重义,不一定是时间上的先后”。(《政道与治道》,页108)“教以基本人伦”,是指政府不能在道德上对百姓作过高要求,“不能在政治上责望人民做圣人”。因为个人道德实践上的道德与政治教化上的道德不同,前者是以成圣为宗极的无限过程,须“由自己存在的主观方面以无限的精诚、甚深的悲愿以赴之”,后者“只是维持一般的人道生活上的规律。此只能对之做外在的维持:既不能内在地深求,亦不能精微地苛求”。否则,就荡越了“政治上的教化意义之大防”,即成极权、泛道德主义〔68〕。不能“君师合一”,意即在宪政政体下,政治人物不可同时即是教主,宗教领袖不能同时即是政治元首②牟先生说:“若想兼善天下,从事政治,则必须遵守政治之常规;教主之意识必须废弃。”(《时代与感受》,《全集》卷23,页270),应该“君师殊途,二元骈行”。牟先生认为,个人自己实践上的人格成就,无论怎样伟大与神圣,当在政治上发挥时,都不可慢越上述限制,而且以其伟大的人格来成就这些限制。“能成就这些限制,在古人就称他是‘圣王’;在今日就称他为大政治家。否则,在古人就叫他是霸者,是暴君,是独夫;在今日,就叫他是极权专制者,独裁者。”〔69〕此外,牟先生还认为,在宪政之下,教化方面的“文化建设”事业,政府不宜全面包办、过多干涉。他大概倾向于在政府提倡、支持下以社会力量为主体来进行。他说:“若一切都交给政府,这又是最不现代化的。那么谁来做这个工作呢?这要诉诸大家的自觉,诉诸大家清明地理性地反躬自问。”显然,牟先生也感到此问题有些棘手。1981年台湾行政院下设的文化建设委员会成立,牟先生建议由文化建设委员会负责提倡、监督,由教育界来落实〔70〕。
如所周知,牟先生之“新外王”是由良知之坎陷以开出“对列之局”、由“理性之内容表现”转出“理性之外延表现”而达成的。“经过外延的表现、形式概念之限定,则政治是政治,教化是教化,政治自成一独立领域,自不可涉教化”〔71〕。如此,与上述政府膺教化之责之说是否龃龉?本文认为,政治不涉道德教化,是从政治之所以为政治、政治自身内在之“形构之理”上说的,是着眼于“政治”自身之“局部”分析地言说的。“政府膺教化之责”是关涉到民族国家之“自尽其文化生命之性”、“存在之理”而说的,是着眼于“生活之全”综合地言说的。两者言说分际不同,并非逻辑上有矛盾。此义可从牟先生下面的话中看出。他说:“政治既入近代而有其独立的意义,则暂时与道德分开,亦仍是可以说的。但须知这种分开划开,是因政治有独立的意义与境域而可以纯政治学地讨论之之‘政治学上的权法’,在此独立境域内,不牵涉那形而上的道德理性,而使民主政体内各种概念清楚确定。这种清楚确定亦不过是为名言的方便,名言上的清楚确定,即不必牵连那么多,只在民主政治的大括弧下就对等平列的事实而确定地说出就够了。这只是政治学教授的立场,不是为民主政治奋斗的实践者的立场,亦不是从人性活动的全部或文化理想上来说话的立场,所以那种清楚确定只是名言上的方便……忘掉前人的奋斗,始只停在观解理性上,囿于政治学教授的立场,遂只割截地把自由下散而为诸权利,并以为一上通着讲,便是抽象的玄虚、形而上学的无谓的争论。这还不算,并以为一通着道德理性、人的自觉讲,便成为泛道德主义,有助于极权,这都是在割截下只知此面不知彼面为何事的片面联想。”〔72〕
可以看出,在牟先生之“新外王”说中,政教是有限的分离,当然也是有限的政教合一③牟先生亦称其为政教之“外在之合一”。详参 《历史哲学》,页244。。
五、结语:“内圣外王合一之教”
本文第三、第四两部分旨在证成牟先生“新外王”之为儒教宪政的第四个条件:儒教与宪政之互相联结。果能成立,则牟先生之“新外王”可得一新解。牟先生曾说:“儒家‘仁者德治’的政治思想不是不对,而是不够。”〔73〕“配合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新外王的精神,需要重新去完成儒家的内圣外王合一之教。”〔74〕本文认为,牟先生之儒教宪政说,即是此“内圣外王合一之教”之结晶。它是传统“内圣外王”之重建。其重建之道是在内圣与外王之间增补一层“中间架构”④牟先生说:“圣德人格之感召不需要有媒介,所以他的‘所过者化’完全是理性的作用表现,不需要借助于架构表现,这完全是超架构表现的。这种境界以及达到此种境界的学问与工夫是中国文化生命的领导观念。”(《历史哲学》,页41)但是,这种领导观念是有局限性的:“知性方面的逻辑数学科学与客观实践方面的国家政治法律 (近代化的)虽不是最高境界中的事,它是中间架构性的东西,然而在人间实践过程中实现价值上、实现道德理性上,这中间架构性的东西却是不可少的。而中国文化生命在以往的发展却正少了这中间一层。”(《历史哲学》,页173-174)。这一中间架构为的是道德理性之“体”能广披地、积极地“繁兴大用”,它体现的是“现代性”之工具理性之能,犹如传统之手艺之进入现代化之机械制造。借助机械之制造,虽然因其“机械性”而有损“称手”之妙,然而却能突破徒手之限制而提高其效能。同样,“中间架构”虽然减少了“圣君贤相”格局下一心“所存者神所过者化”之妙,但是却能使道德理性客观化而成为贞定、厘整社会各方面之常规。“中间架构”根本上是道心之坎陷所成就者。然此“坎陷”只是道德主体暂时退归于认识主体之后而成为认识主体之支持者,并非道德主体之泯灭。必要时道德主体可以自我觉醒以调整架构运行之偏差或副作用,犹如可以用手工随时调整机械制造过程中的故障一般。最高之道德主体为“能主宰其自身之进退与认识的主体之进退者”〔75〕:道德主体之退与认识主体之进,成宪政之“方以智”;道德主体之进与认识主体之退,见儒教之“圆而神”①此亦即中西文化交融所当成就之人类政治前景者。牟先生说:“以内容的表现提撕并护住外延的表现,令其理性真实而不蹈空,常在而不走失;以外延的表现充实开扩并确定内容的表现,令其丰富而不枯窘,光畅而不萎缩。”(《政道与治道》,页135)。此为儒教与宪政联结之奥窍。
牟先生之儒教宪政思想前承清末立宪运动、民初孙文 《建国大纲》之目标,其学理上之发明可谓深根宁极,夐出尘表,然于具体制度之构建上则只可谓其略见大意,粗具轮廓,有待来者之补苴、充实和完善②致力开发“儒教宪政”的当今儒者蒋庆先生无疑系继起此大业者中的翘楚。有论者曰:“牟宗三对于西方民主之批评及其转进,有可能曲通蒋庆的政治儒学,或者说,蒋庆的政治儒学应是牟宗三思路的必然引申。”(张晚林:《政治的客观性及其转进——牟宗三对中国传统政治困局问题的探索》,《天府新论》2015年3期,页64)。
参考文献:
〔1〕顾肃.自由主义基本理念 〔M〕.译林出版社,2013.146.
〔2〕〔美〕柯恩.论民主 〔M〕.聂崇信等译.商务印书馆,2007.10-11.
〔3〕〔德〕康德.永久和平论 〔A〕.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C〕.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108.
〔4〕王瑞昌.尤根·赫曼森民意“驯服”思想述评 〔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9,(5).
〔5〕〔7〕〔12〕〔19〕〔24〕〔25〕〔26〕〔27〕〔28〕〔34〕〔35〕〔58〕〔62〕〔64〕〔66〕〔67〕〔70〕〔74〕牟宗三.时代与感受 〔A〕.牟宗三先生全集:卷23〔C〕.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401,20-21,208,420,208,348-349,22,22,26,36,23,208,206,371,429,442,391-392,372.
〔6〕〔8〕〔21〕〔31〕〔33〕〔42〕〔49〕〔53〕〔61〕〔75〕牟宗三.时代与感受续编 〔A〕.牟宗三先生全集:卷24〔C〕.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282,280,145-146,280,436,140-141,79-85,438,437-438,177.
〔9〕〔10〕〔32〕〔50〕〔54〕〔55〕〔57〕〔68〕〔69〕〔71〕〔72〕牟宗三.政道与治道 〔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23,104、109,134,33,149-150,153,新版序22,107-108,108-109,106,52-53.
〔11〕牟宗三.时代与感受续编 〔A〕.牟宗三先生全集:卷24〔C〕.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288;牟宗三.政道与治道 〔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53.
〔13〕〔14〕〔18〕〔37〕〔40〕〔45〕〔46〕〔47〕〔48〕〔52〕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 〔M〕.台湾学生书局,1992.199,104-105,152-153,11-12,230,259,230,242-243,155,153-154.
〔15〕〔16〕〔29〕〔30〕〔36〕牟宗三.牟宗三先生晚期文集 〔A〕.牟宗三先生全集:卷27〔C〕.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455,457,494,495,494.
〔17〕〔20〕〔39〕〔51〕牟宗三.生命的学问 〔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24,85,33-34,62.
〔22〕〔23〕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 〔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02-103,93.
〔38〕〔60〕牟宗三.人文讲习录 〔A〕.牟宗三先生全集:卷28〔C〕.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4,3-5.
〔41〕〔59〕〔73〕牟宗三.历史哲学 〔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67,245-246,119.
〔43〕唐君毅.中国历史之哲学的省察——读牟宗三先生 《历史哲学》书后 〔A〕.牟宗三.历史哲学 〔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62.
〔44〕〔63〕〔65〕牟宗三.祀孔与读经 〔A〕.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牟宗三卷 〔C〕.王兴国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417,413,414.
〔56〕蒋庆.再论政治儒学 〔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39.
(责任编辑:赵荣华)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了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社科计划重点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编号:SZ20161003824)的资助。
[收稿日期]2016-05-15
[作者简介]王瑞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北京 100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