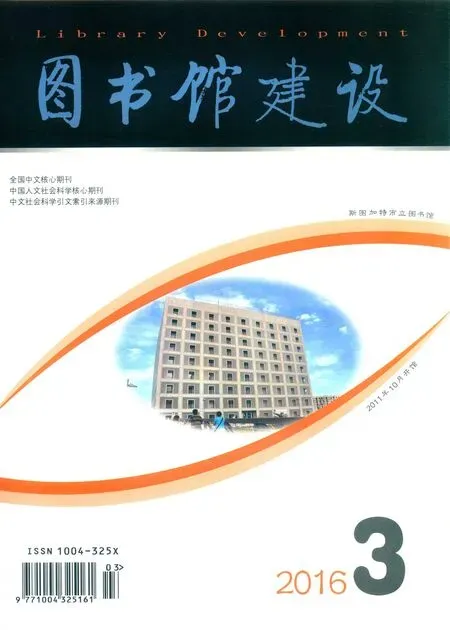论本土知识的数字化处理*
胡立耘(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论本土知识的数字化处理*
胡立耘(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云南昆明650091)
[摘要]本土知识数字化是保存和利用本土知识的有效方式。本土知识数字化处理措施包括对本土知识的收集、选择、描述、存储、传播等各方面。在本土知识数字化处理过程中,其中的技术—社会问题值得关注,包括:本土知识收集中的多种资源形态并存、多元收集渠道的选择,本土知识的信息组织中对待本土语言的立场、元数据方案中的本土因素考量、本体及概念图的应用,本土知识管理系统建设的特点,以及本土知识资源中心的发展等。
[关键词]本土知识 数字化 信息组织 信息管理系统 本土知识资源中心
本土知识(Indigenous Knowledge,简称IK)是特定区域内特定群体所具有的传统知识。本土知识在广义上包括基于传统的各种技能、观念、经验和文学、艺术表达,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革新与创造;在狭义上则主要指与本土生存和发展相适应的技术、经验和认识。不同的机构及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对本土知识进行了界定[1]。与本土知识相关的术语还有本土知识系统、传统知识、地方知识等。在一般意义上,这些概念被互换使用[2]。有学者认为,本土知识甚至可与文化知识、民间文化交替使用[3]。本土知识作为与科学知识并行存在的知识,是本土人民文化认同和传统承继的依据,是本土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并在农业、医药、自然资源管理、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具有科学创新价值。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银行(World Bank,简称WB)、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简称UNESCO)、联合国本土人民工作组(United Nations Working Group on Indigenous Populations,简称WGIP)、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简称WIPO)等国际机构纷纷出台与本土知识有关的相应规定、文件,并积极支持本土知识的数字化。WB发起了本土知识计划,建立专门的数据库收集本土知识实践经验[4]。WIPO开设了传统知识网关,登记各国的传统知识数据库以供检索[5]。UNESCO建立了本土知识最佳实践数据库(IK Best Practices),收录本土知识案例[6],在世界记忆项目、非物质遗产项目中也可看到对本土知识数字化保存的强调。2002年,国际图联(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简称IFLA)和国际出版社协会(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ssociation,简称IPA)继UNESCO的《保存世界记忆宣言》发布后,发布了《永久保存世界记忆:关于保存数字化信息的联合声明》[7];同年12月,IFLA发布了《本土传统知识宣言》,明确指出,应保存、推广、传播本土知识与传统知识,并维护本土人民的本土知识使用权利与知识产权惠益[8]。美国、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菲律宾、印度、韩国、乌干达、南非等国纷纷启动了本土知识数字化项目。本土知识数字化出于多种目的,有的是为了对本土知识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如印度的传统知识数字图书馆(Traditional Knowledge Digital Library,简称TKDL)的建设[9];有的旨在将本土知识纳入国家知识系统中,如南非的本土知识国家战略[10];有的是为了科学研究、文化产业建设、地方经济振兴等。本土知识数字化项目由多方驱动,有的是从下至上的本土诉求,由社区自身建设,由本地人参与收集、使用和学习本土知识;有的是商业驱动,由企业(如医药机构)负责;有的是学术驱动,由学术机构组织;有的基于资源发现的目的,由文化收藏机构或数据服务公司进行公共或商用数据库开发。
本土知识数字化包括对本土知识的收集、选择、描述、存储、传播等各方面。与科学知识的客观、可验证、普适、易编码等特点不同,本土知识具有整体性、即时性、直观性、口头性、经验性、在地性、代际延续性等特点,这些特点导致了本土知识数字化并非如科学知识数字化一样能够客观、无损地直接收集与转换。因此,尽管本土知识数字化具有与科学知识数字化类似的流程与方法,但在数字化过程中需充分尊重本土知识的独特性,体现本土知识在其所处的文化生态系统中的实际情境。
1 本土知识的收集
1.1本土知识的资源形态
本土知识的传承与传播主要有3种形态 :文献形态、非物质形态、实物形态。文献形态是指承载在各种载体上的记录,包括民族文字资料及由田野调查者、旅行者、研究者等以各种技术手段记录下来的文献,类型多样,既有报刊、图书、古籍、手稿、抄本、相片、地图、拓片等书面文献,也有录音、录像、电视节目片段等模拟型及数字型文献。非物质和实物形态的本土知识,是通过口头传统、生产技术、生活习俗、交际仪礼、节日庆典、宗教仪式、表演艺术、社会风俗、手工技艺等非物质形式,或通过如民居、雕塑、碑刻、设施、服饰、器具、工具、工艺品等物理形式承载的活形态知识。
如何收集口头资源的本土知识是本土知识数字化的关键。口头资源由口头传统和口述历史组成。口头传统是由长者和能人传递的特定族群的文化传统,记录这种口头传递的故事,可保存个人、家庭、社区和社会的信仰、实践等基本知识。口述历史记录的是叙述者个人及所处社区的各种事件和事务的记忆、经验、反响,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方法,用以了解本土人民关于文化、经济、教育、健康、家庭、自然资源及社区管理等丰富的历史与文化传统,提供对未曾被以文献方式记录的事件的重构。数字技术的普及使口头文化和实物文化能及时被记录并以接近原样的方式得以呈现和传播,通过数字技术,口头资源以音频或视频方式进入文献系统,可保存更加丰富的信息。例如,可捕获面部表情、身体语言、姿势等在传达语言和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细节,为口头资源提供语言以外更真实、更生动的内容。数字化的本土知识既具有口语、展演或实物的直观性,又能像文字符号一样跨越交流的时空限制。
1.2本土知识数字化资源的收集
本土知识与文化传统、历史变迁、日常生活、宗教信仰、自然资源密切关联,既包括传统故事、歌曲、舞蹈、仪式等形式的文化遗产,又包括传统医药、食品、农业实践、传统工艺等方面的潜在的可专利化的知识,因此需要设计合适的方案来选择、说明、记录、描述和传播这些知识,避免触犯文化禁忌,防止内容被滥用和误用。例如,档案馆和图书馆拥有大量关于本土知识的描述,大部分是过去对本土人民进行管理而产生的。这些文献中,本土人民被对象化,本土人民自己的声音被忽略了。大量人种志研究、旅行者故事、官方报告等,在记录、选择、编辑和翻译的过程中被导入编纂者自己的观点,以他者的眼光呈现,其中有价值的部分虽具客观性但并非中立,虚构的部分甚至把本土人民描写为异国情调或野蛮的另类,包含着知识权力对本土知识的压制。这些资料即使记录了本土人民业已被异质文化的干扰或部分失传的语言或文化,但仍不可作为本土人民的真实观点被接受。在搜集过程中需要甄别过时的、种族主义的、贬低的、性别歧视的、滥用的和不正确的表述。
在本土知识数字化资源的收集过程中应特别注意的问题包括:首先,应征得本土知识持有者的许可和信任。数字化项目应考虑本土人民的利益,应得到本土社区的认同,与社区达成互信;关于数字化项目中的内容选择标准、权重,应咨询本土专家,应得到社区的支持,由他们决定选择哪些本土知识进行记录,以及决定如何将他们的知识呈现、传递,以保证本土资料的安全性、真实性、整体性。其次,鼓励社区参与,在项目设计中的规划与审定、项目进程中的决策与选择、项目评估中对项目成果的利用与反馈等环节,都应吸纳本土成员的参与。让本土人民在参与过程中,评价、补充相关内容,在已有收藏的基础上附加更多的本土价值,激发本土人民尊重和利用本土知识,促进本土人民的能力建设。第三,以各种形式与媒体创建、共享本土知识。不同社区应因地制宜地选择收集本土知识的方式,有些本土知识需要以图表绘制,有的需要用视频呈现,有的以口述历史传递,有的通过表演展现,有的则需演示。有时通过社会服务项目(如在Web课程、展览、制作广播节目和印刷出版物等过程中)收集;也可采用故事、歌谣、短剧等方式获取本土知识中的关键信息。例如,采用数字故事讲述的方式使本土人民“自己讲述自己”并上传到网络数据库,既有利于自我记录与发布,又有利于分组协同学习。再如,使用iTunes或类似数字媒体播放工具,由用户自己通过计算机及辅助设备记录歌谣、故事、技艺展示等。
1.3本土知识的存储方式
识别和优化所获取的本土知识资源,需要对用于记录和存储数据的各种数字技术和环境加以比较和评估。鉴于本土知识的口头特性,声像数字记录装置(如数字摄像机、数码相机、录音设备)是获取本土实践、技巧、歌谣、语言、故事和舞蹈等的基本工具;扫描仪常被用于照片、手稿、地图和历史文献的数字化,3D扫描适用于产生物体的三维数字图像。但有许多问题需要考虑,如声音可保存为WAV和MP3格式,视频内容可采用QuickTime、MPEG-4、MPEG-2等多种格式,存储介质可以是DAT、CD、DVD、存储卡、硬盘,记录环境有录制间、田野情境、表演现场之别,内容可原样呈现也可适度编辑。如何选择,需要依赖于特定项目分析及社区需求分析,需根据数字文档的物理存储机制,使数字文档保存策略能在符合社区的实际条件的基础上,尽可能达到通行、兼容、可用。此外,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还应充分考虑记录的数字迁移,及时对数字文档格式加以转换。
2 本土知识数字化中的信息组织
2.1语言选择
为了体现社区参与,本土知识数据库的设计要求优先考虑本土语言。应尽可能以本地语言收集和呈现本土知识,必要时对所收集的内容进行翻译。在本土知识数据库中,可通过词表实现本土语汇/其他语种及方言/正式用词的转换,为跨语言信息检索打下基础。例如,“中国中药专利数据库及其检索系统”(Chinese TCM Patent Database,简称CTCMPD)开发了中英文双语系统[11-12],并嵌入了中药材词典数据库以便进行中药材名称的拉丁文、英文及中文检索,被认为是传统知识数据库领域的典范之作,得到了WIPO及美国专利商标局的高度评价。另外,由于理解本土知识需要文化情境,除了编制不同语种的词汇对照表外,有些无法准确翻译的词汇或内容应加以注释或链接相关图示、动作示例、说明材料,以便于跨文化信息检索。
2.2元数据
本土知识的信息组织既要考虑通用性又要充分考虑其自身特点。对数字化对象进行描述的元数据设计应尽量选择复用或改造通行的元数据方案。在本土知识数字化中常用的描述元数据方案包括MARC(Machine Readable Cataloging Format,机读目录通讯格式)和DC(Dublin Core,都柏林核心)及用于档案的EAD (Encoded Archival Description,档案描述编码格式),用于教育的LOM (Learning Object Metadata,学习对象元数据),用于文本的TEI(Text Encoding Initiative,文本编码倡议),用于视觉文献的VRACC(Visual Resource Association Core Categories,美国可视资料协会核心类目),用于地理空间的CSDGM(Content Standard for Digital Geospatial Metadata ,数字地理空间元数据内容标准)等。数字化的本土知识系统可存储在不同的机构或数据平台中,如既存于本土社区,又存于学术机构或其他利益相关方,还可整合于图书馆或其他收藏机构的数据平台,应尽可能考虑元数据标准及互操作。例如,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开发的用于文化传统领域的数据库,采用了OAI-PMH (Open Archives Initiative Protocol for Metadata Harvesting,开放文档协议),收割了来自39个机构的元数据,目前包括了超过两百万条DC元数据记录[13]。
本土知识的信息组织者在考虑与标准化元数据兼容的同时,应根据收藏对象及收藏的本地需求调整元数据。例如,在本土社区,亲属关系、年龄层次、社会角色分工等具有特定的意义,设置权限元数据可支持这种概念体系,使数据库的资源在社区既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传播,又具有文化适当性。所谓文化适当,是指人们遵从本土民族的习惯法或文化禁忌,如有些神圣内容不能为本族以外的人所知晓,有些内容只在男性长者中传承,有些歌谣不能在家庭异性长者面前歌唱,男人不能观看女人所举行的某种仪式等。系统设计时需根据本土文化传统、习惯法和知识产权要求,咨询本土社区的传统拥有者,规定本土知识库中资源被查看、下载、修改、编辑等操作的权限。用户是否为特定社区或部落成员,在社区或部落中的地位、角色、性别,与资源中描述的人、动物或物体的关系等特征,都是决定其权限的参考因素。澳大利亚Pitjantjatjara社区设计的Ara Irtitja档案与传统知识系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采用权限元数据反映由性别、家庭谱系、部族关系等构成的限制来决定用户检索系统的不同层次,以满足资料的文化敏感性[14]。
本土知识系统设计还可考虑用户贡献元数据的机制,允许本土社区成员以自己的语词来标注特定资源,上传资料、添加文字说明或口头说明的录音。尤其是添加用户的录音,允许人们以自己的词汇和语言表述自己的故事,这对文化程度不高或不同语种的用户利用数据库表达其观点十分有利。
此外,在本土知识数据库中将元数据与地理信息系统结合,有利于更好地揭示本土知识的特定内容。加拿大、美国等国家都有许多成功的案例[15]。土地不仅与本土人民的生存与生活相关,而且是他们的精神与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建立基于社区地图的数字化项目,有利于描述和管理本土边界,明确社区的土地、渔、猎领地所属权,对社区的自然资源进行管理,还可用来标记具有文化意义的地点或风景、记录动植物分布及本土生物多样性知识、进行森林防火管理[16]。
2.3词汇控制
为了提高检索效率,保证本土语言的跨语言检索和跨文化理解,在本土知识数据库建设中,有必要开发和使用基于本土知识体系的分类表和主题词表。(本土知识体系的)词汇控制可通过开发特定的词表或类表,也可对已有的受控词表作相应的改进。例如,澳大利亚的《ATSI叙词表》(ATSI Thesaurus)拓展了美国国会标题表(Library of Congress Subject Headings,简称LCSH),补充了与本土知识领域相关的词条及词表结构,高度本土化的则增用一些本土语词及增加分类号[17];其修订版名为《AIATSIS叙词表》(AIATSIS Thesauri)①。该词表提供主题词表、语言词表和地名词表,在语言词表方面,列出了250多种澳洲特有的语言,包括不同语言的各种拼法及其语支;地名词表中有本土地名及非本土的对照名称[18]。语言和地名词表与地理空间关联,可提供地图浏览,依照本土视角的地理知识进行本土称谓和家族历史检索。该词表已为澳大利亚各图书馆所使用[18]。再如,新西兰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协会、全国毛利图书馆与信息工作者协会共同开发了《毛利标题表》(Mori Subject Headings,简称MSH)运用于各图书馆。2008年,新西兰国家图书馆与Taranaki部落合作,开发了Taranaki毛利数字档案馆,该数字档案馆除了采用《毛利标题表》外,还增加了该部落方言的相关词汇,以便人们用毛利语检索资源;所有关于毛利人的出版物,包括早期出版的相关材料,都依据该词表标引了主题词,并纳入编目系统中[19]。
2.4本体及概念图
本土知识与现代科学知识是两个不可通约的本体,当一个知识系统被包容或解释成另一个知识系统,会导致不兼容,如关于时间、空间、宇宙的概念等。对本土人民而言,人造传统、人文传统与自然环境相互关联,一个文化物件的描述、分类与其传统不可分离,如物候历中动植物的作用,巫术或法事中道具的意义等,与现代科学文化语境是全然不一致的。在本土语言中,一个语词可能是一个人的名字,也可能是地名、仪式行为、物件,或者是人与图腾的某种特定联系。一个人或人群在不同的语境中可被指称不同的名字。因此,神话、亲属关系、土地归属等尽管有不同的视点,其相互关联构成了语义之网。在数字化过程中,本土知识可能被简单化和重新组合,造成对传统知识的理解破裂,因此,本土知识数据库建设应充分考虑本土人民与世界联系的表达方式,凸显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涵与意义。构建本土知识本体有利于呈现本土社区的文化—技术联系,反映本土观念及文化的复杂性。出于特定
ā的文化情境和利益立场,不同的本土社区在环境状态、农业和森林、基础社会服务、语言文化艺术等方面各具特点,应设计特定的本土知识本体,定义相关概念,指引各种概念之间的联系,以便信息组织达到更为准确的效果。
由于部分本土人民识读能力有限,而且其对事物与概念的认识具有直观性,在信息组织过程中,还可用视觉化技术揭示本土知识中特定的文化内容。在数据库中,对于与本土文化和观点相联系的关键内容,如图腾、神圣仪式、亲属关系等,用地图、家谱、概念图等多种形式进行视觉呈现,并辅以相关图片、文献、多媒体资源及其他网络收藏的链接,在数据库和网站设定认知地图,揭示本土文化中各种知识元素的相互关联。具体做法是邀请本土人民链接图片、舞蹈、声音、地点、故事线和踪迹,形成一个有意义的网络[20]。设计认知地图必须了解该本土社区长期以来积淀下来的宗教、哲学、伦理、规范等组成的规则,反映本土社会中不同的学习方式,尊重本土社区中不同层次的知识/诀窍拥有者的意见,体现知识链接在特定的社会文化逻辑中所产生的意义。类似的认知图方式还有深图技术(Deep Mapping),如斯坦福大学的Michael Shanks团队编制Traumwerk软件用于深图开发[21]。深图将不同的地图技术组合起来,如将航空图、照片、田野工作记录组合在同一个场景中呈现不同的意义,在地图上将历史与现在、口述资料与回忆资料、文献与个人感受等任何关于特定地方的材料并置和交互,以记录和描述该区域。
3 开发本土知识管理系统
3.1系统特点
一个成功的本土知识管理系统应符合本土社区的实际情况,具有以下特点:(1)简单的用户界面。许多潜在用户计算机素养偏低、键盘操作能力有限、识字少,因此,系统应有简单直接、用户友好的界面。(2)健壮性。由于预设用户没有足够的计算机经验,系统应能承受多种非预期的输入及其他操作,并易于恢复。(3)安全性。由于本土知识中存在神圣或秘密内容,系统应保证数据库的使用与网络传输有可靠的安全机制。(4)弹性。系统应全面考虑在本土社区中与传统相联系的相关概念,并提供相应的管理工具,以便提供最大的弹性修改相关设置,使软件易于定制。(5)动态发展的可适应性。本土知识系统和基础架构应有弹性和实用性,能可持续发展,整合新的技术。(6)互操作性。软件工具应建立在国际标准上以保证各数据库间可互操作,以及在不同平台和操作系统上运行,以便达到最大程度的共享。(7)低成本。尽量使用便宜、免费的、开源的、可组合的、广泛为本土和草根社区所接受的软件。系统多采用一系列的开源软件加以组合,或改造免费数字图书馆软件,如Fedora Commons、DSpace、Greenstone等常被用于本土知识管理系统的开发。
3.2实例
Stevens对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的本土知识管理项目进行了考察,发现可采用不同的方法和工具来管理本土知识,以保护口头传统和信仰系统,并分析了基于本土的数字化项目所存在的技术条件、安全性、可获取问题及其解决方案[22]。美国的史密森纳美洲印第安国家博物馆的文化中心开发了一套经济、简单和健壮的软件工具来描述、标注和管理多种类型的本土知识的数字和物理对象,其检索、浏览和演示界面提供了丰富的用户体验[23]。在澳大利亚的坤堪(Quinkan),研究者与当地长者一起合作以数字化保护岩画艺术,开发了名为Matchbox的编目系统,使用被修饰的DC元数据来描述资源[24]。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本土知识管理软件是IKM(Indigenous Knowledge Management),该软件系统是一套开源软件系统,成本低、简单而健壮,提供DC作为缺省的元数据框架,扩展了权限元数据。该软件可供本土社区开发、维护和保存本土知识并定义与本地习惯法相符的获取限制和权限管理。搜索界面支持本土社区获取内容的需求及用户交互需求,除了提供基于文本或关键词检索、浏览多媒体资源外,还可开发与地图、时间表、年谱、词表或本体关联的检索机制,并提供注释和讨论工具,最大限度地允许用户根据自己的意图创造性地关联和注释资源集合[25]。基于本土需要的TAMI则独具特色,TAMI代表文本(Text)、声音(Audio)、电影(Movie)和图像(Image),是一个保护北部澳大利亚本土语言、文化和环境的本土知识数据库项目。其基本特点是没有预先设定元数据框架及分类范畴,检索方式是对所有资源略图的浏览,相对于常规的数据库,TAMI缺乏框架和结构对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预期关联,看似缺乏逻辑,但它依据的是本土的认知和产生知识的方式与结构,用户成为设计者,检索、收藏、下载、编辑所需资源,并可对收藏进行分类及标注关键词。最大限度地允许用户根据其自己的意图创造性地关联和注释扁平化的资源集合,文盲和文化水平低的人也可使用它[26]。
4 设立本土知识资源中心
本土知识资源中心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在本土社区设立的为本土人民提供服务的中心,一种是本土知识资源的收藏与研究中心,二者相互关联。
4.1社区中心
基于社区的本土知识资源中心负责获取与收藏丰富的本地历史和社区传统,在澳大利亚,本土社区常常将本土知识中心以本地语言命名,如Wujal Wujal社区把他们的知识中心命名为Binal Mungka Bayen知识中心,并开发了识字和识数方面的教育项目,有68%的社区成员使用该中心[27]。该本土知识资源中心的核心任务是识别、收集、记录、存储本土知识并提供给本土人民检索、传播与利用。通过建立本土知识资源中心,数字内容被集中呈现,这些内容有的来自本土收藏,有的来自私人或机构的捐赠,有的原先被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教堂、社区成员、人类学家收藏,后被返还给社区。在数字时代,一些本土知识学术研究机构、文化收藏机构将馆藏本土知识资源数字化后,以数字复本的方式回流到本土社区,这被称为虚拟返还。虚拟返还使得更多的本土资源为本土人民重新拥有。
建立基于社区的本土知识资源中心需要分析社区需求和中心的目标,以决定用何种合适的软件来支持本土知识库的建设。例如,澳大利亚北部地区的一个本土社区Warumungu开发了名为Mukurtu Wumpurrarni-kari的档案系统,系统包括相片,数字视频,声音文档,文化物品的数字图像、文献等,并根据文化敏感性进行了相应的权限限制,用户可对资源加以评论和叙述,同时,计算机技能低的人也能使用该系统[28]。
4.2收藏与研究中心
本土知识资源收藏与研究中心一般设立在大学、研究机构或文献收藏机构,Warren等勾画出了本土知识资源中心的基本功能,包括本土知识文献化、使所记录的知识被存储和为人们所利用、设计教育材料并开展培训工作、使更多的人了解如何记录本土知识、促进国家和国际网络的信息交换[29]。
本土知识研究资源网络建设是传播最佳实践的有效途径,越来越受到重视。例如,著名的国际性本土知识网站——国际研究与咨询网络(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Advisory Networks,简称CIRAN,http://www.nuffic.nl/ciran/),旨在增进国际本土知识网络的信息交换,其资源按主题、地区、信息来源加以组织,包括本土知识项目、最佳实践、相关组织和网络、电话、会议等内容;本土网(Native Web,http://www.nativeweb.org),是一个国际性的非营利教育组织,旨在用电信技术传播世界各本土地区、本土人民、本土机构的信息,研究本土人民对技术与互联网的使用,提供资源、指导和服务来促进本土人民使用信息技术以及本土和非本土人民的交流;本土人民相关问题与资源网(Indigenous Peoples Issues & Resources,http://indigenouspeoplesissues.com/),整合了期刊、视频、电影、声音记录,会议、工作坊等资源,覆盖北美、南美、澳大利亚、非洲、欧洲、中东、东南亚、 中亚等地区。此外,还有农业与乡村发展本土知识中心(Centre for Indigenous Knowledge for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简称CIKARD,http://iitap.iastate.edu/cikard/cikard.html),世界本土知识研究中心(Centre for World Indigenous Studies,http://www.halcyon.com),本土门户(Indigenous portal,http://www.indigenousportal.com)等。
5 结 语
本土知识数字化建设是发现、评价、保存、推广本土知识的重要手段,对于促进本土发展、保护本土权益、弘扬传统文化、丰富人类知识体系等均具有重要作用。本土知识数字化有利于协调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本地与西方的多元张力,实现本土知识的有效保护和全面利用。
数字化系统并非客观的转换工具,本土知识的数字化并非简单地将本土知识作为一种知识集合纳入信息系统以使之合法化并整合到科学系统的框架内。本土知识数字化蕴含了关于真实世界及知识的本质的、特定的文化与历史的设定。文献的重新媒体化及时间的变迁,都可能导致材料意义的改变。计算机上的信息与实践中的知识并不是一回事。本土知识数字化并不是把本土知识作为过去的存留而被冻封式保存,而是要把它放在当代及后世的时间轴中,联系全球背景来考量其与本土利益需求的相关性。本土知识数字化首先应探询的是本土人民关心和期望的是什么,如何保护本土人民最为关切的本土知识;其次才是本土知识有什么用,如何利用。这要求从知识、历史、文化、传统、法律、规范、技术等多种视角,广泛地思考不同的文化和知识传统及其所联系的社会机构,本土人民政治和文化语境等问题,从而使数字化成果既能在本土社区充分发挥作用,又能在全球知识系统中彰显其独特价值。
注释:
①AIATSIS即澳大利亚原住民与托雷斯海峡岛民研究所,是致力于研究、收藏、出版澳洲本土文化的机构。
参考文献:
[1]张永宏.本土知识概念的界定[J].思想战线,2009(2):1-5.
[2]Boven K,Morohashi J.Best Practices: Using Indigenous Knowledge[EB/OL].[2015-08-11].http://www.Unesco.Org/most/bpindi.htm.
[3]Agrawal A.Indigenous Knowledge and the Politics of Classification[J].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2002,54 (173):287-293.
[4]World Bank.Indigenous Knowledge Program[EB/OL].[2015-09-21].http://www.worldbank.org/afr/ik/what.htm.
[5]WIPO.Online Databases and Registries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 and Genetic Resources[EB/OL].[2015-09-21].http://www.wipo.int/tk/en/resources/db_registry.html.
[6]UNESCO.The Management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s (MOST) Programme[EB/OL].[2015-08-20].http://www.unesco.org/new/en/social-and-human-sciences/themes/most-programme.
[7]国际图联和国际出版社协会筹划领导小组.永久保存世界记忆:关于保存数字化信息的联合声明[EB/OL].(2002-06-27)[2015-08-20].http://archive.ifla.org/V/press/ifla-ipa02-cn.pdf.
[8]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IFLA Statement on Indigenous and Traditional Knowledge[EB/OL].[2015-09-21].http://www.ifla.org/publications/ifla-statement-on-indigenoustraditional-knowledge.
[9]Traditonal Knowledge Digital Library[EB/OL].[2015-10-09].http://www.tkdl.res.in/tkdl/langdefault/common/Home.asp? GL=Eng.
[10]张永宏.非洲建构自主发展动力体系的新探索:南非本土知识国家战略述评[J].全球科技经济望,2009(4):27-34.
[11]Chin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atents Database[EB/OL].[2015-07-21].http://221.122.40.157/tcm_patent1/englishversion/help/help.html.
[12]中国中药专利数据库及其检索系统简介[EB/OL].[2015-07-21].http://chmp.cnipr.cn/chineseversion/help/help.html.
[13]Shreeves S L,Kaczmarek J S,Cole T W.Harvesting Cultural Heritage Metadata Using the OAI Protocol[EB/OL].[2015-09-21].http://chaos.vtls.com/oai_docs/OAI_shreeves.pdf.
[14]Ara Irtitja Project[EB/OL].[2015-09-21].http://www.irititja.com/about_ara_irititja/index.html.
[15]Chapin M,Lamb Z,Threlkeld B.Mapping Indigenous Lands[J].Review of Anthropology,2005(34):619-638.
[16]Hunter J.The Rol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 Indigenous Knowledge Management[J].Australian Academic & Research Libraries,2005,36(2):109-124.
[17]Moorcroft H,Garwood A.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Thesaurus[M].National Library Australia,1997.
[18]AIATSIS.Pathways: Gateway to the AIATSIS Thesauri[EB/OL].[2015-09-21].http://www1.aiatsis.gov.au/.
[19]Mohi J H,Roberts W D.Delivering a Strategy for Working with Māori,and Developing Responsiveness to an Increasingly Multicultural Population: A Perspective from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New Zealand[J].IFLA journal,2009,35(1):48-58.
[20]IAPAD Community Mapping PPGIS,PGIS,CiGIS and P3DM Virtual Library[EB/OL].[2015-08-20].http://www.iapad.org/bibliography.htm.
[21]Shanks M.Traumwerk[EB/OL].[2015-08-20].http://documents.stanford.edu/michaelshanks/81.
[22]Stevens A.A Different Way of Knowing: Tools and Strategies for Managing Indigenous Knowledge[J].Libri,2008,58(1):25-33.
[23]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NMAI) [EB/OL].[2015-09-20].http://www.nmai.si.edu/.
[24]Lissonnet S,Nevile L.Quinkan Matchbox Project: Challenges in Developing a Metadata Application Profile (MAP) for an Indigenous Culture[EB/OL].[2015-09-20].http://ausweb.scu.edu.au/aw03/papers/lissonnet2/paper.html.
[25]Christie M.Words,Ontologies and Aboriginal Database[J].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Incorporating Culture and Policy: Quarterly Journal of Media Research and Resources,2005:116,(8):52-63.
[26]TAMI: A Database and File Management System for Indigenous Use[EB/OL].[2015-08-20].http://www.cdu.edu.au/centres/ik/db_TAMI.html.
[27]Taylor S.State Library of Queensland Library Services: Overcoming Barriers and Building Bridges[J].Australian Academic & Research Libraries,2003(4):280-281.
[28]Aboriginal Archive Offers New DRM[EB/OL].[2015-08-20].http://news.bbc.co.uk/2/hi/technology/7214240.stm.
[29]Warren D M,Von Liebenstein G W,Slikkerveer L.Networking for Indigenous Knowledge[J].Indigenous Knowledge and Development Monitor,1993,1(1):2-4.
Digitalization of Indigenous Knowledge
[Abstract]Digitalization is an effective method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indigenous knowledge.The digitalization process of indigenous knowledge includes collection,selection,description,reservation,distribution,etc.In indigenous knowledge digitalization process,there are technical-social related issues of concern,which include: a variety of resource forms coexist,multiple collection channels in selection,the attitude toward indigenous language in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progress,consideration of localization in metadata scheme,application of ontology and concept maps,characteristics of indigenous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construction,as well as indigenous knowledge resource center development.
[Key words]Indigenous knowledge; Digitalization;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Indigenous knowledge resource center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族地区口承文献的保护与利用研究”的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0BTQ027。
[中图分类号]G250.74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
胡立耘女,现工作于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情报与档案学系,教授,硕士生导师。
[收稿日期:2015-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