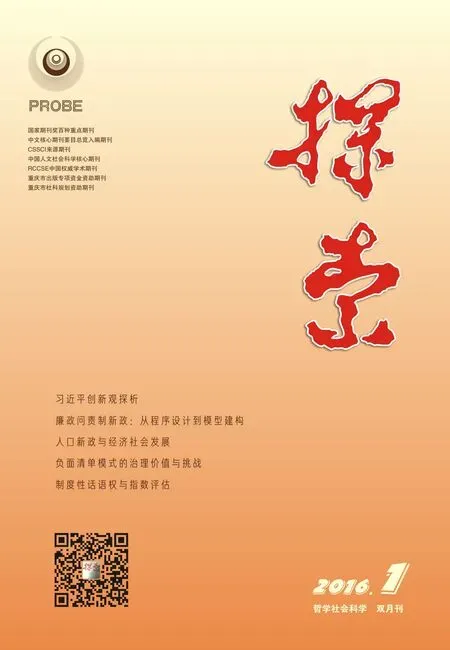人口新政及其经济社会影响
陈友华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江苏 南京210046)
1 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之关系
1.1 人口与经济
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是经济学与人口学长期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从需求与供给两个不同的视角分析经济增长及其影响因素,从中可以看出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按照经济学理论,经济增长短期看需求,长期靠供给。
短期来看,一地的市场规模取决于人口数量、购买力与购买欲望。人口数量的增减给短期经济增长带来或正或负的影响。自1963年以来中国人口增长速度趋缓,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下降至10‰以下,到2025年前后中国人口将停止增长,随后转入下降。由此可见,人口数量对中国短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正逐渐衰减,并在不久的将来转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不同人群的消费行为与消费能力不同,购买力与购买欲望不仅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还与人口结构密切相关,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
长期来看,一地的经济规模取决于劳动、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自2012年以来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呈加速减少之势,伴随着教育的扩张,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逐渐延后,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而现已进入劳动力市场的80后与90后们,其受教育程度、思想观念、劳动热情、家庭负担和对生活品质的要求等与其父辈相比已有根本性的不同,每个人的平均有效劳动时间明显缩短,致使整个社会的有效劳动投入快速减少,并大大快于同期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速度,从而给经济增长带来不利的影响。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短期还是从长期看,中国的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人口的数量增长(人口增长速度不断趋缓)与结构变化(少子老龄化与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正发生转变,人口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正逐渐消失,而消极影响则加速积累[1]。
1.2 人口与社会
作为社会基本构成要素的人口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异常复杂。基于人口属性而产生的社会关系包括代际关系、婚姻关系、家庭关系、社会性别关系等。中国目前面临的主要人口问题是少子老龄化与出生性别比例失衡等人口结构性问题,并对婚姻与家庭结构和生活安排、社会保障制度、收入转移、医疗保健和长期照护、代际关系和社会分层等产生重大影响。而社会发展反过来又通过改变人们的社会观念和人口行为对妇女生育率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导致人口的数量、结构、素质与分布等构成要素的变化[2]。由此可见,人口与社会之间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过程。
2 人口新政实施背景
2.1 人口形势
新中国成立后人口增长过快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可能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一直是中国人口问题关注的焦点。但自20世纪70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计划生育以来,妇女生育率持续下降,1992年后妇女生育率维持在更替水平以下,人口过快增长势头已经得到有效遏制。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妇女生育率进入低水平后并没有稳定下来,而是呈现出持续下降的态势,目前已不足1.5,甚至陷入低生育率陷阱[3]。低生育率意味着人口内部潜藏着负增长的潜能,而这种潜能正在加速集聚,2025年后将加速释放。届时,历时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人口负增长将不可避免。伴随着持续(超)低生育率时代的到来,少儿比例持续走低,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劳动年龄人口自2012年开始转入持续加速减少,出生性别比长期严重失衡,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的人口形势早已发生历史性的根本变化。
2.2 经济形势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GDP年增长率,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总体上经济增长速度很快,1978—2014年间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70%。二是经济增长起伏波动很大,经济增速最快的1984年的GDP年增长率高达15.18%,而经济增速最慢的1990年的GDP年增长率只有3.84%,前者是后者的近4倍。三是经济增长出现明显的周期性。1978—2014年间经历了四次高峰与四次低谷,其间一般以9年为一个周期。四是经济快速增长过后,紧随而来的总是经济增速的急剧回落,而回落到谷底后又出现强劲的回升。
现在的问题是:本轮经济增速回落后能否像以往一样回得去,目前对此存在很多争论。通常认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但有学者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典型的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速的节节下滑是由中国的体制机制造成的。中国过去快速的经济增长把这些问题掩盖掉了,一旦经济增速下滑,体制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并最终导致经济的失速。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应该进入中低速增长阶段。理由是:基数增大,人均GDP达到11 000美元左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约束增加,生态环境标准提高[4]。第三种观点认为国际经济周期的变化导致了中国经济的下行,中国经济下行是外部因素造成的。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较低,经济快速增长的潜力仍较大,这次中国经济下行是暂时的,中国经济年增长8%的潜力还能持续20年[5]。
实际上,上述三种观点都或多或少忽略了人口这一终极变量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极端重要性。作为变量的人口具有惰性(相对于其他经济社会变量而言)、累积性、惯性与超长周期性(与经济周期相比)等特点。正如前文所述,包括数量与结构在内的中国人口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少子老龄化与劳动力短缺愈演愈烈,使得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人口形势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已然有了根本性的不同,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具有客观必然性[1]。
2.3 社会形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其社会形势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突出地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与独生子女政策密切相关的“失独”等负面效应加速显现;二是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调同方向叠加,使得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及其与此相关的问题加速显现;三是中国的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向相对不足转变的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中国的劳动力人口从2012年开始持续减少;四是少子老龄化向纵深发展;五是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党群、干群关系长期处在紧张状态。所有这些对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健康发展、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家庭的幸福均构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2.4 “单独二孩”政策遇冷
2014年全国各地陆续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然而却普遍“遇冷”。2013年与2014年,全国出生人数并未出现明显回升。这充分表明,无论是生育政策的约束力,还是计划生育的影响力都已经式微,群众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少生优生成为绝大多数人的自觉行动。这是计划生育的成就,更是中国面临的最大人口问题。“单独二孩”政策实施是一个全国性的社会实验,“单独二孩”政策遇冷,为加快“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提供了足够的经验支持,也打消了人们对“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可能出现的较为严重的出生堆积的种种担忧。
2.5 改革突破口
中国的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众多。如何寻找改革的突破口,则考验着执政者的智慧。一方面,人口与经济社会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人口过快增长问题早已得到有效解决的同时,人口结构性问题凸显,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及计划生育机构改革与转型发展乃大势所趋。另一方面,生育政策调整本身就是一个还权于民的善举,自然会赢得广大群众的广泛赞誉,而来自利益相关者的阻力也相对容易被清除,因而自然成为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党中央审时度势,在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分别对计划生育机构改革、“单独二孩”政策与“全面二孩”政策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不仅借生育政策调整之机赢得了百姓的广泛支持,而且某些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也得到了有效缓和,从而为下一步深化改革赢得了时间与群众基础,充分展现了党中央的智慧与胆略。
3 人口新政与经济社会发展
3.1 独生子女政策的风险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标志着独生子女政策的终结。为什么要实行“全面二孩”政策?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认清独生子女政策的风险开始。实际上,独生子女政策所带来的风险是巨大的,只是被有意屏蔽与忽略掉而已。独生子女政策的风险主要体现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
在宏观层面,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1)易诱发持续超低生育率出现。(2)加速人口老龄化。(3)在一个具有歧视性性别偏好、廉价且简单易行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人工流引产技术迅速蔓延的国度,必然导致出生性别比例失衡及其相伴问题的产生。(4)持续低生育率必然导致劳动力短缺。(5)人口不振(特别是少子老龄化)必然导致生产不振与消费不振,经济增长乏力。(6)贪污腐败风险。当生育被确定为一项要被准许的权利,同时又缺少对权力的有效制衡时,必然导致贪污腐败的出现甚至蔓延。(7)道德风险。一是计划生育领域某些强制性做法的推出,导致社会价值体系紊乱,对社会稳定与社会秩序构成威胁。二是影响代际和谐,易使子女背负不孝骂名。三是政府面临诚信缺失的风险。例如以往政府为了鼓励人们实行计划生育,对百姓作出了各种各样的承诺,而当年的这些承诺在今天难以兑现。(8)计划生育导致党群、干群关系长期处在紧张的状态。(9)把出生人口划分为符合政策与超生两类,并对超生者及其子女长期实行歧视性的社会排斥政策,社会因此而被撕裂。(10)数据失实风险。(11)能为子女创造更好条件的中高社会阶层人群的生育行为更多受到生育政策限制,从而人为地扩大了生育率的阶层差异,导致人口素质的逆淘汰。(12)国防风险[6]。
在微观层面,其风险与危害则更为具体与显著,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生存风险。特别是独生子女的伤残夭折给家庭与社会带来难以承受之重。(2)部分妇女儿童身心健康面临受损风险。(3)养老风险,包括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风险、独生子女责任最大化风险、独生子女本人的养老风险与家庭经济支持能力弱化风险。(4)空巢综合症风险。(5)家庭内部劳动力短缺风险。(6)独生子女教育偏差风险。(7)子女培养奢侈化与劳动力培养成本急剧上升风险。(8)家庭内部冲突增多风险[6]。
3.2 人口新政的意义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于中国的人口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意义是十分巨大的,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3.2.1 人口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解除了部分群众想生二孩又怕触犯计划生育法律的顾虑与担忧,会促使生育率的暂时回升,减缓人口老龄化速度,延缓劳动力减少的步伐,政策性独生子女高风险家庭将因此而减少,家庭结构得到某种修复与改善,也有利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生性别比例长期失衡的治理,有助于实现中国妇女的生育率从非常状态向正常状态的转变,增强中国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以往积存的生育势能徐徐释放,将因此新增1 500万至2 500万的出生人数,这相对于13.7亿人口规模的中国来说属于“杯水车薪”,中国人口长期发展趋势不会因人口新政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3.2.2 经济
从短期来看,“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将导致出生人数的增加,直接带动相关的食品、玩具、母婴医疗、儿童服饰、家用汽车、住房、教育、健康、家政及日用品等方面消费需求的增加,刺激相关领域投资,增加就业。
从长期来看,对经济增长也具有积极意义。虽然近期会略微推高人口抚养比,但是新增人口进入劳动年龄后,将降低人口抚养比。有研究表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所导致的生育率回升与出生人数增加将使中国的经济潜在增长率提高约0.5个百分点。政策调整后,对资源环境增加的压力微弱,不影响国家既定资源环境战略目标的实现。
3.2.3 社会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前述的独生子女政策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部分得以规避。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相对于以往的生育政策而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意味着长期被剥夺自由生育权的公民的回归,部分体现了对公民生育权的尊重,也是“以人为本”“还权于民”执政理念的展现。第二,有利于妇女儿童的身心健康,长期看有利于出生人口素质的提升,也有利于孩子教育回归到正常的轨道上来。第三,规避了独生子女政策所导致的各种问题,有利于家庭的和谐与稳定,增强了家庭的发展能力与发展后劲。第四,在增强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同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也得以显著提升,例如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也因此而增强。第五,有利于贫困的消解。“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使得超生人数大大减少,从而部分地避免了“因超生受处罚致贫”与“因超生受处罚返贫”等现象的发生。
世事万物多是利弊互现,短期与长期收益可能不完全一致甚至相悖。长期地看,“全面二孩”政策的功能主要是积极的与正面的,但“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导致二孩出生增多,短期看也存在某些所谓的“坏处”。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家庭经济负担的暂时加重;二是时间精力付出的暂时增多;三是家庭生活质量的暂时下降;四是生育安全与出生质量隐忧的增加。因此,“全面二孩”政策要想取得预期的效果,相关的配套改革与相关服务必须跟进。
3.2.4 其他
地方政府的财力不足是中国长期悬而未决的社会现象,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地方政府逐渐寻找到破解地方财力不足的“良方”:“省市吃地皮,县乡吃肚皮”。社会抚养费成为部分基层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计划生育也因此在部分地区成为一座不冒烟的工厂。以往百姓的生育积极性很高,而目前百姓的生育积极性大幅度下降,绝大多数群众最多只想生育两个孩子,想生育多孩者越来越少。超生者中二孩早已经占绝对多数,而“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意味着公民生育的第二个孩子都符合生育政策规定,因而部分基层政府作为第二财政来源的社会抚养费基本被切断,可能使其财政更加捉襟见肘,甚至会危及其正常运转。中央政府对此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及时作出必要的制度性安排,以保证中国社会的平稳运转。
4 “全面二孩”政策所引发的对公共服务压力的担忧与消解
4.1 基本公共服务的压力是否会陡增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行,高龄产妇有所增加,对这部分群体的优生优育、生殖健康方面的公共服务增多。但由于目标人群不是特别大,而且从“单独夫妇”想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意愿很低推论,中国目前一孩夫妇生育二孩的热情也可能较低。因此,因“全面二孩”政策实施而新增的怀孕、生育与节育增多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压力不大。同时由于“单独二孩”政策实施的经验与对“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准备,应该能应对自如,不会出现意外情况。
4.2 公共服务供给能否满足民众的需求
经过数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政府可动用的资源与能力大大增强。1963年中国出生了2 960万人,在当时经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中国也艰难地挺过来了。目前中国的经济社会支撑能力远非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所能比,虽然今天民众的要求与以往相比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支撑出生堆积的能力大大增强,完全有能力满足“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因怀孕与出生人数增多而增加的对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需求。
4.3 部分地区公共服务压力大与“全面二孩”政策的关系如何
大城市人口出生率普遍较低,但大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压力普遍较大,确是不争的事实。出现上述情况,主要不是因生育政策调整导致出生人数增加所带来的,而是如下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大量人口流入大城市,导致大城市人口数量膨胀较快。(2)公共资源的非均等配置,民众对优质公共资源的争夺。如教育资源的差别化配置导致各种层级的学校所提供的教育质量差异悬殊,名校因此而诞生,从而导致民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如果公共资源的差别化配置不加以改变,目前大城市面临的公共服务压力很难有缓解的可能。
参考文献:
[1] 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中国的经济增长[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4):58-63.
[2] 李建民,原新,陈卫民,朱镜德,黄乾,姚从容,吴帆.中国人口与社会发展关系:现状、趋势与问题[J].人口研究,2007(1):33-48.
[3] 郭志刚.清醒认识中国低生育率风险[J].国际经济评论,2015(2):100-119.
[4] 刘世锦.GDP增长转换是规律[J].资本市场,2015(4):9.
[5] 林毅夫.8%的增长潜力中国可以再有20年[N].文汇报,2014-11-14(T05).
[6] 陈友华.独生子女政策风险研究[J].人口与发展,2010(4):1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