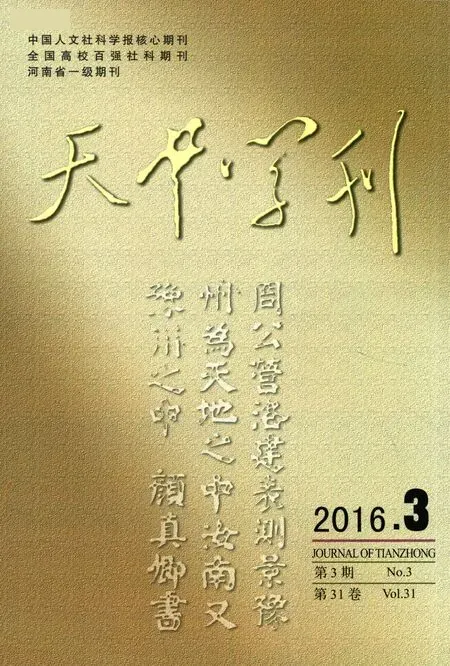论南宋文学传承中的“中原之音”
王睿
(河南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论南宋文学传承中的“中原之音”
王睿
(河南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在南宋文化的大环境中,中原文化在南宋文学中显现出独特的“中原之音”。南宋初年中原文化居于主流地位,但随着南方文化的兴起而逐渐衰微,直到宋末又重新振起。中原文化在南宋的临安、江西、永嘉、福建四大文化圈中,为一批中原士族的后代所传承,表现为思乡恋阙的爱国情感、收复河山的抗战理想和慷慨愤激的英雄气概。中原文化影响下的文学风格平实质朴,注重对传统的尊重和继承,与纤弱工巧的“南方之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双方在文学创作上体现为“唐律”与“古体”的交锋。
中原文化;文学传统;南宋
在朝代更迭之际和文化传统的接续与传承之间,总有一些文化精粹能够抵制异质文化的侵蚀,保持其特质,并在与新文化的融合中获得新的生命力。在北宋与南宋之交,中原文化在江南一带持续传承、传播和发展,增强了南宋政权执政的基础,在抵制异族入侵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原文化在南宋的文学中显现出独特的“中原之音”。这“中原之音”使得一代代文人在流亡之时始终保持着对故土的思念,对华夏民族文化的坚定信心。终南宋一朝,文学流派和文坛风气屡次变更,但“中原之音”始终在政坛和文坛发挥着重要影响。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南宋社会上低迷柔弱、追求华丽的“南方之音”逐渐占据上风,“中原之音”逐渐低落,这使得南宋文学的格调不断降低,造成了文学水平的下降和文学生命力的丧失。当南宋末期的文学成为标榜新潮、炫耀技巧的消费性产品而非传统文化的载体时,民族文化的根基开始动摇,南宋的政权也就摇摇欲坠了。今天研究“中原之音”在南宋文学中发展流变的过程,对于建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增强民族的精神凝聚力有重要的意义。
一、南宋文学的“中原之音”
此处所说的“中原”不仅是一个地域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北宋灭亡之后,南渡文人回望故国,感伤流涕时屡次提及“中原”。南宋人提到“中原”,大都指与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相对的具有高度文明成就和悠久历史的华夏文明。然而,“中原之音”作为一个文学与文化的概念,作为与格调卑弱但在南宋中期以后却大行其道的“南方之音”相对的概念而存在,首次是由朱熹提出的。朱熹曾评价南宋文人韩元吉:“韩无咎文做著尽和平,有中原之旧,无南方啁哳之音。”他又在《语类》中对当时的文风进行批评:
今时文日趋于弱,日趋于巧小,将士人这些志气都消削得尽……及绍兴渡江之初,亦自有人才。那时士人所作文字极粗,更无委屈柔弱之态,所以亦养得气宇。只看如今,秤斤注两,作两句破头,如此是多少衰气![1]2702
文中的“绍兴渡江之初”是指南宋初年,这时韩元吉是文人的杰出代表。韩元吉(1118—1187年),字无咎,颍川(今河南许昌)人,自其五世祖韩亿开始,世居中原,家族号称“桐木韩氏”。自宋室南渡后,寓居信州上饶(今属江西),隆兴年间官至吏部尚书。韩元吉在政治上是一个坚定的主战派,主张抗金收复失地。他在文学史上也是著名的诗人和词人,与陆游、朱熹、辛弃疾、陈亮等当代胜流和爱国志士交游密切,多有诗词唱和。作为辛弃疾的同僚和好友,韩元吉是豪放词派的成员,词风以豪放劲健、悲凉沉痛为主。朱熹虽然祖籍福建,属南方文人,但是文化归属上却与韩元吉一致,陆游、辛弃疾、陈亮等人虽原籍各异,但在文学中表现的“中原之音”却完全一致,表明中原文化占据了南宋初年文化的主流。
在南宋文坛上,“中原之音”的咏叹与爱国之情显然是联系在一起的,南宋文学的主流——思乡恋阙的爱国情感、收复河山的抗战理想和慷慨愤激的英雄气概都是“中原之音”的具体表现。韩元吉诗词大多表达了对故国的思念和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多次提到中原、神州、故乡等词。如《水调歌头·雨花台》“中原何在,极目千里暮云重”;《水调歌头·寄陆务观》“梦绕神州归路”;《瑞鹤仙·送王季夷》“故乡路阻”,并多次提到“闻鸡起舞”“勒石燕然”等。韩元吉的词作成就也很高,如《好事近·汴京赐宴闻教坊乐有感》:“凝碧旧池头,一听管弦凄切。多少梨园声在,总不堪华发。杏花无处避春愁,也傍野烟发。惟有御沟声断,似知人呜咽。”唐圭璋评曰:“此首在汴京作。公使金贺万春节,金人汴京赐宴,遂感赋此词。起言地,继言人;地是旧地,人是旧人,故一听管弦,即怀想当年,凄动于中。下片,不言人之悲哀,但以杏花生愁,御沟呜咽,反衬人之悲哀。用笔空灵,意亦沉痛。”[2]183这首词几乎入选所有的宋词选本,是韩元吉的代表作,也是“使金文学”的成功之作,因此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南涧甲乙稿》中称其“诗体、文格均有欧、苏之遗,不在南宋诸人下”[3]2148,认为他的文学创作继承了欧阳修和苏轼开创的优良传统,在南宋文人中成就显著。
不仅是韩元吉,陆游、辛弃疾、陈亮等人作品中也都有显著的“中原之音”,可见“中原之音”已经由一个文学概念上升到了文化的概念。如辛弃疾为韩元吉所做的《水龙吟·甲辰岁寿南涧尚书》云:“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辛弃疾对韩元吉的抗战理想赞誉有加,词中的“长安”“神州”皆指代故国。而陆游怀恋中原的诗歌也非常多,如《示儿》“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秋思》“雁来不得中原信,抚剑何人识壮心”,《秋兴》“中原本是关情地,幽州宁谓非吾乡”。陆游虽非中原人氏,但在文化上却将中原当作了自己的“故乡”。
“中原之音”还表现为平实质朴的文学格调。朱熹将韩元吉的文风概括为“和平”的“中原之旧”,与“啁哳”的“南方之音”相对,正是就其文学风格和格调而言的。“和平”就是平和,朱熹认为韩元吉的文风代表了典型的自北宋传来的那种厚重、平实的文风,也是从欧阳修和苏轼两位文学领袖传承下来的文风。而南方的文风是“啁哳”,本意为鸟叫声,形容声音繁杂而细碎。传统文艺观的标准向来崇尚浑融雅正,可见朱熹眼中的南方文化是无法与中原文化相比的。这种“中原之音”与“南方之音”的区别主要表现为文风和格调的差异,其实与作者的籍贯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如南宋的著名词人史达祖,祖籍汴京,虽为寓居临安的北人,但文化表现上却显然是“啁哳”的“南方之音”,在文学上属于姜夔的清空骚雅词派,以咏燕词著称。如其著名的《双双燕·咏燕》:
过春社了,度帘幕中间,去年尘冷。差池欲住,试入旧巢相并。还相雕梁藻井。又软语、商量不定。飘然快拂花梢,翠尾分开红影。 芳径,芹泥雨润。爱贴地争飞,竞夸轻俊。红楼归晚,看足柳昏花暝。应自栖香正稳。便忘了、天涯芳信。愁损翠黛双蛾,日日画栏独凭。
从艺术上看,这首词描摹燕子惟妙惟肖,穷形尽相之外,还细致入微地刻画了燕子初回旧巢的心理和神态,堪称咏物佳作。但从另一方面看,这首词却雕琢过甚,不脱尖新纤巧之讥,虽然工巧华丽,但是格调不高。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云:“梅溪才思,可匹竹山。竹山粗俗,梅溪纤巧。粗俗之病易见;纤巧之习难除,颖悟子第,尤易受其熏染。余选梅溪词,多所割爱,盖慎之又慎云。梅溪好用偷字,品格便不高。”[4]1492从文化上看,梅溪词的纤巧,正是繁杂而细碎的“南方之音”的表现。
韩元吉早年也写过轻薄俗艳的作品,甚至广为流传,但晚年自悔少作,将其焚毁。韩元吉《焦尾集序》云:“予时所作歌词间亦为人传道,有未免于俗者,取而焚之。然犹不能尽弃焉,目为《焦尾集》,以其焚之余也。”[5]104韩元吉焚词的动机便是避免贻人以“俗”的口实,他认为这些作品格调不高,于是焚毁一部分,尽量保留平和雅正之作,以与繁杂而细碎的“南方之音”相区别。韩元吉之子韩淲与赵汝谈、赵汝谠兄弟唱和时,作品多为五言古体诗,当时被称为“选体”。这种雄浑质朴的文学格调在南宋被当作“中原之音”的艺术表现。韩淲《余杭拉赵履常昆弟同曾甥守约游巽亭》:“平湖溜清涨,乱石夹远流。洗盏与客言,展席惬我游。人生贵自适,世道将焉求。晚峰忽前列,鸟鸣来白鸥。”诗风高古,表现出对中原文学风格的继承。又如祖籍中原的赵汝谈《次曾景建红泉碧涧韵》云:“石不能言语,云如过去身。意求虽彷佛,事往或湮沦。洞壑龙离隐,池塘草得春。山民忽惊避,吾此岸乌巾。”[6]32024其风格显然是对《文选》这一前代经典的继承和模仿,也是“中原之音”在诗学方面的表现。
二、南宋四大文化圈中的“中原之音”
南宋的文坛相较北宋而言,群体意识更强,文学社团更多,再加上国土变小,交往更加密切频繁。南渡以后的诗人群体以浙东与江西为中心,向周边地区辐射,逐渐形成了文化圈。如南宋中期最为显著的是临安、江西、永嘉、福建四个文化圈。临安为南宋首都,其文化地位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浙东和福建为学术和文学的重镇,而江西在北宋就是文学发达、诗人密集的地区,在南宋时其交通枢纽的地位越发显著,不仅有大量诗人寓居,四方往来之人皆路经于此,更加促进了其文化的繁荣。从这些宋代文学群体的活动中可以看出中原文化的传播及其在不同地域的差异。
第一,临安为文人四方辐辏之地,而其政治中心的地位决定中原文化作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然而实际情况是“南方之音”先是较“中原之音”为胜,而后逐渐与后者融合,两种文化在此形成了竞争和交融的局面。欧阳光认为:“在南宋中后期的京城临安,或前后,或同时存在着若干个诗社,它们各自聚集了一批志趣相投的社友,频繁地举行唱和活动。”[7]259他认为,南宋在临安曾有杨万里诗社、许及之诗社等多个“西湖诗社”,自南宋初期到宋末一直都有活动。如杨万里与陆游、张镃、姜夔曾结为诗社唱和诗词,戴表元记载:“循王孙张功父使君以好客闻天下。当是时,遇佳风日花时月夕,功父必开玉照堂置酒乐客,其客庐陵杨廷秀、山阴陆务观、浮梁姜尧章之徒以十数,至辄欢饮浩歌,穷昼夜忘去,明日醉中唱酬诗或乐府词累累传都下。”[8]136在临安结成的诗社中,成员大多是长期寓居的诗人,主要有葛天民、张镃、姜夔、潘柽、韩淲、赵汝谈、赵汝谠等人。这些人原籍大都不在临安,或为南方士子,或是中原世族的后代。但无论原籍何处,临安诗人群体普遍学习写作纤丽工巧的晚唐体诗歌,受南方文风影响较大。如杨万里在《诚斋诗话》中称:“近时后进有张镃功父、赵蕃昌父……姜夔尧章,功父云:‘断桥斜取路,古寺未关门。’绝似晚唐人。”从中可见,杨万里在临安诗人群体中,起着诗坛盟主的作用,他交游广泛,品评诗人,主持诗会,提携后进,在文学活动中宣扬自己的诗歌主张。临安诗人群体早期的诗风深受杨万里诗学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晚唐体特色,即“南方之音”。据韩淲《寄抱朴君》一诗的记载,杨万里后辈的临安诗人群体曾在庆元五年(1199年)结成诗社,参加者有姜夔、葛天民、韩淲、潘柽、盖希之等人。后来又有赵汝谈、赵汝谠等人参加过诗社。其文学早期表现为“南方之音”,如葛天民、张镃、姜夔、潘柽等人的诗歌多为律诗,艺术上绵密精巧,风格崇尚晚唐,体现为“南方之音”的格调。嘉定元年之后,临安诗坛也不再是晚唐体独领风骚的局面,古体诗逐渐兴起,韩淲、赵汝谈、赵汝谠等祖籍北方的士人又引导了文学风向的改变。他们的诗歌在体裁上多选择古体,尤其是被称为“选体”的五古,内容和风格上的“中原之音”都表现较为突出。自此“中原之音”与“南方之音”在临安诗人群体中出现了竞争与融合的局面。
第二,江西在南宋成为许多北方家族及其后代的聚居地,因而中原文化在此处的影响更大,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圈。北宋时江西就是人杰地灵之地,晏殊、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乃至此后的多位江西诗人,他们显赫的文名既给后人带来了骄傲的资本和厚重的文学遗产,也成为江西后辈无法超越的标杆。江西诗人群体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一方面远绍北宋“江西诗派”以及曾几和吕本中的诗学,另一方面受到杨万里直接的影响,将江西宗派的“情丽奔绝”与唐人的“惨淡深长”①较好地融合。南宋中期的江西诗人主要有曾丰、赵蕃、韩淲、徐文卿、陈文蔚、晁伯谈等。刘克庄在《湘南江西道中十首》中“派里人人有集开,竟师山谷友诚斋。只饶白下骑驴叟,不敢勾牵入社来”,描述的就是南宋中后期江西诗社的情况。在嘉泰元年的上饶地区,韩淲与赵蕃以及徐文卿、陈文蔚唱和颇多,以号称“上饶二泉”的韩淲、赵蕃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影响力较大的诗社[7]279。他们的诗词作品追求平和雅正的“中原之音”,是中原文化的代表。“二泉”晚年诗名卓著,前来问诗者络绎不绝,显现出中原文化在诗坛的影响力。
江西文化圈中,自北方南渡而寓居江西者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深,而那些原籍江西却流寓他乡的诗人,诗风更多倾向于南方文化。如姜夔本江西饶州鄱阳人,但长期流寓四方,其作品显示出南方文学的特色。韩淲、赵蕃、何文蔚等人为南渡世族,其诗歌多为五言古体(即“选体”),崇尚陶韦,对细碎雕琢、格卑力弱的晚唐律诗极为反对。刘克庄曾称“近岁诗人惟赵章泉五言有陶阮意”,方回说:
上饶自南渡以来,寓公曾茶山得吕紫微诗法,传至嘉定中赵章泉、韩涧泉,正脉不绝。今之学永嘉四灵者不复知此。贵溪郑君圣予过我,论诗所谓得正脉者也。貌瘠而气腴,年妙而词老,令予求其声于徽弦之外,岂借听之误欤?[9]868
由此可知韩淲、赵蕃这些北方世族的后代,将中原文学中的“正脉”传承下来,一直影响到宋末的方回、郑圣予等人。江西诗人群体的诗学与“永嘉四灵”相对,反对晚唐体的格卑力弱,如韩淲曾对“凋残沈谢”的晚唐体诗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发出了“谁把中兴后收拾,自应江左久参差”的感慨。
江西文化圈的成员大多是理学家兼诗人的身份。如“二泉”曾问学于朱熹,徐文卿、陈文蔚皆朱熹弟子。他们十分关注诗歌的经世教化功能,反对纯粹为艺术形式和审美感受而作诗,表现出中原儒学文化传统在南宋的传承。如徐文卿《偶作》:“绿树何稠迭,清风稍羡余。枕萦云片片,帘透雨疎疎。修笕通泉壑,残碑出野鉏。丘陵知几变,耕稼杂陶渔。”方回称其“与赵昌父、韩仲止声名伯仲”,评此诗“中四句俱雅淡”,道出了江西诗人群体在晚唐诗风兴盛的情况之下对中原文化的坚持。陈文蔚的诗歌大多为阐明心性的“语录体”,艺术性较强的作品如《庚戌春下鄱阳舟中诸作》:“浩荡春江洗客愁,歌声欸乃发中流。溪斋却忆凭栏日,数尽来舟与去舟。”自然质朴,不事雕琢,富于理趣。其后辈理学家谢枋得、方回等人也传承了他们的诗学观念,追求自然淡泊、平和高远而意蕴深沉的境界。南宋中后期“派家”“正脉”之类的说法都是江西文化圈在文学与哲学上对中原文化的继承。
第三,永嘉及浙东文学群体组成的“永嘉文化圈”,在南宋中期是审美特征最为鲜明、艺术追求最为突出的一个群体。文化圈的领袖是潘柽和许及之,其核心成员是号称“永嘉四灵”的徐玑、徐照、翁卷、赵师秀,也包括叶适、薛师石等人。“永嘉文化圈”在学术上独树一帜,文学上也具有鲜明的特色,明确地举起了晚唐体的大旗,效仿姚合、贾岛,诗歌特点鲜明,成就突出,名声大振,成为南方文化的代表。“四灵”之后,大量永嘉诗人结为诗社相互唱和。如王棹《薛瓜庐墓志铭》云:
永嘉之作唐诗者首四灵。继灵之后,则有刘咏道、戴文子、张直翁、潘幼明、赵几道、刘成道、卢次夔、赵叔鲁、赵端行、陈叔方者。作而鼓舞倡率,从容指论,则又有瓜庐隐君薛景石者焉。诸家嗜吟如啖炙,每有文会,景石必高下品评之,曰:某章贤于某若干,某句未圆,某字未安。诸家首肯而意惬,退复竞劝,语不到惊人不止。[10]12
可以看出“四灵”对永嘉文化圈结社唱和、切磋诗艺的风气造成很大的影响。一方面,“永嘉四灵”在“理学兴而诗律坏”的情况下崛起。由于理学家普遍反对宋代中期兴起的文学消费化和商品化的热潮,文学创作的艺术性也不高,“永嘉四灵”审美感受鲜明的文学作品便应运而生。他们的晚唐体诗歌风格野逸清瘦、不事用典,学力浅薄、才气短小的诗人也容易学习和模仿,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也容易理解和欣赏。他们在文学消费化和商品化的浪潮中成了突出的典型,成为此后诸多小诗人竞相模仿的对象。另一方面,永嘉在文学传播上有突出的地域优势。永嘉与临安、婺州同属浙东,对文学风尚的追求比较一致,如临安的潘柽、姜夔、葛天民等人皆是晚唐体诗人;陈亮、巩丰为婺州人,也容易受到晚唐诗风的影响。“永嘉四灵”具有江湖诗人的身份,他们长期流寓四方,与各地的诗坛名家往来唱和,这就使得永嘉文化圈的文学能够成为引领全国文学潮流的典范。
第四,福建文学群体组成的福建文化圈与江西文化圈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是传承中原文化的重镇。福建曾是两宋之际许多渡江士大夫首选的避乱之地,南宋建立之后仍是许多文人聚居之地。南宋中后期比较著名的福建诗人主要有朱熹、敖陶孙、徐似道、黄景说、刘克庄、林希逸等。朱熹虽然是理学家,但其诗歌成就同样很高,是福建诗人的代表。除陶渊明外,朱熹还特别喜爱韦应物那种萧散淡远的诗风[11]66,其拟古学古之作是对中原文学传统的继承。朱熹的这种诗学观念不仅影响到福建后辈诗人,也影响到其门下的江西诗人,如赵蕃、韩淲、徐文卿、陈文蔚等。所以,福建诗人的风格一方面接近浙东,另一方面也接近江西诗人。他们的诗歌既有自然清丽的晚唐风味,也有高远淡泊的陶韦余韵。徐似道、黄景说、敖陶孙、刘克庄、林希逸等福建文人,以往诗坛皆将他们归于“晚唐体”派,归于学习“四灵”的江湖诗人行列,其实从文学表现来看,他们早年确实学晚唐,但是在嘉定末年受到“选体”诗风的影响,开始主动变革,欲超越“四灵”,脱出“唐律”与“选体”的局限,创作出笔力雄厚、意境高远而又精致工巧的诗歌。如刘克庄在结集于嘉定十二年的《南岳旧稿》之后,就开始创作超越“晚唐”风味的诗歌,曾创作出一批纵横排宕、高古劲健的诗篇。他虽然一生都喜爱“唐律”,但其诗风却存在着从雕琢到自然,从纤巧到豪放的转变,其晚年诗风尤为平淡朴质,若仅以“晚唐”来概括未免偏颇。敖陶孙也存在着这样的情况,敖陶孙诗作多为古体,往往放意而行,风格雄浑深厚。如《秋日杂兴》其四:“阵云起西北,中原暗黄尘。岂无康时算,无路不得陈。书生亦过计,夜夜占天文。匣剑似识时,中宵哑然鸣。我亦发悲歌,沾衣涕纵横。”王士祯云:“臞翁古诗、歌行,颇有盛时江西风气。”[12]243又云:“器之非江西诗派中人,而诗深得江西之体。”[13]233可谓别具只眼者。敖陶孙、刘克庄等福建诗人多为“上饶二泉”的晚辈,他们曾拜访过“二泉”,在诗学上受他们的影响较深,如韩淲有诗《刘克庄潜夫诗编》赞赏提携刘克庄。由此可知,宋末福建与江西文化圈相互影响,共同体现了中原文学与文化在南宋的影响。
三、“唐律”与“古体”的交锋
在上述四大文化圈中,临安和永嘉文化圈是南方文化的代表,而福建与江西文化圈则是中原文化的代表。在南宋政坛和文坛上,这种对文化上“中原”认同感的差异,是两个群体显著区别的标志。南宋政坛上发生的党争,时常表现为主战派和主和派的争论、道学派和反道学派的争论,在其引起的文人集团消长与流派的演变中,出现了所谓“中原旧家”与“南方之音”对话语权的竞争。竞争的一方为“中原旧家”,包括南渡者及其后人,还有虽然本身为南方人,但是完全服膺元祐学术的那些人,如朱熹、陆九渊等。理学党人基本是由这些人组成,他们守家学,重气节,文风质朴,诗学多宗江西,被称为“北宋典型”。竞争的另一方可称为“南方文士”,“南方”在此是一个社会文化的概念。其成员多为南方士人,在思想、学术与文学上缺乏世家大族的传承体系,在艺术求新求变,在诗学上弃江西而习晚唐,文风尖新精巧。南宋中期的游士阶层多属于这个文学群体,江湖诗人中的一部分也属于此类。这表面看起来是两种不同文学倾向和文人集团的论争,是政治态度、道德判断与地域风俗的论争,但根本上是文化的论争。
“中原旧家”与“南方文士”的文学表现有着显著的差异,“中原旧家”多崇尚“古体(选体)”,他们的诗词作品在内容上表达思乡恋阙、收复河山的爱国感情,在风格上表现为雄浑质朴的文学格调,在思想上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发扬,因而在趋新之人眼中思想保守。而“南方文士”则崇尚“唐律”,在诗歌内容上对现实和政治有所回避,多写山林闲适生活,在风格上以野逸清瘦为主,注重诗歌的艺术技巧和审美趣味。终南宋一朝,“唐律”与“古体”在文坛上反复争胜,其背后正是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在文学话语权上的争夺。嘉定末年以后,“四灵诗派”崛起,他们举起“唐诗复兴”的旗帜,将“唐律”推向了新的高度,以此和“中原旧家”推崇的“选体”相抗衡。这种论争表面上是学诗途径之争,是诗歌体裁和风格选择之争,但背后反映的实际是宋末诗坛上晚唐范式与江西范式的竞争,也是文学话语权的交锋。《隐居通议》云:“古诗一变骚,再变选,三变为唐人之诗。至宋则骚、选、唐错出。山谷负修能,倡古律,事宁核毋疏,意宁苦毋俗,句宁拙毋弱,一时号江西宗派。此犹佛氏之禅医家之单方剂也。近年永嘉复祖唐律,贵精不求多,得意不恋事。可艳可淡,可巧可拙,众复趋之,由是唐与江西相倾轧。”[14]卷十“四灵诗派”是永嘉的晚唐体诗人群体。大致在嘉定十三年(1219年)之后,他们所代表的“唐体”势力日益强大,几乎达到了以往江西诗派的地位。钱钟书说:“经过叶适的鼓吹,有了‘四灵’的榜样,江湖派或者‘唐体’风行一时,大大削弱了江西派或者‘派家’的势力,几乎夺取了它的地位,所谓‘旧止四人为律体,今通天下话头行’。”[15]358可见,早年“四灵”对推扬“唐律”还显得势单力孤,而随着“四灵诗派”的崛起,“唐律”风行,逐渐压倒了江西后派。刘克庄云:“近世诗学有二:嗜古者宗选,缚律者宗唐……盖四灵抉露无遗巧,君含蓄有余意。余不辨其为《选》为唐,要是世间好诗也。”[16]卷九十七其中的“嗜古者”主要指“江西后派”诗人,而“缚律者”主要指“四灵诗派”诗人。为“唐律”者“抉露无遗巧”,而“嗜古者”则“含蓄有余意”。刘克庄一度“欲息唐律,专造古体”[16]卷九十四,为赵汝谈所劝止。宋末的方回对“唐律”取代“古体”表示不满,他说:“永嘉水心叶氏忽取四灵晚唐体。五言以姚合为宗,七言以许浑为宗,江湖间无人能为古《选》体。而盛唐之风遂衰,聚奎之迹亦晚矣。”[17]卷四这些都说明,南宋中期的“四灵诗派”与“江西后派”在诗体上的分歧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而后诗坛由崇尚“唐律”向崇尚“选体”转变,也表明江西诗学重新压倒晚唐诗学,标示着“中原之音”的重新振起。然而,由于低迷柔弱、绮丽工巧的“南方之音”长期占据上风,降低了南宋中后期文学的格调,造成北宋以来的文学传统的破坏。诗坛不仅难以恢复北宋旧貌,连杨万里、陆游一代的“中兴诗坛”风气也败坏殆尽,文学水平的降低和文学生命力的丧失,都对文化传统造成很大的破坏。南宋中后期的社会普遍缺乏文化上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其灭亡除了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因素外,和文化传统断裂也有很大关系。
宋代虽屡遭外侮,但经济、文化、思想方面成就斐然,达到了我国历史的最高峰。近代大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认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经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天水一朝。南宋文学中体现出的“中原之音”,不仅是对北宋文学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对整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在传承的过程中,中原文学传统受到南方本土异质文化的挑战。在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的竞争中,形成了临安、江西、永嘉、福建这四个大的文化圈,其中江西与福建汇集了一批致力于继承北宋以来的文学与文化传统的作家,他们的文学创作,为南宋诗坛注入了一种刚健的力量。南宋诗词中的爱国内容、激烈豪放的感情、平实质朴的风格和追求平和淡远的艺术境界,正是中原文化在文学领域的体现。而诗歌风格和体裁的交锋,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江西诗派和江湖诗派的文学群体,显示出南宋中后期不同地域文化的族群在文学话语权上的激烈争夺。南宋中后期中原文学和文化的低落,对社会的世道人心造成极大的消极影响。《四库全书总目·橘山四六提要》称:“淳熙、绍熙之间,正风会将变之时,故所作体格稍卑……”[3]2152这说明南宋中后期是世道人心日益衰落的时代。南渡初期诗文中的那种“英雄气”与立志恢复故土、北望神州的壮志豪情一去不返,“中兴气象”也已荡然无存。宋代中原之音的变迁与衰落,今天仍带给我们许多教训和启示:文化兴则民族兴,文化弱则民族弱。当今中国对文化传统的重视,对文化自信力和文化传承的培养和保护,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中原文学与文化传统的研究,对充分开发和利用本土文化资源,提高中原地区的文化竞争力都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 “情丽奔绝”与“惨淡深长”皆出自杨万里《诚斋集》卷七十八《双桂老人诗集后序》,四部丛刊本。
[1]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 唐圭璋.唐宋词简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3]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7.
[4] 张璋.历代词话[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
[5]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216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6] 傅璇琮,等.全宋诗:51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 欧阳光.宋元诗社研究丛稿[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8] 戴表元.戴表元集[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
[9] 傅璇琮.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8.
[10] 陈起.江湖小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2008.
[11] 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2] 郑方坤.全闽诗话[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13] 王士祯.带经堂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14] 刘埙.隐居通议[M].清·海山仙馆丛书本.
[15] 钱钟书.宋诗选注[M].北京:三联书店,2002.
[16]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M].四部丛刊景旧钞本.
[17] 方回.桐江集[M].清·宛委别藏本.
〔责任编辑 杨宁〕
On central Plains culture in the Literary Tradition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ANG Rui
(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46, china)
In the culture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appeared in a unique form.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resides in the mainstream status. With the rise of the southern culture,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gradually declined till the end of the Song.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in Lin'an, Jiangxi, Yongjia and Fujian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ere inherited by the descendants of a group of central Plains nobles. Their literature works mainly about the heroic patriotic feelings, homesickness and the ideal to resist against invader.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is plain and simple focusing on the traditional respect and inheritance compared with the delicate Southern culture. The two cultures are also in a fighting between the styles of Tang Poems and Ancient verses.
central Plains culture; literary traditio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206.2
A
1006-5261(2016)03-0076-06
2015-11-18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2013-QN-603)
王睿(1981—),男,河南郑州人,讲师,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