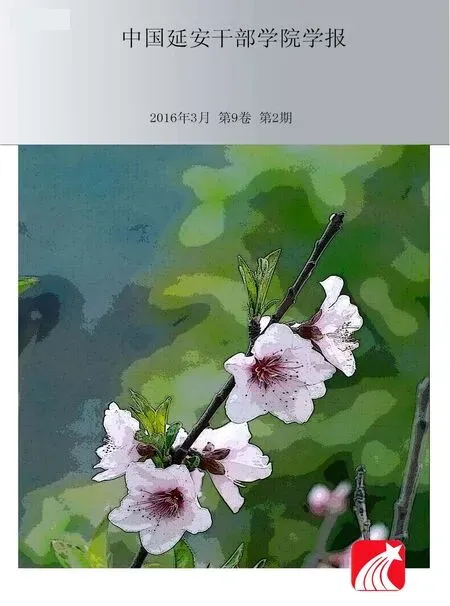关于建国以来社会发展机制“路径选择”的再思考
——以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为考察中心
张 明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93)
关于建国以来社会发展机制“路径选择”的再思考
——以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为考察中心
张明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93)
【摘要】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的协调运行是维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从根本上而言仍未突破人类社会一般规律性制约——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其平衡机制更多地是通过彰显社会主义本质属性而得以呈现。毛泽东时代在动力机制问题上为“落后亦即优势”意识所累,过分夸大在一般意义上社会历史发展动力机制中“非主导性”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并进而陷入依赖阶级斗争扩大化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误区,无形构筑了社会发展的阻力;在平衡机制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平衡困境”批判的单一式理解,人为将平衡机制凌驾于动力机制之上,最终陷入平均主义误区,导致社会发展动力机制的严重缺失。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总结毛泽东晚年平衡机制与动力机制“失序运行”的失误,辩证处理了二者的协调运行关系,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局面。
【关键词】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发展;动力机制;平衡机制;毛泽东
人类社会从本质上而言是由各个要素有机构成的综合统一体,各要素之间维系着各不相同的关系,在迥然相异的运动机制指引下加以运行,但从本质上而言,其都受基本的运行机制——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的制约。“所谓动力机制,是指一个社会赖以运动、发展、变化的不同层级的推动力量,以及它们产生、传输并发生作用的机理和方式。所谓平衡机制,则是指一个社会的各个组成要素和部分之间如何协调相互关系,保持平衡,以有序、稳定状态运行的机理和方式。”[1]简言之,动力机制就是解决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而平衡机制则是解决保证社会和谐稳定的问题。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不同社会制度下,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并且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并非始终保持“同向效应”的理想状态。因此,如何正确辨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并科学处理二者之间的协调运作关系,是事关社会主义社会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毛泽东时代由于主客观原因的限制,在此问题上走向了误区,并留下了深刻教训。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科学总结毛泽东时代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失序运行”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一
探寻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是人类社会自诞生以来就孜孜追寻的“终极问题”,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形态对此都做出了艰辛探索。有封建时期将推动社会历史发展动力归结为统治者德行的“道德说”和异化、扬弃异化、实现理想状态复归的“异化史观”,也有资本主义时期将社会历史发展动力归结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终结人类历史”的学说。但是,上述关于社会发展动力机制的探索,都未能在一般意义上寻得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的“元理论”。对这一问题做出开拓性贡献的是马克思,他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现实出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深刻阐释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动力机制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当然,承认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作为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只是就一般意义或本源层面而言的,其并未抹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终极动力机制”的具体表现以及其他动力性因子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的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社会,而对于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鲜有涉笔。因此,无形造成了对社会主义社会动力机制问题的集体“失语”状态。甚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未能做出明确指示。这直接导致苏联斯大林时代否认矛盾存在,认为社会主义是完全和谐的统一体。进而认为,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机制不再是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而是苏联各阶层之间政治上的一致性和爱国主义精神。尽管斯大林后来修正了社会主义“无矛盾”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之间仍然存在矛盾,但并没有将其视为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机制。在此问题上,毛泽东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在矛盾普遍性原则的指导下,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2]214很明显,毛泽东明确将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视为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机制。因此,就当时中国社会主义“较不发达”的现实而言,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则是解决先进社会制度同落后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也是中共八大决议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机制的集中表述。然而,毛泽东晚年由于主客观原因的限制,在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机制问题上却走向了如下误区:
(一)主观能动性的无限拓展、客观规律定在性的突破与动力机制的解构
在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中,人的因素始终占据主导性地位。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是不可能脱离作为推动历史发展主体之个人而存在,社会是由无数个人所组成的,脱离个人则无所谓社会之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以往任何哲学的本质在于: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前提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3]67换言之,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并不是处于离群索居或幻想之中抽象的人,而是处于具体物质生产活动之中的现实的个人。伸张人的主体能动性、彰显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之一。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人的主体能动性是实践能动性的指称,即人们运用实践活动改造自然、社会和自身。但这种能动性是建立在历史辩证法的客体向度基础之上,即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客观物质基础、规律的承认。“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创造。”[4]585所以,历史辩证法主体向度的彰显并非是对客体向度的取代,而是建立在对客体向度的充分承认基础之上。毛泽东从青年时期开始就十分重视人的主体能动性,“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就成为青年时期的“座右铭”;在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明确指出唯物辩证法“最重要的方面是能动性……提高中国人民的能动性、热情,鼓吹变革现实的中国是可能的。”[5]311
然而,毛泽东晚年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方面存在着重要缺陷——将马克思主义人的能动性错误地等同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人的能动性更多地是从实践角度而言的,即特指人的客观实践活动的创造性。而毛泽东则将这种能动性混淆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且更多地将其视为与客观规律相对抗的主观能动性,对制约实践活动开展的客观条件(即历史辩证法的客体向度)重视不够。[6]427当然,主体思想形成与发展都不可能脱离其所处的客观历史条件,毛泽东也不例外。中国自近代以来就一直处于拖后挨打的局面,实现民族独立、国富民强是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至死不渝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后,防止被开除“球籍”的紧迫感时刻萦绕在毛泽东的心头而挥之不去。在“落后亦即优势”思想的指导下,“只争朝夕”,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敢想、敢干、敢革命”,打破客观规律限制,做到“人定胜天”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人民的“集体无意识”。“大跃进”就是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扭曲表现,忽视客观规律、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不仅不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反而构成了社会发展的阻力机制。
(二)作为“非主导性”因素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作用的“路径依赖”与不断变革、构筑社会发展动力机制的幻象
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从本质上而言分别是由生产力、经济基础所决定,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阐述了上述思想。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我国主要矛盾展现为先进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应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不断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夯实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然而,毛泽东认为,中国在“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下,要实现生产力的快速提高与经济基础的夯实,则必须通过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和进行上层建筑的革命,以更为先进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带动落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进步发展。实事求是而言,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有其内在合理之处。马克思主义尽管强调了生产力、经济基础在归根结底意义上的主导地位,但并没有以这种主导地位来排斥、否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虽然由生产力所决定,但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也能发挥反作用——促进或阻碍。分析主义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科恩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出发,运用“绝对停滞”——束缚关系绝对阻止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相对低下”——现存生产关系对于推动生产力发展并非最适宜、“利用的束缚”——利用生产力方式的束缚、“发展的束缚”——生产力增长被束缚等概念建构了“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理论。[7]366-381这是对生产关系反作用的鲜明洞察。同样,马克思主义尽管承认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从归根结底意义上而言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但并没有走向“经济决定论”的极端而忽视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与反作用,甚至承认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上层建筑也可能发挥决定性作用。“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8]696
对马克思主义的上述思想,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就曾做过阐释与发挥,集中批判了只重视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而忽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反作用的“机械唯物论的见解”。“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9]325-326因此,毛泽东认为,建国后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关键在于通过不断的调整生产关系,通过生产关系的变更重新赋予生产发展的动力机制。以农村人民公社为例,“一大二公”、追求纯之又纯的公有制,自认为能够通过变更生产关系推动农村生产力发展,但最后却极大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严重阻碍农村的发展与进步。在上层建筑问题上亦是如此,毛泽东晚年更多地强调政治、思想观念等上层建筑的作用,极力推行政治、思想层面的革命运用,进行心灵深处的革命运动,努力锻造共产主义的“新人”,寄希望依靠不断进行的阶级斗争赋予社会发展的动力。不可否认,尽管这对于提升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与高尚道德起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因超越了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最后不可避免地以失败而告终。可见,承认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是只有“一定条件下”才能得以成立,而“这一定条件”是建立在对生产力、经济基础“归根结底”意义上决定性作用的肯定基础之上。
二
动力机制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支持,社会发展动力的缺失,往往会导致社会发展车轮的停滞不前。然而,一个社会倘若要健康、持续发展,仅仅依赖动力机制并不能达及,平衡机制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其原因在于:动力机制推力作用的发挥往往着眼于社会的前进——更多地停留于经济、军事等强势层面,并且在动力机制的基本构架中,各方利益、各要素力量并非以均等化构成而发挥作用,因此不可避免会导致部分非平衡性因子的产生。尽管非平衡性因子——诸如竞争的弱肉强食性和机会的不均等性,在某种程度上构成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机制。但从长远看,非均衡因子所造成的结果相对集中于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必将会打破社会发展的大天平,最终不可避免导致社会的动荡与混乱。因此,从根本上而言,以动力机制取代平衡机制,最终并不能保证社会的健康、持续与稳定发展。而毛泽东时代在平衡机制问题上最大的误区就是过分地强调平衡机制的作用,甚至为追求所谓平衡机制而刻意牺牲动力机制,以平衡取代动力,最终陷入平均主义误区,导致社会发展动力机制的严重缺失。其具体表现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平衡困境”批判向度的单一式理解
众所周知,马克思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终身奋斗目标,其中关于资本主义批判的核心便是资本主义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所不容回避的“平衡困境”问题。所谓“平衡困境”即是指资本主义由于其与生俱来的内在缺陷,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平衡机制的缺失,最终阻碍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具体而言,资本主义的核心便是资本逻辑,而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维持肉体生存的同时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构成了资本家发家致富秘密所在。“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3]266在马克思所生活的年代,资本家依据其占有生产资料的“先天优势”将工人变成机器的附属品,极力压缩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从而扩大剩余劳动时间,使社会财富占有在极少部分人手中,人为地使工人生活在社会贫困线以下以获得充裕的劳动力,造成了工人片面、畸形的发展。因此,工人阶级起来推翻旧的社会制度,追求自身的全面自由发展将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此外,由于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指引,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往往处于各自分散的状态,社会资源的配置主要是由市场所调控,而市场所遵循的法则就是利润最大化,其不可避免导致社会资源的集中、过剩、缺失、再集中、再过剩的循环往复过程。这种非平衡性的重要表现就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发生。可见,资本主义由于自身所不可克服的缺陷,必然导致社会发展平衡机制的缺失,从而最终走向覆灭的结局。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平衡困境”的猛烈批评,深刻影响了毛泽东的思想路径。因此,如何消灭资本主义、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如何避免资本主义“平衡困境”在中国显现,始终成为毛泽东晚年的主要思考域。批判、防范资本主义的“恶性”层面在中国显现固然无错,但问题是毛泽东片面理解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平衡困境”的批判。
一方面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平衡困境”的猛烈批判,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积极性因素的充分肯定基础之上。资本主义“平衡困境”更多地集中于生产关系层面,而在生产力层面,马克思则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意义。“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277而资本主义在数百年历史发展征程中,其关键动力机制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竞争。“资本家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3]266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上述动力机制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是持有充分的肯定态度,而毛泽东并未能清晰地洞察马克思的上述含义,而过分地强调对资本主义“平衡困境”的批判,将资本主义视为洪水猛兽而严加防范,对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合理性意义未能深刻理解,这是毛泽东晚年的一大失误。因此,就不难理解缘何在毛泽东时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共识性内容。
另一方面未能科学理解资本主义的“平衡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动力困境”所决定的,未能清楚把握对资本主义困境的批判不仅要集中于“平衡困境”,而且不应忽视对“动力困境”的批判。具体而言,资本主义的“平衡困境”从本质上而言是由其“动力困境”所决定的,所谓“动力困境”即是指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资本主义初期成为推动其发展的动力机制,在取代封建主义方面具有极大的革命性。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资本主义私有制愈来愈成为阻碍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伴随而来的就是革命的时代。上述“动力困境”是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其决定了资本主义“平衡困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资本主义“平衡困境”是对其“动力困境”的集中彰显。因此,关于资本主义“历史困境”的批判更为关键的是要聚焦于“动力困境”,而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晚年更为侧重于“平衡困境”的批判,侧重于关乎资本主义制度的伦理反抗与道德控诉,更加侧重于对于人性、政治层面的改造、操作。
(二)更加注重社会主义“平衡机制”的建构,打破平衡与动力二元互动格局与平均主义误区、“动力机制”缺失的“悲剧”
资本主义在“平衡机制”问题上最大的困境就是由生产资料私人所有所造成的两极分化现象。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两极分化现象十分严重,甚至达到极其残忍的地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非人道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对两极分化、工人受压迫和剥削等现象的控诉。因此,在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对抗性社会分工将被消除,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中,实行各尽其能、按需分配,“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294在公有制基础上追求个人的自由发展、个性解放是作为资本主义“平衡困境”的“对偶”而加以设定,因而其既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平衡机制”,亦是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机制”。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理想状态的设定,深刻形塑了毛泽东的思想逻辑路径。可以说,毛泽东晚年关于中国社会未来发展路径的规划与勾勒,从本质上而言主要是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尽管不可否认其中也夹杂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同思想”等因子作用,但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平衡机制”的设定,在毛泽东的逻辑构架中始终占据主导性地位。毛泽东关于未来中国社会理想状态的设定,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平衡困境”的批判,极其注重社会主义“平衡机制”的建构问题。但是,其内在的问题是,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平衡机制”的设定,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现有物质文明充分吸收的基础上,即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而毛泽东忽视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历史阶段性,盲目追求“名不符实”的“平衡机制”,最终为“平衡”所累,陷入平均主义误区,极大限制了社会主义社会“动力机制”的发挥。具体而言:
一是忽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追求纯之又纯的公有制,以寄希望构建社会理想“平衡机制”的基石。在马克思的理论逻辑视域中,资本主义社会的“平衡困境”是资本主义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调和的矛盾产物,因此从本质上而言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决定的。私有制决定了工人必然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不平等地位,也决定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平衡机制”必将会被无情解构,从而导致资本主义总体性危机的到来。因此,未来社会就是在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实现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重建。正是基于马克思的上述思想,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的顺利发展必须建立纯之又纯的公有制,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设想就是典型体现。但问题是,马克思关于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充分继承基础之上,是在物质产品极大丰裕的基础上才能达及。“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3]269也就是说,未来公有制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之否定”,而“否定之否定”则是包含对前一阶段合理性的充分认可,即是扬弃。进一步而言,公有制的建立是历史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的产物。而在中国资本主义发达较不充分,其基础性动力提供不足的情况下,盲目追求纯之又纯的公有制最终只能沦为不切实际的空想。
二是刻意追求理想的“平衡机制”,将按劳分配视为资产阶级法权加以批判,盲目推崇按需分配,最终走向平均主义误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中,未来社会的“平衡机制”是直接作为资本主义的“反面”而存在。因此,在未来社会中,维系社会正常发展的平衡机制主要集中于共产主义的制度层面。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平衡困境”的深刻担忧,毛泽东晚年力图避免资本主义“平衡困境”在中国的重现,因此其晚年主要思考域集中于社会主义“平衡机制”的建构问题。二元对立性思维模式也据此成为毛泽东晚年思维模式的重要特征之一,社会主义处处与资本主义处于“你死我活”的对立状态之中,马克思关于理想社会“平衡机制”的设定也进而被全盘挪用到中国。因此,在实践中,与之相适应的必然是片面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诸如在分配制度上主张以按需分配取代按劳分配,人为消灭货币、商品,盲目追求平均主义。其实,马克思所设定的理想“平衡机制”是建立在社会“动力机制”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即“平衡”是建立在对“动力”的充分尊重基础上,“平衡”是生产发展高度发达基础上的“平衡”,“平衡”从本质上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动力”的发挥,而非起阻碍作用。但是,毛泽东晚年忽视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套用马克思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平衡机制”,超越了历史发展的具体阶段性,为中国社会主义建构了一套“不合体”的“平衡机制”。此符合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平衡机制”运用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必然会导致某种程度的“脱节”与机制“失效”等问题,从长远而言只能阻碍社会的持续发展。
三
毛泽东时代在社会发展机制问题上走向了理论误区,未能真正把握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发展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的本质内涵,也进而未能科学处理二者之间的协调关系。因此,在发展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地遭遇了系列挫折与阻碍。但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毛泽东时代关于社会发展机制“失序运行”的经验教训是留给当代中国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其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与总结,并且成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与逻辑起点。
(一)以改革社会生产关系为手段,重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
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从根本上而言未能脱离人类社会一般性规律的制约——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马克思主义对生产方式内在的决定性作用与反作用都表示了充分肯定,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也从实证角度证明了二者的现实性与合理性。然而,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只能是在“一定条件下”才具备现实性,这种“一定条件”并不是对生产力“决定性作用”的否认。换言之,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是建立在对生产力“决定性作用”的充分肯定基础之上,是在从根本上由生产力所决定特定幅度内的多样性“冲动”或“抗争”。而毛泽东晚年在此问题上过分夸大了生产关系的反作用,走向了极端片面性。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总结毛泽东晚年在此问题上的失误与教训,以改革生产关系为手段,重构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的社会发展动力机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10]4这里所言的“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主要是指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一致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即毛泽东时代主观建构的共产主义社会先进生产关系和建立在纯之又纯公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所谓先进上层建筑。脱离于具体社会历史发展现实的人为主观建构,必将最终沦为不切实际的空想,不但无利于推动生产发展、巩固经济基础,反而会引发连锁负面效应。
邓小平的改革正是以毛泽东时代的虚幻生产关系与经济基础为切入点,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切实座架于客观现实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真实经济基础生存状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比较不发达的现实情况,决定了生产关系的基本层次与内涵特性,即在社会经济形态上必须摆脱纯之又纯的公有制经济,建立一种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混合制经济;在经济体制层面必须抛弃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理想社会存在的单纯依靠计划的单一经济手段,实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述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层面的改革,不是所谓强调“反作用意识”所催生的使落后生产力符合先进生产关系的运作,而是建立在对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符合的基础之上,是对社会发展动力机制基本运行方式的充分承认与当下重构。
(二)以坚守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作为社会平衡机制恰当建构的合理性依据
毛泽东时代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平衡机制的建构,从其理想规划而言,基本上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想蓝图。但是,其最大的问题在于脱离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具体历史阶段性限制,不恰当建构了“超脱”的社会发展平衡机制。关于社会平衡机制的建构,不应当从先哲的理想蓝图出发,也不应当从主观意愿、愿望出发,其必须根植于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具体历史现实,即建立在现实合理性基础之上的恰当性建构,即所谓“合法性建构”问题。因此,判断是否为“合法性建构”的依据不能是本本,也不能是主观思想,而只能是现实存在。因此,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平衡机制的“合法性”建构必须建立在对社会存在的真实、恰当把握基础之上。毛泽东时代之所以不恰当构建了社会平衡机制,其关键原因在于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性的错误定位。尽管毛泽东承认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仍然处于较为落后的发展阶段,但是“落后亦即优势”的意识加之“开除球籍”的危机感与紧迫感,使得快速发展、跑步前进成为时代构筑的“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在革命战争年代神话般胜利经验的催化下,中国在极短时间内就能进入共产主义似乎理所应当地成为必然性命题。因此,作为准共产主义存在形态的中国,业已悄然成为毛泽东时代人们“集体无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当时关于社会平衡机制正是基于不久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基本现实而加以建构的。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性做出了较为科学合理的判断——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平衡机制的建构必须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其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平衡机制的建构不能以牺牲动力机制为代价,其更多地应偏向于对动力机制的激励,但在此过程中也必须发挥平衡机制的作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现实,决定了主要矛盾是发展生产。而毛泽东时代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错误判断——更多地转向阶级斗争、转向社会主义理想平衡机制的建构,直接导致了社会发展动力的严重缺失。而后毛泽东时代,首当其冲的任务便是重构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以生产关系的改革为抓手,以促进生产发展为主要目标。在此过程中,必须着力解决重构社会发展动力机制的主要矛盾。较之于动力机制的重构,平衡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应更多地居于次要性地位。因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工作重心是搞好经济建设,坚持“一个中心”坚决不动摇。然而,辩证法的非平衡性原理关于非主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其主导型作用的规定,也预设了平衡机制不容抹煞的历史性作用。因此,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也明确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平衡机制的建构。
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平衡机制作用的发挥,更多地是通过彰显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路径而加以实现。毛泽东时代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认识,更多地是侧重于从静态层面出发、从社会主义的结构性要素出发而加以理解。因此,社会主义必然呈现出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理想社会设想基本符合的结构性存在,诸如公有制、按劳分配、阶级斗争和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等。社会主义的平衡机制也据此由上述结构性要素所决定,并发挥其调节、稳定社会发展的作用。其实,上述关于理想社会主义状态的描述在某种程度上也内在构成了社会主义平衡机制的主要内容。换言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社会主义的平衡机制从本质上优于资本主义社会平衡机制,因而具有先在的历史必然性,其更多是内在地由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所决定。但是,毛泽东时代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一定的片面性——理想性与静态性。这直接导致了社会平衡机制的非现实性与固化性生成,即社会平衡机制与社会现实生存状态的部分“脱节”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平衡机制强化与动力机制弱化的交互作用。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较之于以往显现出其独具的特征——现实性与动态性,即在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科学判断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实现了结构与功能的双向互动,并且基于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更多地向功能层面偏转。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不仅包含特有的结构性要素,诸如公有制、按劳分配等,其在初级阶段也具有特定的功能性要求——解放发展生产力等。正是基于关乎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科学判断基础上,社会主义社会的平衡机制更多地是通过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科学理解得以呈现,其建构得以符合现实生产发展需要,以更加生动、科学的形式“出场”。
总而言之,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是关乎社会主义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二者处于辩证统一的动态关系格局之中,缺一不可,过分偏向任何一方都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科学处理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的关系问题,如何在既保证社会发展动力澎湃的同时也使社会发展充满平衡因子的作用,仍是需要我们不断加以思考与探索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李忠杰.论社会发展的动力与平衡机制[J].中国社会科学,2007(1).
[2]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毛泽东哲学批注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6]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7]G·A·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M].段忠桥,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张海波】
Further Reflections on the Selection of Mechanism for Socialist Developmen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cusing on Dynamic Mechanism and Equilibrium Mechanism for Social Development
ZHANG Mi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Abstract:The coordination of dynamic mechanism and equilibrium mechanism is key to the sustainab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a society. The dynamic mechanis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socialist society has not broken through the restraints of the general law of human society, i.e., the movement of inner contradictions of production mode, while the equilibrium mechanism presents itself, to a great extent, by manifesting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socialism. During Mao Zedong Era,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mentality of “backward is also an advantage”, the decisive role of “non-dominant” factors in dynamic mechanis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history in general was overstated, which resulted in the mistake of generalizing class struggle to promot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onsequently set up an obstruction to social development. As for equilibrium mechanism, due to the one-sided understanding of Marx’s criticism on the “equilibrium predicament” of capitalism, it was placed high above dynamic mechanism, which led to the mistake of egalitarianism, and consequently the loss of dynamic mechanism for social development. The CPC, represented by Deng Xiaoping sorted out he mistakes made by Mao in his late years, straightened out the “disordered operation” of the two mechanisms, addressed the coordinating relationship of the two in a dialectical approach, and thus opened up a new prospec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socialist society; social development; dynamic mechanism; equilibrium mechanism; Mao Zedong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6)02—0039—08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问题意识、特色情结与理论自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路径研究”(15MLC006)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明,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研究员、博士后,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
【收稿日期】2016-0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