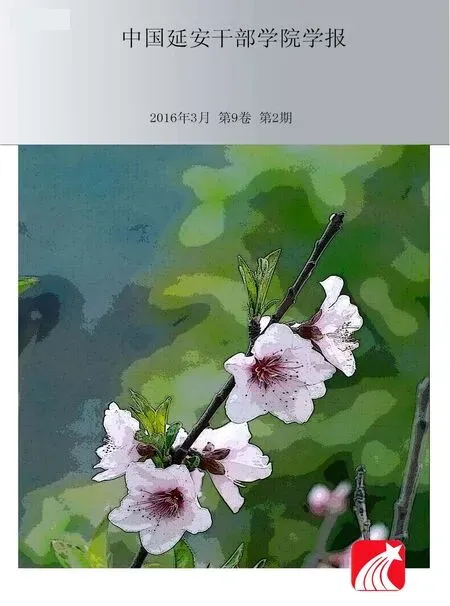农地流转中的政府和市场要素研究
张悦,刘文勇
(1.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海淀100193; 2.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北京海淀100081)
农地流转中的政府和市场要素研究
张悦1,刘文勇2
(1.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海淀100193;2.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北京海淀100081)
【摘要】在我国农地流转实践中,政府和市场是最主要的两个影响要素。政府在农地流转中扮演着制度制定者、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不过,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存在角色差异。“村集体”与“村委会”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政府需要完善村委会的监督机制。农地流转市场可以分为“交易内层次”和“交易外层次”,不同的市场环境中,农地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有明显差异。政府应该加大农地租出者的非农就业能力,提高其种植农地的机会成本,同时增加农地租入者的补贴,以此促进农地流转。
【关键词】农地流转;政府要素;市场要素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地流转速度不断加快、规模持续扩大。农地流转面积占承包农地总面积的比例,从1992年的不到3%增长到了2014年的28.8%。在农地流转快速发展的浪潮中,政府和市场作为最重要的要素,共同建构起农地流转发展的大环境,决定着农地流转实践的走向。政府是保证“土地”作为流转商品的基本特质的主体,保障实施“地权稳定性”和“地权完整性”。市场是农地流转所发生的环境,交易是否发生,取决于参与农地流转交易活动双方所面临的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
一、文献回顾
已有文献对农地流转中政府的角色和行为进行的研究,包括当前政府在农地流转中的作用、问题、原因,以及对政府角色定位和功能完善的建议。关于政府在农地流转中扮演角色和发挥作用的研究,大部分学者持有相似的观点。刘飞飞(2010)[1]认为在农地流转的过程中政府应该扮演“掌舵者”角色,在尊重市场机制配置农地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与优势前提下,必须充分发挥宏观调控作用。曾祥炎和王学先(2004)[2]认为政府干预的目的是调节市场失灵,中心任务是纠正土地买卖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郭晓鸣等人(2010)[3]认为政府应该在农地流转中起到以下作用:政策指导、程序设置及服务、流转后的就业及社会保障。政府在当前的农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制度、机构、服务和监管上的缺位;二是地方政府在农地流转中的过度介入导致的越位(萨仁娜等,2010[4];刘红沙,2010[5];李鹏,2010[6])。
也有学者对农地流转的市场环境要素做了研究和讨论。农地流转是农户在最大化收益动机下的一种市场交易行为(胡新艳,2010)[7]。因而,农地流转必然受到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的影响。交易成本方面,罗芳和鲍宏礼(2010)[8]的研究指出交易成本越高,则土地自给自足的可能性越大,即农地流转的可能性越小。罗必良等人(2012)[9]研究指出,农地流转的交易过程、外部环境和第三方组织产生的交易费用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农地流转合约安排产生的交易费用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Dieninger和Jin(2005)[10]的研究指出,减少土地租赁市场的交易费用有助于实现更显著的额外的生产收益。机会成本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必然引起耕地流转,这也是农地流转的重要动因之一(文雄、曾福生,2001)[11]。Kung James Kai-Sing(2002)[12]的研究发现农户租入农地的需求受其非农就业状况和劳动力转移状况的影响。农户家庭非农就业率每提高1%,农村土地流转率就将提高16.26%(谭丹、黄贤金,2007)[13]。刘卫柏(2011)[14]研究发现非农收入比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意愿产生正向影响,非农收入越多的农户越倾向于参与农地流转;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来看,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户比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农户更加倾向于参与农地流转。赵阳(2007)[15]另辟蹊径地通过Logistic模型从农地市场发育的角度进行分析,发现非农就业是影响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决定性因素。
已有研究呈现出了政府和市场要素对农地流转的重要影响。本文对此问题展开进一步的分析,并在分析的基础上对农地流转中面临的现实发展困境提出相应的建议。
二、农地流转中的政府
在中国当前的农地流转中,政府是最主要和最必要的参与主体之一。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政府应在制度变迁中充当不可替代的角色,尤其是在制度规范与法制建设以及农村土地优化配置过程中,政府作为制度创新主体担负着重要的责任。
(一)农地产权制度中的政府角色
农地产权的确认和维护,依赖于农地产权制度的建立与维护,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是一个值得单独讨论的因素,因为政府为产权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如果将政府视作一个主体,那么它在产权制度发展过程中可能的作为有两种:一是制定并担保产权结构;二是提供好的公共产品。换句话说,政府既是制度环境的创造者与守护者,又是制度环境中不可或缺的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首先,政府是产权制度的制定与担保人。历史上涉及农地产权制度的案例不胜枚举,农民革命中革命者所倡导的对农地重新划分,实际上就是新政权废除旧的农地产权制度、制定新的产权结构的过程。将视角移回到当前社会,政府的作用亦未曾变更。在1980到1984年左右,中国政府在事实上承认了原先“一大二公”的农业生产体系的失败,在全国范围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政府在这个制度的变迁过程中所担当的就是制度制定者的角色。1984年,中央要求农地承包时间15年不变, 1993年又再一次提出农地承包的时间年限继续延长30年,这些政策都是在替现有的农地产权制度背书。2004年以来,历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是如此。
其次,政府是诸多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政府之所以提供公共产品,是因为公共产品必然存在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搭便车”的行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从而导致“市场失灵”。如果私人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必将被挤出市场。因而,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只能是政府,对农地产权制度同样如此。
此外,在我国当前的农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政府的角色具有特殊性。在农地私人所有制的情况下,政府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制度维护者。在农地国家所有制的情况下,政府是土地的所有者。但是,在我国农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并没有一个实体化的主体来拥有农地的所有权利。权利虚化的村集体不知道以何种形式维护农地的完整所有权。因此,政府这个原本意义上“所有制”的担保者,容易因为各种诱因参与到产权的认定乃至行使过程中来。
(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角色差异
我们不应简单地将政府看作单一主体,而应该为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是中央政府,二是地方政府。一般来说,与农地流转相关的政策、法规等文件都是由中央政府发布或审定的。中央政府对于农地流转实践并非第一线的操作者,其出台农地流转法律法规是以国家为主体,追求国家层面的利益最大化(或称效率最大化)。这使得中央政府的提案一般都会符合基本经济规律,促进生产力快速有效的转移。但是,也正因为中央政府并非农地流转实践的第一线操作者,农地流转实践过程之中容易出现“一刀切”的问题:中央政府一般很难认识到不同环境中,特别是不同市场条件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情况下,各地的农地流转实践的具体情况,适合的政策也难以制定。
在农地流转的实践中,应该划分出来的第二个层次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概念是宽泛的、变动的,出于简化分析对象的考虑,可以认为直接参与农地流转实践的政府便是地方政府。在很多情况下,县域经济所主导的县级政府是最可能的地方政府主体。不过,也存在某些强势的市政府,地方政府可能表现为市一级的政府。而且,一些村委会也承担了部分地方政府的责任。相对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是“短视”的、“务实”的,容易为了政绩而不执行中央政府已有政策,或是实施与中央政策并不完全一致的,但更符合当地农地流转实践的政策法规。
(三)政府对村委会的监督机制
基于《宪法》的农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农地制度的本质特质。“集体”与“个体”的概念并不一致,后者是一个单独的“实体”概念而前者是一个虚化的“集合”概念,这样的“集合”概念难以如一般性实体那样承担明确的权利,由此引发的排他性产权不明晰导致了诸多问题。为了尽可能地减少产权不明晰而导致的租值消散,应该在完善现有的中国农地制度基础上所构建的“村集体”与“村委会”之间的“委托—代理人”机制,以政府作为外部力量,监督“村委会”可能出现的投机行为,以强制政策设置信息流通和公开的体系,减少“委托—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从而促使排他性产权的明晰过程不会受到“委托—代理人”机制的负面影响。
对于现有的中国农村地缘政治,可以套用“委托—代理人”的体系来分析。尽管农地是“集体所有”的,但是集体并非一个实体概念,在现实之中需要一个实体来完成管理工作,因此,需要村集体通过村民代表大会选举的形式,成立村委会来具体承担相关职能。当然,村委会的成员也是来自村民自身,因而,村委会的成员事实上同时存在了“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双重身份。但是,为了简化逻辑、便于分析,仅探讨村委会成员的代理人身份。基于“委托—代理人”理论,村委会作为代理人应该比委托人,也就是普通的村民,拥有更多的机会掌握信息,并且了解到何种资源分配方式会更加有利于自己。“代理人”的投机行为无疑将会增加委托人(村集体)的成本。上述现象出现的必然性在于,村委会的效用函数(利益相关内容)与村集体的效用函数之间的不一致性。
在理论上,为了从一定程度上抑制代理人的投机行为,委托人会设立一定的监督机制来约束代理人的行为,并且构造某种方面的惩罚机制来警戒违规行为。不过,前提是这些“监督机制”与“惩罚措施”的执行成本,要低于由于代理人的投机行为而造成的损失。但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当前的农地制度下,由委托人(村集体)设立“监督机制”与“惩罚手段”来约束代理人的行为几乎是不可能的。普通村民很难有能力挑战村委会,更难以设立所谓“监督机制”或者“惩罚手段”来约束村委会。其原因是村委会成员往往也在村级党组织中任职,而农村的村党委书记,往往是由上一级的乡镇党委直接指派的,因此普通农户容易将村委会看作是政府的代言人,甚至村委会本身成员也容易产生这种错误认识。在这种错误的认识下,村委会很容易被认定为是政府的代理人,代表政府在管理村庄,而不是代表村集体谋求集体利益最大化。
委托人(村集体)的相对弱势地位,使得真正意义上由委托人发起的对待代理人(村委会)的监督机制很难顺利地建立起来。政府及党政机关应该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的措施协助委托人建立良好的监督管理机制。比如,可以通过政策,迫使代理人(村委会)将原有的专有信息公开,降低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在现有政策中,基层党组织和政府所专门建立的“村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就是对上述机制的实践探索。事实上,带有政府命令性质的各村的村务公开、党务公开,乃至财务公开,都属于此类范畴。如果以上的政策真的能够实现,那么原本应该归属于村集体的排他性产权将更少地转化为代理人也即村委会的寻租行为,因而排他性产权的明晰化也就能够得到实现。
三、农地流转中的市场
总体而言,农地流转交易市场可以被划分为两个层次:“交易内层次”与“交易外层次”。交易内层次市场环境,仅仅局限于农地流转活动本身,参与主体是诸多的农地租出者与农地租入者,他们在交易内层次相互碰撞,交易成本在这一层次中产生影响,这是简单的市场交易活动过程。交易外层次市场环境则是指农地流转交易活动所处于的宏观经济环境,通过机会成本对交易活动本身产生重要影响。
(一)交易内层次的市场
市场在农地流转交易内层次的作用主要是降低交易成本。商品交易过程中信息的获取是有成本的,很多交易会由于难以获取交易对象或者交易成本过高而停滞。调查发现,很多农户如果选择进行农地流转,更可能的农地流转交易对象是存在血缘关系的亲属。究其原因,在于如果交易对象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则寻找到交易对象的成本比较低,而且也不容易出现合约违规的现象。但是也有不少农户反馈出一些与自己亲属交易的弊端,比如,没有办法商谈价格。事实上,这是因为寻找普通的农地流转对象交易成本过高导致的。面对这样的困境,需要发挥市场的作用,建立作为信息公开和交流平台的农地流转中介组织,提供交易流程服务,以便让农地流转的双方迅速地找到对方并顺利达成交易。
农地流转中介的创建形式,既可以是以“乡镇”为单位的较小地域的农地中介,也可以是以“省”为单位的较广地域的中介。在条件成熟时,甚至可以尝试考虑建立健全全国性质的农地中介。应该说较小区域的农地中介是政府比较容易接受的,农地的流转一般是在特定的地域内,管理起来比较轻松。相邻村落之间的农地流转在实践中也会出现。调研中发现,黑龙江省有的农地租入方所租种的耕地就来自相隔数十里的另外一个村落,属于跨村落间的农地流转。应该鼓励跨区域乃至跨省间的农地流转。比如,一个黑龙江农户,如果拥有足够强的管理能力,并且可以通过合法的市场手段解决劳动力与劳动资料等诸多问题,就应该鼓励跨省租种,以更好地拉平生产效率之间的不均衡。事实上,跨省的农地流通并不算是什么新鲜的现象,目前在北京周边地区,已经有很多外地农户愿意租京郊的农地来耕种经济作物,这从本质上来说就是省际间的农地流转,更好的农地流转也会促进农地利用效率的提升。
农地流转中介的资质,既可以是“公立”性质的,也可以是“私立”性质的,甚至可以是“公私并存,各有所长”。政府有诸多不必要的担心,认为农地流转信息的流通可能会影响国家安全,实则不然。私立的“农地流转中介”就像“城市房屋流转中介”一样,会主动去寻找信息并且贩售这些信息,促使市场活跃化。只要这些“私立”的农地流转中介所贩售的信息价格低于农户自主寻找信息所需要花费的交易成本,市场就将保留它们存在的必要性。政府所设的农地流转信息中介可以着力发布指标性的、宏观性质的信息,将琐碎的、需要市场调节的农地流转信息留给私立的农地流转中介也未尝不可。
(二)交易外层次的市场
在讨论农地流转市场的时候,易于出现这样一个错误倾向:将“农地流转”市场割裂开来,忽略了农地流转市场存在的外生影响问题。由于我国人均农地面积小,而农业人口众多,因而有大量的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特别是从农业流入第三产业,因此中国的农地市场问题从某种侧面来讲也属于我国第三产业发展状况的反馈。内外两个市场之间的联动作用是紧密的,甚至是决定性的。近年来政府提出的城镇化的进程,将极大程度上影响农地流转市场的交易外市场,对农地流转市场的达成起到至关重要的联动作用。具体来说,外部市场将不只是接纳农地租出者的劳动力输出,更重要的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机会成本。
农地流转交易内层次的市场极易受到交易外市场的影响,而这是机会成本的终极体现,将影响利益最大化的实现。一个拥有良好交易外市场的地区,比如小城镇就业较容易的地区,农户家中闲置的农地更容易被投入到交易内市场中。一个农户能够从非农领域所获得的最高收益,就是他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而一个农户能够在农业领域获得的最高收益,则是他从事非农工作的机会成本。一个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不是决定于主观上是否愿意响应参与农地流转、形成集约化生产的号召,而是决定于他在参与流转后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与从事非农生产的机会成本差值如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实现农地在一定范围内流转,形成农业种植的产业化、专业化与规模化经营,除需要对农业产业本身发力之外,亦应该着重发展第三产业。制定相关政策,将小城镇中的第三产业发展起来,提高农户的农业外就业机会,提升农户种植农地的“机会成本”。
相对应地,从农地租入者的角度来分析,如何加大对种植大户的扶持,则是提高农地租入者收益的另一组政策方向。这些政策措施是为了降低农地租入者种植农地的机会成本,促成实现农地的集约化生产。在这个方面,常见的举措是加强农业补贴的力度。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即开始了农业补贴的政策,而在21世纪初开始出台了包括减免农业税、对粮食进行直接补贴、对良种进行选择性补贴等一系列农业补贴和支持政策,希望提高潜在农地租入者的种地预期收益额度,促进农地流转过程中农业租约的形成,最终实现农地利用的最大化。与上述政策类似,政府政策中所执行的粮食作物确定最低收购价格等粮食保护措施,也是在相同方向起作用。
针对机会成本的市场可以采取“区别对待,分头支持”措施。对于农地租出者,加大其在第三产业的就业能力,促使其种植农地的机会成本升高。而对于农地租入者,增加以农业种植用地为直接补贴对象的农地补贴,提高其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两者看似矛盾,却有统一的目标,即尽可能平稳地分化现在农地上的农户,通过农地流转,使得农业生产规模化和农业人口城镇化两种趋势相伴随。
参考文献:
[1]刘飞飞.基于农地流转的政府角色定位及行为模式探究[J].安徽农学通报,2010.16(13).
[2]曾祥炎,王学先.加强政府对农地流转的干预——对台湾第二次土地改革的反思[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2).
[3]郭晓鸣,韩立达,王静.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政府行为——基于成都市的分析视角[J].农村经济,2010(12).
[4]萨仁娜,张绍良,卞晓红,章兰兰.湖北省赤壁市农地流转市场中的政府行为[J].国土资源科技管理,2010(10).
[5]刘红沙.论农村土地流转中政府职能的优化[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8).
[6]李鹏,王文昌,王秦俊.农地流转中政府行为失范的成因及对策探究[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
[7]胡新艳.促进我国农地流转的整体性政策框架研究——基于市场形成的逻辑[J].调研世界,2007(9).
[8]罗芳,鲍宏礼.非农就业对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影响的理论分析[J].广东农业科学,2010(7).
[9]罗必良,汪沙,李尚蒲.交易费用、农户认知与农地流转——来自广东省的农户问卷调查[J].农业技术经济,2012(1).
[10]Klaus Dieninger, SongqingJin.The potential of land rental markets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78 (2005), 241-270.
[11]文雄,曾福生.从农业劳动力视角看我国农地流转的成因[J].经济地理,2011(4).
[12]Kung, J.K.S.Off-Farm LaborMarkets andtheEmergence of LandRental Markets inRural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es,2002(30):395-414.
[13]谭丹,黄贤金.区域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以江苏省宝应县为例[J].中国土地科学,2007(12).
[14]刘卫柏.基于Logistic模型的中部地区农村土地流转意愿分析——来自湖南百村千户调查的实证研究[J].求索,2011(9).
[15]赵阳.共有与私用——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经济学分析[M].北京:三联书店,2007.
【责任编辑刘传磊】
On Government and Market Factors in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ZHANG Yue, LIU Wenyo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3;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Abstract:Government and market are two major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transfer of agricultural land in China. Government plays a role of policy-maker and supplier of the public goods. However, the roles play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are different. “Village committee” is the “entrusted-agent” of the “village collective”, and government should improve oversight mechanism over village committees. Based on the “level within the transaction” and “level outside the transaction” on the market of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transaction cost and opportunity cost on the transfer. At present, it is important to increase the non-farming employment ability of the land leasers, improve their opportunity cost of crop-planting, and meanwhile increase subsidies for land renters so as to promote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Key Words: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government factor; market factor
【中图分类号】F301.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6)02—0132—05
【作者简介】张悦,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刘文勇,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文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6-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