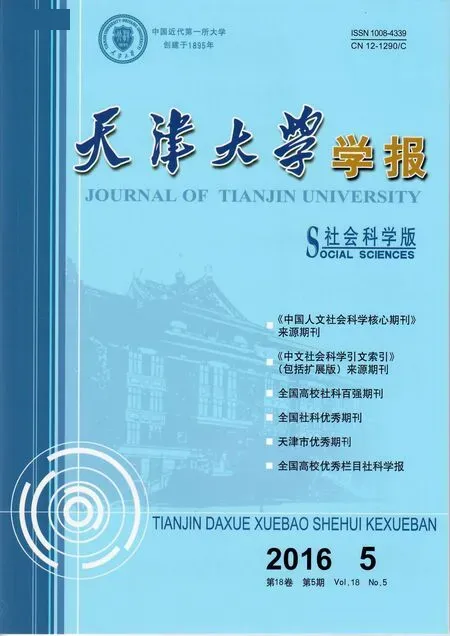韵律对汉语介词功能转化的影响
王用源
(天津大学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 天津 300072)
韵律对汉语介词功能转化的影响
王用源
(天津大学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 天津 300072)
文章以“于”“以”等介词功能的转化为观察点,考察了汉语韵律对介词功能转化的制约和影响。汉语介词功能转化的途径和去向既受到韵律的驱动,同时也要受到韵律的制约。韵律可引发句法结构的重新分析,从而导致介词功能的转化。不管是介宾短语词汇化,还是含有介词的跨层结构词汇化,抑或是介词虚化而来的连词参与跨层结构的词汇化,都要受到双音节音步韵律节奏的制约。韵律促使介词附缀化,特别是后缀化,还可导致介词的零形化。
韵律; 介词; 功能转化; 语法化; 词汇化; 零形化
句法位置、韵律制约、语用驱动等诸多因素可引发介词的再虚化,从而导致介词功能的转化。不同介词处于不同的句法位置,在韵律制约下表现为不同的功能转化方式,有的从介词虚化为连词,再由连词功能转化为构词功能,有的从介词功能直接转化为构词功能,有的成为零形式。已有学者探讨过介词的发展演变与韵律之间的关系,如冯胜利先生揭示了介宾短语不能自由地出现在句末动词之后的原因,论述了韵律驱动的介词移位、韵律导致的介宾分置等问题[1]。在介词功能转化的过程中,韵律又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如何影响介词功能转化的途径和去向呢?本文主要以“于”“以”等介词功能的转化为观察点,考察韵律对介词功能转化的制约和影响。
一、 韵律驱动下的介词功能转化
有些语言单位由词汇形式语法化后,可继续虚化,以另一种身份参与词汇化,从语法层面“回到”词汇层面,但这不是简单的、可逆的循环演变。不少学者早已注意到“于”进一步虚化后可从介词转化为构词成分。如郭锡良(1997)指出介词“於/于”可进一步虚化,同别的词构成固定结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介词“于”已经向语素的方向虚化了[2]。马贝加(2002)认为:“有的介词失去词的身份,成为构词成分。”[3]刘丹青(2003)指出,“语法化不一定停留在某种虚词阶段,而可能朝更虚的单位语法化,进入下一个阶段,形成语法化链,直到语音上成为零形式”[4]。这些都是语法化的结果,导致这些词汇化、零形化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认为韵律是重要因素之一。
下文的分析,我们将看到韵律驱动和韵律制约下的介词功能转化大致可表现为四种情形:一是双音介宾短语在特定的句法位置高频使用后实现词汇化,介词功能得以转化为构词功能(如“于是”“何以”);二是韵律可引发含有介词的双音跨层结构重新分析,从而导致介词转化为词内成分(如“善于”“加以”);三是介词转化为连词后,在韵律驱动下再参与构词(如“以免”“以期”);四是韵律结构容许含介词的超音步(如“来自于”“倾向于”),但同时对其进行调节,最终致使部分介词零形化。本节先谈前三种情况,第四种情况下节再谈。
(一) 韵律驱动下的介宾短语词汇化
当单音介词与单音宾语的组合高频使用并处于特定的句法位置就可能词汇化,介词就从独立的语法单位演变为构词成分,其介词功能和语法意义消失。在韵律的驱动下,能词汇化的介宾短语一般是双音节的,个别为三音节的(如“于是乎”)。介宾短语的词汇化首先离不开韵律的作用,在韵律驱动下,介宾短语组成一个音步,成为一个韵律词,进而才有可能实现词汇化,这也是多音节介宾短语难以词汇化的原因所在。下面分别以“于”字和“以”字介宾短语的词汇化为例来考察其介词功能的转化。
先秦,介宾结构“于是”很常见,其中“是”是表示时间的指示代词,用于对上文所提及的时间背景进行复指。“于是”有时写作“于时”,如《诗·周颂·我将》:“我其夙夜,畏天之畏,于时保之。”郑玄笺:“于,於;时,是也。早夜敬天,於是得安文王之道。”“时”可用来指上文提及事件发生的时间,但常用“是”来指代,所以多作“于是”。“于是”常用于句首或后一分句的句首,占据连词的位置,就容易被重新分析为连词①。例如②:
例1:庄公将杀管仲,齐使者请曰:“寡君欲亲以为戮,若不生得以戮于群臣,犹未得请也。请生之。”于是庄公使束缚以予齐使,齐使受之而退。(《国语·齐语》)
例2:于是明日得之城阴而刺之,济阳君还,益亲之。(《韩非子·内储说下》)
例3:对曰:“昔桓公之霸也,内事属鲍叔,外事属管仲,桓公被发而御妇人,日游于市。今齐王不信其大臣。”于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子之闻之,使人遗苏代金百镒,而听其所使。(《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如果说例1的“于是”仍是介宾短语也未尝不可,但例2“于是”后面有时间名词,“于是”就可分析为表承接关系的连词,例3“于是”位于句首,主语“燕王”后面还有个“因”,“于是”只能分析为连词。
“以”字介宾短语的词汇化与“于”不同。据郭锡良(1998):“‘以’字在甲骨文中是一个动词,西周以后是一个非常活跃的虚词,先由动词虚化成介词,再由介词虚化成连词,或构成固定结构,再凝固成词,转化成构词语素。”[5]“以”的介词宾语前置是一个特殊现象,其他介词的宾语很少前置(“为”“与”的一些宾语可前置)。先秦“以”的代词宾语常前置,如“是以、胡以、何以”等就是宾语前置式结构,由于这些组合的高频使用,且常位于后一分句的句首,经常用来陈述动作行为的原因或询问原因,这些结构可经过重新分析而发生词汇化。“代词+以”词汇化并沿用至今的主要是“何以”和“所以”,有的没有沿用下来,如“是以、此以”。后来,在汉语的发展过程中,介词宾语不再前置,“以”也可以与单音宾语实现词汇化,如“以是、以此”等[6],但这类结构的词汇化程度很低。例如:
例4: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左传·僖公四年》)
例5: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复返也。(《史记·魏公子列传》)
以上是双音介宾短语词汇化致使介词功能转化为构词功能,但不是所有的介宾短语都能词汇化,还要受到句法位置、使用频率、语用驱动等因素的影响。如果介词宾语不是单音节的,介宾短语就不能词汇化,也就不能导致介词功能的转化,究其原因,双音介宾短语在特定的句法位置高频使用,构成韵律词,再转变为词内成分,根本原因在于韵律的驱动。
(二) 韵律驱动下的跨层结构词汇化
有些介宾短语可以词汇化,有些含介词的跨层结构也可词汇化[7],如“终于、由于、善于、可以、足以、加以”等,这些结构的词汇化也离不开韵律的影响。
先秦两汉时期,“于”是一个多功能介词,由它构成的介宾短语通常位于谓词(动词V或形容词A)之后,“于”先与后面的成分组成介宾短语,充当补语,其结构为“V/A+[于+N]”,“V/A+于”属跨层结构。据张赪(2002)[8],大约从汉代开始,介宾短语从谓词后大规模前移,谓词后的介宾短语成了残留成分。有人认为,“恰恰正是这种残留成分比较容易发生语法化,此时它有了向前面动词靠拢的倾向”[9]。我们认为,“于”附着在谓词后的直接原因不是因为它是残留成分,而应归因于汉语韵律的影响。冯胜利认为汉语古今的重音范域是不同的,核心重音后移是汉朝以后汉语的一大特点,核心重音的后移致使介宾附加语前移[1]4。留在谓词后的介宾短语受限③,需改变句法结构来满足重音的指派,于是“于”开始附缀化。
“至于”,《现代汉语词典》标注为动词(表示达到某种程度)和介词(表示另提一事)[10]。“至于”原为动介跨层结构,其结构为“至+[于+NP]”,“至”“于”在线性序列上相邻,受韵律影响,重新分析为“[至+于]+NP”。汉代以后,“至于”发生词汇化,变为一个动词,而后再语法化为介词[7]269-270。不少学者将句首的“至于”视为连词,即“至于”再语法化为连词,“于”的介词功能就彻底消失。暂且不论“至于”的词性,就介词“于”而言,其介词功能的转化无疑是韵律驱动的结果。再如,“由于”,《现代汉语词典》标注为介词(表示原因或理由)和连词(表示原因)。两汉时期,“由于”是动介跨层结构,后来逐渐凝固继而词汇化。当“由于”后接体词性成分或非小句的谓词性成分时,具备介词的功能;当它位于句首,后接可充当小句的谓词性成分时,就具备连词的功能。跨层结构“V于”还可词汇化为动词、副词等,动词如“善于、敢于、甘于、归于”等,副词如“终于、便于”,这些都是在韵律驱动下的附缀化。
“以”的跨层结构词汇化比“于”复杂些。在韵律的影响下,“于”一般后缀化,而“以”有前缀化和后缀化两种,这与“以”的介词宾语省略有关,也与韵律的影响有关。现代汉语介词的宾语一般不能省略,而古汉语介词“以”的宾语省略最为常见,因其宾语的经常性省略,致使“以”的发展演变不同于其他介词。刘丹青(2004)指出:“介词悬空是造成汉语语法史上若干重要的语法化和词汇化的重要原因。”[11]介词宾语的省略为介词与其他词进行线性组合提供了句法条件,也为自然音步的重新组合提供了契机。
“以”可由介词悬空进一步虚化为连词,“以”不前附也不后附时,独立成词,即由介词转化为连词;有时在韵律的驱动下可以前附或后附,与其他词组合进而发生词汇化(下文再讨论介词“以”转化为连词后的词汇化)。
“而以、可以、足以”均因“以”的宾语省略后,“以”与前面的单位构成一个韵律词而逐渐词汇化的[12]。“而以”是由连词“而”和悬空介词“以”词汇化而成的复合连词,但它未沿用至今。“可以”是由助动词“可”和悬空介词“以”词汇化而成的助动词。“足以”是由形容词“足”与介词“以”词汇化而成的助动词。“以”的宾语省略后,它还可以与其后的单音节词组合成一个韵律词而实现词汇化,比如,“以为”是由悬空介词“以”和动词“为”词汇化而成的动词。
“以”后带介词宾语,但受到韵律的调节,“以”也可能附着于前一音节,发生重新分析进而词汇化,我们将这类结构记作“X以”。《汉语大词典》收录了下列含“以”的词条:于以、不以、及以、予以、借以、加以、得以、既以、业以、有以、无以、施以、由以、藉以、给以、难以等。其中有些使用频率不高,词汇化程度较低,未能沿用至今,如“于以、既以、有以、由以”。个别“以”通“已”,如“既以、业以”。《汉语大词典》收录的并非都完成了词汇化,且有些例证欠妥,如“不以”的第一个义项为“不为,不因”,其例证为:
例6: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禄,不以大言受小禄。(《礼记·表记》)
例7: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第二个义项“不用;不靠”,例证为:
例8: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孟子·离娄上》)
我们认为,例6~8中的“不以”均未词汇化。《现代汉语词典》只收录了“借以”(连词)、“加以”(连词、动词)、“予以”(动词)、“得以”(动词)、“给以”(动词)、“难以”(动词)、“致以”(动词)④等。这些“X以”的词汇化源于“X+[以+介词宾语]”结构,两汉以后,受到普通重音指派规则的影响,“以”并入谓词,被重新分析为“[X+以]+宾语”,这类“X以”词汇化后多为动词。也有由“[V+宾语]+[以+介词宾语]”演变而来的,动词宾语省略而成“V+[以+介词宾语]”,“以”后缀化而形成“[V+以]+宾语”,如“加以”的词汇化[13]。
从“于”“以”介词功能的转化可见,跨层结构的词汇化往往是经过重新分析来实现的。冯胜利认为:“‘重新分析’只告诉了我们这里发生了什么,并没告诉我们为什么这种现象一定要发生。……我们的解释是:这里动词跟介词的重新分析之所以一定要发生是汉语的特殊韵律结构的要求,是由重音的指派所造成的。”[1]221我们赞同此说,并认为跨层结构的词汇化是韵律驱动的结果,不符合汉语韵律结构要求的跨层结构难以词汇化。比如,当V不是单音节时,即使“V+于”能组块也难以词汇化,如“消失于”;当V不是单音节时,“以+V”也难以词汇化,如“以获取”。我们就得到这样的认识:跨层结构的词汇化也离不开汉语韵律的驱动,韵律可引发重新分析,从而导致介词功能的转化。如果将跨层结构形成的韵律词看成是介词附缀化的结果,那也是韵律驱动下的介词附缀化。
(三) 介词“以”转化为连词后的词汇化
介词“以”很早就进一步虚化出连词功能了,且用法灵活。连词“以”常跟“上、下、来、前、后、内、外”等词搭配,表示一定的范围义,这些组合高频使用进而词汇化,“以”的连词功能转化为构词功能。“以上、以下”等中的“以”是介词还是连词尚有分歧,多数学者认为这个“以”是连词,少数学者认为是介词。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古代汉语虚词词典》[14]和何乐士《古代汉语虚词词典》[15]都认为与“上、下、来、往、南、北”等词组合表示范围、时间的“以”是连词,向熹也认为“以上、以下”中的“以”为连词[16]。《马氏文通》认为“‘以’字司‘上’‘下’‘往’‘来’与方向等字,皆以为推及之词”[17],属介词;史冬青认为“以上、以下”中的“以”是引进动作行为涉及的方面或范围的介词[9]156-157。我们认为是连词性语素。《现代汉语词典》将“以上、以下、以后、以前、以内、以外、以来”都标注为方位词,它们还可通过隐喻来指称时间。还有一些组合尚未词汇化,如“以”与方位词“东、西、南、北”等的组合。除了常跟方位词组合外,“以”还可与“往、降”等组合成表示时间、范围的词“以往”“以降”等。
介词“以”虚化为连词后,“以”后面常接单音动词(记作“以V”),在语音上,“以”和单音动词组合为一个韵律词;在位置上,常位于后一分句句首,后一分句大多用来陈述动作行为的目的或结果,这为“以V”演变为连词提供了条件。同时,“以V”的词汇化也离不开V的变化,单音动词后面的宾语最初是名词性成分,后来扩展为谓词性成分后,这些结构就容易被重新分析,进而词汇化,如“以免、以期、以至、以致、以便”等。譬如,刘红妮(2008)对“以免”中“免”的宾语变化进行过考察,认为“以免”词汇化与“免”后所接成分的扩展有关,还与韵律上的和谐要求有关[18]。刘红妮(2009)认为“以V”类连词最初都是连词“以”加动词的非句法结构,都是在“VP1(,)以VP2”的句法环境中词汇化为连词的,也都经历了“以”因损耗而附缀化[19]。例如:
例9:某因此仇不共戴天,只得逃亡在外,以期将来报复。(明朝《七剑十三侠》)
例10:我倒早有此心,想将真经传入汉邦,以期感化愚民。(民国《汉代宫廷艳史》)
连词“以”要实现跨层结构的词汇化,就要求后接动词是单音节的,这是韵律的要求,否则连词难以转化为词内成分,如“以获取、以满足”。值得注意的是,介词“以”以后缀化为主,而连词“以”以前缀化为主,“以+V”词汇化后词性还是连词。在韵律的制约下,“V+以”是介词“以”并入动词;而“以+V”是连词“以”前缀化,在韵律的驱动下V演变为次要动词,并发生非范畴化,然后“以V”才得以词汇化。
二、 强化和零形化引发的介词功能转化与韵律制约
介词强化和零形化都是语法化过程中值得关注的现象,它们之间的关系密切。刘丹青(2001)认为:“语法化中的强化指在已有的虚词虚语素上再加上同类或相关的虚化要素,使原有虚化单位的句法语义作用得到加强。”[20]介词零形化,是指谓词后的介词因进一步虚化导致脱落而成为零形式。沈家煊(1994)指出:“语法格的各种表现形式可以排成一个等级,语法化的程度越高就越倾向于采用形尾和零形式:词汇形式(>副词)>介词>词缀/形尾>零形式。”[21]刘丹青也认为:“一个实词一旦开始语法化,那么它就踏上了语义虚化、句法泛化、语用淡化、语音弱化的不归路,由不足语法化、到充分语法化,到过度语法化,直到表义功能趋向于零、句法功能似有似无、语音形式走向消失。”[20]就语法化链的虚化过程来说,谓词后介词的虚化一般遵循这样一个过程:介词→后附缀/词缀→零形式,或介词→零形式。
介词的强化和零形化都是导致介词功能转化的因素,而这两种介词功能转化过程都要受到汉语韵律的制约,分述如下。
(一) 介词强化与韵律制约
根据强化介词所在的位置,可分为介词前的强化和介词后的强化。刘丹青(2001)认为:“为了维持语言的交际功能,语言常在语法化的一定阶段对语法手段加以更新或强化。”[20]就介词来说,其介引功能在使用过程中不断损耗,于是语言可采取同义强化的机制来补偿。刘丹青提及的是介词前的强化现象,如用“在”来强化“于”形成“在于”,这是“在”作为强化成分加在原有介词“于”之前来实现的。介词后也可以添加强化成分,陈昌来(2002)指出:“不少动词后介词在语音上跟前面动词相连,一些介词已经跟动词组合成一个合成词,并且‘动+介’后可以再带一个介词。”[22]为什么在原有介词后还可以再加上一个介词呢?我们认为“于”最初是用来补偿“自”介词功能的损耗。因为单音谓词与单音介词这一跨层结构在韵律的驱动下凝固为韵律词,介词发生附缀化(有些甚至词汇化为动介复合词),导致介词功能逐渐损耗,这时,在不违背普通重音指派规则的条件下,可在介词后再添加一个同义介词来强化,譬如“来自于、发自于、摘自于、倾向于”等。例如:
例11: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尚书·武成》)
例12:至于佛氏之学,来自西域。(章学诚《文史通义》)
例13:这些影响来自于社会,更多地来自于家庭。(1994年报刊精选)
例14:这种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地球内部和外部力量——太阳能。(北大语料库)
例15:你有了财富,你就必须拿出一部分来回报社会,因为你的财富来自社会。(1995年人民日报)
以上用例,其强化过程可分析为:
(a)[来+[自+NP]]
(b)[[来+自]+NP]
(c)[[来+自]+[于+NP]]
(d)[[[来+自]+于]+NP]
(e)[[来自]+NP]
汉代以后,受韵律结构影响,“来自”后的单音节NP受限。当NP为非单音节时,(a)中的“自”受到韵律作用,附着于“来”,重新分析为(b),“自”的介词功能损耗,为了满足语用需要,可通过添加强化成分“于”变为(c)(不是必须强化),但(c)只是过渡形式,不符合韵律结构的要求,在普通重音指派规则的制约下,“于”还会发生介词并入动词的运作,重新分析为(d)。动补结构(a)向动宾结构(b)发展,通过强化后又变为动补结构(c),这一强化运作又不符合韵律规则,因此汉语韵律会对此进行调节,迫使“于”附着于“来自”,发展到一定阶段并在语用需求的促发下,“于”可能脱落而成为零形式(e)。这样(e)和(b)在表层形式上就完全一样了,但是(e)中的“来自”与(b)中的“来+自”是不同的,由于“于”的零形化,(e)中“来自”将实现配价增值。
上例只是个案,不同“单音节V/A+P”的词汇化程度是不同的,P的书面色彩越浓,这一组合的使用频率越高,“单音节V/A+P”凝固为词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如“善于、属于、限于、加以、难以、借以、趋向、倾向”等。P虚化为词内成分后,其介引功能损耗,但是否需要强化,这与介词的虚化程度有关,如果虚化得越彻底,添加介词来强化的可能性就越小。据初步考察,介词后用来强化的介词一般是古老介词,所以,如果被强化介词已经很虚化了,添加比它更虚的介词的可能性就小。譬如,虽然有“源于自”“来于自”之类的用例,但相对于“源自于”“来自于”来说,它们属于“特殊序叠加”[23],用例极少。
从以上介词的强化和介词功能的转化来看,汉语韵律结构导致原有介词发生介词并入动词的第一次运作,介词功能的损耗和语用需要可引发介词强化,韵律又对强化形式进行制约,迫使强化介词发生介词并入复杂动词的第二次运作,并入后形成的三音节超音步受到标准音步的制约和语言经济原则等因素的影响,致使非单音节NP前的强化介词逐渐零形化。
(二) 介词零形化与韵律制约
目前,介词零形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于”字上。谓词后介词的零形化有三类:一是原有介词直接零形化;二是双音化和右向音步引起的零形化;三是强化引起的零形化。
1. 原有介词直接零形化与韵律制约
以“于”为例,如果谓词是单音节的,介词“于”可直接被删除。为什么要采用删除的运作呢?两汉以后,汉语是动词指派重音,“省略动词后面的介词,则可使动词直接将重音指派到后面的宾语之上”[1]239。这种情况下,介词功能直接消失。例如:
例16:辛巳,朝于武宫。(《左传·成公十八年》)
例17:辛巳,朝武宫。(《史记·晋世家》)
例18:卫侯欲与楚,国人不与,故出其君,以说于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例19:卫侯欲与楚,国人不与,故出其君,以说晋。(《史记·晋世家》)
若不采用删除介词的运作,有些“V/A+于”可构成一个双音步,就可能从韵律词演变为词汇词,如“归于、善于”,介词的介引功能就转化为构词功能。
如果V/A是双音节的,即使“V/A+于”能组块,但三音节“V/A+于”也难以词汇化,其中的“于”不稳定,要受到汉语普通重音指派规则的排挤,从而导致介词功能的转化甚至消失。张谊生(2010)对“V/A双+于”进行过考察,认为当“于X”位于双音节动词、形容词后面时,一部分“于”仍然是介词,但也有一部分已转移后附,已成为或接近一个类后缀。并进一步指出:“从韵律化和双音化的角度来看,无论这个‘于’目前是介词还是附缀,只要发展到一定阶段,并且在表达需求的促发下,所有双音节‘V/A’后面的‘于’,都有可能脱落而成为零形式。”[24]
可见,“于”之前谓词的音节数量决定着“于”的去向,但从本质来看,是韵律制约着介词“于”的去向。如果谓词是单音节词,介词“于”要么直接被删除,要么与单音谓词组合转化为词内成分,有时还要受到双音化和右向音步的影响而零形化(详见下文)。如果谓词是双音节的,“于”要么直接被删除,要么后缀化,在不影响韵律结构的情况下,可暂时被容许,但因其不符合典型的重音指派规则,最终可能零形化,继而使前附成分的配价增值。张谊生(2010)也认为导致“于”脱落的基本动因就是“V/A于”受到双音节音步的韵律节奏制约,次要的动因就是因附缀的“于”的功能羡余性和“V/A+X”格式表达的经济性而形成的语用需求的驱动[24]。可见,“于”是否走向零形式最终还是要受到韵律的制约和语用的驱动。
2. 双音化和右向音步引起的零形化
受到汉语双音化趋势和标准音步的影响,不少跨层结构可实现词汇化。当双音化和标准音步制约的对象不同时,就可能形成两股力量的竞争,最终导致介词零形化。上文论及,当谓词是单音节词时,介词“于”要么直接被删除,要么与单音谓词组合实现跨层结构的词汇化。根据音步组合方向中自然音步从左往右(右向音步)的原理[25],在句法结构中,谓词不仅可以跟后面的介词进行组配,还可以与前面的相邻单位组配。
单音谓词受到双音化的影响,可能演变为双音节,自成一个音步,从而排挤原有的“于”,致使其零形化,例如:
例20:董卓忠于陛下,而无故为吕布所杀。(《三国志》(裴松之注))
例21:初,邈至长安,盛称东郡太守曹操忠诚于帝,操以此德于邈。(《后汉书》)
例22:他忠诚于革命事业。——他忠诚革命事业。
古汉语单音谓词双音化后,其后的介词“于”会被排挤,以至零形化,其零形化过程为:忠于→忠诚于→忠诚。
单音谓词不双音化,但受到右向音步的影响,可先与左边的单音节句法成分组合为一个音步,谓词后的介词就没有机会与谓词组合为一个标准音步,从而导致介词最终零形化。例如:
例23:六宪政改正提案权,属于国会。(《清史演义》)
例24:台湾问题纯属于中国内政。(1996年人民日报)
例25: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1996年人民日报)
“属于”是跨层结构词汇化而来的,但如果“属”前有一个副词,副词与“属”首先组成一个音步,“于”就会被逐渐排挤掉,介词功能消失。
值得注意的是,“忠”双音化为“忠诚”后导致“于”的零形化,而“纯属”不属于双音化(尚未词汇化),它是在韵律音步的制约下率先组配后导致“于”零形化。这两种情况都是单音谓词后“于”零形化的途径。类似的还有不少,如“适于→适合于→适合”“归于→归功于→归功”“居于→群居、聚居、杂居”“善于→极善”等。
3. 强化引起的零形化与韵律制约
谓词后的介词强化是添加同义介词来抵消原有介词介引功能的损耗,强化介词的位置不同,零形化的主体就不同。强化引起的零形化分为以下两类。
一是原有介词功能损耗后,通过在原介词前添加同义介词来强化,进而实现新旧更替,导致原介词的零形化。这一零形化过程实际上就是同义介词的新旧更替,如“在”强化“于”,进而替代“于”。正如刘丹青(2001)所言:“强化结构大多不能长期维持,老虚词往往会从复合虚词中脱落,最终还是变成以新代旧的单纯更新现象,例如‘在于’作为复合处所介词早已从汉语中消失了,口语中剩下了‘在’。”[20]类似的还有“到于”“至于”等中“于”的零形化。这主要是由强化引起的,当然也有语用等因素的影响。
二是介词后的强化最终还是强化介词零形化,被强化介词转化为构词成分。原介词并入单音谓词,进而成为构词成分,如“来自于”中的“自”、“倾向于”中的“向”,其中“于”为强化介词;介词后的介词强化一般不会导致原介词零形化,而是强化介词自身在韵律要求和表达经济性的制约下趋于零形化,当然,这不是简单的一加一减的过程,这一过程要受到韵律的制约。在韵律的作用下,强化成分最终还是脱落,但引起介词前谓词属性的变化。这也表明:强化不是必需的,即使采用强化,也只是暂时的,而进一步虚化才是永恒的。如果说零形化是语法化的顺向产物,强化是语法化的逆向产物,那么,逆向产物最终还是要被卷入语法化大潮之中,这是大势所趋。
三、 结 语
文章以“于”“以”等介词功能的转化为观察点,考察了韵律驱动下的介宾短语词汇化、跨层结构词汇化,以及介词“以”转化为连词后的词汇化,并分析了介词强化和零形化引发的介词功能转化,尝试揭示了汉语韵律对介词功能转化的制约和影响。汉语介词功能转化的途径和去向既受到韵律的驱动,同时也要受到韵律的制约。韵律可引发句法结构的重新分析,从而导致介词功能的转化。不管是介宾短语词汇化,还是含有介词的跨层结构词汇化,抑或是介词虚化而来的连词参与跨层结构的词汇化,都要受到双音节音步韵律的制约。另外,一些看似不符合韵律规则的现象,如介词强化,最终也要受到韵律的调节。
注释:
①上古汉语中,“是”常作代词,而中古汉语中,“是”演变为判断动词,其代词功能逐渐弱化,因此,固定结构“于是”中“是”的指代功能逐渐弱化甚至消亡,这加速并巩固了“于是”的词汇化,可以说,“于是”的语法化也离不开“是”的语法化。
②本文所用语料主要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语料库(http://ccl.pku.edu.cn/corpus.asp),其他语料将在相应位置进行说明。
③冯胜利(2000)指出:“PP附加(修饰)语必须在动词之前,唯有补述语PP可在动词之后出现。”
④《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没有收录“致以”,而第6版将“致以”作为词条收录。
[1]冯胜利.汉语韵律句法学:增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2]郭锡良.介词“于”的起源和发展[J].中国语文,1997(2):131-138.
[3]马贝加.近代汉语介词[M].北京:中华书局,2002:20.
[4]刘丹青.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85.
[5]郭锡良.介词“以”的起源和发展[J].古汉语研究,1998(1):1-5.
[6]罗竹凤.汉语大词典:缩印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7]董秀芳.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269-281.
[8]张赪.汉语介词词组词序的历史演变[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2:261.
[9]史冬青.先秦至魏晋时期方所介词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9:294.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11] 刘丹青.先秦汉语语序特点的类型学观照[J].语言研究,2004(1):37-46.
[12] 何洪峰.先秦介词“以”的悬空及其词汇化[J].语言研究,2008(4):74-82.
[13] 方环海,李洪民.“X以”的成词过程:以“加以”为例[J].古汉语研究,2011(4):31-36.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古代汉语研究室.古代汉语虚词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714.
[15] 何乐士.古代汉语虚词词典[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6:496.
[16] 向熹.简明汉语史: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94.
[17] 马建忠.马氏文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67.
[18] 刘红妮.“以免”的词汇化[J].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8(4):39-43.
[19] 刘红妮.“以期”的词汇化及相关问题:兼论“以V”的词汇化、共性与个性[J].语言科学,2009(1):57-67.
[20] 刘丹青.语法化中的更新、强化与叠加[J].语言研究,2001(2):71-81.
[21] 沈家煊.“语法化”研究综观[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4):17-24.
[22] 陈昌来.介词与介引功能[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114.
[23] 张谊生.介词叠加的方式与类别、作用与后果[J].语文研究,2013(1):12-21.
[24] 张谊生.从错配到脱落:附缀“于”的零形化后果与形容词、动词的及物化[J].中国语文,2010(2):135-145.
[25] 冯胜利.汉语韵律诗体学论稿[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2-4.
Influence of Rhythm on the Functio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Prepositions
Wang Yongyu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China)
The paper observes the function transformation of prepositions likeYu(于) andYi(以), and investigates the constraints and effects of Chinese rhythm on function transformation of prepositions. The functio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prepositions is not only motivated by rhythm, but also constrained by rhythm. Rhythm may invoke reanalysis onsyntacticstructure, accordingly leading to the function transformation of prepositions. The lexicalization of whatever prepositional phrase, the preposition-anticipated “Cross-layer structure”, or that the conjunction which resources from prepositions abstraction anticipates in the “Cross-layer structure”, are all constrained by the rhythmic of disyllabic foot. Prosaic stimulates the cliticization of preposition, especially suffixation, and may also result the zero-formalization of preposition.
prosodic; preposition; function transformation; grammaticalization; lexicalization; zero-formalization
2015-11-2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资助项目(13YJC740104).
王用源(1980—),男,博士,副教授.
王用源,wangyongyuan@tju.edu.cn.
H141
A
1008-4339(2016)05-473-07
——论胡好对逻辑谓词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