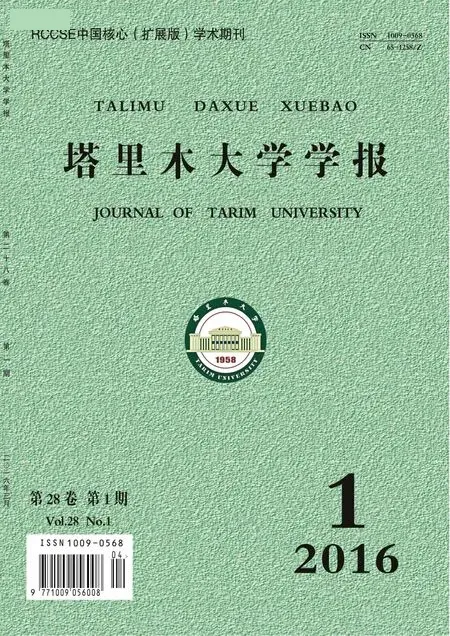新疆古代游牧民族体育文化融合考
连殿冬
(塔里木大学体育工作部,新疆 阿拉尔 843300)
新疆古代游牧民族体育文化融合考
连殿冬
(塔里木大学体育工作部,新疆 阿拉尔 843300)
本文采用历史分析法、文献资料法及逻辑分析等方法,对新疆古代游牧民族体育文化融合背景、主要表现形式和途径进行研究。本文认为:独特的自然与人文生态环境促进了新疆古代游牧民族体育文化融合与发展;体育文化融合表现形式主要有叼羊、舞马、樗蒲、踏鞠、乐舞艺术、马球和马伎等;体育文化融合途径主要是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与新疆古代绿洲农耕民族地区、中原地区、中亚地区和西亚地区之间的交流、互动和融合。
新疆古代; 游牧民族; 体育文化; 融合
目前学术界对新疆地区体育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从研究对象来看,主要是对现代体育和民族传统体育两大种类的研究;从研究内容来看,涉及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主要有起源与特征、价值与功能、旅游资源与项目开发、项目分类、传承保护与发展等诸方面的研究。尚未出现有关新疆古代游牧民族体育文化融合的专门性研究成果。多姿多彩并散发出异域魅力的新疆游牧民族体育是历经两千多年多元文化交流、互动和融合背景下的结晶。它既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多元一体格局”当中重要的“一元”,也曾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多元一体格局”的生成作出过重要贡献。因此,对新疆古代游牧民族体育文化融合的背景、主要表现形式和途径进行深入研究,力图为现代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保护与发展提供参考。而且,在国家安全、边疆安定及民族团结受到严重挑战与威胁的当下,对其进行深入探究,有助于正确阐明新疆历史,实现新疆多元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构筑多民族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目标,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和国家软实力,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 新疆古代游牧民族体育文化融合的背景
1.1自然生态环境与新疆古代游牧民族体育
历史上,许多游牧民族栖息、生存于新疆古代地区,这与新疆的自然生态环境息息相关。新疆草场资源丰富,北疆的天山北麓、伊犁河谷、阿勒泰地区、巴里坤地区皆有大片的草场资源;南疆的天山南麓、帕米尔高原的山间盆地和谷地也有大片的草原和零星的草场资源,这些丰富的草场资源为新疆古代游牧民族提供了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生存之地。游牧民族皆“随畜牧而转移”[1]、“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2]。而且,自古以来,新疆丰富的草场资源就是古代游牧部落或民族相互争夺,你来我去的必争之地。曾经在新疆古代地区游牧或称雄的游牧民族主要有乌孙、大月氏、匈奴、柔然、突厥、回鹘、坚昆、契丹、蒙古等民族。因此,在这种反复易主的过程中,也促进了新疆古代游牧部落或民族之间体育文化的交流、互动和融合。
1.2人文地理环境与新疆古代游牧民族体育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交汇处,其地理形势主要为“三山夹两盆”,即北部阿尔泰山、中部天山,南部昆仑山环抱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因此,独特的地理区位使得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处于多种文化区的包围和辐射之中,即东有中原文化、南有绿洲农耕文化和印度文化、西有波斯、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而且,伴随着历史上“草原丝绸之路”的开通与畅通,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与周边许多地区和国家发生着频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与互动。正如我国著名的东方学家季羡林先生所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3]可见,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使得多种文化类型在此汇聚、碰撞、冲突、交流、互动和融合,从而形成了兼容并包的、具有融合性特征的游牧民族文化。而且,多元文化生态也造就了种类繁多和独具特色的游牧民族体育。因而,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在促进新疆古代游牧民族体育文化多元化和多样性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1.3经济文化类型与新疆古代游牧民族体育
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类型属于畜牧经济文化型。对于这种“畜牧经济”,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中提到:“在游牧的畜牧部落中——所有畜牧部落最初都是游牧的,——与其他自然条件相等的土地是以原始的无边无际出现的,例如在亚细亚草原上和亚细亚高原上。他们利用土地作为牧场等等,畜牧民族所借以生存的畜群就是在这上面饲养的。他们把土地当作自己的财产对待,虽则他们从来没有固定这种财产。”[4]在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结构中,畜牧业为其主要的产业及生产方式。这也使得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的经济结构较为单一,生产资料种类较少。由于游牧民族极少生产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因此,其生活中所必须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则通过与邻近的农耕民族进行贸易或通过战争途径获得。其中“互惠贸易”是其获得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常用途径。而且,在这种经济交往中往往夹杂着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在这一过程中,新疆古代绿洲农耕民族地区的民俗体育和中原地区的体育活动伴随着相互间经贸交往而流传到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从而丰富了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体育文化的多样性。
1.4政治交往与新疆古代游牧民族体育
自汉代以降,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政治交往与联系就没有中断过。其政治交往主要通过三种途径:一是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向中原王朝称臣或朝贡;二是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的首领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三是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与中原王朝之间常以和亲方式进行通好。在这三种途径当中,“和亲通好”对于推动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与中原地区相互间体育文化的交流具有重要的作用。对此,历史文献中多有记载。在汉代,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乌孙王昆莫就曾迎娶细君公主为妻,从而使乌孙与中原汉王朝建立起比较密切的政治关系。
总之,通过和亲通好等途径的政治交往,新疆古代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建立起比较密切的政治联系。在这一过程中,流行于中原地区的乐舞艺术和民俗体育活动逐渐流传到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体育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而且,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的体育活动如舞马、马伎等也东渐到中原地区,从而丰富了中原地区军事体育与民俗体育的内容,其亦为中华民族体育“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2 新疆古代游牧民族体育文化融合的主要表现形式
2.1叼羊
叼羊是一种集对抗性、集体性、竞技性和力量性的马上运动,一般在节日庆典中举行,参加者大多是部落中骑术的佼佼者。新疆古代许多游牧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创造和发展出了丰富多彩的草原体育文化,其中“叼羊”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体育活动之一。“叼羊”不仅盛行于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而且在邻近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蒙古等国家以畜牧业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的游牧民族地区或国家也广泛开展。而关于“叼羊”的起源,学术界和民间历来众说纷纭。纵观文献资料和民间传说,“叼羊”最有可能起源于柯尔克孜族和哈萨克族。不论“叼羊”起源于柯尔克孜族的战争说,还是起源于哈萨克族的狩猎说,其在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大规模的迁徙与转移过程中,由一地流传到另一地,由个别民族从事进而随着古代游牧民族间的交流与互动,而被许多游牧民族所借鉴与吸收。新疆塔吉克族人更是将叼羊活动与本民族生产生活资料“牦牛”相结合,推陈出新了颇具地域特色的“牦牛叼羊”活动。而且,伴随着游牧民族回鹘人与新疆古代绿洲农耕民族地区的民族融合和文化整合,叼羊活动也逐渐被新疆古代绿洲农耕民族地区所吸收和借鉴。
总之,随着不同历史时期游牧民族的大规模迁徙,促进了新疆古代游牧民族之间及其与新疆古代绿洲农耕民族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在这一过程中,“叼羊”这一游牧民族所喜闻乐见、灵活多样和易于开展的体育活动被新疆古代许多游牧民族和绿洲农耕民族所借鉴、吸收和融合,其逐渐成为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和绿洲农耕民族地区民众在节日庆典中经常举行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形式之一。
2.2樗蒲和踏鞠
历史上,随着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与波斯和中原地区的经贸交流与文化往来,其也吸收和借鉴了许多波斯和中原地区的体育活动内容,如源于波斯的“樗蒲”和源于中原地区的“踏鞠”活动曾经在新疆古代游牧民族突厥社会生活中极其盛行。据《北史》记载:“(突厥)男子好樗蒲,女子踏鞠”[5]。
樗蒲,或作摴蒱、摴蒲,又名蒱博、蒲戏等。它起源于波斯地区,后随着中西文化经贸往来,又盛行于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和我国中原地区,成为我国古代博戏的一种。学者戈春源根据东汉马融编撰的《樗蒲赋》所记载:“枰则素旎紫厨,从西域传来”,推测出樗蒲有可能来源于西方,例如从阿拉伯传来的[6]。根据文献记载可知,樗蒲属于骰棋戏的一种,即根据骰子所掷之实际情况而下棋。有学者称此类棋戏为“赛跑棋”,即根据掷骰子所得之数,沿着规定的路线走棋子,先到达终点者为胜。而且,樗蒲的博具也种类繁多,主要有五木、马、杯和枰。五木,即樗蒲所用的掷具,类似于如今的骰子;马,即根据五木所掷的情况而在棋盘上行走争道的棋子;杯,即掷放五木的器具,为后世骰盆的前身;枰,即棋盘,供“马”之行棋所用[7]。简言之,随着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与中亚、西亚地区的文化交流与互动,樗蒲这一发端于波斯地区的体育博戏活动又被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所吸收与借鉴,逐渐成为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民众日常休闲娱乐项目之一,其后又随着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它又东渐到中原地区,成为中原地区士大夫阶层所崇尚的休闲娱乐方式之一。
踏鞠,亦称“蹴鞠”、“蹙鞠”,是一种球类游戏。起源于我国战国之际,起初主要作为军事训练的手段而在军队中盛行,随后它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休闲娱乐方式而开始在宫廷及市民社会中普遍开展。关于“踏鞠”,《汉书·枚乘传》记载有:“蹴鞠刻镂。”颜师古注:“蹴,足蹴之也;鞠,以韦为之,中实以物;蹴蹋为戏乐也。”[8]而且,陈继儒在《太平清话》中亦记载曰:“蹋鞠始于轩,后军中练武之剧,以革为圆囊,实以毛发,今则鼓之以气,又有滚弄、飞弄之技,不知始于何人。”[9]总之,踏鞠源于战国之际的中原地区,后随着中原地区与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又被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所吸收与借鉴,成为游牧民族地区妇女和儿童所喜闻乐见的休闲娱乐活动形式之一。
2.3乐舞艺术
新疆古代许多游牧民族皆能歌善舞,如古代的突厥人“饮马酪取醉,歌呼相对”[10];高车“男女无小大皆集会,平吉之人则歌舞作乐”[11];黠戛斯“乐有笛、鼓、笙、筚篥、盘铃”[12]等等。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的歌舞艺术多具有融合性的特点,其既有中原地区歌舞艺术的元素,据《汉书·西域传》记载:“时乌孙公主遣女来至京师学鼓琴,汉遣侍郎乐奉送主女”[13]。从记载中可知,远在汉朝时期,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乌孙就与中原汉王朝建立起比较密切的政治关系,乌孙公主还派遣她的女儿不远万里到汉朝的京城学习音乐和舞蹈艺术;也有新疆古代绿洲农耕民族地区歌舞艺术的内容,据《文献通考》记载:“(公元568年)其后帝聘皇后于突厥,得其所获康国、龟兹等乐,更杂以高昌之旧,并于大司乐习焉,采用其声,被于鐘石,取周官制以陈之。”[14]这里的“后帝”即周武帝宇文邕,他迎娶突厥阿史那公主为皇后,西域各国独具特色的乐舞艺术均作为陪嫁物而东来。而且,从中不难看出,新疆古代绿洲农耕民族地区的龟兹、高昌乐在新疆古代游牧民族突厥社会生活中极为盛行;还有古代中亚地区康国舞蹈艺术的身影。据《旧唐书·外戚传》记载:“延秀久在蕃中,解突厥语,常于主第,延秀唱突厥歌,作胡旋舞,有姿媚,主甚喜之。”[15]可见,武延秀被扣留在突厥数年,既学会了突厥语,也练就了一身“胡旋舞”的本领。从中也不难看出,源于古代中亚地区康国的“胡旋舞”在新疆古代游牧民族突厥社会生活中极其盛行。
2.4马球
马球是人们骑在马上,手持马球棍,在策马飞奔的过程中用马球棍将球打进球门或球洞的一种集骑术、集体性、竞技性、技巧性和对抗性的球类活动。关于马球运动的起源,学术界多有争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起源说:一是波斯说;二是吐蕃说;三是中原说。不论古代马球运动起源于何时何地,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与畅通、吐蕃势力入侵新疆以及中原王朝政治势力深入新疆等历史因素的影响,促进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间文化交流、互动与融合,伴随着上述历史进程,马球运动也传播到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有着悠久的驯马、养马和马球运动的传统。20世纪80年代,在新疆南疆帕米尔高原上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县城北发现了一个长150米,宽50—60米,有围墙和土台的古代马球场,说明在古代的塔什库尔干地区,马球运动非常盛行;20世纪70年代,在挖掘和整理新疆吐鲁番地区的阿斯塔纳古墓群过程中,出土了一件7世纪时期的打马球俑,该马球俑高37厘米,人物装束为唐装,所骑之马为白马,整个造型似正在策马飞奔,栩栩如生;而且,在故宫博物院里,藏有一幅辽人陈及之所绘的《便桥会盟图》,图中所绘的场景是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在渭水便桥上大会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的故事。此图上就绘有突厥人举行马球比赛的场景。
总之,从上述诸多文献资料和考古文物来看,随着不同地区民族体育文化的交流和互动,马球运动也被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所借鉴与吸收,逐渐成为其军事训练和民众日常生活中健身娱乐的重要活动内容。
2.5马伎
马伎肇始于古代的骑兵,是指骑马驰逐的技能,重在表现人的花样骑式和马上技巧[16]。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不仅盛产良马,而且也是马伎的发源地。据《新唐书·回鹘下》记载:“黠戛斯……戏有弄驼、狮子、马伎、绳伎等。”可见,新疆古代游牧民族黠戛斯人在唐代以前就已经熟练掌握了马伎技能。并且,随着新疆古代游牧民族或大规模迁徙或相互征战与侵伐或结盟与臣属等方式的交流与互动,源于一地一域的马伎被许多游牧民族所吸收与借鉴,逐渐成为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征战和军事训练中重要的手段,也是节日庆典中重要的表演内容。在辽人陈及之所绘的《便桥会盟图》中,亦绘有许多精彩的马伎表演。
舞马亦属于马伎的一种。所谓舞马,即训练马跳舞,是人们用音乐的节拍,训练马进行有节奏的舞蹈动作[17]。 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不仅出产良马,也是舞马的发源地。而且,比邻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的大宛国也盛产舞马。据《文献通考》记载:“大宛,其国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种,其马有肉角数寸,或解人语及知音乐,其舞与鼓节相应,观马如此,其乐可知矣。”[18]
另一方面,随着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与互动,源于草原游牧民族的马伎也逐渐东渐到中原地区。成为中原地区军事训练和杂技百戏中一项重要的表演内容。据《汉书·韩延寿传》记载:“延寿在东郡时,试骑士,……又使骑士戏车弄马盗骖。”[19]弄马,即马伎表演;盗骖,是在马车疾行时,暗中解去“骖马”(古代驾在车前两侧的马),而不使驾车者觉察到。可见,盗骖是一种难度较大而又带有一定危险性的马上技艺。到了(南)宋朝,马伎表演已经呈现职业化的发展趋势,也就是出现了专职表演马伎的职业艺人。宋朝孟元老所著的《东京梦华录·卷七》中多有关于马伎表演的描述。而且,随着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与互动,源于西域的舞马也东渐到中原地区。据《宋书》卷6记载,刘宋大明三年(公元459年)“十一月已巳,……西域献舞马”[20]。并且,凭借着中原地区高度发达的音乐舞蹈艺术,将源于西域的舞马不断地吸收、借鉴和融合,最终由唐王朝创造出一种成熟而又绚丽的舞马艺术。历史文献中多有记载唐朝宫廷中的舞马活动。据《太平御览·乐部》记载:“(唐)明皇在位尝令教舞马四百足,分为左右部,目为某家宠、某家骄,时塞外亦以善马来贡者。上俾之教习,无不曲尽其妙。因命衣以文绣,络以金铃;饰其鬣,间杂以珠玉。其曲谓之倾杯乐者数十曲。奋首鼓尾,纵横应节。又施三层板床,乘马而上,抃转如飞。或命壮士举一榻,马舞于榻上,乐工数十人,立于左右前后,皆衣淡黄衫,文玉带,必求少年而姿色美秀者。每千秋节,常命舞于勤政楼下。”[21]可见,源于西域的舞马经历唐中期创造性的融合与发展,逐渐成为唐王朝宫廷节庆体育文化中重要的活动内容和组成部分。
3 新疆古代游牧民族体育文化融合途径分析
3.1新疆古代游牧民族间体育文化的互动与融合
历史上,曾经有许多游牧部落、民族在新疆古代地区栖息、繁衍。根据文献记载,先后在新疆古代地区游牧过的部落、民族主要有塞人、月氏人、乌孙人、羌人、鲜卑人、柔然人、铁勒人、吐谷浑人、突厥人、吐蕃人、回鹘人、女真人、契丹人、蒙古人、西夏人等。除蒙古人以外,许多游牧部落、民族都消失了,或经过长时间地迁徙和融合,以新的族称继续活跃在新疆的历史舞台上。因此,在新疆古代诸多游牧民族间交流与互动的过程中,其民族间的体育文化也经历着交流与互动的过程,并呈现着融合化的倾向。发端于一地一域的体育活动如叼羊、舞马、马球、马伎等游牧民族所喜闻乐见的体育项目被新疆古代许多游牧民族所借鉴、吸收与融合,从而使新疆古代游牧民族体育文化呈现出融合性的特征。
3.2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与绿洲农耕民族地区体育文化的互动与融合
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与绿洲农耕民族地区之间因“比邻而居”更加便于相互间的体育文化交流与互动。其体育文化间的交流与互动主要呈现出以下几种方式:一是政治交往。如汉宣帝时期,龟兹王絳宾迎娶乌孙公主女为妻,从而使双方建立起比较密切的政治关系。因此,随着双方的政治往来,龟兹乐舞艺术极有可能传入乌孙,而乌孙的草原体育活动也有可能输入到龟兹地区;二是臣属关系。如隋朝末年,突厥逐渐强盛,其势力范围“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22]。由此,新疆古代绿洲农耕民族地区的乐舞艺术和杂技百戏活动也被突厥人所吸收与借鉴;三是民族迁徙。公元840年,也即唐开成五年,15部回鹘人在首领庞特勤的带领下,由漠北草原经阿尔泰山举族迁徙到西域,并在今吐鲁番地区建立了高昌回鹘政权。回鹘人逐渐由游牧生产生活方式而转变为农耕生产生活方式,在这一过程中,游牧民族地区盛行的叼羊、摔跤、马伎等体育活动也被新疆古代绿洲农耕民族地区所吸收和借鉴。简言之,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与绿洲农耕民族地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促进了双方体育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亦使双方体育文化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性趋势。
3.3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与中原地区体育文化的互动与融合
历史上,随着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与中原地区通过政治交往、经贸往来、战争、移民等途径或主动或被动的交流与互动,也促进了双方体育文化领域的“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在这一过程中,中原地区的乐舞艺术和踏鞠等体育活动逐渐流传到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从而丰富了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体育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盛行的舞马、樗蒲、马伎等体育活动也逐渐东渐到中原地区,亦为中原地区体育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注入了异质的元素。正如陈寅恪先生在评论李唐王朝所开创的盛世局面时所评论的那样:“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23]简言之,异质的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体育文化的东渐,为中原地区体育文化注入了“塞外野蛮精悍之血”,从而促进了中原地区体育文化的自我更新和发展,其亦为中华民族体育“多元一体格局”的生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3.4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与其它地区体育文化的互动与融合
随着草原丝绸之路的开通与畅通,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与中亚、西亚地区的文化经贸交流与互动日趋频繁。在这一过程中,中亚地区的康国人承担着重要的角色。《隋书·康国传》记载:“善于商贾,诸夷交易多凑其国。”[24]以至“力田逐利者杂半”[25]。可见,中亚地区的康国人是名副其实的商业民族。而且,伴随着康国人往来于草原丝绸之路上,盛行于中亚地区康国的舞蹈类型“胡旋舞”和起源于波斯的樗蒲活动逐渐流传到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并被其吸收、借鉴与融合,逐渐成为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民众日常生活中健身和休闲娱乐的重要活动内容。简言之,中亚和西亚地区体育文化的输入亦丰富了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地区体育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
4 结语
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人文地理环境、单一的经济类型和多方的政治交往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促进了新疆古代游牧民族体育文化的融合与发展。其体育文化的表现形式呈现出多样性、多元化和融合性的特征。而且,新疆古代游牧民族体育文化融合的途径主要是新疆古代游牧民族之间、其与新疆古代绿洲农耕民族之间、与中原地区之间及其与其它地区之间的交流、互动和融合。可见,多元文化的交流、互动和融合促进了新疆古代游牧民族体育的生成、发展和繁荣。借古鉴今,我们应当加强新疆游牧民族体育文化研究,使新疆游牧民族体育文化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充分发挥作用,实现新疆游牧民族体育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促进民族团结和边疆安定,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服务。
[1](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2879.
[2](后晋)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195.
[3]季羡林.朗润琐言:季羡林学术思想精粹[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119.
[4]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殖民地及民族问题的论著[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出版,1956:561.
[5](唐)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3289.
[6]戈春源.赌博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22.
[7]薛新刚,林飞飞.中国古代休闲体育及社会之对待——以六朝之樗蒲为例[J].体育科学,2012,32(10):92-97.
[8]夏征农主编.大辞海·体育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33.
[9]陈继儒.太平清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5:82.
[10](唐)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3289.
[11](北齐)魏收.魏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1410.
[12](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6148.
[13](东汉)班固.汉书[M].长沙:岳麓书社,2007:1453.
[14](元)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1152.
[15](后晋)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4733.
[16]王赛时.中国古代的马伎[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87,(03):28-32.
[17]钱松,赵玉霞.丝绸古道上的舞马与马舞艺术[J].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04,2(4):7-15.
[18](元)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1294-1295.
[19](东汉)班固.汉书[M].长沙:岳麓书社,2007:1200.
[20](梁)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25.
[21](宋)李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2593.
[22](后晋)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153.
[23]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03.
[24](唐)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1849.
[25](唐)玄奘.大唐西域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8.
Study on the Integration of Nomadic Sports Culture in Ancient Xinjiang
Lian Diandong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Tarim University, Alar, Xinjiang 843300)
Based on the methods of historical analysis, documentary analysis and logic analysis, this paper studied the background, main form and way of integration about Nomadic sports culture in Ancient Xinjiang. It found that under the interaction of multiple factors including unique natural ecological and human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 single of economic patterns, as well as political exchanges,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omadic sports culture was promoted in Ancient Xinjiang.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culture are demonstrated in the forms of Taking the Lamb, Dancing Horses, Chupu, On the Bow, Music and Dance Art, Polo and Equestrian etc.; The ways of its sports culture integration are interacted between the culture of the nomadic and farming groups in ancient Xinjiang, between the Central Plains Area, between the Central Asia, West Asia.
ancient Xinjiang; nomadic; sports culture; integration
2015-06-1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青年项目(12CTY033)
连殿冬(1978-),男,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体育文化。E-mail:liandiandong@163.com
1009-0568(2016)01-0023-07
G812.9
ADOI:10.3969/j.issn.1009-0568.2016.0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