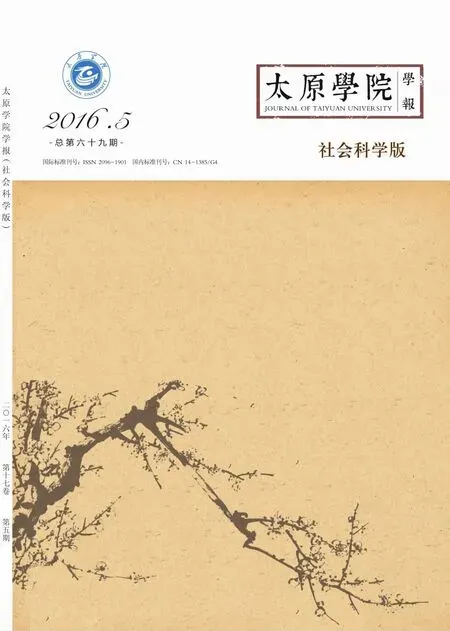边界爱情:盛开在腐尸上的玫瑰
王 晓 芳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边界爱情:盛开在腐尸上的玫瑰
王 晓 芳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最整肃的环境里往往能滋长出最纯粹的浪漫,在极度压抑人性的社会突然迎来解禁时,初获自由的人们总是愿意相信爱情,因为浪漫的感情能使尖锐的现实变得柔和。在《荒山之恋》中王安忆用“他们”的故事证明:爱情不是俄狄浦斯情结的衍生物,也非厄勒克特拉情结的投射,它是性欲和情欲水乳交融时灵魂所能到达的高级境界。在爱情和婚姻接壤的道德边界,选择爱情的他们同时也选择了彼岸,王安忆用死亡给道德以交代,给爱情以解脱。
《荒山之恋》;爱情;婚姻;欲望;死亡
1980年文革结束不久,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相继出现,人们用文学的形式展示着思想、政治高压下肉体和灵魂的伤痛,并逐渐深入地剖析着这场灾难的缘由,王安忆在这场控诉和反思的浪潮里以《荒山之恋》留下了特定语境里自己的思考和声音。她讲述着一个涉及婚姻之外的爱情、爱情之外的性欲的故事,而这正是伦理文化中关于性道德要讨论的主要内容。那个时代人们的生存内外交困,然而爱情还是不期而遇,并且以狂风暴雨的威势摧毁着婚姻的围城,风息雨停之后,满目狼藉之中,爱情已然无路可走。
一、欲望之中的婚姻
《荒山之恋》采用传统的双线结构,小说的男女主人公是在故事展开到将近三分之二处才相遇的,而在此之前的篇幅是对他们各自生活的叙述,在这漫长的前奏叙述中,小说展示了男女主人公各自的家庭环境和情感婚姻。不同的成长经历赋予了他们相互迥异的性格,大提琴手的孱弱优柔和金谷巷女孩的强势爽利如同太极图中的阴阳鱼相反相成。
(一)亦妻亦母
“是爱情还是母爱,永远也分不清,那股爱几乎称得上是博爱,有着自我牺牲的伟大,有时由于叫人羞愧和自卑,反给了人莫大的痛苦。”[1]37一语成谶,由俄狄浦斯情结衍生出来的婚姻只能安然地存在于真正的爱情出现之前。
小说中的大提琴手自幼生活在一个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里,祖父是一位极为专制严厉的老人,阴森的大宅里祖父的“眼睛在鹰钩鼻子的两侧射出犀利的光芒”[1]3,十六岁就嫁过来的母亲成为祖父建立权威的主要工具,祖父的龙头拐杖虽然时时打在母亲单薄的脊背上,但这丝毫无损于母亲在孩子们眼里的尊严,母亲支撑着整个家庭,而父亲成为了一种似有若无的存在“像风一样没有声息地飘过”[1]3,这就是大提琴手自懂事以来对家庭生活的全部印象。童年是人们内心最隐秘的记忆,也是人们命运框架的形成期,一方面他从小遵从祖父的日日召见并承训,祖父的严厉暴躁导致了他的胆怯懦弱,另一方面看到母亲勉力支撑家庭生活的同时,还要承受祖父的责打,他内心十分敏感脆弱而忧愁,母亲在他眼里无疑是坚强能干的,而他自己却是那么优柔孱弱,所以他对母亲的依赖之情即使在他长大成人,甚至成家立业之后都没有改变。求学之路因为他饥馑难耐的本能欲望而中断,在随后知青下乡的浪潮中他快速逃离了阴翳着祖父威严的家,而在农村中用辛苦异常的劳动洗刷着自己在学校行窃的耻辱,身体的极度劳累终止了他无时无刻的自我谴责。至此,即便经历着这么许多,身体的锤炼和年龄的增长依旧没有改变他脆弱如孩童般的心灵,他是一位患有严重的俄狄浦斯情结和约拿情结的成年人,他的潜意识里深深拒绝着长大,并且无时无刻不在寻求着母体的庇护。正是这样一个不成熟的他遇上了一个过于成熟的女人,他们的故事便顺其自然地发生了,如果没有金谷巷女孩的出现,也许这就是人们眼里所谓的完美爱情、幸福婚姻。
大提琴手和妻子初次相遇在一个剧团大院旁的杂树林里,当时的他正在一个人躲着抹眼泪,被她看到后迅速走开。小说以大提琴手来沪求学展开,接着片段性地回忆过去的家庭生活,直到下乡插队和考进文工团遇见后来的妻子,这一系列的活动中,他在遇到困境时都会哭泣,再配上王安忆所描画的欣长纤弱而苍白的形象,使得他柔弱得像个孩子:“他那种女性般纤弱的气质,更唤起了她沉睡着的母性,”[1]36他们是天然的互补,作者丝毫不隐瞒他们的感情质地,这个女人的爱是那么丰盈盛大,面对如此虚弱的男人,她甘愿成为一个亦妻亦母的角色,他对她的依赖让她感受到了被需要的幸福。他们第一个女儿出生时,“他像是一个体质与精神都过于孱弱的孩子,需要比别人多出一倍或数倍的母爱才能成熟。他如同孩子吮吸乳汁似的,吮吸着她的融入了母性的爱情。”[1]60直到第二个女儿出生时,他才真正长大,开始变得强壮,懂得了如何为人夫为人父。至此大提琴手似乎完成了成长任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成为了一个刚毅的男人,而只是从性别模糊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具有强烈性别自觉意识的男人,这是决定他能否真正体验到纯粹爱情的关键一点,因为爱情应该是天然、自发的两性之爱。两个女儿相继出生以后,成熟起来的他性欲逐渐强烈,而此时狭窄的生活环境和忙碌疲惫的妻子都令他的欲望暂时无法满足,欲望像幽灵,隐身在内心深处等待着现身的契机。故事行进到这里一切似乎都已准备妥当,看似稳固的围城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地震般的摧击。
(二)两个人的战争
“爱情其实是一场战争,那战争真是持久而激烈。”[1]65在这场战争中他们彼此都想征服对方,棋逢对手的惺惺相惜,寸土不让的锱铢必较,强烈的占有欲望被他们理解成爱情。
大提琴手在少年离家求学时,金谷巷的女孩还只是一个躺在襁褓里的女娃娃,她没有父亲,却有很多“叔叔”,而这些“叔叔”就是母女俩的经济来源,金谷巷女孩认为母亲只将贞洁献给过一个叔叔,那就是她的父亲,其实这应该只是女孩一厢情愿的想法,带着青春特有的天真和那个时代特有的浪漫主义色彩。童年是人格的塑形期,而且孩童天然地具有模仿能力,小小的她常在门缝里偷看到那些叔叔对母亲又敬又爱,母亲享受着叔叔们众星捧月般的娇宠,所以她极力模仿母亲周旋于男人之间的技巧,同时又因为这些方法的攻无不克使得她十分轻视那些稚嫩的男孩。那些往来于她家的叔叔都是些父辈的人,这是她最早也是接触最多的异性,加之她的生活里缺少父亲的角色,对父爱的欲望不自觉地转移到这些男人身上,“她可是喜欢年长的男人,活出了年轻,脸上有了皱纹,胡茬黑黑的,吃过苦受过大煎熬,这才像个男人。”[1]50这是她自己点明的择偶标准,带着强烈的厄勒克特拉情结,至此金谷巷女孩的性格已经基本形成趋于稳定,娇媚聪敏、自私自傲,就像那位后来娶她的复原军人说的:“生生叫那帮没骨头的男人宠坏了。”[1]59从他的这句话来看,他之后将采取与众不同的方式来对付这个目中无人的金谷巷女孩。
他们初次相遇在金谷巷口,他对女孩的冷漠与忽视立刻点燃了金谷巷女孩的好战之心,“她并不仅仅为了征服这个男人,这个男人本身究竟引起她多大的兴趣却也难说,而是要与上海的女人做一次较量。”[1]57这就是她对这个男人最初的企图,因为她的过分自信自傲,所以她容不下她的视野之中存在未被征服的疆域。而这个男人其实早在高中宣传队里的时候已经喜欢女孩了,这次退役回来的目的也是为了娶她、占有她、享用她的一切。然而前车之鉴历历在目,男人深知金谷巷女孩的秉性,因此他并不急于求成,而是策略性地步步为营。两人都表面上佯装着满不在意,而在暗中较量,彼此都以征服对方为目的,几番博弈下来,各擅胜场,女孩终于遇到了真正的对手,这种关系决定了他们同输共赢的结局——征服对方的同时也将被征服,这场两个人的战争最后以他们握手言和一起走进婚姻的围城而落幕。厄勒克特拉情结并不仅仅指年少的女孩爱慕年长如父的男人,年龄只是特点之一而非唯一,冷静沉稳老练如这个军人一样的男人,虽然和金谷巷女孩年龄相当,却依然能够唤起女孩内心深处潜藏的恋父情结,他的性格和能力能够满足女孩被保护和被宠爱的欲望,于是这种感情被延展成爱情。女孩婚后虽然生了孩子,却还和做姑娘时一样爱玩,男人虽然拥有了金谷巷女孩,却时时感到不安,他深知女孩个性,太紧太松都会让女孩想要逃走,于是他只好暗中监视,既让女孩感到自在快乐,又显得自己大度,一切都充满了小心翼翼的揣度和设计。信任是爱情的果实、婚姻的基石,而他们两个人的战争从围城外延续到围城内,正因为对彼此间爱情的疑虑,所以这座缺乏信任的围城摇摇欲坠,只需要一个小小的契机,刹那间便可土崩瓦解。
故事叙述到这里,气氛也酝酿到了顶点,大提琴手和金谷巷女孩在各自的围城里昏昏欲睡,他们都迷失在一种童年的阴影里,看不清爱情真正的面容。
二、婚姻之外的爱情
(一)何为爱情
爱情是永远能够被人们津津有味地谈论起的话题,然而爱情何时出现?又是如何产生的?关于爱情的源起人们似乎甚少关注。爱情是精神之爱和肉体之爱自然结合的最高境界,没有精神之爱的爱情只是肉体垃圾的演绎,而排除了肉体之爱的爱情被肢解为冰冷的道德理论。在人类处于茹毛饮血的进化早期,最基本的生存欲望占据了所有的思维和精力,性欲和食欲一样与生俱来,只是性欲在身体成熟时才逐渐被唤醒。人类的童年时期性欲如同饥饿一样,属于身体的自然需求,而没有被寄予任何精神内容,生殖则只是享受性欲满足的快乐后伴随而来的副产品。在身体的基本需求被满足后,人类开始分出一些精力来建造精神世界,于是爱情诞生了,它源起于升华的性欲,当人类开始对世界进行物质和精神的分类切割时,爱情也被肢解为肉体之爱和灵魂之爱,也正因如此,爱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柏拉图理想中的爱情是摒弃了肮脏卑下的肉体之欲的精神之爱。他的爱情失去了现实的载体,而变成了一种冷静的旁观,他本意在净化提纯爱情,实际上却与这种美好的愿望背道而驰,因为他逾越了爱情的范畴。情人眼中出西施,这是对爱情的盲目性、排他性的中国式的意象派表达,而在西方以佛洛依德为代表的心理学将这种爱情的特性表达得更为精准:“假如爱情达到最高的境界,利他主义也可在客体上作原欲的投资。一般而言,性的客体对象可将自我的自恋症吸去一部分,因此自我对于客体对象的估计往往过高,假如于此之外再辅以利他主义,以使利己者有求于客体,那么其性的客体对象遂成为至高无上之物,而完全吞没了自我。”[2]这正如马斯洛所言:完全的爱也是以忘我为标志的。这样的爱情太过深切,因而极易冲动地去僭越一些规则,比如婚姻。由于爱情的不确定性与土地财产继承的确定性之间的不对称,导致人们制定出一套规则——婚姻,来调整二者的失衡现象。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真正的爱情应建立在两个自由的人互相承认的根基之上,情人们会觉得自己既是自我又是他者:既不会失去超越,也不会变得残缺,他们将一道在世界上证明自己的价值和目标。对双方来说,爱情都能在奉献自我的同时揭示出自我,都会使这个世界变得丰富。”[3]这是波伏娃站在女性角度提出的爱情标准,这段话出现在第六部“生存辩护”的第二十三章“情妇”中,可见波伏娃在此所强调的自由的人应该是婚姻之外的人,因为女性不管从心理上还是生理上较之于男性更易陷入爱情的危险地带,女人通常可以为爱情牺牲一切,比如沦为情妇甚至献出生命。波伏娃的爱情观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价值,她在感性和理性中找到了平衡,为女性勾勒出理想的爱情蓝图,也许损害了爱情的纯粹,却可以规避爱情的风险。在中国文化里,对爱情的界定有着一种悲壮诗意的美,“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4]生同寝死同穴不离不弃的相守就是中国文化里爱情的至高境界。
(二)他和她的爱情
真正的爱情不是俄狄浦斯情结或者厄勒克特拉情结的投射或延伸,而是独立于童年阴影之外的阳光,将彼此的生命照亮。“他们似乎仅是在一夜之间发现的,那爱情是喷薄而出,光辉灿烂的一轮红日高悬。”[1]92他们的爱情不可抑制地出现了,在前期的酝酿中已臻于圆熟。
金谷巷女孩和大提琴手相遇时他们已经不是自由之人,本该只是一个为了满足金谷巷女孩虚荣心的游戏,却不想这游戏如同罂粟一旦沾染就身不由己。她虽已结婚但并不是贞静自持的女人,她喜欢挑逗男人,看着他们为她神魂颠倒的样子,她虽不动情,却暗自得意。男人虽有妻女,但懦弱敏感孤僻的性格使他甚少与人交谈来往,自然也不会参与到众人围着女人的逗笑中去。然而骄傲的她怎么能容忍视域里还有未被征服的领域,所以她主动出击了。两人都经历着各自的婚姻,身心都已被唤醒,“他明知她是逢场作戏却不由自主地被引动了心;她确是逢场作戏,不料却有点弄假成真。”[1]88爱情和理性常常势不两立,可是若执意要追究,爱情也是可以在分析中寻得一点理由的,比如互补的性格。内敛孤僻的他意外地喜欢上了她的明艳活泼,惯于招蜂引蝶的她却被他的清冷静谧所吸引,因为他们都是彼此并不喜欢甚至不屑的那种人,所以这场爱情的由来显得更为神秘。显然他们敏感的身心已经在爱情萌发的最初时刻捕捉到它的危险讯息,但为时已晚,大提琴手虽然惯常地选择退缩,然而身体却只想忠于自己的欲望,他对这个女人的性幻想让他自己既害怕又兴奋。而这个女人却沿袭着自己极为自私的习惯,不畏冒险寻求着刺激和享乐,向来“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的她第一次乱了自己的心,这危险的信号让她感到害怕。他的好奇心、她的好战心以及周围神秘而微妙的氛围成为了他们爱情的催熟剂,肉体的欲望和灵魂的欲望共同挟持着他们悲壮而快乐地走向没有光的前方。人性一般都遵循着利己主义原则来进行选择,而正如弗洛伊德所言,在爱情的最高境界中,利己主义原则会变为利他原则,当这段婚外情被公之于众后,这个女人承揽了一切责任去保护她爱的男人,而这种行为反常于她极为自私的性格,所以这样做理由只有一个,她爱他胜于爱自己,利己主义原则变为利他原则。不管是外在的限制指责还是内在的道德鞭笞都无济于事,爱情的力量强大得令人恐惧。
三、无处安放的爱情
“大概还是不算真爱吧,真爱,就是真死真活也不顾惜了。”[1]51这是女孩在面对如过江之鲫的男人之后,依然不为所动时的自白,这也是她对自己爱情命运的预言。他们一步步地走向荒山,走进荒无人烟的所在,摆脱一切人为的桎梏,将爱情安置在逐渐腐烂的尸体里。
婚姻之外的爱情虽然不合法,但爱情从来都不屑于礼法的衡量,礼法左右着爱情的现实命运,却无法改变爱情的内在感受,不管是悲惨还是幸福的结局,于身处爱情中的人而言都甘之如饴。假戏真做不是他们的初衷,身不由己是情不自禁的无奈,她的母亲说过,人的一生只会爱一个人,有的人一生都遇不上,有的人遇上后就擦肩而过,有的人不但遇上还能相守。
大提琴手对妻子一直感恩有加,因为她扮演着亦妻亦母的角色,小心修补着这个男人内心的创伤,耐心地陪着他长大,但他从来没有说过“爱”。金谷巷女孩嫁给了一个与自己旗鼓相当甚至更胜一筹的男人,享受着这个男人如父般的宠爱和暗中监视下的自由,虽然育有一子,可她仍然贪玩,并无母性,也许正是这样的性子使她终究没有被高尚传统驯化,而仍旧保存着天性里的随心所欲。
两个为世人公认的完整幸福的家庭因为一段意外出现的爱情而濒于破裂,他们各自努力挽救各自的家庭,大提琴手的妻子努力调动他的工作,以为距离可以冲淡一切,金谷巷女孩的丈夫用暴力胁迫着他们分开,然而一切都于事无补。不容于世的爱情该何去何从,懦弱的他无法抉择,而果决的她选择不惜所有地追求所爱,以自杀的形式自卫,维护自己拥有爱欲并追求满足的权利,“他不反对生命,而只是反对生命的形式,因为他要自卫。”[5]从金谷巷女孩出嫁前认为:那些凭权势钱财讨女孩欢心的男人或者主动献身于这些身外之物的女人都算不得真正的男人或女人,可见她是一个至情至性的人,她喜欢打扮,喜欢捉弄男人,可见她是一个热爱生命,享受生活的女孩,那么让她放弃爱情,如行尸走肉般地苟活着,对于这个生机勃勃的金谷巷女孩来说,这样枯槁的生命形式是无法忍受的。叔本华和大多数哲学家一样对女性抱有极端歧视,但他对于爱情的看法在此却可以成为男女主人公爱情命运的注脚:“恋爱的主要目的,不是爱的交流,而是占有——肉体的享乐。所以,纵是确有纯洁的爱,但若缺乏肉欲的享乐,前者也无法予以弥补或给予慰藉。毋宁说,落到这种境地的人,多半还是走向自杀。”[6]当然这是从男性角度出发所给出的爱情定义,不可否认其某种程度的正确性。现实法则对他们之间不合法的爱情虽然作出了裁定,然而被宣判为死刑的只是他们的肉体之爱,至于精神之爱仍然是自由的。但他们似乎无法忍受身体距离的遥远,于是他们选择了自杀。当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时,欲望主体因极度紧张,而呈现出生命本能中的回归惯性,他们选择逃回母体子宫,回到无生命的沉寂中去,死亡是人们最后的避难所,“向死亡的下降是对于痛苦和欲望的一种无意识的逃避,它是反抗痛苦和压抑的永恒斗争的一种表现。”[7]所以王安忆对男女主人公爱情结局的安排,是对他们僭越社会规则的惩罚,给世人以公正的交代,但其实作者是有所偏私的,在1980年的时代热潮里,即便困难重重,她仍旧希望人的欲望能得到正视与尊重并且可以自由地舒展,让他们的爱情在死亡里永生。在他们自杀殉情的第七天,人们在草丛里发现了四肢交缠在一起的他们,腐烂腥臭的尸体滋养着艳丽的玫瑰。
[1]王安忆.岗上的世纪[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05.
[2]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引论·新论[M].罗生,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376.
[3]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李强,译.北京:西苑出版社,2004:260-261.
[4]汤显祖.牡丹亭[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229.
[5]贝克勒.向死而生[M]张念东,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3:97.
[6]叔本华.生存空虚说[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100.
[7]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87:19.
[责任编辑:何瑞芳]
Border Love: Rose Bloom on Carrion
WANG Xiao-fang
(School of Humanity,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325035, China)
In the most purge environment, it can usually grow the most pure romantic, extremely when in a society in which the most depressed humanity suddenly usher lifted, people eligible for early freedom are always willing to believe in love, because romantic feelings can make sharp reality become soft. In “Barren Love”, Wang An-yi uses “their” experiences to prove: Love is neither Oedipus complex derivatives nor Electra complex projection, but it is sexual desire and lust harmony soul which can reach senior realm. In the boundaries of love and marriage or morality, they chose love; they also chose the other side of seashore. With death, Wang Anyi gives an answer to morality, and gives relief to love.
“Barren Love”; love; marriage; desire; death
2016-07-29
王晓芳(1991-),女,江苏南通人,温州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作家及文学作品研究。
2096-1901(2016)05-0057-05
I207.42
A
——浙江机场集团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金谷严重违纪违法案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