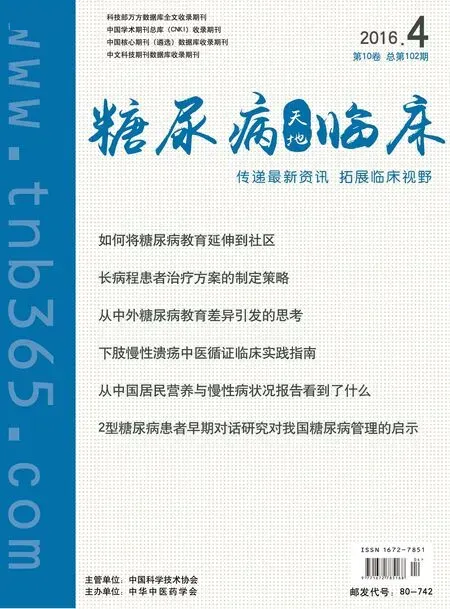从中外糖尿病教育差异引发的思考
鞠昌萍 孙子林中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从中外糖尿病教育差异引发的思考
鞠昌萍 孙子林
中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国外糖尿病教育的发展历经数十载,甚至可追溯到百年前(1914年)的饥饿疗法,已逐步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并“以糖尿病患者为中心”的教育体系。然而,健康教育的模式因各国文化背景、生活习惯、政策法规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总体说来,国外糖尿病教育拥有满足患者需要的规范化课程、训练有素的糖尿病教育者以及完善的评估系统。
外国糖尿病教育现状
英国
英国国立健康与临床优化研究所(NICE)指南明确指出,糖尿病患者一经确诊,必须接受符合全国统一标准的结构化教育课程,然后进行每年1次随访和后续教育。这种结构化的糖尿病教育模式逐步得到广泛认可。英国与德、日相比还强调全国统一标准和进一步跟踪随访。
结构化教育模式是将糖尿病患者教育分为饮食、运动、低血糖的处理、胰岛素注射、自我血糖监测、并发症预防等几大模块,在每次随访过程中用相关知识进行教育,定期反馈并进行再教育。通过血糖变化、胰岛素注射技术考核、糖尿病自我管理技能来评估自我管理能力和行为改变。
意大利
在注重内容系统全面的基础上,认为糖尿病小组教育模式更值得推荐,该模式要求糖尿病患者以小组为单位,接受定期的系统教育(3月/单元,共7单元),教育内容则涉及饮食、运动、药物调整、并发症等各方面。而小组活动的组织者(如医生、护士、营养师等)则需要学会如何教学、管理小组,以及学会如何引导小组活动。
德国
医院内分泌科定期举办糖尿病自我管理学习班,给予患者系统全面的糖尿病相关知识培训,并给予个性化指导及个体化治疗方案设计。
日本
糖尿病患者除可享受“一站式”服务(即饮食、运动、药物、心理等指导),还可根据自身意愿选择相应糖尿病教育课程。
美国
糖尿病教育探索更为全面系统。从理念看,以患者为中心,关注心理行为改变,提倡授权教育;从教育工具看,注重教育工具的开发和使用,食物模型使用广泛,开发并在全球推广糖尿病看图对话工具;从教育的提供者来看,一方面糖尿病教育团队健全,不仅涉及专职医护人员,还纳入专兼职医疗社工、志愿者等,另一方面还关注教育者水平,自1986年就实施糖尿病教育者认证(CDE),此外,糖尿病患者也被纳入糖尿病教育团队中,开展“患-患互助”模式下的糖尿病同伴支持教育,让那些接受过良好教育和培训的同伴教育者(本身也是糖尿病患者)与糖尿病患者进行“经验”交流,分享专业医护人员所没有的自身糖尿病管理经验,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广泛推崇;从教育的标准化来看,自1983年就制定了糖尿病自我管理教育(DSME)项目标准,目前已日臻成熟为美国DSME/DSMS项目标准,该标准不仅对教育内容、形式进行了规范,而且有完整的教育评价标准。
中国糖尿病教育现状
与国外相比,我国糖尿病教育起步较晚,在上世纪90年代后才逐渐受到重视。虽然起步较晚,但我国糖尿病教育工作者不仅借鉴国外糖尿病教育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开展糖尿病教育,如建立糖尿病自我管理培训学校、开展小组教育、分阶段糖尿病管理、同伴支持教育,推广看图对话的糖尿病教育等;也积极探索适合中国的糖尿病管理与教育新模式,如门诊-住院-出院后全程健康教育模式、PBL教学模式、医院-社区网络一体化教育模式,随着科技的发展,我国的糖尿病教育者也成功地将移动通信设备运用于糖尿病教育中。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CDS)糖尿病教育与管理学组也自2008年和2013年起,分别启动中国糖尿病教育者培训项目和糖尿病教育单位认证,以推动糖尿病教育的国家标准建立。这些努力和探索对糖尿病的防治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仍有不足之处。
思考
差在哪
第一,我国至今并没有属于自己的糖尿病教育质量评价标准。尽管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已启动糖尿病教育单位认证,但仅局限于北京、上海、江苏等发达省、市。
第二,绝大多数医院仅依靠内分泌的医生护士开展糖尿病教育,缺乏一支构建合理、科学、全面的多学科协助的教育团队;没有糖尿病教育者职位,更没有规范严格的教育者准入制度,糖尿病教育质量无保障。尽管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借鉴国外经验,开展糖尿病教育者认证,目前只有491位取得“糖尿病教育者”证书,相对我国超过一亿的糖尿病患者人群而言仍是杯水车薪。
第三,我国糖尿病教育分布不均,医疗教育资源相对集中于大中城市的大学附属教学医院(基本为三级甲等医院),而广大农村地区的众多糖尿病患者可能未能受到任何一种形式的糖尿病教育。
怎么做
总体说来,我国糖尿病教育在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取得了不少进步,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我国糖尿病教育与国外糖尿病教育仍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后期的糖尿病教育研究工作中,我们除了需逐步建立统一的教育评价标准、优化教育团队外,还需实现糖尿病教育高质量、广覆盖、易实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糖尿病教育模式/体系和评判标准。
doi:10.3969/j.issn.1672-7851.2016.04.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