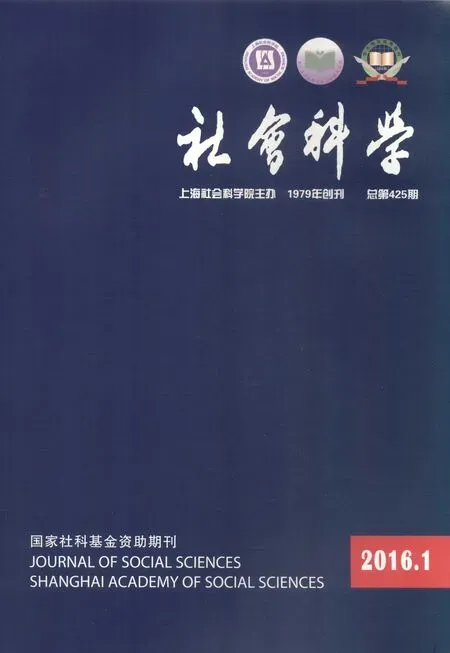描述的意义理论及其悖论表征*
王天思
描述的意义理论及其悖论表征*
王天思
当代意义理论的发展,正从关于实在的意义理论走向关于描述的意义理论。由指称论和观念论意义理论的描述指向,功用论和行为论意义理论中描述与规定的关联,语义论和语用学意义理论的描述和规定向度,描述的意义理论呼之欲出。描述具有规范的性质,对描述的深层次研究,必定涉及作为其前提的规定,并指向认识的人类学特性。作为悖理性描述,悖论是意义理论描述性质的表征,是意义理论中具有标志性的界碑。悖论作为意义理论的表征,意味着描述的意义理论将导向知识人类学。
描述;意义理论;规定;悖论;人类学特性
当我们用语言谈论对象的时候,涉及两个不同的层次:一是就对象本身而言;一是就关于对象的描述而言。区分这两种不同层次,关于语言哲学的理解就会展开一个新的层面。意义理论是语言哲学的核心内容,作为对词或词组及语句所表达的意思的探究,意义理论的描述向度涉及一些重要的哲学基本问题。
在传统使用中,描述和规范是一对相对的范畴。而关于描述的研究表明,描述必须以规定为前提,因而具有规范的性质。对描述的深层次研究,必定涉及对作为描述前提的规定,而对描述和规定的研究,则必定指向认识的人类学特性,从而走向知识人类学,*① 王天思:《描述和规定》,《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这无疑意味着描述的意义理论意义非同寻常。
一、 指称论和观念论意义理论的描述指向
在语言分析哲学中,指称理论发生了由实在意义上的指称理论到描述意义上的指称理论的转换。在两种不同情况下涉及意义理论,则使问题一方面变得更为复杂,另一方面又更耐人寻味。
总体而言,意义理论中的指称论是经典实在论的意义理论,意义理论中的观念论已经转向描述论的意义理论,而意义的发展是从指称论所强调的对象事物——特别是非语言事物,发展到观念论所强调的观念——特别是关于语言事物的观念(比如“上帝”、“幽灵”等)。密尔之所以接受休谟的经验论却又倾向于意义指称论,乃是因为指称论意义理论反映了专名的意义来源,而从通名开始直到复杂的描述,意义理论都必定转向观念论。我们或者可以把指称论意义理论看作观念论意义理论的特例,或者可以把专名解释为最简单的观念而不只是一个标签,或者把标签本身也看作观念。这也是密尔在对待抽象概念时又转向观念论的原因。
就描述而言,观念论的意义理论要远比指称论的意义理论合理,因此也更容易理解。
作为最原初的意义理论,指称论是具有合理性的,只是由于没有办法处理描述关系,在其发展中必定会遇到越来越复杂的情况而显露其不合理性,最后也因其不合理性而只能作为特例保留在关于描述的意义理论中。因为在抽象描述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指称论意义理论会越来越穷于应对,其在实体名称情况下的合理性只能成为特例,就像相对论条件下牛顿力学成为特例一样。
当弗雷格批驳洛克和休谟的观念论时,他即是在试图依靠逻辑(有时候借助语言)建立一种客观的意义理论,一种经典实在论意义上的意义理论。但弗雷格是一个交叉路口式的哲学家,他的处境和他的丰富使他的哲学研究(approach)不会是单一导向的。在可能导向客观主义结果的致思的同时,他也提供了功用论意义理论的某些基本观点。这种状况使得后人在他那里通过对客观主义倾向的否定,自然导向了功用论意义理论。这种功用论倾向经过维特根斯坦那个更大的交叉路口,透过更复杂的可能路径,指向描述并最终走向知识人类学。
在前期哲学中,维特根斯坦循着罗素的思路,将把握世界的逻辑结构看作是哲学的最终目的,因而《逻辑哲学论》被自认为是哲学的完成。而这个世界的逻辑结构,事实上正是传统实在论的逻辑形式。作为从前期哲学的哥白尼式转向,在后期哲学中,维特根斯坦不仅明确认为,“我们必须摈除一切解释,而必定取代其位置的只有描述(Beschreibung)”,而且提出了“语言游戏”理论。当维特根斯坦说“语言游戏”这个词就是要强调语言是生活形式的一部分时,就明显以“语言游戏”等方式走向功用论意义理论。在维特根斯坦那里,“‘语言游戏’概念是为了强调这一事实:语言的言说是活动的组成部分,或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因此他也把“由语言和行动交织而成的整体称为‘语言游戏’”*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London, the Macmillan Company,1953. p.11, p.5, p.47.。语言游戏致思的描述指向,在其后来的展开中一览无余。
继洛克、休谟和密尔等(的观念论)把词以及弗雷格把语句或命题看作意义的基本单位之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试图在语词和人类学特性之间进一步找到更大单元的意义基本单位,从这个意义上说,维特根斯坦已经涉及知识人类学,只是在“语言游戏”中,仍然主要停留在语言的层面,而没有由此真正深入涉及人类学特性。而蒯因则走向了更大的知识体系。他写道:“即使以陈述为单位,我们也已经把我们的格子画得太细了。具有经验意义的单位是整个科学。”*[美]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江天骥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页。关于意义单位的这种逐步扩大趋势,与描述在量子领域的相反走向殊途同归,最后必定都通过描述展开作为其前提的规定,并指向认识的人类学特性,走向知识人类学。至于赖尔等哲学家关于这种趋势的不同观点,即坚持认为意义的体现者是词或词组而不是语句,可能只有用意义本身的层次划分得到统一的理解,但最后走向人类学特性(包括人类的特定处境)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当代哲学发展的重要趋势;这一趋势是哲学的“实践转向”的逻辑结果。
由维特根斯坦等哲学家从弗雷格出发所走出的这条道路,弗雷格本人并没有选择,其意义理论的功用论倾向在后期已几近放弃。关于他后期是否仍然坚持只有在语句或命题的语境中才能找到词的意义这个基本观点,答案是不用争论的。弗雷格的主观意愿无从考察,但他这种努力的客观结果是从逻辑,经过语言走向了一个与观念论相似,但却是在更高层次上的知识人类学方向。这一方向在逻辑的文化转向——归根结底是人类学转向——中展示得淋漓尽致。在逻辑的人类学转向中,弗雷格的“心理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之间的界限正在模糊甚至消失。事实上,观念和语词(言)只有个人和群体约定的不同。这一点,在维特根斯坦关于不存在“私人语言”的思想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
维特根斯坦认为不存在“私人语言”,因为语言是进行思想交流的,没有这种功能的“私人语言”谈不上是一种真正的语言。其实,作为一个类的存在,观念也和语言一样,即便存在所谓“私人观念”,这种观念也只能在个人思维中存在,不是这里讨论的对象,因为这样的观点不是任何可能的地方讨论的对象。
二、 功用论和行为论意义理论中描述与规定的关联
观念论意义理论为从经典实在论意义理论发展到关于描述的意义理论奠定了基础,但这一基础仍然可以在柏拉图意义上走向观念的实在论。所以作为从经典实在论意义理论向关于描述的意义理论发展的进一步努力,功用论意义理论自然而然从批驳观念论的这种自然倾向入手:进一步从一个词的意义是与之相联系的观念,发展到这个词所完成的功能。赖尔由此进一步排除了观念论意义理论的经典实在论最后堡垒(或可能堡垒,或残余)——“抽象主体”或“精神主体”。
赖尔的功用论意义理论已经把观念引向主体,而当其强调语词使用的正确与否时,观念已经变成只作为基础起作用,关注点已经转向主体的语言使用了。从语词的客观功能到语词的主体使用,完成了从更客观的观念到更主观的主体使用之间的转换。功用论对语境的关注,所强调的是语言活动与生活实践甚至与人类学特性的内在关联。因为无论是语词的功用还是人们的使用,都必定导致关于语词形成及其使用的人类学特性。维特根斯坦认为:“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London, the Macmillan Company,1953. p.20; p.24, p.28.这种功用论观点通过“语言游戏”等走向了更深层次的具体,他之所以既反对指称论又反对观念论,一个共同的理念就是反对实体,也就是既否认物质实体,也否认精神实体。其结果自然而然是否认经典实在论意义理论而走向了关于描述的意义理论。维特根斯坦甚至反对把意义本身看作一个实体,主张不问词的意义而只问其使用。
维特根斯坦不仅和弗雷格一样,认为“一个词只有作为一个句子的组成部分才有意义”,而且在涉及名称的使用时,深刻地论述到:如果“X存在”只是简单地意味着说“X”有意义——那么,它就不是一个讨论X的命题,而只是一个关于我们语言使用的命题,也即关于“X”这个词使用的命题。*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London, the Macmillan Company,1953. p.20; p.24, p.28.
关注语言的用法就是从主要关注对象到主要关注描述,就是关注描述。关注描述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当我们谈论或描述时,对描述对象的关注和对对象描述的关注是根本不同的。在两者间作出区分,不仅不是可有可无的,而且必不可少。它涉及几乎所有知识问题的解决。其中之一就包括比如“非存在物”等问题。
在维特根斯坦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从实在到使用的转向,从实在到使用就是从经典实在论到功用论;在塞拉斯那里,我们则可以看到这种转换的纯粹性。而蒯因对观念论的行为主义批评则将功用论只是与人类相联系的连接点,进一步扩展到人类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从经典实在论意义理论到关于描述的意义理论的转换。只是蒯因没有真正走完这一步,而是走向了分析哲学传统所导向的语言本身。
蒯因认为意义只存在于语言之中,并随语言的变化而变化。他由此走向“言语行为”,这本身就已经走向了人类学特性。行为主义者正是因为看到了“谈论观念甚至对心理学来说也是一种坏事”,从而得以蹬开“观念”这一垫脚石,不自觉地迈向了知识人类学。
行为论意义理论由实用主义者将行为主义心理学引入哲学,并由罗素和蒯因等移植到语言哲学。行为论者用可观察的行为取代意识中的观念来说明词的意义,这也就是从把主观的、私人的经验作为说明意义的基础,转向根据语言产生的效果——即语言对听者的影响研究语言的意义。皮尔士认为语词的意义是从某种行为的效果获得的,杜威则认为他的工具主义就是“一种关于思维和认知的行为主义理论”。*John Dewey, Essays in Experimental Logic,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16. p.331.行为论观点对罗素也产生了影响,他后来也认为:“懂得一种语言并不是说对于这种语言里的词的意义能够作出清楚明白的说明;懂得一种语言是说听到这个词时产生适当的效果,而使用它们时也有适当的原因。”罗素甚至断言:“我们已经确定的是一个词可以和环境的某种引人注目的特点(一般说来,这种特点是经常出现的)联系起来,并且在发生这种联系以后,它还会和可以叫作这种特点的‘观念’或‘思想’的东西联系起来。如果有了这种联系,那么这个词的意义就是环境中的这一特点;这一特点可以引起人们说出这个词来,人们听到它也可以引起关于这个特点的‘观念’。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意义’,其它种类的意义都是从这种意义发展出来的。”*[英]罗素:《人类的知识》,张金言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7、88页。这本身就表征着一种极为重要的哲学意蕴。蒯因也认为,“意义根本上是一种行为特性,所以,除了隐含在人们的公开行为倾向中的东西,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意义的相似与区别”*W.U.O. Quine, “Ontological Relativity”,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LXV, No.7, 1968.。他由此提出“刺激意义(stimulus meaning)”,认为“除非相当固定和直接地限于感觉刺激,一个句子S没有相对于它自己理论之外的任何意义”*W.U.O. Quine, Ward and Object, MIT Press, 1960. p.24.。作为一个语句在特定时候对特定说话人的意义,“刺激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有个别性、具体性的特点,与后现代主义具有某种关联。
无论是功用论还是行为论,都只是在功用和行为方面涉及描述,而没有真正涉及作为描述前提的规定。规定是一种语义行为,因而必须涉及语义学。这就是意义理论必定要涉及语义学,意义理论必定会走向语义论的学理根据。
三、 语义论和语用学意义理论的描述和规定向度
戴维森的语义论意义理论源自塔尔斯基的真理理论,而塔尔斯基的真理论则与规定密切相关。不管在什么意义上,真理概念都意味着“符合”。融贯论远离了符合论,所以不是在严格意义上谈论“真理”概念;实用论则明确将关于“真理”概念的讨论转向功用意义上的工具论。这些方向在解决真理问题讨论中所遇到的一些难题的同时,也势必把真理论所涉及的“符合”意义撇在一边。问题的实质是,传统真理论所讨论的问题不仅包括“符合”意义上的真理讨论,而且包括不属于“符合”意义上的问题讨论。因此融贯论和实用论应运而生,将不属于“符合”意义或传统真理论讨论的问题分离了出去,既解决了传统真理论所涉及的两方面难题(本来就不是传统真理论本身能够解决的),又开辟了两个与实践相关的不同于传统真理论所讨论的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真理论所讨论的“符合”意义上的问题被消解了,这个问题仍然存在并且存而未决。这也是几种真理论同时并存不能相互取代的根本原因。
然而,“符合”意义上的真理问题必须更精确地定位自己的问题域。这在融贯论和经典实在论真理观应运而生,相应领域分离出去以后,完全具备了条件。这就是塔尔斯基所致力于探索的语义学真理论。
塔尔斯基的语义性真理讨论“以真理(truth)概念为中心”,主要问题是给真理概念下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即“一个实质上适当并且形式上正确的定义”。而要给真理下一个适用于所有自然语言的定义,又必定会遇到说谎者悖论。这种悖论产生于语句自指所导致的“在语义学上封闭的语言”。塔尔斯基一方面对语义悖论进行了很有影响的探索;另一方面又认为要给真理下一个内容恰当并且形式正确的定义,必须避免这种悖论。塔尔斯基认为他的符合论真理论的精细刻画表明,要使真理论得到精确表达,必须区别语言层次,区分对象语言和元语言;而且关于真理定义的这种表达只能在形式语言中才能成立,其根本原因是只有形式语言才是“在形式上可规定的”,“现在,只有各种演绎逻辑系统的形式化语言具有规定明确的结构”,没有任何一种自然语言是在形式上可规定的。而这个“可规定的”,是在自然语言中“真的”一词下定义的必要条件。因为只有形式语言才具有明确规定的结构,其语义学词项只有通过定义才能被引入元语言中。只有在形式语言中,由于“不包含任何非定义的词项”,尤其是“非定义的语义学词项”,符合论意义上的真理的定义或“任何其他语义学概念的定义”才能“每个定义在直觉上如我们所望”。*A.Tarski, “The Semantic Conception of Truth and the Foundations of Semantics”, Readings in philosophical analysis, ed. Herbert Feigl, Wilfrid Sellars,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49.p.52, p.57, p.61.而这种“每个定义在直觉上如我们所望”,事实上就是规定所给予的。这样,就在实质上涉及规定问题。
在卡尔纳普那里,事实上,元语言和对象语言的区分在根本上涉及规定。语言谈论的对象除了作为对象的实在和语言本身(元语言),还可以根据描述和规定作更精确的区分。按照规定的层次,我们可以区分出对作为实在的对象的描述和对描述本身的描述。描述的层次就是作为其前提的规定的层次。
这里的“规定”显然更精确地定位了符合论真理论的问题域,塔尔斯基事实上已经将古典符合论真理观中的“直觉”缩到“规定”的范围,而不像古典真理论“直觉”那样无所不包。也正因为如此,符合论真理论正好找到了自己的合理定位,避免了与融贯论和实用论研究所对应的领域的混淆。因此,赞扬塔尔斯基语义学真理论的人看到了真理符合论的新生,而反对者则仍然在古典符合论真理论的论域抓住符合论本身的老问题——比如达米特就抓住“我们是否有能力知道是不是符合实际情况”,否证塔尔斯基语义学真理论的成立。这一点,显然与塔尔斯基本人也仍然自觉不自觉地在古典符合论真理观论域中讨论问题有关。
事实上,当塔尔斯基将语义学真理论限制在形式语言中时,他已经在不自觉地把符合论真理论限制在规定的基础上,只有相对于规定而言,才存在是不是符合的问题,或者说才可能谈论是不是符合的问题,而不必去管“我们是否有能力知道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正因为如此,以格雷林为代表,否定语义论与符合论密切关联的哲学家意识到了:“塔尔斯基的理论并没有以任何具有特殊意义的方式保持符合论的直觉。”*[英]格雷林:《哲学逻辑导论》,牟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6页。由此,我们既可以看到“多余论”真理观的逻辑起点,也可以看到戴维森的语义论意义理论的描述涉入及其努力价值。
在戴维森看来,一种语言的意义理论可以看作就是该语言的真理定义,由此他提出语句的成真条件也就是给出其意义的一种方式。但是,意义理论涉及自然语言,而塔尔斯基的真理定义只能在形式语言中才能成立。戴维森不能只是论证“一种采取真理定义形式的意义理论怎样才能得到经验检验”,还必须面对一个“在先的问题”,即“是否存在能就自然语言提出这样一种理论的真正机会”。戴维森把这一困难,作为自己思考的重点问题,并由此提出了自己以“戴维森纲领”著称的语义学意义理论。“对于自然语言真理谓词形式表征的可能性,我采取一种乐观的、纲领性的观点。”*Donald Davidson, “Truth and Meaning”, Syntheses,vol.17, 1967. pp.309-310, p.313, pp.320-321.从弗雷格、乔姆斯基特别是塔尔斯基的工作中,戴维森看到了把塔尔斯基的真理定义应用于自然语言的可能性。他的基本根据是:意义理论的任务是描述和理解自然语言,而不是去改造它。
塔尔斯基在分析真理概念时企图借助意义概念,而戴维森则反过来,把真理当作是原始的、基本的概念,从而通过阐述真理的结构了解意义。因此,戴维森把“真的”看作一个已经得到解释的词,把塔尔斯基的真理定义看作是语言的意义理论。
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只有在规定的情况下,“真的”才是确定的、已经预设了解释的词。因此,一方面,戴维森的意义理论作为一种语义的意义理论是恰当的,它建立在塔尔斯基语义真理论的基础上。另一方面,戴维森的意义理论是把塔尔斯基的语义真理论颠倒过来使用,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不管他是不是事实上跳过了意义理论涉及自然语言;而塔尔斯基的真理论只适合于形式语言这一困难,因此,仅就把塔尔斯基的“真的”一词看作是已经得到解释,必定存在一个问题:只有在形式语言中这种真理定义才能成立,也就是说,只有基于规定的情况下才能成立。除非我们把涉及经验的概念也叫作规定,否则塔尔斯基的语义真理论在经验领域是不能成立的。因而戴维森的语义的意义理论在经验领域也不可能成立。所以结论只能是:由于建立在对语言的描述基础之上,而语言又是建立在规定的基础之上,戴维森的语义的意义理论不是经典实在论的意义理论,而是关于描述的意义理论。
其实,当说到“一个满意的关于复合表达式的意义理论可以不需要一些实体作为所有部分的意义”时,戴维森已经找到了一个超越他之前意义理论的契机。戴维森从弗雷格的意义理论出发,认为意义和指称之间的区别是建立意义理论的途径,由此走向“语义性真理概念”,并走向“对自然语言的活动方式作出解释”的“经验理论”。“一种意义理论(在我稍带着意调整的意义上)是一种经验理论,它意在解释自然语言的作用机制(workings)。”在这里,戴维森虽然把“意义理论”的含义作了改变,将其变成一种“经验理论”,但已经把意义理论从语句与所指对象的关系变成了一种“意在(ambition)解释自然语言的工作机制”,这是从基于语形学的意义理论转向基于语用学的意义理论。事实上,从戴维森意义理论的转向,我们可以看到意义理论的语用学转向,并由此看到意义理论更远的发展趋势。通过“从语句的意义依赖语词的意义”的方式做出解释建立的意义理论是语言学甚至是语形学的;在语言的使用中建立的意义理论是语用学的;从使用者的使用需要和目的的考虑中建立的意义理论是实践的;而在此基础上考虑语言使用者的使用等人类学特性建立的意义理论则是人类学的。
戴维森以一种貌似经典实在论的立场所提出的意义理论,由于塔尔斯基真理论的性质,事实上恰恰是最典型的关于描述的意义理论。经典实在论意义理论认为“一个语句的意义是它所指称的东西”,这几乎是一种日常观点,而日常观点常常经不起推敲。这里的问题在于:“指称问题一般由语言之外的事实确定,意义理论问题则不是,而那些事实可以与异义表达式的指称相混同。”*Donald Davidson, “Truth and Meaning”, Syntheses,vol.17, 1967. p.306.塔尔斯基坚持符合论的真理观,所得到的却是完全不同于传统符合论的语义学真理论;戴维森的意义理论建立在语义学真理论的基础之上,结果只能是意味着完全不同于经典实在论意义理论的关于描述的意义理论。
四、 描述论意义理论的悖论表征
这里涉及一个耐人寻味的转换:他们都在客观上背离了传统符合论,但却得到了一个真正符合真理符合论的语义学真理观和语义的意义理论。也就是说,真理符合论只有在下述意义上才可能成立:真理所符合的不是对象本身,而是我们的规定,包括我们关于对象的某些看上去是客观的规定。这显然不是经典实在论意义上的真理观而是描述意义上的真理观,这也是真正能够成立的符合论真理观。语义论真理观不是回到了传统的符合论真理观,语义的意义理论也不是回到了原初的指称论意义理论,而是实现了一个上升循环,走向了描述的意义理论。
其实,戴维森从塔尔斯基真理观的定义的适当性推到了真理论的适当性,把一种语言的意义理论与这种语言的真理定义相等同,这还是一个并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塔尔斯基真理论的递归性质和戴维森意义理论的相应性质,最后集中到根据一种语言中有限语词及其组合规则的理解构造无限的语句,与人们对这种语言的习得相等同,而语言的习得完全是以人(类)的需要和生存发展为出发点和目的的。这样,语言(包括表达式和语句)的意义不仅要在使用中去找,而且必须从使用者的使用目的、他的认识和实践需要,甚至与他本身使用语言有关的特性中去寻找。这就表明戴维森意义理论的基础所具有的人类学特性,尽管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
塔尔斯基惧怕和回避语义悖论,说明他没有真正在描述的意义上理解真理概念。与塔尔斯基不同,戴维森对悖论所采取的不是回避态度,而是在搁置语义悖论的条件下建立意义理论。
戴维森的意义理论在塔尔斯基的基础上进一步转向了语用学,因而必须正视悖论。他认为塔尔斯基的理论引出了两个论题,其中之一就是“自然语言的普遍特性导致矛盾(语义悖论)”。戴维森对悖论不仅没有像塔尔斯基那样采取回避态度,而且认为悖论问题“值得有一个严肃的回答”,并“希望自己已经有了一个”。事实上戴维森已经得到结论:“当对象语言中量词的范围以特定方式过广时就会导致语义悖论”。虽然这只是语义悖论的表观而不是其真正根源,但这并不妨碍他作出重要说明:“在还没有消除这种概念忧虑的特定根源时,为什么我认为我们有理由继续下去。”*Donald Davidson, “Truth and Meaning”, Syntheses, vol.17, 1967. p.314; p.319, p.320; p.304.这一方面表明戴维森已经深刻意识到意义理论与悖论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表明他对意义理论的理解还没有真正以使用者的需要为出发点和目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戴维森是在搁置语义悖论的条件下建立他的意义理论的。
虽然没有落位到意义理论的出发点,但在戴维森的表述中可以看到一些语用学意义上的涉及。语言的意义就在语言的使用之中,这一点也可以从戴维森为意义理论提出的任务中感觉到:“用一种语言说话的人能有效确定一个任意的表达式的意义或所有意义(如果它具有意义);而意义理论的重要任务就是去揭示这是如何可能的。”*Donald Davidson, “Truth and Meaning”, Syntheses, vol.17, 1967. p.314; p.319, p.320; p.304.要揭示这种可能性,必须深入到描述和规定,而这就必须建立在人类学特性的基础之上。
毫无疑问,戴维森已经超越了语言学的意义理论。按照戴维森对弗雷格的理解,“一种意义理论必须给出关于句子意义是如何建立在语词的意义之上的”*Donald Davidson, “Truth and Meaning”, Syntheses, vol.17, 1967. p.314; p.319, p.320; p.304.,而对于意义理论来说,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语句的意义,因为语句只有依靠语词建立与实在的联系。语词中最重要的无疑是一些重要的基本概念。由于这些基本概念中包含了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指代的实在事物,因而在经典实在论看来就建立起了与外部世界甚至可以看作是客观写照的真实联系。而在描述的角度看来,我们的任何概念都与其说是对实在本身所做出的真实写照的结果,不如说是我们根据一定的理论创造出来的工具性存在。这样一来,我们借助语词,通过概念达到实在,从而建立起语句的意义的目的就没有达到,而且不可能达到,因而显然也完全有可能只是对我们所创制的概念的描述关联。这也说明描述和描述的对象不仅不是一回事,事实上有时候还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越是具有抽象普遍性的句子越是如此,这里隐含着真理论和意义理论转换的机制。
在塔尔斯基的基础上,在戴维森那里,真理论和意义理论相继发生转换,通过退离(back away)使人们获得了一个关于真理论和意义理论的更合理理解和建构。人们关于真理和意义的理解,得以从对象本身的“真”为出发点和归宿,转向以人(类)需要和生存发展为出发点和目的,实现了意义理论的经典实在论理解和描述论理解的视界融合。在语义学意义上,真理论和意义理论既展示了传统符合论真理观和指称论意义理论的合理性,又揭示了它们的局限性;不仅使关于真理论和意义理论,而且使指称论和摹状词理论的研究,从单纯的经典实在论理解推进到了关于实在和关于描述两种视界融合中的理解。指称理论的重要性在于体现了语言和对象(世界)的联系;摹状词理论的重要性在于体现了关于经典实在的语言哲学研究和关于描述的语言哲学研究之间的联系;而所有这些都要以意义理论为归结。不是经典实在论的意义理论,就是描述论的意义理论。
在关于经典实在的和关于描述的两种致思的视界融合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真理多余论”的合理之处和致命弱点,而且能够使实在论立场有一个更合理的理解,从而走出传统实在论的理论困境,并更好地协调反实在论的立场。由此,我们就能看到反实在论立场的某种合理性。达米特从反实在论立场出发,主张抛弃二值逻辑和以真理为基本概念的意义理论,并用“证实(verification)”概念取代“真理”概念。其实,无论对于真理论还是意义理论,实践中外部世界的“回应”都具有根本的意义,这一点对于真理问题的理解至关重要。
戴维森虽然对自己所提出的关于语义学意义理论“纲领性观点”持乐观态度,但也清醒地意识到存在大量难以解答的问题。在戴维森看来,一方面,他“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另一方面,大量问题难以解答。其中就包括有关“信念”、“知觉”和“意向”的语句和蕴含无目的的行为等不能做出系统的合理解释,特别是似乎根本不具真值的祈使句、祝愿句和疑问句等大量语句。而“一个关于自然语言的全面意义理论必须成功地解决这里的每个问题”。*Donald Davidson, “Truth and Meaning”, Syntheses, vol.17, 1967. p.321, p.314.事实上,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从描述和规定的层面深深涉入语言活生生的使用,只有涉及人的需要才有可能。因此,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以人的需要为出发点,从描述层次涉入规定及人类学特性的意义理论。
描述的意义理论不仅具有重要的真理论意蕴,而且在根本上涉及悖论。在描述的意义理论中,悖论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一方面,越是从基于实在的关注到关于描述的关注,越是从实在的关注转向对描述的探索,悖论的地位就越重要;另一方面,越是在描述的意义上,悖论在意义理论中越具有表征性,悖论本身标示着意义理论的描述性质。
在弗雷格之前,由于意义理论建立在语词所指的对象上,当这种语词所指落到实在上时,由于客观世界不存在悖论,所以意义理论与悖论没有关联。塔尔斯基的意义理论建立在语义学真理之上,因此必定遇到悖论。塔尔斯基虽然对悖论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但他认识到这种悖论的重大理论意义。描述的意义理论则与悖论具有了内在联系,因为作为悖理性描述,悖论事实上是意义理论中具有标志性的界碑。*王天思:《悖论的描述成因》,《哲学研究》2014年第4期。而这个界碑,对于系统建立合理的意义理论是关键性的。
在塔尔斯基那里,(语义)悖论成了意义理论的障碍物;而在戴维森那里,重要的悖论问题是可以搁置的东西,而要建立起真正合理的意义理论,就必须与悖论问题联系起来,就像要说明除法的意义必须在根本上涉及除法的规定一样,否则我们就不能说明以零为除数的情况。塔尔斯基认为自然语言会导致悖论,因此主张改造自然语言,他所采取的是回避悖论的策略。戴维森则相反,认为“意义理论的任务不是去改变、改良或改革一种语言,而是去描述(describe)和解决它”。*Donald Davidson, “Truth and Meaning”, Syntheses, vol.17, 1967. p.321, p.314.这意味着对待悖论的积极态度,而悖论作为意义理论的表征,意味着描述向度将涉入意义理论的更深层次,并通过走向知识人类学,对知识论甚至哲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责任编辑:周小玲)
The Descriptive Theory of Meaning and Its Paradoxical Characterization
Wang Tiansi
The theory of meaning is developing from the one about reality to the one about description. A descriptive theory of meaning is coming up from the descriptive pointing of referential and ideational theories of mean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description and stipulation in use and behavioral theories of meaning, the descriptive and stipulative dimension ofsemanticandpragmatic theories of meaning. The deep investigation on description must involve the stipulation as its promise and the anthrop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cognition due to its nature of standard. As self-contradiction description, paradox is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descriptive nature of theory of meaning. And as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theory of meaning, paradox means that descriptive theory of meaning will lead to anthropology of knowledge.
Description; Theory of Meaning; Stipulation; Paradox
2015-08-01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悖论的描述成因和解决方案研究”(项目编号:12BZX004)的阶段性成果。
B812; O144.2
A
0257-5833(2016)01-0127-08
王天思,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哲学系教授 (上海 200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