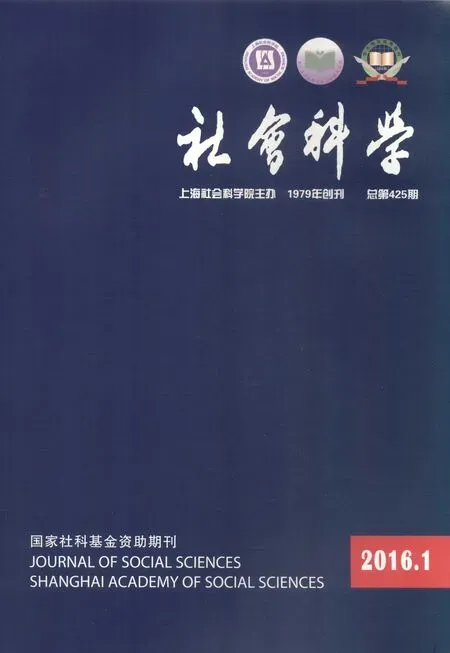海外学者的中国女性作家想像
——以夏志清、梅仪慈、颜海平的丁玲研究为中心
文学武
海外学者的中国女性作家想像
——以夏志清、梅仪慈、颜海平的丁玲研究为中心
文学武
在海外世界的丁玲研究中,夏志清、梅仪慈和颜海平无疑是有代表性的几位学者。夏志清受制于20世纪60年代东西方对峙的历史条件,他的丁玲研究不少地方带有意识形态的偏见,对丁玲极度排斥和贬低。但不可否认,他对丁玲一些作品的评论有其独到之处。而梅仪慈则跳出了意识形态的藩篱,持论相对公允,她更多地从丁玲的作品出发去发现作者的生命,重视女性主义立场,同情丁玲的转向。颜海平把丁玲视作中国现代革命链条上最重要的一位女性作家,其对丁玲革命历程的推崇和敬意是重访现代中国革命精神遗产的自然结果,她更在一个宏阔和多元的文化视野中重新阐释丁玲,把丁玲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海外学者;丁玲;夏志清;梅仪慈;颜海平
作为一个具有传奇经历和独特风格的作家,丁玲不仅在国内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声誉,就像美国权威的学术著述《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百科全书》所言:“丁玲作为一个二十世纪最有力量、最活跃的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仍占据着一个显著位置。”*① 《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百科全书》,参见孙瑞珍、王中忱主编《丁玲研究在国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4页。事实上,海外学者对丁玲的介绍和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其后海外的丁玲研究更是涌现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和学者。在这些学者中,夏志清、梅仪慈和颜海平无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从夏志清对丁玲的很多激烈指责到颜海平对于丁玲参与中国革命运动的充分同情,清晰地显示出海外丁玲研究出现了很大的转向。他们的研究代表了不同时代海外学者对丁玲的不同理解和想像,构成了海外中国女性形象研究历史的重要环节。
一
在海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夏志清先生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他在1961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举奠定了其在海外汉学界的权威地位。即使观点和夏志清相左的人亦对这部书的价值给以肯定:“作者学问之渊博,批评眼光之独到,在此一览无余……”*② 参见刘绍铭《经典之作: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引言》,载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夏志清的这部著作受到当时欧美兴起的新批评理论影响,强调文本细读,把发掘和品评杰作放在了重要的位置。因而他在观察中国现代小说时就以此为坐标,在对许多现代小说家的解读上具有鲜明的倾向性,提出了不少带有颠覆性的论点,他对丁玲的评论也同样如此。
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丁玲并没有被列入专章来论述,只是在《第一阶段的共产主义小说》和《第二阶段的共产主义小说》两个章节中论及。尽管篇幅不多,但依然能窥出夏志清对丁玲小说的总体态度。在夏志清看来,丁玲和把文艺视为政治工具的蒋光慈不同,在转向革命阵营之前,丁玲是一个非常忠实于自我的艺术家,因而她早期的创作具有独特的个性。夏志清说:“在她写作的第一个阶段里(1926—1929),丁玲最感兴趣的是大胆地以女性观点及自传的手法来探索生命的意义。她的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1928)里那几篇,如《梦珂》及《莎菲女士的日记》等,都流露着一个生活在罪恶都市中的热情女郎的苦闷与无可奈何的烦躁。很明显,由于寂寞及心情混乱,丁玲在她日记式的小说里,把她的怨恨和绝望的情绪都发泄出来。”*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87、319、192、313页。联系到茅盾、冯雪峰当年对早期丁玲的评价,夏志清这样的评价还是相对客观的。由于夏志清一再声称自己所用的标准“全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原则”*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87、319、192、313页。,因此他在考察丁玲转向左翼阵营后的创作时,也是以自己对文学的理解来衡量丁玲小说的水准,他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丁玲也是根植于这样的理念。夏志清认为丁玲此时的文字粗糙,缺乏艺术魅力。夏志清特别以丁玲的《水》为例,严厉批评了丁玲小说艺术上的倒退。夏志清认为《水》固然在主题上有着积极的意义,但让人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的丁玲接受了盛行的新写实主义的理论,在处理这样的题材时流露出强烈的概念化和公式化倾向,因而在艺术上完全失败了。夏志清批评说:“在强调集体和叙述的方式这两点上,《水》完全符合这种公式。《水》是一篇极端紊乱的故事,手法笨拙不堪……一看《水》的文笔就能看出作者对白话词汇运用的笨拙,对农民的语言无法模拟。她试图使用西方语文的句法,描写景物也力求文字的优雅,但都失败了。《水》的文字是一种装模作样的文字。”*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87、319、192、313页。同样,对于丁玲后来创作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夏志清也更多地从艺术上发现它成功和失败的地方。比如对于这篇小说中描写农会干部程仁和黑妮的恋爱心理,夏志清在引用了小说中一段语言后以赞许的笔调说:“程仁深爱黑妮,可是不敢去看她,因为她是一个地主的家属……在任何革命时代以前的小说里,这一段叙述实在不算特别,可是由于当时对心理描写的反对,程仁的心理状况在这单调无味的小说里,实在是一个难得的精彩片段。”而对于这篇小说艺术上存在的问题,夏志清也尖锐地指出:“这种写实主义充其量只是肤浅的写实,因为作者对干部的批评只局限于整风运动的目标之内。而且书中的语言,不管是如何的口语化,却不能够发掘人心。”*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87、319、192、313页。在夏志清的文学史观和批评观中,他想极力避免他的上一代批评家所深受的反映论、印象论等的影响,更为看重文学独立自足的艺术世界,一再借用劳伦斯的“勿为理想消耗光阴,勿为人类但为圣灵写作”名言强调小说家把握艺术触角的重要,因而他在解读丁玲小说时得出上面的一些结论就不足为奇了。
从文学史的视野来看,应当承认,夏志清对丁玲的这些评论有着一定的合理性,他对丁玲受到影响的新写实主义小说十分反感某种程度上也恰恰击中了左翼文学的弊病。新写实主义理论最早来源于日本的左翼文学理论家藏原惟人,后来经由“太阳社”的林伯修、蒋光慈、钱杏邨等人系统介绍到中国。左翼文学理论家钱杏邨曾经系统阐释过新写实主义理论,提出无产阶级要写的“现实”是“一种推动社会向前的‘现实’”,“要把‘现实’扬弃一下,把那动的、力学的、向前的‘现实’提取出来……这样的作品,才真是代表着向上的、前进的、社会的、生命的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的作品”*钱杏邨:《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问题》,《拓荒者》创刊号1930年1月。。写实主义文学在钱杏邨这里成为了先入为主的观念,它把文学演变成抽象观念的附庸,把文学和现实生活的复杂关系简单化。同时,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也被尊奉为至高无上的创作原则和方法。而丁玲的《水》正是这种创作方法的直接运用,被左翼批评家视作新小说的萌芽和开端。然而这样的作品由于完全忽略作家对生活和艺术的真实感受,呈现出来的却是概念化很强的“脸谱主义”特征,并没有触及到现实主义核心。当时的韩侍桁在批评沙汀的新写实主义小说时曾经概括说:“很少可疑,这作者是追随新写实主义的理论而写作。他企图在他笔下强调起集团生活的描写,于是他的作品里,不但没有个人生活的干骼,就连个性的人物都没有……”*韩侍桁:《文坛上的新人》,原载《现代》1934年第4卷第6期。这样的批评同样可以用在《水》的身上。夏志清如此严厉否定丁玲以《水》为代表的公式化作品,不应该完全归到他对丁玲乃至左翼文学的偏见,他的确是在文学史的脉络上做出了严肃思考。
但不可否认的是,夏志清对丁玲又充满着颇多的误读,甚至是扭曲,这不可避免地伤害到这部学术著作的价值。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现代小说史》写作的年代,正是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处于冷战的时期,这样的冷战思维在夏志清的这部著作中留下了无法抹去的痕迹。因此,尽管夏志清口口声声地宣称:“一部文学史,如果要写得有价值,得有其独到之处,不能因政治或宗教的立场而有任何偏差。”*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17、191、311页。但夏志清在评论一些作家尤其是左翼作家时仍然带有很强的情绪,政治上存有的先入为主的偏见窒息了他的学术生命,许多论点的提出并非建立在科学的评判之上。夏志清对丁玲的论断很多地方就是如此,换句话说,他很多时候是带着一副有色眼镜来研究他的评论对象。如夏志清对于丁玲参加左翼文学运动一直愤愤不平,认为这严重伤害到作家的才华,他甚至不无刻薄地说:“丁玲在1930年的声誉,主要是基于她早期的小说。由于这些小说对性的问题比较开放的缘故,它们遂被认为比谢冰心和凌叔华的较为含蓄的小说优越了。可是自1931年开始创作无产阶级小说后,这点微带虚无主义的坦诚态度也丧失了。剩下来的,只是宣传上的滥调。”*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17、191、311页。但凡有现代文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20世纪20、30年代兴起的中国左翼文学运动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对其采取简单化的否定态度并非求真和科学的心态,即使对于丁玲本人来说,她放弃以前的文学理念而转身于左翼文学运动,对于她自身的文学创作来说,也是一次新的尝试和丰富。虽然《韦护》、《水》、《田家冲》、《母亲》等没有达到她早期文学的高度,但并非一无是处。况且后来在延安时期,丁玲仍然创作出了《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夜》等颇有现实主义深度的小说,对此夏志清在他的著作中却只字未提,无论如何,对于一个严肃的文学史研究者而言,都是不小的失误。对于丁玲反映土改的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夏志清也是精心引用了一大段翻身农民批斗地主钱文贵的文字,以此来暴露新政权所谓的“血腥”、“恐怖”和“不人道”的一面,从而达到否定土改运动的目的。夏志清把丁玲的这部小说作为了一本社会学资料来看待,进而也否定它的文学价值。他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一本企图表现农村真相的著作,写得虽然卖力,但却是一本枯燥无味的书……大部分是对村民及来村中的干部的简短素描。”*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17、191、311页。当夏志清带着某种成见得出这样观点的时候,遭到有识之士的批评就毫不奇怪了。捷克汉学家普实克认为夏志清划分和评价作家的首要标准是政治性而非艺术性的,并不是像他宣称的那样。夏志清对丁玲等左翼作家的评论完全无视普通人的尊严,为此普实克批评说:“对于作家丁玲的政治观点正确与否,我们或许意见不一,在评价她的不同作品时,也很有分歧;但对于夏志清谈及丁玲的生活与性格的方法,我们却不得不表示抗议。在描写到这位女作家的私生活时,夏志清只是一味地重复道听途说的谣言,而且用了最低级的词语,读来令人心生厌恶。”*[捷克]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参见李欧梵主编《抒情与史诗:现代中国文学论集》,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94页。后来夏志清在回答普实克的指责时尽管承认“自己对丁玲的评价有失公允”*夏志清:《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参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25页。,但他坚称自己对《水》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评价并没有错,而是对丁玲早期小说和延安时期的作品关注太少。可见,在对丁玲及其他左翼作家的评价上,夏志清的态度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如果说夏志清的著作在对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师陀等作家的评价上显示了自己独到的眼光,从而使得他的文学史观享有盛誉的话;那么他在丁玲的论述上总体而言却缺乏开创性的见解。政治立场的局限使得夏志清的这种评论往往从单一的视角入手,缺乏多重文化视野的观照和文化心理的剖析,不自不觉中陷入自己所设的文学史陷阱之中,因而他所呈现的丁玲必定是单调和平面化的红色革命作家形象。
二
继夏志清之后,20世纪70和80年代在美国汉学界又出现了一位重要的丁玲研究者,这就是密西根大学教授梅仪慈女士。为了研究丁玲,梅仪慈曾经在1981年亲自来中国多次访问丁玲。不仅如此,她还花了很大的力气用来尽可能搜集丁玲的文献资料。她自己曾说:“我这次访华目的之一是要阅读丁玲写过的每篇作品,也包括那些曾在当时刊物或地方小报上发表过的不易搜集的短文在内。另一目的是要找寻那些丁玲小说作品首次刊登的杂志或报纸……”*梅仪慈:《丁玲的小说》,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48页。显然,梅仪慈花费的力气和拥有的条件比起夏志清要大得多、好得多,这也使得梅仪慈的丁玲研究很多地方超越了夏志清。她把丁玲还原为一个杰出的女性作家、一个具有强烈女性主义色彩的作家以及虔诚的革命殉道者的形象。
与夏志清的丁玲研究明显不同的一点,梅仪慈对于丁玲早期作品给予了异乎寻常的关注。夏志清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丁玲早期的作品,更谈不上深入的文本解读和分析,然而在梅仪慈看来,丁玲早期的文学特点和成就无疑在这个作家一生中都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丁玲独特的生活经验造就了她早期作品的内容和特点,比如大多表现青年女性的叛逆意识和苦闷心理。梅仪慈评价《莎菲女士日记》时说:“在丁玲最著名的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毁灭的威胁主要并非来自社会对淳朴女性的摧残,而是来自对抗这个世界的过程中最后对自己的认识。”“在早期作品的女主人公中,莎菲女士是最具代表性的,或可说是性格最鲜明的形象,因为在她的身上作家花的笔墨最多。”*梅仪慈:《丁玲的小说》,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48页。这里可以看出,梅仪慈的评论和当时大陆还在盛行的社会学批评有很大的距离,她并没有仅仅从社会、经济等层面来追究莎菲悲剧的成因,而是从女性自我的矛盾中去揭示,因而更为合理。难能可贵的是,梅仪慈还采用文学叙事学的方法对丁玲小说的艺术结构进行了颇为精彩的分析。梅仪慈敏锐地发现,在丁玲早期的小说中,经常采用日记体、书信体等“第一人称叙述法”,其原因就在于这样的叙述方式有助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而大大促进了人物的塑造和题材范围的扩大。而随着丁玲创作思想出现变化时,作家所采用的手法也会出现变化,如当丁玲20世纪30年代转向革命文学的题材时,“第一人称的叙述方法”就不适用了,于是丁玲在《水》等作品中采用被普鲁谢克称为“点彩法”的叙述方法,“以互不相连的瞬间一现的情景和身份莫辨的人物对话的只言片语来表现被饥饿和灾荒折磨得不堪忍受的农民群众觉悟的不断提高”;而在丁玲后来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作家的技巧更为精细,“她尽力把对人物个性化描写和对某个小范围的社会集群中代表人物的生活经历的叙述结合起来”*梅仪慈:《不断变化的文艺和生活的关系》,参见袁良骏主编《丁玲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第468、469页。。而梅仪慈的深刻之处在于,她从这种叙述变化中看出了中国现代文学随着社会进程所发生的微妙变化。随着新的社会秩序建立,那些主观性的叙述方式没有了立足之地,作家也必然要抛弃这样的方式,否则就会陷入危险之中,梅仪慈为丁玲研究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
作为一个女性研究者,更因为丁玲作品始终关注中国女性的生活和命运,梅仪慈也敏感地发现丁玲和女性主义有着无法割断的联系,而这也恰是夏志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一个明显遗漏的地方,他在论述丁玲的时候根本没有涉及到此类的主题,连对夏志清十分推崇的王德威也曾经遗憾地提到这一点。梅仪慈对丁玲女性主义的解读,也使得丁玲的形象在革命作家和革命战士的身份之外,又增加了中国女性主义作家先驱的角色,内涵无疑更加丰富。
梅仪慈眼中的女权主义并非西方严格的女权主义理论,她说:“我在谈到丁玲的女权主义时,指的并不是妇女的权力,而是她们对于女性独特地位的觉悟以及丁玲作品中对这一点的描写。”*梅仪慈:《不断变化的文艺和生活的关系》,参见袁良骏主编《丁玲研究资料》,第472;472;472;474;474;478、479页。这在一点程度上避免了照搬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从而对丁玲做削足适履的研究。梅仪慈注意到,在丁玲早期作品中,女性主义的主题是十分明显的,不仅丁玲本人受到她母亲强烈自尊、独立人格的影响,而且她早期作品中的女性几乎都在为维护女性的独立人格而苦苦奋斗和挣扎:“到1931年为止丁玲的大部分短篇小说,都几乎令人忘情地集中表现了年青妇女怎样设法在女性的社会地位之上或超出这种地位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在上述早期的文学作品中,由于主人公通常是女性,对主观自我和女权主义的两种考虑便自然地融为一体。”*梅仪慈:《不断变化的文艺和生活的关系》,参见袁良骏主编《丁玲研究资料》,第472;472;472;474;474;478、479页。梅仪慈接着较为详细地探讨了丁玲作品女权主义内容的几个阶段及在不同期间呈现的变化。梅仪慈认为丁玲早期作品女主人公在追求爱情和打破旧传统观念的重要表现就是她们在性的方面所表现的大胆和反叛,这是女权主义的重要内涵。她说:“她的确暴露了女性性欲的某些方面,而这些在以往和以后的中国文学中都没有得到描写。使丁玲作品突出地区别于‘五四’时期对于爱情流露的一般描写的原因,不仅在于她是一个多少比其他人更直率勇敢的女性,而且在于她时常将性解放主义同妇女个人的自我探索结合起来。”*梅仪慈:《不断变化的文艺和生活的关系》,参见袁良骏主编《丁玲研究资料》,第472;472;472;474;474;478、479页。这就从女性主义角度证明了丁玲文学创作在文学史上的独创性。后来随着丁玲转向左翼阵营,她作品中的女权主义色彩大大减弱,“对性本身的关心已经超出了原来的范围而被对灾难和紧急任务的描写所替代,或者说降到了次要地位”*梅仪慈:《不断变化的文艺和生活的关系》,参见袁良骏主编《丁玲研究资料》,第472;472;472;474;474;478、479页。。但随着丁玲延安时期创作高峰的来临,其作品中再次呈现出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如《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及杂文《三八节有感》等。与以前描写女性的角度不同,“她不再写只表现个别女子内心斗争的东西,而是抨击妇女所遭受的苦难以及她们在社会中所受到的特殊歧视,虽然在她当时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那个社会是非常进步的”*梅仪慈:《不断变化的文艺和生活的关系》,参见袁良骏主编《丁玲研究资料》,第472;472;472;474;474;478、479页。。这再次证明了丁玲的文学并非完全由意识形态所主导,她内心深处仍然充满了对文学内在生命的追求。
夏志清曾经对左翼作家追求文学历史使命和社会功能的做法给以了极为严苛的批评,这也导致了他对丁玲参加革命以后的创作几乎全盘否定。然而,对于丁玲创作和社会生活、革命关系等的理解上,梅仪慈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夏志清的偏狭,给予了同情和肯定。梅仪慈认为,丁玲一生的文学创作和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即使那些最主观的感情流露也都清楚地反映了她周围不断出现的政治和社会的变化。” “随着文学明显的政治化,丁玲文学事业中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就进入新的阶段”*梅仪慈:《不断变化的文艺和生活的关系》,参见袁良骏主编《丁玲研究资料》,第472;472;472;474;474;478、479页。。梅仪慈并不认为这样的结合必然会给文学带来伤害,相反,丁玲仍然在此后的创作中有新的贡献。梅仪慈的专著《丁玲的小说》中用了相当的篇幅来论述丁玲转向革命后的创作道路。如对于丁玲早期的“革命加恋爱”小说,梅仪慈肯定它们在丁玲文学过渡期的价值:“上述的三部小说并非只是给一个当时陈腐题材翻些新花样。”因为从本质上看,这些革命加恋爱公式的文学是浪漫一代的典型特征,“那些在三十年代写作公式小说的左翼作家们,虽然他们富有浪漫气息、主观精神而且激情洋溢,但当他们描写革命志士的时候,多少是抓住了一些历史的真实”*梅仪慈:《丁玲的小说》,第91页。。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在对丁玲小说《水》的评价上,梅仪慈也有自己的见解。虽然她并不认为《水》是一部艺术上成功的作品,但她对夏志清否定《水》真实性的观点也进行了驳斥,她以左拉的《萌芽》为例,说明丁玲的写法和左拉一样是为了凸显生命的尊严,对于作品主题来说是必须的,并不存在违反真实性原则。对于丁玲后来的土改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梅仪慈用了整整一个章节来论述,足见她对这部毁誉褒贬不一的作品的重视程度。对于中国现代历史上这场翻天覆地的土改运动,梅仪慈毫不隐瞒她的同情,这在西方世界学者中是比较罕见的,她说:“土改如同长征一样是有震撼人心和巨大教育意义,农民在土改中提高了觉悟,摆脱了几个世纪来被压迫被剥削的困境,破天荒第一次获得了新生活,看到未来光明的前景……当然,在如此复杂而又激烈的社会变动中,难免出现一些失误和不足。”*梅仪慈:《丁玲的小说》,第217页。可见,在梅仪慈眼中,这场土改运动在道义上具有无可争辩的合法性,这和夏志清对待土改运动的态度具有很大的不同。可以看出,海外中国文学研究者逐渐抛弃了以意识形态来左右作家评论的模式,这样的进程正是文学研究深化和日趋多元的标志,梅仪慈塑造的丁玲形象就是这种研究方式调整的产物。虽然梅仪慈的研究有时深度不足,流于平面化的论述较多,也缺乏夏志清那些颠覆性、震撼性的观点,但毕竟把丁玲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三
进入到新的世纪,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日益扩大,海外对中国的关注持续升温,海外学者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也进入到一个众声喧哗、成果丰硕的时期。大量的学者以一种更宽阔的文化视野、更新颖的文学研究视角、更为严肃的学术精神来接近研究对象,诸如王德威、刘剑梅等的丁玲研究就代表了这样的趋势。而颜海平的《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的出现对于丁玲研究而言是一次重大的事件,它把一个更为丰富、更具有多元文化意义的丁玲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代表着海外丁玲研究的最新进展。
颜海平的《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虽然并不是一部研究丁玲的专著,但它的核心命题以及价值取向、文化立场等都不能不影响到对于丁玲的论述。颜海平的著作以较大的篇幅探讨了秋瑾、白薇、王莹、萧红、丁玲等女性投身现代中国革命的生活和艺术实践,单是丁玲就用了两个章节,几乎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一;而对于当下很多人所热捧的张爱玲、苏青等女性作家只字未提,这和曾经以很大篇幅论述张爱玲的夏志清形成强烈反差,清楚地亮出了作者犀利的观点。毫无疑问,这是一部重访中国革命精神遗产的学术著作,其对于革命女性倾入了大量的同情和敬意就是最好的明证。而作者也曾经谈到自己这样的研究在现实语境中所可能遇到的尴尬:“在当时被界定为有别于欧美主流的‘区域研究’制度安排下的‘中国研究’及其流行的话语语境中,现代中国女作家的革命性文化遗产的重要内涵似乎是一个说不出来的故事;人们倾向于将中国的革命女性在根本上看作是她们亲身参与的中国革命工具化的牺牲品。在一个全球消费主义超速复制的90年代,写这样的一本书似乎不很合时宜。”*颜海平:《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256、307页。事实上确乎如此,此书写作的背景正是不少学者喊出“告别革命”的时刻,在他们笔下,“革命”排斥了“自由”、“人性”而成为一头可怕的洪水猛兽。然而颜海平却不以为然,仍然以浓重而富有激情的笔调重绘了她心目中中国革命女性的形象,展示了丁玲饱满、传奇却又充满悲剧色彩的一生。在颜海平笔下,丁玲一生都和中国的现代革命紧紧相连,因而她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才把丁玲称为“20世纪中中国最为杰出的女作家”*颜海平:《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256、307页。。她投身革命的经历既浸润着女革命家秋瑾的精神传统,也“意味着中国女性写作史上一个革命性的转折点”*颜海平:《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256、307页。。
正是基于对丁玲革命实践和写作的钦佩,颜海平在对丁玲不少作品的评价上都和信奉自由主义的夏志清形成针锋相对的情形,这最突出地表现在她对《水》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评价上,而丁玲这两部带有鲜明革命印迹的作品恰恰是遭到一些海外学者诟病最多的。对于丁玲转向革命后创作的带有标志意义的《水》,颜海平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肯定了它的合理性。她说:“1931年至1933年间出现的一批小说,以强有力的想象,集中表现了不同的社会难题和被抹杀的人们的境遇。她那不断扩展的、被以不同方式的暴力所毁灭的人类生命和所边缘化的人生存在的集合星座,在中篇小说《水》中以其动人心魄的力量达到了史诗的规模。”*颜海平:《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第294、360、360、362、5、263、265、319页。颜海平认为,丁玲在这部作品中真实展现了集权和暴政的年代底层人民尤其是女性的灾难,忽略了中国这些具体的农村和女性的不幸而去空谈所谓的女性主义没有任何意义,因而丁玲在《水》中所做出的描述具有还原历史的价值。“在《水》中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这种构图让我们想起她早期小说中那些在社会上被抹杀女性的痛苦,这些女性是和那些物质上被剥夺的大多数人的抗争联系在一起的,他们遍布城市乡村,同时也跨越了男女性别的分野”*颜海平:《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第294、360、360、362、5、263、265、319页。。而对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作品,颜海平一方面否认了它是一部所谓的概念化的作品,她认为作品很多地方的描写触及到中国乡村社会复杂的关系,呈现出开阔的艺术视野;另一方面,作品中表现出的翻身农民对土地改革的强烈愿望符合人性本身的要求,不应该冠之以“暴力”、“非人性”等的标签。她说:“土地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关于人的革命性转变的可能和实现,关于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安排的革命性转变的可能和实现。它关系到另一种形成或再形成中的人性本身。在这个意义上,村民们在‘清算钱文贵’的集会上表现出的对他的愤怒,是面对和探讨并变革这个‘世道’的一个关键时刻,此时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触及了这个核心。”*颜海平:《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第294、360、360、362、5、263、265、319页。可见,土地改革不仅仅是简单的生产关系的变革,而且也深刻地改变着人性,颜海平以黑妮精神面貌的变化举例说:“她是生命快乐的显现……土地改革给中国农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中国革命赋予了真实的内容,为人性再造、生命再生留下了一份无价的想像财富。”*颜海平:《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第294、360、360、362、5、263、265、319页。颜海平对于丁玲革命故事和革命叙事的双重解读和欣赏,显示了作者不合流俗的理论勇气,也冲击了那种把早期丁玲和后期丁玲生硬割裂的学术观点。
颜海平对于丁玲研究的突破还更多地表现在她的方法论意识上。由于作者多年在海外学习,接触到许多西方的文学和艺术理论,更由于她有着自觉的方法论追求,因而在论及丁玲的章节中都能看到她的这种努力。颜海平曾说:“我在这些跨国别、跨学科研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认知视域,激发和促成我探索研究和阐释中国现代女作家,中国现当代文化与艺术,乃至现代中国人文历史和社会发展本身的路径和方法。”*颜海平:《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第294、360、360、362、5、263、265、319页。比如颜海平引入了跨学科的意识,把对丁玲孤立的文学研究拓展到电影、戏剧、都市文化、性别理论等的领域中,无形中大大拓展了丁玲研究的空间。关于丁玲与电影、丁玲作品与电影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少有人涉及的话题,颜海平却用了不少笔墨勾勒了丁玲在投身文学活动之前和电影的关系,而正是这样的经历使丁玲“在那些以‘半裸’为标签的‘女性’身上,看到了一个躁动浮华、追逐利禄的社会化的‘mon coeurs’们的挥之不去的游荡阴影——‘孤独倔强’的人们深陷于以他们的生命为营利之物的生存环境之中,而这环境本身则是以排除他们的人性意义为前提的”*颜海平:《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第294、360、360、362、5、263、265、319页。。这是丁玲早期作品中女性主人公的一个重要特点,和丁玲尝试电影明星的一段经历密不可分。不仅如此,颜海平还注意到,丁玲排斥的是电影技术背后隐藏的社会关系及人性代价,而对于电影技术本身并不反感,相反,“在丁玲的一生中,她和摄影机及其种种操作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主动的关系”*颜海平:《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第294、360、360、362、5、263、265、319页。。她通过丁玲写作《梦珂》前所拍照片及成名后所拍照片的区别,证明丁玲是善于运用这些电影技术的。至于丁玲和戏剧的关系,颜海平用了很长的篇幅谈论了丁玲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所从事的戏剧活动,认为这是丁玲延安时期工作和生活的重要部分,理应受到重视。丁玲不仅领导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工作,用戏剧形式来鼓动抗战宣传,而且亲自参与到演戏的进程,扮演主要角色,从而完成了自己革命身份的重新确认。颜海平特别以丁玲很少被人注意到的一部独幕剧《重逢》为例,详细分析了这部作品所蕴含的复杂问题,诸如女性身体与革命忠诚等,“打开了对现代世界中革命人性想像实践的巨大空间,同时也包含着高度的风险和复杂的后果”*颜海平:《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第294、360、360、362、5、263、265、319页。。这也表明丁玲并没有把戏剧简单视为宣传工具,而是赋予了更深的内涵。此外,对于丁玲早期作品中女性的生存状况,颜海平特别从都市文化的角度进行了全新的论述,成功地把文化研究引入到丁玲研究中来。颜海平注意到,丁玲早期作品中的女性大都居住在都市,生活窘困,患有肺病,实际上这是一种都市流行病的症候。上海作为中国现代都市的象征,对那些孤独无助的女性而言,充满了压迫感和疏离感,“作为现代中国的形象与幻象,1920年代末的上海,带着那些被具体地组织和区分开来的特征,第一次出现在丁玲的早期作品中;这座城市引人注目的是一系列复杂的人类身体的形象,它们是权力阶层与其种种‘下等阶层’(positional inferiors)及‘社会混混’(social non-entities)之间张力和矛盾的集合”*颜海平:《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第280页。。而丁玲最可贵的地方在于,在她本人也面临着都市的巨大挤压时,她以女性主义的立场进行了抵抗,捍卫着女性的尊严,从而在自己的作品中展现了中国都市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最大耻辱。都市文化理论的介入,使得丁玲早期作品的社会和女性命运成因得到了很好的解释,而这只有具有较为开阔的学术视野才能做得到。由于颜海平的丁玲研究充分吸收了当代前沿学科的知识,在更新的理论维度上阐释了丁玲现象复杂化的生成,因而她的研究突破了夏志清那种平面化、单线式的格局,对于梅仪慈也是成功的超越。
从上个世纪的夏志清到当代的颜海平,海外不少学者投入精力来研究丁玲,这本身既是丁玲的生命和文学魅力所在,也是她所隐含的诸多富有张力的命题所致,如启蒙与革命、性别与政治、革命与知识分子,等等。可以看到,从夏志清非此即彼的政治二元论立场出发评论丁玲;到颜海平多重视野的文化观照,丁玲的海外形象正发生着质的变化:那种情绪化、充满敌意的观点正越来越让位于科学的、富有同情的学术良心;那种单一的文学研究模式也被更为多元、立体的文化研究而取代,而这必定会给未来的丁玲研究带来深刻的影响。
(责任编辑:李亦婷)
The Imaginations of Chinese Female Writers in Overseas Scholars’ Eyes — Take Xia Zhiqing, Mei Yici,Yan Haiping’s Studies of Dingling as the Center
Wen Xuewu
In the overseas studies of Dingling, Xia Zhiqing、Mei Yici and Yan Haiping are definitely the representative scholars. Xia Zhiqing is limited by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s when the East was in conflict with the West in the 1960s. Therefore, many parts of Xia Zhiqing’s study of Dingling has prejudice ideology. In fact, Xia rejected and belittled Dingling. But there is no denial that his critiques about Dingling have some originalities. However, different with Xia, Mei Yici is not affected by the limitation of ideology. Instead, she studies Dingling from Dingling’s works and pays attention to a feminism perspective and sympathizes Dingling’s change. Yan Haiping regards Dingling as the most important female writer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Yan Haiping’s admiration and praise for Dingling’s revolutionary adventure are the natural result of revisiting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ary spirits. Yan Haiping reexplains Dingling from a vast and multivariate horizon, and she puts Dingling’s studies to a higher position.
Overseas Scholars; Dingling; Xia Zhiqing; Mei Yici; YanHaiping
2015-08-28
I206.7
吗: A
0257-5833(2016)01-0175-08
文学武,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 200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