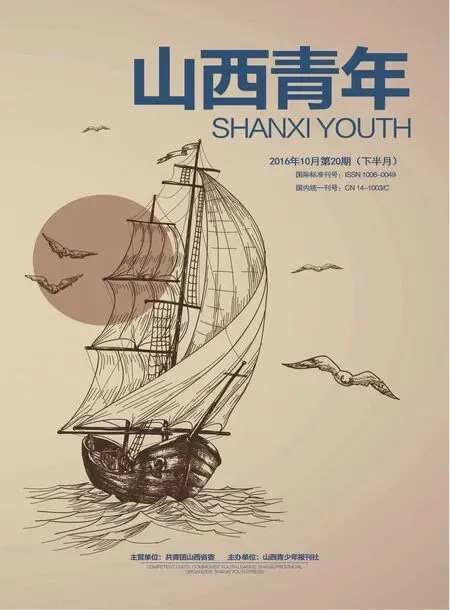从政治与历史渊源看“诗言志”与“诗缘情”
沈 强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 100048
从政治与历史渊源看“诗言志”与“诗缘情”
沈强*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100048
“诗言志”与“诗缘情”是先秦及魏晋时期提出的关于诗歌本质的理论命题,这两个文学观念的提出,与各自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及文学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诗言志”是先秦时期,诗歌作为礼乐制度的一部分,为政治统治服务,主要发挥它的政教作用下提出理论命题。魏晋时期,非功利的纯感性、抒情诗作兴起,人们更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诗歌由政治之诗变为抒情之诗,陆机提出“诗缘情而绮靡”。本文即从政治历史的角度,说明“诗言志”与“诗缘情”提出的必然性,及对诗歌的本质及作用加以探讨。
诗言志;诗缘情;诗歌作用
“诗言志”与“诗缘情”是先秦及魏晋时期提出的关于诗歌本质的理论命题,关于它们的涵义已有很多学者进行过探讨,也有人认为从“诗言志”到“诗缘情”是一个发展过程,这其中有开始、成熟到完成的过程。笔者认为“诗言志”与“诗缘情”这两个文学观念的提出,与各自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及文学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诗言志”与“诗缘情”之间不一定存在着一个文学观念的转变。“诗言志”强调诗歌的政教作用,因为诗歌的产生本身就有实用、政治的目的。诗歌在整个古代社会的发展都是具有实用的目的及作用。就如闻一多先生所言“诗似乎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在这里发挥过的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生活。维系封建精神的是礼乐,阐发礼乐意义的是诗,所以诗支持了那整个封建时代的文化。”本文即从政治历史的角度,说明“诗言志”与“诗缘情”提出的必然性,及对诗歌的本质及作用加以探讨。
诗乐的产生就带有实用政治目的。“诗言志”出自《尚书·尧典》“帝曰:夔,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从《尚书》记载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上古时期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特征及诗乐温柔敦厚的教化作用。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表现形式,与上古时期的祭祀活动有密切的关系。《尚书》、《礼记》、《左传》、《吕氏春秋》、《春秋繁露》都有记载祭祀的相关仪式。《礼记·乐记》“若夫礼乐之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则此所与民同也。”此用于宗庙社稷与事乎山川鬼神,都是礼乐在祭祀中的作用。《吕氏春秋·古乐篇》:“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乃以麋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瞽叟乃拌五弦之瑟,作以为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尧命质来作乐舞《大章》,来祭祀上帝。可以说,祭祀的仪式就是以诗乐舞结合的形式来完成的。祭祀活动是诗歌产生的源头之一。上古时期,自然灾害频多、生存环境恶劣,多干旱、洪水且猛兽逼人。祭祀活动是与上天、祖先交流的形式,是祈福的形式,人们通过祭祀来祈求风调雨顺,先王通过祭祀来安抚统治教化万民,而由祭祀产生的诗乐自然也就带有实用的目的。《春秋繁露·郊祭》:“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兴师伐崇。其《诗》曰:‘芃芃棫朴,薪之槱之。济济辟王,左右趋之。济济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此郊辞也。其下曰:‘淠彼泾舟,烝徒檝之。周王于迈,六师及之。’此伐辞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以此辞者,见文王受命则郊,郊乃伐崇,伐崇之时,民何处央乎。”此篇《郊祭》记载文王进行郊祭,问军事战争之吉凶。祭辞及伐辞之《诗》曰“芃芃棫朴”“文王受命”,出自《诗经·大雅·棫朴》,其下曰“文王受命”出自《诗经·大雅·文王有声》。《诗经》雅颂诸篇,当为祭祀时诗歌。也可见诗乐在政治、军事及教化上的作用。《礼记·乐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这里明确说明诗乐与政教的密切关系,礼乐与天地感应的重要作用。
周代形成一套礼乐制度来维持统治,但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礼坏乐崩,诗乐的政教作用也有所减弱,诗歌则承载着政教作用。一、诗歌考察民风及讽谏教化作用,《诗大序》中言“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段话前一部分,言通过诗歌可以得知一个国家的政治情况。后一部分言诗歌的讽谏教化作用,“正得失”是对统治者而言,是讽谏作用。“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是对百姓而言的,是教化作用。《国语·晋语》(范)文子曰“吾闻古之言,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祅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先王疾是骄也。”赵文子行士冠礼之后,见栾武子、范文子、韩献子等大臣,范文子教导他不要得宠而骄,要听公卿列士献诗,知道政教得失所在,过则改之。二、诗歌的外交作用。《左传》中记载很多诗的外交功能,如在文公十三年,“郑伯与公宴于棐。子家赋《鸿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赋《四月》。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采薇》之四章。郑伯拜。公答拜。”郑伯想请文公帮忙向晋国说情,维持两国的关系,郑国大夫子家赋《鸿雁》篇,以鸿雁哀鸣来比喻国家的处境,请鲁文公帮忙。鲁国季文子赋《四月》篇表示拒绝。子家又赋《载驰》求助,季文子赋《采薇》篇表示愿意帮助,可见赋诗在外交中的作用。《左传·成公二年》齐晋鞍之战,齐侯战败派宾媚人见晋国的使者。晋人要求“必以萧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宾媚人对曰:“萧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则亦晋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诸侯,而曰:‘必质其母以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若以不孝令于诸侯,其无乃非德类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则不义,何以为盟主?……《诗》曰:‘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子实不优,而弃百禄,诸侯何害焉!……”宾媚人的回答中,有三处引用《诗经》来说理,言明厉害,拒绝了晋人的要求,这里《诗三百》显然被当作权威话语来对待,可见诗在外交、应对上的重要作用。
诗歌的社会、教育作用。《论语·阳货》“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在这里教导孔鲤,说诗可以兴、观、群、怨,可以明事父事君之理,可以学鸟兽草木之名。可见学诗,也是因为诗的社会功能。春秋战国时期,诗歌的作用就是赋诗以在外交、政治上表达自己的观点、立场与怀抱;观诗以知政教得失、民俗风气;献诗以讽谏君王、赞颂君王。正是由于诗的政教作用,所以这时期,诸家都提出“诗言志”的论断。如《荀子·效儒》“诗言是其志也”,《庄子·天下篇》“诗以道志”,《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诗以言志”,《礼记·乐记》“诗言其志,歌咏其声,舞动其容”。“诗言志”偏重用诗、赋诗而不是作诗。《诗经》大部分都不知其作者,表达的不是个人之情,而是集体共鸣之志,圣人之志。“诗言志”的提出是当时政治制度、社会氛围、文学尚未独立情况下的必然。
思想是断裂的、不连续的,不存在“诗言志”向“诗缘情”的转化,或是说后出现的“诗缘情”就是比“诗言志”要高明。“诗缘情”的提出,与各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潮有密切的关系。秦始皇统一六国,焚书坑儒,礼乐制度更是不复存在,赋诗言志也不盛行了,诗歌的政教作用减弱,诗歌教化不能成为维系统治的一种手段。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之际,已开始记录抒发个人情志的诗作,如刘邦的《大风歌》,项羽的《垓下歌》,都是作诗抒发自己的情志。刘邦建立了大一统汉朝,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文学也有了发展。汉赋的兴起,使“文学”与“文章”有了区分。汉赋铺陈体物,大量使用双声叠韵的华丽辞藻,同时也拓展了文章描写表现的题材,出现了像司马相如、枚乘那样以文章立足朝廷的文人,汉赋对魏晋诗歌风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虽然汉赋备受统治者青睐,此时的诗歌仍有一定的政教作用。《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云:“自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乐府采诗作乐,观风俗、讽刺政治,诗歌的作用主要还是传统的教化作用,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已经有了个人情感的因素,故《诗大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此时,“诗言志”中“志”的内涵相对于先秦时期已有所改变,“志”不再强调圣人之志、集体之情志,而是个人之情志。汉代个体意识萌芽,初见文学自觉端倪,为魏晋时期文学自觉,文学、诗文评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东汉末年,政局混乱,采诗讽刺,诗歌教化,已经不能发挥维护国家稳定的作用。曹魏时期,政治上选拔人才实行九品中正制度,使人物品评之风盛行,刘劭作《人物志》,论述了如何认识人才、如何发现人才、如何使用人才,形成了人物批评的一些规律。人物的品评与人物的才能、文章相结合起来,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大量文学批评著作有一定的影响。曹丕的《典论·论文》言“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与吴质书》“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钟嵘《诗品》“先是郭景纯用隽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这些都是将人的品质与所作文章一同评论。把人品与文品相结合批评,重视文人,成就了文学的自觉。两晋时期司马氏执政,多数文人作为“前朝遗民”,生活在恐惧之中。《晋书·阮籍传》言“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可见当时文人的生存状态。政治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士庶有别,庶族文人没有晋升之途,士族文人没有政治建树。政治上的无望,使得文化上盛行宴游、清谈之风,思考纯思辨性的命题,探讨宇宙万物的本源。而且长年的征战、频繁的政权交替,造成了人们对生命易逝、离别无常的感伤。因此,文人更重视个人的感受,及时行乐,感物而动,以诗文抒发自己的情志。如曹植《赠白马王彪》其四“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感物伤我怀,抚心长太息。”王粲《七哀诗》“丝桐感人情,为我发悲音。羁旅无终极,忧思壮难任。”徐幹《思室》其二“君去日已远,郁结令人老。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时不可再得,何为自愁恼?”阮籍《咏怀诗》“闻秋兆凉气,蟋蟀鸣床帏。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何劭《游仙诗》“青青陵上松,亭亭山中柏。光色冬夏茂,根柢无凋落。吉士怀贞心,悟物思远托。”陆机《悲哉行》“伤哉游客士,忧思一何深。目感随气草,耳悲咏时禽。”这些魏晋诗人有感而发,诗风慷慨悲凉。这时,哲学、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再密切,诗歌的作用发生了变化,诗的政教作用减弱了,相对应的诗的抒情功能增强了。陆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是政治环境、历史发展的必然。
“诗言志”是先秦时期,诗歌作为礼乐制度的一部分,为政治统治服务,主要发挥它的政教作用下提出理论命题。诗歌在发挥政教作用的同时,自然是有人的情感参与进来。诗中并非不含情,志中也并非不含情,只是当时人们只重视诗的教化作用,而没有诗缘情的自觉。《诗经》中有很多抒情之作,《毛诗》给这些诗加上了政教的帽子。人的各种情感是相通的,屈原之“香草美人”就是把君臣比作夫妻。因着诗的“比兴”功能,所以《诗经》中大量的爱情诗得以保留。《论语·子罕》中孔子引诗“棠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是室远而”。又说“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不管这首诗原来是表达什么情感的,引用的是“找借口不去做某事”的意思。先秦时期不管是“献诗陈志”、“赋诗言志”、“教诗明志”还是“作诗言志”都是言说诗歌的政治实用功能。而随着礼乐制度的瓦解,秦汉政权的更替,政治制度的变化,经济的发展,文学逐渐走出文史哲不分的时代,文学与文章有了区别,文体有了区分,诗歌的作用发生了变化。魏晋时期,非功利的纯感性、抒情诗作兴起,人们更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诗歌由政治之诗变为抒情之诗,“诗缘情”的提出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以后时代应是“诗言志”与“诗缘情”并存,“志”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先秦强调的是圣人之志,国家之志,政教之志,抒发之情是作者之情(作者心情),表达之情是符合圣人之志的情,所用之诗情(读者之情)就是圣人之志。“诗缘情”抒发表达体会的都是诗人之情志,情多是闲情逸致(情感),志多是仕途之志(志向),这个志向有可能是儒家之道,圣人教诲,但不是作为政教之用。“诗言志”与“诗缘情”都是应各自时代而生的理论命题,是诗歌的不同作用的体现,它们体现了人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文学的思考。
[1]朱自清.《诗言志辩》.岳麓书社点,2011.
[2]陆侃如,冯沅君著.《中国史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
[3]冯友兰等著,骆玉明选编.《魏晋风度二十讲》.华夏出版社,2009.
[4]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6.
[5]刘安然,杨隽.《“诗言志”与“诗缘情”》.《文艺评论》,2014(10).
[6]詹福瑞,侯贵满.《“诗缘情”辨义》.《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02).
[7]洪树华.《20世纪“诗缘情”阐释之述评》.《社会科学研究》,2004(04).
沈强(1992-),辽宁兴城人,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硕士。
I207.22
A
1006-0049-(2016)20-007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