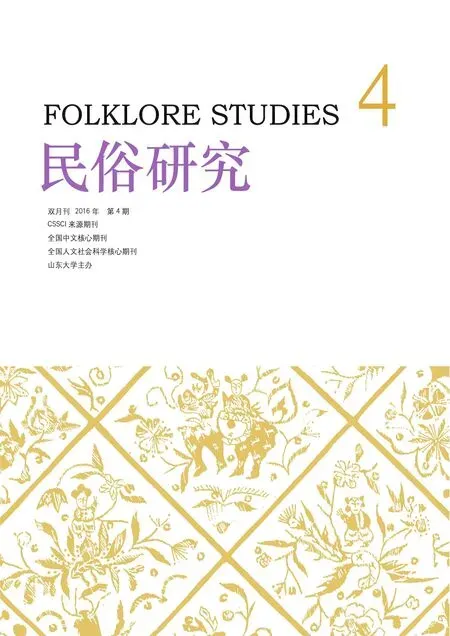地方礼俗教化权利的分享与边界
——以清前期士绅赵执信《礼俗权衡》为例
任雅萱
地方礼俗教化权利的分享与边界
——以清前期士绅赵执信《礼俗权衡》为例
任雅萱
摘要:在清康熙年间的鲁中山区,作为国家代表的地方官以“六谕”“上谕十六条”为依据积极推行乡约。与此同时,士绅阶层在其家乡的建设活动更为频繁,而且有将礼仪在乡间闾里进行推广的趋势。士绅阶层一方面受礼仪的教化,了解官方的话语;另一方面,除去士大夫的身份,他们又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熟知本乡的风土人情。因此,他们对礼俗的讨论,并非只停留在国家礼仪制度层面,而是多从本地乡里的实际风俗出发。国家和地方士绅在基层社会的礼俗教化,存在着权利的分享和边界。二者有所重叠,但彼此又存在着微妙的距离。
关键词:礼俗教化;地方士绅;清前期;边界
在明清史研究当中,学者历来重视士绅这一阶层,并将其视为探讨明清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视角。有学者梳理了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与士绅有关的研究成果,认为东、西方学术界的研究取向经历了从“士绅论”到“乡绅论”再到“地方精英”的过程。①衷海燕:《士绅、乡绅与地方精英——关于精英群体研究的回顾》,《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尤育号:《近代士绅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谢俊贵:《中国绅士研究述评》,《史学月刊》2002年第7期。尽管每一阶段的论述侧重点和定义各有不同,也多有争议,但他们大都认同这一阶层是科举制下的特权阶层。处于该阶层的人往往在地方上较有威望,或者在地方救济、军事、经济、文化中起领导作用,甚至一些官职较高的官员在返乡后仍可影响地方行政事务的管理。在笔者看来,“地方精英”是西方话语下形成的术语,而并非出自中国乡土。②王先明:《士绅构成要素的变异与乡村权利——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西北、晋中为例》,《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2期。因此,本文仍坚持使用明清时代文献中普遍使用的“士绅”一词。
值得注意的是,士绅作为地方社会的领导,虽然在明清时期已经成为王朝意识形态的重要元素,但作为一个阶层要立得住脚,“社会本身必须被士绅化”③科大卫:《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卜永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0页。,意即士绅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要实现其独特的领导权力,是需要有广大乡民的认可作为土壤和根基的。因此,“这样一个由士绅领导的社会,是先创造于意识形态之中,而后变成现实的”④科大卫:《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卜永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0页。。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创建之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范畴内,礼仪的推行、教化与对原有风俗的遵从或改革就显得非常重要。以往学者讨论的视角之一,便是士绅阶层在国家与地方礼俗互动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并且有些学者侧重地方社会的具体研究,了解士绅阶层在“地方”在归入国家“礼教”秩序进程中的作为;注意国家推行教化时,地方士绅的反应以及参与的过程。⑤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科大卫:《国家与礼仪:宋至清中叶珠江三角洲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中山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赵世瑜:《二元的晋祠:礼与俗的分合》,《民俗研究》2015年第4期;陈彩云:《明清时期江南士绅的禁奢思想及实践》,《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杨念群:《影响18世纪礼仪转折的若干因素》,《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邓智华:《士绅教化与地域社会变革——基于庞尚鹏〈庞氏贾村〉的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1期;邓智华:《明代广东士绅的地方教化运动》,《青海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这一过程的实质,正如杨念群所言,“实际上,民间礼仪组织是在和官府分享教化权,也就是与国家分享教化权”*杨念群:《影响18世纪礼仪转折的若干因素》,《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那么,在民间与官府对于教化权的分享中,二者之间的切割边界在哪里呢?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需要我们将礼制秩序向基层社会渗透的路径作更细化的讨论。因此,本文拟通过清代康熙年间山东益都县颜神镇士绅赵执信的例子,来探讨在“礼”向“俗”渗透的过程中,地方官推行的乡约教化与作为士绅的赵执信进行礼俗权衡二者之间的微妙关系,以期理解官、民教化之间的权力边界问题。
本文所关注的核心地域,即位于鲁中益都县西南部的孝妇乡颜神镇。该镇对于鲁中山区而言非常重要:一是它恰好处在东西、南北两条大道上的交汇处,尤其当鲁中东西大道改走章丘、王村、周村、淄川一线,以南又开设新泰县羊流店驿站后,来自东北方向寿光县、潍县等地的货物都要经过这里,或运往西北、西南平原,再北上去往京师;或穿过莱芜县、新泰县运往南方诸省;另一方面,它地处益都县与莱芜县交界的群山之中,是兵戈相交、走私鱼盐之利的便捷之途。正因为这样的地理环境,官府一直将其视为难治之区。生活在这里的村民,是一群名副其实的山里人。康熙初年,身为本地人的大学士孙廷铨,亦自称“山中之人”。清初,颜神镇作为手工业生产和产品集散地的中心位置逐渐凸显,镇中从事琉璃、陶瓷业的匠人们的后代中,也出了许多朝廷大官或对文坛有所影响的文人。因此,原本的匠人家庭摇身一变,成为士大夫家庭。这些在朝中做官的士大夫返乡后,以士绅的身份开始积极致力于地方建设。在参与地方市场管理、颜神镇设县等事务之外,“正礼易俗”的礼俗讨论与改革,同样被他们视为标榜身份与建立权威的重点。
一、康熙年间地方官推行乡约
清代康熙年间,山东中部山区的州县官员开始积极推行乡约,以实现对地方的教化。因此,这一时期在公共场所讲解乡约以及在地方史志中讨论“风俗”的做法颇为流行。顺治九年(1652),清廷颁布“六谕”;康熙九年(1670)又颁布“上谕十六条”。朝廷希望通过乡约教化城市、乡里的做法在地方州县有所体现。就在同年十一月初一,时任莱芜县知县的叶方恒传集绅袍、士民、乡约人等齐聚明伦堂创举乡约,并且规定在之后的每月朔、望日,要在县西关外讲院,或分诣乡村向士民宣述讲语,以达到教化风俗的目的。成书于康熙十三年的《新修莱芜县志》收录了叶方恒当时教化乡民的讲语八则。这八则讲语均用白话写成,通俗易懂,主要是对“六谕”和“上谕十六条”的解读。其中“讲语六”的部分内容论述了上谕和教化风俗的关系,其用语颇为有趣:
本县遵奉上谕,专为人心风俗,苦口劝你们学好。向来说人心不好便要坏了风俗,不知道得风俗坏了的时节更无好人,看样愈趋愈下,便是风俗又可以坏人心,辗转相因,两件毕竟分开不得。譬如山东一省,兼管着古时齐鲁邹滕,论起来,孔夫子是你山东人,孟夫子是你山东人,颜子、曾子也都是你山东人,这几位至圣大贤岂不是天地间一团至灵至秀祥瑞之气结聚生成,所以人杰地灵,就相传邹鲁是文献名邦,为何传到后来便恶人也?有强盗也?
不要说山东本是个好地方,你们本来是个良民。即如本县当初先做贵阳府推官,那贵州管下的土司山洞都是苗蛮,不知王化,杀人造蛊,抗粮行劫,无所不至。本县奉了县委亲去劝化……本县在任绕八个月,那些向化的苗蛮粮也来纳了,贼也不做了,地方也相安,况且你们原知礼义,就使有几个匪类,何难?*(清)叶方恒:《新修莱芜县志》,莱芜市史志办公室藏资料,未出版,第18a-20a页。
这位叶知县通篇在讲人心与风俗的关系,不好的人心可以导致坏风俗的产生,而风俗坏到了一定程度也会影响人心,二者是不可分开的。但说到人心,不免多少有些缥缈。所以接下来他列举了出自山东的孔子、孟子、颜子、曾子等圣贤,意在说明县民本是有礼仪传统的良民。为了进一步证明这点,他将齐鲁之民与贵州土司管辖的“苗蛮”作对比,认为“苗蛮”都可以向化,更何况原本就懂礼义的莱芜县民众。
与莱芜县的情况相似,蒙阴县的地方官也在同一时期积地推行乡约。成书于康熙二十八年的《莅蒙平政录》就收录了知县陈朝军颁布的乡约条例——《为力行讲约以广教化事》。该告示主要是针对“见地方离城颇远,官府耳目未周,安于怠逸,不行讲解”的情况而颁布的,并规定自此以后,乡约、社保人等要在每月逢三之日前往集场,传集乡民逐条细讲,而且知县还会不定期到各集场巡视讲解情况。*(清)陈朝君:《莅蒙平政录》,黄山书社,1997年,第696页。可见,乡村集市是当时宣讲上谕的主要场所。康熙五十二年,长山县知县孙衍颁布《力行教化约》,与士民约定每逢朔望日,先在明伦堂讲读,以训饬士子,然后再到较远的村镇居民聚集之地宣解,目的是使条约家喻户晓。*(清)倪企望:《长山县志》,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492页。
除地方官积极实行讲约教化外,各州县康熙至乾隆年间的方志也有大量关于地方风俗的讨论。比如康熙《章丘县志》“风土”一节就将土俗民风视作“皆街谈巷说,鄙俚不雅”,编纂者还引用齐王问画工的典故,将教化此类土俗与难画的犬马之类相比,言外之意是教化街里的土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又如乾隆《新泰县志》的编纂者认为,新泰县属鲁地,其俗崇尚节俭、信义、有型仁讲让之风。但近来风气“渐趋浮薄”,间有游民不务正业,以及出现不畏王法、逃交租赋的人。地方官认为教化风气,主要还是靠长吏与绅士分任其责。此外,乾隆《博山县志》亦有关于风俗教化的论述,其编纂者的观点基本与新泰知县一致,认为风俗盛衰关乎教化,而其关键在于通上连下的大夫师长和士君子:“大夫师长渐摩于上,士君子砥砺于下,则向化者蒸然丕变而不知矣。”*(清)富申、田士麟:《博山县志》,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40页。在这里,士大夫阶层显然已被分为大夫师长和士君子两类。笔者认为,大夫师长应为在朝中出任过较高官职的官员,而士君子则主要指乡间那些有功名但并未出仕的读书人。
在朝廷、地方官有意识地推行乡约教化的背景下,自康熙年间开始,颜神镇乡宦孙廷铨和赵执信先后对本乡的礼俗展开了讨论。孙廷铨,字枚先,明崇祯十三年(1640)中进士,时年27岁,授直隶大名府魏县知县,调抚宁改监纪推官;后经历明清易代,清朝定鼎再入仕;顺治一朝从天津推官开始,一路担任吏部主事、户部侍郎、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少保等职;康熙二年拜秘书院大学士;次年,以父母年老解职归养,遂于颜神镇写作了《颜山杂记》《南征纪略》《沚亭文集》等书稿。*(清)孙以宁:《重修颜山孫氏族譜序》,《颜山孙氏族譜》,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博山图书馆藏资料,未出版,1931年,第1a页。其中,《颜山杂记》一书有“风土岁时”一节,为我们提供了清初颜神镇风俗方面的材料。孙廷铨认为“观风问俗”虽是细微之事,却亦关乎“得失之林,治乱之迹”,属治理国家的一部分。而要通晓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主要是去看此地的岁时节日,即“伏腊”。他认为节日是谁都无法违背的,并在文中列举了一年中的节日习俗以及颜神镇的婚丧礼俗。
赵执信的《礼俗权衡》一书,比孙廷铨《颜山杂记》的成书时间晚了几十年,但其中关于礼俗的讨论却比孙书详尽。该书分“序”和上下两卷,共八篇。接下来,本文将对赵执信撰写该书的背景及其对礼俗的相关论述进行详细的分析。
二、赵执信与《礼俗权衡》
赵执信(1662-1744),益都县颜神镇人。生于康熙元年,卒于乾隆九年,享年83岁。其祖父赵振业为天启年间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叔父赵进美为崇祯年间进士,官至福建按察使。赵执信本人于康熙十八年中进士,当时他只有十八岁,官至右春坊右赞善翰林院检讨。康熙二十八年,在佟皇后病逝的服丧期间,赵执信因被邀请去看洪升排演的《长生殿》戏剧而遭到黄六鸿的弹劾,随后被削职除名,从此终身不仕。离开京城后,赵执信开始了或家居或南游的余生。赵氏在外的游历,主要集中在康熙三十五年至雍正二年(1724)之间。他曾四次经过淮安、苏州、扬州一带。其中,康熙三十五年,他还到达杭州、南昌、广州、潮州等地。康熙四十四年秋南游,经扬州、苏州、常熟等地时,他在苏州与江浙文人王南村、朱彝尊会面,岁暮返里。康熙四十八年,赵执信在乡撰写《礼俗权衡》《谈龙录》两书,又于年底前往扬州。康熙五十九年冬,他携家眷经蒙阴、沂水、淮安、扬州等地至苏州。直到雍正二年冬,他才返回家乡,并于次年在颜神镇修别墅“因园”一处,自此至去世再未离家。在离京的日子里,他不断撰写不同类型的诗歌和文章,其中文章一类不仅包括常见的策、序、跋、碑记、传、墓志铭、行状、祭文、杂文等等,还有专门就诗歌理论进行论述的《谈龙录》《声调谱》,与当时的文坛之士展开文学探讨。除此之外,他还专门就一乡之礼俗写作《礼俗权衡》。该书的成书时间是康熙四十八年,时逢他第二次从江浙一带还乡期间。
除撰写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礼俗方面的书籍之外,他还多次参与地方建设。康熙四十八年,他与堂弟赵执璲承办颜神镇义集,买断九个行业的税收。雍正十二年,他又作为“地方乡老”的身份参与雍正年间的颜神镇设县一事,他写的《分境议》被时任河东总督的王士俊作为设县的参考依据。赵氏在嘉庆年间编修的《山东盐法志》中还被记载为“商藉”,也就是说他或者他的祖上有从事与盐有关的生意。所以赵执信本人具有多重的身份,他既是考中科举后入京做官的京官,又是在文坛有一定地位的文人,同时作为益都县颜神镇人,他还以地方士绅的角色参与诸多地方事务。
赵执信为何要在康熙四十八年写《礼俗权衡》呢?他曾在书中道出过原委,即希望通过自己家族对“礼”的遵循而影响一乡之俗,起到正礼易俗的作用。他称颜神镇属齐地,山陬僻陋,山区的人读书服礼,并没有浸染宋、元以前的礼仪。自幼在当地风俗环境中长大的赵氏,不能知其是非。中年以来,读的经传多了,游历的南、北地方也多了,所谓见多识广,此时他开始发现“乡之俗殊有不可解者”*(清)赵执信:《赵执信全集》,赵蔚芝、刘津鑫校点,赵执信纪念馆,2010年,第385页。。尤其是在经过多场家门期功之丧后,他认为乡间丧葬一礼,“弥为淆乱”。在其父的支持下,开始对族、称谓、婚、丧、祭等礼仪进行讨论。他论礼俗的标准,主要是根据自身“见闻所及”,而不敢通过杂征妄引来推测礼义的本来之意,再来判定乡俗是否可取。那些不怎么违背礼义的行为,或是不被人熟知的礼仪,则不属于他要论述的内容。
赵执信对自己提出的礼仪规范践行的范围也进行了说明,即为一族一门之规。他认为虽然想要与积习已久的人谈礼似乎是一件格格不入的事,但《大学》《礼记》中有“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闺门之内有礼,故三族和”等观点,说明即使无法要求别人行礼,但起码可以用礼仪来规范一个支系的族人。用其原话来说,即“吾虽不敢以之绳人,独不可以律己乎?虽不能遽施之族党,独不可姑行之门内乎?”*(清)赵执信:《赵执信全集》,赵蔚芝、刘津鑫校点,赵执信纪念馆,2010年,第385页。所以当有访客在见到此书后问他“是可为一乡之书”时,他的回答是:“是大人之意,为一门之书已矣。抑乡邻之君子,有欲因俗而行礼者,或有同好焉。”*(清)赵执信:《赵执信全集》,赵蔚芝、刘津鑫校点,赵执信纪念馆,2010年,第385页。虽然他强调此为一门之书,但当有人问起可否是一乡之书时,他还是委婉地表示希望如此,如有同好者,便可实行。此处表达了作为士大夫的赵执信想要将《礼俗权衡》作为一乡之礼仪规范的愿望。
该书正文分上下两卷。卷上包括“辨族”“称名”“仪节”“家箴”四篇;卷下有“服制”“居丧”“吊祭”“殡葬”四篇。若将此八篇稍作总结便可发现,赵执信对“礼俗”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族”的含义以及族内条规的讨论;二是着重讨论颜神镇及周边乡村的丧葬礼仪,并且对他认为的“陋俗”进行改革。
三、辨族义、定家箴
《礼俗权衡》上卷四篇主要围绕“族”展开,分别讨论了何为族?族内称谓的使用、交往仪节以及拜祭礼仪。首篇即“辨族”。赵执信认为“族”是“人道之相与系维,礼之所托始者”,族是“礼”的根本载体。*(清)赵执信:《赵执信全集》,赵蔚芝、刘津鑫校点,赵执信纪念馆,2010年,第386页。他的理论来源主要是《礼记》。在他看来,“族”主要指由父族、母族和妻族形成的“九族”范围,并以同姓、异姓的标准来判定九族中亲属关系的远近。他理解的九族与汉代孔、郑大儒在注经中提到的九族不同,大儒将上至高祖下及四世孙视为九族。但他指出以实际寿限来算,九代人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所以这种说法是“断断不可通者”*(清)赵执信:《赵执信全集》,赵蔚芝、刘津鑫校点,赵执信纪念馆,2010年,第386页。。而他比较赞同的观点是“三党之说”,其中父族有四种亲属关系,母族有三种,妻族有二种,这样由父、母、妻所形成的族党群体,称为“九族”。在这九族中,又以父、母及妻同姓的人最为亲近,此三族最为重要。而其余六族虽也有亲缘关系,但因为是异姓而关系稍远。这种亲属关系包括:父亲的姊妹之夫及子、自己的姊妹之夫及子、自己的女儿之夫及子,此为来自父亲方面的三族外姓;母亲的母族(外祖母的娘家)、母亲的姊妹及子,此为来自母亲方面的二族外姓;妻子的母族(妻子母亲的娘家),此为来自妻子方面的一族外姓。共六族外姓。在他看来,三族的关系最近,六族关系较远,必须遵循“先三而后六,异姓不得加,同姓不可易”的原则*(清)赵执信:《赵执信全集》,赵蔚芝、刘津鑫校点,赵执信纪念馆,2010年,第387页。。
除辨析九族外,他还认为联宗不过是建立交情的一种手段,拘泥太多,也只是因为共同追溯一个宗祖,而互相称为兄弟。但这种交情,在主持联宗的这一辈还尚可维系,到其儿子那一代就停止了。所以联宗并不像师生、同年这样的情谊自然亲切。其实赵执信在此处是意有所指,他之所以不看好联宗,也是因为颜神镇赵氏一族在明代进行联宗后,至清初族内因先祠和田产而产生过不小的争端。*赵氏一族在清初争夺田产一事,涉及明清两代,情节比较复杂,笔者将另文阐述。
随后,赵执信对族内称谓、出行、宴席等仪节及家箴进行讨论。称谓指九族内各亲属关系之间相互称呼的方式,他认为北方言多质,南方言多婉。其中本乡俗最陋者是称伯叔母、从伯叔母之兄弟皆曰“舅”,被称呼的人也以舅自安。在他看来,这是对母亲的大不敬。至于出行及宴席中要遵守的礼节,主要是按照长幼尊卑依次行拜礼。“家箴”一节阐述了作者对同姓族内规矩和礼仪的理解,并且将这些规矩定为一门之言,“贤者以为规,不肖者以为罪,听之而已”。赵执信认为,赵氏一族家世以宽厚著称,但今日已经变坏。这是为什么呢?他指出:“恣睢始于一二人,而礼度失之千万里。”*(清)赵执信:《赵执信全集》,赵蔚芝、刘津鑫校点,赵执信纪念馆,2010年,第390页。因为族内一二人挑起争端,使得礼度全失。在他看来,遵从孝道、父前四拜、兄前再拜是符合族内交往礼仪的。对生者长辈或同辈的礼节,根据亲疏远近而遵行不同的叩首仪式。而于已经亡故之祖先,则主要遵循另一套祭拜规则,即先祠和坟墓祭祀。他称祭祀亡故祖先是遵孝道的主要表现,正所谓“夫事亡如存,孝道也”,两种礼仪也是“二者相衡,是非了然矣”*(清)赵执信:《赵执信全集》,赵蔚芝、刘津鑫校点,赵执信纪念馆,2010年,第391页。。先祠的祭拜日期有春秋二祭、元旦,及己之生日和每月的朔、望日。坟墓的祭拜在忌日、寒食、十月朔日。显然,在他的观念中,判断是否行孝道的标准,还是要看人们如何对待亡故的祖先。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在丧葬礼仪方面,因此在接下来的一卷四篇文章中,他着重对颜神镇及其周边乡村中流行的丧礼进行了辨析。
四、复古礼仪、革旧丧俗
赵执信在《礼俗权衡》下卷中指出了当地丧葬礼中很多不遵循古礼的“陋俗”,并将《礼记》作为礼仪规范加以矫正。其中最令他诟病的是乡间流行的一些居丧和殡丧风俗。他在“居丧”一节开篇提到:“吾乡之俗,于斯时也,极可笑诧。家大人力矫之,犹未能尽变,故详列而深辨之于篇。”*(清)赵执信:《赵执信全集》,赵蔚芝、刘津鑫校点,赵执信纪念馆,2010年,第394页。在他看来,有哪些不符合礼仪的“恶俗”呢?笔者总结之后发现,他在“居丧”中主要列出四项建议革除的恶俗:首当其冲“至恶最陋之俗”是舍劳。所谓舍劳,即民间所讲的“报庙”和“送盘缠”。“报庙”指当家中有人去世后,家人要持纸钱和浆水到城隍庙或土谷祠中泼浆水、撒纸钱,然后再群哭而归。城居者拜城隍庙,村居者则拜土谷祠,也就是民间常说的土地庙。这样的“报庙”仪式当天要做三次。赵执信认为民间称为“浆水”的东西,是供亡者饮用的水。报庙的寓意是表明死者已经在阴间登记。他称这种恶俗大不可解,不符合古礼。“送盘缠”则在第二天夜晚进行,其仪式过程是:“夜半出,去家以远为期,族党奔赴,里巷杂沓,焚刍灵,喧鼓吹,谓之送盘缠。风雨无阻,至第三日未晓而返,返之夕而殓。”*(清)赵执信:《赵执信全集》,赵蔚芝、刘津鑫校点,赵执信纪念馆,2010年,第395页。意思是在第二天夜晚去离家很远的地方,由族党奔丧,里巷人员众多杂乱,焚烧刍灵,吹奏鼓乐。赵执信及其父已经对这样的习俗进行了改革,即夜晚出去奔丧的族党也不会再去很远的地方,而且绝不允许妇女出门。到赵氏中年丧妻时,他承父亲之命,直接把丧礼中报庙和送盘缠两项仪式革除。不仅赵执信一家将此习俗革除,当时士人之家亦无此习俗。
自“报庙”“送盘缠”至入殓的时间为三天,这正是赵执信提议要改变的第二点。在颜神镇一带均为三日而殓,但是在夏日时节,高温炎热,又怕雷雨天气和苍蝇蚊虫等,因此他认为三天之后再将尸体入棺实则不便,不如缩短入殓时间,早殓为安。三是居丧期间死者所着衣物的材质,惟用绢绵,戒用绸缎。乡人因避讳谐音“绸”同“仇”、“缎”同“断”,反之绢绵有绵绵不断之吉意。赵执信认为这种做法实在可笑:“真是愚骏稚子语,而世家皆守之。夫绢与绸缎,皆出于蚕丝机杼,而顾受命于音。”*(清)赵执信:《赵执信全集》,赵蔚芝、刘津鑫校点,赵执信纪念馆,2010年,第394页。虽盛夏却依旧给死者穿戴厚重的棉衣,加速了亡者的腐烂。四是他强调在居丧期间做佛事必须延请名僧,而不能随便请一些“不习经咒,惟以弹丝吹竹为事”的市井僧徒,甚至更有模仿技戏优伶表演,这些在他看来都是严重违背礼义的做法。他称这种恶状“不可殚书,恐污吾笔耳”*(清)赵执信:《赵执信全集》,赵蔚芝、刘津鑫校点,赵执信纪念馆,2010年,第394-395页。。以上为居丧礼仪中需要改革的内容。
关于“殡丧”礼仪,他认为最有必要革除的旧习是在堂屋外的庭院中搭建丧棚。在出殡时,为停放棺材、接待前来吊祭的宾客以及做佛事的僧徒等,故要搭建棚子。颜神镇一带的风俗是建三种丧棚:第一种建于门前,称“门彩”;第二种是建于墓地前的小棚,供宾客饮食憩息;第三种则是搭建在家户内庭院中的棚子,称“堂祭之棚”。为搭建丧棚,要花费重金:“祭侈者费逾千金,寻常亦以百计”,而且搭建时的劳役由亲族分而任之。*(清)赵执信:《赵执信全集》,赵蔚芝、刘津鑫校点,赵执信纪念馆,2010年,第398页。可见,搭建丧棚要出不少的财力和人力。关于丧棚一事,地方士绅也进行过讨论。孙廷铨在《颜山杂记》中指出大家治丧邀人作棚场的做法是“太侈不可久也”。赵执信在讨论丧棚一俗时认为门彩和建于墓地的小棚都无需革去,但有必要删除在庭院中的堂祭一棚。建于庭院中的丧棚的做法不仅不符合礼制,而且还会带来“假之亲友,阴相煽助,致其相竞以胜,遂使同室分颜,姻娅成隙”等弊端,无益有损,应当改变。*(清)赵执信:《赵执信全集》,赵蔚芝、刘津鑫校点,赵执信纪念馆,2010年,第398页。
除强调需要重点革除的丧葬习俗外,赵执信还在文中对吊客前来吊祭的日期进行了规定,拟定吊规:“于一七、二七受本地人吊,三七受百里以内吊,四、五七受远方吊。其远而早至者重拜之;近而后至者,或以疾,或以远归及有获己,辞于主人,而后主人受之。”*(清)赵执信:《赵执信全集》,赵蔚芝、刘津鑫校点,赵执信纪念馆,2010年,第397页。而对于本来就比较合理的习俗,他则持遵守的态度。比如对待亡者下葬后的祭祀,他指出葬后三日上坟,忌日、寒食、十月朔日祭墓的习俗,“即礼也”。由此可见赵执信对待礼、俗的态度,对于以往符合“礼”的习俗,不在他改革的范围之内。
五、结语
作为乡绅的赵执信、孙廷铨等人,期望通过自身对礼俗的见解和改革,来影响乡里之人,也正是赵在《礼俗权衡》序言中提到的“有欲因俗而行礼者,或有同好焉”*(清)赵执信:《赵执信全集》,赵蔚芝、刘津鑫校点,赵执信纪念馆,2010年,第385页。。“礼”与“俗”本身就不是互相对立的两面,作为乡宦的士大夫一方面是掌握礼仪典籍和王朝推行的礼制规章,另一方面也熟知家乡的风俗,因此他们希望通过告诉乡间里老哪些是符合礼仪规范的风俗,哪些是“恶俗陋俗”,来获得在一乡之中绝对的文化权利。也就是说,在乡村社会中,他们是掌握礼仪话语的核心人物。与此同时,另一股力量也在对同一区域进行着礼仪教化,即来自地方官推行的乡约政策。两者基本在同一时期展开对乡村、市镇中人们礼仪的规范。若我们仔细体会前文中的论述便可发现,二者作为两股教化的力量,实则存在着微妙的边界,或者称之为距离。笔者认为,这种微妙的边界主要表现在受众、内容和地理因素三个方面。
第一,“一乡之约”与“一门之书”的边界,即受众主体有所差异。在清廷颁布“六谕”“上谕十六条”的背景下,地方官依循基层社会行政管理的架构进行乡约宣讲。县官面向的对象是在他所管辖范围内生活的一县士民。在这之中,又以士绅、乡约、社保人等为主要接受对象,然后再由这些里社中有一定管理权利的人向离城稍远的村镇一级的地方扩散、宣讲。知县往往在县城某处专门供宣讲的建筑中实施教化,比如莱芜县和长山县的明伦堂。乡约、社保等则再到下一级的乡村集市中宣讲。所以官方推行乡约的层级结构是“县——士绅、乡约、社保(明伦堂)——普通乡民(村镇集场)”。在从知县到普通乡民的中间一层中,由于士绅身份特殊,又使礼俗教化产生了新的形式。士绅往往会通过“族”组织同姓之人,以这种地方组织来进行礼俗的教化。比如赵执信在《礼俗权衡》中指明其影响范围只是“一门之书”,只对本族本支内的族人进行约束。虽然他在序言中也提到了有望成为“一乡之书”的愿望,但对于这一点他并不强迫,而是希望乡里中有“同好”可以一起实践。然而我们从他对丧礼中“报庙”一俗的革除叙述中看到有“近岁士人家无之矣”一句,表明革去“报庙”习俗已在同乡的士人之家得到践行,这就超出了仅为“一门之书”的界限,成为了同一阶层中的礼仪标准。可见,士绅进行礼俗教化的途径往往是“同族——同一士绅阶层(师生/同年等)”。
第二,教化内容的边界,即他们进行礼俗宣讲或改革的内容各有侧重。知县遵循的理论基础来自皇帝颁布的“圣谕”,带有浓厚的教化民众做“良民”的政治动机。以康熙帝颁布的“上谕十六条”为例,他在条约中着重强调敦孝弟、笃宗族、和乡党、重农桑、尚节俭、隆学校、黜异端、讲法律、明礼让、务本业、训子弟、息诬告、诫匿逃、完钱粮、联保甲、解仇忿等,教化范围较广。当然士绅也有将官府颁布的乡约纳入族谱,作为一族族约的行为。*常建华:《明代徽州的宗族乡约化》,《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常建华:《清代宗族“保甲乡约化”的开端——雍正朝族正制出现过程新考》,《河北学刊》2008年第6期。但我们从赵执信的例子看到,士绅对于礼俗的讨论和改革,也可以奉礼仪经典为依据,从乡村社会的具体风俗入手,以族人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的具体婚、丧、祭等仪式细节为出发点。赵氏在对礼、俗的辨析中,根据《礼记》中仪节为标准,对乡里之中类似“报庙”“扎丧棚”等习俗采取革除手段。然而这些日常生活中的仪式细节,似乎并不在地方官特别关心的范围之内。
第三,国家礼仪教化权利与士绅礼仪教化权利二者之间孰大孰小,很多时候受到地理因素的影响。在赵执信的例子中,因颜神镇距益都县有二百余里,可谓处在距县较远的偏僻山区,甚至有很多镇民或周边村庄的村民不识城市、终身未到县城。虽然它是鲁中山区的一个手工业集散地,但益都县县城的人视颜神镇如庄或屯,似乎县中之人已对颜神镇产生了某种地域上的偏见。*(清)富申、田士麟:《博山县志》,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140-141页。这种距离县城较远的地方,正是官府乡约不易到达的地方。而在这种区域内,当地的士绅便成为进行礼仪规范和教化的主要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士绅掌握的礼俗教化权利要大于县官。所以,在国家和士绅对地方社会进行礼俗教化的过程中,他们所分享的教化权利以及这种权利的边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并非有非常明确的界限,两者往往有所重叠,但彼此又存在着微妙的距离。
[责任编辑龙圣]
作者简介:任雅萱,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香港沙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