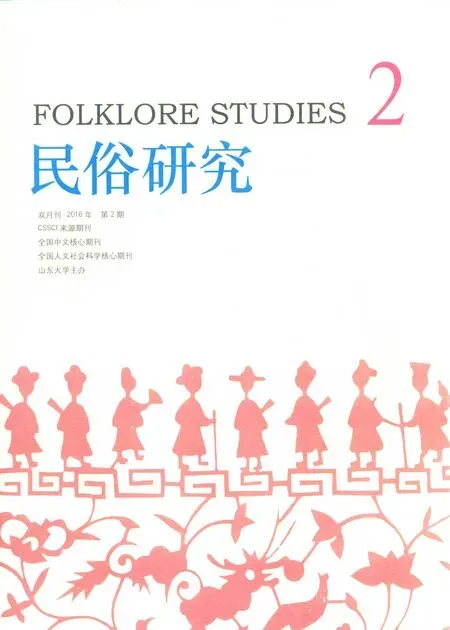日本“山姥”传说的现代文学解构
肖 霞
日本“山姥”传说的现代文学解构
肖霞
摘要:“山姥”是日本流传较广的一个民间传说,但在日本现代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山姥”已不再是传说中“栖息在山中的老女”形象,而是对具有某些山姥特质的女性解构之后而形成的崭新的富于理性思考的女性人物形象。现代社会中的“山姥”,大都是遭遇人间不公,饱受生活磨难的女性。她们是现代社会既有制度和世俗凡尘的受害者,其最终命运往往是被世人当作禳灾辟邪的牺牲者而被供奉于人间道德的“审判台”上,从而成为夫权专制社会罪孽的救赎者。
关键词:日本;山姥传说;女性文学;解构
“天狗”与“山姥”是日本妖怪的代表,作为对山的怪异附加流传至今。一般来说,前者代表男性,是男性社会的象征;后者代表母性,是女性社会的象征。二者虽然性格不同,但在具有多义性这一点上其本质是一样的。正是传说中的“山姥”具有的这种多义性,才使日本现代女性作家创作了很多相关“山姥”的文学作品,从不同的维度诠释了山姥原型——女性(母性)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样式。水田宗子指出:“事实上,神话与民间传说中的山姥形象是多种多样的。日本各地不同的传说故事、古代传承以及民间传说中,山姥以多种变奏的形式被言说,也可以说与《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伊邪那美命、木花之佐久夜姫等具有类似性,也是与神话密切相关的古代传说人物。近年来,主要以民俗学家为中心,对其社会起源、故事特质以及传说类型与分布等展开了研究。山姥以‘栖息在山中的老女’为关键词,与鬼、山神、地母神、山民、歌女、漂泊民、山中强盗等有某些共同之处,是一般人感到恐惧而又亲切的故事角色,在日本人的想象力中占有一定空间。由于其形式、意义的多样性及暧昧性,往往在文学文本中作为不同的人物形象原型出现,并逐渐固定下来。”①[日]水田宗子、北田幸恵編:《山姥たちの物語―女性の原型と語りなおし》,学藝書林,2002年,第8-9页。
一、“山姥”传说的建构
“山姥”传说在日本由来已久,故事情节因地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山姥”也被称为鬼婆、鬼女,是指住在深山老林中的女性老妖怪。一般来说,日本的妖怪都住在深山老林中,并且有吃人的恶习。住在山中的“山姥”往往会为在山林里迷路的行人提供食宿,晚上则一反常态,凶相毕露地将人吃掉,犹如西方格林童话中描写的魔女。后来,这一传说与某些地区因饥饿而减少人口盛行的“姥捨”习俗相结合,也被看作是“姥捨”传承的副产品。
在日本各地,山姥有截然不同的两种形象。一是漂泊在山中的流浪者,或是将伺候山神的巫女妖怪化之后的产物。例如,在北九州,至今还流传着“山姥的洗濯日”一说,年末的13日至20日肯定下雨,因此有不洗衣服的说法。还有的是固定某一天,说是不用水,或是不洗衣服。有的地方与山岳信仰有关,说是嫁给山人或山神的女性,隐藏在山中后来便成了 “山姥”。因此,便有了女性因生产而进山的习俗。二是说村落祭祀时选拔出来的女性隐居山中,久而久之就成了“山姥”。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在《妖怪谈义》(山姥奇闻)中有如下描述:“山姥、山姫传说流行于以信越交界的群山为中心的山国村庄。从关东到奥羽一带,往往将山母看作是近乎于性情古怪的恶鬼,现在则演化成单纯童话中的妖怪。但是,也有一种传说,最初的山姥行走于大山和乡里,帮助樵夫扛抬重担,给织布的村妇帮忙。与北欧的妖精一样,并非单纯是空想的产物。……阿波半田深处的中岛村,山上有一块大石头,名曰山姥石。山姥居住在这一带,时常带着村里的孩子们来到岩石上点火让他们烤火,据说以前有人看到过。在其他地方的山村,也有不少地方将冬天特别暖和的那一年戏说成‘今年山姥在抚养孩子’。”*[日]柳田国男:《妖怪談義》,《柳田国男全集20》,筑摩書房,1999年,第336页。
柳田国男认为,“山姥”传说发生的背景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大和民族在扩展势力的过程中,原来生活在当地的土著民避而潜伏到幽闲之地,长期以来便生儿育女分住在各地,这些都不足为怪。问题在于那些生活在低地的人为何将他们看作为神而加以敬畏呢?二是在山神信仰中以前明显含有对狼的恐惧。狼以群动,其威力或是其敏锐、狂猛足以引起人们的恐惧,加以祭祀可免于被害,于是便给以“大口真神”之称谓,进而对其成长做出各种想象。因此,在各地产生了不同的风俗。还有很多传说,例如狼的首领借老太身姿往来于人间生活,山姥抚养孩子等。三是进入大山的女人。隐藏到山中的女人多是狂女,即虽说是难以承受山力威压的山村女子,但她们往往坚信会被山神所娶乐而进山,也有的传说是说女性因产后精神异常而进入山中。*[日]柳田国男:《妖怪談義》,《柳田国男全集20》,筑摩書房,1999年,第336-337页。另一位民俗学家宫田登指出:“被称为女妖怪的代表性存在的是山姥,这个山姥被说成是居住在深山中的妖怪,时常袭击人。是一种丑陋难看的老太婆形象,有出现在山村捉人而食的令人可怕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山姥在临近生产时来到山村,请求村人帮忙。若村民诚恳帮忙的话,作为谢礼会放下很多财宝,有其亲切的一面。”*[日]宮田登:《妖怪と伝説》(日本を語る13),吉川弘文館,2007年,第62页。也就是说,日本民间传说中多涉及山姥,山姥往往被当作女妖怪来描写。山姥形象的基础有作为女神的山神形象,被标记为山母、山婆,因具有山中老太婆所具有的咒力,从而成为人们信仰的对象。其根源也许在于山中老太婆在祭祀山神的古代,巫女形象是其原型,或可将其看作山神本身。因为在日本,山神原来被当作女神信仰,她不仅要守护山民,还要守护庄稼作物。特别具有生殖功能,既要给猎人带来猎物,又要保证农民的作物丰收。孩子是丰产的象征,从而有山姥生产的话题。
日本的“山姥”原型,可追溯到奈良时代,后经世人的解读与演绎,在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中加以展示,各自形成不同而又明确的人物形象。例如,中世的能与狂言,江户时代的净琉璃与歌舞伎等,都有类似而又不同的“山姥”登场;她们在舞台上以转世而来的身姿向世人诉说苦难的渊源与悲剧的事实,给人带来人生的哲学思考。20世纪以后,被称为柳田民俗学原点的《远野物语》(1910)有5处关于“山姥”的记载,并将“山姥”形象定格在远离世人的深山老林之中。例如,在第三部分中写道:“群山深处住着山人。栃内村和野的佐佐木嘉兵卫现年七十有余。此翁年轻时狩猎进入深山,远远看到岩石上有一美女,正在梳理长长的黑发。面色很白。他以为是个无畏的男人立即开枪,那人应声倒下。跑去一看是个身材高大的女人,解开的黑发比她的身体还长。他想作为其后的证据,随将其头发剪断少许绾入怀中,不久,在回家的路上感到困乏,便到隐蔽处打起瞌睡,在其似梦非梦之际,看到一个高大的男人靠近他,将手插入其怀中并将绾起的黑发取走,他立即惊醒。此人可谓之山男。”*[日]柳田国男:《遠野物語》,角川書店,1955年,第18页。第七部分中写道:“上乡村百姓之家,有姑娘进山拾栗没有回来。家里人以为她死了,便将姑娘的枕头作为替代物举行了丧礼,这样过了二、三年。然而,村人打猎进入五叶山半山腰,在大岩石遮挡的犹如岩窟的地方与这个女的不期而遇。双方都甚为吃惊,问她怎么到这样的山里来?女的回答,进入山中被可怕的人拐走,来到这样的地方。想要逃回丝毫没有机会。问那人是什么样?说看上去与常人无异,只是身材高大,眼光骇人。孩子也生了几个,但说不像他的话就认为不是他的孩子,或是吃掉或是杀掉。……她说,现在也许就要回来了,猎人也感到可怕就回去了。”*[日]柳田国男:《遠野物語》,角川書店,1955年,第19-20页。
关于“山姥”的传说,古典作品《今昔物语集》中有如下记载。例如,第27卷第21节“猎师母鬼欲食孩子的故事”中写道:“过去,两兄弟以猎取山鹿、野猪为业。一天,为射猎山鹿,二人爬到50米外的树上藏身。时值9月下旬,四周一片黢黑。哥哥所在的树上不知是什么东西伸出手抓住了他的发髻。哥哥想,肯定是鬼要吃我才把我提起来的,就通知弟弟说,有人抓我的头发,弟弟回答说,我估摸着射箭。箭射中了,哥哥一看,有一只从手腕处被射断了的手。兄弟二人终止狩猎回家了。这时,母亲非常痛苦,兄弟俩思忖着打开门,母亲欲揍他们,说,这是你们干的吧。两人对母亲说,这是你的手吗?遂将其扔到房间里关上门。其后,母亡、下葬。”第12卷28节是“肥后国书生免于罗刹之难的故事”,其中写道:“有个书生,在回家的途中迷路进入山中。傍晚时分,发现一所房子,里面有个可怕的女人,他立即回马逃出。其女‘身高一丈,口、眼喷火,犹如闪电,张着大嘴兴奋地追来’,书生坠马落入洞中。当马被吃掉时,洞里传出驱鬼的声音。”声音正是法华经卒都婆的“妙”字。这里所说的“罗刹”就是指“山姥”,因《今昔物语集》受佛教的影响很大,所记载的故事也具有浓厚的佛教性质。可以说,当时的“山姥”只是单纯地指山神,是山中异界类的存在,还没有被赋予更多的含义。
“山姥”与人的共存,是日本故事传说的一个特性。日本人虽然知道无意识的可怕,但不想拒绝它;尽管有时想驱逐它,但又考虑到在某些地方具有共存的可能性。现代日本女性作家喜爱“山姥”的原因在于:“不能单纯理解为山姥是作为幻想的生存者所具有的对自在性的憧憬。面对将女性每个人的生殖与性欲当作私有物进行管理,并确保自己在社会、文化中优势地位的男性,山姥在被制度边缘化中迸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并以此为基础展开抵抗与反叛,她们为众多女性作家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女性原型。山姥们的抵抗方法变换自在,反映了幽默、滑稽的山姥性格。与其说从正面表现其姿态,不如说多以别样的姿态诓骗、嘲笑对方。而更为有效的方法,是利用居住在村庄里的女性必备的山姥性,将其附着到普通主妇身上而出现。”*[日]水田宗子、北田幸恵編:《山姥たちの物語―女性の原型と語りなおし》,学藝書林,2002年,第273页。在这里,“山姥性”是指女性旺盛的性欲望,其中主要指母性和生育的性,表现出大地母亲般的强大生命力。正因为如此,山姥性促使女性表现出更为多元、自在的人生价值与生存方式。
二、微笑山姥的归宿与寄托
大庭美奈子在其小说《山姥的微笑》(1976)、《浦岛草》(1977)中塑造了不同的“山姥”形象,展示了女性的性欲、生育与生命力。大庭美奈子曾在新澙就读,新澙县也是“山姥”传说的圣地。在南浦原郡的民间传说中,人们将弥彦山的鬼女称作“弥三郎婆”。能剧《山姥》的舞台就设定在新澙与富山两地的交界处。在新澙县流传的“山姥”传说中,有令人可怕的形象和温顺善良的形象两种。在大庭美奈子的成长过程中,可以说,这种富于地方性的异界传说给她带来无限的想象空间。她喜欢“山姥”的形象,并让她们在小说中多次出现,甚至直接将小说命名为《山姥》,并将其作为女性形象的代言人。
1976年,大庭美奈子发表的短篇小说《山姥的微笑》,以“山姥”命名集中描写了女性一生无法摆脱的“山姥”形象。该小说由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描写了传说中的“山姥”,她们远离人群,居住山中,白发苍苍,蓬头垢面,专食进入山中迷路的男人。在迷路的男人误入自己的小屋并与之相处的过程中,“山姥”具有读取对方心理的特异功能。男人心里想什么,她都能一一说出,恐惧至极的男人竭尽全力逃出她的家;而她则呼啸山林,拼命追赶。第二部分,描写了“山姥”的由来。作者认为,她们“虽说是山姥,但并非就是从一出生就是满脸皱纹的老太婆”,她们与普通女性一样,既有像新鲜年糕那样的肌肤和充满甜酸味的婴儿时代,也有犹如熟绢般滑润、吸引男人的少女时代。长大以后,像鹦贝一样闪光的手指插进男人肩膀的肉里;那丰满的双乳足以让恋人窒息。但是,在日本社会中,这些年轻的“山姥”形象不被人传颂,她们也不居住山中,而是托生于动物形象(譬如鹤、狐、鹭等),变成漂亮的媳妇居住在常人的村落。这些托生于动物的女性,聪明、漂亮,用心周到,一生为男人尽心尽责,但到最后无一不是以悲剧收尾,还原为瘦骨嶙峋、头发脱落的动物之躯逃到山里。不难想象,那些逃到山里的动物,就是充满辛酸和怨恨的山姥。作者认为,她们的吃人,“也是极端爱情的表现”,正是因为极端的爱情所致,才恨不得吃掉它。*[日]大庭みな子:《大庭みな子全集》(第5巻),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09年,第463页。第三部分,作者选取了一个山姥中的“山姥”作为例子,诉说了她作为女性的一生,以及一直向往成为“山姥”的内心世界。
作者回忆了她生就女人的一生经历。她从小就能读懂母亲的心理,学说母亲的话语,“在懂事的时候就已经是个山姥了”。*[日]大庭みな子:《大庭みな子全集》(第5巻),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09年,第464页。上小学的时候,因忌惮大家讨厌的面孔而开始沉默,其后决定专做让大人们高兴的事了。在经历了短暂的思春期的反抗之后,她发现了母亲的衰老与自己的成熟。于是,她恋爱、结婚,学着讨好男人,把自己变成了依附男人,“从骨子里就是无能的、柔弱的生物”。*[日]大庭みな子:《大庭みな子全集》(第5巻),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09年,第467页。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她的献媚与讨好的表现并没有换来男人的好感,她要么被看成懒汉,要么被说成缺乏纤细,是意志薄弱的女人。这是因为男人始终认为“英语中的man是指男人的同时还指人,而女人只有紧贴男人才能成为人”。*[日]大庭みな子:《大庭みな子全集》(第5巻),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09年,第468页。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她永远被置于被嘲笑的地位。为此,她感到恐怖与孤独,沉默之余,内心向往山中山姥那自由自在的生活。刚过40岁,身体有所不适,她被诊断为“更年期障碍”,其后20年这个病一直伴随着她的生活。当有一天她感到身体发凉、疼痛,同时“感到自己的身体犹如他人之物的些微的麻痹的时候,她病倒了。处于昏迷中的她得到平生最好的待遇,丈夫、女儿和儿子三人轮流抚摸母亲的脚、手腕,连排泄物的处理也不让护士做”。*[日]大庭みな子:《大庭みな子全集》(第5巻),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09年,第472页。但是,当医生说到类似的脑血栓患者靠打点滴也可维持2年时,“家中三人围着病人陷入深深的沉默之中”。往后就是儿子的离去,女儿为自己家庭的担心,丈夫的焦虑……。弥留之际的她在最后的微笑中清楚地读出了女儿的心思,进而在女儿的脸上看到了处于远方都市的嘈杂中那不见踪影的儿子的面孔,她似乎听到了儿子为了家族、为了人类延续而不得不离去的宏大理想。她62岁,“在乡里临时居住的房子里度过了她作为人的女性的一生”。现在,“她那灵魂出窍的裸体,用酒精擦洗完毕,皮肤细嫩,充满润泽,犹如蜡制的女神像。头发半是花白,流畅的腹部末端的小丘上,几根银色的芒草在随风飘动,安详闭着的眼帘与几分微笑的嘴边,露出令人不可思议的、天真无邪的、忍住哭泣而笑着的少女般的羞涩。”*[日]大庭みな子:《大庭みな子全集》(第5巻),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09年,第463页。可以说,62岁的死者作为女性美丽动人,充满魅力,是女性中的杰出代表。
最后部分,写即将离世的她看到了被山姥追赶而披头散发逃跑的人,感到“山姥”就在跟前,于是,她“突然感到暖乎乎的山姥的心脏的鼓动、复苏,她微笑了”。*[日]大庭みな子:《大庭みな子全集》(第5巻),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09年,第476页。“她有时思忖,住在山里变成吃人的山姥,与拥有山姥之心住在村里哪个幸福?现在想来二者一样。住在山里,被称为山姥;住在村里被说成是狐狸的化身,与身心健全颐养天命的平凡女性之间,其内在的东西结果相同。”*[日]大庭みな子:《大庭みな子全集》(第5巻),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09年,第477页。在男权中心的社会中,女性不论以何种方式存在都无法摆脱被抨击、嘲笑、揶揄的处境,其人生都是不幸! 大庭美奈子用“山姥”的一生,即少女时代、青春时代、中年时代、老年时代,表现日本当代女性的人生轨迹,展示了生为女人在社会上遭遇的不幸与凄惨命运。
大庭美奈子创作的长篇小说《浦岛草》,直接以植物命名,喻示了故事发生的时空性,以及它所代表的死亡主题。小说通过不同登场女性的目光,描述了一个宏大而又残酷的充满诗性的世界,展示了从广岛的毁灭到战争对人之生命的戕害,人类无限的膨胀欲望,最终导致破灭的独特视角。“浦岛草”是芋科类多年生草本植物,以本州、四国为中心,遍布于北海道、九州等地。它生长于树荫下,叶柄浑厚,长约有50厘米,是一种可分雄雌的有毒植物。晚春时节,花轴从花瓣状的花蕾中长长伸出,呈细条型倒挂,犹如传说中浦岛太郎的钓鱼绳,由此而得名。
小说通过登场人物的相遇、诉说,展示了现代人之间的内心隔阂与交流障碍,以及近似家庭的生存状况。作者将“山姥”式的女性形象与“浦岛草”的形象相互结合,将场景设置在充满战争与暴力且以男性为中心的时代,以不同年龄辈分的女性为中心,以她们的亲身经历为蓝本,集中展示人与人之间的猜疑与虚无人生。小说的舞台分别是东京、广岛和新潟,小说以23岁的菱田雪枝从美国回国开始。雪枝中学时代留学美国,大学毕业后在美国工作,时隔11年回到日本。作为新一代的代表,她带着未婚的男友来到东京的同母异父的兄弟森人家中,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5口之家。这个家庭有比自己大30多岁的哥哥森人与妻子凌子,儿子黎30岁且患有自闭症。除此之外,还有为照看黎从乡下叫来的姑娘与美国士兵之间生下的已经25岁的混血姑娘夏生,还有凌子的前夫麻布龙。5个人的户籍关系与血缘关系虽然都不同,但却以近似家庭的形式共同生活,并在战后一直持续了30年。女主人公凌子是一个关键性的存在,她的年龄与作者相仿,集中体现了作者自身的人生体验与历史记忆。在这部小说中,作者通过对登场的不同年龄的女性——凌子、雪枝、夏生、滋子的人物塑造与描写,从性差角度入手,突出了现实社会中女性与男性所缔结的关系的扭曲,女性不论是鬼女、巫女,还是魔女、山姥,都是生存于半异界的女性,作者通过她们的人生经历,揭示了女性具有的“同性厌恶”与“自我厌恶”的主题。对于广岛这一空间的设定与对原爆问题的论及,将国家间的对立与战争与个人的命运、女性的性相结合,通过女性的个人的性的苦恼,提出了生命问题与人的生存问题,揭示了生的哲学含义。正因为如此,“山姥”作为日本女性的原型,受到日本现代女作家的喜爱,水田宗子在评价大庭文学时指出:“山姥是构成大庭文学文本的中心存在,她憧憬栖息在老庄式的东方思想领域内的山姥,并建构了这个世界。大庭美奈子的山姥让我们通过女性的生与感性管窥到进入如实接受超越个体的生与死的循环境地的人们的姿态。”*[日]水田宗子、北田幸恵編:《山姥たちの物語―女性の原型と語りなおし》,学藝書林,2002年,第30页。
三、灵异山姥的复仇与生命自觉
园地文子的作品多围绕女性的性与生而展开,她将古典作品中的女性与现代女性相结合,以双重构造形式描写现代女性的欲望和情念,展示了女性在封建制度重压下的反叛与抵抗。她在塑造主人公形象时多借用妖怪、灵异附体等超常现象,以表达现代女性的幻想,带有明显的“山姥”特色。这一特色在她60岁以后创作的作品中更加明显。她在《女坂》、《妖》、《女面》等作品中,塑造了一个个“鬼女”“生灵”和“怨灵”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表达了作者对男权制度下被蹂躏的女性的控诉与呐喊。其创作特色是:用巫女的女性形象建构“其文学世界的主体”;用“深受江户后期文学影响的浓妆文体”表现了“王朝的神秘世界”。*[日]亀井秀雄·小笠原美子:《円地文子の世界》,創林社,1981年,第83页。“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其文学的独特性,那就是‘妖’与‘凄’。……潜伏在微暗的女性内部的妖气,以及其可怕性。经过园地的笔,其妖气与可怕性看上去犹如女性的毒气,往往被其感情世界所吸引。”*[日]古屋照子:《円地文子妖の文学》,沖積舎,平成8年,第9页。
小说《女面》(1958)以栂尾三重子、泰子婆媳二人为中心,围绕和歌、能面等传统艺能的学习和了解,描写了女性所受的冤屈和对好色男性的复仇,同时预示着母系对父系的胜利。这部以战前的家族制度为前提创作的小说,以性爱描写为中心,探求受压抑女性自我解放的特异性。小说由三章构成,分别以能面“灵女”“十寺发”和“深井”命名。开头部分描写了一群对“附灵考证”颇感兴趣的男女,整个氛围给人以不可思议的妖冶之感。小说通过描写他们的“灵媒实验”,将读者带入一个充满灵性的神秘世界。三重子是《清流》派歌人并主持短歌杂志,生育一对龙凤胎——秋生和春女。儿子秋生在大学时代学习国文学,后从事怪异学特别是灵魂附体的研究;女儿春女天生弱智,寄养在老家。秋生与泰子结婚不到一年,即在一次登山事故中丧生,后将春女接来同住。为了爱情,30岁左右富有教养的美女泰子选择继续留在婆家,一方面继续丈夫的王朝灵验研究,一方面为婆婆编辑的和歌杂志帮忙。与之有关的两名男性是伊吹和三瓶。伊吹已有妻室,是秋生大学时代的学长,在S大学担任国文学副教授,从事王朝文学研究。三瓶独身,是精神科医生,同时也是位民俗学爱好者。他先是调查了圣经以来中世欧洲的鬼怪附体的历史,后对日本山阴地区的狐狸附体、四国的犬神、九州的蛇神等做了若干考证。最近,又将兴趣集中在王朝文学中的怪物,即死灵与生灵对第三者的附体上。因此,他通过伊吹与三重子、泰子相识,与其他研究者一起每月一次或两月一次地聚集在名流贵妇三重子家,就怪异研究交流心得和看法。伊吹和三瓶都恋着泰子,三重子充分给予泰子自由,希望他们相互接近。泰子与三瓶交往,同时又与伊吹发生关系。当伊吹第二次进入泰子房间后,激情中他朦胧感觉到对方不是泰子而是春女。不久,春女怀孕,在生下孩子后去世。小说以其四人为中心,在现实与梦幻,昏暗、幽玄与奇怪的氛围中展开叙事,将交灵术、幽灵与瘆人的能面、六条御息所等古典道具与人物交织在一起,揭示了三重子的性格特色。同时,小说以蒙太奇的方式展示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并以象征、有趣的表现手法描写了令人可怕的女性复仇。
女主人公三重子是具有浓厚“巫女性的女性”,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伊吹看来,三重子面部白净、充满柔和的轮廓,好似一副能剧女面的面孔。泰子则说:“她就像夜间的花园,将秘密深藏心里,不停散发着混淆的气息。”*[日]円地文子:《女面》,《円地文子全集》(第6巻),新潮社,1977年,第184页。关于三重子的内心世界,作者运用能面的隐喻婉转地予以揭示。当他们一行4人来到京都药师寺家看各种面具时,先是看了“增女”“泥眼”和“深井”等,这些都属于同一系列的面具,然而,躺在病床上的赖人却要求儿子一定给他们看“灵女”面具。“灵女”是药师寺家珍藏的众多面具中的优秀之作,被指定为国宝,很少示人,但这次却指定要给三重子看。泰子看后说:“我在看那个面具的过程中,的确感到可怕!恐怕最适合看那个女面的就是母亲。……表情具敛内面的能面寂静……那确实就是过去只有日本女人才具有的面孔……我家母亲,就像那个面具一样将活跃的精神全部收敛于内而活着的最后的日本女人。我在昨天看到的入神地看着能衣裳和面具而又装作若无其事的母亲面孔的样子,至今还感到茫然,对此就更加明白了。”*[日]円地文子:《女面》,《円地文子全集》(第6巻),新潮社,1977年,第139-140页。后来泰子进一步阐述道:“就像表面平静的山中湖泊,底部水流湍急向着瀑布的方向流去一样,她具有巍然不动,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很好地向其发展的能力。即她就是那个能面的女人。”*[日]円地文子:《女面》,《円地文子全集》(第6巻),新潮社,1977年,第143页。这个具有魅力的女人内涵深刻,“心里的秘密变成花园,在无形之中散发着各种气味。与其自身的秘密所产生的魅力相比,其歌才只不过是外表的衣裳罢了。”*[日]円地文子:《女面》,《円地文子全集》(第6巻),新潮社,1977年,第144页。泰子的话语更多地向人们介绍了三重子的内面性格,即巫女性的女性。也就是说,长期从事能剧表演与研究的艺人赖人执意给她们看“灵女”的目的,加上与其一起生活的泰子的观察与感受已经一目了然,三重子就是生活在现实中的“灵女”,具有附灵的能力,同时也是当代“山姥”的典型。能剧是指“幽灵登场的演剧”,或是指“幽玄的演剧”。在这里,灵即是精灵之灵,是从肉体中解放出来的自由之灵,在能剧中包含接近神的灵,也有包含怨恨作祟的生灵、死灵,即所谓的怨灵。
可以说,园地的文学试图为家族制度重压下的女性寻找一个突破口,她借助于鬼魂作祟的风俗信仰,描写了家灵化的“山姥”形象,以此建构了一个幻觉的世界。“园地的作品世界超越‘巫女性的女性’,进而表现灵本身存在的神秘世界”。那是“‘另一境地’,是‘虚幻世界’。如果女性在此能够超越时空与死去的人对话的话,就能与过去的自己本身相遇。那不是作为回忆或回想来表现,而是通过在‘另一境地’始终以现在式加以表现,具有现实世界与虚幻世界并存的真实感。女性们将心慕的男性呼唤至此,在不同层次上发挥性爱的冲动作用。”*[日]亀井秀雄、小笠原美子:《円地文子の世界》,創林社1981年,第98页。这部小说昭示人们,在对待性、婚姻与家庭的态度上,如果说男人随意、好色,没有责任感,那么作为其对象的女人所采取的复仇,更是不择手段。小说将附灵与性爱相结合,并从巫女的历史性出发,用人的恶孽去解释,登场人物一味追求官能满足而不讲责任,这是对《源氏物语》的最好继承。从登场人物的性格来看,她们神秘而从不发半句怨言,但具有强大的破坏力。
园地文子的另一篇小说《彩雾》(1976),则进一步通过女性的巫女性展示了“生命根源”的问题。小说以自己“分身”的形式借助女主人公堤纱乃的口,使其在现实与虚构的往复之中穿梭,通过对老年与死亡的冷酷直视,展现了一个追求性欲冲动的妖艳“山姥”的内心世界。可以说,作者在自我观察的基础上小心翼翼地描写了年老的实际感受。作者一如既往地发挥她的古典特长,将古代传统文化与现代人的生活感受紧密结合,以挑战年老的形式让其肉体触动性欲的感觉,展示了人的内部深处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原始的性欲冲动。作者在以“妖艳”“物哀”为基础构建的极为高雅的美的感觉与状态的基础上,表现了现代人内心固有的浪漫追求,以及对性之元始冲动的体验。总之,从园地文子的作品来看,日本的“山姥”性,说到底是超越人为制定的性别概念的性差,对于男女两性来说,不论是哪一方,在由一方支配的社会文化空间内都不会生活得舒心;因此,作为“混沌”使者的山姥具有多样性与可解释性,对于男女双方来说,就是一个备受欢迎的存在。
四、孤独山姥的自我救赎
津岛佑子的小说《奔跑在山上的女人》(1980),以身边问题为基础描写了带着没有父亲的孩子的母亲形象,结合自古以来传说中的“山姥”,塑造了一个独自养育孩子的女性。因各种不得已的原因,在现实生活中确有很多这样的女性。作者认为,这些单身母亲“犹如夏天的植物,向着太阳伸展蔓藤,枝繁叶茂,在与这样的植物相似的生命力的驱使下生存”。*[日]津島祐子:《著者から読者へ》,《山を走る女》,講談社,1980年,第370页。生育孩子对她们而言只不过是伸展新的蔓藤而已,但在现实社会却不被允许,女人在此才知道何谓孤独。“我想,所谓‘独身的母亲’即‘山姥’的传说,其实并非是指‘母性’,而是以‘孤独’为主题。我愿在现代社会中再现那种犹如‘山姥’的、一人生育并抚养孩子的女性原初的孤独姿态。”*[日]津島祐子:《著者から読者へ》,《山を走る女》,講談社,1980年,第371页。作者进而说道,我在这里想要探讨的是,所谓私生儿的母亲到底是什么?在日本,将带着孩子的山姥,即金太郎*金太郎:后称“坂田金时”,日本古代传说、童话中的人物,是一个力大无比的英雄形象。其出生的传说有二,一是作为山佬的母亲与雷神交合而生;一是在金时山顶,赤龙赐予其母八重桐的孩子。江户时代的浮世绘中多有描述,静冈、长野、新泻等是传说中的出生地。的母亲看作为有名的私生儿的母亲。我将其与西方的圣母玛利亚相结合而得出统一的形象。欲在此表现被无聊的社会规约所束缚而生存的人们基于自然的、强大能量的憧憬。我想用“奔跑在山上的女人”一词,尽量基于现实地描写我所想象的女性形象。作者认为,“‘孤独’伴随人的一生”。“当今社会将这一‘孤独’只当作令人痛苦的、讨厌的东西,这一倾向日见明显。希望在当今时代,要更多的人再次看清忍受‘孤独’,毋宁接受绝对‘孤独’而生存的一个‘山姥’形象的强大有力。”*[日]津島祐子:《著者から読者へ》,《山を走る女》,講談社,1980年,第371页。
小说一开始,描写了多喜子的梦中感觉,即她隐隐感到临产前腹部的阵痛,然后静悄悄地起床一个人艰难地奔向医院。21岁的多喜子,原为公司职员,后辞职以打零工维持生计。由于工作关系,多喜子与在政府机关供职的前田宏相识。前田32岁,是一个干瘦、老实的男人,操一口方言。由于双方都很寂寞,便在不知不觉中有了更深的接触。不久,前田辞职,带着老婆、孩子回东北老家开店去了,在他走后一个月多喜子发觉自己怀孕了。怀孕后的多喜子并不想追查前田的地址并与他取得联系,她感到从开始就没有联系前田是自己的好运。在经过是生育还是中止妊娠的多次斗争后决定生下孩子。在去医院的路上,多喜子昂首、挺胸向前走去。多喜子瞬间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胸前轻轻地抱着婴儿,全速向前奔跑的自己的身姿。妊娠被母亲知道之后,在母亲的哭声和父亲的怒骂声中,总是思考那些自己的身影。她知道“自己的奔跑并非逃跑,只是想成为坚强而又自由自在的人。想成为不懂得感情之物的人。想成为什么都不懂而被容许的人。”*[日]津島祐子:《山を走る女》,講談社,1980年,第10页。也就是说,内心孤独的多喜子不愿恪守传统和约定俗成的规约,只想按照女人的自然属性自由地生活。对她来说,孩子的父亲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和自己的孩子。
多喜子对原始自然的向往之情非常强烈,因此,小说以梦境的形式三次描述了她心目中向往的原始山林及其景色。例如,她在生育后回到家中躺在床上打盹儿的时候,母亲的故乡开始在她脑海中萦绕并逐渐扩大。那是一座山的斜面。山峦叠嶂,看得见在黢黑的山脊上还有淡蓝色的、就要融化到天空中的山脊。那是一个翻过山还有更加险峻的山的地方。“母亲在多喜子幼年时多次讲述自己成长的山中世界给她听。也许只有二、三次那样的机会,母亲想给多喜子讲一点自己故乡的情况。故乡已经没有一个有直接联系的人了。母亲不曾回去过,甚至也没有带着多喜子和弟弟在旅行途中顺便去过。但是,多喜子却从母亲的话语中按自己的想象描绘那个地方,感到那里总有母亲的身影,一直对那个不曾相识的母亲感到留恋。想象着从近山眺望远山的少女,那完全就是自己的身影。”*[日]津島祐子:《山を走る女》,講談社,1980年,第101页。在多喜子看来,生长于大山中的母亲本身就是“山佬”的化身,她从母亲的言谈中对连绵不断的大山充满向往之情。那自然、自由的天地勾起她无边的遐想,她认为那是远离人世的最美的地方。“多喜子从深山中的小山丘上远眺那些飞奔在淡蓝色山上的、白色的骏马。再看脚下,白叶闪烁的如同波涛汹涌般的葡萄园一直延续到自己站立的高山上。从上面往下看,便是绿色翻滚的荒凉的大海,就像是憎恨大山感情激荡的生物。一望无际的葡萄园,远远看到白色朦胧的盆地里的村落,还有银色的河川。”*[日]津島祐子:《山を走る女》,講談社,1980年,第101-102页。当天晚上,她又梦见母亲的故乡,“覆盖整个山坡的辽阔的葡萄园。应该是一幅极为安静的光景,但是,在远眺那里的景色时却不由地产生一种粗暴的感情。绿叶丛生的波涛,紫色的水花。就像拥有憎恨大山的意志那样,试图从下界远点,尽量远地隔开大山,还有周围的群山,更远的山,淡蓝色的山。”*[日]津島祐子:《山を走る女》,講談社,1980年,第106-107页。母亲生长的大山里出产水晶,母亲带来很多黑水晶、紫水晶和一些无色的六角柱的原石,总是掩盖不住骄傲的心情,从姑娘时代就一直很宝贵地珍藏着。结合那些水晶的想象,多喜子更加向往那美丽的大山世界。也就是说,多喜子继承了母亲的山姥性格,禀性中潜藏着山姥的自然特色,她要按照女人的天性以山姥的方式生存下去。
在多喜子看来,成长于大山中的母亲孕育着生命,是母爱的象征。她曾记得自己小时候与母亲一起去澡堂洗澡时的感触,母亲个头不高,骨骼粗壮,让人丝毫不感觉到肉体的柔软。也许是刚生了弟弟的缘故,“母亲硕大的乳房,在多喜子面部的两则。那是比多喜子的脸还要大的、柔软的乳房。尽管如此,也是毫无表情的乳房。夹在母亲的乳房中间,多喜子除了母亲的肉之外什么也看不见了。太不可思议了,多喜子感到害怕,想要离开母亲的身体。但是,一想起周围深深包围着自己的热水,更为可怕,从而不能离开母亲。”*[日]津島祐子:《山を走る女》,講談社,1980年,第149页。在多喜子眼里,来自大山的母亲就是充满神秘色彩的“山姥”,作为“山姥”的女儿,自己自然亲近大山,对大山充满向往之情。那个没有人间烦恼的自然之天地有开阔的海域、径直的海岸线,除此之外,还有狗拉着雪橇奔跑在冰海上的男人们的身影,那逐渐变小的黑点是少女最为关注的。“从山上能看得见的并非是山脚下的村庄。越过对面的山,能远远地看到大河流淌着的平原,紫水晶般融化的大海向外扩展,海岸线呈锯齿状,有的地方是直的,有的地方是弯的,一直向北方延续,不久,海水被冰锁住,开始泛起白光。少女最喜欢那白色的光辉。从少女站立的山上看上去是最远的地方,可她感到最为亲近。少女的眼睛也没有放过那些用狗拉着雪橇在冰海上奔跑的男人们的身影。小小的、黑点。他们自由自在地滑行在白色的天地里。还有那看上去无边无际的冰海。”*[日]津島祐子:《山を走る女》,講談社,1980年,第108-109页。这个曾经在山上眺望美好风景的母亲,后来则成了“与冰原的光辉、开阔的绿叶毫无关系的小城男人的妻子”。 多喜子想:也许母亲已经绝望了。可是,自己不想绝望,也不能绝望。为了自己心目中向往的出产水晶的大山,她给刚降生的儿子起名为“晶”。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为了突出多喜子作为女人的天性,用大量篇幅描写森林、树木等的植物,甚至用树木的繁茂生长暗喻女人所具有的性欲望,以及无法压制的生命欲求,展示了多喜子的“山姥”形象。在小说第二部分“森林”中,作者写道:“从病房的窗户看到一棵大树,那是棵白杨树,每天下午那棵树就开始发光,树叶随风摇动,白光闪闪地飞舞下落。窗户的四角边框形成饰边,其景色犹如海市蜃楼,表面上看去感觉就在眼前。一到傍晚,那棵树就充分地沐浴在夕阳中,一天中最为灿烂夺目。”*[日]津島祐子:《山を走る女》,講談社,1980年,第21页。这颗在夕阳中闪闪发光的大树勾起了她往日的回忆,那是自己在上高二的时候与上高三的男朋友一起在电影院看过的电影,一部描写印第安妇女生育生命的影片。“某种光景在闪闪发光的大树周围扩散。环视四周,是毫无遮掩的枯干的白色平原。没有树木的绿色,到处布满硕大的岩石,呈现出各种各样的生物的姿态。风吹个不停,干燥的土地表面被大风吹着,看上去犹如被黄色雾霾所笼罩。充满光与热、将大地远远地从水分中隔离出来的太阳也因暴土扬尘而朦胧不清。”*[日]津島祐子:《山を走る女》,講談社,1980年,第27页。在这种极端条件下,影片中孕育生命的女主人公登场了。“女人一个人走在平原上,那是一个印第安女人,女人的背后有印第安村庄,女人一直毫无表情地走在没有人居住的平原上,女人挺着大肚子。”*[日]津島祐子:《山を走る女》,講談社,1980年,第28页。这个凭面孔看上去还是个孩子的姑娘在即将临盆时,一个人带着必要的食物离开村庄,在一块岩石前终于停下来,坐在岩石下等待自己婴儿的诞生时辰。“电影中的女人不久就遭遇强烈阵痛的袭击,两手紧紧抓住岩石,给即将出生的婴儿以全身的力气。挥汗如雨的女人的面孔突然充满恐惧,双眼瞠目。一个陌生的男人正从对面的岩石下死盯着女人,那是电影的主人公。女人睁开眼睛反盯着男人,两手抓住岩石继续发出呻吟声。恐惧消失,只是用一双大眼睛死死地盯着男人。男人也微微地张着嘴,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女人的样子。”*[日]津島祐子:《山を走る女》,講談社,1980年,第29-30页。最后,“女人抱起用布包着的婴儿,站在岩石的旁边。与男人再次对视了一下。然后一言不发、毫无表情地用来时同样的步伐行走在平原上。”*[日]津島祐子:《山を走る女》,講談社,1980年,第30页。这个类似于日本神话中孕育列岛的伊奘冉和伊奘诺的影片,在16岁的多喜子的脑海中深深刻下孕育生命的女性形象,致使她怀孕后第一次体验身体的变化,就“完全沉醉在其变化中,根本就不具体考虑中止妊娠的事,继续过着日子”。*[日]津島祐子:《山を走る女》,講談社,1980年,第32页。当时,她只想生下孩子后如同印第安女人一样自己抱着孩子离开,但是,在现实中她的行为却不被允许,就连亲生母亲知道后也顿然失色,猛然大叫起来,用力地打了多喜子的脸。然后大哭起来。多喜子不知如何是好,母亲双手捂着脸呻吟似地诉说着,然后再次哭起来。为何要生下孩子?多喜子自身也说不出一个“特别的、像样的理由”。
在第6部分“嫩叶”中,多喜子对树木、绿色以及郁郁葱葱的森林充满感激,在她看来,这些自然生长的植物不仅孕育着生命,同时也是生命的象征。每当看到这些充满绿色的植物,她就似乎看到了婴儿与母亲们的矮小身影、母亲背着的婴儿、坐在婴儿车里的婴儿,以及临盆的自己一边仰望头上在盛夏阳光照射下透明发光的茂密树叶,一边走在路上的光景,不由地内心充满欢乐。身处凡界的人们,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如同植物自然生长,同样地拥有欲望和梦想,她在后来认识的中年男子神林身上,“第一次知道了男性对性欲的压抑。也第一次真实地感受到在压抑的痛苦中欲望彰显的力量。对第一次体味到的身体内部的性的快感,有了实际感受。”*[日]津島祐子:《山を走る女》,講談社,1980年,第325页。不仅如此,两人分别在对方身上找到了心灵的依托,感到内心的充实。在她看来,新的家庭并非只是局限于血缘关系,在“母子”“父子”关系基础上建构的相互融洽的人际关系即是现代家庭最好的形态。
多喜子生活的家庭作为战后出现的极为普通的核心家庭,到了20世纪80年代开始走向崩溃。制约家庭关系的社会伦理开始淡化,经济拮据、生活困难,在生活的压力和诸多不如意中,父亲酗酒、变态,夫妻分居,然后就是面临的病痛和无法预防的衰老。21岁的多喜子作为新一代的代表,不再恪守传统社会约定俗成的公约或家庭伦理,而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追求自我的生活。期间,虽然有作为私生子母亲的孤独,有频繁更换工作的辛苦,还要忍受来自家人的辱骂与暴力,但她从不后悔地坚持走自己的路,按照人的自然属性生育、生长,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自我的“成熟”,并用“身体”感受自我的存在。在她看来,父母并非只是养育孩子的存在,努力奋斗感受人生的充实更为重要。可以说,多喜子的人生选择预示着年轻一代对旧的生活方式的颠覆和对新的家庭关系的诸多探索,这既是一个艰难的社会价值选择过程,也是一个现代“山姥”灵魂自我救赎的过程。
[责任编辑赵彦民]
The Deconstruction of “Mountain Basking (yamauba)” Legend in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XIAO Xia
"Mountain Basking" is a wide-spread folk legend in Japan. The image, in modern Japanese female writer's works, is no longer an old woman inhabiting the mountain, but a female character bearing mountain basking qualities with rational thinking after deconstruction. In modern society, "Mountain Basking" mostly refers to the woman figure suffering from injustice, hardship of life. Actually, these women are the victims under special social system and secular laws and their ultimate fate is doomed to the morality "trial", sacrificed for warding off disaster and evil spirits, thus becoming redeemers with sins in patriarchal domination society.
Key Words:Japan; mountain baskin legend; female literature; deconstruction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日本现代女性文学的主题表达与价值取向”(项目编号:12YJA75203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肖霞,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授(山东济南 25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