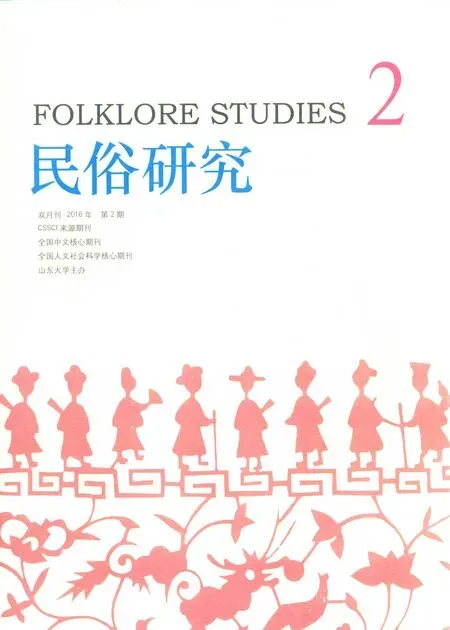“大一统”与差异化——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社会研究——科大卫教授访谈录
“大一统”与差异化——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社会研究
——科大卫教授访谈录
科大卫(David Faure)张士闪
张士闪(以下简称张):科大卫教授,您主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第五轮卓越学科领域计划”(AoE)资助项目“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已进入第六个年头。您当初是怎么想到要操持这样一个时空跨度大、头绪繁多的大型研究计划的?
科大卫:我们一群在香港和大陆的研究者,已经合作了很多年。“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是这么多年合作的共同思路。
张:与弗里德曼的宗族模式和施坚雅的区域市场模式相比,您是从怎样的出发点来理解中国社会的?
科大卫:弗里德曼和施坚雅对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都有很重大的贡献。弗里德曼之前,对华南宗族的研究已经不少,但主要是把宗族看成扩大的家庭。弗里德曼指出,家庭与宗族是两码事,有不同的作用,不同的思维,没有互相演变的成分。再者,宗族不是血缘而是以血缘为依据的地缘制度。这些都是颠覆性的概念。施坚雅也是一个富有创见的研究者,他的三篇论文非常了不起。区域市场的概念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在大家都忘记了中国广大农民是生活在有非常强烈的地缘关系的社会的时候,他提出市场网络对地缘的作用。其次,他以为可以根据市场网络的划分,把整个中国分成不同(但是互动)的经济区域。虽然这对有关地方性异同的问题能解决多少,还不好说,但是施坚雅的大前提是有道理的。他认为中国实在太大,很多时候地区的经历与整体的经历不一定相同。我们去研究中国“大一统”的历史,也需要关注地方上的经历。
张:中国领土广袤,历史悠久,文字系统发达,在“大一统”的国家结构与差异显著的地方社会之间进行阐释,是很有挑战性的。
科大卫:当然。
张:历史上,国家在地理空间的扩张与文化影响的扩大,在促成地方社会文化变迁方面扮演了什么角色?
科大卫:应该说有很多方面吧,但是归根究底,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不同时候的国家有不同的特色。从宋以来,北宋、南宋、元、明初、明中期到清中期、清后期、民国初期、1930到40年代,都是不同形态的国家,有不同的制度,不同的统治理念,不同的宗教和礼仪。在这些不同的时代,国家的版图不一样,在版图之内的渗透也不一样。在珠江三角洲,宋元时期很大部分尚未成陆,遑论这些还没有成陆的地方是否国家的部分。再者,国家对地方社会的影响,不一定是控制,也可以是地方社会很主动、很巧妙地把国家制度引入来处理地方上的问题。所谓地方整合到国家,就是一种认同的过程。我们在田野考察的基础上注意到,这种认同跟地方社会与国家机构打交道的形式很有关系。在华南地区,简单地说,明朝初年国家以地方官管辖的社会,都自认为是“民”,也就是清代的“汉人”;所有土司管辖的社会,都变成我们今天的壮族;没有地方官也没有土司的社会,就是我们今天的瑶族。
张:您曾说过,地方文化的塑造取决于地方社会整合到国家的时机和当时的国家理论。是否可以断言——从某种程度上说,一部中国历史就是地方社会整合到国家的历程?
科大卫:您问的问题,关乎这是谁的历史。我从两方面来回答。第一,我们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历史是多种声音混合的结果,有些声音大,有些声音小。有的历史学者听觉比较灵敏,也有的历史学者对个别的声音听而不闻。我相信,假如中国历史是中国人的历史的话,它需要包括不同的人参与这个历史的经验。第二,我们研究历史的人也知道,一直到近代,我们的基本参考资料都是以国家上层的利益为核心。也就是说,我们一直以来,不是不把地方的历史放到国家的历史之内,而是认为在没有官方记录下的地方历史,根本不是历史。所以,我们需要了解地方的历史,需要重新学习,把没有在我们传统历史记录中发声的人的历史也放进去。
张:我注意到您近年来在研究中经常使用的“礼仪标签”的提法,很是生动形象,这在您所倡导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有什么特别含义?
科大卫:我在田野调查中,注意到地方社会中有些具有个性特征的礼仪传统表达,我称之为“礼仪标签”,认为这是历史人类学探讨历史的一个重要渠道。这些礼仪的实践,建立在“正统”的概念之上。当不同的“正统”传统碰撞的时候,就会形成礼仪的重叠。有一次在福建调查,我看到妇女进庙时需要在腰部戴上围裙。这就奇怪了!既然腰部已经被衣服所遮盖,为什么还要戴上围裙呢?我由此怀疑这一带妇女——在文献上称为“惠安女”——以前的穿衣习惯是裸露腰部,可能有一个时期,这被看成是不雅的,所以就形成了拜庙时戴围裙的习惯。当衣着改变后,已经不需要这样做了,但是礼仪的要求并没有改变,所以围裙和衣服就重叠了。这些礼仪标签,还包括建筑的特征、与地方宗教和祖先祭祀紧密联系的文字传统、地方神祇的故事、村民自己或和尚道士所演绎的乡村仪式等等,它们对于我们探讨地方历史的演变,以及地方社会如何接受并整合到一个“大一统”的文化的历史,很有意义。
张:在历史人类学的视野中,您觉得应该如何看待族谱这类民间文献?
科大卫:一般来说,历史学者习惯看文献记录,人类学者习惯去实地考察。历史人类学讲究对文献资料与实地考察的结合,对社会历史进行研究。就族谱来说,一般研究者往往把族谱当成一本本的“书”,仅仅从中抽取其谱系记录,来收集历史研究的文献材料,却没有把这种文献放入历史发生的具体时空中进行解读。但正如传说的研究需要从它建构的历史开始,比谱系本身更重要的,是编纂谱系的人的历史。编纂族谱的历史,往往就是地方宗族的历史。历史人类学的眼光,是将族谱看作活的记录,随每一代人的需要而改变,而不是收集在图书馆里的死文字。其实也不只是族谱,历史学者所使用的文献,都需要放回历史现场去了解。
张:今年5月,您在山东大学做的“历史人类学与中国乡村社会研究”讲座上,曾经表达过“族谱中的说法,和族谱的历史是两回事”这样的意思,大家很受启发。您能否就此再略加阐发?
科大卫:相信这是你们民俗学习惯的概念。比如孟姜女故事的内容,可以有不同的版本,分别比较这些版本,我们可以了解这个故事的流传,从而了解流传这个故事的人的历史。正如民俗学需要训练一样,读族谱也需要训练。头一课应该让读者知道族谱不是一本书,而是个档案。一本族谱的内容包括不同的文件,读者需要辨认出这些文件的来源。但是在很多时候,这些文件也是通过多次的收集,才放到您手上拿着的这一份文本之内。每一本族谱都有它的历史,这个历史跟编纂族谱的人们的历史都有很大关系。我们很多同行,以“开矿”的心理去读族谱,只会抄录一两段描述性的资料,太可惜了。
张:田野资料的理解和使用,是民俗学、人类学年轻学者们很关心的,您在这方面有什么体会?
科大卫:历史上的乡村老百姓,绝大部分是不识字的人,他们的历史并不是靠书写来记录,而是通过祭祀礼仪表演等活动一代一代地传下来。这些田野资料,是不能以“可信”、“不可信”的标准来判断的;以为“可信”就可以抄用,以为“不可信”就可以不理会,这恰恰是不懂历史的表现。所有的历史材料,包括口头史料,都有它的来源、传播的方法与理由,并经过了持有者的不止一次的修改,但是通过恰当的处理方法就可以了解历史。地方文献、物质遗物、礼仪表演和口头访问等材料,都可以作为历史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资料。比如说,在做口头访问时,往往一句话是怎样说的比这句话的字面内容还要重要。口述访谈是个学习的过程,访谈人需要以谦虚和诚恳的态度,了解被访者的词汇、感受与思路。
张:大约在十几年前,您发表过一个“告别华南研究”的演讲,学界现在还不时有人提及。我知道,您这些年在华北地区跑了很多地方,有什么新的感悟吗?
科大卫:我知道有些朋友对我的研究一直关注。新的体会是很多的,但是把它们表达出来还需要一段时间。
张:当代社会变化急剧,一方面是信息获得空前便捷的所谓“大数据时代”,一方面是大量珍贵的田野资料因为种种原因而损毁严重,这对于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影响巨大。
科大卫:每一代人都会面对这个问题。世界永远在变,我们需要把握机会把我们还可以接触到的历史事物记录下来。保留田野材料的最好办法,就是去了解产生这些材料的世界。
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田野研究是讲究“慢工出细活”的,这对面临现实生存和各种职业考评压力的当代青年学者来说很是不易。
科大卫:我同意这一点。现在学校用处理理工科研究发表的标准来处理人文学科,既不对也有反效果。不对的地方,是理工科面临的是迅速变化的学术环境,大部分理工科的研究,如果在几年之内没有人读,以后也不会有人去读。人文学科是不一样的,变化比较慢,一本好书在出版后几十年还可能有人去读。因为现在国内出版商要靠收费出版生存,已经把学术市场弄坏了。学校已不大相信出版商会对出版物的学术水平负责任,所以就给学者施加压力,必须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论文。但是,人文学科最重要的成果形式还是写书,而不是写论文的传统。我补充一句,文集不能算是书,我们很多人现在连这个道理都不知道了!所以,在目前的学术环境下,我们的年轻学者想下功夫做好的研究是很困难的。但是,“慢工出细活”并不只是适用在田野研究。我们所有人文学科的研究都是“慢工出细活”。“慢工”才有时间去读书,才有时间去思考,现在有多少年轻学者真正去读前辈甚至同行的著作?您这句话反过来说可能更对——“快工出大话”!现在很多研究都是空话、谎话。
[责任编辑龙圣]
作者简介:科大卫(David Faure),香港中文大学伟伦历史学研究教授(香港沙田)。张士闪,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山东济南 25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