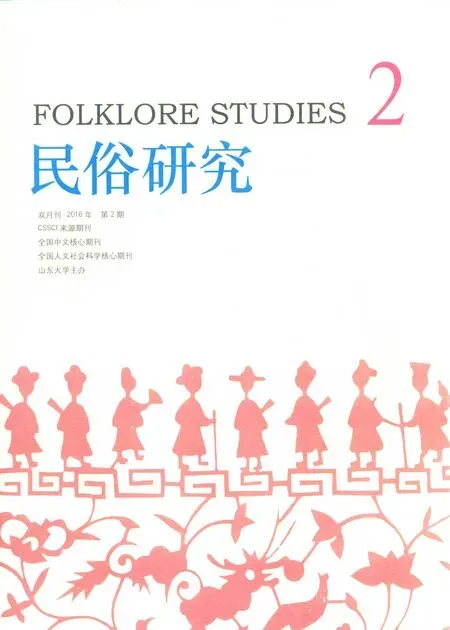汉人传统庄社的基本性质
林美容
汉人传统庄社的基本性质
林美容
摘要:以台湾的研究经验,论述汉人传统庄社的基本性质。其一,汉人庄社是一个仪式共同体,汉人庄社基本上是一个仪式界定的社会单位,人们在所居住的庄社里崇拜神明,举行共同的祭祀,有很强的社会凝聚力。其二,汉人庄社具有法人性格,这可以从传统汉人庄社拥有公地,以及庄社神明拥有田产,看出端倪。其三,汉人庄社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长期共同生活经验的累积,让庄民产生命运与共的一体感,可从庄社地理的说词与每年所抽的年签看出。其四,汉人庄社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村庄和人一样有生老病死,生命不断变化,也有毁庄灭庄的情况发生。其五,村庄是一个意志单位,村庄作为社会集体的存在,可以透过头人表达其自由意志的选择,特别是在与外界建立村庄联盟的时候。其六,村庄是村际关系的交陪单位,透过友庙、交陪境、联庄组织等,村庄与其它村庄建立长期稳定的交陪关系。
关键词:汉人庄社;仪式共同体;法人性格;有机体;意志单位;村际关系
一﹑前言
有关台湾汉人村庄的系统性的研究,可说始于日本学者富田芳郎的研究,1933年他发表《台湾の农村聚落型态》,1935年发表《北部台湾に於ける自卫的农村聚落の一例》, 1936年发表《台湾南部の村落居住景观の比較》,1943年发表《台湾聚落の研究》。他提出台湾北部多散村和小村,南部多集村的型态之观察,并解释南北聚落型态之差异的成因,也描述了在治安不良的情况下,村庄的防卫设备与居住形式,并提出相当多的姓氏分布的资料。①[日]富田芳郎:《台湾乡镇之研究》,《台湾银行季刊》1955年第七期第三卷。
战后台湾人类学先发展原住民部落的调查,因而台湾人类学者最早对汉人庄社进行调查要到1965年才展开,当年李亦园在彰化伸港乡泉州厝调查其家庭及轮伙头的习俗②李亦园:《文化与行为》,(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第83-85页。,以及王崧兴在龟山岛所进行的渔村社会调查③王崧兴:《龟山岛—汉人渔村社会之研究》,《中研院民族所专刊》1975年第六号。和1971-1972年在台湾北、中、南三个稻作农村进行的研究④Wang and Apthorpe,Rice Farming in Taiwan Three Village Studies,Taipei:Institute of Ethnology,Academia sinica. 1974.,1972-1977年之间谢继昌在埔里篮城村调查其社会结构与历史⑤Hsieh, Jih-chang Chester(谢继昌),Structure and History of a Chinese Community in Taiwan,Monograph No.25,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1979.,1976-1978年之间胡台丽在南屯刘厝调查了她的婆家村落有关农村工业化的课题。⑥Hu, Tai-li (胡台丽),My Mother-in-law’s Village: Rural Industrilization and Change in Taiwan,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1984.
这当中,欧美的人类学者也在台湾进行了许多的村落民族志,有些甚至更早就开始了,例如1957-1958年Bernard Gallin 在彰化埔盐乡的新兴村进行调查⑦Gallin, Bernard, Hsing Hsing, Taiwan: A Chinese Village in Chan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1966.,1958-1960年 Arthur Wolf和 Margery Wolf夫妇在三峡镇溪州里进行调查,1964-1965年Burton Pasternak在新埤乡打铁村进行调查,1964-1965年Myron Cohen也同时在美浓镇燕寮进行调查,1966-1967年David Buxbaum在树林镇柑园里进行调查,1969-1970年Emily Ahern在三峡镇溪南里进行调查,1971-1972年Burton Pasternak又接着在美浓镇龙肚村进行调查,1972-1973年和1978年Stevan Harrell 在三峡镇犁舌尾进行调查,1971-72年Katherine Gould-Martin也在树林镇彭厝里进行调查,他们的调查虽然有各自的重点,但基本上都有对他们所调查的村落之全面而整体的(holistic)叙述。*林美容:《村庄史的建立》,《台湾史料研究》1995年第5期。
当台湾本地和欧美的人类学者,不约而同地在20世纪70年代结束二三十年的村落民族志的调查,日本学者悄然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接续台湾的村落民族志的工作,植野弘子最近在台湾出版的《台湾汉人姻亲民族志》即是这段期间在台南佳榕林调查的研究成果。*[日]植野弘子:《台湾汉人姻亲民族志》,南天出版社,2015年。
我自己虽然没有做过村庄民族志的工作,但是我的祭祀圈研究与信仰圈研究,基本上都是在汉人地域社会的基础单位——庄社的基础上展开的。我作草屯镇的祭祀圈的时候,作彰化妈的信仰圈的时候,作高雄县的地方公庙的时候,一个村庄接一个村庄地跑田野。无论在乡镇的范围,或是跨乡镇的范围,或是县市的范围,或是跨县市的范围作田野,因为村庄作为汉人社会的基础单位的想法,也就能够逐渐架构起来祭祀圈与信仰圈这两个有关汉人民间信仰如何形构汉人地域社会的理论概念。因此我对于村庄的重要性与对人们生活的意义,一向不遗余力地勤加论述与推广,《乡土史与村庄史》*林美容:《乡土史与村庄史》,台原出版社,2000年。是我这方面论述的一个总集。本文的重点主要在综合性地说明从在台湾研究的经验所看到的汉人传统庄社的基本性质,以下一些论点在笔者有关祭祀圈与信仰圈的相关论著里可以找到,而大部分的资料与论点则可参考上述的《乡土史与村庄史》一书。
二﹑仪式共同体
祭祀圈基本上就是一个仪式共同体(ritual community)的概念,是一个地方小区的居民基于对天地神鬼的共同祭祀所形成的一种义务性的祭祀组织,这个仪式共同体可小自一个自然村(有时叫角头,有时叫角落,日据时期也会叫做部落)。村庄,大至几个村庄的联合,或是整个乡镇,不管在哪一个层次的地方小区,只要有共同举行公众祭祀者,都可说有祭祀圈的存在,或是仪式共同体的存在。
要理解汉人的村庄,首先就要理解村庄基本上是一个仪式界定的社会单位*林美容:《土地公庙-聚落的指标:以草屯镇为例》,《台湾风物》1987年第37期第一卷。,这一个定义性的理解,或许有些人无法接受,但是传统的村庄,会有村庙,村庙会有主神,主神的辖境即是村庄的范围,村庄的范围尽管也会有地形地貌的界定,或是行政区划的界定,但当我们谈论的是传统庄社的时候,基本上它的界定,主要还是以神明的祭祀范围为准。
村庄作为一个仪式共同体,意味着村庄一定有共同的祭祀活动,所谓的公众祭祀(communal worship),不管它是主神的千秋祭典和巡境,或是元宵的“拜丁鸡”,或是中元普渡,或是土地公生日,或是下元的“谢平安”都是村庄性的公众祭祀活动。而许多的公众祭祀一定会有代表性的头家炉主,轮流性的角头组织,或是志愿性的神明会或轿班组织,或是常态性的丁口组织,各种组织方式维系公众祭祀的年年不断地进行,所以祭祀圈一定会有相关的祭祀组织与活动,这是勿庸置疑的。
台湾汉人的传统庄社可以大体分为两种,一个我称之为未完形的村庄(incomplete village),一个是完形的村庄(complete village),一个村庄完形与否取决于其村庙是否设立。未完形的村庄指的是角头、角落或部落的小庄社,通常会有“地号名”作为庄社的身份认同,土地公庙是成庄立社之初会建立的标记,有时只是简单的石头庙,之后也会发展成小祠或小庙,但是土地公庙通常没有庙门,不成其为神庙。未完形的村庄通常会有土地公庙的相关祭祀,但是土地公并不是村神,因为一般而言,村庙的主神都是土地公以外的神祇,这个小庄社也还没发展到村落(village)的规模,顶多只是个小聚落(hamlet)。一个完形的完整的村庄,是以村庙的建立为指标,基本上在这个层级,有关天地神鬼的公众祭祀大致可以得到满足,村庙的主神成为村庄的境主,其辖域便是村民举行公众祭祀的范围。台湾迄今仍会有一些村庄,虽然在实质的人口聚居规模上,已经达到村落的层次,但是迄今仍保留有神无庙的村落性祭祀方式,我也偏向认为这样的村庄,也在未完形的村庄之列。未完形意味着完形的可能,所以一旦村民为祭祀已久的村神立庙,这个村庄便成为所谓的完形的村庄。
而无论完形或是未完形的村庄,基本上都是仪式共同体,居民共同举行仪式,祭祀成庄立社以来就和他们同在的土地公,祭祀村庙主神和其副祀神,因为这些神明或是和他们的先祖一起同来,或是在拓垦过程中开基有功,或是协助防蕃,或是协助除疫,或是有益农作等等,这些神明作为庄社的象征,作为庄社集体意识的投射,作为庄民凝聚力的来源,其实也深刻书写着庄社的历史。而共同祭祀必定带出来各种各样的祭祀组织,丁口组织、头家炉主、角头组织、神明会、轿班,或是曲馆与武馆的子弟组织,也都和祭祀活动密切相关,而村庙的组织无论是管理人的制度,或是管理委员会的形式,也是村民赋予他们权力来经营管理村民共同有分的村庙。
在此必须说明的是,本文所谈论的是传统的汉人庄社,对于现代的小区,并没有仪式共同体的建立。所以有没有共同祭祀的仪式共同体存在,很明确地可以作为区分传统小区与当代小区的依据。
三﹑法人性格
为了要共同举行祭祀,村庄会有一些共有的财产,以村庙或村庙的主神为名义,而实为村人所共有。这些村人共有的财产,最主要的便是村庙以及其他公众祭祀的庙宇,有时还有一些田地、山林、池塘等庙产。*戴炎辉:《清代台湾之乡治》,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第160-161页。戴炎辉曾论述清代内地及台湾之村庄,具有类似日耳曼固有法之法人性格,并说该法所谓法人系从最古意义的合伙体(corporate)所进化而来,主要是从法律层面来观看汉人的庄社。村庄具有法人性格,主要有两个意义:
(1)村庄拥有财产
戴炎辉说:村庄财产一面为其村庄所有;他面如其被称为公地、公池、公埔及公庙等,即被认为各村庄民全体之所有。*戴炎辉:《清代台湾之乡治》,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第182-183页。而符应上述,村庄债务乃村庄民全体之债务。村庄对外,由村庄之长(乡长)、耆老(首事人)等代表;若无乡长,则由耆老(首事人)代表之。而耆老依村庄之不同,或为各姓的代表或某角落的代表,或不问族性、角落如何,为村庄民全员之代表,而为法律行为。
(二)村庄得为法律行为之单位
戴炎辉说:村庄为村庄而所有财产,为法律行为,为诉讼行为。*戴炎辉:《清代台湾之乡治》,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第182页。对内而言,有村庄规约(通常为习惯法,但予以成文者亦不少)。此不但拘束一般庄民,村庄对于违反者,予以制裁,而且对于一般反社会行为、反人伦行为之轻犯,再就民事诉讼,亦有予以调处、裁判之权限。对外关系,村庄不但与其他村庄订立合约,或与之结盟,而且关于本村庄民与他村庄民之争讼,亦以调处、裁判,或对其他村庄请求处罚、救济。对政府关系,政府不但将村庄内事委其自理,而且例如重要人犯之跟交,亦要求该村庄老大或全村庄民负责。有时村庄被摊派差役、赋役。而村庄由乡长、庄正副代表之。
村庄具有法人性格,这是一般人比较不能了解的事,因为现在村庄的共有财产除了村庙依然存在之外,其他的公地、公埔、公池等,大部分都已经不存在。村庄得为法律行为的单位,现在也比较少看到这样的案例,但是村庄作为地方自治的最小单位,作为目前政府行政区划下的最小行政单位,虽然庄社的运作比起往昔有多头马车的现象,村庙有村庙的头人,村里长是领政府薪水的,小区理事长管理小区的环境等。但是往昔传统小区庄有庄长,庄有庄规,庄有庄产所形塑的法人性格,在当今社会仍可见到。
四﹑命运共同体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来论述台湾汉人庄社的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主要是以村庙年签和有关村落地理风水的资料来阐述。*林美容:《由地理与年签来看台湾汉人村庄的命运共同体》,《台湾风物》1988年第38期第四卷。年签应该是确定村庄之命运共同体最有效直接的证据。常常我们会在村庙或是地方公庙里,看到墙壁上贴着年签或是四季签,通常是年初或岁末时,庙宇的住持或是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或是值年的炉主,在神前掷筈(卜杯)求签,所得的签诗即表示神明所预示村庄未来一年的运气,有些是分春、夏、秋、冬逐季来求,有些分人口、稻谷(俗称年冬)、雨水、生意(俗称生理)、六畜等逐项来求,无论是何种形式皆通称年签或四季签。
在各地调查宗教组织与活动时,与地方父老的访谈中,他们最喜欢主动提起的事情之一就是有关庙宇的“地理”以及他们所居住的村庄、街镇或城市的“地理”,甚至邻近地方有关“地理”的传闻,他们都了如指掌。从这些父老有关地理的口述中,除了体会到他们把庙宇与地方的兴衰祸福用风水的好坏来解释的心态之外,我们更可以体会到这些地理的说法与地方居民之间的连带与影响。
李茂祥曾述及所谓“庄运”,虽云是指坏的运,然村庄之共同命运,算是早有先见。所谓命运共同体,乃指村民是一体的,他们受共同的时、空因素的制约,这一理念与传统的宇宙观有密切的关系,人绝非宇宙独一无二的存在,须与自然界与超自然界保持和谐的关系。基本上,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是文化的(cultural)、理念的(ideological)、理想的(ideal)。*李茂祥:《从社会学的观点概述民俗信仰》,《台湾风物》1987年第24期第4卷。此一概念是否呈现出来,它又是如何外显,是否取得社会组织的支持,总之其实现(realization)是另外的问题。我深信台湾村庄的命运共同体并非只是逻辑的联想,而是汉人宗教理念的实然。可以作为证据的也不只是年签和地理传说两者,在祭神拜天公(三界公)的时候所读的疏文,在很多公众祭祀活动主祭者的祷词中,在庙宇墙壁上所贴的收丁口钱的红纸上,都可能有具体的证据。
五﹑生命有机体
戴炎辉亦曾论述台湾汉人村庄为“有永续的生命之有机的组织体”*戴炎辉:《清代台湾之乡治》,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第182页。,但其所谓生命体系指其法律生命可以代代相续而言。但是这里所要强调的是所要谈论的台湾汉人村庄之为生命有机体,主要强调村庄是“活生生的,它有起始,有发展,有变化,有分裂,有融合,有地缘,有血缘。生命是一种历程,它走过一些轨迹,留下一些痕迹”。*林美容:《湾汉人村落的衍生形态:竹围仔》,《台湾史田野研究通讯》1990年第15期。我在走访台湾汉人庄社的过程中,听了许许多多有关村庄的故事,村庄的发展有兴衰起落,一如家族的发展,有些村庄经历了自然灾害,像是台风或是海啸,有时足以毁灭整个村庄,有些遭遇人为的迫害,像是日本人为了抓土匪而“清庄”,有些是因为民变或反乱,而波及一些庄社。传统的庄社小庄变大庄,是正常的发展,但是大庄变小庄,有庄变没庄,则是异常的发展,无论何者,都标示着村庄一如个体生命,有生老病死,有成住坏空。
我曾经为文探讨庄社的增衍现象,指出“庄头也湠庄仔子”这样清楚的社会事实,正显示庄社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就像人类会繁衍子孙一样,“庄母”也能生出“庄仔子”,例如草屯镇牛屎崎庄分出去的小聚落叫“牛屎崎竹围仔”,镇平分出去的小聚落叫“镇平厝”仔,等等。*林美容:《湾汉人村落的衍生形态:竹围仔》,《台湾史田野研究通讯》1990年第15期。往昔当一个聚落人口增加,现有的聚落空间不敷使用,便会在邻近地区建一座传统的三合院,以前的三合院都有竹围,日久之后便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小庄社,通常与原本的村庄会维持某种程度的关系。
因为领会到传统汉人庄社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在台湾一个庄社长者三四百年,短者近百年,想想一个人死后,子孙都要为父祖写行谊,家族也有族谱,有钱的大家族甚至请人写家族史,无非要让后人了解先人的奋斗事迹与德行。但是村庄的历史与生命轨迹,却乏人闻问,这也是我过去积极呼吁撰写村庄史的动机所在。*林美容:《村庄史的建立》,《台湾史料研究》1995年第5期。
六﹑意志单位
村庄既然是一个具有生命现象的有机体,它自然和有生命的个体一样,会有自我意志(self will),而我们从何得知村庄是有自我意志的呢?村庄又是如何表达其自我意志呢?我在研究彰化妈祖信仰圈的时候,发现彰化南瑶宫十个妈祖会有两种组成方式,一种是“招会份”,一种是“招庄头”*林美容:《彰化妈祖的信仰圈》,《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90年第68期。,也就是最初在起会的时候,一种是到各地找人入会,愿意参加的人在妈祖前面卜杯,妈祖同意就可以缴钱入会,此称为“招会份”。另一种是取得各庄头人的同意之后,整个村庄的人便都参与有份,不需逐一卜杯,此称为“招庄头”,由此可见村庄是可以透过头人表达其自由意志,决定是否参与村庄联盟组织(village alliance)。虽然南瑶宫的十个妈祖会只有两个是采取“招庄头”的方式,但是我们看到即使是“招会份”的方式,也可以猜想其中应该也有村庄头人首肯入会的事,并就地“招会份”,我们仔细考察各妈祖会的角头组织,角头之下基本上就是许多个庄社,各个庄社尽管会员人数不一,但是这个村庄有没有参与哪一个妈祖会基本上是一目了然的事,所以即使是“招会份”的情况,其中也有村庄意志表达的意涵存在。
不仅彰化南瑶宫各个妈祖会的组织我们可以了解到为什么是这些个村庄要入会而不是另外一些个村庄要入会,其间虽有区域内人群特色的因素存在,但是各个村庄确实可以透过头人表达参加与否的意愿,这种情况存在于诸多台湾的联庄性祭祀组织,小则六个村庄(如南瑶宫圣三妈会的六庄联)、十三个村庄(如同安寮十三庄),中则十八庄、二十四庄,大则三十六庄、五十三庄、七十二庄,而像彰化南瑶宫妈祖信仰圈这样涵盖三百五十个左右的村庄大型信徒组织可说绝无仅有,云林马鸣山五年王爷的香境涵盖二百六十个左右的村庄,是唯一可以比拟的。我现在正在研究的西螺广福宫妈祖(老大妈)的信仰圈,更可看得出来村庄之意愿有无的差别,此信仰圈基本上是由两项仪式活动所共同形塑的,其一是历来已经行诸有年的谢平安活动,这是邻近乡庄往昔以来即依例前往广福宫请老大妈来坐镇看戏,而另一项活动是比较晚才发展起来、出于广福宫庙方的积极推动才举办的闰年绕境的活动,这两个活动的范围相差无几,但是村庄之主动意愿的有无却有所差别,我们甚至可以说因为有具有历史性的请神参与谢平安活动,广福宫才有可能主动推动绕境的活动。
七﹑村际交陪单位
传统台湾的汉人庄社凝聚力很强,对外也有互相交陪的需求,上述的联庄组织是一种村庄联盟(village alliance),但是有关民间信仰的发展也些地方像台南,有所谓交陪境的观念与运作,主要是在西港香的香境内,在祭典活动期间,交陪境的村庄会互相到有交陪的庄社以阵头莅临热闹的方式,彼此联谊。而现在台湾许多的地方宫庙都有一些有交陪的友宫,在彼此庙宇的庙会活动时,会互相参与助阵,由头人带队,以诵经团或是阵头来增添热闹的气氛。现在在云林地区,很多村庄的主神圣诞,有庙会的时候,通常邻近几个有交陪的村庄就会有诵经团前来赞扬,甚至不需头人带队,村际之间交陪关系的建立,显示村庄自主性的与别的村庄建立平等关系的需求,这和上述的有一个更层级的超自然存在作为村庄联盟的运作机制,有所不同。
八﹑结论
本文在笔者过去研究民间信仰的基础上,所累积的对台湾汉人庄社的了解,综合性地论述汉人庄社的基本性质。村庄基本上是一个仪式共同体,所以会有许多的公众祭祀活动。它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表示村民受同样的时空条件的制约,长期共同生活所产生的命运与共的感情。村庄具有法人性格,它和法人一样可以拥有财产,在国家的法制下有某种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存在。村庄是一个生命有机体,它有生老病死,有成住坏空,以生的这一点来说,一个村庄可以衍生出来另外一个村庄,这在台湾有许多明显的事例。村庄是一个可以表达自我意志的单位,不要以为村庄不说话,透过头人,村庄可以表达是参与联庄性的祭祀组织,是否参与区域性的神明会等等。村庄也是一个可以和其他的村庄建立交陪关系的单位,虽然看起来是庙与庙之间的交陪,阵头与阵头之间的联谊,其实很多庙宇都是地方公庙(以庄庙的数量居最多),实际上是村庄与村庄之间的交陪。
村庄是一个聚落人群聚居的单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村庄的基本性质,都和民间信仰的组织与活动有密切的关系,在民间信仰的体系内,我们可以看到个体性的宗教活动,也可以观察到家户范围内的祭祀活动(domestic rituals),或是同姓宗族相关的祭祀活动。但是以村庄为基本运作单位所形构的地域性祭典组织(territoral cult),却是民间信仰体系的核心内涵,无论是地方性的祭典组织(local cult)或是区域性的祭典组织(regional cult),我们都可体会到村庄作为一种社会实存的重要角色。
[责任编辑刁统菊]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an Villages
LIN Meirong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Han village are generalized based on my research experiences on folk beliefs. First, it’s a ritual community, that is, the Chinese Han village is a ritually defined social unit. Second, it obtains legal status just like juridical person, which is evidenced by the common property owned by the village itself or in the name of its deities. Third, it is also a destiny community, within which all the villagers identify with the destiny of the village, and which is evidenced by stories and legends about village geomancy as well as the oracles withdrawn yearly. Fourth, it’s also an organic body just like human beings. Not only it can be established and developed, it can also be destroyed and vanished. Fifth, it’s a unit of free will and the headman of the village usually serves as its representative. Sixth, it’s a basic unit for inter-village relations and interactions. The Chinese Han village usually maintains long-term friendship with other villages in terms of organizing multi-village association or simply friendly temples to support festivals with each other.
Key Words:Chinese Han villages; ritual community; juridical personality; organism; unit of free will; inter-village relationship
作者简介:林美容,福州外语外贸学院闽海中心特聘研究员;(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兼任研究员(台湾台北 11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