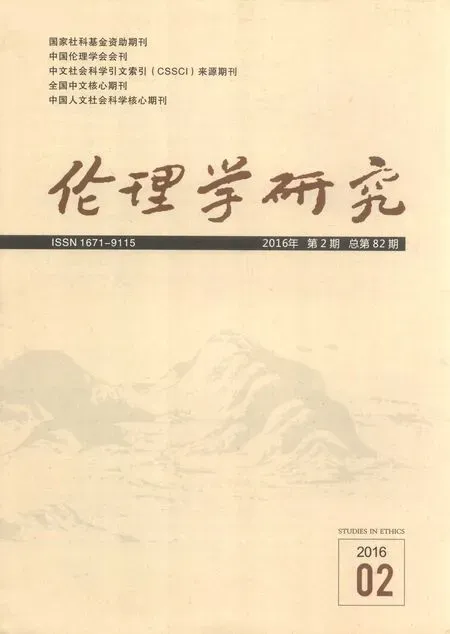“经济学帝国主义”理论辨析
赵昆
“经济学帝国主义”理论辨析
赵昆
“经济学帝国主义”往往会带来对功利最大化的推崇,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对效率的崇尚。因此经常有人将“经济学帝国主义”与功利主义、物质主义和效率主义等混为一谈。但就其实质而言,“经济学帝国主义”与这些主义有关联但却本质不同,更不能相互替代。所以有必要在厘清“经济学帝国主义”理论表现的基础上,将“经济学帝国主义”与上述主义区分开,以便对“经济学帝国主义”进行更好的认识和反思。
经济学帝国主义;功利主义;物质主义;效率主义
“经济学帝国主义”理论观点最早提出于20世纪30年代(威廉·苏特,1933)。至20世纪50年代,以加里·S·贝克尔等为理论集大成者,并于20世纪70年代后开始大行其道。其基本观点认为,人类的一切理性行为都属于经济行为(贝克尔,1957),效率是社会生活中唯一有价值的准则(波斯纳,1973),经济分析是分析人类行为最有效的方法(贝克尔,1976)。由此,“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推行往往会带来对功利最大化的推崇,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对效率的崇尚,所以一提到“经济学帝国主义”,人们常常会想到功利主义、物质主义和效率主义等。有人会觉得,对“经济学帝国主义”进行批判和反思,不就是对功利主义、物质主义、效率主义进行批判和反思吗?其实不然。“经济学帝国主义”与这些主义有关联但却本质不同,更不能相互替代。因此有必要在厘清“经济学帝国主义”理论表现的基础上,将“经济学帝国主义”与上述主义区分开,以便对“经济学帝国主义”进行更好的认识和反思。
一、“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功利基础
“经济学帝国主义”将经济分析带入其他非经济领域,即是一种经济理性的“越界”,其在“越界”过程中,也将功利最大化的追求带入到了所越界的领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哲学基础即是功利主义。因为,功利主义是各种伦理学说中唯一能够作为各门社会科学伦理基础的学说[1](译者序P5)。有学者还直接指出,功利主义即是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前提之一[2],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实质上源于功利主义”[3]。而“经济学帝国主义”是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运用。可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功利主义作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哲学基础。
当然经济学本身就与功利主义密切相关,许多经济学家就是功利主义者。罗尔斯就指出,“我们不要忘记:那些伟大的功利主义者像休谟、亚当·斯密、边沁和密尔也是第一流的社会理论家和经济学家”[4](序言P1-2)。而且由于功利主义认为道德善恶的标准是由行为的功利或功用所决定的,且如弗兰克纳所言,“无论善恶的内容是什么,它们都可以用某种定量的、或至少是数学的方法来互相衡量或比较”[5](P71)。更有学者认为,“功利主义的道德标准实质上是一种效率原则”[6]。因此,作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哲学基础的功利主义,就容易与“经济学帝国主义”功利最大化追求相混淆。但必须分清的是,功利主义虽然可以看作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哲学基础,但切不可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最大化利益追求与功利主义,乃至将“经济学帝国主义”与功利主义混淆甚至等同,二者本质不同,不可混淆和相互替代。
众所周知,功利主义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伦理学传统理论。先秦时期的墨子被看作是中国早期功利主义的代表,宋代叶适和陈亮的思想也被看作是功利之学。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及后来的伊壁鸠鲁等,被看作是西方功利主义思想的先驱[7](P11)。而就西方伦理思想史而言,“功利主义的观点贯穿于整个伦理学说史中,而最早的有意义的功利主义哲学著作是大卫·休漠(1711-1776)、杰里米·边沁(1748-1832)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的著作。”“然而,边沁只是最早、最有影响的功利主义者之一。一般认为对功利主义作出重要阐释的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功利主义》一书。”[8](P109-110)
思想史上,边沁首次提出功利原理(或原则),认为功利原理:就是将能否增大或减小、促进或妨碍利益相关者的幸福为行为准则[9](P58)。约翰·穆勒进一步阐发了功利主义,并明确将自己的学说命名为“功利主义”,他认为功利主义就是把“功利”或“最大幸福原理”作为道德信条和行为标准[1](P7)。而彼彻姆则进一步将功利主义解释为“目的论”或者称为“效果论”[8](P107)。
一般而言,功利主义(简称功利论①),又可称为“功用主义”或“目的论”②或“效果论”(或“后果论”),是一种将功利原则作为判断行为正当或善恶唯一标准的观点。其核心原则即为功利原则,也就是“最大幸福原则”,即“功利原则或‘最大幸福’原则被宣布为道德的基本原则”[8](P110)。功利主义理论类型众多,除了在性质上可分为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10](P233)以外,就西方功利主义而言,主要可以分为行为功利主义(也称行动功利主义)与规则功利主义(也称准则功利主义)。
通过上述对功利主义的回顾可见,虽然“经济学帝国主义”与功利主义密切相关,甚至可将功利主义看作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哲学基础,但将二者等同是不对的。
其一,这是两种不同的理论思潮。如前所述,功利主义理论思潮历史悠久,早在边沁、穆勒时期就已经十分成熟且影响深远了,而“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提出虽然在1930年代,但真正壮大成熟则在1970年代的贝克尔时期。
其二,两者最根本的不同在于性质、主旨不同。功利主义的根本主旨是将功利原则作为检验道德善恶的根本标准;而“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实质是“泛经济主义”,是行为上的“唯经济论”,是市场价值观的泛滥。经济学在“越界”其他领域后,以功利最大化为目标进行经济分析,这看起来同功利主义将功利原则作为道德评价标准类似。但必须注意的是,“经济学帝国主义”所讲的功利或效用,与功利主义评价善恶标准的“功利”不同。
“经济学帝国主义”进行经济分析时所追求的最大化“效用”或“功利”,虽然并不仅仅是指货币、商品或物质利益,也包括非货币的其他利益或非物质利益,如贝克尔就说,在经济分析中还包括家庭技艺、健康、自尊和其他多种“商品”[11](P29)。但“经济学帝国主义”在进行经济分析时,还是将这些“效用”或“功利”全部“货币化”了,也就是全部“价格化”了。当然,这些价格既包括真实的货币价格,也包括贝克尔所说的“影子价格”。他认为,“影子价格和市场价格会产生同样的效果”[12](P9)。并指出在经济分析的过程中,“价格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甚至在货币价格不存在的非市场部门也是如此:经济学家已经天才地发现了各种各样的‘影子价格’,它们发挥着与货币价格相同的作用”[13](P4)。也就是说,经济学在所越界领域进行的经济分析,实际上是将所分析的对象货币化或是商品化了,所谓“影子”价格就是将非商品的对象予以货币般定价,以便于进行价格衡量。而这种货币化的定价,看似价值中立,其实是具有腐蚀或贬低作用的。例如当我们给幸福定价的时候,实际上就降低了幸福的意义和品味。
功利主义所讲的“功利”内容多样,绝不仅是物质性功利。例如彼彻姆认为功利主义所讲的“功利”,虽然其内容有争论,但基本都一直同意为事物的内在价值,而不是外在价值。“除了快乐以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内在价值,这一观点已为不少功利主义者所承认。”[8](P124)因此,功利主义所强调的“功利”,不仅不是最大化的物质利益,而且就内容和形式而言,都在极力避免物质化、经济化或“货币化”;且功利主义所强调的“功利”,也不是行为个体者的“功利”,而是全体当事人的幸福与基本利益[14]。
可见,“经济学帝国主义”与功利主义二者虽然都讲功利,但具体的功利追求不同。不能将“经济学帝国主义”简单地等同于功利主义,二者不是一回事。
还要注意的是,今天我们在日常用语里所讲的“功利”,往往并不是功利主义所讲的“功利”。有学者已经指出,在今天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中,“功利”的丰富涵义被狭义化了,人们所说的“功利”,往往就是指金钱和财富[2]。也就是说,今天人们日常生活中通俗意义上所讲的功利追求,并不能简单等同于作为伦理思潮的功利主义[15]。而那种对物质利益以及其他名利地位的追求,却往往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对社会价值观的腐蚀和干扰。
二、“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物质追求
经济学是重视物质追求的,有人认为,经济学传统中就具有“根深蒂固的物质主义”[16]。这种对物质的重视和追求,在经济学“越界”到其他领域的时候,也带入到了这些社会领域。因此,“经济学帝国主义”在推行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例如《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编者高小勇认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者们是从“价格”和“费用”等角度,看待问题和解释行为的[17](PXIX)。而前文已论述过,哪怕这些价格是“影子”价格,费用是非货币费用,但无疑仍带有浓郁的物质利益色彩。因此不能否认“经济学帝国主义”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而这种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在经济学“帝国化”的过程中,会无形中激发或加速物质主义的形成。也正是在对物质利益高度重视的基础上,使得“经济学帝国主义”与物质主义在相互促进中不断发展。有学者尖锐批评指出,现代经济学所推崇的就是物质主义[18]。因此,有时候人们指责“经济学帝国主义”,往往就包括指责其所激发的物质主义。
“经济学帝国主义”重视物质追求,而物质主义显然更进一步,不仅重视物质利益,而且将物质利益作为生活的第一追求,将物质利益推向了极端。物质主义,顾名思义,就是将物质利益作为终极目的和价值取向。对此,《伦理学大辞典》将之解释为一种强调物质利益,推崇物质享受,以物质生活为第一要义和标准的观点和学说[7](P32)。也就是说,物质主义将物质利益作为最主要的价值利益,认为其他需求均由此派生[19]。也有学者从心理学研究的角度,在总结当前学界对物质主义不同定义的基础上,认为物质主义更关注物质需要等低层次需要,而不关注价值和精神层面的高层次需要[20]。
物质主义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人类思想史中,精神高于物质、内在价值高于外在价值几乎是不证自明的公理。而物质主义却崇尚物质利益,割裂了物质利益和精神文化的联系,夸大了物质利益的作用,从而否定了精神文化和道德理性的意义。人的生活不能仅仅是物质生活,人的物质需求虽然是基本需求,但不是唯一需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早就说明了这一点。物质主义对物质利益的极力夸大,实际上走向了理论的片面化和极端化,由此而否定精神文化生活和道德追求是错误的。
那么,物质主义存在如此明显的错误,为何还会成为现代社会有影响力的价值取向呢?这无疑与现代社会极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与物质财富有关。具体说来,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相继进入了相当长的经济恢复和繁荣期,经济发展、物质财富丰富,人们生活安定富裕。特别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整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处于经济发展的“黄金期”,而加之西方传统宗教价值观影响的削弱,社会进入所谓的“消费社会”。就像法国学者让·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所说,当今社会的人们正在受到物的包围[21](P1)。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物质主义价值观盛极一时,物欲的追求、金钱的满足成为人们生活的主流。人们受物质时尚的影响,正在不断追逐着物质目标[22]。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的物质财富也在极大丰富,也出现了如波德里亚所说的人受到了“物的包围”,人的选择也开始潜移默化地受物质时尚的牵引,越来越倾向于物质的满足和追求。许多人由对物质和追求和渴望,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滑入物质主义潮流。在东西方共同面临物质主义冲击的时候,“经济学帝国主义”思潮也同时流传和发展起来。我们可以说,正是东西方经济发展和财富丰富这一相同背景,使得“经济学帝国主义”与物质主义的关系愈加紧密起来。
可见,具有相同的经济背景,且“经济学帝国主义”也重视物质利益,具有物质追求,从而在此基础上与物质主义具有了一致性。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将“经济学帝国主义”与物质主义简单等同乃至互相代替。
就二者的区别而言,其一,这是两种不同的理论思潮,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不同的理论主张,二者当然也不能互相代替和等同。其二,二者虽然都重视物质利益,但对物质利益的重视程度不同,物质利益各自所处的地位也不同。“经济学帝国主义”重视物质利益,但并不以物质利益作为唯一的评价指标,因为,“功用是抽象之物,真实世界不存在”[23](PVII),否则贝克尔也就不必提出“影子”价格了。而物质主义却将物质利益放在了最高地位,以物质利益为第一目标,以物质利益的获取作为唯一追求,以获得物质财富为成功的代表。所以,即使二者都重视物质利益也要看到它们之间的不同。但要看到,“经济学帝国主义”与物质主义虽有不同,却是相互支持的。
三、“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效率原则
“经济学帝国主义”崇尚效率,以效率为原则。现代经济学的学科视野是以“利益最大化”或“效率”为特点的。效率是经济学的核心概念,经济学本身就蕴涵着效率至上原则[24]。有学者认为经济学的全部内容都是围绕“效率”展开的[25]。“经济学帝国主义”作为对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继续或延伸,无疑更为注重效率原则,其不仅继承了经济学对效率的追求,还将之极致化,“以至于陷入病态的效率崇拜”[26]。例如“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代表、法律经济学家波斯纳就认为,法律的唯一目的应该是提高效率,其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指出,效率是社会生活中的唯一有价值的准则[27](P15)。因此,可以说“经济学帝国主义”是以效率为根本原则。
“经济学帝国主义”以效率为原则,对效率至上的极度推崇,使其与将效率作为唯一价值目标或高于一切价值目标的效率主义密切相关,即二者在对效率的极度推崇上是高度一致的。而抨击“经济学帝国主义”只注重效率,忽视其他诸如公平正义等价值追求,是对“经济学帝国主义”进行批评的重要观点之一。但这同样不能将“经济学帝国主义”与效率主义相互混淆。
效率主义,也可称之为效率至上主义,简单地说就是将效率看作人类社会生活中最高的价值目标,其他的价值目标都必须服从效率目标,或必须以效率为最根本的价值目标。效率主义原本是西方管理学的概念,其产生于19世纪末西方社会的科学管理运动。在西方管理科学领域,弗雷德里克·W·泰勒首倡效率主义。也就是说在西方,伴随着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发展,效率主义首先是作为经济与管理思想出现的。特别是18世纪中期以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大发展,财富积累大发展,经济主体越来越关注利润目标的实现,经济学和管理学界越来越重视效率,开始推崇效率主义。西方有学者甚至认为,企业只要遵循了效率主义,就可以有效解决劳资对抗问题[28]。而在中国社会,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响彻大江南北,人们开始高度重视效率,奉行效率主义。其典型表现就是将效率和GDP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甚至唯一标准和尺度[29]。但当前社会发展越来越表明,单纯注重效率、GDP主义,把社会发展简单看作是GDP的增长,给社会发展和国计民生带来了许多问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GDP的增长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社会发展应该是科学的可持续发展。自党的十七大明确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成为党的指导思想以来,在发展层面上,党和国家正在不断对单纯的效率主义进行扭转。
“经济学帝国主义”与效率主义是有区别的,不能将“经济学帝国主义”等同于效率主义。这种不同,除了表现在二者有不同的产生发展历程,是两种不同的理论思潮之外,主要表现在二者的价值实质不同。效率主义的最高价值是效率,以效率为最高价值目标是效率主义的实质。而“经济学帝国主义”虽然推崇效率,奉行效率至上,但效率主义不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实质。“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实质是“泛经济主义”,是将所有领域都归为经济领域的“唯经济论”,是市场价值观的泛化,其表现形式是经济分析领域的无限扩大,是经济分析方法的无限使用。这种“泛经济主义”的副产品就是效率主义,但不能说效率主义就是“经济学帝国主义”。总之,“经济学帝国主义”与效率主义相互支持、相互促进,但并不能简单等同。
总之,“经济学帝国主义”以功利主义为哲学基础、追求物质利益、以效率为原则,与功利主义、物质主义和效率主义关系密切,乃至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但却不能因此将“经济学帝国主义”等同于功利主义、物质主义或效率主义,更不能以为对功利主义、物质主义和效率主义进行批判和反思,就能够取代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批判和反思。对于“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理论误区及引发的相关问题,限于篇幅,本文不做赘述,但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注 释]
① 其与道义论(又称义务论)的一个根本区分:即是正当与善何者优先。“一般来说,强调正当优先于善,并不以善来界定正当的理论是道义论理论,而以善优先于正当,并以善来规定正当的理论是功利论理论。”参见龚群.论道义论与功利论的一个根本区分:正当与善何者优先[J].道德与文明,2008(1).
② 也有学者认为“用目的论或效用主义、功用主义诸词代替功利主义”是不恰当的,是一种失误。参见王海明.功利主义与义务论辩难[J].社会科学,2003(12).
[1][英]约翰·穆勒.功利主义[M].徐大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2]赵修义.功利主义再反思[J].探索与争鸣,2011(11).
[3]朱富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神话[J].当代经济研究,2003(3).
[4][美]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5][美]威廉.K.弗兰克纳.伦理学[M].关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6]徐大建.功利主义道德标准的实质及其缺陷[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9(2).
[7]朱贻庭.伦理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8][美]汤姆·L.彼彻姆.哲学的伦理学[M].雷克勤、郭夏娟、李兰芬、沈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9][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0]罗国杰.中国伦理学百科全书·伦理学原理卷[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
[11][美]加里·斯坦利·贝克尔.家庭论[M].王献生、王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2][美]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王业宇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
[13][美]加里·贝克尔.经济理论[M].贾拥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14]甘绍平.功利主义的当代价值[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0(3).
[15]龚群.功利与功利主义思潮[J].人民论坛,2011(1).
[16]秋风.告别“经济学帝国主义”[J].社会学家茶座,2007(3).
[17]高小勇.我们都是经济学帝国主义者[A].高小勇.经济学帝国主义(自序)[C].北京:朝华出版社,2005.
[18]卢风.启蒙与物质主义[J].社会科学,2011(7).
[19]陶文昭.后物质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发轫[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6).
[20]陈勇杰,姚梅林.物质主义与幸福感: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的关系探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
[21][法]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2]周穗明.“后现代”的选择:西方兴起后物质主义价值观[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1).
[23]张五常.经济学帝国主义[A].高小勇.经济学帝国主义(序言一)[C].北京:朝华出版社,2005.
[24]刘宝宏.经济学的边界[J].社会科学战线,2008(3).
[25]朱庆育.是一种方法,仅仅是一种方法[J].读书,1999(2).
[26]宫敬才.极端的跳跃还是极端[J].读书,2007(4).
[27][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上)[M].蒋兆康译.林毅夫校.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28]王一多、孟昭勤.从效率主义到以人为本——管理思想上的质的飞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1).
[29]王一多、孟昭勤.效率主义的谬误与危害[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12).
赵 昆,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
山东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经济学帝国主义思潮研究”(14CKSJ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