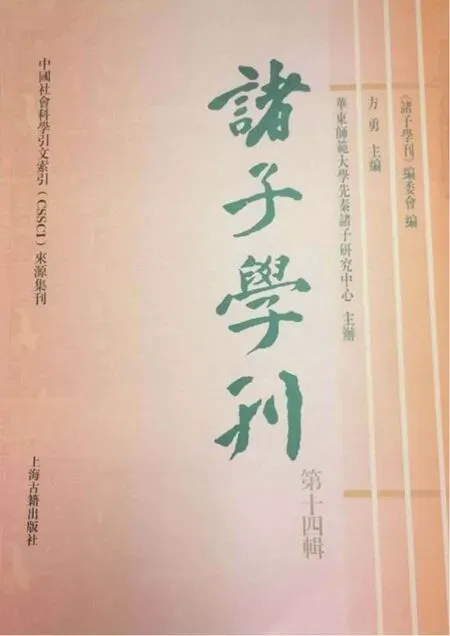人之發現與類之自覺: 晚周諸子“人禽之辨”勘會*
李智福
人之發現與類之自覺:晚周諸子“人禽之辨”勘會*
李智福
晚周諸子之學表現出強烈的人之發現和類之自覺的特色,諸子皆從人與禽獸之區别把握人、人性和人類,即所謂“人禽之辨”。學界向來推重儒家特别是孟子的“人禽之辨”,其餘諸子的“人禽之辨”則相對被忽略。事實上,諸子百家幾乎都參與了“人禽之辨”的哲學思考,在這種“人禽之辨”的哲學檢討中,人性在哲學的意義上實現了自覺,人類在哲學的意義上被發現。人禽本異,斯道不絶,諸子百家的“人禽之辨”最終矗立起人性的莊嚴和人類的尊貴。
雅斯貝爾斯所謂哲學軸心時代的理性突破,實則是人的自我突破。這種突破,在中國晚周諸子時代,自上而言,是將人從天(帝、神)中解放出來;自下而言,則是把人從禽獸中抽拔出來。前者即所謂“絶地天通”,後者則是“人禽之辨”。晚周諸子不約而同地皆從人與禽獸之區别來把握人、人性和人類。“諸子者,入道見志之書”*詹鍈《文心雕龍義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622頁。,“人禽之辨”是晚周諸子“入道見志”的邏輯起點和理論基石,幾乎所有重要的流派都涉及“人禽之辨”。他們在“人禽之辨”中發明人性,發現人類,並因此而構建起“人學”大厦,挺立起“人之爲人”的莊嚴性和神聖性,因而,“人禽之辨”成爲中國哲學的重要特色。本文對諸子百家的“人禽之辨”進行探討,以揭櫫“人禽之辨”所藴含的不同的思想和信念,考察諸子如何以“人禽之辨”爲邏輯起點來證成他們的意義世界和理想世界。本文囊括三家(儒、墨、道),平章七子(孔子、曾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莊子),勘會晚周諸子“人禽之辨”,通過對“人禽之辨”的文獻鈎稽和學理勘會,以見其思想特色,並探討“人禽之辨”對於諸子各自構建哲學體系的意義。
一、孔子(曾子)“人禽之辨”四題* 此文第一部分關於孔子是否“貴人賤畜”之問題,曾就教於《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版編審楊海文先生,并與楊老師反復商榷辯難。楊老師殷殷致意,不吝賜教,並提供楊仁山、熊十力等先生對相關研究之文獻佐證,使得我對该問題之理解更加深入,特此致謝。
《尚書·泰誓》云:“唯天地萬物父母,唯人萬物之靈。”*孔穎達等《尚書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頁。儒家的“人禽之辨”可謂源遠流長,孔子、孟子、荀子都極重視“人禽之辨”。孔子是儒家“人禽之辨”的發軔者,孟荀以下二千多年,中國的“人禽之辨”莫不能在孔子的思想世界裏找到淵源。《論語》*本文援引《論語》原文僅於引文後括號内注明章節,皆據楊伯峻《論語譯注》,中華書局1958年版。記載孔子(曾子)的“人禽之辨”至少有四則:
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别乎?”(2·7)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8·4)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18·6)
厩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10·17)
第一則,孔子看來,“孝”的内涵不是“養”,而是“敬”。犬馬皆可“養”,但不能説犬馬能“孝”,人之異於禽獸者在於有“敬”。《説文》:“敬,肅也。”《釋名》:“敬,警也,恒自肅警也。”*劉熙《釋名·釋言語》,王先謙《釋名疏證補》初刻本。孔子認爲,對父母之“孝”不僅要能“養”,更要懷揣“敬肅”之心。《論語·爲政》:“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真正的孝,是内心的“敬肅”,並因此而顯露“和豫”之“色”,孔穎達《禮記正義》注“毋不敬何允”引何胤語云:“在貌爲恭,在心爲敬。”*孔穎達等《禮記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頁。“能養而不能敬”,這恰恰是子女們對待父母之軟肋。皇侃將這段話解釋爲:
夫孝爲體,以敬爲先,以養爲後。……犬能爲人守禦,馬能爲人負重載人,皆是能養而不能行敬者,故云“至犬馬皆能有養”也。言犬馬者亦養人,但不知爲敬耳。人若但知養而不敬,則與犬馬何以爲殊别乎?*皇侃《論語義疏》,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29頁。
這裏,皇侃完全以“人禽之辨”來解釋這段文字,其又引包咸注“愛而不敬,獸畜之也”。宋明儒的解釋大多也是按照這個思路來解釋此段文字。可見,孔子以“敬”釋“孝”,可謂是一針見血,直指人心。
第二則,“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語出曾子。在《論語》中,曾子是孔子高足中爲數不多被稱“子”的弟子,“曾子”凡出現17次(另,“有子”3次,“冉子”3次,“閔子”1次)。曾子且以“孝友”著稱,因此學者多認定《論語》爲曾子或其弟子親手編次。加之聖學傳承經曾子而子思,經子思而再傳孟子,基本是先秦儒家“道統”之暗綫,多被學者接受。因此曾子在某種意義上即孔子之代言人。此處,曾子以人、鳥面臨死亡時的不同反應來揭櫫“人禽之辨”。皇侃《論語義疏》云:
言鳥之臨死,唯知哀鳴,而不知出善言,此則是鳥之常。人之將死,必宜云善言,此則是人之常也。若人臨死而無善言,則與鳥獸不異。今我將臨死,故欲出善言以戒汝也。故李充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其慎終始在困不撓也。禽獸之將死,不遑擇音,唯吐窘急之聲耳。人若將死,而不思令終之言,唯哀懼而已者,何以别於禽獸乎?”*同上,第188頁。
曾子之意爲,鳥之將死,徒感生命之終結,因此哀鳴不已,是對生命的留戀,是自發的,只是貪生懼死而已;人所高貴於禽獸者在於,人在生命終結之時,生死已然度外,而善仁道義依然在操持中,念念在在,至死不渝,這可與《泰伯》篇曾子之語相互發明:“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曾子樂善不倦、生死以之之信念實得之於孔子。《里仁》篇“朝聞道,夕死可矣”、《泰伯》篇“守死善道”、《衛靈公》篇“蹈仁而死”等都是講孔子在生死面前對“道(善)”之操持,這或許乃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之真諦,此乃是孔子與其諸位高弟“一以貫之”之道。人與禽獸之區别,在生死面前的不同態度,朗然分明。
第三則,孔子反對那些潔身自好的隱士,他們“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在孔子看來,他們避世歸隱,實則“自絶於人”而墮入“禽獸之行”。所謂“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孔子認爲,人之爲人,當有所擔當和抱負,即使亂世,亦不可逃不可避。深得夫子真傳的子路云:“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18.6)皇侃解釋云:“隱山林者則鳥獸同群,出世者則與世人爲徒旅。”*皇侃《論語義疏》,第482頁。孔子反對那些“不仕無義”的“隱士”,他們剔除了那個神聖的“義”字,逃離“君臣之倫”,没有人之爲人之擔當,剥落人倫之義務。孔子云:“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15·29)人若没有道義,即墮入禽獸之行。
第四則,《論語·鄉黨》:“厩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在一般的意義上,人的生命自當高於禽獸的生命,孔子退朝,適逢馬厩失火。馬厩本來是畜馬之所,孔子卻下意識地問人而不問馬,這表現出悲天憫人的情懷,人的生命在他看來比什麽都珍貴,皇侃解釋爲“重人賤馬”*同上,第254頁。,朱子解釋爲“貴人賤畜”*朱熹《四書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21頁。,大抵不差。後世解者卻有不以爲然者,如楊文會(仁山)或出於大乘佛教“普度一切有情”之立場而對朱子“貴人賤畜”之解不以爲然,仁山以《禮記·檀弓下》“敝帷不棄,爲埋馬也”之文獻力證孔子爲愛馬之人,否認孔子會作出“不問馬”之事,因此認爲“不問馬”三字爲後人妄添*楊仁山《楊仁山居士文集》,黄山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173頁。(標點略作調整)。孔子問人不問馬,本是人之常情,仁山之解,當是典型的“減字解經”。
熊十力先生則既反對朱注,又反對楊説。他繼承楊文會“馬從朝中駕車而歸”之説,認爲“馬不在厩可知,何須問馬”,他看來,當時的“紀録者”是“仔細留心,樸實描寫”*熊十力《十力語要》,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頁。,紀録者記下“不問馬”一語,毫無價值評判,因爲厩中早已無馬,因此孔子没必要問馬。實則,厩中有馬,實在不必是孔子之馬,故與孔子是否駕車而歸無關。皇侃云:“廐,養馬之處也。”*皇侃《論語義疏》,第254頁。厩本爲養馬之所,馬厩失火,一般人自然會想到是否傷及馬匹,孔子卻以人相問而不問及馬,正表現出他悲天憫人、人命關天的悲憫情懷,實不必迂回曲解。禽獸誠然也有生命,孔子也主張“釣而不綱,弋不射宿”(7·27),后更有孟子那種“仁民愛物”、横渠那種“民胞物與”的精神,但這與其“問人不問馬”並不矛盾,而是不同層次的問題。“貴人賤畜”是一種現實的關懷,“民胞物與”是理想的人生境界,誠然,禽獸的生命果然如人之生命一樣重要麽?孔子雖然主張“釣而不綱,弋不射宿”,但畢竟還是要“釣”、還是要“射”,因爲魚鳥畢竟是禽獸。但對於人,孔子态度截然不同。孔子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孟子·梁惠王上》)孔子最珍惜的是人的生命,他對作“俑”陪葬都如此憤恨,更何是人!而且,孔子論“仁”論“尊”都講“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記·中庸》),愛人猶有親疏之别,更何況是禽獸呢?如果認定孔子“貴人賤馬”有違他“原本具備‘仁民愛物’的圓融訴求”*楊海文《化蛹成蝶——中國哲學史方法論斷想》,齊魯書社2014年版,第112頁。,雖陳義甚高,卻未必合孔子本意。當然,若退而求其次來看,孔子亦非“賤”馬,楊仁山引《禮記·檀弓下》孔子語“敝帷不棄,爲埋馬也”,可見儒家對動物也藴含了一種憐惜之情,孟子云“君子遠庖廚”亦可作旁證,“民胞物與”是聖賢的精神氣象,但在無情的現實面前,人的生命畢竟還是要高於萬物,高於禽獸,與人相比,禽獸還是要等而下之,縱使孔子不“賤”馬,但也難以以馬之生命與人之生命等量齊觀*另外,王叔岷先生有《〈論語〉“傷人乎不問馬”新解》一文,力辟古今之解,以“後”訓“不”,認爲孔子是先問“傷人乎”,“後問馬”,孔子雖不賤馬,卻有緩急之權,是乃“聖人仁民愛物之心”(见《慕廬論學集》)。王先生雖然言之鑿鑿,但亦多牽強。汪少華先生撰寫《再論“松柏後凋”與“孔子不問馬”》(见《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2輯)一文,對王説進行一一辯難,多持之有故,言之有理,並認爲馬是當時財富之象徵,孔子“問人不問馬”是“對財的輕視,對人的仁愛”。張林傑先生撰寫《〈論語〉問馬派諸説證僞》(《孔子研究》2015年第2期)一文,對包括王叔岷先生在内的古今“問馬派”進行了全面檢討,極具説服力。。以孔孟爲代表的儒家之“仁”畢竟還是要突出人與人之間的惺惺相惜,《論語》中孔子多處論“仁”,但“仁者愛人”一語恐怕最切近其本意;《中庸》:“仁者人也。”許慎《説文》:“仁,親也,從人二。”鄭康成認爲“仁”是“以人意相存問之言”。可見,晚周秦漢數百年間,幾代學者都是“以人釋仁”,洵非偶然。
總的來説,孔子(曾子)的“人禽之辨”發明人性之高貴,高揚人倫之莊嚴,這無疑是對當時世道澆漓、人同禽獸的思想匡正,也是對早期法家“治人如治水潦,養人如養六畜,用人如用草木”*黎鳳翔《管子校注》,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211—212頁。的學術反撥,宋儒言“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朱熹《朱子語類》卷九十三,朱傑人等《朱子全書》第十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096頁。,洵非虚矯之論。孔子“人禽之辨”,發明人性,儒家諸德大體皆備。其爲中國哲學靈根深植,實開孟、荀“人禽之辨”之先河,後來的孟子、荀子各開門户,獨出機杼,更入精微,並以“人禽之辨”各自建立起自己的哲學體系。
二、孟子:“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
諸子中最盛言“人禽之辨”的是孟子,“人禽之辨”對其哲學之建構又極重要,其在思想史上之影響亦最大,中國士大夫的精神信念“不爲聖賢便爲禽獸”*李翰章編纂《曾文正公全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74頁。乃在孟子思想的“人禽之辨”中奠基。古今學術界對孟子“人禽之辨”爲論甚夥,其中不乏精覃之作,但主要集中在“人性”與“獸性”不同之方面,實則孟子之“人禽之辨”不僅就“性”言之,更有其他方面。本文將對孟子的“人禽之辨”作具體之分梳,以考察其“人禽之辨”之不同面向。
其一,以“性”言之,孟子認爲人性爲善,獸性爲惡。“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但此“善”雖“幾微”,卻成爲人與禽獸最根本之區别。此“幾希”之善如水之源泉,如果能盡極“存養之道”,於内可成就聖賢人格,於外則可實現天下之大化,否則,即與禽獸無異。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本文援引《孟子》文獻,皆自楊伯峻《孟子譯注》,中華書局1960年版。(8·19)
其二,以“心”言之,人心爲善,禽獸之心爲惡。孟子認爲人有“惻隱之心”、“恭敬之心”、“羞惡之心”、“是非之心”等所謂“四心”,禽獸則無,“四心”缺一則落入禽獸之行。“四心”中最爲孟子所推重的是“惻隱之心”,此人所獨有的“惻隱之心”是架構其一整套成聖成賢學説的基石,即學界所謂“性由心顯”、“以心注性”、“以心善言性善”。以下是孟子言“心善”的文獻: 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3·6)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弗敬,獸畜之也。”(13·37)
此“四心”中之“恭敬之心”,又爲孟子在君臣關係中特别強調,孟子反對君對臣以“犬馬蓄之”(10·6),而強調君對臣要有十分“恭敬之心”。孟子強調君對臣的“恭敬之心”,實則即所謂“以德抗位”,孟子云:“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8·3)。這表現出儒家士大夫高自標持、志抗云表的精神信念,標誌着中國士人之獨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意識的徹底覺醒。
其三,以“理”言之,人能“經權之辨”,禽獸則無。人有自覺運用自己理性的能力對是非善惡作出評價,並付諸行動,禽獸則無此能力,理性思考是人類特有的能力。“嫂溺援手”即是此證: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7·17)
又,孟子看來,陳仲子即使餓死也不偷吃李子,以爲兄長接受世俸不義而不居兄室,以爲鵝叫聲不雅而不食鵝肉等行爲,也是迂腐之舉,不知經權之變。孟子看來,“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6·10),换言之,不知經權之辨,不敢大膽運用理性進行思考,泥執所謂絶對原則,則往往會適得其反,有墮入“蚯蚓之行”的危險。
其四,以“思”言之,人有自覺的自我意識,能對自我之行爲進行反思,而動物則不能,這種能不能“自反”、有無“自反”之能力也是孟子“人禽之辨”的重要内容: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横逆,則君子必自反也: 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8·28)
孟子之意是,面對“横逆之人”之挑釁,首先要自我反思,如果認定“仁”、“禮”、“忠”等在我,則可認定對方是“妄人”;若對方一味“横逆”,不知自我反思,即距禽獸不遠。孟子云:“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揣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3·2)能否自我反思,是孟子“人禽之辨”的重要内容,此與孔子“一日三省吾身”有某種淵源關係。
其五,以“養”言之,人能自覺的存養“良心”,存養“夜氣”,從低級的感觀欲望中解放出來,培養至大至剛、集義所生的“浩然正氣”,這些“存養工夫”爲人類所獨擅,而禽獸則没有此等能力,人若不能及時存養“良心”和“夜氣”,則“違禽獸不遠”。
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11·8)
其六,以“禮”言之,人類之愛有“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人倫之禮有“君臣之義”、“男女之别”,這在禽獸世界是毫無分别的。孟子看來,墨子“兼愛”是“無父”;楊朱“爲我”是“無君”,因此楊墨之學是“禽獸之學”。孟子云: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横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6·9)
孟子論楊墨,難免有斷章取義之嫌,似有違其“以意逆志”之原則,但卻有矯枉過正之苦衷。他反對墨子“兼愛”,實則是將高不可攀的“兼愛”理想落實爲一種立足人間世、世間情的現實主義原則;其反對楊朱“爲我”是對已經被嚴重誤解的楊朱思想和天下因“爲我”而“忘義”的世風進行一種釜底抽薪的批判,這裏表現出孟子濃厚的“天下溺而受之以道”的匡正思想。孟子云:
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5·4)
總而言之,“人禽之辨”最爲孟子所嚴防。以上我們對孟子“人禽之辨”的六類劃分,皆涉及孟子所認爲的人之所以爲人的“大本大原”,並因此而建立起一整套“内聖外王”的思想系統。明代思想家吴廷翰云:
聖賢扶正立教,取其可以爲天下後世訓者,所以爲正也。使告子之説行,則人將以性爲惡、爲僞、爲在外、爲與物同,而人類化爲禽獸矣。猶幸而有孟子之説在,則人皆以性爲善、爲真實、爲在内、爲與物異,而仁義之道明,人類不至於禽獸。其爲功也孰大焉!*吴廷翰《吴廷翰集》,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30頁。
吴氏之論,強調了孟子“人禽之辨”之於人、人類、人倫的普世意義。孟子將“人”從“禽獸”世界徹底隔離了出來,以心爲燈,直擊私欲之黑幕;以性爲照,不爲禽獸之草昧,爲人之自我向“真善美”之境界提升鑄就了基石,奠定了信念,所謂“人皆可爲堯舜”是也。韓昌黎認爲孟子嚴防“人禽之辨”,其功“不在禹下”*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14頁。,可謂肯綮之言,大禹救天下,孟子救人心,身與心合,乃可謂是人,若無此心,禽獸而已。
三、荀子:“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以二足無毛也,以其有辨也”
儒家另一位極重“人禽之辨”的思想鉅子是荀子,其嚴防“人禽之辨”實不亞於孟子。荀學是“性樸論”還是“性惡論”,學界有争議*周熾成《儒家性樸論: 以孔子、荀子、董仲舒爲中心》,《社會科學》2014年第1期。,但荀子並没有從“本性”的角度來揭櫫“人禽之辨”卻是事實。荀子“人禽之辨”,分别以“辨(禮)”、“義”、“敬”、“群”、“孝”等五義言之,在荀子看來,此五者爲人類所獨有,而禽獸世界則無。
其一,荀子認爲,人倫有辨(分),即有貴賤尊卑之分、父子夫婦之别,此即所謂“禮”,禽獸則無。人與禽獸之别,不在於感性的形相即“二足而無毛”,而在於人能辨别親疏、貴賤、高下、美醜、羞恥等,並能以“禮”爲裁制,作出相應、適度、自覺的選擇。禽獸世界是草昧不分、牝牡無别的野蠻世界,而人類則有辨、有分、有禮,並能在聖人之“禮”的教化中,離開野蠻狀態,走向“始乎誦經,終乎讀禮”的文明。人類因“辨”而有“分”,因“分”而有“禮”,在荀子看來,這是人類脱離蒙昧狀態走向文明的標誌。《荀子·非相》云:
人之所以爲人者何已也?曰: 以其有辨也。饑而欲食,寒而欲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則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以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狌狌形狀亦二足而無毛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胾。故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獸有父子,而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於分,分莫大於禮,禮莫大於聖王。*本文引《荀子》文獻,皆自梁啓雄《荀子簡釋》,中華書局1983年版。
按,人禽之辨,荀子三致其意。《禮記·曲禮上》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别於禽獸。”*孔穎達等《禮記正義》,第15頁。此處論“人禽之辨”明顯與荀學有某種淵源關係。
其二,荀子認爲,人有“義”而禽獸無。“義”在荀子這裏是指人對是非善惡的判斷、甄别能力,這種判斷能力是人類理性的力量,並因此而付諸實踐。這個“義”近似亞里士多德所講的人特有的對“善”的感覺,亞里士多德云:“和世界其他動物相比,人的獨特之處就在於,他是唯一具有善與惡、公正與不公正以及諸如此類感覺的動物。”*亞里士多德《政治學》,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頁。亞里士多德此處所講的,恰恰是荀子所謂的“義”。荀子云:
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王制》)
有狗彘之勇者,有賈盜之勇者,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争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畏衆強,牟牟然唯利飲食之見,是狗彘之勇也。(《榮辱》)
其三,荀子看來,人類能“群”而禽獸則不能。荀子認爲,人類有辨、有分、有禮、有義,這些理性的力量爲人類的“群”打下了基礎,這個“群”之意是指人類的社會性、組織性和政治性,“群”意味着人類要有組織,有組織則不能無“君”。“群”強調的是人類存在的社會之維,禽獸不能“群”,而人類則能“群”,“群”在人類進步、脱離洪荒、戰勝禽獸方面起根本作用。荀子云:
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爲用,何也?曰: 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 分。分何以能行?曰: 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王制》)
其四,荀子認爲,人能“敬”,禽獸則不能。“敬”是對仁人賢士的尊重和肯定,是一種發自肺腑的崇尚、畏慕之心。荀子看來,無論面對聖賢還是不肖,首先都要持有一種“敬”的精神,否則就會墮入禽獸之倫。這種“敬”實則是“禮”和“義”的心理、精神狀態,這是對人類比較高的道德要求,與孔孟“恭敬之心”相似。荀子云:
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矣。……故仁者必敬人。(《臣道》)
其五,荀子看來,人能“孝”而禽獸不能。禽獸對於父母没有“孝”的意識,但人類卻能“孝”,人類之“孝”的題中之義則是在父母生時能“敬”,死時能“哀”,這似與前文所引孔子論“孝”有某種淵源關係。更難能可貴者,荀子論“孝”超越孔孟的地方在於他更強調“從義不從父”這個原則。以下是荀子論“孝”之文獻:
喪禮之凡,變而飾,動而遠,久而平。……一朝而喪其嚴親,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則嫌於禽獸矣,君子恥之。故變而飾,所以滅惡也;動而遠,所以遂敬也;久而平,所以優生也。(《禮論》)
以上五論,可見荀子“人禽之辨”之大體内容。荀子云:“草木疇生,禽獸群焉,物各從其類也。”(《勸學》)荀子論“人禽之辨”更強調的是“人類”作爲一個“類”的“社會之維”,如前文所引《王制》篇之言,他認爲天地萬物從水火、草木、禽獸到人類,表現出一個從低級到高級的遞高序列,人是這個萬物序列金字塔之制高點,荀子在中國思想史上第一個提出“人爲天下最貴”這一命題。荀子“人禽之辨”與孟子相比,一方面,他與孟子側重於“道德個體”之覺悟相比,更側重發明“人倫社會”作爲一個“類”之文明和進步,章太炎云:“若以政治規模立論,荀子較孟子爲高。”*章太炎《國學講演録·國學概論》,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9頁。十分中肯。荀子認爲人具有“群”性和亞里士多德強調“人天生是一種政治動物”*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第11頁。極爲近似;從另一方面來看,荀子“人禽之辨”的底色與孟子並無必然之判,也表現出對人、人倫和人道的高揚,對人類神聖、人倫莊嚴之持護,他反對它囂、魏牟之學時云“縱情性,安恣孳,禽獸行”(《非十二子》),這不是和孟子將“楊墨之學”視爲“禽獸之學”如出一轍麽?荀子雖然以“人性惡”爲後世之詬病,但檢討其“人禽之辨”中對人、人類、人倫之高揚,當明其言“人性惡”之苦衷,當是對人之一種警醒,直面人性之惡,亦需要莫大之勇氣。韓昌黎云荀學“大醇而小疵”*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第37頁。,可謂知言之論,荀學之根荄,實在與申韓李斯無必然之關係。
四、墨子:“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
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墨出於儒,又反撥儒,傅斯年先生所謂“墨家所用之具全與儒同,墨家所標之義全與儒異”*傅斯年《傅斯年“戰國子家”與〈史記〉講義》,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9頁。正是此意。墨與儒之間表現出順逆兼有的複雜關係,這種複雜的順逆關係在墨子的“人禽之辨”中也表現了出來。墨子論“人禽之辨”主要有二。
其一,墨子繼承了儒家傳統的思想,強調人類有“義”、“節”和“禮”,這在禽獸則無。所以他倡導天下之“公義”,此即所謂“尚同”。墨子看來,“公義”是社會共同體共同認可的價值尺度,人類只有以這種“公義”作爲是非善惡之標準,乃能免於禍亂與傾軋。墨子通過倡導人類之“公義”而把人與禽獸區别開來,實則是認識到人是社會性的存在,這實爲後來荀子“人能群而禽獸不能群”思想之先鞭。以下是墨子以“公義”論“人禽之辨”之文獻:
方今之時,復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兹衆,其所謂義者亦兹衆。……天下之亂也,至如禽獸然,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尚同中》)
其二,墨子察覺到人類高於禽獸的另一個重大標誌即人類能從事生産勞動(“賴力”),而禽獸則不能(“不賴力”)。墨子認爲,禽獸生存靠的是自發、自然的條件,比如鳥以羽毛禦寒,麋鹿以蹄腿驅蚤,逐水草而飲食,皆得之自然,而不用從事紡績、耕耘、製造等生産勞動。但人類卻能“耕稼樹藝”、“紡績織紝”,生産勞動將人類從蒙昧狀態中解放了出來。既然勞動是人類的特有能力,所以人應該積極從事生産勞動,不可不勞而獲,因此墨子崇尚勞動,以“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見《莊子·天下》。本文援引《莊子》原文,皆據郭慶藩《莊子集釋》,中華書局1978年版。的大禹爲偶像。李澤厚先生指出:“強調生産勞動創造社會財富,是墨子思想基礎。”*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2頁。墨學這個基礎,正是以“人禽之辨”爲邏輯起點的。以下是墨子以“賴力”論“人禽之辨”的文獻:
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異者也。今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爲衣裘,因其蹄蚤以爲絝屨,困其水草以爲飲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樹藝,雌亦不紡積織紝,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非樂》)
可見,墨子的“人禽之辨”對儒家傳統的“人禽之辨”有繼承,有背反,有補充,是一種相反相成的關係,但更多的應該是補充。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韓昌黎説“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第40頁。以“精神貴族”自居的孔孟之道恰恰有忽略“生産勞動創造社會財富”這一社會根基的危險,與孟子“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孟子·滕文公上》)之説相比,墨子“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之言無疑是誅心之論。墨子強調人類“賴其力者生”,時刻警醒作爲“四民之首”、以精神貴族自居的知識分子不要成爲社會蛀蟲的“五蠹之首”*韓非子作《五蠹》,“五蠹”之首即學者,亦即知識分子。韓非子云:“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説,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爲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韓非子·五蠹》)。
五、老子與莊子:“人禽之齊”與“人禽之辨”的“吊詭”
道家追求“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以天合天”(《莊子·達生》),因此至少在形式上没有儒墨那麽色彩強烈的“人禽之辨”。相反,老子與莊子在很多時候更強調“人禽之齊”。如老子云:“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老子》五章)在這個意義上,老子哲學表現出芻狗與百姓、人與萬物齊平的價值立場,此即王弼所謂“萬物萬形,其歸一也”*樓宇烈《王弼集校注》,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17頁。。“芻狗”並不是禽獸,而是一束稻草紮成之犬,王弼注云:“聖人與天地合其德,以百姓比芻狗也。”*同上,第14頁。老子之學似乎没有表現出對禽獸的濃厚興趣,他“芻狗百姓”的立場實則是反對統治者過於“有爲”而對百姓生活的干擾,而要讓統治者“輔萬物之自然”而不要“妄爲”,老子並非無情不仁,也不是芻狗萬物,這實則也即後世莊子所謂的“吊詭”。
及至莊子,更強調“萬物一齊,孰短孰長”、“以道觀之,物無貴賤”(《秋水》),因此,在莊子哲學中,“人”與“禽獸”在形式上並無高下之别、貴賤之分,而是表現出人與禽獸在存在價值上應該平等、在生存方式上應該一致、在生存場所上應該共存等一系列“去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如莊子云:“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併。”(《馬蹄》)“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山木》)《齊物論》更是援引大量禽獸與人類的不同選擇來證成人與禽獸的區别,在價值上並無高下之分。
因此,莊子之學極容易被解釋爲“禽獸之學”,孟子罵楊墨爲“禽獸”,莊孟並世,雖無文獻記載二子相及,但孟子辟楊墨,理所當然亦會辟莊周。荀子説“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解蔽》),揚雄説“莊楊蕩而不法”*汪榮寶《法言義疏》,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280頁。,晉人王坦之云:“莊子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莊生作而風俗頽。”*王坦之《廢莊論》,謝祥皓等《莊子序跋評論輯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32頁。這些對莊子的不滿,大概或多或少都與莊子把人視爲“禽獸”有關。明儒羅明祖則直接認爲莊子要“闔一世之人”爲“禽獸”,莊學是“教人等於禽獸”的“禽獸之學”:“(莊子)謂天下而可無是非也,則必闔一世之人而罔兩焉、蝴蝶焉、蛇蚹焉、蜩翼焉,亦庶乎其可也,豈其然。”*羅明祖《羅紋山全集》卷十一,明末古處齋刻本。然而,莊子之學,果然是“禽獸之學”,讓人淪爲禽獸麽?諒莊子也不會將人類等同於禽獸,雖在形式上言説“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天道》),但其深刻的含義絶非“混同人禽”,讓人淪爲禽獸。劉熙載論莊子“寓真於誕,寓實於玄”(《藝概·文概》),莊子的荒誕之中實則隱含着真誠而嚴肅的哲學立場。莊子消解儒墨“人禽之辨”的深意在於:
其一,莊子看來,與人類相比,禽獸無智巧,因此也就無掠奪,無憂慮,無傾軋。渾樸未分的原始世界是人類的失樂園,彼時大道周流,歲月静好,萬物和睦。莊子把現實苦難的根源歸本於文明的進步,因此他呼吁回歸“萬物群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馬蹄》)的唯美世界,這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的原始社會代表了莊子思想中永恒的鄉愁。
其二,莊子看來,大千世界中的飛鳥、游魚、蝴蝶等無憂無慮,乃是因爲他們没有執着於權勢名利。章太炎在《齊物論釋》中根據《瑜伽師地論》將世間分别分爲“有相分别”和“無相分别”,“有相分别”即有意識的名相分别,爲人類所專擅,這種分别有“計度尋思”,因此會招致痛苦;“無相分别”爲蟲獸草木之分别,“今世説生物者,謂蟲獸草木種種毛羽花色香味,或爲自保生命,或爲自求胤嗣,而現此相,然彼此豈如人類能計度尋思邪”*章太炎《章太炎全集·齊物論釋定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9頁。?莊子云:“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庚桑楚》),在莊子看來,蟲子正是“天”的象徵。因此,章太炎解釋云:“然物類最劣者,唯是動不得已,金石悉然,蟲亦近之。委心任化,此唯蟲能蟲,心無勝解,此唯蟲能天,聖人樂天,亦效是爾。”*同上,第121頁。换言之,蟲子之欲求皆自然而然,並無積慮憂思,因此它既是“蟲”,又是“天”。一如《逍遥遊》所云:“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他們滿足了基本的生存條件之後没有過多的欲望。莊子“齊一人禽”的意義在於:“在人類學的意義上,解構人性中的負面要素,如權勢名利的追求,這些恰好是在動物身上看不到或者表現不明顯的。”*陳少明《人、物之間——理解莊子哲學的一個關鍵》,《中國文化》2011年第2期。莊周夢蝶,不分周蝶;濠上觀鰷,無隔人魚。
其三,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法自然”,莊子稱之爲“以天合天”。老莊筆下的“自然”,絶非今所謂大自然,而是哲人之“玄鑒”與天地宇宙經過“玄之又玄”的交感體貼之後“道之世界”,這個“自然”世界呈現出萬物和静、鬼神不擾、日月合節的原始和諧圖景。在這個世界裏,“禽獸世界”已經不是優勝劣汰、弱肉強食的野蠻狀態,而是呈現出群生連屬、和諧共生的平和圖景,因此人類應該走出屠殺掠奪的人類世界,而去效法天地宇宙中的原初和諧。莊子云:“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天道》)因此,莊子“人禽一齊”,其實是對原始和平、自在的呼唤。
其四,禽獸生活在山林川澤之中,莊子希望人們去親近天地山川,所謂“禽獸可繫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馬蹄》),莊子呼吁人類應該走出狹隘的人類中心世界,實則是將人類被狹隘私欲遮蔽的天地宇宙打開,實現一種神來物集、萬象在旁的人生高遠之境,去發現“天地之大美”,在天地宇宙中自由自在地生存,而不是斤斤計較於生死得失、善惡利害。
可見,莊子“人禽之齊”並不意味着讓人“模仿動物”,也不是“仿生哲學”*魏義霞《莊子的動物情結與仿生哲學》,《學海》2013年第1期。。莊子亦非就動物論動物而“主張動物有其獨立的價值與權利”*方旭東《“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新議——基於當代動物權利論争的背景》,《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至少莊子本意恐非如此。事實上,如我們上文所言,莊子“人禽一齊”是表現出一破一立的傾向: 其所破的人類文明的盲目性和人類智巧的荒唐性,警惕文明和智巧會走到文明的反面;其所立的是生命的高情遠意,脱離低級的感觀欲望而當馳騖於更高遠的精神追求,在天地宇宙的廣大之中審視自我的存在,從利益焦灼的狹隘世界中抽離出來。後者,不正是“人禽之辨”嗎?實則,莊子哲學中滲透着濃厚的人之自覺意識,比如,人有時間意識,而禽獸則無,人能意識到“生死亦大矣”(《田子方》),禽獸則無生死意識;又比如,人有精神,禽獸則無。莊子云:“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天下》)禽獸是没有“精神”的,因此也不能“與天地精神往來”,有無“精神”實則也是莊子的“人禽之辨”。同時,對於仁義道德這些人世的普世價值,莊子也是維護的,但他反對“虎狼之仁”的狹隘之仁,而呼吁“至仁無親”;他反對“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呼吁大仁大義;他反對沽名邀譽之仁,而呼唤世界的真情。在此意義上,莊子實則也是嚴防“人禽之辨”的,莊子的“人禽之辨”深埋於他的“人禽之齊”之中,這其實是莊子哲學叙事方式的“正言若反”的“吊詭”使然。如果不能深入體味這種“吊詭”之邏輯的個中三昧,簡單將莊子之學視爲“禽獸之學”,難免會得其皮相,忽略他“荒唐之言”背後的“莊嚴之意”,往往走會向莊子的反面。莊子由“人禽之齊”而走向“人禽之辨”也就是章學誠所謂“倚伏之理”(《文史通義·質性》)的另一種表現。
莊子的“人禽之辨”強調的是人對自我生命的自覺,人高於禽獸者在於人對精神的追求,對永恒精神的嚮往。這迥異與孔孟對人性之自覺、荀子對人類社會性之自覺、墨子對人類功利主義之自覺。莊子眷戀的是生命本身,強調的是生命的自在。
結 語
如本文所分析,晚周諸子哲學的突破實則是人的自我突破,諸子百家對“人禽之辨”都給予了充分的關注,並進行了相應的論證。“人禽之辨”在他們的哲學體系中各自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表現了他们對人、人類、人倫的自覺。孔孟突出的是人性的自覺,強調的是人高於禽獸者在於“有善端”的精神信念,魏晉名士阮籍斥“殺母者禽獸不如”是對他們的一次生動回應;荀子則更強調的是人的社會之維,突出人是社會性的存在,人高於禽獸者在於“人有義”、“人能群”;墨子則突出“生産勞動創造社會財富”這個人類生存的底綫,因此強調人類高於禽獸之處在於人類“賴力”而生;老莊則以其一貫的“吊詭”方式在形式上叙説“人禽一齊”,但其深層的底色卻在抒發人對生命的自覺、對自由生存的企慕、對永恒精神的追求,這些是禽獸所不具備的,也是人高於禽獸之所在。諸子論“人禽之辨”,皆獨出機杼,各有所長,展現了思想的豐富性和複雜性,在中國思想史上影響深遠,孔孟的“人禽之辨”奠定了儒家士大夫的精神信念,壁立千仞,至大至剛;荀子的“人禽之辨”奠定了人類存在的社會之維,實已藴含了“社會契約論”的萌芽,其強調“群”的概念對中國的政治哲學産生重要影響,直到嚴復翻譯英國古典自由主義者约翰·密爾的《論自由》依舊借用荀子“群”這一概念(《群己權界論》);墨子“賴力”之學正可彌補孔孟儒學高自標持爲“精神貴族”之不足,近代章太炎推崇顔元之學實則是推崇其中深刻的墨子精神*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第72頁。;老、莊由“人禽之齊”最終走向“人禽之辨”,既充滿了對所謂人類文明的批判精神,又表現出了人類對超越自我、向天地宇宙回歸的高遠之情。
蒙培元先生指出:“中國哲學是關於人的學説,是關於人的存在、意義和價值的學説。”*蒙培元《中國哲學主體思維》,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頁。諸子“人禽之辨”莫不歸本於對“人”之發現,對“類”之自覺。人、人性、人類、人倫的莊嚴在“人禽之辨”中樹立。人禽本異,壁立千仞;斯道不絶,朗照洪荒,諸子百家的“人禽之辨”最終矗立起人性的莊嚴和人類的尊貴。不可否認的是,儒家特别是孟子基於“人性論”的“人禽之辨”最能體現出人之爲人的大本大原。釋教講“一念成佛,一念成魔”,這種“佛魔之辨”可與孟子“人禽之辨”相發明。孟子“人禽之辨”更深刻的意義在於警醒人類,時刻當心内心之一念,人是“人”而不是“禽獸”,一念之間卻往往成爲萬惡之淵藪。因此,明儒劉蕺山在《人譜》中指出:“敬肆之分,人禽之辨也。此證人第一義也。”*劉宗周《劉宗周全集》第2册,《語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頁。蕺山之論,近接陽明,遠祧孟子,以“人禽之辨”爲“證人第一要義”,良有以也。
* “勘會”,即比較研究之意,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册),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88—189頁。
關鍵詞 諸子 人禽之辨 人性 人類
中圖分類號B2
作者簡介李智福(1982— ),男,河北井陘人。哲學博士,西北政法大學哲學系講師。研究方向爲中國古典哲學、經典與解釋。已於《中國哲學史》《周易研究》《鵝湖月刊》《光明日報》(國學版)等刊物發表論文數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