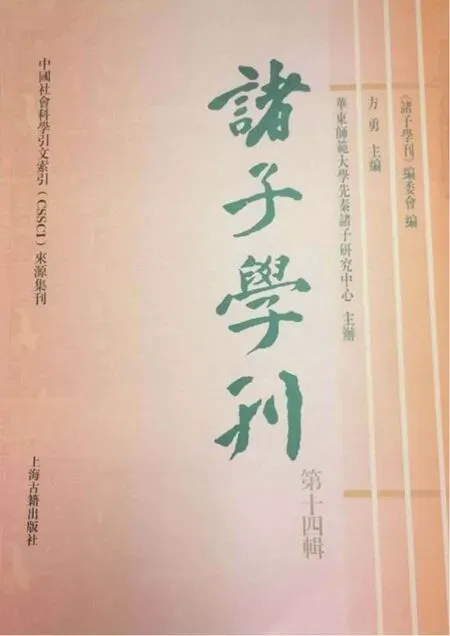《養生主》篇末句解
王鍾陵
《養生主》篇末句解
王鍾陵
《養生主》末句有兩個難點:“爲薪”與“火傳”是何意?何謂“指”?對於前一個難點莊學史上主要有以下七種解釋: 釋“爲薪”爲“前薪”,釋“爲”爲“取”,以“有涯”、“無涯”釋“薪”、“火”,以形神釋“薪”、“火”,以佛教“四大”、“元神”概念解釋“薪”、“火”,以“大道”釋“火”,以“化”釋之。關於後一個難點。在莊學史上有兩種相關聯的解釋占主導地位: 手指與指着,一爲名詞,一爲動詞。朱桂曜、聞一多則以“脂”釋“指”。《莊》書中的物字往往代指人和物兩者,指人也時常用物字。這在《齊物論》中已有其例。因而,此處“指”字即代指個體生命。火喻生命,“指窮於爲薪”者,是説個體的生命之火像薪一樣是有盡的,“火傳也,不知其盡也”,則是説生命之火的流轉是無盡的。要之,《養生主》末句,喻寫生命的周流。其在表達上的特色,便是在比喻中化入了名辯論題中的詞語。
一
“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是《養生主》篇的末句,這是本篇一個歧解衆多的句子,歷代詮釋大體圍繞着兩個難點進行:“爲薪”與“火傳”是何意?何謂“指”?
對於前一個難點莊學史上主要有以下七種解釋:
第一,釋“爲薪”爲“前薪”。郭注:“窮,盡也;爲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而不絶;明夫養生乃生之所生也。”*郭慶藩《莊子集釋》卷二上,第一册,中華書局1961年1版,第130頁。在文字的訓釋上,郭注顯然不通,成玄英衍之欲使其通:“爲,前也。言人然火,用手前之,能盡然火之理者,前薪雖盡,後薪以續,前後相繼,故火不滅也。亦猶善養生者,隨變任化,與物俱遷,故吾新吾,曾無係戀,未始非我,故續而不絶者也。”*郭慶藩《莊子集釋》卷二上,第一册,中華書局1961年1版,第130頁。
第二,釋“爲”爲“取”。俞樾批評郭注:“此説殊未明瞭,且‘爲’之訓‘前’,亦未知何義,郭注非也。《廣雅·釋詁》:‘取,爲也。’然則‘爲’亦猶‘取’也。‘指窮於爲薪’者,指窮於取薪也。以指取薪而然之,則有所不給矣。若聽火之自傳,則忽然而不知其薪之盡也。郭得其讀,未得其義。《釋文》引崔云:‘薪火,爝火也’,則並失其讀矣。”*俞樾《莊子平議》,嚴靈峰編輯《莊子集成續編》第三十六册,(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版,第14—15頁。俞樾以“取”釋“爲”,似乎在字詞上能説通了,卻没有説明它的寓意是什麽,且又將全句的意思説成是火使薪盡。俞樾的訓釋往往見字而忘義,比較篤實,不能超凌。俞樾忽視了林希逸早就説過:“此生死之喻也,謂如以薪熾火,指其薪而觀之,則薪有窮盡之時,而世間之火,自古及今傳而不絶,未嘗見其盡。”*林希逸《南華真經口義》卷四第十,第142頁,嚴靈峰編《莊子集成初編》第七册,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年版。《莊子集成初編》與《莊子集成續編》每册所收書,各自編排頁碼,一書如跨册,則頁碼亦跨册連續編排。“生死之喻”四個字抓住了這幾句與上文的關係。但“指其薪而觀之”的説法,則未免生硬。葉玉轔譯曰:“用手指來折斷樹枝做柴燒,柴有完的時候,但是火可以傳續下去,没有窮盡的時候。”*葉玉轔《白話譯解莊子》,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頁。折斷樹枝,即是取柴。與俞樾一樣,葉玉轔也没有説明其寓意爲何。
第三,以“有涯”、“無涯”釋“薪”、“火”。奚侗持此論,其曰:“爲,猶助也。指之窮於助薪,有涯者也;火之傳也,無涯者也。以有涯隨無涯,故不知薪之盡也,亦殆而已矣。此設譬以申篇首之義,自來注家均未得其旨。”*奚侗《莊子補注》,《莊子集成續編》第四十册,第27頁。雖然話説得挺自得,但於文本上實無根據。奚侗並没有抓住《養生主》篇乃生命哲學論這一本質,只就個别論點加以聯想耳。劉武説:“歷來修詞家,均以薪傳爲師弟傳受之喻,謬誤相承,由來已久,不知此段以薪喻生,以火喻知,以薪傳火喻以生隨知。蓋薪有盡,而火無窮,以薪濟火,不知其薪之盡也。以喻生有涯而知無涯,以生隨知,不知其生之盡也。蓋儆人不當以生隨知也,即證明首段‘吾生也有涯’四句。”*劉武《莊子集解内篇補正》,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84頁。中華書局將王先謙《莊子集解》、劉武《莊子集解内篇補正》合編爲一書,而頁碼各自編排。劉武此説顯然同於奚侗,不過,稍加詳密耳。然而,劉武回避了對“指”字的詮釋,文句尚未能貫通,又何以能視之爲《莊》文本意。
第四,以形神釋“薪”、“火”,此釋從者最多。林雲銘釋此句云:“喻形有死而神無死。”*林雲銘《莊子因》,《莊子集成初編》第十八册,第82頁。宣穎説:“夫形萎而神存,薪盡而火傳,火之傳無盡,而神之存豈有涯哉!”“神字是此篇之主,卻不曾説出,止點火傳二字,使人恍然得之。”*宣穎《南華經解》卷三,《莊子集成續編》第三十二册,第92頁。馬魯注曰:“薪喻形,火喻神。薪以然火,薪無不盡,而火之傳延無窮。”*馬魯《南華瀝》,《莊子集成續編》第三十四册,第89頁。劉鳳苞也説:“形有盡而神無盡,如火之傳於薪,薪有盡而火無盡也。古今道統相承謂之薪傳,意本於此。”*劉鳳苞《南華雪心編》,《莊子集成初編》第二十四册,第127頁。王先謙亦注曰:“形雖往,而神常存。”*王先謙《莊子集解》,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31頁。陳壽昌則直取宣穎之語爲注曰:“喻形委而神存也。”*陳壽昌《南華真經正義》,《莊子集成續編》第三十七册,第58頁。然而,離形常存之神,不獨非“内篇”之義,亦非外、雜篇之義也。《刻意》篇頗重於神,然所述乃守神之義:“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莊子·刻意》,《莊子集釋》卷六上,第三册,第546頁。這是要求形神相合。
今之人中,王叔岷亦取形神義,他對俞樾的解釋有肯定,有批評,其曰:“俞氏釋‘爲薪’爲‘取薪’,蓋是,‘不知其盡’,謂不知火之盡,俞氏釋爲‘不知其薪之盡’,未審。”*王叔岷《莊子校詮》上册,第114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發行、臺灣商務印書館代售1994年版。王叔岷以爲:“薪喻形,火喻心或神。”他注“指窮於爲薪”曰:“喻養形有盡。”注“火傳也,不知其盡”曰:“喻心或神則永存。”*同上。鍾泰説:“盡者年而不盡者性。有涯之生,别有無涯者在也。”*鍾泰《莊子發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3頁。整本《莊》書中哪有離開個體生命的無涯的“性”?離形之性實即離形之神耳。陳鼓應認爲“指窮於爲薪,火傳也”是比喻“精神生命在人類歷史中具有延續的意義與延展的價值”*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上册,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03頁。。仲兆環襲用陳氏此語*仲兆環、車子、劉玉香、知意譯注《南華經》,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頁。。“精神生命”一語按通常的理解即指精神,因此這仍然説的是一種離形之神。傅佩榮“解讀”云:“‘薪盡火傳’之喻中,‘薪’是指人的形體,‘火’是指人的心神所領悟的智慧。這才符合‘養生’的真正意旨。”*《傅佩榮解讀莊子》,臺灣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57頁。“火”指心神所領悟的智慧,那麽心神亦即精神是什麽呢?這完全是不通的解釋。還説“這才符合‘養生’的真正意旨。”薪盡了,亦即個體生命都不存在了,還有什麽生可養?
第五,以佛教“四大”、“元神”概念解釋“薪”、“火”。形神之義很容易同佛教學説相關聯。陸西星説:“薪喻四大,火喻元神。薪則不可謂此薪爲彼薪,火則不可謂此火非彼火,達觀者可以無變於死生之故矣。”*陸西星《南華真經副墨》,《莊子集成續編》第七册,第144頁。焦竑則直以佛典作解釋:“按佛典有解此者曰:‘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焦竑《莊子翼》,《莊子集成續編》第十一册,第127頁。薪火之喻,在兩晉南朝的儒佛争論中,早已被引用過。神明不滅,本即佛教要義。所謂“元神”者,是中國傳統的“元氣”概念與“神明”概念的結合。《陰持入經》卷上云:“身爲四大,終各歸本,非己常寶,謂之非身。”*《大正藏》第三十三卷,第10頁。《大正藏》,全名爲《大正新修大藏經》,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人編,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出版部印1990年版。由此,内涵爲地、水、火、風四種元素以及其堅、濕、暖、動之屬性的“四大”概念,同以薪盡喻人亡,可以相比附。所謂“薪則不可謂此薪爲彼薪”是説此人非彼人,所謂“火則不可謂此火非彼火”是説神明不滅,靈魂可以轉世。靈魂既可轉世,則“達觀者可以無變於死生之故矣”。然而,此所述已非莊子的思想了。
第六,以“大道”釋“火”,錢穆説:“火喻大道。佛典以神形喻薪火,非莊子本旨。”*錢穆《莊子纂箋》,東大圖書公司1993年版,第26頁。錢穆欲以中國傳統的“道”的概念來澄清莊子的本意,然“火喻大道”在《養生主》篇中並無任何依據,錢穆本人也没有對爲何認定“火喻大道”的原因,作出任何説明。此外,錢穆未説及的是,此論原發自王闓運。王闓運注“火傳也”曰:“夫形亦薪也,道亦火也。無薪則火何傳,無形則道何寄。”*王闓運《莊子内篇注》,《莊子集成續編》第三十六册,第85頁。然而,此注只能説是王闓運的自我發揮,並非對《莊》文的釋意。
第七,以“化”釋之。釋性?椾E明確地用“化”來注此句:“薪有盡而火無窮,形有盡而主無盡也,形形相禪,化化無窮,正如薪火之傳,何有盡極。”*釋性?椾E《南華發覆》,《莊子集成續編》第五册,第81頁。釋性?椾E所説的“化”是禪化之化,是講人的類生命的綿延,不僅氣局小,而且底藴薄。
王夫之對莊子這句話的解釋,没有明確説到“化”,但其内容則超脱出人的類生命的綿延:“夫薪可以屈指盡,而火不可窮。不可窮者,生之主也。寓於薪,而以薪爲火,不亦愚乎!蓋人之生也,形成而神因附之。形敝而不足以居神,則神舍之而去;舍之以去,而神者非神也。寓於形而謂之神,不寓於形,天而已矣。寓於形,不寓於形,豈有别哉?養此至常不易、萬歲成純、相傳不熄之生主,則來去適然,任薪之多寡,數盡而止。其不可知者,或遊於虚,或寓於他,鼠肝蟲臂,無所不可,而何肯聽帝之懸以役役於善惡哉?傳者主也,盡者賓也,役也。養其主,賓其賓,役其役,死而不亡,奚哀樂之能入乎?”*王夫之《莊子解》卷三,中華書局1964年版,第33頁。
“形成而神因附之”、“神舍之而去”的説法,使人感到王夫之所説的“神”仍然是外之於形的。但他又説:“舍之以去,而神者非神也”,“寓於形而謂之神,不寓於形,天而已矣。”這就否定了離形之神説。然而,在他的話中,與作爲“賓”的人生相對的,又有一種永恒的相傳不熄的“生主”,他要求人們養此生主,就可以死而不亡。這生主是什麽呢?王夫之没有明説,如果聯繫他所説的“鼠肝蟲臂,無所不可”的話,此生主可以理解爲大化的運動。然而,大化是不可養的。所以,王夫之的解釋,最終還是説不通。
當然,我們也可以這樣來推衍王夫之的意見: 將大化的運動抽象化爲個體生命存在之主,將個體生命納入大化之中,這就是死而不亡也。養生主者,亦即自覺地認識到個體生命與大化的這種關係,這樣便可生死適然,任天年之多寡,數盡而止,一切采取任其自然的態度。然而,“生主”此一概念終帶有主宰者的意味,這種意味則同“大化”的概念又相對立。
綜上所述,“薪”、“火”之喻,迄今未有正確的解釋。
二
關於後一個難點。在莊學史上有兩種相關聯的解釋占主導地位: 手指與指着,一爲名詞,一爲動詞,莊學家基本上都是取兩者中之一義也。
取手指意者,可舉者如下: 羅勉道釋曰:“如以指計薪,薪多而指有窮盡,及火相傳,燒而不知其即時罄盡。”*羅勉道《南華真經循本》卷四第六,《莊子集成續編》第二册,第126頁。焦竑抄襲羅釋曰:“竊意以指計薪,薪多而指有窮,及火相傳,燒不知其即時盡矣。”*焦竑《莊子翼》,《莊子集成續編》第十一册,第127頁。王先謙則注云:“以指析木爲薪,薪有窮時。”*王先謙《莊子集解》,第31頁。此外,上引王夫之“夫薪可以屈指盡”一語,屈指,彎曲指頭之謂也。上引葉玉轔譯文:“用手指來折斷樹枝做柴燒。”以上五釋,均解“指”爲手指也。
上引林希逸曾曰:“指其薪而觀之。”*林希逸《南華真經口義》卷四第十,《莊子集成初編》第七册,第142頁。此語爲陸西星所沿承:“指薪而觀會有窮盡。”*陸西星《南華真經副墨》,《莊子集成續編》第七册,第144頁。林雲銘注曰:“薪之窮可以指實。”*林雲銘《莊子因》,《莊子集成初編》第十八册,第82頁。宣穎注云:“指,可指而見者也。”*宣穎《南華經解》卷三,《莊子集成續編》第三十二册,第91頁。馬魯與陳壽昌均承用宣注*馬魯《南華瀝》,《莊子集成續編》第三十四册,第89頁;陳壽昌《南華真經正義》,《莊子集成續編》第三十七册,第58頁。。劉鳳苞注則曰:“薪可指而盡。”*劉鳳苞《南華雪心編》,《莊子集成初編》第二十四册,第124頁。以上七家,均釋“指”爲指着之意。
脱出上兩種解釋的,可舉褚伯秀、胡文英、王闓運三家。
褚伯秀曰:“竊詳經意,指應同旨,理也。理盡於爲薪,故火傳不知其盡,義甚明。”*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道藏》第十五册,第228頁上欄至中欄。褚伯秀自認爲“義甚明”,其實,“理盡於爲薪”一語就不通,至少是不明晰。而且,他在下文的長段解釋中説的仍然是離形之神,並未見“理”字的落實。可謂故爲其詞也。
胡文英注“指窮於爲薪”云:“言薪指刻而可窮也。”*胡文英《莊子獨見》,《莊子集成初編》第二十一册,第54頁。指刻者,頃刻是也。這是將“指”偷换爲“指刻”也。
王闓運注“指窮於爲薪”則曰:“指公孫子之辯也”,注“火傳也”又曰:“公孫子以指喻薪,必云薪非薪,火非火,然薪不傳火,火必附薪,故窮於指而火自傳。”*王闓運《莊子内篇注》,《莊子集成續編》第三十六册,第85頁。這兩個注釋是自相矛盾的,既説“指窮於爲薪”爲公孫龍之辯;又以一種模擬的口氣説“公孫子以指喻薪,必云薪非薪,火非火”。前者實然也,後者假設也。並且,王闓運並没有説清何謂“窮於指”。
正是因爲對“指”的解釋長久陷於困境,因此朱桂曜、聞一多的以“脂”釋“指”説,受到了歡迎。朱桂曜曰:“‘指’爲‘脂’之誤,或假。……脂膏可以爲燃燒之薪,故《人間世》云‘膏火自煎也。’此言脂膏有窮,而火之傳延無盡;以喻人之形體有死,而精神不滅。”*朱桂曜《莊子内篇證補》,《莊子集成初編》第二十六册,第104頁。聞一多在《莊子内篇校釋》中,於引述了朱桂曜的解釋後説:“案朱説是也。古所謂薪,有炊薪,有燭薪,炊薪所以取熱,燭薪所以取光。古無蠟燭,以薪裹動物脂肪而燃之,謂之曰燭,一曰薪。燭之言照也,所以照物者,故謂之曰燭。此曰‘脂窮於爲薪’即燭薪也。”*聞一多《莊子内篇校釋·養生主》,《聞一多全集》第九卷《莊子編》,第40頁。陳鼓應以爲:“朱、聞之説勝舊注,可從。”*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上册,第115頁。曹礎基也認爲:“朱、聞所説是有道理的。指窮於爲薪即脂爲薪而窮,脂肪作爲燭薪而被點盡了。”*曹礎基《莊子淺注》,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47頁。歐陽景賢亦云:“這一句,解説頗多分歧。比較起來,聞説於義爲長。唯燭薪,恐並不限於以薪裹動物油脂而燃之者。”*歐陽景賢、歐陽超《莊子釋譯》上册,第68頁。陳鼓應、歐陽景賢、張耿光、陸欽、仲兆環、黄錦鋐、孫通海、張采民與張石川的注、譯均取聞義*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上册,第117頁;歐陽景賢《莊子釋譯》上册,第69頁;張耿光《莊子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54頁;陸欽《莊子通義》,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1、82頁;仲兆環《南華經》第46、47頁;黄錦鋐《新譯莊子讀本》,臺北三民書店1974年版,第42—44頁;孫通海譯注《莊子》,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60頁;張采民、張石川《〈莊子〉注評》,鳳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頁。。
然而,以“指”作“脂”,雖注家多從之,而實無多少根據。既無版本可依,又無《莊》書用字習慣及同時代人用字之慣例可爲之證。
自然也有不取朱聞之義者。大約是受到王夫之“夫薪可以屈指盡”的影響,張默生釋“指窮於爲薪”曰:“此言薪被點燃,彈指之間,即燃盡也。”*張默生《莊子新釋》,齊魯書社1993年版,第142頁。這與胡文英以時間詞釋“指”相似,顯然也屬望文而生義者也。《莊》文中何處有屈或彈之意?
有趣的是,聞一多在《莊子章句》中竟將郭象“前薪”之釋、形神之義以及以“脂”爲“指”的意見,混合在一起而曰:“薪即燭,燃脂以爲燭,脂有窮而火之傳延無盡,以喻人之形體有死,而精神不滅,正不必以死爲悲。古秉燭之法,兩薪交錯,新薪將盡,斷以後薪,是謂火傳。”*聞一多《莊子章句·養生主》,《聞一多全集》第九卷《莊子編》,第97頁。引文中“斷”字疑爲“續”字誤。相對於“後薪”的“新薪”,自當爲“前薪”也。其實,在聞一多之前,阮毓崧即已在其注中,試圖將郭注成疏與形神之説結合起來:“善爲薪者,其前持之薪甫盡即必以後薪繼續之,故其火相延不熄未有知其盡時者,此借薪火以喻死生,明夫形往而神存與薪盡火傳無異也。”*阮毓崧《重訂莊子集注》,《莊子集成續編》第四十一册,第74頁。這種混雜式的解釋,自然是不可能正確的。
由上述可見,“指窮於爲薪”句中的關鍵字“指”字,由古及今均無解也。
三
綜觀《莊子》内篇用到“指”的除本篇“指窮於爲薪”外,一共只有三處: 《齊物論》用之:“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此外,《人間世》用之:“會撮指天。”《大宗師》亦用之:“句贅指天。”然而兩篇所用“指”字爲指向之意,爲動詞。作爲名詞的,僅本篇和《齊物論》的兩處。
我們在《逍遥遊》《齊物論》中已經看到,《莊》文中有活用名家的名辯論題作爲比喻及利用名家辯題重加申述用以表達自我意旨的情況,“指窮於爲薪”句也應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公孫龍《指物論》本有“物莫非指,而指非指”*王琯《公孫龍子懸解》,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48頁。之説。“指”者屬性之謂也,“物莫非指”者,就是説物即是屬性,這是公孫龍的原意。但既謂“物莫非指”,則自可以“指”代“物”也。《莊》書中的物字往往代指人和物兩者,指人也時常用物字。這在《齊物論》中已有其例。因而,此處“指”字即代指個體生命。火喻生命,“指窮於爲薪”者,是説個體的生命之火像薪一樣是有盡的,“火傳也,不知其盡也”,則是説生命之火的流轉是無盡的。這樣講,就能講通了。
然而,認識到這一步,還没有探其根由。拙著《中國前期文化——心理研究》曾説:
對於生命的直接性認識,使得原始人不能對不同部類的生命作出本質的劃分。生命現象之網在他們面前拉開,雖然每一個氏族、部落在自然、社會的總聯結中有一個特定的位置,以至於色彩、方位都被作了專屬性的分割,死後的埋葬也相應有其特定的朝向,但是各個特定的網眼又是彼此相通的。以婚姻爲中介,各氏族、部落可以産生溝通關係;以文化爲中介,人與自然也相互模塑着。於是,在原始意識漫天撒開的大網中乃有一股靈氣在流轉。這一股流轉的靈氣的表現形式,便是各種形式的生命之間的感應和轉换。*王鍾陵《中國前期文化——心理研究》,重慶出版社1991年版,第346—34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40頁。
如果聯繫《大宗師》篇子來將死、子犁稱造化將以之爲鼠肝蟲臂之類的文字來思考,則可以看出在莊子“火傳也,不知其盡也”的論述中,有着一種根源於原始生死觀的對於生命跨越各種存在形式而周流的體認,只有認識到這一步,我們才能對於莊子以泛自然主義看待生死問題以至各種社會問題之深厚的緣由有切實的把握。
這樣一種闊大的生命周流感,乃莊子天鈞義的底藴是也——這一點是喜愛天鈞義的王夫之限於時代而不可能認識的。但值得指出的是,生命跨越各種形式的周流,既然是通過物化的方式來實現的,這當中就不存在一種離形之神,它是生命物的具體的、直接的轉换,並不存在一種精神性的東西的轉移。莊學家們多失誤於此也。
要之,《養生主》末句,亦即本篇的第六段,喻寫生命的周流。其在表達上的特色,便是在比喻中化入了名辯論題中的詞語。
關鍵詞 莊學史 解釋 喻寫 生命周流 名辯論題
中圖分類號B2
作者簡介王鍾陵(1943— ),男,現爲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主要從事唐前文學及文學批評研究,曾在《中國社會科學》《文學評論》《文學遺産》《社會科學戰綫》等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著有《中國中古詩歌史》《中國前期文化——心理研究》《文學史新方法論》《神話與時空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