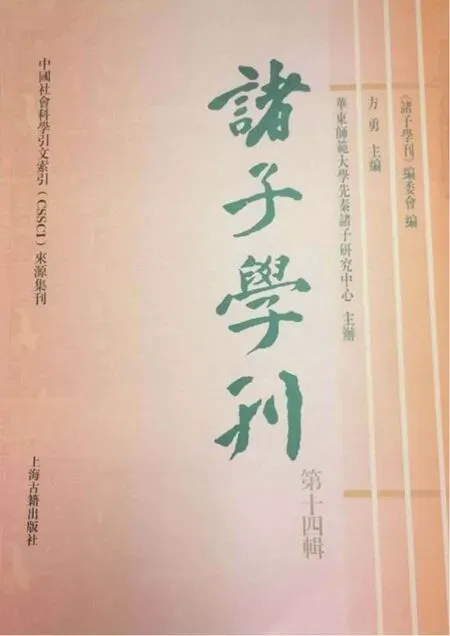儒家的心性修養與人格構建
韓 星
儒家的心性修養與人格構建
韓 星
面對中國社會因處於急劇變遷所産生的各種問題,傳統儒家的心性之學也許是治本之舉。孔子很少離開人專門講心,顔子一派講“心齋”,後來不占儒家的主流地位。孟子則提出“四心”、立“本心”、“求其放心”、養心諸説,成爲後儒心性學的源頭。荀子以心爲天君,爲身形之主宰,重治氣養心之術。《大學》講“正心”。董仲舒提出了人心副天心的主張。宋明理學家進一步發展了早期儒家學者有關心性的理論,同時吸收佛教、道家的心性學説,把“心”分爲道心、人心,強調心的主宰功能和作用。心的主宰作用不但是心性學説的核心,也是儒家人格建樹的關鍵。儒家心性之學追求内在的自我超越,強調心爲主宰,體現在人格建樹上主要是通過致誠盡性,下學上達,達至天人合一的境界,從而成爲聖人。
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化、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社會處於急劇變遷之中,人們過分追求物質的滿足而輕視心靈的需要和精神的發展,結果導致道德滑坡,人格退化,並嚴重影響到了社會穩定和秩序構建。怎麽解決這些問題?除了外在的完善法律和進行道德教化以外,傳統儒家的心性之學也許是治本之舉。明代王守仁針對當時的社會問題就提出了“破山中賊”和“破心中賊”兩大思路,甚至把後者看成是根本。
一、心 爲主宰
儒家認爲最重要的是以心爲主宰,強調每一個人的心就是每一個人的主人。在中國思想史上,“心”是一個具有本原性和主體性雙重功能的範疇,是在中國特有的文化背景和歷史語境下産生的概念,包括了人體的頭腦、四肢、百骸、腑臟在内的器官所産生的生命作用,以及它能起的思維、想念和意識所反應的見、聞、覺、知等功能,類似於今天的知、情、意的總體。它既不是純生理的,也不是純精神的,而是生理、精神合一的;它既不是如西方哲學所説的“唯心”,也不是“唯物”,它是“心物一體”的。中國思想中一系列心理範疇: 情、性、志、意、思、感、想、悟等等,都由“心”演生,與“心”密切相關。儒家強調“本心”、“正心”、“養心”、“求放心”、“操存此心”等,以使心常在腔子裏,並成爲一身之主,使人與動物相同的五官百體之欲都聽命於心,這也就是孟子“先立乎其大者”的基本含義。
在孔子那裏,很少離開人專門講心,而《論語·雍也》説顔回“其心三月不違仁”,是儒家講心的起點。後來顔子一派受道家影響,更講“心齋”。《莊子·人間世》講了這樣的故事: 顔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孔子説:“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顔回問道:“敢問心齋?”孔子説:“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齋也。”這些話未必就是孔子所説,但也可以説是孔門後學顔子一派的主張。這種心性修煉由於有太明顯的道家色彩,後儒認可和實踐的並不多,只是儒家心性生命修養的一股潛流,到了明代王陽明才得以發揚光大。陳來先生在《儒學傳統中的神秘主義》一文中從西方學術範疇“神秘主義”的角度,梳理和發掘了中國儒學中通過入静而實現的神秘體驗這一傳統,並認爲這一傳統主要出現在宋明理學的心學派當中,在中國思想史上“提供了一種有别於西方哲學的特殊形態”,他稱之爲“體驗的形上學”*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編《北京大學百年國學文粹: 哲學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孟子提出了“四心”説,即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和是非之心,認爲要做一個真正的人必須具備此“四心”。《孟子·公孫丑》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孟子·告子上》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爍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認爲“四心”即是道德之心,亦即是仁、義、禮、智道德的萌芽。可以看出,一方面他是以否定的方式説不具備此四者則不成爲人;另一方面,他是以肯定的方式説此四者爲人所固有。在此基礎上,孟子強調人要確立“本心”。人雖然具有與生俱來的善性,但是人生在世,受各種物欲引誘,本來的善性在一天天變惡。孟子認爲:“此之謂失其本心。”(《孟子·告子上》)這裏的“本心”就是“我固有之”的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和是非之心,“失其本心”也就是“放其良心”。他以牛山之木爲比喻,説道:“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孟子·告子上》)因此,他教人用工夫下手的方法就是“求其放心”,把失去了的善心尋找回來。他以人丢失了雞狗爲例,説道:“人有雞犬放,則之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怎麽能够把心找回來?他進一步強調要時時“操存”。他因孔子的話説:“‘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唯心之謂與?”(《孟子·告子上》)孟子還講“養心”:“養心莫善於寡欲。”(《孟子·盡心下》)還講“存心”:“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孟子·離婁下》)孟子講心的地方很多,可以説爲心學的鼻祖。後來宋儒談心都是宗法孟子。
荀子講心的地方也很多,但與孟子在理路上有明顯差别。荀子以心爲天君以治五官,爲身形之主宰,《荀子·解蔽》云:“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關於心是形之君,《荀子·天論》進一步解釋説:“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臧焉,夫是之謂‘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在荀子看來,好、惡、喜、怒、哀、樂等感情是人生來就有的,這些感情所依存的耳、目、鼻、口、形等器官也是人生來就有的,但是,耳、目、鼻、口、形這五官都有一個天生就有的主宰者,那就是心。荀子之所以稱心爲“天君”,就是因爲它是天官之君,更是天情之君。關於心是神明之主,《荀子·性惡》云:“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今使塗之人伏術爲學、專心一志、思索熟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也。”這裏荀子講心爲神明之主是從個體的修養角度説的,如果一個人能够伏術爲學、專心一志、思索孰察、積善而不息,就可以通於神明而參於天地;反之,他如果只是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那就不可能通於神明,不可能成爲聖人。聖人是經過漫長艱苦的修養過程,始終以心爲主宰,身心和諧,下學上達,進入理想的人格境界。
對於具體的修養方法,《荀子·修身》講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濕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庸衆駑散,則劫之以師友;怠慢僄棄,則照之以禍災;愚款端愨,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這是講變化氣質,校正個人的缺點,與孟子把良心存養起來再下修養的工夫不同。荀子可能受到稷下黄老道家的影響,強調心性修養要“虚壹而静”。《荀子·解蔽》云:“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道?曰虚壹而静。”虚壹而静是荀子對黄老學派静因之道的繼承。荀子繼續解釋心的性質,他説:“心未嘗不兩,而有所謂壹;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静。”這是講心之爲物,非常具有伸縮餘地,儘管收藏,儘管複雜,儘管活動,仍然無害於其虚壹而静的本來面目。他繼續論證:“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謂虚。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虚。”這是講養心的具體方法,在於不以已有的知識妨礙將要接受的知識。又説:“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這是講人類的心同時産生幾種感知,心要能够“同時兼知之”,這就是求一。只要不以夫一害此一,心有所旁騖也是可以的。又説:“心卧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静。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静。”這是講心之爲物,變化多端,治心但求静。只要能静,夢也好,行也好,謀也好,都没有妨礙。可見,荀子的治心養心主要是針對知識的,同時也注重外部的陶冶工夫;而孟子則不是專爲知識,他強調内部的修養,求其放心,操之則存。
《大學》講“正心”:“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 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按照八條目的先後關係講,正心在修身之先,是先有正心而後才有身修,但這裏卻講“身有所”云云,是説先有身不正,而後才有心不正,顯然於理不通,所以程顥認爲“身”爲“心”之誤,應該加以改正,這是有道理的。“正其心”,也就是要以端正的心思(理智)來駕馭感情,調節身心情緒,以保持中正平和的心態,集中精神修養品性。正心是修齊治平的根本。正心主要在於正觀念。觀念是心靈的主導,決定着人的思維方式、情感方式、行爲方式,決定着人的一切。
可見,早期儒家通過心性的體認、悟解,強調主體的主動性、能動性,強調通過内心修養和德性提升,去體驗並獲得與客體對象的交融合一,側重於闡發人的肢體的倫理内涵,致力於追求主體的道德踐履的效用。
漢代儒者對這些心性問題不太感興趣,講得也不是非常清楚。董仲舒從天人感應的基本觀念出發,提出了人心副天心的基本主張,藉以溝通天人,以天的權威提高儒家仁義道德的權威,但這在一定程度上偏離了先秦儒家的心性學説。當然,他的思想中有一些觀點值得注意,如他在《春秋繁露·通身國》中説“身以心爲本”,在《春秋繁露·天地之行》用了個比喻,説:“一國之君,其猶一體之心也: 隱居深宫,若心之藏於胸;至貴無與敵,若心之神無與雙也;……内有四輔,若心之有肝、肺、脾、腎也;外有百官,若心之有形體孔竅也;親聖近賢,若神明皆聚於心也。”顯然,在董仲舒看來,心是人身之君,是人之爲人的決定因素,心想做什麽,人身就會隨心欲而動,它對人的主宰就如同皇帝對大臣的主宰一樣。心是整個身體思想、道德、意識的中心,決定人的仁貪、善惡、賢不肖。人禁制貪欲之性、醜惡之行,得依靠心。《春秋繁露·深察名號》云:“栣衆惡於内,弗使得發於外者,心也。故心之名也栣也。”禁制各種各樣的貪欲惡念,使之不得外發爲言論行爲,心的這種作用叫做“栣”。他強調“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春秋繁露·身之養重於義》),認爲心是身體的根本,心有能够捍禦外物的能力,必須以義來加以調養。
隋唐以後,佛教勢力愈發強盛,儒家也更多地受到佛教心性學説的影響。宋明理學家進一步發展了早期儒家學者有關心性的理論,同時又吸收了佛教、道家的心性學説,因而多有理論上的創獲和實踐上的修爲。
首先,他們把“心”分爲道心、人心。
道心即善心,人心則可善可不善。道心與人心,並不是説人有兩個心,而是指人心的兩重性。這一對概念原出於《古文尚書·大禹謨》:“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唯精唯一,允執厥中。”此十六字在漢唐時僅作文字訓詁,並無奥義。至宋代理學家以義理解經,將這十六字説成是堯舜心傳。北宋理學家程頤以天理人欲解釋道心人心,把二者對立起來,並由此提出滅人欲、明天理的主張。程顥也有類似的説法。南宋朱熹對程頤之説作了發揮,但與程頤稍有不同。當學生問“人心”與“道心”的區别時,他説:“此心之靈,其覺於理者,道心也;其覺於欲者,人心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六《答鄭子上》)“只是一個心,知覺從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覺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朱子語類》卷七十八)所謂道心,指以義理爲内容的心,出於天理或性命之正,本來便稟受得仁義禮智之心,發而爲惻隱、羞惡、是非、辭讓,則爲善。所謂人心,指原於耳目之欲的心,人生有欲,饑食渴飲,可爲善,可爲不善,雖聖人亦不能無人心。不過聖人不以人心爲主,而以道心爲主。人心能無過無不及,能得其正而不偏者即爲道心,兩者没有不可逾越的鴻溝。道心只有在與物相接的人心中才能顯現出來。但道心微妙難見,人心易流於人欲,故人人當精察於二者之間。朱熹很重視道心人心的概念,認爲天下之理,無過於堯舜十六字心傳。他進一步解釋説:“人心唯危,道心唯微,論來只是一個心,哪得有兩樣?只就他所主而言,那個唤作人心,那個唤作道心。”(《朱子語類》卷十一)朱熹的學生蔡沈在《書經集傳》注曰:“心者,人之知覺主於中而應於外者也。指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
在人心與道心的關係上,朱熹強調兩點: 一是道心以人心爲基礎,二者又互相依存,相即不離;二是道心爲主,人心聽命於道心*張立文主編《心》,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頁。。他説:“人心便是饑而思食,寒而思衣底心。饑而思食後,思量當食與不當食;寒而思衣後,思量當著與不當著,這便是道心。”(《朱子語類》卷七十八)認爲人心是饑而食、寒而衣之心;道心則是當衣食時,思量該不該食,該不該穿之心。道心在人心的基礎上作爲人心的指導而産生,離開人心則無所謂道心。又説:“道心則是義理之心,可以爲人心之主宰,而人心據以爲凖者也。”(《朱子語類》卷六十二)道心主宰人心,人心以道心爲準則。朱熹雖然提出道心與人心相分的思想,但他仍指出道心人心並非二心,它們只是一心的兩種表現。心與理,欲雖有聯繫,但亦有區别,故不能把道心直接等同於理,把人心直接等同於欲。
與朱熹同時的陸九淵,反對以天理人欲解釋道心人心。陸九淵説:“《書》云:‘人心唯危,道心唯微。’解者多指人心爲人欲,道心爲天理,此説非是。心,一心也,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則曰‘唯危’,自道而言,則曰‘唯微’。”(《陸九淵集》卷三十四《語録上》)朱熹所解釋的“人心”是“人欲”,“道心”是“天理”;陸九淵解釋的“人心”是“人道”,“道心”是“天道”。朱學陸學在此而有分野。明代王陽明以良知爲本心,本心即道心,本心雜以“人僞”爲人心。他以本心之得失來區分“道心”與“人心”。《傳習録·卷中》説:
“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學而敏求此心之理耳。心即理也。學者,學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非若後世廣記博誦古人之言詞以爲好古而汲汲然唯以求功名利達之具於外者也。……道心者,良知之謂也。
這就是説,王陽明繼承的是孟子所主張的求其放失的本心的反身求誠的修煉方式,而這種方式的根基就是“心即理”。顯而易見,在王陽明看來,人們的這種即理之心是放失了,把它找回來是心學的奮鬥目標。至於百姓的平常心,那顯然已不是心學所説的心了。
其次,他們強調心的主宰功能和作用。
朱熹説:“心,主宰之謂也。”“心者,一身之主宰。”(《朱子語類》卷五)所謂一身之主宰,是指心能够統御人身體的各個部位,如耳、目、鼻、舌、身等。又説:“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朱子全書》卷四十四《觀心説》)心的主宰表現爲一而不二,它爲主不爲客,作用於物而不爲物所管攝。又説:“心者人之神明,所以聚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四書集注·孟子·盡心上》)心作爲人的精神主體,能够聚合事物之理以應和事物的變化發展。心怎麽做人的主宰?宋儒發揮了原始儒家的相關思想,提出了“心統性情”之説。
在中國思想史上,孟子首先論及心與性情的關係問題,他説:“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孟子·盡心上》)他認爲,仁義禮智之性根於心,盡心則能知性,性、情都是心所固有的。張載則明確提出“心統性情”的命題,他在《性理拾遺》中説:“心,統性情者也。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發於性則見於情,發於情則見於色,以類而應也。”張載認爲,心是統合性情與知覺而言的,《正蒙·太和》云:“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心一方面表現爲具體的知覺,另一方面這些知覺活動無不受内在的本性所決定和支配*陳來《宋明理學》,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9頁。。其中性是根本的,“天授於人則爲命,亦可謂性。人受於天則爲性,亦可謂命”(《張子語録中》);“性即天也”,所以“性又大於心”(《張子語録上》),有性再加知覺,便成爲心,即就天地之性或道德理性與心理知覺或經驗認識之心合而言之,心之名乃立。因此,心能够主性情。
朱熹發揮了張載“心統性情”的思想,使之成爲自己學説的重要組成部分。朱熹的“心統性情”就是指“心”主宰、統攝、包含、具有性情。一方面,朱子對心、性、情三者作了區分,尤其指出心與性情的差異;另一方面,他又肯定三者的統合、一致。他對“心統性情”的理解和發揮主要是從“心兼性情”和“心主性情”兩個方面説明心統性情的内容*陳來《朱子哲學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51—263頁。。所謂“心兼性情”,強調心爲意識活動的總體範疇的意義,同時也表明朱熹是用心統性情作爲自己心性理論的總體構架模式的。他説:“横渠云‘心統性情’,此説極好。”並解釋説:“統,猶兼也。心統性情,性情皆因心而後見,心是體,發於外謂之用。”(《朱子語類》卷九十八)又説:“性,其理;情,其用。心者,兼性情而言;兼性情而言者,包括乎性情也。”(《朱子語類》卷二十)所謂“心主性情”的“主”,有“主宰”、“管攝”等義。他説:“性者,理也。性是體,情是用,性情皆出於心,故心能統之。統,如統兵之‘統’,言有以主之也。”(《朱子語類》卷九十八)這裏強調的是意識主體對性情的主導、控制作用。他還説:“性對情言,心對性情言。合如此是性,動處是情,主宰是心。”“虚明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於中,無少欠缺,便是性;感物而動,便是情。”(《朱子語類》卷五)可見,朱熹從未發已發、動静、體用三層次來解釋“心統性情”*張立文《朱熹思想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514—516頁。。性即理具於心而爲心之體,性發爲情爲心之用,體用結合即是心統性情。而且,情發於義理是“道心”,發於形氣之私是“人心”。張載、朱熹強調“心統性情”,其主要意義在於表明: 進行精神修養既須認識本性,又須培養情操、調節情感。
陸九淵以發明本心爲宗旨。《象山年譜》這樣評價:“先生之講學也,先欲復其本心,以爲主宰,既得其本心,從此涵養,使日充月明,讀書考古,不過欲明此理盡此心耳,其教人爲學端緒在此。”所謂本心,即是人所固有的仁義禮智之心,也即是人先天而來的道德意識。所謂發明本心,即徹底地反省吾心固有之道德義理。一切道德準則皆出於人之本心,本心是一切道德之根源,人只要發明此本心,順此本心而行,便自然當如何即如何,而一切行爲無不合於道德*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354—355頁。。陸九淵強調人生修養必須就孟子所説的“先立乎其大者”,即先明本心,收拾精神,自做主宰。
我治其大,而不治其小,一正則百正。恰如坐得不是,我不責他坐得不是,便是心不在道。若心在道時,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語録》)
此理即本天所以與我,非由外鑠。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真能爲主,則外物不能移,邪説不能惑。(《與曾宅之書》)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須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内,當惻隱即惻隱,當羞惡即羞惡,誰欺得你,誰瞞得你?(《語録》)
人須是力量寬洪作主宰。(《語録》)
顯然,在陸九淵這裏,先明本心就是發掘人心先天固有的善端,人之爲人在於心,爲人須自作主宰,不要爲外物牽引。立得此本心,人才能自立,自立乃確立人的自我主體性。
王陽明從陸九淵“心即理”説出發,認爲:
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即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即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即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説無心外理,無心外物。(《傳習録》下)
這裏的“意”是指意識、意向、意念。“意之所在”是指意識的對象。這裏作爲意識對象的“物”,主要是指“事”,即政治、道德、教育活動,而不是指整個客觀世界。概括大意是説,心是身體的主宰,心的本體原本是不動的,心的“發動”、“感通”就是意識,意識所指向的對象就是“物”,即“事”。離開了意識的指向性,“事”就不會存在,或没有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因此,“心外無物”、“心外無理”。“心之本體”即是天理,而“天理之自然明覺”即人之本來的是非之心,便是“良知”。王陽明認爲天地萬物都依賴良知而存在,離開了人的良知,宇宙天地便不能存在。“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爲草木瓦石矣。豈唯草木瓦石爲然,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爲天地矣。蓋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傳習録》卷中)又説:“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靈明覺即所謂本然之良知也。其虚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凡意之所用,無有無物者: 有是意即有是物,無是意即無是物矣。物非意之用乎?”(《答舒國用》,《全書》卷五)這就是説,作爲身之主的心的本質屬性是虚靈明覺,是良知,它表現出來的則是“意”,即主體意識。
余英時先生有一篇《新年話“心”》在网絡上流傳,他指出傳統上我們是非常注重心的,但是整個20世紀,中國人最活躍的分子最關心的問題則是權力問題。有權力,就可以號令别人,就活得好,不管别人的死活。20世紀末到今天,大陸實行市場經濟以來,人心爲金錢所動,錢與權成爲衆人追求的目標。這個原因是我們的心,道的心,高尚的心,高貴的心慢慢被大家忽略了。又因爲没有宗教,再加上長期以來主導意識形態提倡唯物論,人都是物,具有階級性,忽視了人性。在這樣一個思潮之下,中國的心就越來越失落了。心的失落是一百年來中國文化危機最大的關鍵之一。這就是造成當前信仰缺失、道德淪喪、人心墮落、社會離析、違法犯罪司空見慣狀況的内在根源。
二、人 格建樹
我們今天使用的“人格”一詞是從近代日文引入的,而日文又是對英文personality的意譯。英文personality的最初詞根是拉丁文的persona,意即面具,當時是指演員在舞臺上戴的面具,與我們今天戲劇舞臺上不同角色的臉譜相類似。後來心理學借用這個術語,用來説明每個人在人生舞臺上各自扮演的角色及其不同於他人的精神面貌。西方人主要是從人的心理、生理方面解釋人格的,最常見而簡明的解釋是State of being a person,人的存在狀態,實際上是指一個人是怎樣以自己的内心活動和外在言行來表現自己的存在。中國古代雖無人格一詞,然有“人品”、“爲人”、“品格”與其相對應。“人品”即人的品格,不單純表現爲品德,是性格、道德、智慧、意志、行爲等内涵的統一,是一個人之所以區别於他人的特質,是一個人在一系列行爲中表現出來的、之所以區别於他人的、比較穩定的特質和傾向,體現了個人相對於他人的獨立存在。
儒家的人格具有兩個相互關聯的方面: 一是強調人所具有的獨特品格,使人與禽獸區别開來;一是強調人的品性所呈現的價值層級,它使人與人區别開來。
就第一方面而言,《尚書·泰誓上》強調“唯天地萬物之母,唯人爲萬物之靈”,《孝經·聖治》也引孔子的話説:“天地之性人爲貴”。孟子在“人禽之辨”的討論中,將孔子的“仁”内化爲一種心理感受,進而升華爲道德的自覺意識。孟子認爲人之所以爲人,人之所以高於動物,正在於道德規範背後的心理差别,“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孫丑上》)但是單純的心理差異,還不足以將人與動物區别開來。“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孟子·離婁下》)這樣,能否將此“惻隱”之類的心理感受常存於心,並發自内心地去實行,是“人所以異於禽獸”的根源。也就是説,人與動物不同的地方,就是在肉體的四肢五官之外,另有一種超然的善的心。人所具有的這種道德自覺,並不是爲了製訂一些條條框框來刻意地限制自己,相反,正是爲了把自己從動物界的限制中解放出來。這是對人性的一種提升,也是人優越於動物的證明。
荀子講人之所以爲人者:“人之所以爲人者,何已也?曰: 以其有辨也。饑而欲食,寒而欲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則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以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獸有父子而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於分,分莫大於禮,禮莫大於聖王。”(《荀子·非相》)荀子還説:“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荀子·王制》)就第二方面而言,儒家的人格是有不同劃分的,一般的是自下而上地劃分成小人、士、君子、賢人、聖人、天(神)。如孔子把人格分爲中行之人、狂者、狷者、鄉願四等。《論語·子路》載:“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陽貨》載:“子曰: 鄉願,德之賊也。”孔子在此把人分爲四個層級: 上等爲“中行”之人,即以中庸之道爲行爲準則的人,這種人也即我們所説的聖人。其次爲狂者,其特點是勇於進取,敢爲天下先,但又往往急於求成,急躁偏激。再次爲狷者,其特點是有所不爲,愛惜羽毛,寧願不爲而不妄爲,但又膽小謹慎,左顧右盼,迂遠拘泥。最不可取是的鄉願,其特點是八面玲瓏,四方賣乖,人人稱好的“好好人”,是一種欺世盜名的小人人格。孔子認爲“中行”之人,世上難遇,可教可誨的主要對象是狂者和狷者。
孔子還把人格和人的理性發展劃分爲五個階段,故可分爲五品即五個等級: 即“庸人”、“士”、“君子”、“賢人”、“聖人”。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之庸人?”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賢以托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此則庸人也。”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則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義在身而色無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通道,自強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則君子也。”公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富則天下無宛財,施則天下不病貧。此則賢者也。”公曰:“何謂聖人?”孔子曰:“所謂聖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識其鄰。此謂聖人也。”“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故其事大,配乎天地,參乎日月,雜於雲蜺,總要萬物,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若天之司,莫之能職;百姓淡然,不知其善。若此,則可謂聖人矣。”(《孔子家語·五儀解》)
孟子把人格分爲六個層級: 善人、信人、美人、大人、聖人、神人。《孟子·盡心下》載: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
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這裏聖與神相連相通。趙岐注《孟子》説,“大而化之”,即“大行其道,使天下化之”,這是聖;“聖而不可知之”,即“有聖知之明,其道不可得知”,或“聖道達到妙不可測的境界”,這是神。
中國現代哲學史家馮友蘭根據人對於宇宙人生覺悟的程度不同,在《新原人》中把人生境界由低到高分爲四種: 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在自然境界中的人,他的行爲是順着他的本能或順着社會的習俗。他對自己的行爲,並没有什麽覺悟,混混沌沌而没有什麽煩惱,也没有什麽追求,跟動物差不多。功利境界中的人,所做的事,都是爲了“利”,一大部分是爲了自己的私利,所以,他所做的事,他只有功利的意義。道德境界中的人,他們的行爲是爲“義”的,他們自覺自己是社會的一員,因而自覺地在社會中盡職盡責,爲社會做事。他們所做的事,有道德的意義,因而他們的境界是道德境界。在這種境界中的人,是賢人。在天地境界中的人,有最高的覺悟,他不僅自覺其是社會的一員,而且覺悟其是宇宙的一員,不但盡人倫,而且要盡天職盡天倫。他所做的事都順應大道的流行。這種境界中的人,即是聖人。“聖人,人之至者也”,是人當中的頂級的人。這四種境界分别對應四種不同的人格,即:
自然境界——俗人
功利境界——能人
道德境界——賢人
天地境界——聖人
這裏我們應該特别強調聖賢人格。作爲理想人格模式,聖高於賢,聖是人中之萃,溝通天人,但更傾向於天;賢也是人中之傑,但更傾向於地。聖賢與其他層次比較起來,卻還是最高,所以《周易·頤卦》云:“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聖人顯然與天地是一個層次,並且負有最重大的歷史使命: 教養賢者以及百姓。聖人難做到,故古往今來能稱得上聖人的屈指可數;賢人大多可爲,古往今來賢者濟濟。一般而言,聖人原型爲聖王,秦漢以後爲王聖(名不副實),只有孔孟未曾爲王,卻是真聖人,爲萬世師表,成爲儒家人士追求的最高理想。賢人本來應該是聖人的輔佐,但在後來歷史上,實際上聖賢之間的關係一直没有處理好,所以聖難以爲王,賢難以升格上去。郭店楚簡《五行篇》指出,“聖”德,聖與仁、義、禮、智五德之所和,屬於天之道的境界,仁、義、禮、智四德之所和,屬於人之道的範疇。周敦頤還提出了一個層層上升的模式:“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通書·志學》)就是説士是讀書明理之人,尚且要“見賢思齊”;進而賢人還要效法聖人。但是“聖人有所不知”,又要希天。所以正統儒家的精神,無時無刻不在鞭策自己向賢聖大路上邁進,進到人的最高價值領域,成爲聖人。所謂希賢希聖就是從低層次不斷地經過修養上升到高層次,直到聖人在理想境界。
唐君毅在《孔子與人格世界》中有精彩闡析,深刻地揭示了儒家聖賢人格的基本精神:
聖賢之人格之精神之所以偉大,主要見於其絶對忘我,而體現一無限之精神。故一切聖賢,皆注定爲一切有向上精神之人所崇拜。穆罕默德、耶穌、釋迦、甘地、武訓,都是人們瞭解其人格中有絶對忘我之無限精神時,不能不崇拜者,聖賢不須有人們之所長。然人們之有所長者,在其面前皆自感渺小。耶穌莫有知識,但有知識的保羅必得崇拜耶穌。釋迦並不多聞,但其弟子多聞的阿難,最後得道。世間一切有抱負、有靈感、有氣魄、有才情、有擔當之事業家、天才、英雄、豪傑之人們,在聖賢之前,亦總要自覺渺小,低頭禮拜。人們未嘗不自知其長處,可以震盪一世,聖賢們或根本莫有。如武訓之爲乞丐,更是什麽亦莫有。但是我們所有的一切,對他們都用不上。耶穌、釋迦、武訓對於人們所要求所有之一切,他們都可不要。於是我們在他們之前,便覺我們之一切所有,由富貴功名、妻室兒女,到我們之一切抱負、靈感、氣魄、擔當,皆成爲“莫有”。我們忘不了我們之“自我”,而他們超越了他們之自我,忘掉他們之自我,而入山,而上十字架,而行乞興學。我們便自知,我們不如他們。他們超越過我們,在精神上涵蓋在我們之上。我們在他們之前,我們便不能不自感渺小,自覺自己失去一切家當,成空無所有。而他們則反成爲絶對之偉大與充實。這一種偉大充實之感覺,便使一切人們,都得在聖賢們之前低頭。你若低頭,表示你接觸了他們之偉大充實,你自己亦分享了他們之偉大充實,而使你進於偉大充實。你不低頭,而自滿於你世俗之所有,如富貴功名,如你的抱負、靈感、氣魄、才情,與擔當,你反真成了自安於渺小。這亦就是崇拜聖賢之人格之精神,是人不能不有的道理。你不崇拜上帝尚可以,然而你不崇拜那真能忘我、而體現絶對無限、而同一於上帝之精神的聖賢人格,卻絶對不可以。崇拜人格,亦是一宗教精神。這種宗教精神,可以比只崇拜上帝、只崇拜耶穌一人更偉大之一種宗教精神。此即中國儒家之宗教精神之一端,當然除此以外,儒家之宗教精神,亦包含崇敬天與祖先及歷史文化。
不過,聖人與基督教的上帝畢竟有本質性的不同。西方人格化的上帝,是創造這個世界的至高無上的造物主、主宰者、絶對權威,“天是上帝的座位”,“地是他的腳凳”。人世一切合理的東西都本於上帝,譬如説講世人要彼此相愛,是因爲他們都是上帝恩愛下的弟兄,“愛是從上帝來的”,“上帝就是愛”。既然如此,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人可以居於特殊等級,成爲特别權威,只有上帝能够高高在上地督導人們。而中國的聖賢不像西方基督教的“上帝”。孔子在中國被奉爲“聖人”,而不是被奉爲“神”,當然聖人達到了天地境界,有了神性,但畢竟不是神,是身處大衆之中,以自己的道德人格力量感召大衆向上,凝聚國民精神,具有“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的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是即凡而聖、超凡入聖的人物。西方基督教也講“聖”,指的是“神”,不是指“人”,例如聖父(上帝)、聖子(耶穌)、聖靈、聖母。基督教也有“聖徒”之稱,那是指靈修高潔、與上帝心靈相通、負有傳播福音特殊使命的使者。孔子並不反對“神”,但也不相信“神”,而是與“神”保持距離。孔子説:“敬鬼神而遠之。”他的弟子描述他:“子不語怪力亂神。”
因爲聖人的要求很高,孔子的學生曾經説他是聖人,他則謙虚地説:“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論語·述而》)意思是:“説我聖,説我仁,我都不敢當!我只是永不自滿地學習,永不疲倦地教誨弟子而已。”但是從他的一生來説,他是一步一步地實現了成聖的過程。對此,《論語·爲政》中有孔子對自己的一段總結:“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簡單的譯解就是説:“我十五歲時,始有志於學。到三十歲,能够以禮自立了。到四十,我能够對一切道理能通達不再有疑惑。到五十,我能够能知道什麽是天命了。到六十,凡我一切聽到的,都能明白貫通,不再感到有什麽困惑。到七十歲開始做事都能够稱心如意,但並没有逾越社會的一般規矩法度。”這段話,應該是他在七十歲以後時所講的話,應該是孔子站在人生的制高點上對自己一生的爲人和事業的回顧和總結,可視之爲聖人人格建樹過程的典型。
儒家後學在這個問題上有不同的發揮,孟子的聖人觀念比孔子要寬泛,他把包括孔子在内的前代諸賢們許爲“聖人”,認爲“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孟子·萬章下》)這裏雖然把孔子與其他三人並列,其含義還是有很大差别的。孟子認爲孔子是“聖之時者”,是集大成。他還説“人皆可以爲堯舜”(《孟子·告子下》),這就向世俗世界灌輸了“聖人可及”的思想。宋明新儒學的先驅韓愈以孔孟的傳道者讚美聖人:“古之人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原道》)程朱從孔子立場上進一步賦予聖人完美化、神聖化的意義,大談“聖賢氣象”,認爲聖賢人格儘管奠基在“内向”的精神支柱上,但又必然表現於“外在”的言行舉止上,從而使接觸的人感到一種氣氛。這種氣氛就叫“氣象”。學做聖賢的“作聖之功”首先得在“氣象”上下工夫:“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是熟玩聖人氣象,不可止於名上理會。如是,只是講論文字。”(《程氏外傳》卷十)“凡看文字,非只是要理會語言,要識得聖賢氣象。”(《遺書》卷二十二上)這就是説,古代聖人因時間久遠,今人已經無法面對面接觸,獲得直接而生動的感受。爲了完整地把握古聖先賢的思想,領略他們的風采,就要善於在他們遺留下來的語言文字中感受他們的“氣象”。還説“聖賢有間”,即孔子爲聖,孟子只配稱賢,更非凡夫俗子可及。到了王陽明手裏,重新闡揚孟子“人皆可爲堯舜”的聖人觀,通過知行合一致良知,人人都可以成爲聖人。顯然,這是佛教“人人皆可成佛”的佛性説的儒家翻版。版本雖異,宗旨仍然是強調聖人作爲理想人格,不但是普通人應該學習的,而且是可以達致的,當然這是從本來意義上這麽説的。
結 語
儒家認爲人的價值在於不斷完成自己的人格,其最高目標就是成就聖賢人格。爲了實現這一理想人格,儒家提出了反省内求和格物外求兩條基本的修養途徑,其中反省内求的主體就是心性修養。而心性修養作爲建樹人格的基本途徑之一,又集中在強調心的主宰作用。心的主宰作用不但是心性學説的核心,也是儒家人格建樹的關鍵。儒家心性之學追求内在的自我超越,強調心爲主宰,體現在人格建樹上,主要是通過致誠盡性,下學上達,達致天人合一的境界,從而成爲聖人。修聖人之道,貴先立乎其本,本立而道生。本者何?心是也,心爲人之主宰,確立本心,人格的主幹才能够樹立。因此,心之“誠”無疑是心性修養,是希賢希聖的基本實踐途徑。
傳統上認爲是子思所作的《中庸》云:“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天道就是誠,人道就是追求誠。這就是原天以啓人,盡人以合天,通過盡性知天達到天人合一的崇高境界,唯有至誠盡性的人可以參天地造化化育萬物的過程,這樣的人當然只能是聖人。孟子説:“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孟子·離婁上》)孟子先賦予天以“誠”這樣的道德屬性,然後説人應該“思誠”去取得與“天道”的一致。又説:“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孟子·盡心上》)他認爲反省自己,達到誠的境界,就是最大的快樂。孟子在這裏還没有涉及理想人格的問題。荀子雖“不求知天”,但也把“誠”看作是進行道德修養的方法和境界。他説:“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至誠則無它事矣,唯仁之爲守,唯義之爲行。”(《荀子·不苟》)《大學》引申《中庸》關於“誠”的學説,以“誠意”爲治國、齊家、修身、正心的根本。唐代李翱融合儒、佛思想,以盡性或復性爲“誠”,“誠”是聖人的本性所在:“是故誠者,聖人性之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默,無不處於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李翱《復性書上》)認爲人之本性原爲純善,但被情欲所蔽,因而必須去情欲,“復其性”,使“其心寂然,光照天地”,達到至静而又至靈的内心狀態。北宋周敦頤以誠爲人的本性。他在《通書》中説,“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聖人是儒家最理想的人格典範,周敦頤認爲成爲聖人的根本條件是“誠”。張載説:“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正蒙·乾稱》)這就明確地指出了儒者致學目的是成聖。程頤在《識仁》篇中以“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作爲其境界追求的最高理想,這裏的“仁者”具備多方面的修養,實際上就是達到了“天人合一”境界的聖人。朱熹認爲“誠”是天理之本然,他説:“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四書集注·中庸注》)認爲爲人應由内心的真心實意爲本,只有“立誠才有可居處”,因此是實踐聖人之道的充分條件。
總之,現在我們重申傳統儒家“以人爲本”的理念,要使這個理念不成爲空洞的口號或者形式的教條,最主要的是要從人的内心開始,找回失落之心,確立本心,本立而道生,上達天道,常懷敬畏之心,鑄就多層次的道德人格,造就一個和諧文明的社會。
關鍵詞 心性學説 心爲主宰 人生境界 人格建樹 致誠盡性 聖人
中圖分類號B2
作者簡介韓星(1960— ),男,陝西藍田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思想文化史、儒學研究,在《哲學研究》等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100多篇,出版有《先秦儒法源流述論》《儒法整合: 秦漢政治文化論》《孔學述論》《中國文化通論》《儒家人文精神》《儒教的現代傳承與復興》《儒學新詮》等,主編《中和學刊》《中和叢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