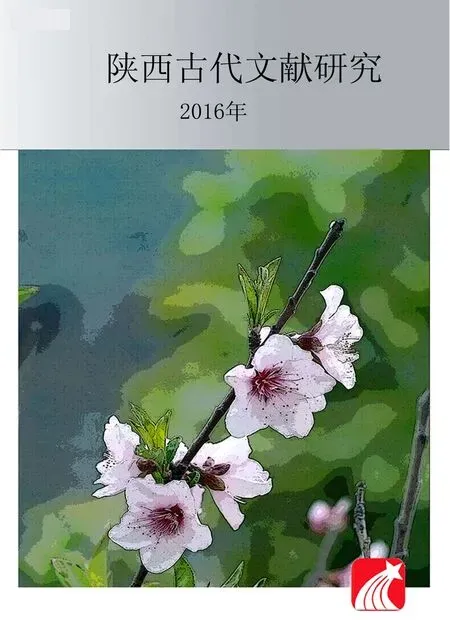《礼记说义纂订》编刊与整理述论
马梅玉
《礼记说义纂订》编刊与整理述论
马梅玉
《礼记说义纂订》24卷,明末杨梧著。杨梧(1583—1658),字凤阁,号念劬,陕西泾阳人。关西杨氏自明代以来,家世学《礼》,屡中高科。杨梧本人在万历四十年(1612)以《礼记》魁乡举,后其从子杨昌龄又于弱冠之龄以明《礼》举乡荐第一,复登进士第。于是海内治《礼》学者率以为宗,杨氏《礼》学遂声名大震。①杨梧生平参龚鼎孳《青州郡丞杨凤阁先生传》,见康熙十四年刊本《礼记说义纂订》卷首。以下引及杨昌龄《刻〈礼记说义纂订〉记略》、钱谦益等人序文,均见康熙本卷首,不一一标注。
杨梧《礼记说义纂订》成书于顺治十三年(1656),关于此书撰作之原因,杨昌龄《刻〈礼记说义纂订〉记略》称:“家世学《礼》,每对人曰:‘世道交丧,挽回之力唯礼为大。’又曰:‘教子者不始于《曲礼》、《内则》,明经者不察于《丧记》、《祭义》,而欲感发天良,端本兴治,其道无繇。’”因此杨梧“闭户经年,著成此书,其苦心为人处,经学、制举,取之咸宜”。足见其为往圣继绝学之决心,以及此书游离于经学与制举间的特质。
《礼记说义纂订》撰成后,杨梧从子昌龄请钱谦益、龚鼎孳、杨廷鉴分别作序,钱谦益序称:“先生之精诣深造,勃窣理窟,非仅资帖括、媒青紫已也。”钱氏点明此书“资帖括、媒青紫”的实用价值,同时也认为此书“精诣深造”,有超出传统经义讲章之处。杨廷鉴序有慨于礼学“习者既伙,疏者亦日繁,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赞颂杨著“以独出之见,折衷盈庭,譬之丽水之金,泛索之丽水弗得也,广收其沙而汰之,而金者乃出”。龚鼎孳《青州郡丞杨凤阁先生传》则着眼于介绍杨梧之生平概况。
然而三序既成,杨昌龄却“遭嫉者排挤,罣吏议”(龚鼎孳《青州郡丞杨凤阁先生传》),刊书之事暂时停滞,直至康熙十四年(1675)才被追还清白,而此时杨梧已忧愤而卒。昌龄遂“续刻此书,少抒遗恨”(杨昌龄《刻〈礼记说义纂订〉记略》),又请徐乾学、汪琬、慕天颜等作序。徐乾学序称此书“无分章过脉之拘,无析言破义之陋,灼然异于俗学”,徐氏精于礼学,有《读礼通考》120卷,其评价大体公允。慕天颜序云:“戴《记》一经得汉宋诸儒而尊,得凤阁先生而信。”则将杨梧于汉宋诸儒并举,认为杨书平实可信。
《礼记说义纂订》系“积五十年而成之者”(徐乾学《序》),“萃众说而撷其精,衷百家而钩其秘”(杨廷鉴《序》),其所引诸说或已亡佚,赖此书以存。其著作缘起,据其自序云:“科举原以明经,吾惧《礼》之亡于科举也,不揣固陋,拟著一书,上穷渊源,下光发挥。”可见,在杨梧看来,《礼》学与制举的关系并非势同水火。同时他也意识到世俗的制义读本常割裂经义,误导初学,故撰《礼记说义纂订》来阐明经义。不过他采用的著述体例与此前的应试读本差别并不大,徐乾学《序》对这一点有所揭示:“观其钩微掇要,固科举家所必资……今使岩谷韦带之儒,禁人勿为帖括,人必笑其迂疏。杨公父子以明《礼》取高科,而著书有源本如此。”徐氏进而发掘此书的现实意义,认为俗学之顽固已不能用学术直道救药,而要靠身处于科举而不为俗学者来曲线救治,从而赢得更多的读者,重返经学的正道。徐氏所论正合杨梧著书的本意,也印证了此书确实做到了“经学、制举,取之咸宜”,是一部具有特殊学术价值的经学读本。
清初朱彝尊撰《经义考》,其卷146著录“杨氏《礼记说义》”,云“未见”,仅据汪琬文集录出《礼记说义纂订序》一篇。蒋光煦《东湖丛记》卷2“续经义考”条载:“仁和沈椒园廉访(廷芳)撰《续经义考》,未成书也,稿本散佚,曾见其副。其《杨氏(梧)礼记说义纂订》二十四卷,所录□□(按,缺字当指蒙叟钱谦益)序、徐健庵司寇(乾学)序及龚芝麓尚书(鼎孳)《传略》。”并引沈廷芳按语云:“予获是书于闽中,读之而叹其精当明备,四十九篇之条理秩然,中惟《中庸》、《大学》二篇,以朱子有章句,故不复释,亦以见其有识。因为录二序一传,以存梗概。不录汪序者,前考中已见也。”①蒋光煦:《东湖丛记》卷2,清光绪九年缪氏《云自在龛丛书》本。沈廷芳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除庶吉士,授编修,据其按语可见乾隆时部分学者对此书价值的认可。
《礼记说义纂订》于康熙十四年刊刻,后世罕见传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此书,提要以此书“不载《经》文,但如时文题目之式,标其首句,而下注曰几节。大旨以陈澔《礼记集说》、胡广《礼记大全》为蓝本,不甚研求古义”②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95页。,而列入存目。其实此书的体例在当时颇为常见,自南宋卫湜《礼记集说》流行以来,因其采摭群言最为赅博,故此后注《礼记》者多取用卫书之体例与内容,或出具姓名,或不标出处(如陈栎《礼记集义详解》等)。而杨著的不言所出、“不复考订同异”(《四库全书总目》)与其“经学、制举,取之咸宜”(杨昌龄《刻〈礼记说义纂订〉记略》)的著述宗旨有关。杨梧在书前凡例中说:“非敢剿说扬己,实欲刊落繁文,以便观览。”明其宗旨,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纯熟的考据眼光评价杨著,便略显严苛了。
新时期学界对此书的认知尚笼罩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下,黄开国主编《经学辞典》、李正德等所纂《陕西著述志》等书也基本袭用提要的论断,未能深入发掘此书的经学史价值。而严佐之《经学、制举,取之咸宜:17世纪下叶的一种经学读本—以清杨梧〈礼记说义纂订〉为例》①参见巩本栋等编《中国学术与中国思想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99—514页。一文,通过对此书及其同时代相关著作的广泛考察,认为杨梧所著《礼记说义纂订》及与其体例相近的“经学读本”在17世纪后期的清顺治至康熙中期大量涌现,其社会文化意义非同一般。其两栖于学术和应试之间的特点,与当时的经学、制度密切相关,对清代经学发展进程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严文更从经学史的角度,发掘此书融合经学与制举的双重属性,认为清初学问与功名分为两途,因此“经学之书不宜场屋,制义之书不宜学问”。而杨梧身处清初经学的转型时期,试图将经学著作与世俗读本合而为一,最终达到假科举以明《礼经》的目的。严文视野开阔,观点独到,对杨著的价值挖掘得最为充分。由此可见,杨梧此书之价值除体现在学术本身外,还体现在其文化史意义上。此书虽非纯粹的学术研究,亦绝非仅供应试的出版物,与通常意义上的经学专著和世俗读本均不相同。
目前学界对此书版本的著录、研究,重要者有王锷《三礼研究论著提要》与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著录此书版本也仅有康熙刻本及其影印本。缘于四库馆臣将此书列为“存目”,未能充分发掘和认识其价值,当下对于《礼记说义纂订》一书,尚没有相应的点校整理成果,这与此书的学术史、文化史价值不相匹配。且目前通行的《四库存目丛书》影印清康熙刻本,将原书序文、传略、凡例、目录、参正校勘姓氏尽行删去,这对全面了解此书的成书过程、撰作背景颇不便利,影印正文复有千余字的脱漏,内容亦不够完备。因此,我们欲为学界提供一个最为完整而可信的《礼记说义纂订》校订本,力求形成一部符合新时期学术品格的古籍整理著作。其主要内容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前言:主要就《礼记说义纂订》的版本、内容、价值等做详细的考论,尤其对此书版本情况以及点校时所用底本的选择做重点描述。
(2)校勘:此书仅有清康熙十四年杨昌龄刻本,故以他校及本校为主,慎用理校。选取卫湜《礼记集说》、陈澔《礼记集说》、胡广《礼记大全》、阮刻《礼记注疏》、孙希旦《礼记集解》、朱彬《礼记训纂》等作为校本。其中所涉《礼记》本文虽不多,仍参取历代石经、宋清诸儒研核《礼记》之著作,逐次考斠,抉摘舛讹。
(3)标点:采用现在通行的古籍标点体例对《礼记说义纂订》进行标点。
(4)序跋:今日通行之《四库存目丛书》本《礼记说义纂订》(据国家图书馆藏康熙本影印),书前诸序(近一万字)悉数删落。可据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刊本之完本,依次补出卷首之杨廷鉴序(1656)、钱谦益序(1656)、龚鼎孳序(不著时日)、杨梧自序(1656)、汪琬序(1675)、徐乾学序(1675)、慕天颜序(1675)、解几贞序(1675)、凡例八则、杨昌龄《刻礼记说义纂订记略》(1675)、《礼记说义纂订》目录、参正校勘姓氏等,庶几《礼记说义纂订》之刊刻流传可得而观焉。
(5)评述:汇集清代以来目录学著作对《礼记说义纂订》的著录(如《经义考》、《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四库全书总目》等),以及前人文集、笔记中涉及《礼记说义纂订》的版本、抄传、价值评定等内容(如蒋光煦《东湖杂记》卷2之《续经义考》条等)。
(6)传记:附录有关杨梧生平、家世的相关资料,清代以来陕西、泾阳等方志中所涉杨梧及其家族文字皆予以辑录,可为读书知人之助。
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范畴之一,触及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并因时代的变迁和解释模式的不同而叠加构成了一个丰富的文化系统。近世以来,在西学强烈冲击和内部新旧更替的双重压力下,传统文化开始经历解体、重构的艰难历程,礼学的价值也受到强烈的质疑。近二十年来,礼学研究逐次复苏,然而其重心基本上在先秦礼学,对明清礼学的研究仍然薄弱。有鉴于杨著的特殊学术与文化价值,即此书将经学与制举熔为一炉,与一般性的学理著作不同,我们欲对《礼记说义纂订》进行点校整理。为了熟悉礼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意蕴,当下亟须关注、研读古代的经学读本,而杨著兼教科书与学术著作于一身,在通俗性和学术性上均有较高的价值。因此,对此书进行精心校证,对于当下阅读此书以及经学史的研究,均当有所帮助。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