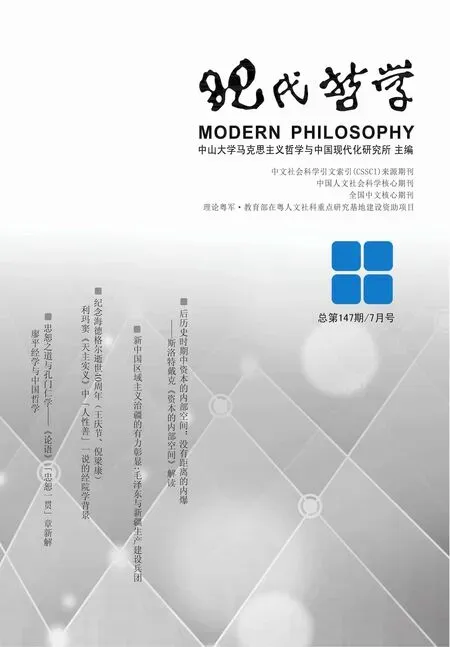巴迪欧的数学本体论究竟意味着什么?
袁 蓓
巴迪欧的数学本体论究竟意味着什么?
袁 蓓
数学本体论的提出从直接意义上说是巴迪欧反叛海德格尔“诗歌本体论”的理论尝试,后者一方面既未摆脱传统形而上学“本原”和“在场”的叙事逻辑,另一方面又脱离社会历史语境抽象地讨论存在问题。巴迪欧认为,超越传统形而上学既需要将“存在”从“一之规范性权能”中释放出来,同时也要对理论所由以产生的社会生活本身进行批判改造。在此基础上,数学本体论首先提供了一种新的关于存在的理解,即“一不存在”、“存在是多”。更为重要的是,面对当代裹挟电子媒介而来的数码操控,以及资本主义商品世界呈现出的统一性量化趋势,数学本体论还构成了对这一新的社会现实的历史映现和超越。
数学本体论;超越形而上学;一与多;数码操控;资本主义量化;事件
尽管哲学的数学想象早在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数本原”时就已被点燃,而纵观整个西方哲学思想谱系,从巴门尼德到柏拉图,从笛卡尔到康德,直至现代语言分析哲学,一种数学的敏感性也从未消散于哲学理论的建构。但是,诚如巴迪欧(Alain Badiou)自己所言,把数学与本体论直接等同起来还是足以让哲学家与数学家难以接受的。*Alain Badiou, Being and Event, London: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 2005, p.9.不过,争议的焦点并不在于哲学叙事中的数学介入,毕竟长久以来,这种介入恰恰为哲学的持存释放了活力。而是在今天,面对终结形而上学的呼声愈演愈烈以及虚无主义的普遍蔓延,沦为实证科学并与技术万能主义相纠缠的数学非但无法开出一剂有效药方,反而对此难逃其咎。对海德格尔来说,数学就绝不构成消除“对存在的遗忘”这一形而上学羁绊的主要途径,因为“数学本身就是盲点,是虚无的巨大力量,是知识对思想的抵消”。*Ibid., p.9.既然如此,那么为何巴迪欧仍要不遗余力地重申数学本体论呢?
这里再度回到海德格尔将有助于问题的澄清。从直接意义上说,“数学本体论”的提出是巴迪欧力图替代海德格尔“诗歌本体论”的一种尝试。*Ibid., p.10.众所周知,当代的形而上学几乎笼罩在了海德格尔的名下,其独特之处在于,指认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降的形而上学历史其实是存在的意义被遮蔽和遗忘的历史。为此,他宣称要返回前苏格拉底的早期希腊时期,一个存在之“思”与“诗”同时发生的时代。在那时,存在的原始意义,即“涌现”(Physis)、“无蔽”(Aletheia)和“聚集”(Logos)尚未被遮蔽,它们还未经过柏拉图主义理性化操作与科学技术加工而变为今天广为人知但却更为狭隘的“自然(物理)”、“真理(符合论意义上的)”和“逻辑”。海德格尔指出:“自早期思想以来,‘存在’就是指澄明着—遮蔽着的聚集意义上的在场者之在场。”*[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孙周兴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564页。在巴迪欧看来,海德格尔的上述思路并没有超越传统“在场的形而上学”的基本逻辑。如果说以往的形而上学总是会设定某种本原、实体或中心,对于现象而言,它是一种藏而不露的本真(即原初、根本和自明)状态,是使现象得以持存的原因和根据。而哲学的任务就是无限接近、到达和揭示这种本真状态,使其“在场”。那么,海德格尔的哲学追根溯源一种消隐的“存在的原始意义”,强调寓居并借助于“存在者”的“存在之显现”,就仍然是一种“由在场的弥散与本原的丧失所萦绕的本体论”。*Alain Badiou, Being and Event, pp.9-10.只不过他将传统所惯常言说的本原,如上帝、意识或绝对理念等替换成了“存在”(to be)。因为在他看来,前者(所谓的上帝、意识)其实已经是一些“存在者”(beings),即已被确定之物(对象);而“存在”本身不是某种对象,它是使“存在者”得以可能(成其为自身、显现自身)的背景和条件*“存在”(to be)是系词结构,它在定义和陈述任何对象(beings)时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在定义“苹果”时,我们会说“苹果是红色的”、“苹果是甜的”、“苹果是圆的”等等。通过描述“红的”、“甜的”、“圆的”等属性,“苹果”得到了界定。但其实这些不同陈述包含着一个共同的东西,即系动词“是”(to be)。这个“是”才是更为根本和原初的,它本身尚未被确定,有待于成为任何东西。一切既定之物都要借助“是”来确定和显现自身。,所以“存在”才是更为原初和本真的。虽然海德格尔区分了“存在者”与“存在”,但是“本原”和“在场”的叙事逻辑在他那里并没有消失。*也即是说,在海德格尔的视域中仍然存在着一个最为原初和根本的东西(“存在”),它是一切对象(“存在者”)的根据,这其实并没有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本原”逻辑。当然不同的是,传统形而上学往往用“理性”来书写“存在”,所以柏拉图的“理想国”最终留下了数学家而驱逐了诗人。相反,海德格尔却用“诗歌”来书写,因为他认为数学同谋于技术恰恰是使存在被遮蔽的始作俑者,而“诗的声音——只有诗的声音——作为汇聚去蔽力量的可能性根基而唱响,能够抵制技术强加于有用性存在的无限封闭”。*Alain Badiou, Manifesto for Philosoph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p.50.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巴迪欧给予海德格尔的“诗歌本体论”以激烈的反叛,因为它“与历史一样—陷入了过度在场的死胡同,存在于其中隐藏了自身”。*Alain Badiou, Being and Event, p.10.不过仍然有待追问的是,巴迪欧为何一定要选择数学本体论来进行反叛?“数学是本体论”展现出哪些不同于传统话语的理论特质?它的意义和价值究竟何在?
一、何以“存在”是“多”而不是“一”?
事实上,当现代技术已然将人类从地球上彻底地“连根拔起”,巴迪欧并非没有洞悉海德格尔转向隐喻和诗歌的旨趣所在。毋庸置疑的是,自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从而为近代以来的哲学奠定了主体-客体辩证法的理论基调,实证科学(数学与物理学等)的兴起非但没有改变反而促使哲学在这条“客体化”(即把对象当作主体的表象物,主体能够对其进行处理和操控)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以致当我们的生活世界身陷于资本操控与技术座架而歧途难返时,哲学除了宣称自我终结之外竟做不出任何反应。*比如,当代广为人知的“形而上学的终结”、“主体之死”无一不表征着“哲学之死”。在哲学郁郁寡欢与茫然无措的情况下,诗歌的想象被再度点燃。巴迪欧指出:“时至今日,海德格尔思想中令人信服的影响力在于他汲取了诗歌中的重要因素,这就是客观拜物主义的缺席,真理与知识的对立,最后是表征我们时代本质的无方向性(disorientation)。”*Alain Badiou, Manifesto for Philosophy, p.74.显然,由于诗歌远离现实、弥散着自由的隐喻(抵制客体化)且表征了某种晦暗朦胧(不指向明确方向),所以把它与哲学进行“缝合”(suture)就构成了海德格尔反叛(对抗)现实的一种策略。但是这种“缝合”却带来了一个消极后果,这或许是海德格尔自己也始料未及的,就是原本逼仄狭小的哲学空间被彻底侵占。换句话说,哲学本身被搁置和取缔了。“哲学没有完成‘笛卡尔式的沉思’,便误入歧途热衷于意志的审美,完满的悲怆,遗忘的命运以及迷失的踪迹。”*Ibid., p.58.而这一点恰恰是巴迪欧不甚满意和难以接受的。巴迪欧固然不反对诗歌介入哲学运思,这其实是他颇为赞赏海德格尔的地方。他所不能接受的是把哲学与诗歌、政治或是科学等单一条件进行“缝合”,即哲学将全部思想和功能交付给某一个孤立的条件(如纯粹诗歌),从而放弃一种诸条件*巴迪欧认为存在着四种条件,分别是爱、艺术、科学和政治。同时共存空间的建构。“缝合”的理论操作意味着诸条件对称的局面被打破,哲学成为某种单一话语的“独白”,因而这在本质上就没有摆脱巴迪欧长期以来所极力反对的传统形而上学诉诸于“一之规范性权能”(the normative power of the One)的思维方式和问题框架。在巴迪欧看来,传统形而上学的本质特征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就是“一将存在框住”(the enframing of Being by the One)。*Alain Badiou, Briefings on Existence: A Short Treatise on Transitory Ontolog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p.34.那么它是如何表现的呢?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解,“存在”(Being,也即to be)本是尚未确定,有待成为任何对象的。但由于传统形而上学所关注的是“是什么”(What is)而非“是”(is)的问题,所以未确定的“存在”被理解成了既定的“存在者”(beings)。而近代以来自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存在”就完全变成了主体表象物,即所有存在物都是由意识所构造的,存在等于被意识的存在。滥觞于笛卡尔、中经康德和黑格尔直至尼采,形而上学将原本未确定的“存在”全然变成主观设定的(由主体审视、控制和利用的)“存在者”,这种主体性话语霸权的确立(即主体设定存在,主体成为永恒在场的本原和根据)就体现出了“一框住存在”的性质。后来海德格尔反叛这种主体理性形而上学,指认诗是存在最原初的语言,不过是用一种话语霸权替代另一种话语霸权,而“一将存在框住”的情况并未改变。*因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并未突破传统形而上学“本原”和“在场”的叙事逻辑。巴迪欧认为,只有将“存在”从“一的规范性权能”中彻底释放,才能谈得上反叛传统形而上学,而他的“数学本体论”恰好提供了可能的视域和途径。
首先,巴迪欧的策略是探寻柏拉图的踪迹宣称“一不存在”(the one is not),也就是从根本上取消“一”之存在的可能性。柏拉图曾在《巴门尼德篇》中指出,如果“一存在”,这个假设就首先说的是“一”,肯定“一”就意味着它不是“多”。也就是说,“一”与“多”是漠不相关、彼此孤立的。那么从这个孤立的“一”出发进行推导最后得到的结论却是“一”本身的自我矛盾和毁灭。*由于本文篇幅有限,柏拉图的详细论证可参见《巴门尼德篇》的相关章节,本文不再赘言。这个结果自然是柏拉图难以接受的,所以他推翻了“一存在”的前提,指认并不存在一个孤立的、与“多”相分离的“一”。对于“一”,必须把它同“多”联系起来才能理解。应该说柏拉图还是敏锐地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事实上,当我们说“一存在”时,并不意味着只有“一”,不是说我们只谈到了“一”而没有论及他者。将“一”与“存在”看成完全等同、彼此毫无差异,这是巴门尼德的观点。“一存在”其实是一个判断,任何判断都有主词和谓词,二者具有不同含义。在“一存在”这个判断中,我们为主词“一”加上了谓词“存在”,这就意味着“一”被增加了新的内容。后来康德区分“综合判断”与“分析判断”进一步表明,一切真正的知识必须首先是综合判断,即谓词不包含在主词概念之中,二者的连接为主词增加新的内容。而康德之后,黑格尔更是激烈抨击形式逻辑“A是A”的无差别同一,指认后者完全是一种纯粹的同义反复,没有说明和增加任何内容,因而也就不可能构成知识。所以,柏拉图后来提出“一不存在”,显然也是看到了真正的命题都是主词与谓词有差异的统一。因为当我们说“一存在”时,假如这个命题是有意义的,我们就绝不是在单纯地意指“一是一”,而是“一”与“存在”两个差异内容的统一连接。这里面其实已经发生了“一”同“他者”的联系,而“他者”的出现(差异性)就包含了“多”的意思,所以绝对孤立的“一”是不存在的。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中所进行的“一”和“多”的讨论后来得到了巴迪欧的高度评价。他指出,由柏拉图的“一不存在”我们可推导出一种“多之他者性无止境的自我区分”(otherness of the multiple becomes an unending self-to-self differentiation),在这里“非一致性多”(inconsistent multiple)的主题被发现了。*Alain Badiou, Briefings on Existence: A Short Treatise on Transitory Ontology, p.36.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迪欧确立了数学本体论的理论基石,即“存在是多”而不是“一”。
虽然否认“存在是一”,巴迪欧却又宣称存在着一种“一的影响”(effect of one-ness)。他指出,仅仅纯粹的多,也即“非一致性的多”实际上是不可思的。“一切思想都以可思之物的某一情势(situation)为前提,也即一个结构(structure),一种‘计数为一’(count-as-one),在其中被显现的多(the presented multiple)是一致的和可数的。因此,非一致性的多——在给它以被结构的一之作用(the one-effect in which it is structured)之前——只能是一个无法被捕捉的存在视域。”*Alain Badiou, Being and Event, p.34.简单来说,巴迪欧虽然并不承认“一存在”,但却认为存在着针对“非一致性多”进行的“计数为一”的“操作”(operation)和“结构”,也即“情势”。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其实巴迪欧还是在强调,对于“多”,我们也必须把它同“一”联系起来才能理解。不过在这里,他对于“一”与“多”关系的处理却借鉴了集合论“属于”(belonging,∈)的数学逻辑。巴迪欧指出:“多是根据一种属于的逻辑形式被内在设定的,也即根据这样一种模式,在其中‘某物=a’一般是按照一个多元β来显现的。这可以写成a∈β,即a是β的一个元素。被计数为一的不是多的概念(concept);对一-多(one-multiple)是什么的思考无法被书写。一只能被归于∈的标记;也就是说,被归于一种赠予的操作(the operation of donation),它指向一般意义上的‘某物’与多之间的关系。符号∈,即对任何一之存在的取消(unbeing of any one),规定了被多所指引的‘某物’以一种统一的形式显现。”*Ibid., p.44.也就是说,在巴迪欧看来,存在本质上是多,所以当我们宣称一个“多”存在时,是在这个多属于另一个多,也即它成为另一个多的一个元素的意义上指认其“存在”的。举例来说,对于一个叫“张三”的人,由于他本人是多(有待成为任何一种人,to be anyone),如“张三是中国人”、“张三是男人”、“张三是哲学家”、“张三是父亲”等等。所以当宣称“张三”存在时,我们会追问到底是在哪个意义上说他是存在的。因此,想要确证“张三”的“存在”,我们必须在一个具体情势中,在他适合于某个集合计算和识别其要素的法则的意义上去讨论。也就是说,需要首先给予限定,比如指明是针对一个“中国人集合”,即一个所有元素都是中国人且被计数为一个整体(count as one)的集合。在“张三”属于“中国人集合”(不是“哲学家集合”),也即他被这个集合计数为一个成员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张三存在”。
将数学引入本体论,巴迪欧的目的是想要超越传统形而上学“本质主义”的话语方式。我们知道,哲学自古希腊以来就表现出“多中求一”的理论冲动,也就是说,人们想要从感性万物(“多”)中找到一个永恒在场的不变根据(“一”),以解释万事万物的生灭变化。这使得传统哲学从一开始就呈现为一种由“本原”和“在场”所萦绕的本体论叙事,其逻辑后果则是巴迪欧已经指出的“一框住存在”。不同于海德格尔走向诗歌的不甚成功的反叛之路,巴迪欧选择了数学作为批判的武器。不过显见的是,尽管巴迪欧以回归数学的姿态重构本体论,但是他所推崇并诉诸的既不是被毕达哥拉斯学派视为“第一原理”的数学,也不是与技术主义纠缠不清的实证数学,更不是语言分析哲学视域中沦为语言游戏或语法规则的数学。因为在他看来,以上形式的数学都无法改变传统形而上学的解释框架,而真正富有借鉴意义的是集合论。那么集合论究竟具有哪些特质呢?事实上,所谓集合,是就“属于”关系而言的诸种元素(“多”)的“聚集”(collection),也即“计数为一”,它“排除了任何对多的明确界定”。*Ibid., p.60.也就是说,集合论关注的是不同方式的计数问题,也即诸种元素如何被整合和计算为一个整体,而对于它所操作的元素究竟“是什么”(即本质问题)则并不关心。“通过对各种变量进行统一(uniformity),集合论表明它不讨论这个一(the one),也不下定义(without definition)*集合论不讨论“the one”(这个“一”),这与巴迪欧宣称“the one is not”是相一致的。因为讨论“the one”还是从传统形而上学实体论的视角去理解“一”,即把“一”视为现象背后永恒在场的某种本原、本质或根据,比如这个“一”是“上帝”、“意识”、“绝对理念”等等。集合论也不“下定义”。因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下定义”就是通过“属+种差”的方式揭示某个事物的本质,以把它同其他事物区分开来。因此“下定义”仍然属于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操作。,在其法则内部所全部显现的都是多。任何多都内在必然地是诸多之多(multiple of multiples):这是集合论所展开强调的东西。”*Alain Badiou, Being and Event, p.45.可以看到,集合论同样讨论“一”与“多”,但其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从一种结构和关系的视角出发去考察二者的。在这里,“一”不是传统形而上学中框住存在的本原或实体,而是一种“计数为一”(也即“使……成为一个元素”)的操作、结构和影响。这意味着“一”与“多”所关涉的不是本质与现象,而是指向一种关系性的存在方式。“属于一个多的东西(what belongs to a multiple)通常也是一个多;成为一个元素(being an‘element’)并不指涉一种存在地位(a status of being),一种内在性质(intrinsic quality),而仅仅是关系(relation),将要成为……元素(to-be-element-of)的关系,借此一个多通过另一个多被显现。”*Alain Badiou, Being and Event, pp.44-45.由于“一”是“计数为一”的操作,是给予“多”的一种影响。所以“存在是多”在本质上并未改变,只不过是“多”的显现方式发生了变化,即在“一的影响”下,“多”由“非一致性”的变为了“一致性”的。这样一来,在“一”与“多”之间并不存在哪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由此传统形而上学“本原”和“在场”的叙事逻辑也就被取消了,存在作为“多”彻底地从“一之规范性权能”中释放出来了。
二、数学本体论的历史性之维
当数学本体论宣称“存在”是“多”而不是“一”,当话语逻辑从“多中求一”转向“诸多之多”,这似乎足以表明巴迪欧完成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超越。但事实上,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巴迪欧指出:“哲学直到最近才懂得如何用与资本相称的术语来思考,因为它曾让这个领域最本质的方面去徒劳地怀念神圣的束缚,执迷于在场(Presence),服从于诗歌的模糊的统治,怀疑其自身的合法性。它不曾知道如何让思想理解下述事实:即人已经无可逆转地成为‘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而这里的问题既不是丧失也不是忘却,而是至高无上的目标——尽管仍然以计算时间愚蠢的含混性为特点。”*Alain Badiou, Manifesto for Philosophy, p.58.以上叙述所针对的虽然还是海德格尔,但是巴迪欧却在这里揭示了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事实上,传统形而上学的症结并非海德格尔所指认的存在意义的遮蔽或是存在本身的遗忘,所以,他作为药方所提出的“诗歌本体论”也就自然会沦为一种浪漫式怀缅。不管是做出存在论区分(即区分“存在”和“存在者”),还是用诗歌去书写存在,倘若理论建构的终极旨趣依然锁定于“奠基”,那么传统形而上学就不会从根本上被颠覆。因为超越形而上学并不在于某种话语逻辑的改变或是理论根基的重置,而是在于对思想所由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本身的批判和改造。在这一问题上真正带来变革的是马克思。针对青年黑格尔派所热衷的以思想上的变革取代现实中的革命,马克思就曾直截了当地给予批判:“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页。马克思的非凡之处就在于,他并没有通过开启一种新的理论视角或是寻找一个新的话语逻辑来重建形而上学,相反,他所要做的是彻底颠覆一切形式的形而上学。这表现在:一方面,他着眼于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内在同构关系,揭示形而上学建构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他清楚地看到,思想本身的改变是以现实生活的变革为基础的,所以超越形而上学必须以批判和颠覆它所由以产生的社会生活为基础。这样一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缘何在《资本论》开篇伊始马克思选择“商品”而非传统哲学普遍言说的“存在”作为研究起点了。倘若说“存在”就是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它实际上包含着整个社会结构和组织关系。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当商品成为统治一切的普遍性力量,商品结构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主导性结构,当一切物和人无不受到商品形式的规制时,“存在”也就获得了“商品”这一具体的历史规定性。马克思深知,只有理解并超越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生活才能真正洞察存在之本质问题。所以,他从一开始便选择“商品”而非“存在”作为其理论研究的对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迪欧并没有给予海德格尔的诗歌本体论以过高评价,尽管后者可以说重新奠定了现代哲学的理论基调。因为海德格尔同样脱离了现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生活的现实语境来追问存在本身的意义,如此一来,他的解释框架依旧是抽象乏力的。相比之下,当巴迪欧提出“数学是本体论”的命题,绝不意味着他要为形而上学重新奠定一种数学基础,而是“数学作为一种存在的历史情势建构了本体论”。*Alain Badiou, Number and Number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8, p.212.也就是说,数学本体论在巴迪欧那里不单纯是理论思辨,它还与当下社会历史生活的建构相联系,是其时代定位与现实诊断的一种表达。
从最直接的意义上说,将数学视为本体论,这源自“数”在当代社会生活与日俱增的地位和影响。只有当现实存在本身获得了“数”的普遍规定,才会在哲思层面产生数学本体论。历史唯物主义早就指出,意识形态本身“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页。,思想、理论和观念的变化是“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同上,第73页。因此,数学本体论的提出是当代社会历史条件发展变化的产物。按照巴迪欧的定位,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由数统治的时代;思想臣服于可数的多的法则”。*Alain Badiou, Number and Numbers, p.1.这表现在“数”不仅操控了日常的政治与经济生活,甚至也控制着人们心灵和文化的表达。比如,当代民主政治的主要表现与实现形式就是“一人一票”的公民投票,而投票制度首先遵循的原则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这里面其实已经蕴含着一种“计数”法则,更不用说计算选票结果所需要的各种算法直接与数学密切相关了。特别是在计算机网络普及化的今天,随着各种投票系统、软件和网站层出不穷,投票也逐渐由“线下”的真实活动变为“线上”的虚拟操作。这意味着整个投票活动不仅是一个不断“计数”的过程(计算选票),而且投票本质上表现为一种由“0”和“1”两个数字操控的代码运行模式。根据鲍德里亚的分析,在当代,无论是公民公决、还是民意调查,一种“数字性在纠缠我们这个社会的一切信息,一切符号,它最具体的形式是测试、问∕答、刺激∕反应”。*[法]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88页。也就是说,人类整个交流模式都可被还原为一种0∕1、问∕答的二元信号系统。这样一来,原本旨在彰显自由和民主的公民投票则走向了相反面,变得强制和随机起来。因为选民的回答事实上早已按照预先设计好的程序(系统)被控制了。“当民主达到先进形式阶段时,它的分配比例将大致相等(50∕50)。投票酷似粒子布朗运动或概率论,就好像是大家都在盲目地投票,就好像是一些猴子在投票。”*同上,第99页。在这里,“数字性”,这种新的操控形态的生成是显而易见的。
鲍德里亚曾指出,受代码支配是当今时代的主要模式,这从根本上不同于工业时代的生产模式。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从“生产主导”向“消费主导”的根本转型。在消费社会中,伴随现代电子媒介(电视、手机、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与全面普及,一切物、人及其活动都被编制到符码体系之中。这意味着重要的“不是商品价值,而是计算价值,即这一切不是为了生产而被调动,而是作为操作变量被编目,被传唤,被勒令运转,不是变为生产力,而是变为代码棋盘上那些遵守相同游戏规则的棋子。生产的公理仍然倾向于把一切都仅仅简化成要素,代码的公理则把一切都简化成变量。前者通向一些力量的等式与平衡,后者则通向一些变动而随机的集合……”*同上,第17页。今天,消费社会的符码操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当代资本主义消费过程中,消费品并不以其自身的物理功能或使用价值,而是以象征性符号价值获得确证。换句话说,“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从广义的角度)用来当做能够突出你的符号,或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1页。其次,主体一旦参与到消费活动中,也就进入到了一个“全面的编码价值生产交换系统中”*同上,第60页。,从而获得一种符号认同与交流。最后,伴随消费逻辑取代生产逻辑,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操控策略也发生变化,即由工具理性和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统治转变为消费意识形态统治:“消费是用某种编码及某种与此编码相适应的竞争性合作的无意识纪律来驯化他们;这不是通过取消便利,而是相反让他们进入游戏规则。这样消费才能只身替代一切意识形态,并同时只身担负起整个社会的一体化,就像原始社会的等级或宗教礼仪所做到的那样。”*[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刚译,第78页。简而言之,在鲍德里亚看来,当今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由数码、符号全面操控的时代,他甚至将其视为一种“代码恐怖主义”。*[法]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第14页。如果鲍德里亚的这一判断并非危言耸听,现代电子媒介的符号编码确实深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数字化”成为当今时代的本质特征之一,那么巴迪欧从理论层面提出“数学是本体论”也就绝非偶然了。
倘若我们更进一步思考就会不难发现,这种数字化在当今时代的全面崛起,实际上正是资本力量作用的结果。巴迪欧指出:“如果数的支配——比如在民意调查或选举中,在国民核算或私人企业中,在货币经济中,或是在对主体的反主体的评价中——并不是以数本身或是对数的思考为依据的,那么这是因为它遵从了一种简单的情势法则,这就是资本的法则。”*Alain Badiou, Number and Numbers, p.213.那么资本的法则是如何体现的呢?简单来说,在今天,资本趋向于抹平“质”的差异,将一切都还原为可计算的“量”。这种“量化”的“统一性”霸权逻辑就是资本的法则,其直接后果就是“数”对我们日常生活无处不在的支配。根据马克思的分析,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细胞的商品包含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二重属性。使用价值是商品的有用性,它决定于商品体本身的物理属性,因而体现了商品质的差别。交换价值“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9页。,它表现了商品量的差别。尽管一切商品都可从质与量之双重维度加以考察,但是“在考察使用价值时,总是以它们的量的规定性为前提”。*同上,第48页。因为交换活动得以进行的关键在于,商品总是在量而非质的层面上被加以比较和衡量。比如我们可以说一担米等于若干量铁,但却不能直接说米等于铁。所以说,“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本身中,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为同它们的使用价值完全无关的东西。”*同上,第51页。特别是在商品经济普遍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当交换价值超越使用价值成为交换的终极目的,这意味着“量”超越了“质”占据主导。因为此时,人们更为关心的是通过商品生产和交换获得的价值增殖,而价值增殖无非就是一种数量的增长,至于具体交换的商品究竟是小麦还是钢铁则无关紧要。所以马克思指出:“所以要生产使用价值,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基质,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同上,第217页。只是这里仍需追问的是,既然商品只能从量的层面加以比较,比如一定量小麦等于一定量铁,那么两种不同商品之间所共同等量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呢?按照马克思的理解,这种共同的东西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人类劳动。抽象劳动是去除了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即去除了质的差别的劳动。它“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同上,第51页。正是由于抽象人类劳动物化在商品中,商品才具有价值。所以,商品的价值量最终是由凝结在其中的劳动的量来计算的。而劳动本身的量又是由劳动时间来衡量的,也即是用小时、天等一定的时间单位作为尺度的。到这里已经不难发现,在经过一系列的追溯后,其实商品最终是落脚于一种时间的量。因此可以说,在现代商品经济中,真正给予商品以本质界定的其实是形式化的量,而商品原本内在的质反倒不那么重要了。
在当代社会中,一切“存在”可以说都具有了商品形式。这意味着存在物“已经不再作为在劳动力有目的地发挥作用时执行一定职能的物质因素了。它们只是作为一定量的对象化劳动来计算。无论是包含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或者是由劳动力加进去的劳动,都只按时间尺度计算”。*同上,第228页。与之相伴随,一切劳动过程也无一不成为价值形成过程。前者,即劳动过程的本质在于它是生产使用价值的有用劳动,在这里“运动只是从质的方面来考察,从它的特殊的方式和方法,从目的和内容方面来考察”。*[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27—228页。而在价值形成过程中,“同一劳动过程只是表现出它的量的方面。所涉及的只是劳动操作所需要的时间,或者说,只是劳动力被有效地消耗的时间长度”。*同上,第228页。这种交换价值取代使用价值,价值形成过程取代劳动过程,即质的方面被扬弃并进而过渡到可数的量,可以说是现代商品世界的一个本质特征。而数学本体论正是对这种统一性量化现实过程的一种表现。前文已述,巴迪欧本体论的基础是取消“一”的存在,而宣称“存在是多”。但是巴迪欧又认为,纯粹的多是无法显现和被思考的,所以他指认存在着“一的影响”,即一种给予“非一致性多”以“计数为一”的操作和结构。在这种“一的影响”下,纯粹的多被整合和集聚,变成一致性和可数的“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统一化”的过程,即“非一致性多”被统一化为“一致性多”的过程。反观现实,无论是从“质”的层面被加以规定的使用价值以及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还是从“量”的层面被加以规定的交换价值以及生产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可以说它们本质上都是“多”。但不同的是,“质”是“非一致性的多”,因为某一定在之物与他物相互规定的链条总是无限的,所以“质”是无限多样化的,也即是“非一致性的多”。而“量”是“一致性的多”,在马克思的商品分析中,商品的价值与抽象劳动最终都落脚于一种时间的量。这种时间的量一方面是以秒、分钟、小时和天等一定的时间单位为尺度,是由每分每秒、每时每刻累加而成的,所以它是一种“多”。但另一方面,时间的量是可被计算和限定的(可数为一),因而作为一个可被规定者,“量”是“一致性的多”。当代资本主义商品世界出现“量化”趋势,即将多样化的“质”还原为(统一化为)可数的“量”,正是“非一致性多”被统一化为“一致性多”的过程。事实上,资本积累与增殖始终与对时间量的计算密切相关。资本的本性在于最大限度的获得剩余价值,而要实现这一点,无论是通过增加绝对剩余价值还是相对剩余价值,都与劳动时间量投入的多少直接关联。此外,资本流通时间的长短也制约着资本能否迅速增值。正是由于时间的量对于资本运行至关重要,所以“量化”才成为资本主义商品世界的本质特征和主要趋势。巴迪欧指出:“要思考并超越资本及其平庸的规定(对时间的一般运算),我们必须从资本已经揭示出来的起点出发:存在从本质上说是多……”*Alain Badiou, Manifesto for Philosophy, p.57.这样来看,巴迪欧宣称“存在是多”并且引入数学集合论讨论“多”的统一化(即计数为一)过程,这是从资本所由以揭示的起点出发进行的理论建构,是一种回到历史生活同时又旨在揭示历史生活的“历史性”思考的结果。
三、再思考:数学本体论究竟意味着什么?
如果说数学本体论与当下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情境具有一种内在同构关系,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巴迪欧的理论探索仅仅停留于单纯地描述和解释资本主义发展的诸种新情况呢?事实正好相反。在巴迪欧那里,数学本体论同时也是建构新的解放政治学的一种理论探索。也就是说,巴迪欧理论建构的真正旨趣在于对理论所由以产生的社会生活本身进行批判性改造,更具体地说,就是对裹挟数码操控的资本力量进行超越。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再度审视数学本体论将具有特别意味。
巴迪欧指出,数学本体论的功能不仅是阐释现代哲学的特殊问题,而是也要解决“什么不是关于存在之为存在”的问题。而“‘什么不是关于存在之为存在’的领域(这并不是一个领域,而是一个切口,或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是一个增补)是根据两个相近的和全新的概念组织的,这就是真理和主体的概念”。*Alain Badiou, Being and Event, p.15.如果说传统本体论是在“一之规范性权能”的框架中追问“什么是存在之为存在”,那么当数学本体论宣称“一不存在”,也就同时遭遇了“什么不是存在之为存在”的问题。在巴迪欧的视域中,解答“什么不是存在之为存在”的关键最终落脚于“事件”(event)。*Ibid., p.189.这里“事件”概念的提出可以说是巴迪欧哲学的一个重要事件,因为它勾画出了其替代性想象的基本轮廓。那么究竟什么是事件呢?简单来说,巴迪欧将“事件”视为一种“超越-存在”(trans-being),一种“存在的中断点”。(Being’s breaking point)。*Alain Badiou, Briefings on Existence: A Short Treatise on Transitory Ontology, p.60.我们知道,巴迪欧本体论的基本命题是“存在是多”,但与此同时他认为“多”是不能脱离与“一”的关系被理解的。不过迥异于传统的是,在处理“一”与“多”关系时,巴迪欧引入了数学集合论的“属于”逻辑。也就是说,“存在”作为“多”,总是在它属于另一个“多”、被另一个“多”计数为一的意义上说是“存在”的。所谓“存在”(to exist)就是“属于一个情势”(to belong to a situation)。*Alain Badiou, Being and Event, p.372.与之相对,“事件”则是一种纯粹“偶然性”的出现,它不被“计数为一”。“从情势的角度来看,如果存在一种事件,那么它是否属于该情势是不可判定的(undecidable)。”*Ibid., p.18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迪欧将“事件”看作是“超越-存在”,是对“什么不是关于存在之为存在”问题的解答。假如“情势”是被“计数为一”的“一致性多”的领域,它象征一种有序、封闭和僵死的结构,那么“事件”所代表的就是对任何既定结构的中断和打破。在《存在与事件》的英文版前言中,巴迪欧还曾对“事件”做过一个相当精炼但却富有深意的界定:“真理只有通过与支撑它的秩序决裂才得以建构,它绝非那个秩序的结果。我把这种开启真理的决裂称为‘事件’。真正的哲学不是始于结构的事实(文化的、语言的、制度的等),而是仅仅开始于发生的事件,始于仍然处于完全不可预料的突现的形式中的事件。”*Ibid., pp.xii-xiii.在这里,给予真理性事件以积极忠诚的行动者就是“主体”。巴迪欧认为,主体是致力于人类解放运动的“真理斗士”。*Ibid., p.xiii.可以看到,倘若说今天我们身处于其中的“当下”正是由资本力量所塑造和操控的,而资本本身又表现出一种不断结构化的螺旋式发展。尽管资本结构并非僵死静止的,但它却也呈现出一种吞噬性的封闭状态。这种封闭性就体现为所有人与物无一例外都要遭受资本结构的统摄,资本家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主体-客体历史辩证法亦丧失效力。那么巴迪欧赋予“真理事件”以突发性决裂的理论内涵,并且强调主体是对这种真理事件的忠诚,就无疑彰显出了中断和打破资本结构化之平衡与封闭的理论旨趣。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主义从其诞生到今天的发展,其背后往往需要“契约精神”、“诚信理念”等这种包含忠诚形式和要素的主体支持。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主体的认同与忠诚反过来亦可以成为超越资本力量的一种解放策略的突破口。正如哈贝马斯已经看到的,当代资本主义危机转变为一种“认同危机”,即资本主义社会经常无法有效维持大众的普遍认同和积极忠诚。
所以,数学本体论在今天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存在与事件》中,巴迪欧曾这样写到:“我们的目标是确立元本体论(meta-ontological)的命题,即数学是关于存在之为存在的话语的历史。这个目标的目的是给予哲学以两种话语(和实践)的可能的连接,而这两种话语自身并不是哲学:即数学,这个关于存在的科学,以及事件的介入性学说,准确地说它表达了‘什么不是存在之为存在’。‘本体论=数学’的命题是元本体论的:这排除了它本身纯粹是数学的,或纯粹是本体论的可能。这里必须承认一种话语的分层。这个命题的展开规定了某些数学片段的使用,然而它们受到的是哲学规则的制约,而不受当代数学法则的制约。简言之,数学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就在于它在历史上说明了每一个‘对象’都可化约为一个纯粹的多……”*Ibid., pp.13-14.关于数学本体论,巴迪欧的这段论述可以说向我们释放了足够的信息。在他看来,数学本体论首先提供了一种新的关于存在的理解,它旨在揭示“存在”是“多”而非“一”。其实,巴迪欧将数学(主要是集合论)这一原本意在考察各种数量关系的形式科学引入本体论讨论,无非是要建构一种“数多”的理论景观。而这一操作就其直接的意义来说,不过是一种用与资本相称的术语进行思考的结果。“存在是多”,这是从资本所由以揭示的起点出发得出的。因为在今天,资本主义商品世界展现出统一性量化的形式化趋势,我们的生活到处充斥着数量关系的冷酷算计,而当今时代又是一个全然由数码操控的时代。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来看,数学本体论就不单纯是一种“存在论”,即从纯理论逻辑层面抽象地、一般地思考何谓“存在之为存在”,而是它提出“存在是多”的命题本身构成了对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一种历史的映现。其次,在巴迪欧的视域中,数学本体论还是元本体论的。这意味着哲学本身不是某种单一话语的“霸权”(比如海德格尔的“诗歌本体论”),而是诸种条件(主要指爱、艺术、科学和政治)相聚共存的场所,是多元话语的内在生产。就此而言,巴迪欧提出“数学是本体论”的命题就不仅仅是关于世界的命题,而也是关于话语的命题。它标明了一种存在的言说得以发生的多元化空间状态。而要实现这一点(即吸收多元哲学条件并使之共存),巴迪欧认为,我们就需要打破传统哲学“存在之为存在”的“一”之理论框架,引入“什么不是存在之为存在”的问题,后者所关涉的就是“事件”。因为“事件”所代表的就是对一切既定情势和结构的中断和增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数学本体论还彰显了一种解放政治学的维度,即主体通过对真理性事件的忠诚以从资本结构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由此再度审视巴迪欧的数学本体论,或许借用他本人评价阿尔都塞的一个表述倒是再合适不过——“哲学就是一个行动,而不是解释”。*[法]巴迪欧:《小万神殿》,蓝江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7页。
(责任编辑 林 中)
袁 蓓,(北京 100871)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B565.59
A
1000-7660(2016)04-0015-10
——围绕《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的若干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