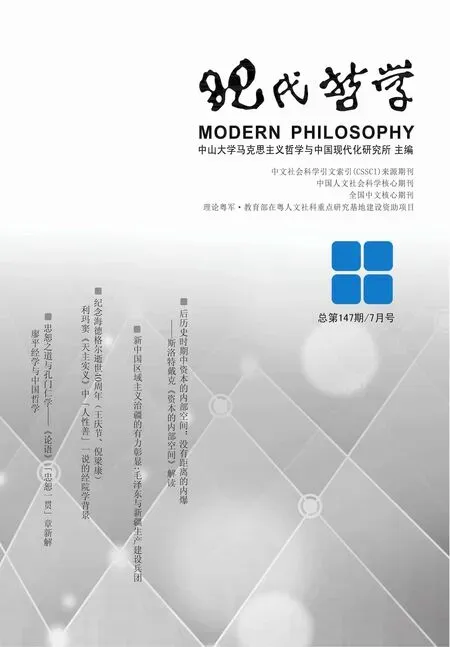从“土改补课”到合作化:改造落后乡村运动中的再次动员与制度转化
李飞龙
从“土改补课”到合作化:改造落后乡村运动中的再次动员与制度转化
李飞龙
土地改革以后,新政权虽然对乡村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的整合,但远未达到政令通行贯彻无阻的目的。尤其在“山高路远、地广人稀”黔南地区,仍有一些被认为是土改不彻底的三类村,因而需要对这种传统内向型的落后乡村进行再次改造。在宣传引导、组织建立、利益与情感启发等措施的动员之下,改造落后乡村运动得以完成。但是,这场立足于“土改补课”的改造落后乡村运动却随着合作化运动的深入最终演变为集体化的实现途径。
合作化;土改;黔南;改造落后乡村
1954年到1956年,正值农业合作化运动推进之际,全国“仍有一部分(全国大约有10%)乡村的工作处于落后状态”。为此,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特意讨论了《关于改造落后乡工作的指示》*《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报告》(1954年5月1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第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61—273页。,试图解决“土地改革运动中反封建斗争发展不平衡和不彻底而遗留下来的落后”问题*《中共中央关于改造落后乡工作的指示》(1954年8月1日),黔南州档案馆:1-1-229。。不过,这场立足于“土改补课”的改造落后乡村运动却随着合作化运动的深入最终演变为集体化的实现途径。
这种转变和发展在基层是如何体现的?改造落后乡村运动的动员效果又怎样?目前还未有专门的讨论。笔者曾经梳理了土改后改造落后乡村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尝试去解释改造落后乡村过程中分配土改斗争果实与农业集体化实践之间的关系*李飞龙:《土改后改造落后乡村政策的历史演变》,《东岳论丛》2013年第10期。,但仅限于政策层面的考察。因此,对土改后基层改造落后乡村运动的研究,可为我们从微观和实践层面反思土地改革和合作化提供一个切入点。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新解放区的黔南为考察中心,通过对黔南乡村社会状况、运动发起、村庄动员与制度转化的梳理,试图呈现国家与山区社会之间的关系,以期对建国初期的政治运动进行反思。
一、黔南乡村社会与
“土改补课”的发起 黔南位于贵州省中南部,自古以来由于多山,交通极其闭塞。清代,黔南对外联系基本上是靠驿运,陆运靠人挑、马驼,水运则靠木船输运。清乾隆年间爱必达曾对黔南乡村这样描述,都匀府“四乡村寨,跬步皆山,溪流萦绕,田颇膏腴”*[清]爱必达、[清]张风笙著,杜文铎等点校:《黔南识略·黔南职方纪略》,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7页。。近代以后,公路、航运、无线电、邮政等新式交通、通讯的兴起推动了贵州现代化的发展。不过,相比较全国,贵州仍是最为落后的省份之一,尤其在黔南乡村。李菲记载,惠水县有一个乡下病人到县城医院住宿,“不睡病床而睡在地板上,据他说:‘床上白白的布、太干净,恐怕弄脏,我不敢睡。’由这个故事,我们可知道一般乡下人的生活,是怎样的苦楚了!”*李菲:《惠水一瞥》,刘磊主编:《抗战期间黔境印象》,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39页。抗战时期,黔南多县遭到了战争的巨大破坏。贵州商人吴禹丞在1944年日军侵犯黔南后写到:“独山、荔波、三都、丹寨、都匀五县,焚掠之惨,历史上恐为前例。”“以独山而论,人民之无家可归者比比皆是,为饥寒、疾病所困者,仍占十分之八九,为数在十万以上。”*吴禹丞:《不堪回首话黔南》,刘磊主编:《抗战期间黔境印象》,第478—479页。可以说,在新政权接收贵州之前,黔南乡村处于一个相对封闭而又十分落后的境地。
新政权建立以后,黔南开展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建立和巩固了各级人民政权。到1952年下半年,伴随着以民族地区为重点的第四期土改的结束,黔南地区的土地所有权发生了激烈变动,以前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和生产工具。不过,即便如此,黔南地区的实际情况仍十分复杂。山多林密、坡陡沟深的地貌特征并未改变,传统的社会形态依旧存在,加之又是少数民族众多的民族杂居之地,民间秘密会社根基深厚,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向来自成系统。历史上,贵州曾多次爆发反对中央政府的民变。新中国成立以后,也曾出现大规模的匪乱。1950年3、4月份,贵州全省性的匪乱达到高潮,较大的土匪计约460余股,武装土匪达到十二三万人,机枪在千挺以上。*潘焱:《回忆贵州剿匪斗争》,《回顾贵州解放》(一),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页。实际上,虽然新政权对乡村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的整合,但远未达到政令通行贯彻无阻的目的,黔南地区仍有一些被认为是土改不彻底的地区。
而且,基层干部出现了“松劲”的现象。土改后所涌现的新型乡村干部为了追求生活质量的改善和生产资料的积累,逐渐恢复了传统乡村社会发家致富的手段,对政治运动的热情和精力较土改前大为降低。黔南地区就存在很多干部“不想干工作了,去搞个人发财”的现象,都匀县138个农村支部书记,有20个不愿意干工作,有34个农村党员要求退党。*中共都匀地委:《关于各县开展批评富农思想所揭发检查的富农思想情况汇集》(1955年11月27日),黔南州档案馆:1-1-366。乡村干部利用其权力追逐个体利益的现象也十分普遍,雇工、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等趋利手段成为主要的实践形式。据都匀等9个县4055个农村党员的统计:雇工的党员有51人,放高利贷、出租土地的有66人,买卖土地的有61人,自由经营的有123人,总计有301人,共占农村党员总数的7.4%。黎平尚重支部22个党员有6个买田、1个卖田、3个雇工,这部分党员占支部党员总数的45%。*中共都匀地委:《关于开展批判富农思想的情况报告》(1955年12月13日),黔南州档案馆:5-1-64。在乡村干部中,甚至出现了套购粮食、黑市交易、隐瞒产量等抵触国家统购统销政策的现象。据黔南地区福泉等八县2851个农村党员的统计:对粮食统购统销抵触、闹缺粮的有367人,违反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有256人,拦路抢购、抬高价格、黑市出售的有82人,三者合计705人,占核查党员总数的25%。对丹寨、平塘1773个积极分子的检查,上述情况的计有715人,占核查积极分子总数的48.3%。三都县二区发生过全区性闹粮事件,平塘县卡罗党支部全体党员全部闹粮。*同上,黔南州档案馆:5-1-64。新型乡村干部是由普通小农转变而来,土改前积极参与政治的目的或许就是为家庭经济水平的提高,在政治参与和家庭致富之间,乡村干部的选择和倾向十分明显。
即便是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的持续推进,民族地区仍不能做到政令的通行无阻,“仍有一部分(全国大约有10%)乡村的工作处于落后状态”。为此,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特意讨论了《关于改造落后乡工作的指示》*《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报告》(1954年5月1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第5册,第261—273页。,试图解决“土地改革运动中反封建斗争发展不平衡和不彻底而遗留下来的落后”问题。*《中共中央关于改造落后乡工作的指示》(1954年8月1日),黔南州档案馆:1-1-229。基于“土改补课”的改造落后乡村运动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实际上,早在1953年1月29日,中共都匀地委就发出在汉族第三类地区(即土改不彻底的地区)进行复查的指示。指示强调,复查问题确定只在汉族地区的第三类村进行,其他地区不进行,少数民族地区一律不进行复查。重点放在领导生产、建设和检查贯彻执行民族政策等工作上,并强调在复查中,要按照土地改革的方针路线进行,重点打击的对象是土改中漏网的地主和土改后进行破坏活动的地主。*中共黔南州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黔南州历史大事记:1930-1989》,内部资料,1996年,第62—63页。
到1954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改造落后乡村运动之前,黔南地区还存在189.5个三类村,占整个黔南地区行政村的14.8%,其比例远高于《关于改造落后乡工作的指示》中10%的判断,也说明了黔南地区乡村社会的复杂性。这些三类村一般具有这样的特点:一是处于沿边地区,多数处于省与省、县与县的结合部,交通不便,生产落后,生活贫困,并且多为少数民族聚集或杂居地区。在榕江县21个三类村中,少数民族聚集的村庄有13个,少数民族杂居的村庄有5个,汉族村只有3个。二是社会治安比较混乱,地痞流氓、烟民较多,行凶、偷盗、开赌场、强奸妇女、贩卖大烟等现象还时常发生,影响着乡村日常治理的正常运行。三是镇反不彻底,土匪(匪首、惯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这五类人并没有彻底清查。黎平县肇兴乡一村就查出20名。*中共都匀地委:《都匀地委关于加强边沿区工作消灭三类村的几点意见》(1954年4月1日),黔南州档案馆:1-1-258。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对三类村进行再次动员和整合不可避免。
二、落后乡村改造中的再次动员
土地改革运动后,土地的经营权和所有权高度集中于农民手中,农民既是土地的所有者,又是土地的自主经营者。土地的产权可以自由流动,允许买卖、典当、出租、赠予等交易行为;同时,国家通过土地登记、发证、征收契税等方式对土地进行管理。在这种土地制度下,黔南乡村的农业发展、农村经济与农民生活都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两面性,即传统生活的延续性和新型社会的变迁性共存。在“山高路远、地广人稀”的三类村,这种延续性显然大于变迁性,因此需要对这种传统内向型的三类村进行再次动员。
(一)宣传引导:村庄动员的再次介入
宣传引导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会议、报纸等媒介集中、反复地宣传鼓动民众来促使群众动员的实现。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它是“一个社会改变或形成民众特殊态度、意见和舆论的重要工具”*朱启臻等:《社会心理学原理及其应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61页。,甚至是“统治的支柱,也是运动的支柱”*王海光:《旋转的历史:社会运动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4页。。有的学者更是认为,宣传是“社会运动传播其思想、主张和认同感的一个最为有效的渠道,是社会运动动员大众和寻求同盟的有力武器,是取得社会同情和关注以及舆论上击败对手的法宝”*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51页。。
在改造的三类村中,亟需通过宣传引导来达到村庄再次动员之目的。1955年10月的《对改造落后乡工作的指示》中,中共都匀地委要求工作组在“进村后首应召开党团支部会(有党团支部的乡),贫农会、积极分子会等各种会议,说明我们的意图,解除群众顾虑”;并且对会议的时间进行控制,“目前农村任务艰巨繁杂,应控制开会时间,易短不易长,以免影响生产”。*中共都匀地委:《对改造落后乡工作的指示》(1955年10月26日),黔南州档案馆:1-1-407。改造落后村政策的传达多采取在民众聚集的场合公开进行,所以开会是最基本的方式,干部会、小组会、贫雇农会、民兵会、妇女会等一系列的会议,形形色色,不一而足。通过宣传,工作组将国家的意志向乡村社会作了广泛的传达。实际上,开会“可以使人们从人数上产生一种安全感”,而且“一个人的话可以启发另一个人”。*[加]伊莎白·柯鲁克、[英]大卫·柯鲁克:《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安强、高建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33页。对于谨小慎微的个体农民来说,人数上的安全感和优越感可以消除他们的种种顾虑,促使其行动起来。
中共都匀县四区潘洞乡(四村)的三类村改造就是靠宣传引导实现了农民阶级观念的树立。在改造落后乡村的工作组进村后,广大贫雇农并不认为地主是斗争的头号对象,干部才是最让人愤恨的群体。贫雇农认为“干部多占果实,作风不民主,比地主阶级的破坏活动更要明显”,因而贫雇农(特别是土改中未分到东西的贫雇农)要求斗争干部比斗争地主迫切。而乡村干部则出现了分化,落选的老干部对政府表现不满,开始诉群众的苦,摆自己的功,内心恐慌,又怕追贪污,暗地骂提意见的人无情。新干部则表现谨慎,当老好人。通过宣传,打通了干部和农民的思想隔阂,耐心地说服,解决了干部和农民的思想顾虑,使得乡村干部认识到自己的缺点,能够接受群众意见,武装委员蒙玉位就在小组会检讨说,“我们团结不好,最主要的是我自私……”。而干部的认错态度也得到了群众的谅解,最有意见的农民蒙银贵说,“不能光怨村干,也是我们的觉悟低”。之前干群紧张的关系得到好转,改变了连开会都是偷偷摸摸的局面,斗争锋芒基本上转向地主阶级。*中共都匀县委员会:《关于四区潘洞乡(四村)三类村工作简报》(1954年5月8日),黔南州档案馆:5-1-94。
(二)组织网络:村庄动员的结构建制
鼓动社会成员最终参与到社会结构中来,还要依靠组织和社会网络来实现,“组织在一个具体社会运动的微观动员过程中确实发挥着关键作用”。*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240页。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动员就是依靠其强大的组织和社会网络来实现的。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组织随着执政党成员的增加和组织的扩大在全国几乎所有的村庄建立起来。不过,黔南地区的党组织力量并非那么强大,中共都匀县的云朵农业生产合作社,在1955年前只有2名党员。*中共都匀县委农村工作部:《云朵生产农业合作化经过整顿变三类社为二类社》(1955年4月29日),黔南州档案馆:5-1-94。经过落后乡村运动的改造和发展,黔南地区的党组织和党员数量都有大幅提升。1954年,中共都匀地委在境内发展党员6600名,建立农村党支部699个,党支部和党员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黔南州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史志编纂委员会:《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第40卷)·党群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2页。云朵农业生产合作社不仅从三类社上升为二类社,党员的数量也增加到7人。*中共都匀县委农村工作部:《云朵农业生产合作化经过整顿变三类社为二类社》(1955年4月29日),黔南州档案馆:5-1-94。福泉县在1955年的改造工作中,在9个落后乡发展党员39人,新建党支部5个。*中共福泉县委农村工作部:《福泉县改造落后乡工作总结报告》(1955年9月30日),黔南州档案馆:5-1-67。丹寨县在改造落后乡村运动中共发展党员77人,团员101人,党组织在落后乡村普遍建立起来。*中共丹寨县委:《丹寨县委关于改造落后乡工作总结报告》(1956年3月31日),黔南州档案馆:5-1-94。正因为有了强有力的党员队伍和党组织,才保证了落后乡村改造的顺利推进。
作为上级党政组织向传统村庄社区传递和贯彻意志的重要渠道,工作队在改造落后乡村运动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因为上级干部直接进入村庄,参与社区管理,领导群众运动,对于相对封闭的山区而言,其动员的效果更为明显。1954年,中共贵州省委共派出150人的工作队到黔南各县进行三类村的改造工作。同时,中共都匀地委又要求各县均应加配一部分干部,从而强化三类村改造的领导机构和组织力量。*中共都匀地委:《都匀地委关于加强边沿区工作消灭三类村的几点意见》(1954年4月1日),黔南州档案馆:1-1-258。为此,中共都匀地委1954年共投入改造落后乡(村)干部155人(包括社会力量),其中县级干部6人、区级干部26人、少数民族干部40人;1955年共投入改造落后乡(村)干部85人,其中县级4人、区级20人、少数民族干部29人。*中共都匀地委:《都匀地委关于改造落后乡工作计划》(1955年9月24日),黔南州档案馆:1-1-407。在都匀县四区潘洞乡(四村)的三类村改造中,最先建立的就是工作队。该工作队以都匀县四区区委委员陶铸之为组长,都匀县抽4个干部,四区抽3个干部组成工作组,同时派遣农民积极分子5人,工作队共有13人。*中共都匀县委员会:《关于四区潘洞乡(四村)三类村工作简报》(1954年5月8日),黔南州档案馆:5-1-94。针对民族地区的特点,中共都匀地委还十分重视民族干部的选派和培养。在1955年上半年选派的干部中,有各县委抽派县委级干部15人,区委级干部40人和若干一般干部,除有一定政治水平和工作经验,一定领导能力和作风正派,民族观念较强的公安、武装干部的要求外,绝大部分要求选派少数民族干部,以适应民族地区的特点。*中共都匀地委:《都匀地委关于改造落后乡工作计划》(1955年9月24日),黔南州档案馆:1-1-407。实际上,工作队帮助党和国家实现了民众动员、干部监控、乡村治理的目标。此外,治保组织、民兵队伍等其它组织网络也在村庄动员的结构建制中起到了维护村庄治安、防止阶级敌人破坏的作用。
(三)利益与情感:村庄动员的运作方式
村庄动员还需要利益诱导和情感启发。“社会运动最常见的决定因素是利益……因为只有运动参与者承认他们的共同利益,社会运动潜能才可能变为现实。”*[美]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吴庆宏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152页。在土地改革运动中,通过土地、财产等重新分配动员了乡村社会的民众,促使他们参与到群众运动中来。韩丁在描述山西张庄发动群众时这样描述道,农民“只要积极参加斗争,就可以实实在在地分到土地、房屋、衣服和粮食。大伙一旦看清了这个事实,就相继投入到以后的运动中去”*[美]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韩倞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172页。。在黔南改造落后乡村运动前,地主仍在乡村社会中具有一定的权势。大麻寓乡地主涂克堂、朱玉祥(红帮头子)操纵2个行政组,在乡村社会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农民对此仍存敬畏之心,甚至不敢在公共场所随便讲话。在和平乡,地主邓家势力仍未打垮。因此,在落后乡村的改造中,打击封建势力仍是村庄动员的主要内容之一。麻江县共开展了24场斗争会,参加人数达13500多人,斗倒了45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地主36人、富农3人、其他成分6人),依法逮捕了17人。*中共都匀地委:《地委于三个月来改造落后乡工作情况的报告》(1956年1月20日),黔南州档案馆:1-2-150。黎平县高河乡,逮捕了掌握乡政权(正副乡长)的反革命分子4人。*中共都匀地委:《落后乡改造工作简报》(1955年12月20日),黔南州档案馆:1-1-407。荔波县览革乡7户地主,退出帮工粮1831元。三都县孟明乡3户违法地主上交罚款850元。*同上。其实,改造落后乡村运动就是通过重划阶级、斗倒地主,再将大量的地主富农的财产分配给贫雇农,以满足贫雇农对物质财富的要求。这些得到物质财富的贫雇农自然成为村庄运动的主力军。
在利益诱导的同时,情感启发也必不可少。裴宜理在《重访中国革命》一文中认为,“激进的理念和形象要转化为有目的和有影响的实际行动,不仅需要有益的外部结构条件,还需要在一部分领导者和其追随者身上实施大量的情感工作。事实上,中国的革命案例确实可以读解为这样一个文本,它阐释了被动员起来的情感能力如何可能有助于实现革命宏图”。*[美]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李寇南、何翔译,刘东主编:《中国学术》,2001年第4期,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98—99页。杜赞齐也持有相似的观点,中国共产党获得政权的基本原因之一是共产党能够了解民间疾苦,从而动员群众的革命激情。*[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9页。关于这一点,中共都匀地委有清晰的认识。在1955年的《关于中心八县改造落后乡工作会议情况报告》中,中共都匀地委总结了“前段落后乡村改造工作中主要经验和教训”,其中第三条就是“要有领导有组织有准备的召开斗争会,并注意掌握群众情绪,以免会场冷淡,地主顽强斗不垮”。*中共都匀地委:《关于中心八县改造落后乡工作会议情况报告》(1955年10月17日),黔南州档案馆:1-1-407。在情感启发下,农民的生存反应发生了很大变化,阶级意志逐渐取代了家庭伦理。福泉县大麻寓乡马骆新寨的少数民族,以往民族意识强烈,不愿意批斗和再划本族内部地主,经过情感启发之后,阶级斗争意识增强。和平乡农民郑必才斗争他的哥哥郑必仁(地主),揭发他在解放前曾压迫群众和勾结土匪。*中共福泉县委农村工作部:《福泉县改造落后乡工作总结报告》(1955年9月30日),黔南州档案馆:5-1-67。
三、从“土改补课”到合作化的制度转化
在改造落后乡村的再次动员之下,黔南地区各县的改造落后乡村工作于1956年4月基本结束。其中,丹寨县于1956年3月基本完成落后乡的改造工作,前后进行了7个多月,在运动中落后村寨发动起来的群众达到85%以上。*中共丹寨县委:《丹寨县委关于改造落后乡工作总结报告》(1956年3月31日),黔南州档案馆:5-1-94。平塘县的改造工作从1955年10月到1956年3月达到高潮,共持续了5个月,改造约合15个乡,占总乡数的25%,改造工作基本完成。*中共荔波县委:《关于改造落后乡工作总结》(1956年4月16日),黔南州档案馆:5-1-93。地理位置最边缘的从江县也于1956年4月基本完成。第一批改造10个落后乡和4个落后村,第二批改造13个落后乡和4个落后村,改造落后乡约占全县总乡数的32%。*中共从江县委:《改造落后乡情况总结与今后意见》(1956年4月6日),黔南州档案馆:5-1-93。至此,黔南地区改造落后乡村运动基本结束。
在此过程中,中国乡村社会完成了从“土改补课”向合作化的制度转变。以1954年的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和《关于改造落后乡工作的指示》为标志,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改造落后乡村运动。此时改造工作具有明显的“土改补课”性质,《指示》强调,“乡村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是绝不能跳跃的,过去遗留下来的任务必须进行补课”。同时,也十分明确地规定了劳动剥削分配的去向,“依法处理某些封建分子非法据有的土地与其他重要生产资料,以补足贫雇农的要求”。*《中共中央关于改造落后乡工作的指示》(1954年8月1日),黔南州档案馆:1-1-229。也就是说,改造落后乡村运动在斗争果实的分配上,都是分配给贫雇农,为农民个体所有。由此判断,早期的改造落后乡与土地改革基本无异,是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
将“改造并建立互助合作组”作为改造的目的也说明了这一点。因为互助组时期,不论是临时互助组还是常年互助组,都是组织农民在一起进行集体劳动,“土地、耕畜、农具和产品仍属农民个人所有”。“互助组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政治经济学名词简释·社会主义部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9页。只是,此时“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提上国家实践农业集体化的议事议程。为此,《指示》也对此进行了说明,“改造落后乡村,完成上一阶段遗留的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既须在性质上和新的历史任务——社会主义革命划开,又须在工作步骤上密切联结进行,前者要为后者直接创造条件,开辟道路”。*《中共中央关于改造落后乡工作的指示》(1954年8月1日),黔南州档案馆:1-1-229。
在黔南地区,中共都匀地委也明确地规定了改造落后乡村要“补足贫雇农”的要求,“错划阶级、农民、富农、小土地出租者、地主,划错成份者要订正。富农错划地主,其土地财产土改被没收分配,现有者坚决退回,无则了之。农民之间互相划错成份者,根据群众意见决定订正与否,地主错划农民成份或其他成份者,应坚决纠正,并按照政策进行没收和退减”。*中共都匀地委:《关于加强边沿区工作消灭三类村的几点意见》(1954年4月1日),黔南州档案馆:1-1-258。不管是没收的剥削所得,还是退回的土地财产,都要求给予其本人,而非集体所有。在福泉县的8个落后乡村改造中,没收漏网地主的田889挑、土253挑、山林15幅、房屋226间,共有1117户农民分到了价值19773元的斗争果实。大麻寓乡有朵少成、杨树清2户,解放前住20多年岩洞,靠讨饭为生,在土改中分了田地,仍未分到房,在改造落后乡村运动中分到了房,才从岩洞搬到房子中。*中共福泉县委农村工作部:《福泉县改造落后乡工作总结报告》(1955年9月30日),黔南州档案馆:5-1-67。其实,全国其他地区的改造亦是如此。天津郊区没收、征收及收回国有土地47270余亩(其中菜田4256亩,稻田、水浇田25220余亩),马达水车357台,普通水车590台,大车626辆(其中胶皮车275辆),其他大件农具4900余件,牲口1192头(其中骡子758头),房屋7357间,大件农具5800余件,余粮(折玉米)709万斤。共有20947户农民(包括少数中农和非农业)分到了果实,其中贫雇农为19677户,约占这些村全体贫雇农(包括新中农)的50%。分得果实的贫雇农约有三分之一以上具备了上升为中农的条件。据195个村统计,有141个村完全或基本上解决了贫雇农的问题。*《天津市郊区改造落后乡村的总结》(1955年4月1日),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天津市档案局编:《天津土地改革运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04—305页。
不过,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深入,改造落后乡村运动的“土改补课”取向逐渐发生转向,农业集体化的实践成为改造落后乡村运动最为重要的衡量标尺。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中预言,“农村中不久将出现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这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88页。他进而认为,落后乡村也应立即组建合作社。他强调“现在各省还存在着一些土地改革不彻底的落后乡村”,“在这类乡村中,也可以把可靠的贫苦农民积极分子组成合作社,同时,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充分地发动群众,坚决消灭封建势力和反革命势力,为顺利地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创造必要的条件”。*《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1955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01页。在此背景下,黔南地区很快就将农业合作化与改造落后乡运动结合起来,并将合作化发展作为考量改造落后乡村的标尺之一,改造落后乡村运动也就成为了集体化运动的实现途径。在1955年10月17日中共都匀地委的《关于中心八县改造落后乡工作会议情况报告》中,确定了完成改造落后乡村工作的五个标准,即“(1)彻底打垮封建势力。(2)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现行活动。(3)树立起以贫农为核心的政治优势。(4)把生产互助合作运动掀起来。(5)在改造落后乡期间,不但要完成落后乡的改造任务,而且要同时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中共都匀地委:《都匀地委关于中心八县改造落后乡工作会议情况报告》(1955年10月17日),黔南州档案馆:1-1-407。10月26日的《对改造落后乡工作的指示》也明确规定,各县将合作化运动“贯彻到落后乡改造工作中去”。*中共都匀地委:《对改造落后乡工作的指示》(1955年10月26日),黔南州档案馆:1-1-407。到1956年年初,中共都匀地委更加明确地要求,各县“完成初级合作化,在有条件的县份要求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高级社”。*中共都匀地委:《地委于三个月来改造落后乡工作情况的报告》(1956年1月20日),黔南州档案馆:1-2-150。其实,在全国合作化的浪潮中,合作化运动实际上已经成为改造落后乡村最为重要的内容。
此后,黔南农业社在落后乡村普遍建立起来。据黔南地区中心八县统计,到1956年1月已在落后乡村建成农业社76个,正进行建立的社107个(这部分农业社在元月25日前全部结束)。三都县巴佑乡建社后,入社农户达到总农户的60%。这八个县的落后乡村已经形成合作组雏形330个,组成联组190个,提高常年组502个,发展临时组398个,90%以上的农户都参加了互助合作组织,为合作化运动做了充分准备。麻江县的落后乡村还总结出创办合作社的经验:一是由老社负责派出骨干帮助建社;二是定期召开互助合作会;三是互助组和党团积极分子进行串联。*同上。丹寨县在完成落后乡村改造时,建立了高级社17个,入社农户为1917户,初级社5个,入社农户348户,组织起来的户数达到2263户,占落后乡寨户总数的87.3%。*中共丹寨县委:《丹寨县委关于改造落后乡工作总结报告》(1956年3月31日),黔南州档案馆:5-1-94。截止1956年底,黔南地区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自1952年开始,4年间共建社5026个,其中高级社1219个,初级社3807个,入社农户为182946户,占总农户数的94.12%。*中共黔南州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黔南州历史大事记:1930-1989》,第94页。至此,包括落后乡村在内的黔南农村已被完全纳入到农业合作化之中,土地和主要的生产资料完全归集体所有,而不是贫雇农,早期改造落后乡村的“土改补课”取向也最终发生转变,演变为合作化运动的实现途径。
四、结语:乡村社会的持续动员
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上,乡村动员早已有之。从抗战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将强大而高效的乡村动员用于征兵、减租减息、政权建设等各方面的实践中。就征兵而言,各村最普遍的做法是开展“革命竞赛活动”,用先进的个人带动落后的个人,先进的家庭带动落后的家庭,先进的村庄带动落后的村庄,*[美]胡素珊:《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王海良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第343页。形成了典型的“模范-仿效”的波浪式动员机制。*陈周旺:《从“静悄悄的革命”到“闹革命”——国共内战前后的土改与征兵》,《开放时代》2010年第3期。解放战争时期,分清敌我为核心的阶级斗争成为乡村社会动员最为核心的内容之一,阶级身份、阶级利益、阶级矛盾、阶级冲突取代了传统乡村旧的身份、利益、矛盾、冲突,乡村社会原本多元化的柔性结构被改造为两极对立的刚性结构。*李里峰:《中国革命中的乡村动员:一项政治史的考察》,《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将原有的乡村动员手段和策略应用于新解放区,比如中国的大西南。由于近代以来国民党中央政府迟迟未能实现对西南乡村的直接控制,中国共产党组织也没有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加之地理条件的“山高路远、地广人稀”,使得国家权力与西南乡村之间并未建立起紧密联系。为此,乡村社会的动员力度和难度也较老解放区有很大不同。在经过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以后,包括黔南乡村在内的边远地区仍有大量被认为是土改不彻底的三类村。为此,国家通过改造落后乡村运动,借助于宣传引导、组织网络、利益情感等手段,对落后村庄进行了再次动员,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国家权力贯彻畅通的目的,从而为农业合作化创造了条件。在此过程中,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浪潮,原来立足于“土改补课”的分配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改变,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不再归贫雇农所有,而直接属于集体。也可以说,改造落后乡村的群众动员成为农业合作化最终完成的保障和手段。
合作化运动之后乡村社会的动员仍未结束。人民公社、大跃进、整风整社、“四清”、农业学大寨、文化大革命等运动都与乡村社会动员密不可分,甚至生产救助、卫生扫盲也伴随着这种乡村动员,因而中国乡村社会的动员具有持续性和制度化的特征。1978年以后,中国农村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乡村政治生活渐入正轨,动员型的政治参与已为自主性的公民权责所代替。尽管如此,非常规乡村社会治理手段仍未真正终结,革命年代理念的延续性和路径的依耐性仍旧存在,这一点尤应为当今乡村政治所重视。
(责任编辑 欣 彦)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治理的历史经验研究(1949—1966)”(12BDJ024)的阶段性成果。
李飞龙,江苏东海人,(西安 710062)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贵阳 550025)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史研究所教授。
B2
A
1000-7660(2016)04-0050-08
——黔南示范小城镇集锦(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