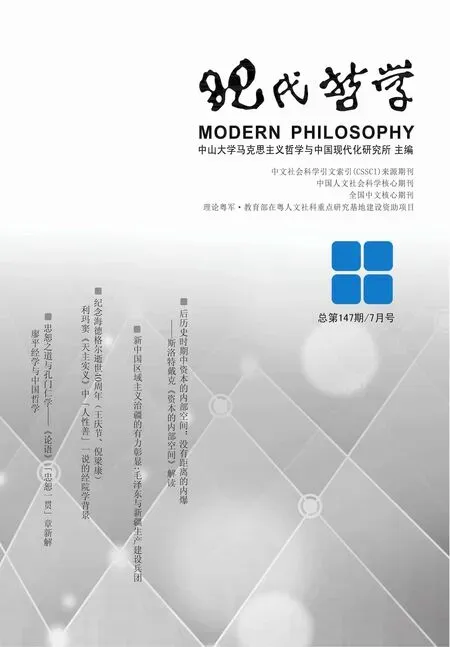多维度与范式转换:国内关于“中共治疆”的研究述评
龙其鑫
多维度与范式转换:国内关于“中共治疆”的研究述评
龙其鑫
近十几年来,中国大陆学界在关于“中共治疆”问题的探讨上呈现出多维化的研究趋势,而台湾地区的相关研究也日渐多元化与客观化。此外,两岸学者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认知上逐渐趋同。国内关于“中共治疆”的研究日臻繁荣,往后的研究在文献材料、叙述话语、借鉴视阈与研究范式等方面可有更进一步的探索与提升空间。
中国大陆;台湾;民族;新疆;中国共产党
21世纪以来,尤其是乌鲁木齐7·5事件的发生,新疆的区域局势成为了人们关注的重要领域,并引发了学界对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下文简称“中共治疆”)的研究热潮。所谓“中共治疆”问题,可看作是边疆区域化了的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所面临的困境,因而其与人们常言的“新疆问题”具有高度的耦合性。近十几年来,国内学者进行了多维的跨问题式研究,在文献的搜集和耕耘、研究范式的转换以及研究方法的拓新等方面,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进路,照亮了该问题的研究前景。由于研究者所掌握的历史文献、实证材料与社会信息的差异,关于“中共治疆”问题的研究呈现出地区性的分化特征,而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汉语学界是相对集中的研究区域。因此,笔者以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相关研究为考察对象,对近十几年来的研究状况作一简要述评。
一、多维化的研究:中国大陆的研究动态
“中共治疆”之所以成为中国大陆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讨论的热点问题,与新疆地区在中国共产党国家战略部署和中国边疆经略史中的地位密切相关。“中共治疆”问题是中国社会“总体”治理中的“区域”范本,全国形势与新疆局势之间存在着“结构互动”的关系,这一基本前提构成了具体研究的分析框架和参照系。于是,许多中国大陆的学者,分别从不同问题入手,深入探讨了中国共产党新疆治理的各方面内容。
(一)“治疆”问题之缘起与多维化探讨
鉴于近十几年来的新疆局势,学界对“新疆问题”之缘起有着许多探讨,并努力将探讨视域拓展开来,以全面认识“中共治疆”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无论是对于中国共产党,或是学者本身而言,其必须直面新疆治理在各方面涵盖性极强的“问题丛”,“中共治疆”折射出的是新疆社会的复杂性和跨问题结构。
在以往人们的认识中,外来因素的影响是导致治疆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既包括外部国家的政治介入,也包括旧有的“双泛主义”与极端势力的渗透。其中,美国的国家政治干涉被视为“惯性”存在的外来因素。中国社科院学者刘卫东就指出,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新疆问题的主要国外干涉者,“除了不断使用立法机构手中固有的权力之外,还借助媒体、非政府组织、学术界之口影响社会舆论,并以此向美国行政部门和中国政府施压”*刘卫东:《美国国会对中国新疆问题的干涉》,《国际资料信息》2010年第2期,第1—8页。。此外,土耳其对新疆局势的介入具有历史的常态性,并与困扰新疆社会治理甚久的“双泛主义”有密切关系,但以往在美、苏(俄)等国家的“掩护”下未能成为人们注意的主要对象。随着苏联解体与中亚、西亚局势的变动,新世纪以来“双泛主义”残渣泛起,土耳其的政治介入性干涉逐渐为部分国内研究者所深入了解。例如,兰州大学硕士田毅在其硕士论文中指出,土耳其国内弥漫着“泛突厥”情结,“土耳其从政府到一般民众对境内的‘疆独’势力进行或明或暗的支持与纵容”,这将是影响中土关系的主要绊脚石,也是新疆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田毅:《反“疆独”视角下的中国与土耳其关系研究》,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然而,“如果一味将新疆问题主要归为外来影响,某种程度是减弱责任意识,减少对工作失误的反思,客观上不利于自身的改善”,新疆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李晓霞指出。她还强调,新疆的内部治理方面也是问题缘起之所在,如“疆内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社会矛盾累积难解、社会治理方式调整难度大等。对于什么是影响新疆稳定的最主要因素,有政治、经济、宗教、民族等不同说法”*李晓霞:《不能把新疆问题一味归于外来影响》,共识网,2014年10月10日,http://www.21ccom.net/articles/china/ggzl/20141009114366_all.html。即是说,“中共治疆”所面临的问题之缘起是复杂的,而问题缘起的复杂性往往需要在长时段的历史性探讨中进行辨明,从而将治疆“问题丛”梳理与归纳,并逐一展现出来。
因此,不少学者已经着手从长时段的历史性研究去进行探讨。例如,马大正就指出,民族分裂主义是新疆地区由来已久的历史问题,我们对这一历史问题的研究“必须区分割据与分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以避免“双泛主义”分裂史观的扰乱。此外,以往在社会管理、意识形态、教育出版事业与政府干部等方面存在着偏差,这是问题缘起的多结构原因,接下来要以大力度进行政策纠偏。*马大正:《论百余年来新疆反分裂的几个问题》,《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9—16页。姚新勇也指出,新疆问题之缘起是“复杂面向”的,尤其是诸如民族、宗教与人种等方面有着长时间的矛盾积累,近几十年来又有诸多内外部因素交织在一起,“新疆问题既带有古老地区性宗教冲突的色彩,也是原有东突厥斯坦分裂运动的继续,同时是现代多民族国家文化认同断裂的暴力表现,是新形式下国家制度及民族政策失效的征兆,是新疆内部不平衡、欠公平发展的产物,是社区、乡村有机结构坍塌的结果,是全球化浪潮及国际政治因素的刺激效应,也是境内外舆论过度放大的结果。这一切加之新疆绿洲生态的脆弱性,就决定了‘新疆问题’注定是复杂的、长期的”*姚新勇:《“新疆问题”的复杂面向》,《文化纵横》2014年第2期,第52—57页。。
随着中国大陆研究者的深入探讨,“治疆”问题缘起之复杂性逐渐成为主流认识,单一的外部因素已经不能够作为充分原因。如李晓霞、马大正与姚新勇等学者所言,新疆问题涉及新疆治理史的方方面面,必须置于历史总体进程中进行考察。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症结,包括“历史与现实、世俗与宗教、经济与政治、民族文化差异、地缘等诸多内外部因素”,都可藉历史的总体性和跨问题结构,以提纲挈领地进行把握。
(二)“民族区域自治”及其民族政策:“治疆”核心问题及其争论
民族问题,是研究者们探讨“中共治疆”问题的切入点,而党与政府也一直坚持以“民族区域自治”为制度基础解决民族问题。因此,“民族区域自治”成为了研究者们的关注焦点,被视作为“中共治疆”的核心问题,并引发了许多讨论。中国大陆学界对“民族区域自治”这一问题进行激烈讨论的背后,跨越并涵括了多个问题的争论,隐含着多维的价值立场和取向,但力图有效地解决问题是学者们的共通诉求。
随着新疆、西藏等民族地区局势的日趋紧张,不少研究者认为“民族区域自治”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并作深刻的反思。其中,北京大学马戎就指出,民族自治地方与非自治地方在人们心中创造了“一个地理上的二元‘空间区隔’”。这是因为:第一,“自治地方的居民并不全都属于某一个(或几个)‘自治民族’的成员,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除了维吾尔族,还有哈萨克族、蒙古族、回族、汉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等,并不是一个民族就可以概括了的”;第二,在包括新疆在内的自治地方,政策优惠与自治民族之间存在非匹配性,除教育政策优惠外,行政流动、就业与福利保障等方面也存在着区域与民族的差异性,这就形成了一种“民族空间区隔”体系,“在客观上有可能加强了各族居民之间的空间区隔与感情隔阂”。*马戎:《如何看待中国社会的“汉—少数民族二元结构”》,包智明主编:《社会学名家讲坛》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83页。就此,马戎延续其提出的民族问题“去政治化”观点,认为包括新疆在内的“民族区域自治”及相关的民族政策应当要“以苏为鉴”,主张民族与区域之间的关系应当逐步淡化。此外,他还指出,欧美以“族群”(Ethnic)而非“民族”(Nation)为族际问题基本话语,其处理少数族群的“文化化”政策导向较为成功,值得我国借鉴,政策优惠或权利机制应该从地方性行政运作向全国性法制运作实现过渡。相应地,他主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应具体为“政治一体”和“文化多元”两个层面,且应当强化前者,逐步淡化后者。若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及相关民族政策等民族问题解决不好,这些民族问题或被高度“政治化”,那么“中国在21世纪可能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国家分裂”。*马戎:《族群、民族与国家建构——当代中国民族问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24页。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虽然当前中国民族关系出现了新的问题,但处理的关键是要坚持与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把自治地方与自治民族的相关政策与权利制度化和法规化,而不是否定“民族区域自治”。其中,中国社科院郝时远就认为包括新疆在内的自治地方,在一系列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中都处于发展劣势,这使得民族问题与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也决定了包括新疆在内的民族问题不能急于求成地“一劳永逸”式解决。民族问题需要通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来逐步解决,“我们需要借鉴和吸取世界范围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其中包括前苏联与欧美国家的经验教训,“但绝非照搬、照抄,或妄加推断”。*郝时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民族关系》,谢立中主编:《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5—42页。此外,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的政策优惠,郝时远认为包括新疆在内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经济社会滞后,在此情况下“对少数民族共享社会公益权利的照顾性政策是有限的”,他也承认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地区的少数民族“共享同样的照顾政策,当然是不合理的”,但是将这些比较效应“作为‘逆向歧视’例证而动议取消这些政策则更不合理,关键在于如何避免政策的‘一刀切’问题”,重点是要做到“从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去进行调整,而这正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也是民族工作部门的责任。*郝时远:《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三题》,《当代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研究》第7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9页。中国社科院陈建樾则认为,“之所以要赋予少数民族群体及其地区优惠政策”是因为:其一,市场在处理国内地区与群体收入差距方面失灵;其二,市场失灵需要通过政府干预来改善;其三,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有助于缩小和均衡群体收入与地区差距,实现社会和谐。*陈建樾:《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民族问题的解决》,《世界民族》2005年第5期,第1—13页。
在关于包括新疆在内的自治地区局势是否会导致国家分裂的问题上,郝时远认为这是否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项民族政策(包括民族教育政策)有关,是值得深思的问题,而“回答这些问题都需要科学的实证研究,而不是情绪化的主观判断”*郝时远:《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三题》,《当代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研究》第7集,第21页。,不能因为一些问题而全盘否定包括新疆在内的各自治地方政策优惠。此外,陈建樾则从现代政治制度史的视角分析认为,自治是现代民主的必要前提,“民族自治的政治模式为实现国内各民族的平等、发展和繁荣提供了一个制度平台”,自治模式可以“通过不同的赋权管理方式换取各个少数民族对多民族国家政治和发行的认同”,但是他也承认,如果自治制度不能充分体现各民族的利益诉求,“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整合就会受到破坏”。*陈建樾:《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民族问题的解决》,《世界民族》2005年第5期,第1—13页。
在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施下的族际关系问题上,郝时远强调“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是为了‘区隔化’各个民族,而是为了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郝时远:《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三题》,《当代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研究》第7集,第28页。,各自治地方的民族内部事务问题与社会发展问题,需要通过完善民族区域内的自治条例、法制与工作方法等制度而解决。国家民族(state nation)与民族权利之间是非矛盾的,“对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国家民族的整合是各个组成部分在共享和互利秩序中的协调”,统一并不消除多样性,关键在于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从而逐渐消除各方面的民族差距。*同上,第29页。王希恩则指出,这一问题关乎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性质,即“它是趋向于‘分’,还是趋向于‘合’”,一方面民族区域自治给予少数民族充分的自治权利,另一方面这不是一种纯粹的“民族自治”,“而是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结合、民族因素和地域因素结合”,即本质上是“一种着眼于各民族的‘合’的制度”,包括新疆在内的各自治地区成立时,在制度设计上已经奠定了“合”的基础了。然而,民族区域自治“这一制度还有着诸多的不完善之处,在如何更好地发挥它的优势方面还有这很多的工作要做”。*王希恩:《也谈在我国民族问题上的“反思”和“实事求是”——与马戎的几点商榷》,《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1期,第1—17页。
(三)“视野向下”的范式转向:社会(基层)的向度及其实证化
以往的“中共治疆”问题,主要以论述中共治疆政策的合法性和长久性问题为主,多属地方党史或政治史的“上层”研究路径。例如,《中共新疆地方党史(1937-1966)》*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共新疆地方党史(1937-1966)》,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与“中共新疆地方史丛书”*《自治区2001-2005年党史工作规划》,《新疆党史》2002年第1期,第8—9页就主要讲述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在新疆的活动,以及和平解放之后中国共产党对新疆地方的一系列治理政策与重大事件。此外,朱培民、王宝英的《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史》是近年关于中共治疆政策的代表作,作者综合了以往的研究成果,主要阐述毛泽东、邓小平与江泽民三代领导集体治理新疆的政策与历史,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领导地位、指导思想、重要指示与工作部署。*朱培民、王宝英:《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
然而,随着新疆地方局势的变动,社会(基层)作为问题缘起的基础渐成共识,于是有许多学者指出,地方党史与政治史的“上层”研究已经难以适应当前社会的变动趋势,因此新时期的研究应该实现“视野向下”,即由政治层面下移至社会(基层),着力于反思方面,从实证考察与社会(基层)治理实效化等方面加强研究。例如,马大正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新疆稳定问题的观察与思考》就是该领域较早的研究成果,作者将历年对新疆的调研报告精选结集成书,指出“随着边疆历史研究的深入,我们日益感到研究历史与了解观状密不可分,只有了解了现状,才能更好发挥以史为鉴的文学功能。同时史学工作者也应直接从事现状调研,并进一步开展相关的对策性研究”,并综合“党、政、军与学”等各方的协作力量进行调研工作,进而上升至治疆的战略高度,提出对策,实施综合治理。*马大正:《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新疆稳定问题的观察》,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附录。再如,在对新疆、西藏等民族地区的研究上,马戎就主张“实证调查和文献阅读,二者不可偏废”,因此他带领其团队“先后在我国各民族地区开展了不同专题的社会调查,在这些调研活动基础上汇集出版了12本文集”,“这些文集的各篇大多集中于基层社区的专题调查,收集了反映当地各族民众的教育、就业、生活消费和族际交往基本情况的数据,讨论了各地区有关民族关系的一些具体政策,也间接涉及部分相关的制度问题”*马戎:《如何思考中国民族研究》,《当代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研究》第7集,第81—83页。,其中很大部分是新疆社会方面,涉及对口援疆项目调查、民族教育与双语教育、职业结构变迁与跨地域流动等方面,大大拓宽了社会(基层)的研究向度。
正由于马戎与马大正等学者鼓励并亲身进行实地性的调研研究,使人们从以往“上层”研究走向社会基层,使研究的“视野向下”,也为实证调研与治理实效化的研究路径指明了道路,所以相关研究相继出现。
近年来,人们日益注意到基层治理对于新疆局势的重要性,所谓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重在基层”,该论题已经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基层的党组织建设主要分为农牧区与城市两部分。其中,在农村整体方面,左兰的《新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挑战和应对措施》指出了农村在社会经济各项指标上对于新疆地区的重要性,而“乡镇党委和村党支部是党在农村执政组织体系的末端,直接面对一大农民群众”,加之新疆农村在民族、宗教、经济与自然结构方面相较于内地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因此新疆需要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提高干部队伍整体素质,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以及拓宽丰富文化生活。*左兰:《新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挑战和应对措施》,《西安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第54—57页。在新疆,农牧业是农村社会结构的一项传统部分,因此然娜的硕士论文《新疆少数民族农牧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现状及对策研究——以富蕴县为例》以富蕴县为考察对象,分析了少数民族农牧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性,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例如“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的滞后,党在农村的执政能力不强,经济发展不平衡挑战村级党组织的工作能力等”,并提出要在思想、制度、组织、经济与作风等五方面加强新疆农牧区的基层党组织建设。*然娜:《新疆少数民族农牧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现状及对策研究——以富蕴县为例》,新疆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此外,新疆社会的城市及社区基层党组织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部分。乔中明的《多民族聚居城市社区党组织是维护稳定的基础——以乌鲁木齐市为例》指出,“多民族聚居的城市社区基层党组织处在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的最前沿”,因而城市社区党组织建设是重要且急迫的,而主要工作是要使社区党组织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当前应在实体化管理、重点复杂区域社区、社区党组织及其社会掌控力等方面加强建设*乔中明:《多民族聚居城市社区党组织是维护稳定的基础——以乌鲁木齐市为例》,《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30—33页。。近年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维护新疆社会稳定上的作用也逐渐为人们所关注,其中,兵团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尤为重要。张旭团的《发挥机关基层党组织在新疆稳定与发展中的作用研究——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例》就指出:“兵团要切实履行‘屯垦戍边’的职责使命,使自身成为‘安边固疆的稳定器,凝聚各族群众的大熔炉,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示范区’,其必须发挥好机关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张旭团:《发挥机关基层党组织在新疆稳定与发展中的作用研究——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例》,《兵团党校学报》2014年第6期,第36—39页。
长久以来,宗教问题及其相关政策,被视为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的最主要部分之一,也是研究者们最为关注的方面之一。关于该问题的研究,中共地方党史与政策史的跨结构研究是常用路径。以陈旭的《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在新疆的运用与实践》为例,一般以重点叙述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在新疆的成功实践与历史经验为主,而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促进了新疆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维护了国家安全和统一”是基本结论。*陈旭:《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在新疆的运用与实践》,《宗教学研究》2014年第1期,第8—12页。然而,随着新疆局势的变动,一些相关人士批判指出,“必须清醒认识当前新疆宗教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必须转换以往的研究路径,社会实地的考察研究应是新的研究路径。例如,宗教极端化是近年新疆社会的非正常氛围,兵团学者白关峰以解剖麻雀式的个案分析指出,新疆穆斯林妇女和青少年的宗教行为变迁被认为是宗教极端化的一个典型现象,“受到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一些青少年和妇女的行为表现变得极端化,穿着的服饰更趋保守,更具宗教色彩,宗教情绪加重”。宗教极端思想,在青少年和妇女中渗透的手段和途径多样化、隐蔽化,除了通过地下讲经与日常交往之外,新媒体已经成为宣扬宗教极端思想的重要途径,并有向实施暴力转变的倾向。白关峰还介绍了兵团党政机关的工作,在团领导的群众工作、社会管控的“网格化管理”、宗教人士培养等方面加强工作,以防止宗教极端思想向青少年和妇女中渗透。*白关峰:《宗教极端思想向妇女和青少年渗透问题研究——以兵团第三师四十四团十八连为例》,《兵团党校学报》2015年第1期,第40—43页。也有一些学者主张,关于新疆宗教的研究与工作视野要往实处转移,当下的工作时要“去极端化”,同时端正“去极端化”工作的态度,并在全社会形成共识。例如,徐卫刚主张,党政机关与干部要“通过不断提高老百姓对伊斯兰教宗教知识和教义的正确理解,自觉抵御各种形式的宗教极端思想,进而切断非法视频和非法讲经人士散布的歪曲伊斯兰教义的宗教极端思想流向社会的渠道,引导信教群众自觉区分正常宗教活动和非法宗教活动”*徐卫刚:《“去极端化”不是一件小事情》,《新疆日报》,2014年11月6日,A10:时评。。
二、递进与互动:台湾地区的研究状况
台湾地区的边疆学界是大陆知识界分化出去的一个群体,其关于“中共治疆”问题的处理和看待,有一个客观化与深化的递进过程,在反思上世纪前半期的治疆教训之后,再观察20世纪后半期新疆治理的新景象,这是迁台后的边疆学人的治学理路。
(一)台湾地区的研究变迁
早期的台湾学界,主要是从大陆知识界分化出去的中国边政学研究者,尤其关注20世纪后半期中国边疆的社会政治变迁,这与他们归纳20世纪前半期中国边疆治理的经验教训之反省式研究遥相呼应。20世纪后半期的新疆政制变迁是台湾地区研究者关注的内容之一,但受到资料来源与政治立场的限制,所以台湾研究者多选取政治学的研究方式,如有学者就从“中共政权”性质入手分析“维吾尔自治区”*陈嘉猷:《中共政权“维吾尔自治区”之研究》,国立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硕士论文,1983年。,但不免存在一定的意识形态与体制偏见。
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资料获取的丰富化,台湾学者的研究趋于平和。除了新疆民族问题一直为台湾学者所关注之外*孙承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问题研究》,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硕士论文,1995年。,中国共产党的新疆治理政策也得到了重新认识*单文雄:《中共的新疆政策(1949-1992)》,国立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硕士论文,1993年。。此外,也有一些新论题得到重视,如关于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的移民政策研究*罗联芳:《中共移民新疆之研究》,国立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硕士论文,1983年;康添财:《中共移民边疆政策之研究》,国立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硕士论文,1987年。,对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宣传工作及其促进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功能等*吴凯莉:《多种族地区运用传媒塑造国家认同的研究——以中共运用新疆日报社论为例》,中国文化大学硕士论文,2000年。。其中,“民族区域自治”仍然是台湾学者较为关注的问题,并视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政制新创,尤其是“自治区”政治制度及其与“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万仁政:《中共中央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关系之研究》,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硕士论文,1997年。,成为台湾研究者需要理清的问题。近十几年来,台湾地区的新疆研究者对“民族区域自治”大致上有两种代表性看法:
其一,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有成就也有不足。例如:国立台湾大学法律系客座教授陈东壁在《大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之研究》一文中认为,“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吸纳欧美、苏联与中国历代经验所得的“宪政制度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有其自身的沿革史。在民族区域自治各项制度的操作上观察,新疆等民族自治区少数民族权利得到照顾,却也有许多地方法制需要规范化。新疆、西藏等边疆民族自治地方在立法、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等方面的自治权得到特殊化照顾,但又与内地存在一定的距离。由于中国共产党突出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制度及其操作特殊性,以至于许多少数民族地方制度与全国统一局面不相协调,于是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进行事实上的变通”。陈东壁“肯定大陆民族区域自治实践所取得的一些成就,同时还将指出,大陆若欲以此一制度彻底解决民族矛盾,尚需时日”。*陈东壁:《大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之研究》,《台大法学论丛》第24卷第1期,第73—119页。
其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成效显著,其中包括对新疆的有效治理。例如,吴启讷在《民族自治与中央集权——1950年代北京藉由行政区划将民族区域自治导向国家整合的过程》一文中认为,“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对清末与民国边疆政策的改弦更张,但也继承清朝与民国政府的国家整合目标,汲取中国历代中央王朝与苏联政府强化中央集权、防止边疆民族分离的历史经验。以新疆为例,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具有“自上而下、广封众建、分而治之”的制度制衡功能,使维吾尔族的新疆主体民族地位受到“其他少数民族的稀释与制衡”。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既实现边疆自治,又达成国家整合,从而实现了中央政府对新疆、西藏等边疆民族地区直接有效的政治统治和行政管辖。*吴启讷:《民族自治与中央集权——1950年代北京藉由行政区划将民族区域自治导向国家整合的过程》,《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5期,2009年,第81—137页。
吴启讷是近年台湾地区崛起的边疆史研究新锐,在陈永发的指导下,吴启讷的博士论文《新疆:民族认同、国际竞争与中国革命,1944-1962》以详实的历史材料,叙述了20世纪以来,新疆突厥语穆斯林民族主义及其政权与苏俄当局和中国政府的历史关系,并论述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政治手段将伊宁“三区革命政府”统合在其“党-国家”体制之内:在新疆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但又在“维吾尔”省级自治区以下设置各级民族自治地方,从而形成“众建以分其势”的民族间行政制衡效果,再辅以“经济整合、驻军屯田和移入汉族居民”等政策,使得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在新疆的稳固统治。然而,吴启讷也指出:“伴随中国对新疆控制的加强,本地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同步上升,对抗中共统治的活动从未止歇。此一过程仍处在进行状态中。”*吴启讷:《新疆:民族认同、国际竞争与中国革命,1944-1962》,台湾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
当代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的状况是台湾研究者最直接的素材,尤其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之后,台湾研究者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维稳政策、族际关系处理,新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徐碧霞:《中共治理新疆的困境与挑战——以7·5事件为例》,清云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侍建宇、傅仁坤:《乌鲁木齐七五事件与当代中国治理新疆成效分析》,《远景基金会季刊》第11卷第4期,2010年11月,第149—190页。,以及新疆少数族群文化状况及治理政策*季茱莉、邱荣举:《中国少数族群文化政策: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个案分析》,《中华行政学报》2011年第8期,第177—193页。。近年来,随着中共中央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重视有加,台湾学者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研究兴趣也被带动起来,其中有学者从新疆屯田戍边历史进程去看待中国共产党建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功用*孟鸿:《从屯田戍边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边政》第176期,2008年12月,第17—34页;刘学铫:《再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边政》第188期,2011年12月,第1—34页;,也有学者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史的考察,肯定“兵团的发展不仅关系新疆的稳定与发展,更关系中国边防的安全”*李淑芬:《中共治理新疆与生产建设兵团前期发展之研究(1949-1966)》,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在职专班学位论文,2012年。。
(二)陆台互动与跨史观叙述
伴随着两岸的相互开放以及时代形势的变迁,大陆与台湾的中国边疆研究者们在互动中取长补短与相互借鉴,对一些关键的历史问题的认知日益接近共识。大陆方面,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关于一些新疆历史问题的研究上,阶级史观日渐褪色,维护国家利益与统一的史观话语逐渐增强。例如,对“三区革命”的认识与评价就有了一定的变动,近年来关于“三区革命”的书写逐渐强化了以国家统一的立场看待问题的角度,也坦陈了苏联在其中所扮演的地缘挑动角色。著名学者厉声指出,三区革命具有多面性,其内部的“统一与分裂的斗争,成为20世纪新疆历史上第一次由民族领袖带领民族群众反对分裂新疆的重大政治斗争。斗争的焦点是拥护和平与中国统一,还是实行反汉排汉、分裂中国”*厉声:《苏联与新疆三区革命》,《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文选》中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062页。。台湾方面,随着体制性偏见与意识形态的淡化,以及大陆文献史料的开放,台湾学者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上,如关于“伊宁事件”(即“三区革命”)的论述逐渐从更大的历史格局进行审视,对中国共产党在其中的作用也有了更为客观的评价。例如,吴启讷就认为“伊宁事件”是苏联的地缘政治“筹码”,而中国共产党也是其中的博弈力量,并在新国家建构中将“三区”由“国中之国”变化为“省中之省”。*吴启讷:《从“国中之国”到“省中之省”:1949-1955年伊宁与北京在新疆民族自治问题上角力的背景、过程与结果》,《两岸发展史研究》第4期,2007年12月,第217—275页。近年来,随着台湾政治气候的变迁,台湾的“中国边政学”研究者们更加注重与大陆学界的互动,以在台办刊五十多年的《中国边政》为例,“除了坚持‘大中国’研究方向,还进一步扩大两岸学术交流,缩减意识形态对立的内容,使两岸的边疆民族研究在学术上更为趋向统一,出现了相互交流边疆民族研究的历史和现实可能”*吴楚克:《台湾〈中国边政〉述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14卷第2期,2004年6月,第130—135页。,而包括当代新疆局势及其治理在内的“大陆边疆政策、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是其主要刊发内容之一。
虽然两岸保持着原本的一些史观话语,如大陆方面依然持存对“三区革命”是反抗国民党当局的“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分”的革命定性,而台湾方面则维持着从国民政府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的评述,但是这并不妨碍两岸在新疆研究的关键问题上逐渐趋同,也不妨碍两岸对新疆治理史的共同书写。例如,近年两岸学者共同编写的《中华民国专题史》就是研究趋同化的成果,其第13卷(“边疆与少数民族”专题)就涉及中国共产党的近代新疆政策问题——“三区革命”,并由台湾方面的吴启讷博士执笔。*王川、张启雄、蓝美华、吴启讷等:《中华民国专题史(第十三卷 边疆与少数民族)》,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15—253页。该部分从“全球两大阵营冷战的视野”出发,采取了新的更为宏大的视野,也圆融了各方的看法,两岸非一致的观点以述说而价值无涉的书写形式得以兼顾,既有国民政府的立场,也有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战略,更论述了伊宁政权的施政状况与苏联的地缘利益,呈现出“跨史观叙述”的圆融互动局面。
三、关于“中共治疆”研究的评述与展望
通过对以往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关于“中共治疆”研究的考察,笔者认为:一方面,以往的研究积累了许多基础性的材料、视角与方法,为之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可参考观点;另一方面,以往的研究也存在一些可商榷性的观点与方法,往后的研究应当引以为鉴,以下是具体的评述与展望:
第一,加强两岸学界在当代新疆问题或“中共治疆”等问题的研究互动,在跨史观交流中取长补短。例如,以往两岸学界的研究在文献材料的搜集与运用上存在着良莠不齐的局面。虽然中国大陆学者占据搜集第一手文献的客观优势,但是台湾地区的学者对第一手文献的运用更为深入。以台湾吴启讷的博士论文《新疆:民族认同、国际竞争与中国革命,1944-1962》为例,他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所搜集的中共西北局、中共西北局新疆分局与中共新疆党委的党政工作文件,被充分地运用到其博士论文之中,且有深度的文献梳理与解读,从而对中共领导人的新疆治策思想有较深入的探讨,这是大陆学者较少重视的工作。然而,部分中国大陆学者在对地方通志、统计年鉴、新闻报刊、人物回忆录、口述记录与社会经济调查报告等等能够体现历史场景的材料之掌握上,又比台湾与国外学者所掌握的要广泛且多样,从而在经验认知方面更有优势。因此,以后的研究在文献材料的处理上,两岸学者需综合彼此之长处,鉴彼此之不足。
第二,“民族”或“族际关系”的话语色彩趋浓,往后研究可考虑淡化。在近十几年的新疆研究中,援“论”入“史”的研究范式成为趋势,基本上能够合理地处理“史”与“论”之间的关系,但是在“论”方面存在着史观方法单一化的趋势,“民族主义”与“族际主义”的强化,使“民族”话语掩盖了诸如阶级、职业、性别、政党、单位与区域等因素,以至于研究的视野被窄化,纠结于民族与民族关系问题而难以抽离,同时使部分研究陷入单一的民族主义立场。例如,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相关研究强化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国族主义史观,而阶级史观则有被淡化的趋势。与之相对,在国外研究中,同情乃至支持民族分离主义的话语也相应强化,部分国外学者在后殖民主义史观与社会冲突论的主导下,将新疆比附为中国的“内部殖民地”(Internal Colony)*B. Sautman, Is Xinjiang An Internal Colony? Inner Asia, Volume 2 (2), 2000, pp.239-271.,夸大民族之间的差异与对立。在国内外族际主义话语的持续渲染下,新疆研究容易向单一的民族问题研究转化,不利于拓宽分析与解决问题的研究视域。因此,往后的研究需考虑淡化民族或民族主义话语,同时注重阶级、区域、职业与单位等因素,这不仅可开阔研究的视野,越过“族际主义”的视野,也可使研究扬弃单一的民族主义立场。
第三,中国学者可批判地借鉴国外相关研究的研究范式。一些国外学者,如澳大利亚亚格里菲斯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的亚洲研究所研究员Michael E.Clarke与美国乔治城大学历史系教授James Millward,擅长在现代性、全球化进程和地缘政治博弈等视域中,以宏大而富有战略高度地研究新疆问题,诸如中亚“大博弈”(Great Game)的时局分析*Michael E.Clarke, Xingjiang and China’s Rise in Central Asian-A History, Routledge Press, 2011.,以及“欧亚十字路口”(Eurasian Crossroads)的地缘分析等视角*James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呈现出新颖的“中共治疆”研究思路。然而,在西方族际主义主流研究视角及其强势话语的覆盖下,加之国外学者对中国社会历史了解程度的良莠不齐,国外关于“中共治疆”的研究并未充分考虑该问题的复杂性和跨问题结构,因而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部分国外学者的意识形态偏见依然会继续存在,我们应当持存一种批判的借鉴态度。
第四,关于中共治疆的政治上层研究路径依然是主流,往后的研究应当注重多维的研究路径。虽然已有部分学者试图跳出以“政权更替”为划分标准的历史思维,转而从民族、地缘政治、政策改革与文化氛围等因素去关注中共治疆的全体构象。但是,当前的很大部分研究都以政权更替、政治事件与政策变迁作为论述结构的基础,过于注重政治层面的研究,从而导致政治上层的叙述逻辑长期占据主流,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政治上层之下的社会结构、经济制度与文化状况等等底层方面。因此,往后的研究可考虑将视野从政治下移至社会层面,应该开拓“中共治疆”的经济史、环境史及文化史等方面的内容书写,以社会基层或社会总体的角度去研究“中共治疆”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具有跨学科研究特质的区域社会史应当是“中共治疆”研究的可取路径。如此,“中共治疆”的研究不仅可以在社会层面拓展研究视野,使运用的社会历史材料来源多样化,以及使分析问题的思考空间扩大化。
(责任编辑 欣 彦)
龙其鑫,(广州 510275)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博士生。
B2
A
1000-7660(2016)04-004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