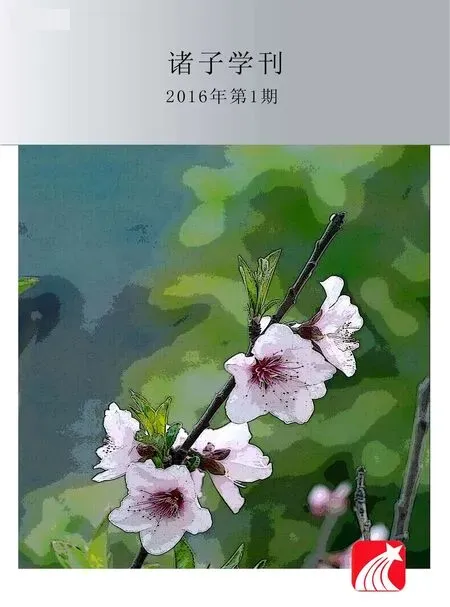熔經鑄子:“新子學”的根與魂
李若暉
熔經鑄子:“新子學”的根與魂
李若暉
漢唐以經為大道所在,諸子為六經之支與流裔。然至唐宋之際,經學已陵夷衰微,實不足以達道。於是文士蜂起,倡言“文以明道”。程頤則以經學與文章皆無與至道,義理之學方可進道。於義理之學中,又驅逐異端,獨以儒學為正統。於是宋明理學起,而經學、儒學離。至晚清,西學東漸,儒學拙於應物,學者乃以諸子對應西學,儒學正統遂傾。近代經學沉淪,子學復興,但復興後的子學棄經學而附哲學,於是中國傳統義理之學的固有格局與内在脈絡被打散。當代“新子學”的建立,必須與經學相結合,以中華文化的大本大源為根基,立足於中華文化自身,面對中華文化的根本問題,重鑄中華之魂,此即當代“新子學”之魂魄所歸。
關鍵詞 經學 諸子 大道 新子學
中圖分類號 B2
一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經部總敘》開篇有云:“經稟聖裁,垂型萬世。”*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上册,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頁。以經為中華傳統文明之核心。然斯義顯晦曲折,隨時俯仰,曷勝嘆哉。
檢《白虎通義·五經》:“經所以有五何?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班固《白虎通義》下册,陳立疏證本,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447頁。《文心雕龍·宗經》:“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劉勰《文心雕龍》上册,范文瀾注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21頁。以經為大道之所在,此固漢唐經學之通義。
至於諸子之學,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分中國哲學史為兩大階段,即子學時代與經學時代。“上古時代哲學之發達,由於當時思想言論之自由;而其思想言論之所以能自由,則因當時為一大解放時代,一大過渡時代也。”*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載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第二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8頁。反之,經學時代則始於“董仲舒之主張行,而子學時代終;董仲舒之學説立,而經學時代始。蓋陰陽五行家言之與儒家合,至董仲舒而得一有系統的表現。自此以後,孔子變而為神,儒家變而為儒教。”*同上書,第269~270頁。其實,即便在先秦時期,諸子也與經學息息相關。王葆玹指出:“中國有一俗見長期流行,即以為五經純為儒家經書,經學為儒家所獨有。”實則“五經在秦代以前,乃是各家學派共同尊奉的典籍”。*王葆玹《今古文經學新論》增訂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4頁。章太炎《國故論衡》卷下《原儒》言“儒有三科: 關達、類、私之名。”達名為儒,“是諸名籍,道、墨、刑法、陰陽、神仙之倫,旁有雜家所記,列傳所録,一謂之儒,明其皆公族”。後世所謂儒家,實後起之私名。“今獨以傳經為儒,以私名則異,以達名、類名則偏。要之題號由古今異,儒猶道矣。儒之名於古通為術士,於今專為師氏之守。道之名於古通為德行道藝,於今專為老聃之徒。道家之名不以題方技者,嫌與老氏掍也。傳經者復稱儒,即與私名之儒殽亂。”*章太炎《國故論衡》,龐俊、郭誠永疏證本,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481~490頁。經子關係,誠如《漢書》卷三十《藝文志》二《諸子略》序所言:“《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弊端,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亦股肱之材已。”*班固《漢書》第6册,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746頁。即便由子學著述的主要文體“論”來看,劉寧認為:“秦漢以下所形成的子學‘論著’,在體制上,受到《荀子》的深刻影響,形塑中國式思想‘論著’之基本體式的,既非玄遠的形上之思,亦非複雜而深刻的邏輯思辨,而是經驗化的,以‘述説’和‘辨析’為主的荀子之文。這對於理解漢語思想的表達傳統,顯然是極值得思考的。”*劉寧《漢語思想的文體形式》,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37頁。“論”之一體與經密邇相關,《文心雕龍·論説》所謂“聖哲彝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劉勰《文心雕龍》上册,范文瀾注本,第326頁。是也。
二
惜乎“經學自唐以至宋,已陵夷衰微矣”*皮錫瑞《經學歷史》,周予同注釋本,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56頁。,實不足以達道。於是文士蜂起,倡言“文以明道”。如柳宗元《柳河東集》卷三十四《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故不苟為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柳宗元《柳河東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42頁。
原其初,文章與文集之起,即與子學相陵替。章學誠《文史通義·文集》曰:“自治學分途,百家風起,周秦諸子之學,不勝紛紛,識者已病道術之裂矣。然專門傳家之業,未嘗欲以文名,苟足顯其業,而可以傳授於其徒,則其説亦遂止於是,而未嘗有參差龐雜之文也。兩漢文章漸富,為著作之始衰。然賈生奏議,編入《新書》;相如詞賦,但記篇目: 皆成一家之言,與諸子未甚相遠,初未嘗有彙次諸體,裒焉而為文集者也。自東京已降,訖乎建安、黄初之間,文章繁矣。然范陳二史所次文士諸傳,識其文筆,皆云所著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則文集之實已具,而文集之名猶未立也。自摯虞創為《文章流别》,學者便之,於是别聚古人之作,標為别集,則文集之名,實仿自晉代。而後世應酬牽率之作,決科俳優之文,亦泛濫横裂,而争附别集之名,是誠劉《略》所不能收,班《志》所無可附。而所為之文,亦矜情飾貌,矛盾參差,非復專門名家之語無旁出也。夫治學分而諸子出,公私之交也;言行殊而文集興,誠偽之判也。”*章學誠《文史通義》上册,葉瑛校注本,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296~297頁。
然漢魏風氣,固以子勝於文。余嘉錫《古書通例》卷二《明體例》論“漢魏以後諸子”有云:“周秦以及西漢初年諸子,……其平生隨時隨事所作之文詞,即是著述,未聞有自薄其文詞,以為無關學術,而别謀所以自傳之道者也。自漢武帝以後,惟六藝經傳得立博士,其著作之文儒,則弟子門徒,不見一人,身死之後,莫有紹傳。故其時諸家著述,有篇目可考者,如東方朔、徐樂、莊安等,乃全類後世在文集。然九流之學,尚未盡亡,朔等或出雜家,或出縱横,考其文詞,可以知之,故猶得自成一子。自是以後,諸子百家,日以益衰。而儒家之徒,亦流而為章句記誦。其發而為文詞,乃獨出於沉思翰藻。而不復能為一家之言。一二魁儒碩學,乃薄文詞為不足為,而亟亟焉思以著述自見矣。……東漢以後,文章之士,恥其學術不逮古人,莫不篤志著述,欲以自成一家。流風所漸,魏晉尤甚。曹子建之在建安,一時獨步。然其《與楊德祖書》云:‘吾雖德薄,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録,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植年四十一而薨,竟不至於皓首,故其所志不就。然觀其言,知其不以能翰墨、工辭賦自滿也。魏文帝《與吴質書》云:‘偉長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為不朽矣。’又《典論·論文》云:‘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此上所引並見《文選》)於建安七子中獨盛推徐幹者,以其辭賦之外,能自成著作也。此足見當時之重諸子而薄文章矣。又《與王朗書》云:‘生有七尺在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魏志·文帝紀》注引)以儲君之尊,擅詩賦之美,而猶自撰書論。至明帝乃詔三公,以為‘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立於廟門在外。’(亦見《魏志·文紀》注)然不聞並刊詩賦,其重視子書可知矣。……魏桓范《世要論·序作篇》曰:‘夫著作書論者,乃欲闡弘大道,述明聖教,推演事義,盡極情類,記事貶非,以為法式。當時可行,後世可修。且古者富貴而名賤,廢滅不可勝記。惟篇論俶儻之人為不朽耳。夫奮名於百代之前,而流譽於千載之後,以其覽之者有益,聞之者有覺故也。豈徒轉相放效,名作書論,浮辭談説,而無損益哉?而世俗在人,不解作體,而務泛溢之言,不存有益之義,非也。故作者不尚其辭麗,而貴其存道也。不好其巧慧,而惡其傷義也。故夫小辯破道,狂簡之徒,斐然成文,皆聖人之所疾矣,觀范之持論,蓋謂著書者以明道為尚,不以能文為高。東漢以後,文詞漸趨華藻,雖所作諸子,亦皆辭麗巧慧,故范以為小辯破道。然而當時文士,其學本無專門傳受,强欲著書以圖不朽。談道初無異致,而行文正其所長。故雖欲於文章之外别作子書,而卒不免文勝其質,轉不如西漢人之即以文章為著作,尚去周秦不遠也。”*余嘉錫《古書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7~73頁。
唐人則將文章靡麗之風歸罪於齊梁浮豔,進而標舉漢魏風骨。如陳子昂《陳子昂集》卷一《修竹篇序》有云:“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徵者。僕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絶,毎以永歎,思古人,常恐逶迤頽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陳子昂《陳子昂集》,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15頁。《新唐書》卷一〇七《陳子昂列傳》:“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雅正。”*歐陽修、宋祁《新唐書》第13册,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4078頁。齊梁文風的特徵即是講究形式,文體駢儷,流連抒情,而輕論道經邦。《周書》卷四一《庾信列傳》:“子山之文,發源於宋末,盛行於梁季。其體以淫放為本,其詞以輕險為宗。故能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鄭衛。”*令狐德棻等《周書》第3册,中華書局1971年版,第744頁。殷璠《河嶽英靈集》卷首《集論》亦曰:“孔聖删詩,非代議所及。自漢魏至於晉宋,高唱者十有餘人,然觀其樂府,猶有小失。齊梁陳隋,下品實繁,專事拘忌,彌損厥道。”*殷璠《河嶽英靈集》,王克讓注本,巴蜀書社2006年版,第4頁。於是文士慨然以弘道自任。韓柳之外,如《全唐文》卷三八八獨孤及《唐故殿中侍御史贈考功郎中蕭府君文章集録序》:“君子修其詞,立其誠,生以比興宏道,殁以述作垂裕,此之謂不朽。”*董誥主編《全唐文》第4册,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941頁。《全唐文》卷五二二梁肅《祭獨孤常州文》又録獨孤氏語曰:“文章可以假道,道德可以長保,華而不實,君子所醜。”*同上書第6册,第5306頁。
三
考《河南程氏遺書》卷六《二程語録》六:“今之學者,歧而為三: 能文者謂之文士,談經者泥為講師,惟知道者乃儒學也。”*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第1册,載程顥、程頤《二程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95頁。又卷十八《伊川先生語》四:“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同上,第187頁。同卷又曰:“今之學者有三弊: 一溺於文章,二牽於訓詁,三惑於異端。苟無此三者,將何歸?必趨於道矣。”*同上。所謂三學,亦即後世所謂考據、辭章、義理三學。其中“訓詁之學”,即“牽於訓詁”,對應於“談經者泥為講師”,指漢唐經學而言,是經學考據,已不足以闡道。“文章之學”,是“溺於文章”,相應於“能文者謂之文士”,乃唐宋古文之謂,則文學辭章,實無能於載道。義理之學,歧而為二,一為異端,近辟釋道二氏,遠拒諸子百家*熊賜履《學統》即以老子、莊子、楊子、墨子、告子、道家、釋氏為異統。且曰:“自開辟來,歷羲農以迄姬孔,宇宙間惟有儒爾。老氏出,而異學始作俑焉。楊朱、莊周、列禦寇之徒首先和之,不數傳而汗漶若洪水矣,不可以止塞矣!……其為説也,愈變愈弊,愈差愈遠,如為長生,為方藥,為陰謀,為刑名慘刻,為縱横捭闔,為符咒幻術,為放蕩,為清譚,為禪宗寂滅。大率皆無之一言為之鵠而盪其波也。其於吾儒也,或竄入其中,或駕出其上,或峙為三教,或混為一家。而老氏遂為萬世異端之鼻祖矣!”熊賜履《學統》下册,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578~579頁。;一為儒學,斯趨於道。
程子此語關係甚大。其以經學與文章皆無與至道,而謂義理之學方可進道。於義理之學中,又驅逐異端,舉凡二氏諸子,概加擯斥,獨以儒學為正統。於是宋明理學起,而經學儒學離。其最著者為《宋史》,既沿歷代正史體例,以經學傳授作《儒林列傳》,而獨以理學諸人為《道學列傳》,其序實隱括道統而成。
鵬翔無疆,恨氣之阻,殊不知其身輕靈獨恃翼之展,其翼則以氣流扇動獲力以托舉翱翔。儒學無經學固可逞智快意,其弊則所謂“情識而肆,玄虚而蕩”。劉宗周《證學雜解》二五曰:“嗣後辨説日繁,支離轉甚,浸流而為詞章訓詁。於是陽明子起而救之以良知,一時唤醒沉迷,如長夜之旦,則吾道之又一覺也。今天下争言良知矣。及其弊也,猖狂者參之以情識,而一是皆良;超潔者蕩之以玄虚,而夷良於賊: 亦用知者之过也。”*劉宗周《證學雜解》,載吴光主編《劉宗周全集》第2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78頁。
四
明清之際,傅山倡言“經子平等”,《霜紅龕集》卷三十八《雜記》三:“經子之争亦末矣。只因儒者知六經之名,遂以為子不如經之尊,習見之鄙可見。”*傅山《霜紅龕集》下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6頁。開諸子與儒學並尊之始。至晚清,西學東漸,儒學拙於應物,學者乃以諸子對應西學。如鄧實所言:“嗚呼!西學入華,宿儒瞠目,而考其實際,多與諸子相符。於是而周秦學派遂興,吹秦灰之已死,揚祖國之耿光,亞洲古學復興,非其時邪?……吾即《荀子》之《非十二子篇》觀之,則周末諸子之學,其與希臘諸賢,且若合符節。是故它囂、魏牟之縱情性、安恣睢,即希臘伊壁鳩魯之樂生學派也。陳仲、史鰌之忍情性、綦谿利跂,即希臘安得臣之倡什匿克學派也。墨翟、宋鈃之上功用、大險約而僈差等,即希臘芝諾之倡斯多噶學派也。惠施、鄧析之好治怪説、玩琦辭,即希臘古初之有詭辯學派,其後亞里士多德以成其名學也。……夫以諸子之學而與西來之學其相因緣而並興者,是蓋有故焉。一則,諸子之書,其所含之義理,於西人心理、倫理、名學、社會、歷史、政法,一切聲光化電之學,無所不包。任舉其一端,而皆有冥合之處,互觀參考,而所得良多。”*鄧實《古學復興論》,載《景印國粹學報舊刊全集》第3册,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第1008~1012頁。當時陳黻宸即視諸子與西學為儒學兩大敵:“況於今日,時勢所趨,而百家諸子之見排於漢初者,今日駸駸乎有中興之象,則皆與我經為敵者也。環海通道,學術之自彼方至者,新義迥出,雄視古今,則又皆我經所未道者也。”*陳黻宸《經術大同説》,載陳德溥編《陳黻宸集》上册,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539頁。兩敵聯手,儒學正統遂傾。至於經學,如周予同所言:“經是可以讓國内最少數的學者去研究,好像醫學者檢查糞便,化學者化驗尿素一樣;但是絶不可以讓國内大多數的民衆,更其是青年的學生去崇拜。”*周予同《僵尸的出祟》,載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03頁。
五
近代經學沉淪,子學復興,但復興後的子學棄經學而附哲學,於是中國傳統義理之學的固有格局與内在脈絡被打散。
原其實,先秦至漢初之經説本與子學一體,也是活潑潑的自由思想。漢王朝以秦制律令體系,馴化經説,建構經學,再以之一統思想。*參李若暉《燔詩書 明法令——略論秦制的經學影響》,載《當代儒學研究》第15期,2013年12月,第29~65頁。近年葉國良倡言:“經學的生命力是否旺盛,端看是否有新體系出現,易言之,須有適用於我們這個時代的創新之作,才能維繫經學的生命力,這方面還是有待努力的。”*葉國良《楊新勳〈經學蠡測〉序》,載楊新勳《經學蠡測》,鳳凰出版社2012年版,《序》,第2頁。
如何回到自由經學,並以此為基礎重構子學?漢初司馬遷可以為我們提供參考。《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贊:“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力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録。”*班固《漢書》第9册,第2737~2738頁。太史公正是熔經鑄子,才能“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司馬遷《史記》第10册,中華書局1959年,第3319~3320頁。。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四《史記志疑序》論曰:“太史公修《史記》以繼《春秋》,成一家言。其述作依乎經,其議論兼乎子,班氏父子因其例而損益之,遂為史家之宗。”*錢大昕《潛研堂文集》第9册,載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80頁。
因此,當代“新子學”的建立,必須與經學相結合,以中華文化的大本大源為根基,立足於中華文化自身,面對中華文化的根本問題,重鑄中華之魂,此即當代“新子學”之魂魄所歸!
[作者簡介]李若晖(1972— ),男,湖南長沙人。現為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兼職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哲學、中國古典文獻學、中國德性政治。著有《郭店竹書老子論考》《語言文獻論衡》《思想與文獻》《春秋戰國思想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