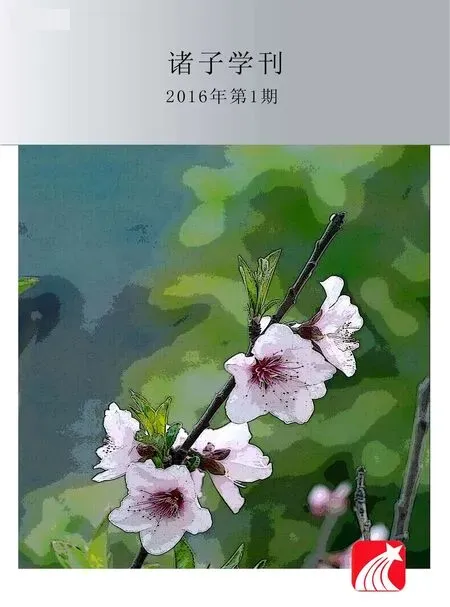淺談“新子學”建設的歷史脈絡
——從傅山到章太炎
周 鵬 賈泉林
淺談“新子學”建設的歷史脈絡
——從傅山到章太炎
周 鵬 賈泉林
明末清初的傅山、清末民初的章太炎,二人均以推重子學著稱,他們的子學思想隔代傳承,給後輩學者留下了豐富的創新資源。我們今天建設“新子學”,如能充分發掘二位先賢的思想精華,在更廣大的範圍裏尋找更多的“子學本位論”者,那麽這條“新子學”之路,必能越發寬廣明亮地展現在我們面前。
關鍵詞 傅山 章太炎 新子學 諸子 子學本位
中圖分類號 B2
方勇教授曾在《“新子學”申論》中指出:“‘新子學’要努力以新的視野去審視古代傳統,重新定位子學之為學術主流,去尋覓經學觀念籠罩下被遮蔽的東西;……‘新子學’還要充實‘國學’概念,賦予其更新、更切實的内涵,以發掘中國學術文化曲折多元的歷史真實,推進具有中國氣派的現代學術的生長。”又云:“就學術與思想的時代性和創造性而言,子學反而更能反映歷史真實。”又云:“經學傳統在中國歷史上並非不重要,但在純粹的學術與思想的標準下,歷代子學才是主流,而且經學恰恰是在子學的滋養下發展的,是子學滲入經學體系之後再政治化的産物。”從這些論述可以看出,如果我們换一副眼鏡,以一種不同於經學的“子學視角”,重新審視我國的古代文化史,眼前便有可能呈現出一幅完全不同的思想圖卷來。做是想者,代有其人,遠有傅山,近有章太炎。
一、 傅山的子學觀
傅山是明末山西大學者。在傅山的遺作中,研究子學的著作占着很大的比例。他在概括子學的特點時曾説:“子書不無奇鷙可喜,但五六種以上,徑欲重複明志,見道取節而已。”*《霜紅龕集》卷二十四《書劄·與戴楓仲》。本文凡引《霜紅龕集》,皆據傅山著、丁寶銓刊、陳監先批校《陳批霜紅龕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傅山認為,子書給人可喜的“奇”與“鷙”,只要讀五六種以上,就可以重新明白自己的志向,看清自己的道路,找到立身為人之大節。可見,傅山研究子學,從一開始就是很自覺地在尋找一種與傳統經學不同的思維模式。
傅山對子書的研究,主要採用了“批注”、“評注”、“校改”的形式,他在這方面有自己的原則標準和方法論,概括起來有三點,即“經子平等”、“自居異端”及“餐采”*依魏宗禹《傅山評傳》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一) 經子平等
傅山的子學思想最為人所知的便是“經子平等”。自從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諸子百家之學便被視為異端邪説,除老莊外,其精義一直没有被認真研究。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曾説:“諸子者,入道見志之書。……夫自六國以前,去聖未遠,故能越世高談,自開户牖。兩漢以後,體勢漫弱,雖明乎坦途,而類多依采,此遠近之漸變也。”傅山對此評論道:“心鷙氣堅,眼偏手辣,似無忌憚,而非無忌憚。以其言,濟其事,不華不腐,不周不漏,中古之風也。難難。”*《雜著録》手稿,山西省文物局藏。顯然,他是把《文心雕龍》也看成了子書,才會給予這麽高的評價。不過,他並不像劉勰一樣“宗經”,他説:“經子之争亦末矣。只因儒者知六經之名,遂以為子不如經之尊,習見之鄙可見。”*《霜紅龕集》卷三十八《雜記三》。傅山認為揚經貶子、經尊子卑不是學術史的真實狀況。他應用訓詁的方法論述道:
即以字求之,經本“巠”字:“一”即天,“巛”則川。《説文》:“巠”水脈也,而加“工”焉,又分“二”為天地,“↑”以貫之。“子”則“一”“了”而已。古“子”字作。巠、子皆從“巛”者,何也?巛即川者,水也。巛則無不流行之理。訓詁者以上之巛為發形,亦淺矣!人,水也,子之從巛者,正謂得巛之一,而為人也。與巠之從巛者同文。*同上。
通過對巠、子的字源學分析,説明二者同屬於巛,巛即川,水也;巛之一是人,人亦水也。“經”“子”既然同源於水,故没有高低貴賤之分。傅山還説:“即不然,從孩稚之語,故喃喃孔子、孟子,不稱孔經孟經,而必曰孔子孟子者,可見有子而後有作經者也。豈不皆發一笑。”*同上。即是以經學來説,也是先有子即孔子、孟子,而後始有經書,從没有聽説過什麽孔經、孟經的。由此可見,傅山欲讓“經子平等”的思想是多麽强烈!
(二) 自居異端
其實,漢以後對子學的研究並没有斷絶,歷代都有子學論著問世,但這些學者或以為諸子可與經學合觀,或主張儒釋道以及百家之説皆得道之一理,或明言九經可與諸子同讀而不能高下軒輊,或倡言諸子在某些論點特具卓見而有益世道,他們雖然重視諸子學,但每每還受着正統偏見的束縛,在潜意識裏以儒學為宗。即以明清之際而論,李贄對先秦諸子都有涉獵,並有《老子解》《莊子解》《孫子參同》《墨子批選》等專著,方以智有《諸子燔痏》《藥地炮莊》等子學著作,王夫之亦寫有《老子衍》《莊子通》《莊子解》等書;黄宗羲則“九流百家之教無不精研”(《清史稿·列傳二百六十七》)。但是在這樣開通的學術風氣下,學術界並没有擺脱正統思想的束縛,那層尊經的窗户紙,始終没有人去戳破。而敢於恢復諸子與儒家本來平等之地位,並在諸子學研究中作出更多成績的,應推傅山。他説:“異端辭不得,真諦共誰詮。自把孤舟舵,相將寶筏牽。灶觚垂畏避,薪膽待因緣。吐鳳聊庭這,雕蟲愧祖先。”*《霜紅龕集》卷十一《覽岩經詩即事》。
傅山與李贄一樣以異端自命,且一往獨深,對先秦子書作了大量的批注、評注、校改、訓詁。現存有他對《老子》《莊子》《管子》《墨子·大取》《公孫龍子》《荀子》等批注性的專著,還有他對先秦諸子所做的大量的讀書零條劄記。從這些遺作看,數量之多,内容之泛,思想之精,中國學術史上可謂空前絶後。比如: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之,是以不病,不病即不殆也。夫之將知,正是知不知耶!*《霜紅龕集》卷二十二《讀子一·老子》。
古人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何也?古公而今私也。如以臧獲二種論之,臧主耕,獲主織;獲,人也,臧,人也。*《霜紅龕集》卷三十五《讀子四》。
所謂離者,乃其藏也。得見白其白,得見堅其堅,見其白則不見其堅矣。所見之白,所不見之堅,實相附離也。所不見之堅,離在一偏,即當與所見之一争盈矣。而卒不相盈,故能相附離,能相附離,自然藏於中,猶言石能藏堅白也。*《霜紅龕集》卷三十四《讀子三·公孫龍堅白論》。
《荀子》三十二篇,不全儒家者言。而習稱為儒者,不細讀其書也。有儒之一端焉,是其辭之復而啴者也。但其精摯處,則即與儒遠,而近於法家,近於刑名家。非墨而又有近於墨家者言。*《荀子評注·後記》手稿,藏山西省文物局。
評老子,拈出“知不知”,評墨子之兼愛,謂之“古公而今私”,論公孫龍之“離堅白”,認為堅白“實相附離”,論荀子,看出其精摯處實乃法家與刑名家,這些均可謂打中諸子要害之論,而傅山以一人之識力為之,真可謂能為往聖剖心之人。
(三) “餐 采”
傅山自居異端的主張,並非感情用事,亦非絶對排斥儒學。他説“古學”不可廢,尤重《左傳》,對孟子之學還多所讚揚,對孔子弟子如子遊、子思等,尊稱為“先君子”。他尖鋭批判的是那些“雕蟲愧祖先”的“後儒”,這些人奴性十足,執經傳注,在故紙堆中討生活。他認為欲要“執古之道,御今之有”,必須全面研究子學。因此,他提出一個“餐采”的觀點:
失心之士,毫無餐采,致使如來本迹大明中天而不見,諸子著述雲雷鼓震而不聞,蓋其迷也久矣。雖有欲抉昏蒙之目、拔滯溺之身者,亦將如之何哉!*《霜紅龕集》卷十六《重刻釋迦成道記敘》。
申商管韓之書,細讀之,誠洗東漢、唐、宋以後之粘,一條好皂角也。*《霜紅龕集》卷二十五《家訓》。
吾以《管子》《莊子》《列子》《楞嚴》《唯識》《毗婆》諸論,約略參同,益知所謂儒者之不濟事也。*《霜紅龕集》卷三十四《讀子三》。
治學如同就餐,不可偏食,如果僅讀一家之書,聽一家之言,必然耳目昏蒙,思維停滯。學者應該運用“餐采”的方法廣泛涉獵,重新形成一個“雲雷鼓震”的百家争鳴的局面。傅山還認為“餐采”之法可以“解粘”,像申不害、商鞅、管仲、韓非、莊子、列子,以致佛家諸經論皆是洗儒者之粘的“皂角”(皂樹所結之莢,含堿,古代用以洗滌衣物的油塵和污穢,即今之肥皂)。只有對各家“約略參同”,才可以“解去粘縛”,而諸子書中收“解去粘縛”之效最速者,則為老莊。
(四) “老夫學老莊者也”
傅山是一位自覺地、公開地把老莊學説作為其治學底藴的學者,他不止一次地表達過自己對老莊尤其是莊子的欽慕,如“老夫學老莊者也”*《霜紅龕集》卷十七《書張維遇志狀後》。、“吾師莊先生”*《霜紅龕集》卷二十八《雜著二·傅史》。、“吾漆園家學”*《霜紅龕集》卷十六《王二彌先生遺稿序》。。而正因為傅山自覺地以老莊為本構建學術體系,他便跳出了宋明以來以儒解莊的藩籬,講過許多大膽的話,比如:“讀過《逍遥遊》的人,自然是以大鵬自勉,斷斷不屑作蜩與鴬鳩為榆枋間快活矣。一切世間榮華富貴,那能看到眼裏。所以説金屑雖貴,着之眼中,何異砂土?奴俗齷齪意見,不知不覺打掃乾淨,莫説看今人不上眼,即看古人,上得眼者有幾個?”*《霜紅龕集》卷二十七《雜著一》。他又説:“釋氏説斷滅處,敢説過不斷滅。若儒家似專專斷滅處做工夫,卻實實不能斷滅。‘世路莫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如此指摘,何等嚴毅。學者概因一個‘怕’字,要遠他,所以士大夫不無手鬆腳脱時。若但能平常淡淡看去,鬼不向人不怕處作祟也。”*《霜紅龕集》卷三十四《讀子三》。明朝滅亡的慘痛教訓,讓傅山深深感到宋明理學禁欲主義的弊端。傅山從佛學的角度指出,這樣做其實是“斷滅法”,“人欲”實際上是不可能“斷滅”的。他又從學理的角度對儒學展開更猛烈的批判:“後世之奴儒,生而擁皋比以自尊,死而圖從祀以盜名,其所謂聞見,毫無聞見也,安有所覺也。不見而覺幾之微,固難語諸腐奴也。若見而覺,尚知痛癢者也,見而不覺,則風痺死屍也。”*《霜紅龕集》卷三十一《讀經史·學解》。在傅山看來,所謂儒者,只會希圖功名富貴而已,即便是有些聞見,大都也不過是一些不知痛癢的行屍走肉罷了。由此可見,傅山以老莊思想為後盾,徑直把儒家當成了自己的對立面,把司馬遷所謂莊子“詆訿孔子之徒”的論斷給坐實了。
從以上論述我們可以看出,明清之際的子學研究,已越出了學術研究範圍,帶有民主啓蒙的因素,所以明末清初的最高統治者,不約而同地應用政治權力扼殺研究子學之風。康熙皇帝一道上諭即説:
朕披閱載籍,研究義理,凡厥指歸,務期於正。諸子百家,泛濫奇詭,有乖經術。今搜方藏書善本,惟以經學史乘,實有關係修齊治平助成德化者,方為有用。其他異稗説,根不准録。*《東華録》卷十三,中華書局1980年版。
這條記載雖記於傅山辭世一年以後,但其晚年便已施行,可見康熙帝對諸子的嚴厲態度。其實,早在明末,朝廷即對諸子之書“數申詭異險僻之禁”,在清初則是“止許刊行理學政治有益文業諸書”,對包括子學著作在内的其他書籍“通令嚴禁,違者從重究治”。雖然晚明以來研究子學之風很烈,但經學獨尊之勢依然如故。傅山研究子學,深感壓力巨大,共鳴者很少,所謂“自把孤舟舵,相將寶筏牽。灶觚垂畏避,薪膽待因緣”(《覽岩經詩即事》)即是此意。這種狀況在黄宗羲、王夫之那裏均有同樣的表露。黄宗羲説:“鋒鏑囚牢取次過,依然不廢我弦歌。”*《南雷詩曆》卷一《山居雜詠》,清乾隆鄭大節刻本。王夫之説:“思芳春兮迢遥,誰與娱兮今朝。”*《薑齋詩文集》卷八《祓禊賦》,《四部叢刊》影印《船山遺書》本。他們都寄希望於將來,在艱辛的生命旅程中,自居異端,自持船舵,精神百倍地去迎接“芳春”。於是直到兩百年後的近代,中華終於又聽到了這樣的聲音:
非儒學派的恢復是絶對需要的,因為在這些學派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學和科學最佳成果的合適土壤。*《胡適學術文集·中國哲學史·先秦名學史》,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766頁。
與傅山“經子平等”的觀點不同,胡適把子學作為與西方近代科學文化的結合點,這體現了某種近代的需求。而真正恢復子學在國學中之獨立地位的,則是章太炎。
二、 章太炎的諸子學
章太炎的諸子學建構開始於19世紀末維新變法時期,歷經《訄書》時期、1906年日本講學時期,而1910年《國故論衡》與《齊物論釋》的完成,標誌着章氏諸子學建構的成型。
(一) 《訄書》時期
《訄書》寫作於章氏在政治上追隨康有為轉而走向革命的時期。他將《尊荀》列為該書第一篇,其次《儒墨》《儒道》《儒法》《儒俠》《儒兵》,代表了諸子在章氏心目中的價值次第。《尊荀》曰:“漢因於秦,唐因於周、隋,宋因於周,因之日以其法為金錫,而己形範之,或益而宜,或損而宜。損益曰變,因之曰不變。仲尼、荀卿之於周法,視此矣。其傃古也,禔以便新也。”在章氏看來,社會政治變革既不能像康有為那樣完全虚化、割斷傳統去創新,也不能泥古不化,而是在因循古制的基礎上根據現實需要予以損益,而這正是孔、荀的精義所在。章氏還對歷史上一直遭受打壓的墨家給以較高的評價,認為墨家備受歷代攻擊的“兼愛”與“短喪”實是針對“奔命世”提出的合理主張,正是師法禹的真意。章氏還對莊子消極遁世的言行抱有同情:“夫莊周憤世湛濁,已不勝其怨,而托卮言以自解,因以彌論萬物之聚散。其於治亂也何庸?”在章氏看來,莊周恰恰是因為無法濟世才憤懣,為求一己之解脱不得不提倡遁世之説,其負面效果並不如歷代要求“廢莊”者所宣揚得那麽嚴重的。
不過,章氏《訄書》初刻本論諸子學部分稱不上系統與深入,創獲性的觀點也不多,其意義在於表現出平視儒學與諸子學的氣度。在1901—1904年删訂的《訄書》複刻本,章氏已經與康有為決裂,學術思想也得到了解放。《訂孔第二》是《訄書》複刻本最大的變化,開篇不久即説道:
凡説人事,固不當以禄胙應塞。惟孔氏聞望之過情有故。曰六藝者,道、墨所周聞。……異時老、墨諸公,不降志於删定六藝,而孔氏擅其威。遭焚散復出,則關軸自持於孔氏,諸子卻走,職矣。
這是對康有為“六經皆孔子所作”觀點的批駁,章氏認為六經本是周室“太史中秘書”,道家、墨家等諸子皆通六經。後來秦始皇焚書,只有孔子删定的六經流傳下來,因此孔子的威望驟然提高,先秦其他諸子,不能與其争鋒。緊接着,章氏抬高孟子與荀子,並認為二者“踴絶”孔氏:“夫孟、荀道術皆踴絶孔氏,惟才美弗能與等比,故終身無魯相之政,三千之化。”認為荀、孟時運不濟,没有建立功業,“而流俗多視是崇墮之”。然後章氏又立論:“雖然,孔氏,古良史也……孔子死,名實足以伉者,漢之劉歆。”孔子由古代最偉大的思想家成為一名“良史”,經學等同於史學,孔學於是成為考據之學,地位嚴重降低。《訂孔》一文在思想界影響極大,正是此文啓發了一些傾向革命的學者、留學生從傳統文化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質疑儒家學説的正當性與有效性,先秦諸子也代替儒家成為重塑中國文化傳統的重要資源。
(二) 日本講學時期
1906年9月,章氏在日本演講《論諸子學》*章念馳編《章太炎演講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6~49頁。,這是章氏第一篇系統論述諸子學的文章。在該文中,章氏對諸子學做出定義:“所謂諸子學者,非專限於周秦,後代諸家,亦得列入,而必以周秦為主。”章氏這一定義與今天的“新子學”範圍相近,不再僅限於先秦諸子,而是將歷史上所有在思想上有所創獲的學者文士都涵蓋在内。章氏認為,先秦諸子仍具有後世諸子無法達到的高度:“惟周秦諸子,推迹古初,承受師法,吝為獨立,無援引攀附之事,雖同在一家者,猶且矜己自貴,不相通融。”先秦諸子的特點在於其學説的獨立性與有所師承。章氏亦對經學與諸子學做出區别:
説經之學,所謂疏證,惟是考其典章制度與其事迹而已,其是非且勿論也。……若諸子則不然。彼所學者,主觀之學,要在尋求義理,不在考跡異同。
經學與子學一為客觀之學,一為主觀之學。經學在清代淪為考據之學,無法提供一套價值體系,與之相比,諸子學可提供豐富的思想資源以應對西學的挑戰。
這一時期,章太炎對諸子分别展開了論述。關於儒家,他延續《訂孔》的意見,指斥“儒家之病,在以富貴利禄為心”,得出儒家之士道德不高的判斷。與之相比,章氏對道家有很高的評價:“道家老子,本是史官,知成敗禍福之事,悉在人謀,故能排斥鬼神,為儒家之先導。”他將儒家不講鬼神的傳統追溯到老子,認為孔子只是剽竊了老子的部分學説:
老子以其權術授之孔子,而徵藏故書,亦悉為孔子詐取。孔子之權術,乃有過於老子者。孔學本出於老,以儒道之形式有異,不欲尊奉以為本師,而懼老子發其覆,……老子膽怯,……於是西出函谷,知秦地之無儒,而孔氏之無如我何,則始著《道德經》以發其覆。
孔子的“詐偽”之性在他與老子的關係中被章氏鮮明地刻畫出來。在《訄書》時期,章氏更為看重荀子與墨家,而這一時期,道家的地位得到明顯抬高。
至於墨家,章氏認為其敬鬼神之論與現代精神不符之處:“墨家者,古宗教家,與孔、老絶殊者也。儒家公孟言‘無鬼神’,道家老子言‘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是故儒、道皆無宗教。”而墨家勝過儒、道的地方在於不言天命,而尊信鬼神與無命説恰為相反相成之一體:
不知墨子之非命,正以成立宗教。彼之尊天佑鬼者,謂其能福善禍淫耳。若言有命,則天鬼為無權矣。卒之盜跖壽終,伯夷餓夭,墨子之説,其不應者甚多,此其宗教所以不能傳久也。……墨子之學,誠有不逮孔、老者,其道德則非孔、老敢窺視也。
雖然墨家言鬼神不符合現代人的精神,但墨者具備很高的道德,這是其他諸子所無法比擬的,亦是章氏一直對墨家心存好感之處。陰陽家與墨家同屬宗教,但二者有所不同:“蓋墨家言宗教,以善惡為禍福之標準,陰陽家言宗教,以趨避為禍福之標準。此其所以異也。”
至於法家,章氏沿用韓非之説將法家分為兩派:“其一為‘術’,其二為‘法’。……然為術者,則與道家相近;為法者,則與道家相反。”韓非則是“兼任法術者”。漢武帝時期,儒家融合法家,共同奠定了之後歷代封建王朝的統治模式。章氏認為法家對解決現實問題十分有效:“然儒家、法家、縱横家,皆以仕宦榮利為心,惟法家執守稍嚴,臨事有效。”故而對法家評價較高。
章氏對素來以邏輯學著稱的名家思想評價不甚高,對荀子、墨子的邏輯思想倒十分重視。在討論名的産生時,章氏用佛學解釋荀子的“緣天官”之説:
中土書籍少言緣者,故當徵之佛書。大凡一念所起,必有四緣: 一曰因緣,識種是也;二曰所緣緣,塵境是也;三曰增上緣,助伴是也;四曰等無間緣,前念是也。
他認為,心與五官創制“名”,也即四緣之間互相合作的過程。他用《墨經》與佛家因明論互證,將墨子邏輯論中的“故”等同於因明之因,小故、大故,類似於今天所説的必要條件與充分必要條件,接着又將歐洲三段論與兩者做了簡單對比並認為,因明論立論最為精密。章氏對邏輯學的研究並不深入,他以此證明先秦諸子學中也有不輸於西方的名學,恢復了學人對中國傳統學術的信心。
(三) 《國故論衡》與《齊物論釋》*章太炎《國故論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章太炎《齊物論釋》,《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國故論衡》下卷諸子學九篇是在《論諸子學》基礎上又一次系統而深入的總結。篇目分别為《原學》《原儒》《原道》上中下、《原名》《明見》《辨性》上下。《原儒》的特色在於從考證“儒”的所指出發,提出“儒有三科,關達、類、私之名”。章氏對三者分别予以定義:“達名為儒,儒者,術士也。”只要是通一項學問或技藝,在九流十家中,都可稱為儒。“類名為儒,儒者,知禮樂射御書數。”精通古之六藝者皆為“儒”。“私名為儒”指的是從政以輔佐君王之徒。後世所尊的“五經家”不屬三科之内。在《原道》篇中,章氏反對“談者多以老聃為任權數”的觀點,認為老子使世人皆知權術正是要使權術失效:“老聃所以言術,將以撣前王之隱匿,取之玉版,布之短書,使人人户知其術則術敗。”老子的“絶聖去智”只是摒除先入為主的“前識”,以及“尚賢”之風帶來的“流譽”,使有才能的人能够得其位。在《原名》一文中,章氏對“名”的産生過程有了更明晰的描述:“名之成,始於受,中於想,終於思。領納之謂受,受非愛憎不著。取像之謂想,想非呼召不征。造作之謂思,思非動變不形。”人體五官接於外界曰“受”,通過五官之受傳於心曰徵知,也就是“想”;五官所接之物已逝,“無待於天官”,心仍可“識籠其象”而活動謂之“思”。這些看法顯然有《荀子》的痕迹。
《明見》篇與《齊物論釋》一書皆是用佛學來解釋莊子的思想,這是章氏諸子學的最大突破。《齊物論釋》開宗明義道:
齊物者,一往平等之談,詳其實義,非獨等視有情,無所優劣,蓋離言説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乃合《齊物》之義。
在章氏看來,莊子《齊物論》的真意與佛家的真如哲學一致,佛家將世界萬物看作由八識即阿賴耶識、末那識與眼、耳、鼻、舌、身、意六識生成,只有阿賴耶識也即真如才是真實,末那識執著阿賴耶識為我,生成人我法我,意識與眼、耳、鼻、舌、身互為增上緣生成我執、法執,從而變現世界。章氏認為世界萬物起源於真如,最終又會殊途同歸於真如,這一過程便是莊子的“齊物”,世界萬物雖然在形態上千差萬别,但本質上都是真如平等變現,不平等是由於幻我、心識造成的,所以,“先説喪我,爾後名相可空。”章氏一再强調莊子“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的“天籟”觀,意在强調萬物生命形態的多樣性,不存在一個主宰或標準統攝一切。這一觀點有很强的現實意義:
原夫《齊物》之用,將以内存寂照,外利有情,世情不齊,文野異尚,亦各安其貫利,無所慕往,……然志存兼併者,外辭蠶食之名,而方寄言高義,若云使彼野人,獲與文化,斯則文野不齊之見,為桀、跖之嚆矢明矣。
章氏的《齊物論釋》戳破了西方列强打着傳播文明的幌子,卻行掠奪之實的惡行,為民族獨立與民族文化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論依據。
章氏不同時期對諸子學的闡釋,是分别通過與儒學、佛學的互證來實現的。章太炎始終對民族文化抱有信心,他的諸子學思想,為當時亟需傳統思想資源以應對西方文化衝擊的知識分子提供了一套新的價值體系。諸子學的地位空前提高,正式成為儒學之外另一套獨具中國文化傳統色彩的精神資源。
三、 傅、章子學思想的隔代傳承
上文概述傅、章二人的子學思想。之所以在漫漫的學術史上將二人拈出,是由於他們都是比較典型的“子學本位論者”。我們今天建設“新子學”,需要在歷史的長河中尋找這樣的典型。那麽,經過近三百年的時空隧道,傅、章二人的子學思想又有着怎樣的隔代傳承呢?
(一) 以諸子學應對民族危機
傅山處在山崩地裂的明末清初,本來百花齊放的文化氛圍被這一場民族浩劫硬生生地掐斷,思想界很快又進入了萬馬齊喑的狀態。在這個時候,傅山以諸子學為陣地,“自把孤舟舵,相將寶筏牽。灶觚垂畏避,薪膽待因緣”(《覽岩經詩即事》),因此,他的諸子學不得不染上了一層遺民的黯淡。而鴉片戰争以後,清政府在抵抗列强侵略的戰争中一敗再敗,作為價值體系的儒學未能提供一套可以迅速改變挨打現狀、實現民族復興的有效資源,這導致一批先進士大夫將目光轉向了儒家之外的傳統資源,諸子學應運而興,章太炎正是這一過程的關鍵人物。由於章太炎遇上的是比晚明“亡天下”更可怕的“亡種”的危局,他的諸子學,便帶有了傅山所没有的民族主義的色彩。“今中國之不可委心遠西,猶遠西之不可委心中國也。校術誠有詘,要之短長足以相覆。”*《國故論衡·原學》,第86頁。與梁啓超、嚴復那些大力吹捧西學的學者相比,章太炎始終堅持民族文化的自性。
(二) 重訂諸子與經學儒學的關係
早在明末,傅山第一個喊出“經子平等”的口號;而到了晚清民國,這個口號再一次被章太炎等學人重新提起。在《論諸子學》一文中,章氏釐清了諸子學與經學的最大差别在於經學主要是考證之學,而諸子則更注重義理,如果從應對西方思潮衝擊的角度而言,諸子學無疑更有文化上的兼容性。而在《國故論衡》中,章氏將國學分為小學、文學、諸子學三種,諸子學在他看來就等同於西方的哲學,他想以諸子學為根柢,整合整個西哲。如果説,傅山的平視經子主要是從經子關係本身的歷史演進出發的話,那麽章太炎抬高諸子地位,則更多了一層諸子學現代化的考量,正是他對諸子學的挖掘、闡釋、表彰,使諸子學比儒學更早地具備了現代性面貌。
(三) 對“子學精神”的推重
晚明是一個思想極其解放的時代,陽明心學的獨盛,本身就可以説是“子學精神”的産物。傅山的價值在於,他徑直斬斷了晚明學術囿於政治原因而不願割舍的經學臍帶,使諸子學成為真正獨立的思想,雖然這種行為被視為“異端”,並很快淹没在滿清入關的鐵蹄聲浪中,但穿過歲月的封塵,卻在三百年後的西潮衝擊下,在章太炎那裏復活。章太炎的“子學精神”並不完全等同於西式的個性解放,它更體現了中華先賢對於宇宙生命的深邃思考。“今是天籟之論,遠西執理之學弗能為也。遺世之行,遠西務外之德弗能為也。十二律之管,吹之,搗衣舂米皆效情,遠西履弦之技弗能為也。”*《國故論衡·原學》,第86頁。就應對現代性而言,諸子學可以比儒學表現出更强的生命力與包容性,所以一大批近代知識分子選擇諸子學來解決中國的現代危機。但是,如果更進一步,論及為現代性注入傳統的深度,近代學者中,只有章太炎一人所思及此。可以説,章太炎是近代歷史上第一位兼具現代性與傳統深度,亦即第一位具有“新子學精神”的學者。
(四) 視道家學説為本源
傅、章二人還有一個共同的癖好是,他們都是道家學説的擁躉。傅山公開以老莊門徒自居,老莊的著作是伴隨他一生的常備之物。“三日不讀《老子》,不覺舌本軟。”*《霜紅龕集》卷四十《雜記》五。“癸巳之冬,自汾州移寓土堂,行李只有《南華經》,時時在目。”*《霜紅龕墨寶》,山西書局1936年影印本。在他心裏,《老子》《莊子》才是真正的“經書”。而自視極高的章太炎雖説筆下支使諸子猶如用兵,但其《原道》篇卻云:“老聃據人事嬗變,議不逾方,莊周者,旁羅死生之變、神明之運,是以巨細有校。儒、法者流,削小老氏以為省,終之其殊在量非在質也”,又云“儒家法家皆出於道,道則非出於儒也”。可見在章太炎看來,道、法、儒本是同質的思想,而道家最是諸子之本源。章太炎還在莊子《齊物論》的啓發下,形成了他獨特的“新齊物論”哲學,他想以此為基礎建構一個宏大的哲學體系,這個體系不僅有中國思想,還兼采西方20世紀以前的哲學思想,包括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笛卡爾、康德、黑格爾等。章氏這一體系不但為中國,也為世界不同思想的衝突提供了答案。這些都是今天“新子學”發展的珍貴的歷史資源。
綜上所述,我們發現,確立子學之為本位,是晚明以來一直就存在的思想暗潮,但歷史在前清打了一個大大的盤旋,推遲了這股暗潮浮出水面的時間。傅山第一個發現了這股暗潮,他從義理脈絡上,以藝術家的妙語連珠捕捉到了時代新思潮的星星點點。而三百年後的章太炎,經過了樸學的訓練、西學的洗禮,返回頭再治子學,則使得子學有了更堅實的基礎和更廣闊的視野。今天治“新子學”者,如能充分發掘二位先賢的思想精華,再以二位先賢為導引,在更廣大的歷史時空裏找尋與之相類的同儕,那麽這條“新子學”之路,必能越發寬廣明亮地展現在我們面前,涅槃重生的諸子學,必將實現與現實的完美對接。
[作者簡介]周鵬(1985— ),安徽淮南人。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先秦文學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老莊哲學及諸子學研究。
賈泉林(1987— ),山東泰安人。復旦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章太炎及近現代思想史研究。均已發表學術論文數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