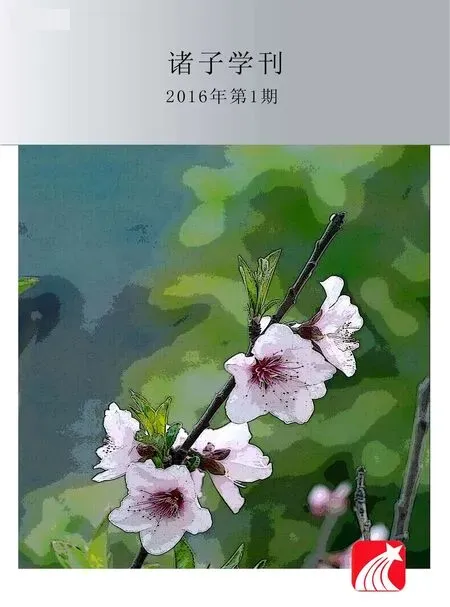“新子學”研究的當代指向與方法尋繹
——兼論劉笑敢《老子古今》的“人文自然”概念*
賈學鴻
“新子學”研究的當代指向與方法尋繹
——兼論劉笑敢《老子古今》的“人文自然”概念*
賈學鴻
思想史意義上的子學涉及起於戰國、訖於漢魏六朝的原創性諸子著作,以及歷代學人對這些典籍的整理、注釋和研究成果。它通過個體智慧的創造,汲取王官之學的精華,把對宇宙、社會和人生的深刻思索融入其中。“新子學”要兼顧歷史與現實的雙重立場,重新挖掘傳統子學的思想價值,為解决當下諸多問題提供參考。因此,要以思想開掘為導向、以服務大衆為宗旨,突破學科界限的束縛,尋求人類的共性價值。方法上,要辯證對待子學資源,不虚美、不隱惡,恰當取棄;要結合古人的思維模式,淡化舊有概念的釐析,重視文本結構義;傳統考據要以闡釋思想為旨歸;借鑒西方理論,要辯證吸收其中適合子學研究的合理性元素;努力創造涵容終極關切的新概念,以應對國學的普適走向。
關鍵詞 新子學 普適走向 古今立場 辯證態度
中圖分類號 B2
2010年曾有一本《零距離美國課堂》流行於世。在該書題為《石為何物,何以攻玉——與〈零距離美國課堂〉探討》的序文中,作者批評中國的傳統教育是“不打不成材”的“棍棒政策”,並引用《説文》對“教”的解釋,就中國教育在社會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質疑。與之相對,文章談到美國的“進步主義學校”,摘引了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教育家約翰·杜威(John·Dewey)的一段話,讓人感慨頗多。文中寫道:
“進步主義學校在美國的興起,是人們對傳統教育不滿的産物。”傳統教育强調“順從、服從……和灌輸知識。書本,特别是教材,它們都是過去的知識和過去的智慧的主要代表。”事實的學習和知識的獲取是傳統學習和静態社會的主要特徵,而這是和進步主義學習相對立的。進步主義學習和民主社會相對應,是通過解決問題來進行學習,以探索和實驗為特徵的。*王文《零距離美國課堂·序》,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10年版。
杜威關於“進步主義學習”的觀點確鑿無疑是正確的,作者對中國傳統教育的批評也不無道理。然而,對書本知識的看法,並非是美國學者杜威的“專利”。早在兩千三百多年前,中國的亞聖孟子就提出了這一主張。《孟子·盡心下》記載: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關於《尚書·武成》,依《尚書正義》引鄭玄説,到東漢光武帝時已經亡佚,今日《尚書·武成》是偽古文,敘“血流漂杵”為商紂士兵倒戈自相殘殺所致,與孟子原意不合。見楊伯峻《孟子譯注》,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325頁。
孟子所説的“書”指《尚書》,《武成》是其中的一篇,記載了武王伐紂的事件。在中國思想史上,儒家思想的邏輯起點就是周公實施的禮樂制度。《論語》中,孔子一再强調“周公之美”,渴望夢到周公。而武王伐紂這一事件,便是周公“製禮作樂”的前提。由於商紂王的殘暴,武王伐紂這一流血事件便被冠上“以至仁伐至不仁”的正義美名。然而,在倡導仁政的孟子看來,一切戰争都是非正義的。武王伐紂造成死亡無數、血流漂杵,從重生愛民角度來説,便是極不仁道的體現。因此,孟子認為閲讀《尚書》也需要甄别取舍、辯證接受。孟子的話雖然出於維護自己的仁政立場,但他對存世典籍的態度,已經表現出清醒的、科學的認識。與公元前300前後的孟子相比,杜威生活在1859—1952年,要晚二千二百多年。遺憾的是,中國這位先哲的箴言早已被後人淡忘,不僅他的觀點没有在後世教育中發揚光大,就連對違背這一理念的教育模式的批判,都要從西方學者那裏尋求給養了,這不能不説是中國國學的悲哀!
然而,令人扼腕之際,便迎來使人振奮之時。華東師範大學先秦諸子研究中心以重振國學和發展傳統文化為目標,倡導“新子學”,宛如潤物之甘露,化生之春風。借此平臺,本文略抒淺見,以待方家指正。
一、 “新子學”之概念界定及其思想開掘的困境
作為傳統國學,除了指代表精英文化的經學之外,還應包括體現個體智慧性創造的子學系統。子學發端於春秋時代的私學,興盛於戰國期間的諸子百家。它汲取了王官之學的精華,又大大超出王官政治智慧的狹義束縛,把對宇宙、社會和人生的深刻思索融入其中,藴涵着哲學、美學、宗教、文學、經濟、軍事、教育、科技等人類全方位的思想和知識。因此,子學是思想史意義上的概念,具體對象是指起於戰國、訖於六朝的原創性諸子著作,以及歷代學人對這些典籍的整理、注釋和研究成果*參見方勇《“新子學”構想》,《諸子學刊》第八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61~367頁。。
研究子學,不僅要梳理傳統主流意義上的思想認識,更要注重挖掘基於生命個體和普通百姓心理的價值取向、生活觀念,如天文、曆算、術數、方技、藝術、譜録等知識。只有不拘於“官學”,而是面向媒體時代的普通大衆的學術定位,才是應時而起的“新子學”的真正價值所在。“五四”運動時期的知識大衆化是近代中國史上的一次思想解放,把普通大衆納入“新子學”的受衆範圍,可以稱為媒體時代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即學術的大衆化。學術大衆化不是要降低研究的水準,更不是片面迎合普通世人的口味,而是要通過規範學術標準,使參與學習者形成問題意識、分析性思維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從而實現知識共用,達成思想共識,進而實現引領價值、移風易俗的目的。同時,學術只是高居“象牙塔”之上,受衆日益減少的清冷局面,或能有所改善。
然而,研究中國古代的學問,傳播傳統文化,古今中外的關係問題是不容回避的學術前提,特别是古今問題。現代人解讀古代經典,必然會面臨兩種定向,即立足文本的歷史還原和面對現實的觀察與思考。這兩種定向既矛盾衝突又不可分割。德國當代哲學家、美學家迦達默爾(Hans-Georg Grdamer,1900—2002,又譯為高達美)就此提出“視域融合”理論,即任何對經典的解讀,都是詮釋者的視域與經典文本之視域的融合*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序言》,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年版。。迦達默爾這種基於本體論的詮釋學,招來不少批評。道家研究學者劉笑敢先生在其著作《老子古今·導論》中,認為“視域融合”理論只是從終極意義上講出了詮釋學的本質共性,是人的存在與理解活動的同一性。然而從動機和心理活動角度上講,這一理論强調了融合,卻淡化或掩蓋了“回歸文本”與“面對現實”之間的衝突。再從詮釋成品的角度來説,“視域融合”理論也忽視了最初結果對兩種定位與定向的取舍。有鑒於此,劉先生結合《老子》的“自然”觀,努力探尋兩種定向之間銜接與轉化的内在機制,並以此為出發點,推出一個自己創設的概念——“人文自然”。
二、 由明晰概念的追索到結構意涵的剖析
“自然”在《老子》中共出現五次。劉笑敢先生根據五種《老子》版本,即河上公本、王弼本、傅奕本、郭店楚墓竹簡本、馬王堆漢墓帛書本,對這五處原文作了逐一對照,從語境和語法角度辨析該詞的豐富含義,細緻程度令人嘆服。他認為,《老子》的“‘自然’不是一般的敘述性辭彙,而是與道、與聖人、與萬物密切相關的普遍性概念和價值,具有最高價值的地位”,是具有普遍意義和名詞屬性的固定語言形式,是“被用作判斷的主詞和賓詞”的哲學概念*劉笑敢《老子古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35、302頁。。由於“自然”的意思太寬泛,人們對其産生很多誤解,或曰“大自然”,或曰“原始狀態”,或曰“隔絶狀態”,甚至解為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的“自然狀態”。於是,劉先生推出了“人文自然”一詞。劉先生强調,“人文自然”概念的提出,一方面為清理各種誤解,另一方面也是一種新的詮釋。從本質上,它揭示和强調了《老子》的最基本精神,同時,也為《老子》哲學在現代社會的應用和發展開闢出一條可能的途徑*同上書,第73頁。。那麽,“人文自然”到底有怎樣的意含(meaning)與意義(significance)呢?劉先生説道:
現代漢語所講的“自然”,往往相當於西方的nature或自然界,不包括人類社會文明及人的文化活動,這一意義不是中文“自然”二字的古代意義,而是近代經由日文翻譯過來的。……今日所説的自然災害,保護自然,自然生態,自然演化,自然而然,清新自然,自然流暢,其意義各不相同。……在很難創造準確的新詞語來表達老子的思想而又不至於造成新的誤解,用人文自然的概念是目前所能想到的最好方案。
……
人文自然就不是天地自然,不是物理自然,不是生物自然,不是野蠻狀態,不是原始階段,不是反文化、反文明的概念。一言以蔽之,老子之自然不是任何負面的狀態或概念。
……
老子之自然首先是一種最高價值,是一種蒂利希(Paul Tillich,1886—1965,或譯為田立克)所説的終極關切的表現。*同上書,第74~76頁。
由以上表述不難看出,劉先生對“人文自然”的解釋,是由釐清概念入手所作的解析,進而創造一個新概念,並賦予它特定的含義,這是一種基於西方理性思維的邏輯思路。西方的學術研究,自17世紀法國哲學家笛卡爾在其著作《方法談》中確立求真求實的科學標準以來,一直沿着追求概念明晰、材料準確、邏輯嚴密這一理路發展。西方語言中的“nature”,包含與“文化”、“約定”、“技術”、“精神”相對的意義。而《老子》中的“自然”,並没有這種對立意義。因此,在概念的内涵與外延上,與“nature”相對應的中文詞語“自然”,不能涵蓋《老子》“自然”觀念的全部信息,二者不能劃等號。而“人文自然”一語,由於加入了“人文”内容的限定,便補足了《老子》所説的“自然”的含義。由此可知,由於中西方思維方式的差異,在把傳統子學推向海外的傳播過程中,中國學者進行了怎樣的努力!
《老子》乃至很多中國古代的典籍,都不是以概念的明晰性為指向,而往往是尋求一種表述的模糊性,强調思想的朦朧與含蓄,即所謂“道可道,非常道”。《老子》所講的“自然”,與“道”具有同一性,有時可作為“道”的替代語,如第二十五章的“道法自然”,概念本身就有歧義特徵。有時它指自然界、自然萬物,如第六十四章的“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有時它又指自然而然,不加人為干預,即使涉及人的行為,也要做出一種“無為”的姿態,如第十七章“百姓皆謂我自然”、第五十一章“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中“自然”的豐富藴涵,很難以一語蔽之。因此,基於西方以概念明確性為基礎的文本解讀,對於傳統思想的境外傳播儘管很有意義,但對中國本土的文獻來説,或多或少有些隔靴搔癢之感。
實際上,通過詳細的文獻對讀、文意辨析,劉先生對《老子》的“自然”已經作出了正確的解釋:“自然”即自己如此,它不排斥可以從容接受的外力,而是排斥外在的强力和直接的干預。它强調質變的漸變特點,是對發展軌迹平穩性的一種内在描述,同時也是對事物“自己如此”或動因内在性的限定和補充,與儒家的“無加諸人”可以相通*劉笑敢《老子古今》,第235~236、306頁。。然而,這種寬泛的意涵,是通過語句表達的,不必一定要轉化成一個概念。或許,“人文自然”的提出,是劉先生為應對常年在國外任教而選擇的一種適合西方思維模式的傳播手段吧。
中國傳統學術,重審美、重體悟,特别强調“言外之意”的表達。明確的概念、嚴密的邏輯,有利於思想的闡述、傳播與接受,但由於缺少直觀的形象色彩和含蓄風格,便損失了美感和藝術韻味,反而又會弱化傳播的效果。基於這種重形象、輕概念的思維特徵,中國古代諸子之書常常通過比喻、意象、寓言等手法,借象明意。解讀者也就形成緣象求意、得意忘象的傳統。因此,象與象之間的關聯,即文本的結構模式,便成為傳達“言外之意”的手法之一。拙作《〈莊子〉結構藝術研究》一書,通過文本結構剖析,對《莊子》的深層意藴進行了全面系統的開掘,如“經傳結構”透視出戰國時代的言經、傳經方式,寓言故事的連類相次與《周易》的卦爻結構有某種關聯,回環否定、重章復沓等局部文本結構形態,直接關聯着“反者道之動”、“周而復始”等“道”的本質屬性*賈學鴻《〈莊子〉結構藝術研究》,學苑出版社2013年版。。從結構入手,是一種先入乎其内、再出乎其外的閲讀方法。入内,深入解析文本;出外,跳出文本,從宏觀上對典籍的思想與表達進行綜合。《莊子·天下》曾批評惠施“往而不返”,結構研究,就是用“往而知返”的方法把握經典。其實,中國古代關於文章結構的研究,到南朝時期就已經漸成體系,特别是明清時期的八股取士制度,使文章結構幾乎成為文人玩味的藝術形式,以至於章法結構脱離了文章的功用,成為束縛思想表達的桎梏。隨着近代八股文的廢止,篇章結構也一並被抛到了故紙堆中。與中國典籍不重視概念的明晰性正相反,在中國歷史發展的漫漫長河中,很多具體行動和措施又常常顯得過於“明確”,缺少辯證性。就像八股文與文章結構一樣,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現象十分普遍,今人實在應當加以反思!
三、 辯證思維在學術研究中的運用
任何事物都是對立統一的,兼顧積極的一面和消極的一面是認識事物的辯證態度。在學術研究中,無論是對待所選擇的研究對象,還是運用具體的研究方法,都應該採取這種辯證思維。事實上,很多子書由於受到時代和作者個人觀點的限制,並非完美無缺,往往具有局限性。就拿《莊子》來説,它視順道為最高原則,對待萬事萬物主張“齊是非”,這就消解了人類與生俱來的價值判斷能力。没有明確的是非標準,便會導致善惡不分的混亂。因此宋代實用主義學者葉適曾為《莊子》作出總結:“好文者資其辭,求道者意其妙,汩俗者遣其累,奸邪者濟其欲。”*葉適《水心别集》卷六,同治九年(1870)李春和刊本,見《叢書集成續編·永嘉叢書》第105册。葉適對《莊子》有清醒的認識,“道”具有包容萬事萬物的屬性,但同時也會魚目混珠、善惡雜糅,讀者則要以意去取。
然而,多數學者對自己所選擇的研究對象,往往溢美過多,客觀批判較少,就連新一代儒學大師牟宗三先生也概莫能外。牟先生對先秦道家的詮釋,從實踐性説起,把老莊文獻中具有客觀實在意味的“道”徹底扭轉為一主觀的境界,並由此判定道家為“純粹的境界形態”、“徹底的境界形態”的形上學*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臺北學生書局1983年版,第103、104頁。。在牟先生看來,道家言道所具有的客觀實在意味純為一種姿態,而“境界形態的形上學”實質上提升了“道”的價值意義,而“道”所包含的“偽”的因素,也即葉適所謂的“奸邪者濟其欲”的一面,被上升到心境修養,從而突出了道家虚一而静的修養境界。牟先生的這一觀點,是基於與儒家對比提出的。學術要服務於社會,是儒家學者的立學之本,對道家理念進行提升改造,便是這一原則的體現。或許,這也是牟先生辯證認識道家思想體系之後所做的態度決擇。
現代“新子學”在研究方法上常常借鑒西方,然而,對産生於西方世界的諸種理論與方法,同樣要進行辯證取舍,以適合本土文本的具體特徵。關於借用西方概念來闡釋中國哲學的“反向格義”之法的弊病,劉笑敢先生進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討,一再强調“西方笛卡爾以來的dichotomy(對立二分)式的概念結構與中國哲學思想中的概念系統不合”*劉笑敢《老子古今》,第93~111頁。。拙作《〈莊子〉結構藝術研究》一書,同樣借鑒了英國形式主義美學家克萊夫·貝爾“有意味的形式”理論。貝爾的理論是針對視覺藝術形式提出的美學假説,與《莊子》文本的語言形式並不相同,但其對視覺形式深層韻味的叩問,與探求《莊子》之道的“言外之意”具有相似性。因此,書中只是由貝爾的“有意味的形式”引出文本形式同樣具有韻味,而探尋其意味的具體方式,則結合了中國南朝梁代文論家劉勰《文心雕龍·原道》的觀點,即“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賈學鴻《〈莊子〉結構藝術研究》,第5頁。。也就是説,參考西方的理論與方法,不能全盤照搬,而是要辯證取棄,借鑒其中的某些合理因素,以此為突破口,再經過本土化轉换,作為闡釋本土典籍的方法思路。
四、 挖掘子學思想普適性的重要意義
諸子之學的興起,緣自先秦時期日益加劇的社會危機。禮崩樂壞,官學解體,文化重心由王官轉移到士人群體。士人是居於君王貴族與百姓庶人之間的知識一族,他們承繼了王官的社會責任,為尋找社會病因,療救世人創痛,紛紛著書立説,所論問題之多、探索範圍之廣、思想争鳴之活躍、研究氛圍之濃厚,空前絶後。然而,諸子承官學而來,思路均是自下而上,以幫助國君治理天下、出謀劃策為最高鵠的。也就是説,諸子之學的出發點,常常是君王,而不是普通百姓。即使是强調道德修養的儒家之學,其對象是讀書人自身,最終目標還是“學而優則仕”。時光荏苒,在21世紀的今天,社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科技進步、知識普及、信息爆炸、經濟騰飛、環境污染、資源將竭、人性危機……面對時代的種種挑戰,“新子學”不能僅僅盯着“上層”,而是要把注意力轉向普通大衆,甚至不同區域、不同民族的文化。因此,關注人性的共同訴求、解決人類的共同問題,是“新子學”的使命。沉睡的傳統子學典籍,早已在那裏静静等候被時代的繩索牽引得精疲力盡的人們。
如上所述,牟宗三先生的“境界狀態的形上學”理論,雖然淡化了對道家認識的全面性,卻突出了老子哲學的實踐特徵與道的價值意義,實質上提升了道家哲學的品格。與此相類,劉笑敢先生的“人文自然”概念,同樣挖掘出道家普適性的功能。他將老子之“自然”與蒂利希的終極價值相聯繫,認為老子之“自然”表達了對人與宇宙關係的終極關切、對人類各種群體關係及生存狀態的希望與期待、對人類各種生存個體存在和發展的關注。同時指出,“人文自然”彰顯了兩個原則,一是實現人文自然的理想就意味着承認自然的秩序高於强制的秩序;二是人文自然的原則高於正義、正確、神聖的原則。劉先生關於道家“自然”觀念的終極思考,實質上是通過概念的界定,實現了迦達默爾所謂的回歸歷史與面對現實的“視域融合”。而從中國的思維傳統看,這一概念與“天人合一”的命題異曲同工。“天人合一”本身就是一種自然狀態,也是人類最理想的生存狀態,它以群體和諧為理想,彌補了儒家“親親”原則的不足,站在宇宙、人生的總體維度來審視世界。正如劉先生總結的:“遵循人文自然的原則,人類社會就多一個價值標準和精神資源,比較容易進入一個新的文明階段。這個新階段的特點應該是人們不僅能在親朋好友中間感到無盡的温馨情誼,而且面對無數陌生的面孔也會感到自在、自然、放心、安心。”*劉笑敢《老子古今》,第88頁。
牟、劉兩位先生的研究方法,或許有不完美之處,但為“新子學”的研究提供了參照,就是既要立足歷史文本,又要面對社會現實,進行個性化和符合時代特徵的解讀。這要求學者既要有傳統國學的功力,又要有面向世界的眼光,既要透徹領悟古代典籍的思想意涵,又要超越文本,進行具體視域下的意藴闡釋。這是時代的要求,是使傳統子學煥發活力的需要。中西方乃至其他諸多民族,把握世界的思維模式差異很大,無論是體悟還是認知,無論是直覺還是分析,無論是還原還是升發,通過學術研究與交流,形成理解,實現溝通,是當代“新子學”的任務。因為,世界是複雜的,“道”是動態的,宇宙也是不確定的,强調自然,倡導多元和諧,或許正是“天人合一”這一古老理念的精髓。
[作者簡介]賈學鴻(1969— ),女,河北涿州人。東北師範大學碩士、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復旦大學博士後,研究方向為先秦兩漢文學、道家文學、傳統文化傳播。現為揚州大學新聞與傳媒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出版專著有《〈莊子〉結構藝術研究》。
① 本文是“揚州大學新世紀人才資助項目”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