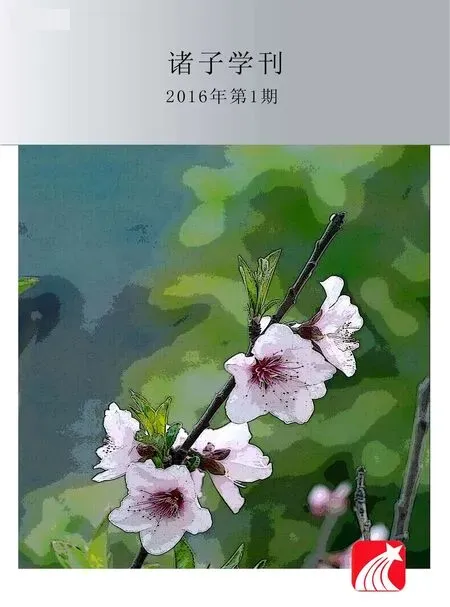重建我們的信仰體系,子學何為?*
宋洪兵
重建我們的信仰體系,子學何為?*
宋洪兵
信仰與理性不必二元對立。所謂“信仰”,並不意味着交出自己的理性,而是對某種價值或境界擁有深切而執著的情感灌注。信仰具有三個層次: 宗教信仰,境界信仰和包括法律信仰在内的規則信仰。三種信仰構成了一個完整的信仰體系。三者之間,前二者事關幸福,後者事關公正。公正應以幸福為目的,但真正全社會幸福感的提升,離不開公正的制度及和諧的社會氛圍。真正良好的社會,必須在守法傳統及規則意識的基礎之上,形成普遍的規則信仰,唯有如此,宗教及境界,方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其正面功能。國學領域的道教、佛教組成宗教信仰,儒家與道家構成境界信仰,法家則專注於規則信仰。三者互動,對於當代中國信仰體系的重建,具有不可忽視的價值和意義。
關鍵詞 國學 宗教信仰 境界信仰 規則信仰
中圖分類號 B2
當前中國盛行“國學熱”,傳統文化呈現復興趨勢。究其原委,當然因為其對於今日之社會仍具價值。由此,探討傳統思想文化的當代價值成為中國學界關注的一個焦點話題。細繹各種研究傳統文化當代價值的文章及著作,所論“當代價值”的思路不外乎幾種: 其一,對接型。這種思路着力於梳理傳統思想與當代社會正在提倡的現代理念不相衝突,完全可以實現傳統與現代的對接。其二,現實需求型。這種思路突出强調傳統思想對於解決當代社會面臨的諸多現實難題所具有的現實功能。其三,互補型。這種思路主張西方的現代性是未完成的現代性,而現代性危機的出現使得中國的傳統思想獲得了新的價值。應該説,上述三種思路在當今學界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同時他們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亦有相當的合理性。本文擬在反思上述研究思路的基礎上,探討當代中國重建信仰體系的過程中,作為國學重要組成部分的子學所具有的理論價值與現實功能。
一、 國學當代價值研究的三種思路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思想界曾有一股反孔、反儒學、反傳統的思潮。在盛行國學熱的今天,前賢激烈反孔、反儒學已經顯得不合時宜,與傳統和解,實現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偉大復興,成為當下知識界的主流話語。儘管如此,在動輒言傳統思想、儒家思想當代價值之今日,陳獨秀、陳序經當年的鏗鏘追問仍然值得我們重視,因為他們曾經的追問至今仍未得到提倡儒家思想當代價值的學者的正面回應。
1919年5月4日,陳獨秀針對北京《順天時報》在此前發表的《孔教研究之必要》一文,在《每週評論》發表署名“只眼”的文章,以為商榷。他認為,“我們反對孔教,並不是反對孔子個人,也不是説他在古代社會無價值。不過因他不能支配現代人心,適合現代潮流,還有一班人硬要拿他出來壓迫現代人心,抵抗現代潮流,成了我們社會進化的最大障礙。《順天》記者既然承認孔教在法律上、政治上、經濟上都和現代社會人心不合,不知道我們還要尊崇孔教的理由在那裏?”又説:“除了君臣父子夫婦之道及其他關於一般道德之説明,孔子的精神真相真意究竟是什麽?”*陳獨秀《孔教研究》,《每週評論》1919年5月4日。
陳獨秀的追問被梁漱溟譽為“鋒利逼問”,他在解讀陳獨秀此篇文章時進一步將其清晰化、明瞭化:“孔子的話不外一種當時社會打算而説的,和一種泛常講道德的話;前一種只適用於當時社會,不合於現代社會,既不必提;而後一種如教人信實、教人仁愛、教人勤儉之類,則無論那地方的道德家誰都會説,何必孔子?於此之外孔子的真精神,特别價值究竟在那點?”梁漱溟還稱讚陳獨秀將舊派先生逼問得張口結舌,“實在説不上話來”*梁漱溟《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208頁。。
20世紀30年代,深受陳獨秀、胡適等人思想影響的陳序經進而提倡“全盤西化論”。1933年12月29日晚,陳序經在中山大學禮堂發表題為《中國文化之出路》的學術演講,主張“全盤西化”,而其致思理由,則與陳獨秀的追問邏輯一脈相承,他説:“從理論方面説來,西洋文化,是現代的一種趨勢。在西洋文化裏面,也可以找到中國的好處;反之,在中國的文化裏未能找出西洋的好處。精神方面,孔子所説的仁義道德,未必高過柏拉圖的正義公道。”又謂:“從比較上看來,中國的道德,不及西洋;為的是中國的道德家本身不好。中國人無論公德私德都不好。教育亦的確落後。法律的觀念薄弱。一國之本的憲法,素來也不很講究。哲學也不及西洋的思想,如柏拉圖哲學之有系統。”*陳序經《中國文化之出路》,《民國日報》(廣州)1934年1月15日。
現在暫時撇開陳獨秀、陳序經具體的學術觀點諸如激烈的反孔、反儒學以及“全盤西化”等言論不談,單就二人對儒學當代價值的追問做一些方法論的反思。依據二人的思路,欲探討某種古代觀念的當代價值,必須與現代社會的諸種觀念價值相比較,尤其與西方民主科學等觀念相比較,如果相對於西方的民主科學觀念,古代觀念具有某種無可替代的特殊價值,那麽我們就可以説這種古代觀念在現代社會具有當代價值,相反,則不能輕易標榜所謂當代價值。這種思路對於我們今日探討國學的當代價值仍有很大的啓發性。
今日要談國學包括儒家、道家甚至法家的當代價值,必須首先在邏輯上回答幾個基本問題: (1) 當代社會的價值觀念領域缺不缺國學提倡的價值觀念?如果我們現代社會根本不缺諸如此類的觀念,那麽國學的特别價值何在?這也正是梁漱溟根據陳獨秀的言論所總結出來的基本邏輯:“教人信實、教人仁愛、教人勤儉之類,則無論那地方的道德家誰都會説,何必孔子?於此之外孔子的真精神,特别價值究竟在那點?”(2) 當代社會的種種現實問題,是否能够從某種觀念也可以具體為國學的提倡就能得以解決?譬如,當代社會出現的公德意識缺失、政治腐敗等現實問題,是否可以從儒家的“以德治國”的觀念提倡得以解決?對上述兩個問題的回答,是論證國學“當代價值”究竟何在的基本前提。
就第一個問題而言,國學的很多觀念其實已經廣泛盛行於當代社會。譬如,就儒家而言,當代社會的各個領域所盛行的,恰恰不是儒家式道德觀念的缺乏,而是諸如拾金不昧、見義勇為、勤儉節約、助人為樂、廉潔奉公等道德説教的氾濫!如此一來,有關儒家思想當代價值的“對接型”思路就會存在很大漏洞。在“對接型”思路中,學者們誤將“輔助性歷史資源”或來自歷史理念的“支援意識”作為一種“當代價值”。姑且不論儒家的民本觀念是否與現代民主相衝突的問題,學界仍莫衷一是,難有定論;即便假定儒家的民本思想與現代民主理念是根本一致的(有學者稱之為“凖現代性”),那麽依照陳獨秀、陳序經的有關當代價值的邏輯思路分析,儒家的民本觀念也頂多能為現代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提供歷史記憶而已,其與源自西方的民主理念相比,無論在理論完善性與制度可行性層面,均無法呈現優越的獨特價值。由此,我們勢必會問: 在民主理念昌明之今日,儒家民本觀念的當代價值何在?畢竟,“凖現代性”終究是參照“現代性”而言的,在“現代性”已經不再陌生的當今中國,儒家民本觀念除卻“輔助性的歷史資源”這一價值之外,是否具有“當代價值”就很成問題。就法家而言,也有不少學者堅持這樣的觀點: 當代中國追求“以法治國”,欲實現“法治”,故本着“古為今用”的原則,法家的“法治”可以提供思想借鑒。這是一種空洞、膚淺的觀點。道理很簡單,因為在民主法治觀念已經深入人心的當代中國,如果單從“法律”的角度來理解韓非子之“法”同時又無法説清其“法治”思想到底能够為現代“法治”提供什麽智慧,那就缺乏説服力。這正如在已經熟練掌握如何製造輕便、高效的電腦技術的當代社會,人們還非常矯情地説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電腦製造技術能為當代電腦製造技術的發展提供思想資源一樣,無法令人接受。
承繼第一個問題的邏輯,回答第二個問題時人們應該理智地意識到,當代社會出現的種種現實問題,迫切需要的是各種現實措施的落實,而非某種觀念的簡單提倡。那種以為提倡某種觀念就能很好解決現實問題的思路,實則具有“文化決定論”的傾向,也即林毓生所批評的“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方法”*林毓生《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174頁。。觀念層面所期待的對現實問題的解決途徑,與真正面對現實問題所需要的有效途徑之間,實際存在着巨大的差異。以儒家“以德治國”觀念為例,有學者提出儒家的德治有助於解決當代中國的腐敗問題。其實,瞭解中國現實的人們都清楚,高尚道德的提倡,在當代中國並不缺乏。當代中國意識形態的正當性肇始於共産黨人的光明磊落與無私奉獻,奠基於鮮明的人民性。但是,我們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出現了現實問題。由此,我們勢必會問: 依照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及共産黨人的高尚倫理都無法徹底解決的現實問題,儒家的政治理念到底對於解決當代的諸多困境又有多大作為呢?説到底,當代社會之所以公德缺失、政治腐敗,關鍵不在於教育領域的價值提倡,不在於個人内在的道德修養,而在於現實社會中各種利益與權力之間盤根錯節的關係。如何理清這種關係,必須依靠制度建設與外部監督。就此而論,依照現實問題而“對症治病”開出的“需求型”思路,是無法解決現實問題的,儒家思想的“當代價值”在此也不合邏輯。
互補型思路,立足於中西文化各自優長之比較,通過發掘中國學術固有之文化特徵,旨在確立起文化自信。若能證成中國固有文化確乎存有優於西方文化之長處,當今加以大力提倡,則不僅於當今國人之生活有當代價值,而且於整個人類文明之進步與發展亦有助益。應該説,這種研究思路值得充分肯定,但是實施難度實在太大。原因在於,一方面,對於研究者的學識要求很高,不僅需要中西貫通,而且更需超越主觀的價值偏好,真正尋出中國文化的精華而非糟粕貢獻給人類;另一方面,面對中國文化對西方文化所具有的“糾偏”或“補充”特質,現代的西方文明是否願意接受和承認,也是一個大難題。當然,這種思路的要點最終還是着眼於中國現實本身,西方文明承認與否倒是一個次要的問題。如果真能在國學中發掘出真正有益於當代中國的思想資源,倒不失為一種值得嘗試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不過,這種思路還可能存在一個致命的弱點,即: 完成現代性的現代西方社會對於前現代思想資源的“稀缺”和“好奇”,並不能簡單視為中國文化的優點,尤其不能簡單將之視為當代中國在完成現代性過程中需要保留的東西(也可能是當代中國需要克服的弊端,比如儒家意義上的倫理關係導向的處事方式)。
鄙意以為,若論“當代價值”,或許當年費孝通的社會調查思路更有啓發性,從瞭解“中國社會究竟是什麽”的問題意識出發,做更多實證性的調查研究*費孝通《個人·群體·社會》,《鄉土中國·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26~327頁。。從社會學、政治學及心理學的角度詳細考察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探討近代以來中國的民主化進程為何如此曲折坎坷的觀念背景及社會土壤,在洞悉阻礙中國民主化的諸種癥結基礎上進而推動中國歷史的發展,或許才是真正的“當代價值”。然而,在現代學科體制之下,這種學術訴求已然超越了人文學科所能承載的研究功能。鑒此,將國學的當代價值重點放在人文素養和思想觀念層面,盡量與現實的具體問題保持一定距離,也即余英時所説的“下行路線”,或許是一個有益的嘗試。本文即在信仰重建層面以及觀念價值層面,超越信仰與理性二元對立的思路,探討國學尤其子學的當代價值。
二、 中國信仰體系的三重面相
在西方哲學史上,信仰往往與非理性聯結在一起。從柏拉圖對理性與非理性的區分並將信仰歸結為非理性領域開始,以至康德“理性不能證明信仰”的命題,都將信仰與理性對立起來。真正理性的人,首先應該意識到,理性並非萬能,理性與信仰的邊界由此形成。當理性不及時,信仰的功能就得以呈現,尤其關涉人類終極關懷及人生意義時,信仰之作用,理性無法替代。世界總是充滿了偶然性及不確定性,如何在這樣的世界上尋求一整套可以説服自己從而讓自己淡定從容生活的理論體系,這是人類不可或缺的本能需求。信仰之突出特質,就在於熱切而深層的情感灌注,在於深信不疑,甚至甘於為此而獻出自己寶貴的生命。一個擁有信仰的人,往往懷着一種純潔的信念,虔誠地躬行實踐,一方面在身心層面獲得人生意義之滿足而不再盲目與茫然,尤其在關涉生死問題時能够平静對待而不致惶恐甚至呼天搶地;另一方面在人際層面又會秉持信仰而實現自律,從而能够在社會和諧方面實現他律所不能及的功能。
理性與信仰之二元對立思路及各有畛域之劃分,使得人們在生活場域多將信仰歸結為放棄理性反思的宗教信仰。例如,《簡明不列顛大百科全書》(第八卷)就將信仰定義為:“在無充分的理智認識足以保證一個命題為真實的情況下,就對它予以接受或同意的一種心理狀態。”*《簡明不列顛大百科全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版,第659頁。伴隨科學的進步以及工具理性的高度發達,信仰的領地逐漸被理性所侵蝕,這就是馬克斯·韋伯所説的“持續千年的世界除魅”。理智化及理性化的增進,使得人們擁有這樣的一種認識:“只要人們想知道,他任何時候都能够知道;從原則上説,再也没有什麽神秘莫測、無法計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們可以通過計算掌握一切。”同時,韋伯也滿懷悲情地意識到,這種伴隨科技不斷“進步”的生活觀念,已經使得人生的内在意義處於不斷“前進”與“攀登”之中。進步無限,人生的意義又在何處?人生艱難為一死,當死亡來臨時,現代人如何消解死亡帶來的恐懼與不安?“亞伯拉罕或古代的農人‘年壽已高,有享盡天年之感’,這是因為他處在生命的有機循環之中,在他臨終之時,他的生命由自身的性質所定,已為他提供了所能提供的一切,也因為他再没有更多的困惑希望去解答,所以他能感到此生足矣。而一個文明人,置身於被知識、思想和問題不斷豐富的文明之中,只會感到‘活得累’,卻不可能‘有享盡天年之感’。對於精神生活無休止生産出的一切,他只能捕捉到最細微的一點,而且都是些臨時貨色,並非終極産品。所以在他看來,死亡便成了没有意義的現象。既然死亡没有意義,這樣的文明生活也就没了意義,因為正是文明的生活,通過它的無意義的‘進步性’,宣告了死亡的無意義。這些思想在托爾斯泰的晚期小説中隨處可見,形成了他的藝術基調。”*馬克斯·韋伯《學術與政治》,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29~30頁。生命意義之惑因真誠信仰缺失而成為現代人的宿命。
如何讓充分理性化的現代人重新尋回信仰,不乏學者懷着悲憫之情開始艱難的理論探索。繼韋伯之後,在20世紀70年代的北美大陸,一位精研法哲學的美國學者在人類理性的園地裏辛勤地挖掘信仰的種子,他就是伯爾曼(Berman, Harold J.)。他於1971年在美國波士頓大學做了一系列的公開學術演講,最後結集出版,即著名的《法律與宗教》。該書的一句名言,對於關注法治的人士來説已是耳熟能詳:“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虚設。”*伯爾曼《法律與宗教》,梁治平譯,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28頁。法律,在法律世俗主義及法實證主義者眼裏,往往被視為一種維持秩序的工具,歸結為工具理性的範疇,即使自然法理論體系,實則也是古希臘哲學理性思維的結果,並不藴涵深切的情感及非理性因素。伯爾曼的理論思路,即是要超越理性與信仰、主觀與客觀的對立二分,從而恢復法律所固有的信仰特質。他提出信仰包涵宗教信仰與法律信仰兩個層面,法律欲獲得完整的神聖性與權威性,僅僅依靠賞罰無法實現,必須關照並真正契合人們追求公平、公正、正義的法律情感:“權利與義務的觀念,公正審判的要求,對適用法律前後矛盾的反感,受平等對待的願望,忠實於法律及其相關事物的强烈情感,對於非法行為的痛恨,等等。這種對於任何法律秩序都是必不可少的情感,不可能由純粹的功利主義倫理學中得到充分的滋養。這類情感的存在,有賴於人們對它們自身所固有的終極正義性的信仰。”*同上書,第39頁。唯有具備上述法律情感,才可能真正形成一種守法傳統。他説:“正如心理學研究現在已經證明的那樣,確保遵從規則的因素如信任、公正、可靠性和歸屬感,遠較强制力更為重要。法律只在受到信任,並且因而並不要求强力制裁的時候,才是有效的;依法統治者無須處處都仰賴員警。……真正能阻止犯罪的乃是守法的傳統。這種傳統又植根於一種深切而熱烈的信念之中。那就是,法律不僅是世俗政策的工具,而且還是生活終極目的和意義的一部分。”*同上書,第43頁。顯然,在伯爾曼看來,信仰,並不僅僅局限在宗教領域,亦不完全排斥人之理性。凡是人類對於某種價值或境界傾注深切而執著之情感,並在實際生活中矢志不渝地加以踐行,此種狀態亦可視為一種信仰。
按照上述對信仰關涉深切而執著之情感的理解,結合中國文化的特質,不難看出,信仰除了宗教信仰、法律信仰之外,其實還具有另外一個層次的信仰,即: 境界信仰。所謂境界信仰,就是對於某種至高境界傾注無限情感,並藉此來克服人生之不確定感,從而確立起人生之意義與方向。馮友蘭曾將人生境界分為四個層次: 自然境界(本着習慣與本能之生活)、功利境界(動機利己之生活)、道德境界(動機利他之生活)與天地境界(不僅關注人類社會且更多關注宇宙且具有超道德價值之生活)*馮友蘭《新原人》,《三松堂全集》第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51~554頁。。四種境界,均不排除人之理性(正如韋伯所説,遵循習慣與本能生活的野蠻人對自己工具的瞭解是現代人無法相比的),但在最高境界即天地境界層面,又往往超越理性,具有某種信仰之特質。與法律信仰一樣,境界信仰,並不排斥理性,甚至必須仰賴理性推理。儒家之成仁成德的聖人境界與道家虚静無為的真人境界,其實均離不開人的理性。孔子之“七十隨心所欲不逾矩”依賴人生閲歷、孟子之盡心知性知天離不開惻隱之心的經驗感知及推己及人的説理,老子之“致虚極、守静篤”亦是史官對人類歷史長視距的反思結果,莊子之“心齋”與在生死面前“安時處順”的灑脱更不脱理性反思之特質。
表面上看,中國文化的境界言説,似乎與古希臘將宗教變為哲學的思路具有相似之處,將道德奠基於人類自身之理性分析,而非彼岸之神祇,從而導致一種超越生死之神秘體驗,確立起淡定從容的生活態度。柏拉圖曾認為哲學家能够在這個世界上幸福生活,即使當死亡來臨時,也會平静對待,因為他相信“在另一個世界上也能得到同樣的幸福生活”*柏拉圖《理想國》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250頁。。顯然,作為古希臘的理性主義者,柏拉圖的“另一個世界”只能是一種境界層面的世界,而非宗教意義上的天國或來世。
問題在於,理性對待人生及生死問題,如果缺乏一種持久的信念及執著的情感灌注,就很難維持一種穩定性。對此,伯爾曼曾以批評古希臘的世俗化過程而對完全理性化的人生表示質疑,他説:“柏拉圖之後,我們已不需要神祇們來告訴我們什麽是德行;我們可以憑藉自己的智力去發現它。所以至少,我們説,希臘哲學世俗化同時也是理性的神化。”他進而指出這種對道德的純粹理智的或純粹哲學的分析所面臨的困境:“這種探求本身由於僅僅依靠理性,因此它不可避免地會阻礙它所倡導的德行的實現。理智獲得了滿足,但是情感則被有意地置於一邊,而這種情感卻是我們採取任何決定性行動的根基。”(《法律與宗教》,第53~54頁)道理固然如此,但如果無法真誠地踐行,缺乏情感投入,單純的理性分析就會演變為智力遊戲,並不能真正決定人們的實際行動,亦不能在終極層面及人生意義維度給予人們安身立命之感。理性反思,不能取代情感認同與真切投入,此種情感認同與投入,往往帶有非理性之色彩,構成人類信仰不可或缺之一部分。畢竟人類不僅僅是理性之靈,而且更是情感之所寓。
中國文化之主流面相,在於關注現世生活。這一特徵,也曾經在一種理性化的思路之下被加以審視,李澤厚曾以基於經驗論的“實用理性”來定性。例如,他在分析孔子的“禮”時認為:“既把整套‘禮’的血緣實質規定為‘孝悌’,又把‘孝悌’建築在日常親子之愛上,這就把‘禮’以及‘儀’從外在的規範約束解説成人心的内在要求,把原來的僵硬的强制規定,提升為生活的自覺理念,把一種宗教性神秘性的東西變而為人情日用之常,從而使倫理規範與心理欲求溶為一體。‘禮’由於取得這種心理學的内在依據而人性化,因為上述心理原則正是具體化了的人性意識。由‘神’的準繩命令變而為人的内在欲求和自覺意識,由服從於神變而為服從於人、服從於自己,這一轉變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21頁。
對照伯爾曼對古希臘將宗教哲學化、道德理性化的批評,李澤厚對孔子思想的“理性化”處理,也受到了汪暉的批評。一方面,汪暉認為孔子之“禮是從原始祭祀和軍事征伐等儀式中發展起來的,它所包含的人情物理與天帝、鬼神的觀念並不相悖”,另一方面,他也如伯爾曼一樣,强調了作為規則的禮所應該藴涵的情感:“在周制衰敗的過程中,孔子力圖闡明周制的規範和神聖性的内在根源,並以‘仁’為中心力圖恢復能够促成大人溝通的品質和信念: 德、誠、敬、仁、義等等。在孔子的道德世界中,唯有獲得這些品質、情感和信念,禮樂才真正構成禮樂。這些在孔子這裏被歸納在禮樂論範疇中的概念與巫之傳統有着緊密的關聯。”*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第一部上卷,三聯書店2004年版,第126~129頁。
這裏提出了一個事關中國文化特徵的理論問題,即向來被視為理性化的中國文化主流(儒家、道家)裏面是否亦藴涵着深切而執著的情感?孔子踐行禮樂時的全身心投入已難以用純理性的思維來對待,自不必論。孟子難以言説之“浩然之氣”所藴涵的神秘色彩,面對生死時能够做到“舍生取義,殺身成仁”,亦非無限情感灌注所能做到。老子之“道”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特質,無不具有玄妙神秘之傾向:“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莊子思想中隨處可見之巫術遺留,《養生主》篇記載庖丁解牛,技近於道之巔峰狀態時,腳踏“桑林之舞”,實則上古巫師之舞。上述特質均超越理性,帶有某種非理性的色彩,只有從情感層面的深切服膺及個人愉悦體驗,才能得到合理説明。中國文化之至高境界,之所以能够上升為“信仰”層面,與其介於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特質密切相關,也正是對至高境界帶有某種非理性色彩的情感,才引領無數仁人志士超越生死以及古代士大夫階層的從容生活。理性與情感,共同構建了境界的内在文化基因。
至此,當把“信仰”定義為對某種價值或境界擁有深切而執著的情感灌注時,就可以區分出三個層次的信仰: 宗教信仰、境界信仰和法律信仰。宗教信仰通過外在的神靈譜系確立神聖性及權威性,以此來尋求安身立命;境界信仰通過一套理念及境界的闡釋來獲得内心的寧静,確立起安身立命的根基;法律信仰對法律所藴涵的公平、公正及正義懷有深切而熱烈的情感。上述三種信仰構成了一個完整的信仰體系。在宗教信仰、境界信仰及法律信仰三者之間,前二者事關幸福,後者事關公正。公正應以幸福為目的,但真正全社會幸福感的提升,離不開公正的制度及和諧的社會氛圍。缺乏公正氛圍的社會,宗教信仰及境界信仰固然可以給特定的社會個體帶來幸福感,然而這種幸福感亦是以逃避現實為代價的自我麻醉。真正良好的社會,必須在守法傳統及規則意識的基礎之上,形成普遍的法律信仰,唯有如此,宗教及境界方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其正面功能,從而實現三種信仰的良性共振,人們也才可能真正過上幸福滿足、寧静淡定的生活。宗教信仰及境界信仰,均是特定人群在特定人生階段面臨人生意義及生死問題時可以提供的理論體系,在其未遇到人生困惑及面臨生死困境時,未必為人生所必須。法律信仰,事關無往而不在的生存環境及日常生活,當為人生不可或缺之一部分。
古代中國,我們的先輩曾擁有宗教信仰和境界信仰。隸屬於當今“國學”(“國學”是近代相對於西學提出的概念,意為中國固有之學,包括經史子集及“小學”)範疇的佛教、道教為古人提供了宗教信仰,包括閻羅天子、城隍廟王、土地菩薩的陰間系統及由玉皇上帝等各種神怪構成的神仙系統;境界信仰則更多源自儒家及道家學説。然而中國古代自秦漢以降,並未形成一個守法傳統。這與崇尚境界、强調教化的儒家思想存在某種内在關聯。無論是孔子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抑或陸賈的“法愈滋而奸愈熾”,還是賈誼的“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都强調禮樂教化之優位性,總是期待通過柔性教化來培養完善人格,而對“法”懷有深刻的戒心乃至偏見。故而,中國古代,教化思想高度發達,法治觀念相對淡薄,並未形成一個“守法”傳統,更談不上所謂“法律信仰”。
追求大道而不屑於刑政之觀念,深刻影響着古代中國的政治文化。王充在《論衡·程材》中將通曉經、史的儒生喻為“牛刀”,而將熟悉法律的文吏比作“雞刀”。他説:“牛刀可以割雞,雞刀難以屠牛。刺繡之師能縫帷裳,納縷之工不能織錦。儒生能為文吏之事,文吏不能立儒生之學。文吏之能,誠劣不及;儒生之不習實優而不為。”雖然儒生能做文吏之事,但因儒生有更高追求,因此不屑於去探討低水準的律令規則。宋代司馬光認為:“夫天下之事有難決者,以先王之道揆之。若權衡之於輕重,規矩之於方圓,錙銖毫忽不可欺矣。是以人君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律令,知本根既植,則枝葉必茂故也。”(《司馬文正公集》卷二十七《上體要疏》)在古代士大夫階層看來,只要把握住了高階的先王之道,低階的律令規則問題自然迎刃而解。由此,中國文化形成了如下特質: 一方面,格外强調高標準的道德境界;另一方面,對於專注於道德底線的律令規則體系又存有輕視之意,不屑為之。重道德輕規則的文化後果,直接導致中國人陶醉於道德高調的同時總是忽略作為道德底線的規則體系的建設。道德高調彌漫之時,久假不歸,掩蓋的卻是没有道德底線的尷尬現實。“守法”傳統的缺失,直接導致規則意識的淡薄,這或多或少可以解釋當代中國引進西方法律體系之後法律體系與社會生活相脱節的現象,因為我們自古以來就缺乏對法律的深切而執著的情感。當然,此專就儒家思想占據主流意識形態的漢代以降的中國歷史而言,如果把眼光放在戰國及秦代的政治實踐之中,其實不難發現,彼時之中國實亦存在以法家為主導的法治傳統,其間並不缺乏規則意識以及法律信仰。古代法家與法律信仰之間的内在關聯,值得關注(後文將詳細論及)。如何移風易俗着力培養“守法”傳統,最終確立起“法律信仰”,實為當前中國面臨的嚴峻而緊迫的時代問題。
三、 國學在重建信仰體系中的角色和功能
當代中國多少人擁有信仰?官方給出的模糊資料約為一億。然而,根據2007年2月7日《中國日報》英文版的統計,當代中國大約有三億人有宗教信仰,是官方統計的三倍(《宗教信仰者三倍於估計》Religiousbelieversthricetheestimate)。也就是説,尚有十億人没有宗教信仰。中國文化崇尚境界的特質決定了中國很難形成一種類似西方社會普遍信仰基督教那樣統一的宗教信仰。在唯物論的教育體系之中,宗教往往被視為馬克思意義上的“精神鴉片”而加以批判。問題在於,當理性到了極致之時,我們如何面對那些理性所不能及的事情?同時,近代以來對傳統儒家及道家文化的不斷批判,人們對於國學的認同感日益疏離,境界信仰也逐漸淡出人們的生活場域。而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政治領域大力弘揚的高尚道德,因無法真正具備打動人心的情感特質,勢必陷入空洞説教的尷尬境地。絶大多數人缺乏宗教信仰,導致人們無所敬畏;境界信仰日益萎縮,導致人們無所追求而活在當下,忙碌、盲目而又茫然;政治領域的道德教化淪為空洞口號,導致人格分裂的同時又呈現出普遍的道德冷感。這幅當代中國的真實文化圖景,藴涵着媚權與拜金現象的必然邏輯,主導人們生存利益的例外規則(“潛規則”)大行其道,國民亦逐漸呈現暴戾、焦慮與浮躁的心態,而在此心態背後,又飽含着人們渴望並實現公平、公正以及有尊嚴的生活的深切情感。尤其步入老齡化社會,無數秉持唯物與無神的老人們,如何平静地對待即將來臨的死亡從而真正安享晚年,而不是戰戰兢兢、充滿焦慮與恐懼地接近人生終點,越來越成為一個普遍性的社會問題。某種程度上可以説,上述問題都與信仰體系之建構有關。那麽,當此之時,國學何為?鄙意以為,國學可以在宗教信仰、境界信仰、法律信仰層面給出諸多有益的啓迪,可以為當代信仰體系的重構做出貢獻。
首先,國學可以在宗教信仰層面有所作為。道教追求長生不死、羽化成仙之信仰,實則藴涵豐富的養生觀念,例如當代中國一些群體嘗試道教之“辟谷”,逐漸成為一種養生時尚;道教之神仙譜系及陰間譜系,能够使虔誠信徒産生敬畏之心,自律自戒。佛教雖源自印度,然在中國得到了長足發展並實現了本土化,其善惡福報觀念、輪回觀念、解除貪嗔癡之欲念而尋求“大自在”之極樂境界等觀念,對於真誠信奉者來説,人生意義及終極關懷問題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決。當代中國,諸多明星皈依佛門,有錢有閑階層手戴佛珠,遼寧海城大悲寺嚴格按照佛陀戒律修行之事成為新聞關注熱點,也在印證一個基本事實: 佛教對於中國的特定人群具有相當吸引力。一個虔誠的道教或佛教信仰者,會生活在自己的信仰世界,體會到宗教信仰帶來的寧静與歡喜,人生之煩惱及茫然隨之消遁。即使是死亡,亦可以坦然面對。然而,由於宗教信仰需要將自我完全付諸一個外在的神聖權威,而外在神聖權威是否真實存在的問題,勢必困擾很多徘徊在宗教信仰大門之外的人,尤其對於長期生活在崇尚境界文化的中國人而言,更是難於接受。因此,道教也好,佛教也罷,或者其他外來宗教如基督教、伊斯蘭教等,都無法成為當代中國人的全民宗教,只有少數群體會選擇宗教信仰,也只有少數群體選擇道教、佛教。佛教在當代傳播存在一個饒有趣味的現象,在某些寺院安養院為居士提供臨終關懷服務,在“南無阿彌陀佛”的佛號助念聲中,不斷有往生領導小組負責人利用温度計測試將亡者幾個身體部位的温度,藉此確定其靈魂往生輪回的位置*參閲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本科生吕中正2011年的“大學生創新實驗計劃”報告《佛教參與社會服務新機制的調查研究——以佛教安養院為中心》。。科學儀器及現代傳媒正在日益介入宗教傳播,亦算與時俱進,增强説服力,影響更多受衆。最近頗為流行的日本作家江本勝的《水知道答案》,通過高倍顯微鏡拍攝122張水在不同語境下的結晶照片,當在正能量的意念及環境中時,水結晶呈現規則美感;相反,則水結晶照片非常難看。這種萬物有靈論的思路難免啓人遐思,所以有篤信中國文化的學者據此“科學實驗”來論證佛教“相由心生,境隨心轉”的理念。
其次,國學可以在境界信仰層面有所作為。正如前文所説,絶大多數中國人其實都具有無神論的傾向,尤其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階層和白領,更是理性得難以把自己交給虚無的宗教權威。一個缺乏宗教信仰的群體,並不等於没有信仰的需求,因為人生意義以及事關生死之終極關懷,是每一個人在其一生之中的某個特定時段都會或多或少遇到的問題。如此,儒家及道家依靠講道理來提升人生境界,並且尋找到一種自我説服的理論體系從而確立起安身立命的信仰,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選項。
儒家思想體系本質上關注社會治理或現代意義上的“政治思想”範疇,然而這並不排斥人生智慧之思考,甚至其社會治理之理想,恰好立足於人格之完善。所以,儒家之政治理想與人格修養乃是一體之兩面,不可分割。近代以來,儒學脱離制度依托而成為“遊魂”,但其人生境界之理論闡釋卻可以通過“下行路線”進入人倫日用,為那些缺乏宗教信仰的人群提供信仰資源。
譬如,在生死問題層面,儒家就能使某一部分人群安身立命,淡定面對死亡的來臨。儒家認為,人生應該是有信念的有意義的人生,在充滿不確定性的實際生活中(“命”),要確立起自己的價值體系從而堅定地以此指導生活,通過不斷修身,最終完美踐行自己的人生信念,此即所謂“立命”(《孟子·盡心上》)。儒家從應然的角度提出了人應該如何活着、怎樣的人生才有意義的問題。如果一個人篤信儒家境界,真的就能做到孟子所説的“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之所以能够做到這樣,那就是内心充滿着更高的價值期待及境界追求,並且願意以生命為代價來加以成全。對於這部分群體來説,生理意義的生死問題已不再是困擾,倫理層面或境界層面的價值問題才是最為重要的。如此,即使面對死亡,也會坦然接受,而不會充滿恐懼與不安。傅偉勳曾以黑澤明的電影《活下去》主人翁渡邊為例,説明崇高的信念對於超越死亡空間獲得人生意義的重要性。渡邊自知患有絶症(胃癌),只有四個月時間的生命,剛開始他聽從一位作家的話,認為“人的責任就是享受人生”,於是到處尋歡作樂,花天酒地。然而縱情享樂給他帶來的除了空虚之外,並未解決他所面臨的生死問題。最後,他在一位活潑開朗的女同事的啓發下,立志要把一塊荒廢之地變為一個全新的兒童公園。在公園落成剪綵那天,他坐在觀衆席上,並在那裏平静安詳地離開人世*傅偉勳《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44~49頁。。懷着一種崇高信念,造福社會,積極行善,確乎能够克服生死大限的焦慮與恐懼。這也正是儒家所極力倡導的人生價值觀。
儒家的境界信仰還體現在“孔顔樂處”。《論語·述而》載:“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雍也》載孔子稱讚顔回説:“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如果有人願意秉持儒家安貧樂道、達觀自信的處世態度與人生境界,現實生活中的煩惱、痛苦與怨恨都會因此而減少甚至消失。當然,這樣的人生,未必能够讓絶大多數人去踐行,只能由一少部分人自主選擇。畢竟懷着深切而執著的情感認同儒家並切身實踐的君子或賢人,確乎鳳毛麟角,放眼中國歷史,看到的更多是汲汲於功名利禄的“偽儒”、“陋儒”或“假道學”。
道家的境界信仰可能最適合缺乏宗教信仰的當代中國人,因為道家對於人之自然生命及生活品質思考最為深入。衆所周知,道家始終關注政治之清静無為與人生境界之超然淡泊。道家强調“貴身”,尊重自然生命,主張生命的本質在於幸福地走完生命歷程。在道家看來,由生而死,是一個自然過程,面對生死,應像對待春夏秋冬演變一樣自然,不管喜歡不喜歡,願意不願意,人終有一死這個基本事實都不會因為個人情感而有所改變,“死生,命也”(《莊子·大宗師》)。死亡,作為自然生命的有機組成部分,並非恐懼、痛苦的代名詞,而是一種自由、休息,“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同上);人們只有勘破生死,自然生活,不為欲望所主宰,不被名利所誘惑,才真正符合生命的本質,快樂欣然地生活,“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莊子·德充符》)。人有死生,天地有覆墜,人力無法控制。然而,人能盡量避免與死生、覆墜一起浮沉變化,更不能因為死生、覆墜而喪失内心的寧静。心没有湮没於各種變化與分别,變得恬静而平和。真正體道、得道之人,不僅不會對終將到來的死亡心懷畏懼,而且超越生死界限而達至“道”的境界(不以心捐道),將生命完全視為一種自然而然的過程,一切都坦然對待,真正實現了境界的自由:“古之真人,不知説生,不知惡死。”(《莊子·大宗師》)道家賦予死亡以自然意義,在於告訴世人,如果一個人面對死亡時都能淡定,他的當下生活還會因名利而産生痛苦、糾結、煩惱、焦慮、憎恨、嫉妒等負面情緒嗎?試想,當一個人糾結於名利場時,忽然得知自己身患絶症即將離開人世,他當前追求的名利還有什麽意義呢?!唯有知死,方能知生。這是道家尤其莊子告訴我們的人生智慧。
秉持道家理念,真的可以給人帶來生活的安寧和幸福嗎?真的能够超越死亡的恐懼嗎?傅偉勳曾經給人們介紹過一對美國夫婦斯各特·聶爾玲(Scott Nearing)和海倫·聶爾玲(Helen Nearing)的傳奇故事。夫婦二人不信仰宗教,篤信中國道家自然無為的人生理念。他們過着一種回歸自然的世外桃源生活,為了健康和長壽,始終積極樂觀地思考,保持一顆善良之心,堅持户外體操和深呼吸,不吸煙,不喝酒,不吸毒,不飲茶或咖啡,吃簡樸的食物,如吃素、無糖無鹽又少肥,55%不炒不煮,避免醫藥、醫生以及醫院。斯各特由此活到了一百歲。在他一百歲生日之前一個月,他決定自主選擇絶食,最後有尊嚴地離開了人世,平静安詳,甚至帶有一種深沉的幸福感覺。他們相信:“死亡只是一個過渡,不是生命的終結,它是兩個生命領域之間的出口和入口。”*傅偉勳《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第54頁。很自然地,這種觀念,讓人想起莊子對待死亡的態度:“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莊子·至樂》)當然,斯各特自主選擇結束自己生命的做法,雖然有所謂“讓生命成熟,然後讓它落下”的道家智慧,但是與道家“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莊子·養生主》)的“盡年”(過滿自己的自然生命)觀念還是有所出入的。
道家還原了人生最本質的狀態,那就是人應該快樂幸福地生活,深刻把握了人們渴望過一種無憂無慮、輕鬆自在生活的心理,直至今日,依然能够打動人心。因為,道家理論以客觀事實為依據,以冷静説理的方式,把當代中國人長期忽略(生活方式層面)而又充滿渴望(主觀動機層面)的生命關懷問題,揭示了出來。接受道家理論,不需要交出自己的理性,只需想明白人生道理,然後不斷堅持、不斷强化這個正確的生活態度,最終形成一種習慣和信仰,從而可以淡定從容地面對人生各種困惑,包括對死亡的恐懼。對於知識分子群體、白領階層、政府公務員等相對高知的群體而言,道家的境界信仰是一種最佳的信仰模式。
最後,國學可以在法律信仰層面有所貢獻。毋庸置疑,作為先秦時期的一個重要思想流派,法家同樣也是國學的有機組成部分。可以毫不誇張地講,中國固有文化的復興,儒釋道固然重要,法家亦不能缺席。問題在於,自古及今,名聲極壞的法家如何對當代建構“法律信仰”有所貢獻呢?這就需要正本清源,重新認識法家,發掘法家之真精神。法家之精神,一言以蔽之曰:“規則信仰”或“制度信仰”。
衆所周知,自漢儒將法家與秦朝二世而亡之興亡教訓連為一體始,古人斥責法家“嚴而少恩”、“可用於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將其定性為暴政工具,今人更在延續古人暴政工具基礎上又批判法家提倡“君主專制統治”,認定其“法治”並非近代民主“法治”,前者為君主專制統治的工具,後者乃是憲政框架下對政府公權力之限制以及對人民權利、自由之保障。鄙意以為,上述兩種思路,要麽帶有儒家意識形態的道德傲慢,要麽帶有現代民主政體的進步偏執,都没有真正觸及法家思想的真正精神。换言之,儒法對立或基於線性社會進化論的政體思路,都無法客觀理性地評價法家。從學理上講,法家並不主張君主可以任意行使權力之“專制”,同時亦不排斥權利,甚至規則之内的自由,亦為法家題中應有之意。如果超越上述兩種明顯帶有偏見或成見的評價,就會發現,法家之“法治”乃是一套社會規則體系及其實現方法,涉及規則屬性、規則製訂、規則執行以及規則運行環境等諸多方面的探討。所謂“規則體系”,體現在社會治理層面,就成為“制度”或“規則”,體現在日常生活領域,就成為林林總總的行為規範及交往禮儀*宋洪兵《論法家“法治”學説的定性問題》,《哲學研究》,2012年第11期。。法家之“法”並非單純現代西方意義上的“law”,其藴涵的規則意識,遠比現代意義的“法”更為寬泛。法家諸子是政治學家而非現代意義上的法學家。因此,與其説法家主張“法律信仰”,莫若説其强調“規則信仰”或“制度信仰”更為貼切。事實上,法家之“規則信仰”或“制度信仰”並不排斥伯爾曼意義上的“法律信仰”,因為二者均强調公平、正義,並且都對這些價值懷有深切而執著的情感。
法家對於“法”的執著超乎想象,已然上升為信仰層面。《韓非子·内儲説上》記載衛嗣君以左氏一座城池换一個胥靡的故事:“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為襄王之後治病,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銅)買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群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胥靡可乎?’王曰:‘非子之所知也。夫治無小而亂無大,法不立而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胥靡本為地位低賤的勞役之人,如果以工具理性來衡量,其與左氏一座城池之間的價值評估,懸殊實在太大,根本没有可比性。絶大多數崇尚工具理性的人,都不會做出衛嗣君那樣的非理性行為。然而,衛嗣君之所以做出這個決定,就在於他心中對“法”及其治國價值的信仰,深信只有言出必踐,才能真正確立公信力,治國根基才有保障。這裏貌似只有維持君主統治的實際需求,殊不知作為法家之理想代言人,衛嗣君的所作所為,正體現了法家對於公平、正義的執著追求。
《韓非子·外儲説左下》記載一個“以罪受罰,下不怨上”的事例: 孔子相衛時,弟子子皋作為獄吏,曾經懲罰過一個人,施以刖刑(砍去腳)。後來,有人譭謗孔子欲犯上作亂,衛君欲將孔子抓起來。孔子及子皋衆弟子紛紛避難,緊急之時,曾遭受子皋施以刖刑的看門人將他們引到地下室,從而逃過追捕。子皋不解,詢問受刑之人為何危難之時施以援手而不趁機報復,受刑之人回答大意是: 我之所以遭受斷足懲罰,那是咎由自取,理應受罰。您宅心仁厚,在判決之時,數次不忍,雖最終秉公執法,然我心悦誠服,甘願受罰。可以想象,如果受刑之人内心缺乏對於公平、公正、正義規則的真心敬畏與情感認同,就很難理解他解救“仇人”的舉動。類似案例,在先秦法家的著作中俯拾皆是,不勝枚舉。《韓非子·外儲説左下》闡述“外舉不避仇”的案例,同樣也在彰顯法家對於公正的信仰:“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為相,其讎以為且幸釋己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讎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解狐不計前嫌,推薦自己的仇人給趙簡主為相國。其仇人感激之餘,欲前往拜謝,不料卻被解狐用箭給射跑了。理由就在於: 舉薦你不是因為我和你之間的私怨不復存在,而是因為你有能力,我有責任與義務向國君推薦有能力之人,不能因為私怨而影響公家之事。如此大公無私之舉,只能從“信仰”及情感層面來解釋。
人們對於法家思想之認識,往往停留於充分趨利避害之人性而定賞罰,認定法家思想體系中人們之所以遵守規矩,其原因在於一種利害權衡,而非心悦誠服的認同。其實,這是一種片面的認識。法家强調人們“守法”,實則始於懲罰之利益權衡,終於公正情感之確立。“以刑去刑”的法家理想,必然伴隨“守法”傳統之形成,以及“規則信仰”之確立。
法家給今人帶來的啓迪,在於如何確立守法傳統及規則信仰的問題。欲在一個規則意識缺乏的社會環境裏規則主導的制度體系確立並切實運轉,其難度可想而知。規則體系的創立實則為移風易俗的過程,意味着對此前各種行為的約束與限制,必然給某些群體帶來不便,甚至利益損失。同時,其阻力不僅來自既得利益集團的抵制,更來自民衆因不理解而産生的排斥情緒。《韓非子·奸劫弑臣》曾描述商鞅變法之前秦國的社會狀態:“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顯也”,顯然,有罪不罰,無功受賞,這是缺乏規則意識。如何克服這種現狀?“商君説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奸,困末作而利本事。”如果去掉賞告奸、重農抑商等具有特定時代語境的措施,單純從邏輯上講,由上而下主導的變法易俗或移風易俗,是一個缺乏規則意識的社會環境形成“守法”傳統的必然邏輯起點。如何解決在此過程中既得利益集團的抵觸與民衆的不合作?法家認為一旦確立起一個正確的目標,就要有足够的政治勇氣加以推行,此時不必太在意社會的不適應。“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奸莫不得而被刑者衆,民疾怨而衆過日聞。孝公不聽,遂行商君之法,民後知有罪之必誅,而私奸者衆也,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强,地廣而主尊。”這就需要執政者的決心與毅力,即使遇到阻力,也要加以推行,在此過程中切實讓百姓感受到移風易俗所帶來的利益和好處。久而久之,原有强制推行的措施在民衆那裏産生的不適感逐漸消失,一種新的社會風俗由此形成。《韓非子·忠孝》記載禹決江河、子産開畝樹桑,其執行過程中民衆皆不理解,亦不合作:“昔禹決江浚河而民聚瓦石,子産開畝樹桑鄭人謗訾。”但最終結果證明這些措施都是對百姓有利的。當然,法家如此主張的前提在於: 執政者所倡導的價值必須真正有利於民衆而非假民衆之名而行私利之實。規則意識的確立以及“守法”傳統的形成,關鍵還在於什麽樣的“法”,這個“法”應切實觀照民衆福祉而非一家一姓一黨一派的利益。
如何彰顯執政者移風易俗的決心與毅力?按照法家的思路,就在於鐵面無私、剛正不阿,即使親人犯法違規,亦不姑息。韓非子及其前輩之所以給漢儒留下一個“殘害至親,傷恩薄厚”的“殘暴”印象,根源就在於他們極端重視規則的權威性,其目的在於通過規則的引導實現天下大治,最終有利於民衆。《韓非子·外儲説右上》借晉文公與狐偃的對話表達法家為何“嚴而少恩”的深層緣由,晉文公問:“刑罰之極安至?”狐偃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施行刑罰的最高境界,就是在自己最親近的人違法犯規時鐵面無私、依法辦事,其目的就在於“明法之信”。如果一個人就連自己最親近的人犯法都不徇私枉法,那麽誰還能懷疑他維持公正的決心和信念呢?人們自然真正從内心相信規則體現的是非、善惡觀念。
法家認為,整個社會規則意識確立起來的充分條件,執政者還必須設計一個制度給正直清廉一個機會。在法家思想體系之中,例外規則或潛規則破壞既有正當規則之公平性,從而導致人們為了自己切身利益不敢清白與不願清白。欲使人們自覺遵守規則,必須打擊潛規則,防範例外規則的蔓延和氾濫,其突破口在於政治領域,在於執政官員之貪腐行為得到有效抑制。倘若政治氛圍為之清明,官員敢於清白、樂於清白,以清白廉潔而獲取應得之俸禄,政治公信力由此確立,社會整體風氣就能隨之好轉,規則意識以及守法意識才會真正形成。
法家上述主張,皆為當代中國之寫照。潛規則氾濫,人們媚權拜金的同時,各種權力尋租應運而生。不按既定規則辦事的社會氛圍,使得人們凡事皆寄希望於熟人關係。有求於人的過程,伴隨着大量人格扭曲及尊嚴盡失的現象。欲克服這種畸形社會狀態,唯有確立規則,鼓勵人們過簡單而有尊嚴的生活,並且制度也切實能够滿足人們這種過簡單而有尊嚴生活的願望。如此,社會規則意識及“守法”傳統之形成不遠矣。
某種意義上説,規則信仰適合當代中國絶大多數人群。因為絶大多數中國人都希望我們的社會越來越公平、公正,都渴望過一種簡單而有尊嚴的生活。這種情感之深切及願望之熱烈,往往以負面的嘲諷甚至批評的形式在网絡上彌漫開來。這是規則信仰賴以産生的社會基礎及情感條件。規則信仰最終能否在社會層面形成,不在於人們是否選擇規則信仰,它必須以政治制度及社會氛圍之切實改良為前提,唯有形成制度主導下的良性社會氛圍,人們才會對規則、制度及法律産生親近感及認同感。也就是説,規則信仰之確立,需要滿足人們追求公平、正義的願望為前提。
國學可以為當代中國的信仰體系重建提供思想資源。但這並非唯一資源。未來中國的信仰體系,必然呈現多元化之特質。多元化信仰體系之建構,社會需要更加開放和包容的心態,彼此尊重各自信仰。不過,可以確定的一個事實是: 國學在此過程中必然有所作為,並且其作用與功能日趨重要,這點並不會因少數堅持現代價值之反傳統鬥士之批判而有所改變。
當然,信仰必須自主選擇,只能引導,不能强制安排。因此,政治最好的選擇,就是為信仰創造良好的社會氛圍,而不必主導信仰。因為虔誠之信仰會存在一定缺陷,尤其當其與大規模的社會運動與政治實踐相結合時,負面因素更不可忽視。正如馬克斯·韋伯在闡述“信念倫理”(Gesinnungsethik)的特徵時曾指出的,恪守信念倫理的行為,並不必然會産生善的結果,有時甚至會導致罪惡的後果。此時,行為者往往會將罪責歸結為這個世界,歸結為人們的愚蠢,或者歸結為命運。“信念倫理的信徒所能意識到‘責任’,僅僅是去盯住信念之火,例如反對社會制度不公正的抗議之火,不要讓它熄滅。他的行動目標,從可能的後果看毫無理性可言,就是使火焰不停地燃燒。”由此,馬克斯·韋伯在社會治理層面更强調“責任倫理”(Verantwortungsetthik)的重要性*馬克斯·韋伯《學術與政治》,第107~108頁。。一旦執政者確定某種政治信仰並加以强制推行,其後果不堪設想。殷鑒不遠,吾輩當謹記。
[作者簡介]宋洪兵(1975— ),男,四川犍為人。歷史學博士,現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教授。著有《韓非子政治思想再研究》《循法成德: 韓非子真精神的當代詮釋》等,目前主要從事先秦諸子及其現代命運的研究。
① 本文係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明德青年學者計劃"資助項目“韓非子思想的當代價值研究"( 編號: 13XNJ012) 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