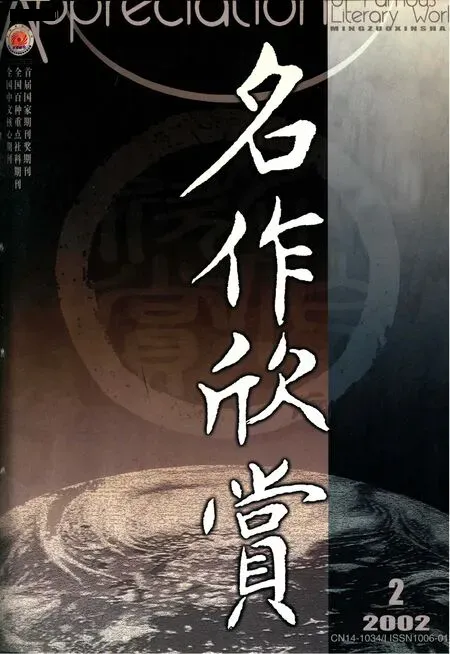孟子和荀子的《春秋》观念异同分析
⊙刘同琪[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西安 710119]
孟子和荀子的《春秋》观念异同分析
⊙刘同琪[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西安710119]
摘要:孟子和荀子是战国时期儒家双峰并峙的人物,对于儒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们的学说主要集中在《孟子》和《荀子》两书之中。就两书之中关于《春秋》的评价来看,孟子认为《春秋》是孔子依照旧有的史料编著而成的,意在拯救乱世、恢复王道,并且对《春秋》作为儒家经典的地位进行了肯定。《荀子》书中论述到《春秋》时,出现的最多的字眼是“微”,通过遣词造句寄寓褒贬之意,在荀子看来,这是儒家特有的一种表达方式。通过对比两书中关于《春秋》的评价的分析,可以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孟、荀关于《春秋》观念的异同点之所在。
关键词:孟子荀子《春秋》异同
孟子是邹国人,他推崇孔子,认为“自有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①。司马迁认为孟子受业于子思的门人,一生游历过许多国家,终因学说不符合当时君主的辟土地、霸天下、朝诸侯的想法,而被认为迂阔而不实用,晚年著书,有《孟子》十四篇传世。荀子同样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在五十多岁的时候游学于齐国的稷下学宫,曾经三次担任祭酒之职。后因人谗害,离齐适楚,春申君任他为兰陵令,春申君去世之后,他便辞官,定居在兰陵,著书十余万言,有《荀子》三十二篇传世。
一、孟子的《春秋》观念
《孟子》一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纵横恣肆的论辩,《孟子》书中在记述这些论辩时,往往引用一些其他的儒家经典,其中以《尚书》和《诗经》最多,对于《春秋》的本文内容却没有引用过一句。但在《孟子》书中有关于《春秋》的基本思想见解的记述和这些关于《春秋》的评价,为后来的儒者普遍接受。《孟子·滕文公下》:“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世衰道微,邪说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②在孟子看来,孔子作《春秋》是可以和禹治洪水,周公平夷狄、驱猛兽等事迹相提并论的壮举。司马迁继承了孟子的这一观点,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因史记而作《春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③也将孔子作《春秋》与禹、周公的功业相提并论。孟子在《孟子·公孙丑下》中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④,认为历史运行的规律是一治一乱的循环。至于导致这一治一乱现象出现的原因,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尧和舜的时代,导致动荡的原因是洪水,于是舜任命禹来治理洪水,禹采用因势利导的方法使洪水流之于海,消除了洪水的灾害,使天下恢复了安宁。在尧、舜、禹之后,导致社会动荡的原因是暴君,在暴君统治之下产生了“邪说暴行”以及夷狄侵扰的外患,于是有周公“相武王伐纣”以及伐奄驱逐夷狄。到了周王朝的末期,导致动乱的原因是乱臣贼子,但此时已没有强有力的圣王了,于是孔子站了出来,企图用修《春秋》的方法来拨乱反正。孟子认为《春秋》是救世之书,是孔子对乱臣贼子横行无忌的局面力图拨乱反正而作的。在孟子看来,孔子认为政治秩序是最为重要的,既然朝廷无力匡救乱局,那么作为士人就必须负起社会灵魂的承载者的责任,这就是孔子为什么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通过修史来讨伐乱臣贼子,恢复社会的安宁,本来是天子的事情,但当时王室衰微,已无力改变天下动荡的局面,孔子作为一个大夫,僭越身份修史讨伐乱臣贼子,所以他说“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通过这段论述,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作的,并对孔子作《春秋》的意图做了明确的表述。孟子的这段论述对后世有着重要影响,此后,不论是经今文学家还是经古文学家,大都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修订的。另外,“《春秋》,天子之事也”则为后世尊奉孔子为“素王”的先声。
孟子还对《春秋》的儒家经典地位作了定位,在《孟子·离娄下》中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⑤孟子认为《诗经》是与圣王相配的经典,圣王与《诗经》相生相灭,如果天下没有了圣王,《诗经》也会消亡,继之而体现圣王之道的是《春秋》,从这个意义上看,《春秋》和《诗经》是相连续的,都是体现圣王之道的经典。孟子认为,从内容上看,《春秋》所记载的是齐桓、晋文之事,即关于大国争霸的史实的记述;从文本方面来看,孟子认为“其文则史”,《春秋》原本是鲁国的史书,与晋国的《乘》,楚国的《杌》属于同一个类别,都是诸侯国的编年体大事记类型的史书。而开始于汉代的经今古文学派的论争中经今文学派认为《春秋》是孔子所写的,每一个字都暗含着褒贬的深意;经古文学派则认为《春秋》是孔子在鲁国旧有的国家史书的基础上进行编排整理而成的。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孟子的观点影响了古文学派关于《春秋》文本性质的看法。孟子还认为《春秋》是其“义”的,这个“义”是孔子在编排史料时所遵循的宗旨,孟子所说的孔子“作”《春秋》,而不是“编”《春秋》,正是针对这个“义”而说的。
《孟子·滕文公下》和《孟子·离娄下》的这两段评论,集中反映了孟子对于《春秋》学的看法,他的这些观点为后世不同学派的《春秋》学者所继承,他对《春秋》作用的总体评价,奠定了《春秋》作为儒家经典的地位。
二、荀子的《春秋》观念
《荀子》一书中关于《春秋》的评价虽然不多,但荀子的《春秋》观念却有他的独到之处,在《荀子·劝学》中,荀子提到了儒者学习的全过程:“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⑥荀子学说中的主干是礼学,荀子认为学习的最终目的是懂礼、用礼,认为诵读《诗经》《尚书》和《春秋》等经典的目的是为了掌握其中的“义”,即文字背后所蕴含的微妙之理,认为掌握这个“义”与否,是人和禽兽之间的分水岭。荀子没有像孟子那样强调《春秋》是王道衰微之后,圣人作为拨乱反正的工具,荀子更加注重的是《春秋》字里行间所具有的“微”的特点,“《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认为《诗经》《尚书》的特点在于广博,而《春秋》的特点在于微妙。关于《春秋》“微”的特点,荀子在《荀子·儒效》中论述道:“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春秋》言是其微也。”⑦荀子认为“道”集中于圣人之一身,《诗经》所体现的是圣人的志向;《尚书》记载的是圣人的行事;《礼》所规范的是圣人的行为;《乐》所反映的是圣人的中和之德行;《春秋》所体现的是圣人的“微”。至于什么是“微”,杨在《荀子注》说:“微谓褒贬沮劝”。《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微,隐行也”。由此可见,这里的“微”指的是《春秋》在遣词造句之中有对政治、道德等是非、善恶的批判或肯定的暗喻。荀子关于《春秋》“微”的特点的论述,对后来的学者有着重要的影响,例如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⑧。
关于对《春秋》文本认识的方面,荀子的观点与孟子也存在着差异,孟子认为“其文则史”,荀子并不认为《春秋》属于史书。在荀子看来,《尚书》才属于史书,而《春秋》则主要是圣人对于政治、道德等所作的褒贬暗喻的集合。在关于《春秋》的内容方面,荀子的看法和孟子相似,认为《春秋》的内容都是“齐桓、晋文之事”。荀子在《荀子·仲尼》中说:“仲尼之门,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五伯,是何也?曰:然,彼诚可羞称也。齐桓,五伯之盛者也……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心也,乡方略,审劳佚,畜积,修斗而能颠倒其敌者也。诈心以胜矣,彼以让饰争,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杰也,彼曷足称乎大君子之门哉!”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荀子对以齐桓公、晋文公为代表的春秋五霸评价并不高,这和孟子的“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⑩的评价很相似。
三、总结
孟子和荀子对先秦时期的《春秋》学的发展都曾经起到过不可替代的作用。总的来说,孟子《春秋》学所关注的重点在于《春秋》所编著的意图以及对《春秋》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做了定位,并且认为《春秋》属于史书。荀子更加强调《春秋》之中字里行间所蕴含的“微”,即通过特定的字词蕴藏着对于政治、德行等进行的褒扬和贬斥。此外,孟子和荀子的《春秋》观念也有相同的地方,他们都认为《春秋》在内容上记述的是“齐桓、晋文之事”,即春秋间大国争霸的事迹。
①②④⑤⑩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8页,第141页,第100页,第177页,第265页。
③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34页。
⑥⑦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4页,第158页。
⑧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01页。
⑨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25页。
参考文献:
[1]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3.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作者:刘同琪,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经学文献整理。
编辑:康慧E-mail: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