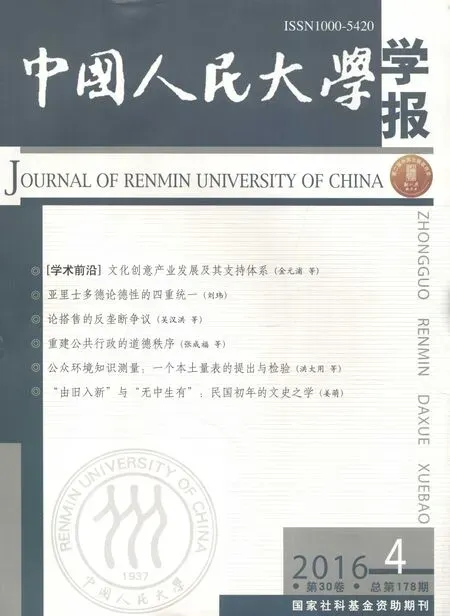形式主义文论中的唯科学主义批判
黄念然
形式主义文论中的唯科学主义批判
黄念然
现代西方形式主义文论打上了深刻的唯科学主义烙印,它的科学至上的理论姿态突出表现在对工具理性的极力追求中。基于还原主义的“悬置”与“抽取”是形式主义文论唯科学主义方法论的重要表征,从理论实质看,形式主义文论带有鲜明的反人文主义倾向。我们要全面、准确地认识形式主义文论的洞见与盲视,对其唯科学主义的理论倾向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唯科学主义;批判
通常意义上的形式主义文论指的是自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到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再到符号学、结构主义文论和后结构主义文论,有着浓厚的形式崇拜情结或重形式轻内容倾向的一派文论,其巅峰时期在20世纪20年代至五六十年代。形式主义文论在其发展历程中不断走向自我终结,原因多种多样,比如:在文学与现实关系问题上从自足论立场坚持把艺术的形成与发展视为以内在合法性为特征的一种自我运动;用“文本先于历史”的观念将现实与历史全部放入括号而形成明显的反历史主义特征;从目的论视角将形式神秘化,等等。但从总的理论渊源来看,则是由于西方形式主义文艺理论对科学主义的笃信,以及在以意义、价值为核心的文艺批评领域中将自然科学的一般原则加以不适当的推广和转换,结果导致了其解释的失效或解释力的丧失。
所谓“唯科学主义”(scientism),特指那种认为只有自然科学的方法才是能应用于任何知识领域的研究倾向。这种倾向认为,只有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才能卓有成效地用来获取知识,并主张自然科学方法应该用于包括哲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一切研究领域。由于它的影响,造成了人文、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概念和方法的竞相模仿、移植或借鉴,它一方面有力地促进了人文、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又使得人文、社会科学逐渐走上定量化、数学化、精确化的道路,并由此形成一种类似新宗教式的文化现象即“科学崇拜”——将科学视为全知全能的人类救世主,而漠视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殊性。西方形式主义文艺理论将自然科学的观念、方法不加限制地搬用到其理论构架与批评实践中,既违背了科学理性的内在精神,也促使其走向自我终结。而这一点在学界的相关研究中并无自觉的认识与阐发,这对于我们全面、准确地把握形式主义文论的洞见与盲视显然是不利的。
一、理论姿态:科学至上及其对工具理性的追求
形式主义强调的工具化甚至是机械性的那种文学批评操作模式,带有鲜明的唯科学主义倾向。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在此方面最具典型性。他们通过对圣伯夫、丹纳等人为代表的欧洲实证主义批评传统和渊源更为久远的人文主义批评传统的反拨,切断了文学同现实、作家以及读者的联系,全心致力于建设一门无所不包又能解释一切的文学科学,就像罗兰·巴尔特所宣称的那样,“结构主义不正是通过成功地描述‘语言’(言语来自语言,我们又能从语言产生言语)来驾驭无穷无尽的言语的吗?面临无穷无尽的叙事作品以及人们谈论叙事作品的各种各样的观点(历史的、心理的、社会学的、人种学的、美学的,等等),分析家的处境同面临种类纷繁的语言和试图从表面看来杂乱无章的信息中找到一条分类原则和一个描述中心的索绪尔,几乎是一样的”[1]P474)。为了让文学批评具有更严格的科学性和更加程式化,建立一种野心更大的批评技术体系似乎就成为其逻辑的必然——对清晰度、逻辑性的追求以及对证据一丝不苟的关切;拒绝接受传统的社会历史分析或貌似客观而实际主观的批评判断;将自然科学运用的那些方法移用到文学研究上来;在工具主义的基础上吸收对任何特殊个案适用的方法与技巧等等。
这一科学雄心首先来自于索绪尔,他选择了符号却放逐了意义,试图通过建构一套普通符号学把所有科学融入其中。语言学作为领航科学,“处于结构主义方案的核心地带”,成为推动索绪尔野心的纲要,并让所有有关符号的科学“都聚集在同一范式的周围”,成为“融化所有社会科学的大熔炉”[2](P66)。到了格雷马斯这里,这种科学主义的雄心发展到极致,符号学结构主义“不仅是语言学的一个简单分支,它还一直试图把所有的人文科学纳入自己的版图”[3](P281),格雷马斯从一开始就总是盘算着:“符号学应该超越语言学,语言学只是它的一部分”*格雷马斯接受多斯访问时所言。[4](P281),并且“能够把人类学、语义学、精神分析和文学批评统一在一杆大旗之下”[5](P281)。他从逻辑学那里借来“isotopie”这一概念用以揭示出全部文本是如何从属于同一语义层面的,并宣称“对于社会科学而言,这些技术可与自然科学中的代数方程式相媲美”[6](P283-284)。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为结构主义最为形式化的分支,符号学结构主义试图通过与自然科学、逻辑学、数学的联姻来最大化地实现上述科学雄心,它“盼望以无所不在的数学术语(‘程序运算法则’、‘确立等值法则’、‘转换法则’),突显出科学的重要性,盼望着它成为严密之模型”[7](P283-284)。美国学者雷纳·韦勒克曾列举了形式主义文学批评中唯科学主义的若干表现:“一种是企图效法一般的科学理想,力求使研究做到客观、取消私人性格和确定(性)。这种企图,整个说来,支持的是一种近代科学发展前的唯事实主义;其次,便是努力模仿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事物的起因和根源,实际上就是努力寻找任何一种关系,只要它在一种编年顺序的基础上是可能的。等而下之者,便是用科学因果律来说明文学现象是为经济、社会、政治条件的原因所决定的;另外一些学者甚至企图引入科学的定量分析法,如使用统计资料、表格、图解等等;最后,一些野心勃勃的学者还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试验,用生物学的概念来追溯文学的进化过程。”[8](P245-246)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否弃人文主义透视,以证明代替直觉,将文本创作者的意图消解在语境交织的客体结构之中的做法到底有什么样的实际效果?我们来看两则例子。一是法国学者路易·艾的回忆。他说:“我记得,作为评判委员会的一员,我给一部厚厚的著作写了一份摘要,那是研究婚姻问题的皇皇巨著,作者是格雷马斯的一位高足。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婚姻是一个两极结构。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真的。但是,这样的结论是否需要做上千页的分析?”*法国学者路易·艾接受多斯访谈时所言。[9](P286)二是让·弗朗索瓦·雷韦尔对罗兰·巴尔特《时尚系统》的评价。雷韦尔讥讽说,罗兰·巴尔特“用一个三段论来展示其论题:老鼠啃乳酪,老鼠是字节(syllable),所以字节啃乳酪。当然,在这方面,结构主义的老鼠是无所不能的,但是,如果老鼠也写作,它还能吃乳酪吗?只有等待社会学家们来告诉我们了”*让·弗朗索瓦·雷韦尔:《“老鼠与时尚”》,载《快讯》,1967-05-22。[10](P289-290)。如果说上述例证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再看一则例子,它能告诉我们将基本的文学虚构体裁种类放入结构主义的语法箱内能否证实这种唯科学主义观念的有效性。德国结构主义学者安德烈·乔勒斯曾出版过一本书《简单形式》,他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结构实体,并以简单形式语法或逻辑方式呈现出来。他讨论了跟文学相关的九种人类语言或符号活动的简单形式,分别是:传说、“萨迦”(英雄史诗)、神话、谜语、谚语、案例、回忆录、故事和笑话。但就像美国学者休斯所指出的那样:“作为一个‘封闭的简单形式系统’,这本书是失败的——因为它既不是封闭的、也不是系统化的。它没有使我们看到由这九种形式所构成的那个整体。它甚至没有正视是否还有其他可能的简单形式这一问题。为什么没有歌曲?祈祷?人物?等等。”[11](P75)相同的例子还见于法国结构主义者艾琼·苏里奥的《二十万个戏剧情景》,这部用速记符号揭示出的不同戏剧情境的学术册子充满了各种速记符号,形同天书,令人望而生畏。
形式主义文论尝试用一种科学精神提出种种模式与假设,以此来解释审美效果是如何由文学的形式和技巧产生出来的,其初衷及其努力是值得钦佩的,但是它试图去发现支撑人类一切社会与文化实践并成为其基础的符码、规则或体系,并为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创造整齐划一的科学纲要的科学帝国主义野心并没有让其学术日子维持多久。因为,“科学主义者的科学雄心,由于解构分析对它赖以描述和把握文化生产的二元对立的诘难,被证明是一场白日梦”[12](P198)。人们对之进行了猛烈的批评,诸如:从其他学科借用术语“以此来控制文学”;“放弃发掘作品的真正意义,相信所有的解释均等有效,从而威胁到了文学研究生死攸关的存在理由”[13](P10);用数学图式、分类学或造词术等披上科学的外衣并从总体上规避人文精神[14](P12),等等,在所有这些批评中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人们给这个科学至上、理性至上的结构主义戴上非理性主义的帽子,因为它“刻意追求悖论和稀奇古怪的解释,津津乐道语义游戏,自恋自醉自身的修辞技巧”[15](P12)。如果我们摒弃那些带有先入之见的批评而理性地看待形式主义文论的话,这种唯科学主义的学术理念确实是以牺牲人道主义精神或人文主义内涵为代价的,并且它还创造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崇拜——科学崇拜,就像它们对文学文本的意识形态发掘十分痛恶一样,这种新的崇拜斩断了文学研究在科学性之外的一切可能具有的品格或特质。
事实上,形式主义的科学之镜也无法完全洞悉或烛照纷繁复杂的、千差万别的、深邃幽微的文学现象或文学活动。至少,它的所谓科学性无法解决文学批评活动中两个相当关键的问题:一是批评家是否在任何时候都能找到作品的统一性;二是能否真正有效地区分文学性与非文学性。就前者而言,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形式主义的统一性假设(如文学文本的形式结构、关系集束、逻辑要素等)常常因为文学文本本身所显示出的不同成分、不同层次、不同结构之间的摩擦甚至矛盾而受到严峻的挑战,就像布鲁克斯自己所言,“诗的语言是反常的”,文学语言的内涵与形式的丰富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唯科学主义的简约模式的先天死敌。“假如可以解释存在于话语世界之中的一切实现了的简单形式并可以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的一个系统能够被建立起来,那将是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重大成功”,然而,现在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各种不同的话语形式是否可以系统地聚拢在一起”,“假如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性的,那么,整个结构主义事业就相当成问题了”。[16](P77-78)就后者来看,形式主义一直致力于从文学文本中抽取文学性,然而非文学现象或非文学文本中同样可以发现某种文学性,就像乔纳森·卡勒发现的那样,“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雅克·拉康的研究显示了诸如在精神活动意义逻辑的结构作用,而意义逻辑通常最直接地表现在诗的领域。雅克·德里达展示了隐喻在哲学语言中不可动摇的中心地位。克罗德·莱维-斯特劳斯描述了古代神话和图腾活动中从具体到整体的思维逻辑,这种逻辑类似文学题材中的对立游戏(雄与雌,地与天,栗色与金色,太阳与月亮等)”。最终的结果显示:“似乎任何文学手段、任何文学结构,都可以出现在其他语言之中,假如关于文学性质研究的目的就是区分文学与非文学,上述发现将令人沮丧。”[17](P40)
总而言之,形式主义文论特别是结构主义文论追求工具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将自然科学的观念、方法不加限制地搬用到人文科学中并想以此来规范文学批评或文学研究,是违背文学的科学研究精神的。它对科学方法或科学语言的错误模仿,以及主张自然科学是人类知识中最有价值、最权威的、最严密的和最有益的“科学崇拜”,无异于取消了人文科学研究的独特性。
二、研究方法:基于还原主义的“悬置”与“抽取”
按照美国哲学家R.卡尔纳普的说法,所谓还原主义(Reductionism,又叫还原论、化约论),实际上是一种相信复杂事物或现象的所有方面都可以通过将其还原为各个组成部分或更为低级的形态来加以理解的信念。在还原论方法的解析下,世界图景将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简单性。还原主义基于一元论哲学的本体论预设,认为“某一种类的东西能够用与它们同一的更为基本的存在物或特性类型来解释”[18](P6)。其核心理念是:“世界由个体(部分)构成”。其基本方法论手段则是化复杂为简单,通过对研究对象的不断剥离与割析,使其恢复到最原始的状态。虽然,还原作为一种思维由整体到部分、由连续到离散的操作,其“分解性”在很大程度上与人类主体思维的割离本性紧密相关,但是人类思维的逻辑点所要求的思维割离性也必然会与实在对象的内在统一性发生冲突或矛盾,因此,辩证法才要求我们充分注意研究对象的内在矛盾性,不能把本来相互联系、相互过渡的对象或对象之间的关系绝对地分割开来,同时,面对心理学科或与心理学科密切相关的学科时,要充分考虑其特殊性,不能将生动丰富的心理现象变为毫无意义的元素集合体,在分解中丢掉原有心理现象的特殊意义。而形式主义文论的还原主义倾向在某种意义上恰恰就像詹姆逊所说:“分离出内在的东西,使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同其他领域的研究对象彻底分家。”[19](P4)在俄国形式主义者那里,它是以“手法”、“支配”、“突出”、“变形”、“故事形态”、“功能”这类概念及分析方法表现出来的。在新批评派那里,切除了“意图谬见”和“感受谬见”的文学文本被看做是一个独立的、自足的实体,文学文本的审美感受被化约为由“张力”、“反讽”、“悖论”这些科学化术语所描述的、文学文本结构中各种对立因素的均衡以及结构和意义的有机统一,由此而形成的理性规范不容任意摆布,它相对独立于作品的最初来源和最后的效果。在符号学那里,建立一个研究对象(比如符号系统的特殊性及其在信息中的应用,或者不同于自然语言的意指系统的功能作用)的模拟物是其根本目的。横组合与纵聚合、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隐喻和转喻之类的区分以及其他简化了的编码,显示了他们用“科学”的符号学去网罗或编织一切知识形态的科学雄心。在结构主义者那里,神话被归约为结构中要素或单元的某种关系集束或结构逻辑(列维·斯特劳斯),鲜活的故事被归并为“词类”或“句子”(托多洛夫的《十日谈》研究),故事的结构被同步于句子的结构(格雷马斯),文学文本的意义只有通过“分割”和“排列”这样的程序才能得到敞现(罗兰·巴尔特),等等。
大致来看,形式主义文论的分解性操作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达成的。一是悬置。也就是用加“括号”的方式,将一切他们认为与艺术性、文学性、诗性无关的东西悬置起来,把文学作品最后化约为某个简单或基本的形式要素,比如俄国形式主义将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化约为“手法”;新批评将文学作品的本体化约为结构和意义的“有机统一”(布鲁克斯)或者决定作品本身价值的“决定性结构”(韦勒克);符号学将文学作品化约为约定俗成的符号及其在系统中的特定位置而产生的功能性意义,等等。就像特里·伊格尔顿所描述的那样,形式主义眼中的文学“不是伪宗教,不是心理学,也不是社会学,而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组织……文学不是传达观念的媒介,不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也不是某种超越真理的体现,它是一种物质事实,我们可以像检查一部机器一样分析它的活动”[20](P4)。从这些排他性的理论集束中,可以充分看到上述悬置特征。二是抽取。这一点在结构主义文论表现得尤为明显。罗曼·雅各布森的“功能结构”、托多洛夫的“叙事语法”、格雷马斯的“行动元”和“符号方阵”等,都是从整体性的文学艺术作品中抽取某种结构性的形式关联,以此来研究文学或概括文学的本质。通过这两种基本的方式,形式主义的文学研究被推回至语言学的研究,并且依赖于语言学的研究。
在形式主义文论的还原主义倾向中,我们看到了一种类似柏拉图的“理念”建构世界式的理想主义,“在其中,真正的文本被表征为由理想的本质投射的阴影,表征为一些本质结构(它被认为通过文本才得以可见)的各种各样的显现”[21](P298)。也就是说,这种类似X光机透视骨骼一样的还原主义在解释文学文本时通过把它化约为一种结构的外观进而否定了它的真正的复杂性、丰富性。此外,我们还将看到这种还原主义的另一个致命问题,那就是:这种化约或还原的文学语言或结构模型根本没有考虑到新的文学形式得以形成的机制或方法,它提供的至多是一种面对过往文学创造活动的抽象的文学形式类型,无法为未来的文学创作活动提供新的指南。
这种还原主义的悬置与抽取对文学这类人文科学造成的一个重大损害就是将人文科学的历史及历史性放入括弧加以阻隔而形成了鲜明的反历史主义倾向。就像伊格尔顿指出的那样,形式主义或结构主义确实“包含着社会的和历史的意义理论的萌芽”,但是总的看来,“它们却无法成长”[22](P120)。因为社会和历史的基本特征在于变化和创新,而形式主义或结构主义“则要排除变化和创新,以便孤立和突出体系”[23](P96)。对索绪尔及其继承者而言,“任何一种语言在它的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都是完整的和完备的。语言史上没有进步,只有变化。语言学研究中的目的性或秩序原则并不存在于语言的历史之中,而存在于某一具体时刻上任何一个特定语言系统的符号之间的关系和对立的逻辑关系中”[24](P27)。索绪尔语言学本来就是从共时性角度针对基于历时性研究并取得极大成功的19世纪语言学的一种反叛与挑战,因此,相比索绪尔语言学对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任意性关系的强调而言,把历史因素降到无足轻重的位置才是它对传统的更大挑战。比如作为“文本先于历史”的这一观念的坚定支持者,罗兰·巴尔特就宣称:“从原则上说,本文全体应最大限度地删除历时性因素,它应相当于一个系统的状态,一个历史的‘断层’……这样我们将宁可有一个虽然多种多样却在时间上凝聚的文本全体,而不要一个虽然紧密但时延较长的本文全体”[25](P174-175)。可见,就其对普遍结构必定存在于一个超越任何特定历史文化的集体心灵之中的这种狂热笃信而言,就像伊格尔顿所说,结构主义是惊人地反历史的,因为“结构主义要求分离出的心灵规律——平行、对立、转换及其他等等——在远离人类历史的具体差异的普遍性层面上活动。从这样一个天神般的高度俯视,所有的心灵都是十分相似的”[26](P120)。从语言学放弃对语音变化之历史的研究,到罗兰·巴尔特所认定的“神话是通过摆脱事物的历史品质才得以建构的”[27](P103),从俄国形式主义坚定不移地将作家的生平研究、心理研究、社会问题研究以及历史语境研究放逐到学术研究的边缘位置,到结构主义把现实与历史全部放入括号,形式主义者通过孤立地突出形式体系或结构而取消了历史。
这种反历史主义的观念在格雷马斯那里达到了极致。事实上,“结构语义学的另一项蕴含就是它的非历史主义”,格雷马斯甚至骄傲地宣称,“我们完全可以合乎情理地假定,我们在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中遇到的不按年代顺序组织的内容,处于一个共同的范围之内。因为这个模型对内容丝毫都不关心……我们必定认为,它是元语言性的”[28](P283-284)。换言之,他那些“从现实中提炼出非时间性的组织起来的结构现实”,无论它处于何种历史语境之中,也无论它们具有何种内容,都跟历史本身无关,结构语义学要完成的就是建构一种超越了人类历史偶然性的、清除了所有经验主义遗迹的、严密的符号模型。因此,对形式主义或结构主义者而言,那种关注某种文类的发展(比如小说),或者关注诗歌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时期到底发生了哪些转变的这种历史性研究并无多大用处。对于他们来说,“既没有要把作品与它所处理的现实联系起来的问题,也不存在将作品联系于使它产生的条件或者研究它的实际读者的问题”[29](P120),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叙述的结构。至于文学史的任务,不过就是讨论文学中各种形式要素的可变异性以及形式要素的某种功能同另一种功能的结合,而非文学作品的起源问题。比如,在俄国形式主义者那里,所谓文学史不过就是艺术形式的因袭与反抗交替出现的内在演化而已,形式之外的其他因素进入到文学史研究中反而妨碍“文学性”的呈现,雅各布森甚至嘲笑说:“过去的文学史家使我们想到了警察,为了逮捕某个人,他们抓人时一个不漏,并且把住处的东西席卷一空,而且凡是过路的人也全部带走。文学史家无所不用——社会背景,心理学,政治学,哲学。非但不是文学的学术研究,他们提供给我们的是五花八门土生土长的学科”[30](P539)。
然而,在苦心孤诣地找到那种所谓的形式结构或模型之后呢?就像伊格尔顿反过来批评的那样,“在阐明一个文学本文的潜在规则系统的特点之后,结构主义者就束手无策了,不知道下一步还该做什么”[31](P120)。形式主义很难解释同一部作品为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评价(既然它们内部有着一个不变的结构或模型)?也许对那些篇幅短小的文学形式,比如歌谣、民间传说、轶事、短篇小说或者稍长作品中的修饰性细节,形式主义或结构主义显示出了较好的解释力,但是“形式主义的方法基本上是共时的,因而不能很好地处理文学史或单部作品中的历时方面。这就是说,作为一种方法,形式主义所能发挥的作用恰恰在作为一个问题的小说开始时结束了”[32](P7)。最终的结果是:形式主义者的文学史就是一部基于形式结构的自身变异历史,用艾亨鲍姆的话来说,就是一部脱离了“文学运动发展和自然延续”、脱离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概念”、脱离了“一系列特殊现象的文学之外的一切材料”的无名无姓的历史。[33](P50)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去理解文学史,那么,即使普希金未曾诞生,《叶甫盖尼·奥涅金》也会自然写成。
三、理论之殇:高倡“主体之死”的反人文主义
虽然形式主义文论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不乏把文学作品看做人文精神的偶像以对抗20世纪的文化蛮荒主义的观念或主张,或者在理论架构上有意识地补足其“人文缺失”这致命一环(比如“穆卡洛夫斯基及布拉格学派在坚持文学史研究的形式主义基本立场的基础上,有限度地引入了文学以外的其他文化形态以及人的审美感知的结构因素”[34]),但总体来看,形式主义的反人文主义的倾向还是非常明显的。这种倾向及特点在结构主义那里表现得尤其突出并被归纳为一个著名的口号:“作者之死”。用伊格尔顿的话来说:“结构主义在括起真实客体的同时也括起了人类主体。”[35](P124)他还不客气地指出:“说结构主义在对待个别的主体方面存在问题,这是很温和的提法:实际上那个主体已被有效地取消,被简化为一个非人结构的功能。”[36](P124)换言之,笃信一种语言或某种结构能够把握一切现实的这种看法既放逐了创作主体也放逐了接受主体。这种反人文主义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关于意义的决定权问题。作为对一种彻头彻尾的创生主义(creationniste)的语言学说的继承与发扬,形式主义认定语言及其内在结构就是造物主。在他们看来,“全部语言结构是一种普遍化的支配力量”[37](P5),文学文本的意义不是由创作者或者接受者来决定,而是由那些控制个人或主体的形式结构或体系来决定的。形式主义者们反复告诉人们,并非作者的语言反映了现实,而是语言的结构产生了现实,创作者并不能控制语言的行动。在这里,主体被降格为一个死者的角色,创作者在创作时的心理活动状况,人们在实际阅读文学作品时发生的情况,以及由人这一主体所创造并接受的文学文本在整个社会关系中所起的作用等等,都被有意识地加以遗漏或否定。在罗兰·巴尔特那里,理想的文本来自于它的能指系统性、意蕴能产性以及它形如蛛网的“织体性”。最理想的写作是:“文的舞台上,没有脚灯。文之后,无主动者(作者),文之前,无被动者(读者),无主体和客体。”[38](P25-26)而理想的文学批评“必须构建的仅仅是作品的系统,而不是作品的信息”[39]。至于批评的任务,“纯粹在于形式:它并不是在被考察的作品或作家那里去发掘某种暗藏的、深刻的、秘密的、至今仍被忽视的东西”[40]。在拉康那里,主体观是以颠覆的形式展示出来的,主体被设想为语言的产物或者结果。像他的“无意识是像语言那样结构起来的”这类公式以及“语言是器官”这样的命题,实际上是宣称人只能在语言中寻找人类的本质,此外别无他途。如果说新批评家们尚把文学看做一种人文理解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了意义或人文的话,结构主义者们却把文学看做一种语言的特别应用,这些极端的结构主义者“选择了一条着眼于技巧的、科学性的文学研究途径,它可能吸引当今之世,但是终究会使得艺术脱离人性而且毁坏批评”[41](P543)。试图建立一种关于文学系统自身的结构或模式,并以此去阐释那些不仅仅在单个作品甚至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发挥作用的结构原则,这种尝试与努力当然值得珍视,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的和主观的因素不应在文学研究中占有任何位置”[42](P15)。
二是文学意义的本源问题。许多形式主义者坚定地认为,任何符号或语词的意义,只取决于它在一个聚合系统中的某种位置,或者它在一个符号组合环境中的特殊运用,但实际上意义也是人类经验的产物。形式主义者无法否定这样的事实,即“许多文学都建立在这样的企图上,即产生和经验相关的符号对等物”[43](P52),并且人类自身的经验或经历似乎也常常因为锐意创新的冲动而否定纯粹符号或结构的重复。文学作品难道不是作家呕心沥血的结晶?不是他的创作生命之子?难道没有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出作家本质的自我?读者难道没有通过文学文本同作家之间进行某种精神或心灵的沟通与交流?语言的结构性描述能够解决文学反应这个问题吗?就连罗兰·巴尔特自己也承认“文学的第二种力量即它的再现力”[44](P9),可是,这种再现力又是谁赋予的呢?难道一个好的文学文本要讲出人生的真谛或者力图要讲述事物的本来面目不是极其正常的事情吗?然而,“结构主义者却要我们相信,作者已经‘死了’,文学话语并没有讲述真实的功能”[45](P76)。就像伊格尔顿质疑的那样:“语言就是一切吗?关于劳动、性、政治权力又该怎么说呢?”[46](P123)当形式主义者用抽象的语言系统将主体踢出言语活动时,它事实上形成了难以克服的二律背反:人们对形式结构的“科学性”满怀希望,自身却被踢进了深渊。
三是产生结构的能力来自哪里?形式主义者拼命致力于客观的语码与主体对语码的使用之间所做的区分,致力于语言同现实联系的阻隔,致力于能指同指涉物之间的划界,致力于把文学的纯形式分析同价值判断割裂开来,它为文学置换了一个人类之外的新主体,这个新的主体就是形式结构或形式系统自身,它“似乎具有传统意义上的个人的一切特质(自律、自我修正、统一性等等)”[47](P124)。这样的看法在罗兰·巴尔特关于批评的真实的论述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古典批评家很天真地相信主体是“实”(plein)的,而主体与语言的关系就是内容与表达形式的关系,但凭借象征的语言,似乎使人们确立另一相反的信念:主体并不是一个个别的实体,人们可随意撤离,决定从言语活动中排除与否(根据所选择的文学“题材”),而在一个虚无的周遭,作家编制一个变化无穷的语言(纳入一个转换锁链中),藉此使不说谎(qui ne ment pas)的书写所表明的,不是主体内部的属性,而是它的虚无(absence)。语言并不是主体的谓项,具有不可表达性,或者用来表达别的事物,它就是主体本身……批评家把它的语言加在作者的语言之中,把他的象征加到作品中去,他并不为表达而去“歪曲”(déforme)客体,他并不以此作为自己的谓项。他不断把符号扯断、变化,然后再重建著作本身的符号。信息被无穷的反筛着,这并非某种“主观性”的东西,而是主体与语言的融合,因而批评和作品永远会这样宣称:我就是文学。它们齐声唱和,正好说明文学向来只是主体的虚无。[48](P68-69)
在这里,我们不否认巴尔特为了拓展批评的空间以及展示文本的多重含义而对传统文学批评追求文学文本的唯一“真意”的做法而作了严厉批评,并认为这样的批评也将有助于批评空间的有效敞开,但是在批评活动中,是谁将自己的语言“加在”作者的语言之中呢?是谁在“扯断”、“变化”、“重建”着符号呢?是语言或者由它构成的结构系统本身吗?难道不正是那个结构主义者们要放逐的主体自身吗?巴尔特给我们提供的教训之一,就是“我们无权把语言当成我们自己的语言,因为语言本身是一个系统,我们一旦进入到这个系统中,就必须放弃自己的绝大部分个性。任何人在说和写的过程中,都会变成一只塞满文字的‘硕大的空信封’。对巴尔特来说,他在这只信封上也只不过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而已”[49](P80)。
四、结语
不可否认,在引用、借鉴科学的方法进行理论架构与批评实践的过程中,形式主义文论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批评思想的“现代性转型”,因为,在古希腊到20世纪的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中,无论是强调世界的“模仿说”,或者注重读者的影响的“实用说”,还是以作者为中心的“表现说”,都没有真正触及文学作品本身,正是形式主义文论所揭示的“客观说”(立足于作品及其形式本身)促成了这一根本性的转变。巴赫金曾辩证地指出:“形式主义总的说来起过有益的作用。它把文学科学的极其重要的问题提上日程,而且提得十分尖锐,以至于现在无法回避和忽视它们。”就这一点而言,“马克思主义科学也应感谢形式主义者,感谢他们的理论能够成为严肃批判的对象,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础能在批判过程中得到阐明,变得更加坚实。”[50](P343)然而,形式主义文论之所以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不断遭到人们的批评并最终黯然衰落,同其自身理论假设的逻辑失位有着密切的关系,更同其唯科学主义的理论倾向有着直接的关联。从自身的发展过程看,形式主义的唯科学主义理念无法解决文学批评实践中以下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一是形式结构的分析与描述是否真的能帮助批评家们完全摆脱所谓意识形态的幻觉?社会生活观念、信仰和价值等是否通过这种客观化的形式分析与描述得到了完全的过滤(正如形式主义批评家所期望的)?二是所谓的艺术自律或艺术自主性能否在这种批评理念或批评实践中得到完全的呈现?批评家在实际的批评中能否真正做到完全剔除对真与善的追求而专注于对美的追求?三是脱离了意义把握的纯粹的形式结构或功能的分析对于批评论域的拓展以及批评的自由性是否构成了严重的危机?从它最终所显示出的理论效应看,它的最终衰落充分说明:当我们把科学所提供给人们的一切观念、方法、模式无条件地适用于任何一个领域和时代时,当我们秉持一种科学万能、科学至上的科学主义崇拜时,这不仅是对科学理性的滥用,还有可能使科学成为吞噬人文主义的异己力量。
[1] 罗兰·巴尔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载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2][3][4][5][6][7][9][10][27][28] 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上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8] 雷纳·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
[11][16][24][42] 罗伯特·休斯:《文学结构主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12][13][14][15] 乔纳森·卡勒:《论解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7] 乔纳森·卡勒:《文学性》,载马克·昂热诺等主编:《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18] 尼古拉斯·布宁:《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9]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语言的牢笼》,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
[20][22][26][29][31][35][36][46][47] 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21] 托尼·本内特:《形式主义与超越》,载王杰主编:《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9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23][45] 拉曼·塞尔登等:《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5] 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30][41] 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7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32]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元评论》,载王逢振主编:《詹姆逊文集》,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3] 鲍·艾亨鲍姆:《“形式方法”的理论》,载茨维坦·托多罗夫编选:《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34] 汪正龙:《穆卡洛夫斯基的美学思想——兼论布拉格学派的美学贡献》,载《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
[37][44] 罗兰·巴尔特:《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就职讲演》,载《符号学原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38] 罗兰·巴尔特:《文之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39][40] 罗兰·巴尔特:《什么是批评》,载《外国文学报道》,1987(6)。
[43] 罗伯特·司格勒斯:《符号学与文学》,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
[48] 罗兰·巴尔特:《批评与真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9] 约翰·斯特罗克:《结构主义以来》,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50] 米哈伊·巴赫金(署名梅德维杰夫):《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载《巴赫金全集》,第二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 张 静)
Criticism on the Scientism in Formalist Literary Theory
HUANG Nian-ran
(School of Liberal Arts,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79)
The modern western formalist literary theory marked with a deep imprint of scientism.The pursuit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is a prominent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cientism.“Suspension” and “extraction” based on reductionism are the important features of scientism methodology.In terms of theoretical essence, formalist literary theory has an apparent tendency of anti-humanism.A sob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endency of scientism in formalism can lead us to fully and accurately comprehend both the insights and the blind spots of formalist literary theory.
formalism; literary theory; scientism; criticize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西方文论批判研究”(11&ZH003)
黄念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黄冈师范学院特聘彩虹学者(湖北 武汉 43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