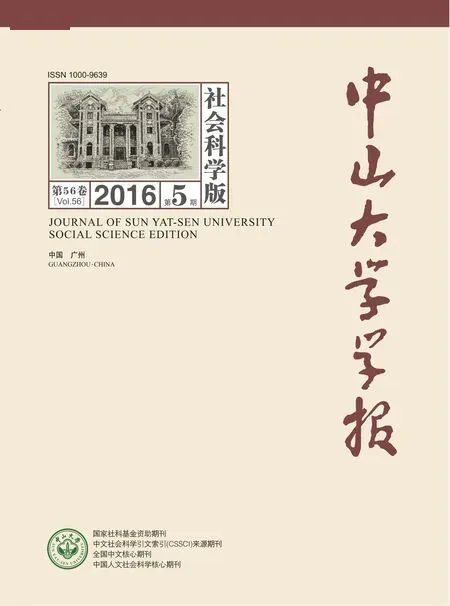论交际诗行为过程“文字单元”的性质及其意义*
赵 辉
论交际诗行为过程“文字单元”的性质及其意义*
赵辉
任何交际诗文本都产生于一个交际行为过程,是一个行为过程结构中的“文字单元”。交际诗的这一性质,将交际主体和诗歌创作主体融为一体,确定了交际诗作为实现交际目的的手段、方式的特性,规定了交际诗文本必须服务于一定性质交际行为目的的实现。因而,每一以诗词交际行为过程的行为要素,即由言说场所、行为的性质目的、行为主体与交际对象的身份以及由此而成的特定的言说关系,在极大程度上规定了交际诗文本“为什么说”、“说什么”、“怎样说”,即诗歌文本的内容、表现方式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风格特征。
交际诗; 文字单元; 主体身份; 行为目的; 限定性
“文字单元”是指一个行为过程结构中的话语言说或文字言说单元。人的行为过程,依据其性质及事件大小的不同,可分为不同的行为单元。许多一定性质的行为过程,都有着一个话语或文字言说的行为部分。交际诗产生于人们不同性质的交际行为。每一交际行为过程,都可分为一般行为和语言(文字)行为两个单元。交际诗即为整个行为过程的文字行为部分,为整个行为过程中的“文字单元”。“文字单元”和一般行为单元都是行为目的实现手段。因而,每一行为过程的“文字单元”,都受行为性质的制约,是一个“限定时空”的言说。它决定着言说所用的文体及其功能,决定着言说主体及言说对象身份,也决定着文本的要素及其逻辑结构。
一、交际诗行为过程的“文字单元”性质
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一种性质的行为,都有一个行为过程。这种行为过程一般都由几个行为单元结构组成,诸如决策、准备、实施等。而一个实施中的行为,也分为不同的步骤和单元。一般而言,我们大多将文本写作视为作品产生的全过程;但事实上,每一文字作品的产生,都有一个“前因后果”的行为过程:“前因”,即驱使主体写作的事因行为过程;“后果”,即文字言说过程。不管是行事形态还是感物形态,文字言说都是一个行为过程的一部分。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文因事而作的观念。自《毛诗序》系诗于事,以为每一诗都是因事而发之后,这一观念,便深入了文人之心。班固认为,汉乐府“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二十五史》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68页。。梁简文帝《答张缵谢示集书》曰:“至如春庭落景,转蕙承风,秋雨且晴,檐梧初下,浮云生野,明月入楼,时命亲宾,乍动严驾……是以沉吟短翰,补缀庸音,寓目写心,因事而作。”*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3010页。《旧唐书》卷168《高釴传》载李石云:“古人因事为文。”*刘昫等:《旧唐书》卷168,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388页。欧阳修《诗本义》说:“诗之作也,触事感物,文之以言。”*欧阳修:《诗本义》卷14,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90页。宋孙复《孙明复小集·答张洞书》谓诗文之作:“或则扬圣人之声烈,或则写下民之愤叹,或则陈大人之去就,或则述国家之安危,必皆临事摭实有感而作,为论,为议,为书、疏、歌、诗、赞、颂、箴、辞、铭、说之类,虽其目甚多,同归于道,皆谓之文也。”*宋孙复:《孙明复小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0册,第 174页。金王若虚《滹南诗话》卷2引《唐子西文录》云:“古之作者,初无意于造语,所谓因事陈辞。”*王若虚:《滹南诗话》,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0册,第471页。元李冶《敬斋古今黈》卷8说:“盖古人因事为文,不拘声病,而专以意为主。”*李冶:《敬斋古今黈》,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6册,第414页。清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载孙逖云:“古人饯别,如《烝民》、《韩奕》,皆因事赠言,辞不妄发。”*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载酒园诗话又编》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06页。清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3“姜夔传条”谓:“因事制辞。”*刘荣平:《赌棋山庄词话校注》,福州: 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7页。章学诚《文史通义》卷4《内篇四·繁称》云:“篇什散着,则皆因事而发,各有标题,初无不辨宗旨之患也。”同书卷4《内篇四·砭俗》又云:“文因乎事,事万变而文亦万变,事不变而文亦不变。”*沧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64、195页。可知在中国古代文人的意识中,“文”学并不是文艺理论家所认为的是主体对来自灵感的纯审美情感的抒写。文因事而作,是中国古来的共识。而所谓“缘事而发”、“ 触事感物”、“因事而发”,都表现出将文本的产生看作一个行为过程中的结构单元的观念。“文”学为言说主体因事而作,可谓贯穿古今、得到普遍认同的一种思想。
所谓“文因乎事”,是说“事”是主体创作动机产生的缘由。没有“事”,就没有诗文的产生。“文因乎事”包含两种主要形态:行事形态和感物形态。
行事形态,即言说主体为事件直接实施者或参与者。一般情况下,言说主体即为事件的行为主体,言说目的与事件行为的目的完全一致,言说直接服务于行为目的的实现。感物形态,是指言说主体感于外物而产生言说动机,进而进行创作。在中国古代,文人多认为感物而动出自人的本性,是一种极为普遍的心理活动。如刘勰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6页。而古代文人相同的遭际和情怀,亦使他们极为善感,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自然物色都有不同一般的敏感。故中国“文”学有着大量的感物形态的作品。行事形态与感物形态虽然有所区别,但不管是行事形态还是感物形态,其创作过程都是一定性质的行为过程。
交际诗是指那些用于应酬的诗歌,如赠、和、答、应制、奉和、寄、酬、饯、问、送、别、宴会、邀请、贺、悼、贻、问、挽词、谒、谢、献、投、示、上、劝勉之类的诗歌。它们都产生于一定性质的交际行为,在诗歌创作中,具有典型的行事形态行为过程中的“文字单元”性质。如李白有诗,题为《张相公出镇荆州,寻除太子詹事,余时流夜郎,行至江夏,与张公相会千里,公因太府王昔使车寄罗衣二事及五月五日赠余诗,余答以此诗》。从这首诗的标题看,这是一首被动创作的诗歌。因为张相公前寄李白罗衣,并有诗相赠。中国古代,有赠无答是无礼的行为,所以李白必须以诗答赠。故说李白作此诗并非主动。从张相公赠罗衣及诗,至李白以诗答赠,是一个你来我往的人际交往行为过程。张相公赠罗衣及诗是李白以诗作答交往行为产生的缘起,李白以诗作答是张以罗衣及诗相赠行为的结果。张相公赠李白以罗衣及诗和李白以诗相答,为一个日常生活行为过程。这一行为过程可分为两个基本的行为单元:张相公赠衣物与诗为一单元,李白答诗表示感谢为一行为单元。由于这一行为单元是以诗的写作为主体,故称之为“文字单元”。
交际诗作为一个行为过程中“文字单元”的性质,在很多这类诗歌的自序中都有反映。魏晋时,作者写诗作文,不少自作诗文之序,交代缘起。如曹植《离友诗序》:“乡人有夏侯威者,少有成人之风。余尚其为人,与之昵好。王师振旅,送余于魏邦,心有眷然,为之陨涕,乃作离友之诗。”*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7,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61页。晋潘尼《答傅咸诗》其序云:“司徒左长史傅长虞,会定九品,左长史宜得其才,屈为此职。执天下清议,宰割百国,而长虞性直而行,或有不堪。余与之亲,作诗以规焉。”*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8,第764页。从诗自序可知,潘尼作此诗是见好友傅咸担当重任而又性情梗直,故作诗规劝傅咸。而潘尼创作此诗,是傅咸先有诗赠潘尼。傅咸诗赠潘尼和潘尼诗答傅咸,是一个人际交往的行为过程。故潘尼《答傅咸诗》就是这一行为过程中的“文字单元”。词如宋冯时行《点绛唇》序云:“闲居十七年,或除蓬州。二月到官,三月罢归。同官置酒,为赋点绛唇作别。”其词曰:“十日春风,吹开一岁闲桃李。南柯惊起。归踏春风尾。世事无凭,偶尔成忧喜。歌声里。落花流水。明日人千里。”*唐圭璋编:《全宋词》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170页。如果没有词序,只看词作文本,我们会更多地将此词视为观赏之作。而从词序,我们就会看到此词作于一个送别的行为过程。朋友为饯别冯时行罢官别离蓬州,宴席之上,词人作此词答谢朋友,抒写不忍别离之意。此词不过是送别这一行为过程的作别的行为表说。
这类诗词有些没有自序,但诗题交待了诗词的本事。唐、宋以来的诗词,许多诗歌的诗题对所作行为性质和行为过程有所反映,如独孤及《夏中酬于逖、毕耀问病见赠》、元稹《沣西别乐天、博载、樊宗宪、李景信两秀才、侄谷三月三十日相饯送》。有些为将事情的缘起交代清楚,将诗题写得特别长,如李白《玩月金陵城西孙楚酒楼,达曙歌吹,日晚乘醉着紫绮裘,乌纱巾,与酒客数人棹歌秦淮,往石头访崔四侍御》,不仅交代了行为的时间、地点,而且交待了行为的起因、过程和行为状态;词如张元干《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侯寘《瑞鹤仙·为刘信叔太尉寿》等等。从诗题、词题看,这些诗词都不过是人际交往行为过程中的一个部分。独孤及《夏中酬于逖、毕耀问病见赠》是对于逖、毕耀作诗问候他病情的酬答,元稹《沣西别乐天、博载、樊宗宪、李景信两秀才、侄谷三月三十日相饯送》是其为白居易等人饯别自己而作,赵彦瑞《月中桂·送杜仲微赴阙》是他送杜仲微赴朝廷时的产物。依照些诗题、词题所提供的信息,我们都可以还原作者写作诗词的完整的行为过程,看到这些作品作为行为过程中文字单元的性质。
中国古代的众多诗词,尤其是一些词、曲,虽没有在诗题上反映创作的缘由,也没有序,仅从文本看,很容易将其视作纯粹地抒写个人情感,但其实这些作品都是因事而作。如唐张说有《五君咏》,《唐诗纪事》卷14载:
说谪岳州,常郁郁不乐。时宰以说机辨才略,互相排摈。苏颋方大用,说与瓌(颋父)善。说因为《五君咏》,致书封其诗,以贻颋。诫其使曰:“当候忌日,近暮送之。使者近暮,吊客至。多说先公僚旧。颋览诗,呜咽流涕,翌日上对,大陈说忠正謇谔,人望所属,不宜沦滞遐方。上因降玺书劳问,俄迁荆州长史。*计有功:《唐诗纪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98页。
从诗题及文本,我们看不出作诗的缘由,以为是偶有所感而作。读《唐诗纪事》,才知其为张说遇贬,投刺苏颋,请苏颋代为向皇上言说自己被宰相排挤遭受冤屈而作。《五君咏》不过是张说为自己鸣冤,谋求复官而再受重用这一行为过程中的一种手段,是这一整个行为过程中的文字单元。而这样的作品,在中国古代诗词中为数不少。
正因文缘事而作是古人的共识,古来文人对“本事”也就十分关注。“本事”虽也涉及作品的品评和敷演作品的意义,但更多是记述作品的写作缘起和写作过程。对于“本事”的关注,先秦已经开始。如《左传》可以说以《春秋》为“本事”。人们研究《尚书》和《诗经》也都将“本事”看得极为重要。《尚书》有书序,《诗经》有诗序,影响所及,直接导致了专门研究诗词本事著作的产生。如唐孟棨《本事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清叶申芗《本事词》。众多的“诗话”、“词话”,也大多有“本事”一例。如《全唐诗话》卷1“李义府”条载:“义府初遇,以李大亮、刘洎之荐,太宗召令咏乌,义府曰:日里扬朝彩……上林如许树,不借一枝栖。帝曰:与卿全树,何止一枝。”*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6页。《古今词话·词辨》上卷载《乐府纪闻》曰:“张祎侍郎爱姬早逝,犹子曙代为《浣溪沙》云:‘天上人间何处去,旧欢新梦觉来时。黄昏微雨画帘垂。’”*沈雄:《古今词话·词辨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04页。
古人的“文”学创作和批评对本事特别关注,说明古人将每一诗文文本创作看作一种特定场域中主体在外在环境作用下的特定产物,创作只不过是一个行为过程中的“文字单元”。所以,古人在“文”学批评和接受方面不仅强调“知人论世”,而且强调“论时”;不仅注重文本,而且注重文本产生的具体过程,强调通过对文本具体的行为过程的认知来把握文本的本来蕴涵。
二、“文字单元”形成的“特定场合”及构成要素
当将交际诗看成一个行为过程中的“文字单元”时,我们会发现交际诗形成的整个行为过程就是一个特定场合,是一种“限定时空言说”*参阅赵辉:《先秦文学发生研究》“余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这不仅表明每一交际的行为过程都发生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不可重复,而且也意味着每一交际行为都具有一定性质、目的及行为场所,它们决定了行为主体的身份和行为对象身份及其构成的行为关系。
(一)特定的行为性质、目的
在一定意义上说,特定行为场合的本质,是其特定的行为性质、目的。人类社会活动的每一行为,都可依据社会生活分类赋予一定的性质,故每一行为都是一定性质的行为,诸如政治、宗教、日常生活行为等等。这些活动又可分为许多细小的种类。如宗教活动又可细分为祭祀山川神灵、祭祀祖先、祈祷、招魂、讲经、打坐、作法事等等。交际行为虽然在性质上有着整体的同一性,但每一个体的具体行为性质却不尽相同。白居易《问刘十九》:“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是具有邀请性质的行为。马录事前往永阳任职时,李颀作《送马录事赴永阳(一作嘉)》勉励他努力工作,并希望“当闻佳政传”,是劝勉性质的行为。干谒性质行为的,如孟浩然《临洞庭湖赠张丞相》、王维《献始兴公》,都是请求言说对象的引荐、提拔。我们将诗歌分为赞美、祝贺、致谢、邀请、表示同情与慰问、要求与干谒等类,这些不同的功用都表现为不同的行为性质。可见,行为性质是区分不同行为的根本元素,它确定着行为的本质差异,是特定行为场合的关键要素。
行为性质是特定行为场合的本质,是指一定的行为性质都具有一定的行为目的。人的每一行为都是具有一定目的的行为。祭祀祖先,目的或为向祖先祈福,或在于培养家族情感,增强部族的凝聚力。讲经是一种宣传宗教经典的行为,目的在于宣扬宗教教义,增强教徒对宗教的信仰。在人类的活动中,往往是行为主体先具有某种目的,而后才有了某种行为;一定的目的必须通过一定性质的行为而实现,因而,行为性质也必定含有一定的目的,行为性质与行为目的融为一体,互为条件。但是,当一定的目的对应一定性质的行为,且作为传统而被确定下来后,行为的性质就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对目的有着相对的制约意义。故我们能通过一定的行为性质,分析行为的目的。行为的性质不同,其目的也就不同。交际诗是一种日常生活中的交际行为,它的性质不同于讲经,故两者的目的也就有因行为性质的不同而带来的差异。从整体上说,交际诗的目的是为着主体和对象在思想、情感等方面进行沟通,培养双方的感情。但由于具体行为性质不同,具体目的也就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如干谒的目的在于求官;询问的目的在于弄清某一方面的问题,如耿湋对佛理有疑问,作《诣顺公问道》;吊则在于向死者表示悼念,对其亲属进行慰问;同是赞美,陆云的《赠汲郡太守诗》赞美奚世都治理汲郡的功绩,而那些奉和应制之类的诗则更主要是讨好帝王。
(二)特定的主体身份
在交际过程中,行为主体都有着特定的身份。主体是一定性质行为的主体,它的意义是通过一定性质的行为表现出来的,行为之外的主体是不存在的。但必须看到,行为主体的本质是行为主体的身份。虽然不同性质的行为都是因主体发动和实施,但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多种不同性质行为的主体。在不同性质的行为中,主体都以与行为性质相适应的身份出现,以一定的身份实施行为,故主体在不同性质的行为中所具有的身份是完全不同的。换言之,即一定的行为性质规定着主体的身份,主体身份的不同,其在行为过程中的行为及作用也不同。就像一个法官,在审判的行为过程中,行使着法官这一身份的职责和权力;而当他去做某项社会调查研究时,他的身份却不一定再是法官,而是以一个调研员的身份出现在调研这一行为过程之中。这说明行为主体只能是特定性质行为的主体,行为的性质赋予行为主体特定的身份。
交际行为也是特定主体身份的交际行为。虽然在某一具体的交际行为之外,主体还有着其他众多的社会身份,如职业身份、伦理身份或其他身份,但一定行为的主体总是以特定的身份出现在某一性质的行为场合,这一身份不因主体的其他身份而随意改变,其他的所有身份在这一行为实施过程中都暂时被消解。故交际过程中,每一主体都是以一定的身份参与交际。如王维有着伦理身份:儿子、父亲;宗教身份:居士;官吏身份:太乐丞、右拾遗、给事中;此外还有画家身份等等。但他在《送元二使安西》一诗所写的送别元二出使安西这一行为过程中,其身份便只是兼具朋友身份的送行者,其他身份都被这送别的行为性质消解。而他作《献始兴公》这一行为的性质则又不同,此诗大概作于王维刚入仕任右拾遗之时,始兴公是时任中书令并封始兴县伯的张九龄,他非常欣赏王维的才华,王维则想利用这一点,干谒张九龄,以求进取,于是有了作《献始兴公》这一干谒性质的行为。显然,在这一性质的行为中,主体的身份不像送别元二出使安西这一送别行为使用的身份,而只能是干谒者的身份。而他那些奉和应制行为主体的身份大多是臣下,如《奉和圣制御春明楼临右相园亭赋乐贤诗应制》。不仅如此,即便是送别行为的性质,也有相送主体身份的差别:《送元二使安西》的相送者身份是兼有朋友身份的送行人;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一词所写相别,是作为情人与歌妓的相别;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所写相送,是幕僚对幕僚的相送;而李白《登黄山凌歊台,送族弟溧阳尉济充泛舟赴华阴》这一送别行为,则是李白以族兄的身份相送。所以说,在以诗交际的过程中,行为主体的身份是被行为的性质所限定的。
(三)特定的行为对象身份
在交际诗创作过程中,交际对象的身份是一定的。特定行为场合的关键要素是行为对象。行为对象是一定性质行为目的的实现所在;没有行为对象,也不会有这一定性质的行为。故每一性质的行为,应该都有特定的行为对象。行为对象因行为性质而异,他可以是人,是一个群体,也可以是某一个体。但是,交际过程中,行为对象的身份也是一定的。
在以人为行为对象的一定性质的行为中,行为对象也具有一定的身份。由于行为对象面对的是由特定行为场所和特定身份的行为主体而形成的特定言说场合,因而,行为对象的身份也因行为场合的特定而被设定。诸如送别场合,一方为送行人,则另一方为行人;行人因送别场合和送行人而确定行人身份。这一定性质行为中的行为对象虽然与行为主体一样,具有多种社会身份,但在这一性质的行为过程中,其他的社会身份也必然被这一性质行为的行为主体所具有的身份消解,只能以这一定性质的行为对象的身份出现在这一性质的行为过程之中。孟浩然作《临洞庭湖赠张丞相》赠张九龄,张九龄在孟浩然干谒的这一行为过程中,其身份也被干谒这一行为性质决定为朝廷高官。奉和应制,是臣子奉和皇帝所作的诗,因而奉和应制这一行为的对象自然其身份都为帝王,而不可能是朋友、老师,或者其他什么身份。陈释惠标有《赠陈宝应》诗,逯钦立引《梁书》曰:“宝应据闽中,与镏异潜有异谋,遂起兵反。沙门慧标作五言诗以送之,宝应甚悦。”“后宝应败,标从坐伏诛。”*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2622页。从所引《梁书》看,释惠标作《赠陈宝应》这一行为对象的身份应该为叛军首领。武则天作有《赠胡天师》,从诗的标题看,武则天的这一交际行为对象的身份当为道士。可见,交际行为过程中,行为对象的身份也是被限定的。
此外,某些交际行为的场所也具有一定的限定性。行为场所是行为实施的空间,在某种程度上承载着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也就是说,一定性质的行为一般都在一定的场所进行,一定的场所也都有着它被设定的固有的目的性。如神坛的设立是人们通过神坛言说取悦神灵,让神灵帮助行为主体增加生产生活资料,或去灾除祸。
有些交际行为虽有固定的场所,如宴饮行为一般在厅堂,奉和应制行为一般在王宫和行宫,饯别一般也有一定的地点。但也有许多交际行为不存在固定场所。如贺四赠王维葛巾,王维作《酬贺四赠葛巾之作》;白居易《闻李六景俭自河东令授唐邓行军司马,以诗贺之》,贺李景俭授唐邓行军司马,既可以在家,也可以在驿站或其他的地方。但是,行为场所主要是由主体的行为性质及目的决定的,有了某种性质的行为经常发生在一定的场所,场所才具有了特殊的性质。因而,当某一性质的行为发生在非特定的场所时,行为的发生场所也临时具有了固定场所的特性。如教学一般在教室进行,而当老师将课堂搬到工场时,并不会因工场非固定教室而改变这教学行为的性质,工场在这一时空也临时具有了教学场所的特性。因而,凡是这特定性质的行为发生的地方,也就自然成为特定的场所。
由此可见,交际的每一行为过程都可以说是一个特定场合。这种特定场合一旦形成,就具有暂时的完全独立性,具有极强的封闭性及限定性。这种独立性和封闭性及限定性犹如一道坚固的围墙,阻止一切特性质行为之外的行为因素的侵入。虽然特定性质的行为是由行为主体发动的,主体也能终止这一行为,但当特定性质的行为一旦实施,进入行为过程,行为性质、目的、主体和行为对象所具有的身份以及由身份而构成的行为关系,就都被严格限定了。
三、交际行为过程要素对“文字单元”的限定性
任何交际行为过程中的“文字单元”,事实上都可以视为一个文本,和其他文学文本一样,都有着几个基本要素:文本功能、言说内容、言说形式、言说风格。交际诗为一个行为过程中的“文字单元”,是行为主体的行为目的实现的主要手段和方式。因而,交际诗的文本功能、内容、形式、风格,也就必然受行为的性质目的、行为主体和行为对象的身份以及构成的行为关系,甚至是行为场所的制约,即诗歌的功能、言说内容、言说形式、言说风格,必然被行为的性质目的、行为主体和行为对象的身份所规定。
(一)行为性质目的决定“文字单元”的功能、内容
一切行为过程中的行为方式及实现方法,都是为实现行为目的服务的,无论哪种性质的行为,目的在行为过程中都占有绝对的支配地位。交际过程中,作为整个行为过程中的“文字单元”的诗歌文本,是实现行为目的的惟一手段。故作为交际行为过程中的“文字单元”的诗歌,必须毫无条件地服务于交际目的的实现,诗歌文本必须承担实现这一行为目的的功能,为目的的实现而言说。因而,任何一个交际行为过程中的诗歌文本,都承载着每一具体交际行为的一定的具体功能。《临洞庭湖赠张丞相》承载着请张九龄推荐自己出仕的功能,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承载着向情人表示依依不舍情感的功能,白居易《问刘十九》承载着邀请的功能,帝王和臣下的宴会唱和诗承载着笼络臣下感情的功能,而臣下的那些奉和应制诗则承载着臣下向帝王表示忠心的功能。
作为交际行为过程中的“文字单元”的诗歌文本,要实现这些功能,就必须依据具体的交际行为性质目的进行言说。王维《献始兴公》为干谒张九龄,讨官而作,故少不了对张九龄“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的赞美,也少不了自己希望得到提携的心愿,如“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的表述。岑参作《送王伯伦应制授正字归》,对王伯伦应制授正字表示祝贺,故内容为对王伯伦才华的述说。刘长卿《送李侍御贬郴州》为李侍御贬郴州时送别,以示对他被贬的同情,故其诗不仅表现了朋友之情,也有着“洞庭波渺渺,君去吊灵均。几路三湘水,全家万里人”悲凉境况的描述。梁锽作《赠李中华》,目的在于劝阻李中华不要入山炼丹,故诗言:“莫向嵩山去,神仙多误人。不如朝魏阙,天子重贤臣。” 晋傅咸作《赠郭泰机诗》缘于郭泰机赠傅咸诗,欲请傅咸提携,而傅咸无能为力,故作诗向郭泰机说明自己无法帮助他,故诗曰:“素丝岂不洁,寒女难为容。” 陆机因与兄弟陆云别离,作《赠弟士龙诗》以表兄弟的别离之情,故其诗主要写兄弟相思和别离的悲情。
即便一些诗歌的言说主体和言说对象的身份没有太大的差异,其言说内容也存在着不同。如那些奉和应制之作,一般都不免讨好帝王,多歌功颂德,间或提些建议。但行为性质、目的不同,其内容也必有差异。张说作《奉和圣制喜雪应制》,产生于与帝王赏雪唱和这一性质的行为,故有着“圣德与天同”的歌颂,也有着“触石云呈瑞,含花雪告丰”的描写。但他的《奉和圣制花萼楼下宴应制》,为宴饮时君臣唱和行为的产物,故在歌颂帝王“皇恩与时合”时,有着“万心翘乐宴”和“醉后传嘉惠”的言说。因而,交际诗作为交际过程中的“文字单元”,文本的功能和言说的内容,都受交际的行为性质、目的制约。
(二)行为主体与行为对象身份对言说内容、方式的规定
我们一直认为,文学创作是主体的直接言说,但这是一个认识误区。苏轼的两首词,《蝶恋花》“密州上元”和《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就很能说明这一点。这两首词都作于熙宁八年正月,第一首写于15日,第二首写于20日,写作时间仅相隔5天。在这5天中,苏轼的人生和观念都没有改变,但它们的内容和风格都有很大不同。如果说直接言说是“主体”,那么就不会有这两首词在内容和风格方面大的区别。因而,这一区别的存在,说明着文学言说主体无法直接进入具体文本的创作之中。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两首词的差别呢?
分析这两首词,首先应注意的是写作场合的不同。《蝶恋花》“密州上元”写于元宵节,词人时任密州太守,应是和属下观赏元宵灯火而作。《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则是词人怀念亡妻之作。就其目的而言,前一首词在于描述元宵情景,后者则是表示对亡妻的怀念。其次应该看到,这两个不同场合的行为主体虽然都是苏轼,但其身份却完全不同,前一首词主体是以元宵观赏者的身份出现,后一首词主体则是以丈夫对亡妻悼念者的身份在写作。作为元宵灯火的观赏者,在和属下观赏元宵灯火的场合,自然不会去抒写“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情怀;而作为一个对亡妻悼念的丈夫,自然也不可能在思念亡妻时将元宵的美景融入纸笔。可见,不是主体而是主体的行为场合所规定的主体身份决定着主体的言说。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是什么身份说什么话”。
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以一定的身份出现在一定的行为场合。不仅主体的每一行为都是一定身份的行为,而且行为的对象也以一定的身份出现在行为中。虽然行为对象是行为的被动实施者,但主体的行为一旦实施,行为主体与对象也就因双方的身份构成了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规定着行为主体以一定的伦理秩序,运用与自己和对象身份相适应的行为方式及知识系统去实现一定性质的行为目的。就如楚辞专家对物理专业的学生讲授楚辞,显然与他对先秦文学的研究生讲授楚辞在内容、表达方式与语言形式方面会大不一样。可见,在行为过程中,行为主体与行为对象因一定的身份构成的身份关系,制约着行为主体实施行为的方式与方法。行为主体不仅要以自己的身份行事,而且必须顾及行为对象的身份,否则,便很难实现行为的目的。
以诗交际,本是文人现实日常生活的一种常见形式,属于现实生活行为。交际诗既然是交际行为过程的“文字单元”,行为主体即诗歌的创作主体,而主体行为目的必须通过行为对象而得以实现,故交际诗的创作主体也必然依据双方的身份关系去言说。如陈子昂《东征答朝臣相送》,为东征时答谢朝中大臣相送这一性质的行为,他的身份为出征将帅,言说对象的身份是具有朝臣身份的送行者。故言说内容不外乎不辜负大臣的重托:“挼绳当系虏,单马岂邀功。孤剑将何托,长谣塞上风。”而在《遂州南江别乡曲故人》中,他的身份是一个旅途中人,送别者则为同乡友人,行为的性质与身份关系与《东征答朝臣相送》不一样,故其言说的也主要是朋友别离的愁情:“楚江复为客,征棹方悠悠。故人悯追送,置酒此南洲。平生亦何恨,夙昔在林丘。违此乡山别,长谣去国愁。”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是以情人的身份酬别作为歌妓的情人,言说为情人关系,故全词都是情意绵绵的情语,而《御街行圣寿》因其身份是臣下,言说对象为君主,是君臣关系的言说,故其词也就有了歌颂和祝愿的主题:“鹤书飞下,鸡竿高耸,恩霈均寰寓。”“椿龄无尽,萝图有庆,常作乾坤主。”
由于身份关系,交际诗不仅言说内容被规定,而且言说的方法也在一定的程度上被规定着。一般而言,由于《易》象思维模式的作用,中国的诗歌有着借象、借景言说情意的传统,言说方式有着趋同性。但在交际过程中,因有着比较严格的伦理等级规定,故交际诗都充分地表现着伦理身份带来的言说差异。如上对下的告诫,大多直言其意。如李隆基《赐诸州刺史以题座右》,主体的身份是帝王,故直言其意:“讲学试诵论,阡陌劝耕桑。虚誉不可饰,清知不可忘。求名迹易见,安贞德自彰。讼狱必以情,教民贵有常。恤惸且存老,抚弱复绥强。勉哉各祗命,知予眷万方。”那些奉和应制诗,言说主体多为臣下,故免不了对帝王的阿谀,使用的意象大多不离龙凤呈祥、紫气霞瑞之类。
(三)言说场所对交际诗景物描写的制约
如前所言,有些交际行为并没有一定的场所,但是,有些交际行为则必须在一定的场所进行。李峤有《秋山望月酬李骑曹》,从诗题知李峤作此诗的场所是月照下的秋山;骆宾王《于紫云观赠道士》的言说场所,从诗题看可知是紫云观。在诗词的创作中,虽然有些以想象来描写景物,但诗人感物而动,所感必然是眼前之景物,而非想象之景物。故这一类诗词,更多的是言说场所的景物描写。因而,言说场合在交际诗环境的描写上,也就有了许多的差异。许敬宗的《奉和仪鸾殿早秋应制》和《奉和过旧宅应制》,因行为场所不同,也就有了诗歌场景描写的不同:前诗奉和在仪鸾殿,故有“斜晖丽粉壁,清吹肃朱楼。高殿凝阴满,雕窗艳曲流”的描写;后诗言说的是皇帝旧居,虽也有“岐凤鸣层阁,酆雀贺雕梁”的描述,但其中“白水浮佳气”、“桂山犹总翠,蘅薄尚流芳”的景物描写,却是《奉和仪鸾殿早秋应制》所没有的。同是送别,杜审言《送和西蕃使》为京城送别,王维《送元二使安西》在渭城,故杜诗有“使出凤凰池,京师阳春晚”、“拜手明光殿,摇心上林苑”的抒写,与《送元二使安西》大不相同。
可见,交际诗作为交际性质行为过程中的“文字单元”,不仅言说的目的为交际行为的性质所确定,言说主体与言说对象的身份及其构成的言说关系,甚至于言说场所也是被规定着的。由于言说主体必须是“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是什么身份说什么话”、“对什么对象说什么话”,因而言说目的、言说主体与言说对象的身份构成的言说关系、言说场合,又规定着创作主体“为什么言说”、“言说什么”、“怎样言说”。
四、余 论
其实,不仅是交际诗,任何“文”学创作,都有一个行为过程。因而,任何一个文本,都可以视作一个行为过程中的“文字单元”。
中国“文”学中的任何文本,在其早期都是以某一行为过程中的话语单元而出现的。《尚书》中的诰、命、誓等都是如此,而作为诸如祭祀礼乐仪式中的“文字单元”更不必说,至于那些具有实用性的文体文本,如颂、史、奏、对策、祝、策、檄、启、诏、书、章表、哀悼、碑诔等,也基本都产生于具有明确实用目的的行为过程之中。它们不仅有着单一而具体的言说目的,而且有着具体的言说对象以及言说主体与言说对象身份所构成的非常具体明确的言说关系,故其限定性也更为直接而明确。那些非交际的诗词歌赋以及小说戏剧亦是如此。从现存的资料看,《春江花月夜》并非交际诗,也无明确的实用目的。或许,作者就是为着抒写游子、思妇的相思,但毫无疑问,它是作者感物而动的产物。而这“感物”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游赏行为过程,是作者在那一个春夜,看到那月、那江、那花,而想那游子、那思妇;亦或作者本身就是诗中的游子,泊舟江边,看那月下的春江,而有了写作的冲动,写了此诗,仅仅是为着自娱。但是,不管如何,从观到感,到文本写作,都是一个行为过程。无这观,便无这感,便也就无这文本的产生。尽管《春江花月夜》没有具体明确的言说对象,但这一行为,依然具有一定的性质和目的以及一定的主体言说身份和言说场所,依然是一个在一定性质行为过程中的“文字单元”。
同样,小说、戏剧之类,虽作者意图各不相同,身份因人而异,内容题材以及艺术形式各有特色,但因为它们也同是特定行为过程中的“文字单元”,是特定言说场合的产物,故其言说文体、内容、形式也都受行为的性质、行为场所、主体和言说对象的身份的限定。为什么写、写什么、怎么写以及作品风格的形成,都由行为的性质目的、主体特定的言说身份与言说对象特定的身份以及由此而构成的言说关系而决定。
【责任编辑:张慕华;责任校对:张慕华,李青果】
2015—08—23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中国文学谱系研究”(11JZD034)
赵辉,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武汉 430074)。
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5.001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解释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