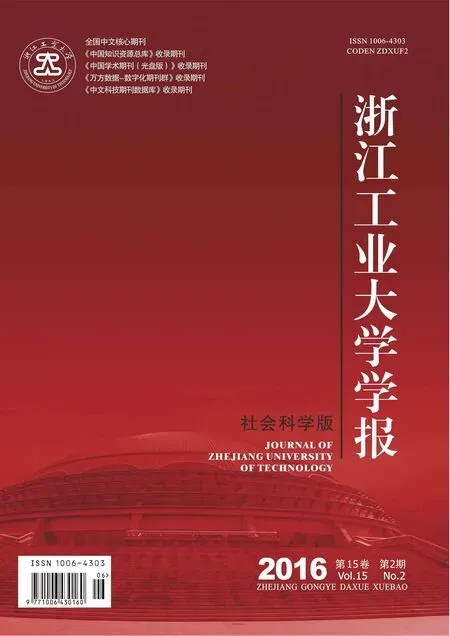论创新驱动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王志军,余 昶,郭 溦
(1.浙江工业大学 组织部,浙江 杭州 310014; 2.浙江工业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论创新驱动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王志军1,余昶1,郭溦2
(1.浙江工业大学 组织部,浙江 杭州 310014; 2.浙江工业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摘要: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要以创新驱动作为导向,更要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在观念和实践、模拟和现实、功利和能力、传统和创新等方面存在着创新驱动不足的问题。要以创新驱动的要求理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内外部机制,妥善处理好创新驱动化、功利化、创新创业草根化、监管服务化和文化社会化等问题。
关键词:创新驱动; 高校; 创新创业教育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要充分发挥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在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方面的作用。创新创业教育,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一种关于“事业心和开拓的教育”已被引入国内高等教育。多年来,国内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先后形成了“融入式”、“广谱式”、商学院、创业型大学等模式,在课程设置、师资队伍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实践中,有必要进一步结合国家战略,特别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展更深入的探索和设计,进而有效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
一、创新驱动发展和创新创业教育的关系
科技创新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源泉,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1]。虽然,马恩经典著作没有直接提出“创新”概念,但多处用了“发明”、“创造”、“革命力量”等概念论述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经济学范畴的创新(Innovation),最初由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提出,他将创新引入创业研究,认为企业家(Entrepreneur)可以通过创新——即“破坏性创造”——打破经济均衡状态,进而组合创造新产品、新工艺、新组织和新市场。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承认其继承了马克思的研究,他指出“技术变革和生产组织变革”研究“同马克思的陈述更加接近”,“只是他研究领域中的一小部分”[2]。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继承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和熊彼特等学者的创新思想,是“科教兴国战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升级版。为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2015年3月,中央《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要求破除创新障碍,激发创新活力,实现科学技术创新成果与产业创新的协同对接,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制度环境。同年,国务院又出台《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要全面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分析政策之间的逻辑衔接,可以发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创新驱动战略落地的具体表现,高校作为推动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主阵地,将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推动者。在此基础上,可以从导向、支撑和责任三个维度理解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关系。
(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导向
上世纪中后期,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对社会发展的更广泛服务成为了全球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大学社会服务功能得到空前的强化,取得了明显的经济社会效益。美国斯坦福大学所在的“硅谷”,麻省理工学院与哈佛大学支持下的“128公路”都是高等教育参与创新创业的典型,大学因此真正从知识和技能传授转向研究型和创新创业型并进。同时,创新创业教育对全体个体发展都兼具了更重大意义,从而开始以全体学生作为教育对象,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观念、企业家精神以及相应的思维能力。传统教学研究型大学向创新创业型、研究型转变,以创新创业教育提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质量,将会是国内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方向。
(二)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支撑
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现实需要。服务支持创新驱动发展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方面需要提升高校创新创业能力,提高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运用的效率;另一方面需要高校加快培养大批高素质的创新创业人才,有效推动和引领全社会的创新创业。这种支撑要实现传统的知识教育向知识创造创新过渡,从普通人力资源积累到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过渡。要通过优化教学内容和方法,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最终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诸方面全面支撑创新驱动发展。
(三)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要勇于担当创新驱动发展的责任
我国整体创新能力尚且不足,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仍然非常匮乏,这是建设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重大障碍。由于体制机制、技术发展和商业竞争等制约因素,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其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比较薄弱,在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上需要长期的积累。高等院校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责无旁贷地担当起创新创业教育的重任[3]。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加强人才培养、加快成果转化,促进社会整体创新创业能力提升,是高等教育对国家战略的积极响应。
二、高校创新创业教育面临的问题
国内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始于上世纪末,通过借鉴学习,逐渐形成了商学院、创业型大学等多种创新创业教育模式。大学毕业生参与创新创业的数量呈现逐年递增的现象,“2014届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比例为2.9%,比2013届(2.3%)高0.6个百分点,比2012届(2.0%)高0.9个百分点”[4]。同时,大学生创新创业以其自身的专业技术优势服务经济社会各方面,在生态农业、现代金融、医疗卫、互联网、交通等多个领域都有成功的案例,逐步从传统的商业贸易转向创新驱动。当然,数量(发达国家大学生创业比例约20%~30%)和质量(成功创业对行业和市场的影响)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不小的差距。2014年,根据YBC(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的统计,我国青年首次创业的成功率不足10%(《南方日报》2010年3%、《新民晚报》2014年10%、《新浪国际在线》2015年5%)低于国际平均水平20%。姑且不论数据的精准程度,单说国内外巨大的差距,都值得进一步探究其中存在的问题。关于具体实践或理论问题学界已有较多的讨论,本文坚持从现象到理论,以创新驱动的视角诠释问题,希望为理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内外部机制提供理论基础。
(一)观念和实践之间的不统一
2002年,教育部确定清华大学等9所大学为创业教育试点院校,期望通过试点探索高校创业教育有效办法。迄今为止,形成了两种趋势,一是通过课程拓展学习或科技竞赛创新训练实现创新教育,侧重创新人才培养,例如北京大学元培实验班等;二是通过创业实践实现创业教育,侧重创业人才培养,例如华中科技大学的法人实体创业教育等。试点工作取得的成果对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但也存在问题,尤其是创新创业教育观念和实践上的割裂。这并不是试点工作本身的问题,而是自上而下推动贯彻过程中的问题。试点工作的要求落实到高校内部时,各个部门关注和侧重点并不相同。团委、学生处等学生事务管理部门把创新创业教育作为一项实践活动,侧重的是竞赛成绩、风险投资等活动效果;科研处、教务处把创新创业教育作为一项教学科研任务,侧重的是专利论文数量、教学改革成果和科研到款等任务业绩。行政推动强调执行,效果如何取决于观念和目标的一以贯之。对于大学生而言,创新和创业是一个有机整体,缺乏整体论的认识,则会造成执行的偏差。每个推动者的视角不同,从创新或创业单方面切入,会造成观念和实践的不统一。
(二)模拟和现实之间的不统一
1997年,清华大学发起创业计划大赛,之后由国家教委推广至全国,现已历时18年之久。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下,创业计划大赛在国内高校全面开花,形成了大学生创新创业的高潮。经过多年的努力,参赛项目中产生了许多学生公司,有的已成为上市公司,有的获得较大规模的风险投资,这对于宣传鼓动、营造氛围作用明显,实现了创新创业量的覆盖和活跃度的提高。然而,如此庞大的创业计划竞赛与我国青年创业成功率不足10%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显然表明创新创业的质量并不高。学生将创业竞赛作为训练创新能力的练兵场本无可厚非,但是拼口才、赛聪明的竞赛难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胜利的。究其原因在于,官方组织的竞赛是已然成为了高校评价的指挥棒,特别是对地方大学影响较大,形成以竞赛成绩为导向,高校科研资源和科研成果全力支撑竞赛的情况,甚至出现参赛学生直接以教师科研项目参赛。这种做法仅仅调动了高校的积极性,却没有调动学生参与的主动性。创业竞赛跨越到现实创业,关键要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动力。学生的兴趣爱好不与市场需求对接,竞赛仍然还是象牙塔里的游戏,模拟和现实之间仍然不会统一。
(三)功利和能力之间的不统一
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创新创业的能力素质,这已经在高等教育界取得了普遍共识。在实际教育中,学生的创新创业活动却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大学生创新创业中的功利有两类,极易混淆。第一类功利是中文语境的功利,指的是追求利益、无视道义。学生受创业成功典型的鼓动和金钱荣誉的吸引,高校则是紧盯就业考核和社会评价,以上市融资成功和考核评价优秀为标准。这种功利往往会让高校和学生走入创业误区,忘记创新创业教育的初衷。第二类功利是西文语境的功利(Utilitarian),往往指的是对个体人的有用性。现在流行的产品体验就是对这种有用性的具体描述,充分认识这种功利是决定创新创业教育成功与否的关键。大学生以兴趣爱好开展研究探索同创业成功、资本青睐是两回事,需要在中间设计明确的限制和边界,科研和产业之间也并不是一定要统一才会有效率,许多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科学成就并不是为了产业化,而是出于单纯的兴趣和爱好。不得不承认,知识学术资本化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但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领域,仍然要引导学生在认识市场真实需求和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之间实现统一。
(四)传统和创新之间的不统一
课程、资金、场地、配套服务等软硬件的升级换代,被认为是改善创新创业环境、推动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手段。然而,有学者就指出,改善创新创业环境是否能够支撑传统教育向创新创业教育过渡,或者说仅靠创新创业环境与传统教育的简单复合是否能够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仍然值得商榷。更多的研究表明,填鸭式、教学型的传统教育主要以知识传授为主,在匹配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后,知识创新的状况不会有明显改变,这也是当前创业成功率低的重要原因。从知识传授到知识创新,是一个批判反思过程。创新是支持创业成功的重要因素,创新不足让大学生最终只能成为普通的市场参与者。与此同时,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对象不是传统认为的学生群体,而应该是学校全体师生员工,教师教学科研和学生创新创业不是分离的,而是统一的,应当提倡的是全校性的创新创业教育。所以,深化教育改革,提倡启发式、开放式、全体参与的创新创业教育,才是传统教育向创新创业教育过渡的关键。
三、创新驱动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内外部机制研究
总体而言,观念和实践、模拟和现实、功利和能力、传统和创新等方面的不统一,根源在于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内外部机制是否以创新为驱动。要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总的原则应以创新驱动作为衡量标准,一方面要注重内部观念操作的协调高效,另一方面要推动创新创业教育对经济社会的促进,使内外和谐共振,达到效率的最大化。
(一)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内部机制
国内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多采用行政推动的方式,有的是科研管理部门为主导,有的是教务管理部门主导,有的是学生事务管理部门主导,协同不足,程序复杂,号召力不够。而在国外,推动创新创业教育往往和技术转移、专利推广等技术创新相关。欧洲各国不少大学都建立了技术转移办公室,如牛津大学全资拥有Isis科技创新公司,负责管理牛津大学的技术转移和学术咨询,并为全球客户提供技术转移咨询服务;柏林工业大学的技术转让部负责管理合作项目。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于2000年成立了创新与技术转移办公室,日本早稻田大学于1997年成立外联推进室,东京大学于1998年成立尖端科学技术孵化中心。
重点考察美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内部体制,我们发现,美国的创新创业教育的成功,与其内部的技术转让体制、机构密切相关。早期,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麻省理工、斯坦福大学等高校已成立了技术专业专门机构。1980年颁布拜杜法案(Bayh-Dole Act)后,美国高校形成了三种运行模式:威斯康星校友研究基金会(WARF)模式,是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学校附属机构;麻省理工学院第三方模式,学校与本校教授Cottrell的独立研究公司(RC)签署协议,由RC掌管学校的专利申请和许可事宜;斯坦福大学的OTL(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模式,学校亲自管理专利事务[5]。另有类似机构称为TTO(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是目前美国大学采取较多的方式。全美已有3300家以上OTL或TTO技术转移机构,据Biotechnology Industry Association研究,1996至2007年间因高校技术转化实现了1870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创造了27.9万个工作岗位(Smith et al.2010;Roessner et al.2009)[6]。
国内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要从行政推动转向创新驱动,必须探索成熟的技术转移制度。2015年《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建立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技术转移机制,特别是要实现研究室到技术转化的服务系统。这是理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内部关系的关键。大学高层管理者要全力支持创新创业教育,成立专门开展创业教育的机构,建立跨学科研究中心,实现多部门参与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行为、技能和态度,帮助学生了解创业者在创业组织中的生活世界。一般来说,研究者提交技术成果,然后由技术转移机构(有时也包括投资者)评估该成果的潜在商业价值是否值得申请专利,让功利的事情交给功利的组织去处理。如果成果通过评估并获得专利,技术转移机构会尝试推销该技术,寻找企业签订技术转让协议,高校可从中获得专利版权报酬或是初创企业的股权作为收益。当技术真正商品化后,高校可继续保持与企业的合作,以便维持对技术的持有并进行投入,亦或如果合作公司是初创企业,则学校职员会作为技术顾问给予建议[7]。在技术转移的过程中,高校、研究者和其所在院系可以按照一定比例对技术成果进行分配。
(二)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外部机制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外部机制是国内创新创业教育研究的热门选题,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注重对高校与企业、高校与社会、高校与政府等关系的梳理和建构,特别是在高校创新创业的税收优惠、专利引导、融资风投等方面有较为深入的本土化研究。最流行的理论是亨利·埃兹科维茨和伯顿·克拉克的创业型大学(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模型,这是对大学在政府、企业之间的重新定位,也是对大学职能的重新审视。普遍认为创业型大学要构建大学——企业——政府三螺旋关系,使创业成为大学在知识传播、创新之外衍生出的新职能。国内有许多大学都提出了“创业型大学”的办学目标,但大多数高校的科研水平难以达到全校性创新创业教育的要求,发展困难较大。
我们认为,三螺旋是一个分析性的规范概念,它描述了学术界、政府、产业三者关系及各自角色转变的机制。完全由政府或企业主导的传统三螺旋仅能提供有限的理念和行动,在这种环境下,政府可能没有听取其它各方的意见而采纳一些方案,企业决策可能仅盯着眼前的市场利润而进行市场行为。尽管大的目标可以实现,但不是最有活力、最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三螺旋模式,因为理念只来源于主导角色:政府或企业。但是,由高校主导的三螺旋,可靠性也并不高。上世纪,国内的企业缺少科学研究的力量,高校在教学科研之外不得不分出一部分力量帮助企业进行研发,这也是高校“产学研”研究的起点,高校的科研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主导作用。但是现在,一方面,企业产品的导向来源于市场需要和客户体验,技术并不是决定性因素,许多大型公司都放弃自主建立的实验室,反而加强了产品的运营,以求更贴合市场;另一方面,国内企业聚集了大量的优秀技术人才,吸收来自世界的先进经验,企业已不需要高校简单的技术支持。
“大学——企业——政府”三螺旋结构中,创新创业从相对简单的一系列由研究扩展到市场和由市场延伸到研究的产业内双向线性过程,转变为了一个非线性过程,形成了大学、企业、政府三个机构领域之间的新结构。也就是说,创新创业并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在“大学——企业——政府”的交互作用过程中产生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要摆脱单一的市场或行政束缚,高校要在促进创新和产业政策体制中,作为有影响力的行动者和平等的合伙人出现。所以,形成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的“大学——企业——政府”的创新创业机制是提升社会整体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高校在三螺旋中的角色,应当回归到基础研究以及长线的应用研究,走在企业的前面去探索技术、积累技术,走在政府的前面去把握产业发展趋势,为市场和企业储备技术和人才,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四、创新驱动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发展趋势前瞻
创新驱动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需要通过培养大批具有创新创业能力精神的人才、营造引领全社会的创新创业文化等方式,全面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这是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发展的目标任务,同时也是未来创新创业教育发展的趋势。
创新驱动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研究和实践,经历了较多的迷茫,曾经针对大学生摆地摊、开网店等商业贸易活动有过激烈的争论。这反映了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缺乏宏观的设计和研究,缺少对其核心本质的考虑。提倡创新驱动的创新创业教育,并不是强调大学生创业一定要有高科技含量、大资金支撑,其目的是强调创新。也就是说,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要鼓励观念创新、技术创新、工艺创新、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拒绝简单地模仿和重复前人的工作。鼓励更多高质量、高水平的以创新驱动的创业活动,鼓励不同层次的创新创业活动,最终以创新激发全社会的生机活力。
效用化。任何讨论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文章似乎都无法避开功利性的问题,依前文所述需要正确认识中西功利观念,本文提倡的是效用化。创新创业教育要摒弃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功利、逐利观念,特别是过于注重眼前利益,缺少基于兴趣的探索研究。要鼓励效用性的功利,更多地关注实际、关注个体人的发展需要。因此,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需要设置必要的限制,一方面让商业的事情交给专门的组织去处理,提高专门化程度,引导学生从一夜暴富的虚幻中回归到脚踏实地的学习研究;另一方面鼓励学生将对兴趣爱好的探索转化为现实效果和有用性,特别是要宽容那些短期可能看不到成效或成果的探索研究。
草根化。如何正确看待精英和草根的问题,既是一个教育理论问题,又是一个教育实践问题。在理论讨论中,以考试竞赛成绩将学生分为三六九等是有失偏颇的观点,早已被教育界所认可。但是在教育实践上,受制于高等教育大众化、教育资源稀缺性等因素,对学生考试竞赛成绩关注较多,把考试优异、竞赛获奖的学生作为精英对待,忽视默默努力、履败履战的学生,这也是现实中未能避免的问题。教育是要激发学生的兴趣,调动学生探索创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比尔·盖茨、乔布斯等一大批草根创业者的成功案例告诉我们,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要鼓励学生自主探索和研究式学习,更加重视草根式、原创性的努力。
管理工作服务化。推动高校创新创业单靠行政命令效果并不好,要从管理转向服务,实现管理工作服务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重点是创新创业服务体系的建设,而不是管理控制创新创业活动,不能用管理的思路取代服务的理念。我们已经习惯以科研数据、学术论文和专利数量的统计工作代替创新创业的具体实践,也习惯了教学科研的评价制度,但这样产生的教学科研成果永远只是一个量的积累,这反映在近年来我国专利论文数量已经名列世界前位,但科技竞争力始终还在中下游水平徘徊,尚没有质的飞跃。这是一种工作的惰性和惯性,短时间难以改变。创新创业的服务,是要站在政府、企业和高校之上,以更高远的视野和更宏观的视角来引导教师和学生的创新创业工作,服务全社会的创新创业活动。
创业文化社会化。“观念的创新、科技的创新、体制的创新,无不回归于文化的创新,这不仅是逻辑的必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实现体制和科技上的创新,必须把建立创新创业文化当作一个重要的前提”[8],创新驱动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已经不仅是大学校园内部的教育,而是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社会活动,需要政府、企业和高校共同推动。所以,其文化包含了大学求是求真的文化,大众草根创业文化、精英创业文化等多种社会文化,最终融合而成将是一种创新创业的文化自觉。培育创新创业精神、激发创新创业潜能,形成创新创业的文化基因,从而引领全社会的创新创业浪潮。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97.
[2]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68.
[3] 马廷奇.创新型国家建设与大学科技政策创新[J].教育与现代,2008(1):18-22.
[4] 麦可思研究院.2015年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报告[N].光明日报,2015-07-17(5).
[5] 雷朝滋,黄应刚.中外大学技术转移比较[J].研究与发展管理,2003(5): 45-52.
[6] ROESSNER D,BOND J,OKUBO S,et al.“The economic impact of licensed commercialized inventions originating in university research”[J]. Research Policy,2013(1):23-34.
[7] SIEGEL D S,WALDMAN D A, ATWATER L E,et al. “Toward a model of the effective transfer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from academicians to practitioners:qualitative evidence from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university technologies”[J]. Journal of Engineering & Technology Management,2004(21):115-142.
[8] 徐冠华.大力构建创新文化环境[J].世界科学,2001(6):10-13.
(责任编辑:王惠芳)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driven by innovation
WANG Zhijun1,YU Chang1,GUO Wei2
(1.Th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14, China;2.College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should be innovation-orientated and support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novation-driven strategy.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China is facing in-coordination problems between the ideas and practice, simulation and reality, utility and ability,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due to the imperfect internal and external system mechanism in universities. Policy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driven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cluding how to handle appropriately the problems of utilitarian tendency, grass-roots tendency, service-oriented supervision, and socialization of culture.
Keywords:innovation-driven; universitie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收稿日期:2016-02-29
基金项目:2014年浙江省软科学研究项目 (2014C35050)
作者简介:王志军(1978—),男,浙江黄岩人,副教授,硕士,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研究;余昶(1983—),男,浙江淳安人,讲师,硕士,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研究: 郭溦(1987—),女,浙江龙游人,硕士,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4303(2016)02-020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