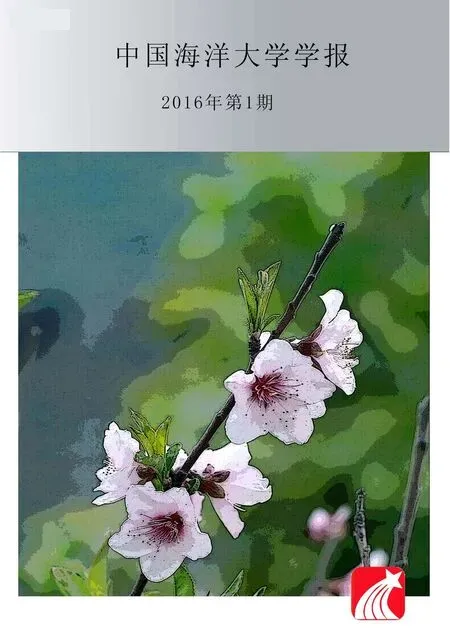异域想象与文人观念:论晚明清初通俗小说中胡僧形象的色情化*
薛英杰
(香港大学 中文学院,中国 香港)
异域想象与文人观念:论晚明清初通俗小说中胡僧形象的色情化*
薛英杰
(香港大学 中文学院,中国 香港)
摘要:作为一个色情符号,晚明清初通俗小说中被色情化的胡僧与黑面、春药、房中术有着固定的联想关系。胡僧的身份定位非常模糊,其体貌描写和情节模式高度类型化。胡僧色情描写所涉及的密教及道教内容经常被混淆为房中秘戏。小说对胡僧色情形象的符号化建构,与藏传密教的内传并无直接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作文人异域想象的结果。胡僧色情形象所折射出来的是文人对外来宗教人士的警惕和被儒家文化所压抑的欲望。
关键词:晚明清初;通俗小说;胡僧;异域想象;文人观念
胡僧形象的色情化,是晚明清初通俗小说中新的写作趋势。它既指胡僧直接参与性事,也指胡僧通过传播春药、房中术等手段间接推动其他小说人物的性行为。胡僧色情形象主要出现在《金瓶梅》《英烈传》《僧尼孽海》《西湖二集》《禅真后史》等晚明小说中。清初小说《续金瓶梅》《水浒后传》《隋唐演义》也包含关于胡僧的色情描写,并且对晚明的思想观念有所承续。为了保证研究的连续性,本文选择晚明清初的时间界限进行讨论。在上述小说中,除了《僧尼孽海》基本由浅近的文言文写成,其他作品都是白话小说。由于它们的语言都能够为一般民众所接受,所以本文统称其为通俗小说。以晚明清初通俗小说为主要对象,本文尝试解答以下问题:小说中胡僧的色情形象具有哪些特点?密教*在小说研究中,学者较多使用密宗的概念。严耀中指出,中国佛教中的“宗”有广狭之分,广义的宗代表佛教的一种理论或一种信奉方式,狭义的宗往往具有一个连续不断的清楚的传受体系。中国密教的流传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属于其他学或其他宗的僧人进行。从广义来看,密教可以称之为密宗。参见严耀中《汉传密教》(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页10-11。本文沿用该书的用法,使用“密教”一词。、道教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胡僧色情形象的建构?胡僧形象的色情化反映了文人怎样的文化观念?
一、胡僧色情形象的模糊性与符号化
晚明清初通俗小说中胡僧的色情形象呈现很高的模糊性。小说很少明确提及胡僧的具体来历。有的小说因借用了历史故事及人物,才会对其来历进行明确说明。例如,以《元史·哈麻传》为蓝本的《僧尼孽海·西天僧西番僧》和提及元代藏传佛教僧人杨琏真迦的《西湖二集·会稽道中义士》。就其他小说看,“西天竺”的出现频率稍多。《金瓶梅》第四十九回“西门庆迎请宋巡按,永福寺饯行遇胡僧”详细解释了胡僧来自“西域天竺国密松林齐腰峰寒庭寺”。[1](P435)《水浒后传》中的番僧萨头陀,自称是“西天竺国达摩祖师第三十八代嗣孙”。[2](P952)但《金瓶梅》和《水浒后传》都没有对西天竺多加叙述。特别是《金瓶梅》关于胡僧来历的描述,被学界公认为性器官的隐喻,并不具有实际的地域意义。西天竺是佛教的发源地。小说作者将胡僧定位为来自“西天竺”,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这一地名与佛教之间的联系及其在中国文化中的陌生感,来突出胡僧的外来佛教背景。
除了缺乏关于胡僧来历的明确介绍之外,小说中胡僧的称谓也非常宽泛。小说中关于被色情化的胡僧的称谓,包括胡僧、番僧、西番僧、西天僧、西域僧、西僧。西番僧指西藏地区的僧人,西天僧指南亚的印度、尼泊尔等地僧人。西域僧、番僧和西僧则是较为宽泛的概念,所涵盖的范围更大,可以与西番僧、西天僧互换使用。特别是番僧、西僧的概念,有时也可以指称来自欧洲的传教士。“‘胡’在西汉时期是一个包含数国的民族的称谓,但在东汉渐渐偏离原意,表示范围变得含混。”[3](P75)因此,东汉之后所云“胡僧”应是对外来僧人的泛称,其用法较番僧、西僧更为随意。《元史》《明史》等正史很少使用胡僧一语。在晚明清初通俗小说中,以意义指向较为模糊的胡僧、番僧的使用频率为最高。仅从称谓来看,小说中的胡僧也没有明确的从属教派和地域来源。
虽然晚明清初通俗小说没有对胡僧的身份给予明确的定义,但这种模糊性没有留给读者太多的想象余地。关于胡僧的色情想象具有几种固定的模式,共同将胡僧建构为一个符号。色情想象的模式之一体现在胡僧体貌特征的描写上。以下所列举小说中的胡僧,都与色情之事有关。
《金瓶梅》“胡僧”:“见一个和尚,形骨古怪,相貌搊搜。生的豹头凹眼,色若紫肝。戴了鸡蜡箍儿,穿一领肉红直裰。颏下髭须乱拃,头上有一溜光檐。就是个形容古怪真罗汉,未除火性独眼龙。在禅床上,旋定过去了。垂着头,把脖子缩到腔子里,鼻口中流下玉箸来。”[1](P434-435)
《僧尼孽海·沙门昙献》“西僧昙献”:“生得粗眉毛,大眼睛,狮子鼻,四字口,身长七尺有奇,矫健迥异常品。”[4](P198)
《僧尼孽海·募缘僧》“胡僧”:“偶有胡僧,长干伟躯,登门募化。”[4](P266)
《续金瓶梅》“大喇嘛和尚”:“生得黑面钩鼻,一嘴连腮拳胡的毛查。”[5](P278)
《水浒后传》“番僧萨头陀”:“身长八尺,面如锅底,头上青螺结顶,两个獠牙露出嘴外,剃了黄须,如刺猬的矗起,耳上挂一对金环,遍身黑毛,胸前盖胆的更长数寸。”[2](P927)
晚明清初通俗小说关于胡僧色情形象的体貌描写比较相似,多以长躯、黑面、粗眉、大眼为主要特征。孙逊《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准确地指出,“豹头凹眼”、“色若紫肝”、“长干伟躯”等词是色情小说描绘男性生殖器的常用语汇,并且胡僧形象在部分小说中已虚化为性的符号。[6](P191)的确,被色情化的胡僧形象往往身躯高大,很是矫健,与他们超强的性能力相呼应。不过,该书把明清小说中的胡僧体貌概括为“面黑、眼碧、双耳悬环”的中亚人种。[6](P189)该说法还有待商榷。唐人诗歌所描绘的胡僧形象,以“碧眼”的特征最为常见。[7](P80)晚明清初通俗小说对胡僧体貌的刻画,也继承了前代文学中胡僧多为碧眼的思维定式。如《初刻拍案惊奇·金光洞主谈旧迹玉虚尊者悟前身》就是用“碧眼横波”[8](P368)一语来形容得道胡僧。《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的胡僧金碧峰因其眼睛的颜色而被人称之“碧眼禅师”。[9](P51)应该注意的是,这些碧眼胡僧都颇有道行,受人敬重,与色情之事毫不相关。但晚明清初通俗小说中胡僧的色情形象并没有“碧眼”的特征。上述材料中的“凹眼”“大眼睛”等描写关注的也是眼睛的大小形状,而非颜色。特别是粗眉与大眼相结合,很容易带给人一种凶恶恐怖之感。可见,小说作者在将胡僧形象色情化的时候,有意回避了碧眼胡僧的形象,择取了更易激起人们恐惧之感的黑面僧人形象。特别是被冠以“番僧”、“西番僧”或“喇嘛”之称的僧人,其黑面的特点则更加突出。长躯、黑面、粗眉、大眼等外貌描写词汇,在不同小说中反复出现,将胡僧建构为一个在体貌上高度相似的符号。
“胡僧药”是晚明清初通俗小说中胡僧色情想象的另一种模式。在明人观念中,胡僧与神奇药物之间存在着固定的联想关系。《隋唐演义》中的番僧送给单雄信夫妇催产调经的丸药,帮助二人产下一女。《梼杌闲评》中的番僧送给魏进忠三种药,曰:“这一枝药可治虚怯之症,不论男女五劳七伤虚损劳症,皆可治之。这一枝膏子药,专治妇女七情六欲、忧愁郁结,并尼僧、寡妇独阴无阳之症。这一枝草药,治一切跌打损伤并毒蛇虎狼咬伤,酒调一服即效。”[10](P228)《梼杌闲评》没有直呼这位僧人为番僧,但其外貌描写可以印证他是一位西番僧。“山里老僧真异样,身长腹大精神壮。面如锅底貌狰狞,耳挂铜环光晃亮。体裁柿叶作禅衣,手挽香藤为拄杖。好如六祖下天堂,喇玛独现西番像。”[10](P222)虽然这位番僧与色情之事无关,但他也具备长身、黑面的体貌特征,并且所送药物在魏进忠平步青云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关于胡僧的色情描写中,胡僧带到内地的“胡僧药”则为春药。通常的写作模式是遇到胡僧、请胡僧用斋、胡僧奉送春药、服药的人陷入危机。《金瓶梅》中的胡僧送给西门庆春药,直接推动了西门庆的死亡。《水浒后传》中的萨头陀送给丞相共涛春药,助长了他的淫欲和野心,也间接导致了他的灭亡。暹罗国国王则因为盲目相信“胡僧药”的神效,以致误食萨头陀献上的毒药。《隋唐演义》中送给单氏夫妇药物的番僧,准备前往西京向太子进奉耍药,曰:“那太子是个好顽不耐静的人,所以咱这里修合几颗耍药,要去进奉他受用。”[11](P81)这里所云“耍药”,指的应该是春药。秦叔宝得知番僧的意图后,叹息国家面临着危机。
关于“胡僧药”想象的细节也有雷同之处。胡僧所用斋饭都是荤菜,而且食量惊人,以此显示其与中土僧人之间的不同。关于春药的细节描写也常与道教相联系。《金瓶梅》曰:“我有一枝药,乃老君炼就,王母传方……形如鸡卵,色似鹅黄。三次老君炮炼,王母亲手传方。”[1](P437)《水浒后传》曰:“采先天之精气,炼日月之光华,水火炉中升了九转,服下之时,一点纯阳从涌泉穴起,直透泥丸宫,填满脑髓,巩固元神,能使玉女消魂,金童返本。”[2](P930-931)《金瓶梅》中的胡僧和《水浒后传》中的萨头陀都利用“老君”“王母”“元神”“玉女”等道教用语,来吹捧自己春药的功效。并且,胡僧盛放丹药的容器大都是葫芦。“于是向褡裢内取出葫芦儿,倾出百十丸……又搬向那一个葫芦儿,捏取了二钱一块粉红膏儿。”[1](P437)“身边取个小葫芦,倾出一丸药。”[2](P930)“向袖中摸出一个葫芦,倾出豌豆大一粒药来。”[11](P81)可见,不仅葫芦是“胡僧药”相关描写中的重要道具,其关于胡僧取药手法的描写也很相似。综合小说关于“胡僧药”的描写来看,虽然只有寥寥数笔,但其情节高度模式化,文本之间有着若隐若现的联系。这说明文人关于“胡僧药”已经形成了相对一致的观念,即胡僧被认为是神奇春药的拥有者,能够提高汉人的性能力,同时春药本身所具有的危险性也威胁着服药者的安全。
从模糊性和符号化的角度来看,晚明清初通俗小说对胡僧色情形象的塑造似乎有些矛盾。胡僧没有明确的地域来源和宗教归属,其身份定位极为模糊。本来胡僧身份的模糊性可以让叙事更加多元化,但小说所建构的胡僧色情形象非常固定,所使用的写作手法很一致,并未让胡僧的叙事功能发生多样性的转变。小说在模糊胡僧身份定位的同时,也删除了胡僧群体内部的多样性。这说明在小说作者的观念中,没有必要追究胡僧的真正身份,而附属于胡僧的色情描写也理所当然。依据“胡僧多为黑面”“胡僧多有春药”等固定逻辑,小说建构了胡僧与色情之间稳定的表述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一种观念的产物。所以,关于胡僧的模糊化处理也可以看作该形象符号化的一部分。一方面,“胡”“番”“西”等意义指向较为含混的词语,将胡僧群体统一归纳为一个符号,即来自异域的和尚。另一方面,缺乏身份定位的胡僧,更加能够突出自身的神秘性,为突出其高强性能力的符号化描写做铺垫。
二、胡僧色情描写中的密教与道教
除了在身份定位、体貌特征、情节模式方面具有鲜明的写作特点,晚明清初通俗小说中胡僧的色情描写还涉及了密教、道教的相关内容。胡僧色情描写的典型手法之一是以史料为依托,并加入带有宗教色彩的发挥。《僧尼孽海》中的《西天僧西番僧》一文,讲述了元顺帝宠臣向顺帝推荐西天僧西番僧、以助其淫乐的故事。作品以《元史·哈麻传》为基本框架,辅之以房中术的内容,并加上个人的夸张,正是此类描写的代表。《西天僧西番僧》曰:
元顺帝时,哈麻常阴进西天僧,以运气术媚帝,帝习为之,号演揲儿法。华言大喜乐也。哈麻之妹婿集贤学士秃鲁帖木儿,性奸狡,有宠于帝,言听计从。与老的沙、八郎、答剌乌、吉的、波迪哇儿祃等十人,俱号倚纳。亦荐西番僧伽璘真于帝。伽璘真善秘密法,谓帝曰:“陛下虽尊居九重,富有四海,其不过保有现世而已,人生能几何,当受此秘密大喜乐禅定。”帝又习之,其法亦名双修法,曰演揲儿,秘密法,皆房中术也。[4](P231)
该段描写与《元史·哈麻传》的内容基本一致。文中所谓“演揲儿法”“大喜乐”“双修法”,实际上是藏传密教的无上瑜伽部分。严耀中《汉传密教》详细辨析了中国的密教源流。印度密教传入中国后分为两大流。一支在汉末三国时期传入中国内地,与汉文化相融,形成了汉传密教。另一支传入西藏,与西藏原有宗教相融合,被称之为藏传密教,在元代大量传入内地。印度密教中以男女双修为表象之一的无上瑜伽部分,因与内地的儒家观念相悖,在汉传密教中变得较为隐晦,而是较多地保存在藏传密教中。“藏传密教里的无上瑜伽部分认为肉体本身就是反映出森罗万象的曼陀罗,男女双修就是般若空性的智慧和大悲利他的方便相结合。”[12](P232)“演揲儿法”是藏传密教的一种修行方法,即“观想、控制印度医学所谓的脉,当风息入于中脉之际,与具备资格的助伴入定,从而证悟‘与生俱有’的大悲智慧”[13](P228)。“大喜乐”是“在此禅定境界中内生之乐为‘无漏’之乐,与世俗受外境刺激、不能持久之乐不同”[13](P231)。
但是,晚明清初通俗小说中关于藏传密教无上瑜伽部分的写作,并没有将其视为严肃的宗教修行,而是通常把它当作房中术的同类。《英烈传》在讲述西天僧西番僧向元顺帝传授秘法的故事时,将演揲儿法形容为“房中运气之术”[14](P5),视西天僧西番僧为擅长房中术的淫邪之徒。《僧尼孽海·沙门昙献》形容西僧昙献时,曰:“善运气术,其畜物时缩时伸。”[4](P198)此处“运气术”的说法,应该受到了《元史》所述演揲儿法的影响,并且直接把这一密教修行方式理解为控制性器官的手段。《僧尼孽海·西天僧西番僧》在上述引文之后,通过引用古代房中书关于九种交合姿势的描绘,以解释西天僧西番僧所授“演揲儿法”“大喜乐”“双修法”等秘法。“龙飞势”“虎行势”“猿搏势”等九种交合姿势,在《素女经》、《素女妙论》中均有叙述。《西天僧西番僧》对这九种姿势的描绘,虽然大致以房中书为底本,但进行了自己的删改。例如,在谈到第一种“龙飞势”的效果时,《素女经》曰:“女则烦怳,其乐如倡。致自闭固,百病消亡。”[15](P15)《素女妙论》曰:“男欢女悦,两情娱快,百疾消除。”[16](P38)可见,房中书关于男女交合之术的指导,不仅重视身体愉悦,也希望达到养生功效。但《西天僧西番僧》的“龙飞势”条,仅谈到“男悦女欢”,[4](P231)并没有消除疾病的考虑。《西天僧西番僧》对这九种交合姿势的描述,都有意摒弃了房中术的养生目的,而是突出男女身体上的愉悦。《元史·哈麻传》已经将西天僧西番僧所习秘法定义为房中术,而《西天僧西番僧》则通过删减关于房中书的引用,剔除了房中术较为严肃的养生意义,将西天僧西番僧的秘法描绘成纯粹追求性享乐的行为。
除了以史料为依托,小说也描写了民间举行的藏传密教仪式。丁耀亢《续金瓶梅》详细描述了信奉喇嘛教的胡姑姑及其主持的大喜乐禅定仪式。作品首先介绍了胡姑姑的来历及其法术。
却说这金国喇嘛教中有一胡姑姑,年纪六十余岁,名号百花宫主,系西番回回之妇。后因老回回殁了,与这些喇嘛往来,皈了邪教。……他传的一个法术,名曰“演折揲法儿”,又曰“大喜乐禅定”,专以讲男女交媾为阴阳秘密之法。又有一种邪药,男子吃了通宵行乐不泄,妇人吃了身体酥软昏麻,能使人醒了又迷,迷了又醒,一似酒醉相似。又供奉一尊铜佛,俱是二身男女搂在一处,交嘴咂舌,如画的春宫一样,号曰“极乐佛”。[5](P260)
“演折揲法儿”即“演揲儿法”。“极乐佛”指的应是明代文献中经常出现的“欢喜佛”。欢喜佛是被喇嘛奉为“大威德金刚”的密教塑像。[17](P422)丁耀亢是一位佛教信徒,曾受准提戒。《六月望日因病受准提戒》曰:“老病持斋素,安知关鬲寒。闻韶不思味,避谷未成丹。骨瘦从宽戒,佛慈减日餐。大悲同护念,即作准提看。”[18](P499)准提信仰受到汉传密教较深的影响。从该诗可见,丁耀亢对佛教的态度是比较严肃的。《续金瓶梅》的仪式描写非常具体,不仅仅提及演揲儿法、大喜乐禅定、欢喜佛等藏传密教概念,而且详细叙述了禅定仪式所用佛像和“胡旋舞”、“天魔舞”等表演。这种详实的描写说明丁耀亢对藏传密教法事有相当的了解。不过,在面对与汉地文化格格不入的藏传密教性修法事时,他也抱以敌视的态度。《续金瓶梅》把胡姑姑所信奉的喇嘛教定位为邪教,把欢喜佛描绘为立体春宫。作者认为参加大喜乐禅定的喇嘛“心内蛇形色是宗”,用“分明是二十四解春宫,却道是五十三参法相”来形容西番神像。[5](P276-277)小说这样描述大喜乐禅定给旁观妇女带来的情欲刺激:“把这大觉寺里尼僧们弄得半颠半倒,恨不得也学这演揲法儿,好不快活,却去冷清清看经念佛,怎如得他们这等禅定。”[5](P279)虽然作品没有直接引用房中书的性描写话语,但“阴阳秘密”“邪药”“春宫”等词汇中也有房中秘戏的影子。由此可见,即使像丁耀亢这样与佛教有着深厚渊源、对密教也有一定了解的文人,在描绘与藏传密教无上瑜伽部分相关的内容时,依然会取道房中术的路径,将其看作色情行为。
丁耀亢之于藏传密教无上瑜伽部分的态度,在文人笔记中可以找到回应。例如藏传密教的重要塑像欢喜佛,因其形制呈男女交合之状,文人不约而同将其理解为淫邪之道。宋懋澄《九籥集》“秘戏”条[19](P219)、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春画”条[20](P659)、董含《三冈识略》“淫像”条[21](P82)都记载了欢喜佛。其中,《三冈识略》所记多为清初事迹,对佛像的认识继承了明人观念。“秘戏”、“春画”、“淫像”等条目名称说明,晚明清初文人把密教塑像理解为房中秘戏的工具。正如吴世昌所说,“明人对于这些佛像的原来名称大都茫然,只能用些‘邪’‘淫’等字样来表示厌恶而已”。[17](P432)由于房中术与藏传密教无上瑜伽部分都包含男女双修的内容,所以前者较容易就成为了理解后者的中介。萨义德《东方学》认为,伊斯兰的形象在东方学中的功能,“与其说是代表伊斯兰教还不如说是代表中世纪的基督教”。[22](P76)与中世纪欧洲人以基督教为中介理解伊斯兰教相仿,明人是通过道教房中术的渠道来理解藏传密教无上瑜伽部分。经过房中术的处理之后,晚明清初通俗小说所写的藏传密教实为房中术的另一版本。但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用以描写藏传密教无上瑜伽部分的房中术内容,在严肃意义上并非道教的一部分。
一方面,胡僧色情描写所谈及的房中术是一种攫取精气、肆意纵欲的邪术。房中术是道教修仙术的一种。但小说关于胡僧的色情描写,显然与修炼成仙无关。胡僧所制春药,都是为了增强服药者的性能力,以获取更大的性快乐。上文所云《僧尼孽海·西天僧西番僧》对房中书的引用,更是主动剔除了其修炼成仙的部分。另一方面,小说作者常常将房中术安插在胡僧身上,无视佛道两教在性修方面的差异。《水浒后传》中的萨头陀这样描述自己的法术:“还有抽添铅汞、调养炉鼎之诀,须得唇红面白、无疾病的壮健妇女做了鼎器,然后面授秘诀,自能返老还童,寿与天齐了。”[2](P931-932)“抽添铅汞、调养炉鼎”是房中术的典型术语,也是明清小说中道士的常见作为。这种把道教行为置于佛教人物身上的做法,说明小说对房中术的使用相当随意,基本抹杀了房中术本来的道教修行色彩。苟波指出,“在通俗小说中,‘房中术’已经逐渐丧失了原有的宗教和养生意义,而被演变为表现男女交合情节的一个由头。”[23](P393)既然小说中的房中术内容已经偏离了宗教修行的意义,被房中术处理过的藏传密教与其原本含义相差更远。在胡僧的色情描写中,道教与佛教之间的界限被取消,都被俗化为房中术的表演。
晚明清初通俗小说中胡僧色情描写所涉及的宗教内容,同样体现了上节所述胡僧色情形象的模糊性及符号化的特点。藏传密教无上瑜伽部分与道教房中术,不仅激发了小说的色情想象,也是色情描写的参考资源。这两种色情想象资源在小说中基本没有界限,常常被混为一谈,体现了很强的模糊性。而这种模糊性,没有发展为多元的宗教描写,而是被统一纳入房中秘戏等色情描写传统之中。如果说第一节分析是从形象特征的角度,验证了胡僧色情形象的符号化,那么第二节则从色情描写的宗教内容方面,说明胡僧色情形象的建构路径也实现了符号化。在晚明清初通俗小说中,被色情化的胡僧不仅与黑面、春药有着固定的联想关系,而且以房中术为路径修习秘法,是房中术在世俗意义上的实践者。
三、胡僧形象色情化所反映的文人观念
学界往往将明清小说中胡僧形象的色情化归因于密教文化的广泛内传。*参见孙逊.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187-207;万晴川.论藏传密宗思想对明清小说中性描写的影响[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33(1):48-53;徐嘉莉.胡僧·性·密宗[J].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2002,23(1):55-61;李明军.禁忌与放纵:明清艳情小说文化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5:143-148。但从上文关于晚明清初通俗小说的论述可知,这批小说并没有把胡僧定位为藏传密教的僧人,胡僧的色情描写也被泛化为房中术的翻版,与藏传密教的意旨关系不大。文人对于胡僧的身份以及藏传密教的性观念,没有太多深入了解的兴趣,而是通过模式化的描写将胡僧建构为色情的符号,把藏传密教纳入房中秘戏的范畴。项裕荣指出,目前小说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密教文化直接影响了小说描写,对僧人强盛性能力的刻画可以看作是俗文学叙事的夸张。[24](P54)考虑到胡僧色情形象的建构与藏传密教之间并无太多叠合,以密教文化内传来解释胡僧形象色情化的说法,还需进一步斟酌。
值得注意的是,胡僧的色情化形象主要出现在通俗小说中。明清诗歌对胡僧的描写,仍然是士大夫阶层趣味的表达,并未脱离唐代诗歌及小说的描写路径,即关注胡僧的奇特相貌、预知能力及神异行为等特点。*参见李红. 论唐代的胡僧现象及其在小说中的体现[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8(2):65-70;查明昊.唐人笔下的胡僧形象及胡僧的诗歌创作[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2): 79-83;赵纯亚. 魏晋至唐时期小说对胡人形象的建构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12。元顺帝宠幸番僧一事在明代诗歌中多有反映。但这些诗歌基本没有涉及番僧淫行的描写。刘炳《燕城怀古》:“番国胡僧青鼠帽,天魔宫女彩龙舟。”[25](P633)瞿佑《天魔舞》:“天魔舞,不知危。高丽女,六宫妃。西番僧,万乘师。”[25](P2382)杨子器《元宫词·顺帝》:“学舞天魔才摆队,长安又领接番僧。”[25](P3193)被明代文人视为亡国之徵的天魔舞,往往与番僧相联系。上述诗歌将天魔舞与番僧并提,视番僧为元朝亡国的重要原因。但鉴于简洁的表达和严肃的主旨,它们没有将番僧形象色情化的意图。不过,胡僧与色情之间的联系在诗歌中也有出现。明末清初诗人蒋薰《陇西牡丹二十四咏·醉西蕃》,吟咏了一种形似胡僧的牡丹花。“胡僧东渡醉花茵,花气浓于曲米春。惊散帘前双蛱蝶,风流不似洛阳人。”[26]花可以用来比喻女性生殖器,而且双蛱蝶有成双入对之意,因此胡僧在花茵中醉卧的场景在某种程度上充满了情爱意义。但即使这种涉及胡僧形象色情意味的诗歌,其表达仍然非常含蓄,与小说直白细致的描写完全不同。另外,明清文人笔记及文言小说虽然对胡僧淫行有所刻画,但在整体规模和细节刻画方面都无法与通俗小说相提并论。因此,通俗小说是胡僧色情想象产生的主要文体基础。
由于通俗小说注重迎合民众的通俗趣味和讲求情节的生动新奇,小说作者对胡僧色情形象的建构具有很强的随意性。他们不仅无视宗教方面的区别,也不介意对历史进行篡改。晚明小说《禅真后史》写道:“又擢番僧怀义为白马寺王。”[27](P320)但根据《旧唐书》的记载,“薛怀义者,京兆鄠县人,本姓冯,名小宝……则天欲隐其迹,便于出入禁中,乃度为僧。又以怀义非士族,乃改姓薛,令与太平公主壻薛绍合族。”[28](P4741)显然,怀义和尚本来是今天的西安户县人,史书中也没有记载其具有少数民族的血统。《禅真后史》此种随意更改僧人身份的做法在《僧尼孽海·沙门昙献》中也有出现。《沙门昙献》以《北齐书》所载“武成胡后”的记叙为框架,讲了胡后与昙献私通的故事。《沙门昙献》明确说明:“昙献者,西僧也。齐武成时,入贡于中国,遂住持于相轮寺。”[4](P197)但实际上在史书中看不到有关昙献出身的记录。怀义和昙献之所以被小说附加以番僧或西僧的身份,可能是因为二人都被视为性能力高超的和尚,与人们关于胡僧性能力的想象有契合的地方。此类篡改是胡僧色情形象的极端体现,说明文人对胡僧与色情之间联想关系的建构,已经超越了历史事实的束缚,彻底实现了胡僧色情形象的符号化。
晚明清初通俗小说中胡僧形象的色情化表面上是宗教问题和历史问题,但这种机械化的符号处理归根结底是一种文人想象。葛兆光《宅兹中国》通过分析中国古代旅行记所载“女人国”“狗国”“尸头蛮”等异域故事,指出“古代中国关于‘异域’的这些描述,并不是关于当时人对于实际世界的知识,而是对于‘中国’以及朝贡体制中的‘天下’与‘四夷’的一种想象。”[29](P83)与“女人国”等荒诞不经的异域故事不同,晚明清初通俗小说关于胡僧的描写还没有完全脱离当时的宗教背景和历史背景。但是宗教思想并未真正渗透到小说描写中,历史记载与小说描写也有诸多差异,所以宗教与历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文学提供了想象的触发点。与“女人国”等故事类似,晚明清初通俗小说中胡僧形象的色情化也是建立在华夷观念的基础之上。
作为华夷观念的典型标志,胡僧的“胡”既具有外来宗教的指向,也代表地域和民族上的分别。“对于外来的宗教、习俗和其他文明,(宋代)士人有了一种基于民族主义立场的反感,也有了一种深深的警惕。”[29](P58)这种警惕在明代的体现之一是朝臣和士人反对藏传佛教的议论。《明宪宗实录》成化十年三月庚戌条曰:“礼科给事中王坦言,释氏之教,本无益于人之家国,今大应法王劄实巴以夷狄之人,假释氏之名,徒以惑人,亦非真有得于释氏者也。”[30](P641)王坦向明宪宗的这番进谏,代表了明代士人关于藏传佛教的典型看法。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始终不占据文化的主流,屡屡受到儒士挞伐。由“夷狄之人”带来的藏传佛教,在文人眼中都不算是真正的佛教,而是一种骗人的手段,会给国家带来危害。小说中胡僧的宗教背景未必是藏传佛教,但文人对藏传佛教的态度能够反映他们对胡僧的看法,也间接地影响了小说关于胡僧的描写。
与文人之于藏传佛教的警惕态度有所不同,晚明清初通俗小说中胡僧的色情形象首先反映了一种基于性别秩序方面的警惕。男女有别、尊卑有序的社会伦常秩序,是汉人区别于胡人的重要标志。晚明清初通俗小说色情化异域人物时的常用手法,是将其性行为建立在违背伦常的基础上。在《海陵佚史》中,金代海陵王将所杀宗室家的妇女纳为自己的妃嫔,其中包括他的从姊妹、再从姊妹。[31](P123)这种违反同姓不婚规定的做法,正是《海陵佚史》序中所云“赤族之诛夷,亦知夷虏之凶残狼戾,无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伦者乎”。[31](P49)《禅真后史》曰:“骨查腊举兵离洞,已经数月。其妻辛氏并爱妾三人,皆与嫡弟骨藜芦有奸。”[27](P197)骨查腊、骨梨芦均为与中央为敌的苗人。将叔嫂私通这样的违背伦常之事加之于苗人身上,也是文人刻意拉开中原与苗地之间道德界限的做法。胡僧因为来自异域,与家庭、亲属等没有直接联系,所以其具体的色情描写一般不会涉及同姓不婚、叔嫂私通等内容。不过,他们之于社会性别秩序的潜在威胁,仍然在小说中得到了反映。《僧尼孽海·募缘僧》中的胡僧进入武弁家后,捆缚夫人,奸淫小姐,打乱了武弁家原本正常的性别秩序。在《僧尼孽海》的《沙门昙献》和《西天僧西番僧》中,胡僧肆意出入宫闱、淫乱后宫的行为,不仅造成了宫廷性别秩序中僧俗混杂的情况,还破坏了尊卑有别的等级秩序。其对性别秩序的威胁,构成了对夫妇和君臣伦常的双重挑战,已经从家的层面上升到国的层面,可能给政治秩序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例如《水浒后传》的番僧萨头陀就帮助共涛杀死了暹罗国国君,让国家陷入危机。
不过,仅以警惕心态尚不足以完全说明胡僧色情形象所反映的文人观念。晚明清初通俗小说中被色情化的胡僧一般都具备高超的性能力,例如《僧尼孽海》的西僧昙献和《禅真后史》的番僧怀义。同时,他们提供的春药是普通人提高性能力的重要工具,例如《金瓶梅》的胡僧和《水浒后传》的萨头陀。夸张外来宗教人士的性能力及其春药功效,在中国文学中并不少见。19世纪的中国人关于基督徒的想象也采取了相同的思路。夏燮在《中西纪事》中这样解释男女基督教徒同处一室的问题,曰:“至同教男女共宿一堂,何以有黑夜传情之事,则以本师预目其妇人之白皙者,临时投以药饵,受者不悟而吞之,能令有女怀春,雉鸣求牡,盖即世俗春方之品,正所谓鸩以为媒者也。”[32](P34)文人关于19世纪的基督徒与晚明清初通俗小说关于胡僧的色情想象,发生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中,所以其具体描写方式有所不同。但在文人的想象中,基督徒和胡僧都成为春药的持有者。这种色情化外来宗教人士的相似策略,说明文人在深层心态方面仍然有一致的地方。为什么中国文人要采取色情的方式来异化外来宗教人士的形象,特别是喜欢夸大外来宗教人士的性能力呢?“投射在集团类型的形成中当然起到了作用。人们经常倾向于把在他们自己那里无法接受的冲动归到外来者身上。对外来集团的定型源于内部集团下意识的需要。在外国人身上,拘谨的儒家伦理被抛弃,想象力被容许任意驰骋。性机能不足的感觉也潜伏在对野蛮人生殖器官的夸大中。”[33](P42)冯客关于中国文人对基督徒的色情化处理问题的解释,对本文很有启发意义。文人将那些在儒家文化内部难以启齿的性行为加之于胡僧身上,既划清了华与夷之间的界限,又满足了自己言说性事的冲动。而晚明清初通俗小说关于胡僧高超性能力的描写,可能也影射了汉人对自身性能力的担忧。
晚明清初通俗小说中胡僧形象的色情化过程,必然受到了宗教和历史要素的推动。如何廓清文学描写与宗教文化、历史背景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本文不赞成过分强调藏传密教在胡僧色情形象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而是尝试从观念的层面来分析文学形象转变背后的文人心态问题。中国文人对异域人物的色情化策略各有特点,但终究无法离开华夷观念的立场。与其他异域人物类型的色情化不同,胡僧色情形象在文人观念中的符号化,与将和尚色情化的中国文学传统有关。在考究晚明清初通俗小说中胡僧的色情形象时,将其置于考察普通和尚色情化问题的背景中,显然非常重要,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笑笑生著,刘本栋校订,缪天华校阅.足本金瓶梅[M].香港:文城出版社,1988.
[2] 陈忱著.水浒后传[A].《古本小说集成》编委会编.古本小说集成[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3] (日)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A].白鸟库吉.白鸟库吉全集:第四卷[C].东京:岩波书店,1970.
[4] 旧题唐伯虎选辑.僧尼孽海[A].如意君传·痴婆子传·僧尼孽海·春梦琐言(思无邪汇宝第24辑)[C].台北:台湾大英百科,1995.
[5] 丁耀亢著,禹门三校点.续金瓶梅[M].济南:齐鲁书社,2006.
[6] 孙逊.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7] 查明昊.唐人笔下的胡僧形象及胡僧的诗歌创作[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2):79-83.
[8] 凌濛初编撰,石昌渝点校.初刻拍案惊奇[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
[9] 罗懋登著,陆树崙,竺少华校点.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0] 刘文忠校点.梼杌闲评[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11] 褚人获著.隋唐演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2] 严耀中.汉传密教[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13] 卓鸿泽.“演揲儿”为回鹘语考辨——兼论番教、回教与元、明大内秘术[A].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1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227-258.
[14] 赵景深,杜浩铭校注.英烈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5] 佚名.素女经[A].叶德辉编,杨逢彬,何守中整理校点.双梅影闇丛书[C].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
[16] 佚名.素女妙论[A].孙德敦主编.皇家藏书第26卷[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
[17] 吴世昌.密宗塑像说略[A].吴世昌.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一卷[C].北京: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421-456.
[18] 丁耀亢撰.李增坡主编.张清吉校点.丁耀亢全集(上册)[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
[19] 宋懋澄撰,王利器校录.九籥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20]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1] 董含撰.致之校点.三冈识略[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22] (美)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23] 苟波.道教与明清文学[M].成都:巴蜀书社,2010.
[24] 项裕荣.试论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淫僧形象——以明代话本小说为讨论中心[J].明清小说研究,2012,(4):50-62.
[25] 钱谦益撰集.许逸民、林淑敏点校.列朝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6] 蒋薰撰.留素堂诗删[A].四库未收书辑刊编纂委员会编.四库未收书辑刊第七辑19册[C].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27] 清溪道人著,余芳,麦笛校点.禅真后史[M].济南:齐鲁书社,1988.
[28]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八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9]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0] 钞本明实录(第八册)[M].北京:线装书局,2005.
[31] 无遮道人编次.海陵佚史(思无邪汇宝第1辑)[M].台北:台湾大英百科,1995.
[32] 夏燮著,高鸿志校点.中西纪事[M].长沙:岳麓书社,1988.
[33] (英)冯客著,杨立华译.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高雪
Exotic Imagination and Literati's Ideas: The Eroticization of Foreign Monks in Late-Ming and Early-Qing Vernacular Fiction
Xue Yingjie
(School of Chines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a)
Abstract:Foreign monks in vernacular fiction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are often constructed as lascivious characters who are associated with having black faces, keeping aphrodisiacs and teaching men sexual techniques. Characterized by a lack of elaboration of monks' identities, descriptions about eroticized foreign monks are quite similar in terms of physical appearances and plots. Furthermore, many terms for sexual practice in Tantric Buddhism and Taoism are applied to the art of the bedchamber in these descriptions. Therefor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eroticization of foreign monks is not terribly relevant to the transmission of Tibetan Tantric Buddhism in China. To a great extent,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the literati represent foreign monks as a threat to their moral identity, which betrays a suppression of their sexual desire in Confucian culture.
Key words: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vernacular fiction; foreign monks; exotic imagination; literati's ideas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5X(2016)01-0122-07
作者简介:薛英杰(1989-),女,山东青岛人,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明清文学和中日比较文学。
*收稿日期:2014-1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