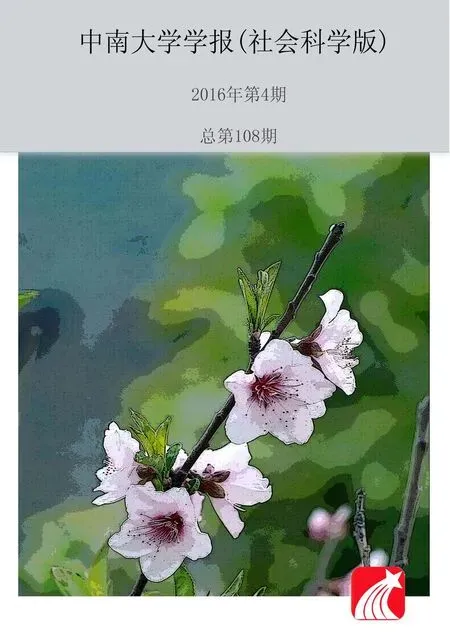从传统文化看《活着之上》对“新道统”的构建
晏选军,尧育飞
(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从传统文化看《活着之上》对“新道统”的构建
晏选军,尧育飞
(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通过对传统文化中“道统”和“文统”理念的借鉴和吸收,《活着之上》成功构筑起小说内部的“新道统”。在这一“新道统”的价值体系和精神坐标中,“反功利”和“安贫乐道”的传统思想起着重要作用,二者交互作用,共同塑造了小说的基本价值取向,也尝试着对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作出一种回应。
新道统;《活着之上》;反功利;安贫乐道
社会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问题,历来颇为引人关注。聚焦这一问题的《活着之上》问世之后,评论界反响甚大。论者为小说呈现出的知识分子纠葛的生存世界和精神世界而着迷,他们谈到知识分子的生存与超越问题,谈到知识分子的灵魂的失落与反抗,也谈到了知识分子的底线意识等等。应该说,这些研究力图比较全面地揭示出《活着之上》“如何写”与“怎么写”的问题,但是对作者阎真何以如此写,当前的研究者似乎着墨并不多。赵勇曾在《南方文坛》撰文指出,小说展示了知识分子的底线意识或者说书生气。他认为:“聂致远痛苦纠结的原因概源于此。表面上看,他似乎守着一种精神资源和价值体系,但是面对当今这种现实格局,仅仅在‘致良知’‘知行合一’‘义利之辨’等层面反躬自省,往往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或者也可以说,他所坚守的古代知识分子传统只能使他退回内心。”[1](99)赵勇的眼光的确有其独到之处,但他并未详细阐述这种“精神资源和价值体系”。谢文芳在《绝望反抗招魂——关于阎真的〈活着之上〉》中也隐约触及这一点,她认为这是知识分子“失魂”的表现:“《活着之上》吸收了传统文化资源,着重描绘了当下知识分子魂飞魄散的流浪人生,一个个死去了操守和底线的知识分子成为失魂时代的孤魂野鬼,在热闹却寂寥的旷野里游荡。”[2](81)但是对于阎真所作的招魂努力,所招来的“魂”,依旧没有进行深入的诠释。
实则在面对媒体采访时,阎真坦率地吐露了他的心扉:“我不认为传统道德观念都是虚伪的和不适用的,或者说过时的。传统文化对当代知识分子来说,仍然有思想资源的价值。当然传统又是复杂的,多样的,负面的因素也不少。但我认为,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还是可以做到的。比如,像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杜甫和曹雪芹等等文化英雄,他们用自己的血泪人生以至生命,证明了比自我生存更高的价值和意义的真实存在,这就是《活着之上》的价值和意义。”[3]屈原、陶渊明、杜甫、曹雪芹等传统文化人物何以成为阎真的选择?由这些人物构筑的文化谱系与传统文化中重要的“道统”和“文统”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他们在《活着之上》的叙事中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传统文化中这些有价值的思想资源经过小说的检验最终结果如何?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厘清这部小说和传统的关系,对我们今天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也不无帮助,这也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一、继承与吸纳:传统文化与“新道统”的确立
《活着之上》是当今一部出色的聚焦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小说,纵观这部当代小说,读者不难发现,其中涉及了一大批我们耳熟能详的古代人物,比如曹雪芹、屈原、司马迁、杜甫、朱熹、张载等。这些文化英雄在小说中出现的次数并不算特别多,但每次出现,都是聂致远在面临人生选择和灵魂拷问之时。此时的聂致远会想起这些在历史长河中逝去已久的传统文化巨人。他们那烛照千古的人格和精神,鞭策着聂致远别去走“歪门邪路”。与当代其他小说相比,这是一个别具意味的现象,显然不是作者无意为之。毕竟,这些对于小说而言重要的人物都是中国人,而且是古代中国人,没有一位是西方的,荷马、苏格拉底、莎士比亚这些有着相似影响的西方文化名人都不见踪影。这就引发了我们进一步的思考:为什么?作者意欲何为?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这些中国传统文化人物稍加分类,小说的这条传统脉络就比较清晰了。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杜甫、曹雪芹,按照这个序列开列出来的是一条粗略的中国文学英雄的谱系,姑且名之曰“文统”,意味着通过文学创作体现出才情和不妥协的底线意识,这也与当今中国文学史主流书写的历史脉络大致相同;另一群人物则是以孔子、张载、朱熹为代表,在小说中他们被称为“圣贤”,以开万世太平为目标,代表着对道德和精神起着笼罩性影响的“道统”。
关于“道统”,早在两千多年前,《论语·尧曰》曾言:“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4](193)提出的乃是帝王继统的法则,实际上也就是“政统”。司马迁在《史记》中,引用其父司马谈的话后直抒胸臆说:“‘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5](卷一百三十)司马迁这段自我激励的话,则为后世士人构建起了道通先贤的精神坐标系。韩愈在《原道》中云:“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及其传焉。”[6](147)韩愈是从学术发展的进程,厘定了一个儒学的统绪。发展到朱熹那里,则明确了“道统”这一概念:“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7](P14)
古人构筑“道统”体系,为的是正本清源,宣扬自己的学说,并给自己的名山事业树立一个合理的坐标。一般而言,道统和文统都有着自己的标准和运行规则。但有时这两个对中国文化有着重要影响的传统也会交汇到一处,比如韩愈,就被苏东坡评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8](卷一五),认为他文、道兼综而均致其极,这种评价对后世影响深远。在《活着之上》中,两大传统并非简单的交汇,而是毫无保留地缠绕在一起。这当与作者的创作意图不无关系,因为在文化层面,作者所要探讨的是“传统文化在今天在多大程度上还有思想资源和价值资源的意义”[3]。故而作者不能专美两大系统中的任何一个,而只能尝试二者的融合叠加,因为它们都时刻在为传统文化提供着优秀的思想资源和价值资源。事实上,这两大系统在小说主人公聂致远那里,被纠合成一个新的精神文化系统,不妨名之曰“新道统”。①
“新道统”在道统框架内,吸纳了符合道统文学观的诗文统绪,李白、苏东坡等人因而被顺理成章地纳入其中。但何以取屈原而不取宋玉,当有文学的原因,也有人格的因素;取杜甫、李白而略过韩愈,更可见其价值取向。最终呈现在“新道统”谱系中的人物,都成了聂致远精神世界的巨人。这些文化英雄构筑“活着之上”的精神谱系,而聂致远自觉地将自己定位在这个谱系中,试图成为这一谱系中的一环。正因为他的努力方向如此,使他不能不为前人所感奋。这种给自己建立精神坐标的做法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显得不太常见,却是传统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追求乃至安身立命的根本。贪夫廉,懦夫有立志,凭借构筑这一精神谱系和价值定位来自我激励、自我感召,小说成功地续接起中国传统士人一以贯之的传统。
这种精神谱系在中国的小说传统中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在传统小说中广泛出现的“登榜”“排榜”现象,就是构建谱系努力的反映。在《水浒传》中,有梁山好汉的天罡地煞的座次榜;在“说唐”系列小说中,有隋唐好汉排行榜;《封神演义》被俗称为《封神榜》,更可见这种构建的努力已为传统小说读者所广泛接受。在《儒林外史》中,则有著名的“幽榜”,其精神谱系直接根植于儒家道统观中,与《活着之上》所构建的“新道统”谱系颇为接近。它们同是通过预设这些价值榜单和精神谱系,将“众多人物和事统筹起来,从而起到介绍人物与人物定位、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等作用”[9](133)。《活着之上》正是借助这个“新道统”,并预设聂致远自觉努力进入这个价值坐标体系,其思想和价值观便不能不受这一小说传统的影响,在某些方面甚至被笼罩于这些文化巨人之下。
基于此,聂致远在精神上自然具有了特别坚韧的一面,那种为信念而奋斗的动力也更为充足了。当然,因为谱系上的文化人物是英雄,是巨人,在自己能践行他们的准则时,便是欣喜,是愉悦;在自己困于现实达不到这一境界时,那些巨人又仿佛是巨大的阴影,造成沉重的精神压力。他们默默凝视却又无处不在,聂致远是常常感受到这股压力的,作为知识分子的纠葛和灵魂的挣扎也因此产生,小说的情节、人物的性格也藉此推动。尽管这样的价值先行,或许会让小说中的人物有出现脸谱化倾向的隐患,但对于揭示小说的价值取向而言,无疑是最为简捷和有效的。从这个角度看,《活着之上》在当代小说中有其独特的价值。
二、“反功利”与“安贫乐道”:“新道统”中的两大思想基石
如作者所言,在《活着之上》这部作品中,他意图将传统文化放置在当代社会之中,去检验传统的道德理念,在当代社会是否还有涅槃再生的可能。上文提到,这种检验起初是通过叠加两大传统谱系,进而构建“新道统”来达成的。在小说中,“新道统”如何显现其威力?它是如何作用于主人公聂致远的?它之令聂致远感到压力和焦虑的背后,究竟包含着哪些重要的传统思想元素?通过对小说文本的仔细解读,我们可以归纳出“新道统”的主要思想资源,及其在小说中显示的张力,最终得以自洽性的解说。
首先,“新道统”最主要的思想资源应是来自先秦思想家的“反功利”思想。
已有研究者指出:“在价值论的意义上,《活着之上》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上存在的一个永恒悖论:精神与物质的矛盾,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之辨’。”[10](102)关于这一点,小说多次触及。面对金钱的诱惑,聂致远反复吐露了这样的心声:“寒假之前我整天想着的一件事就是钱、钱、钱。没有办法不想。一个男人,总不能空着手回去过年。”[11](52)“吵架归吵架,生活还是生活,这就是钱、钱、钱。”[11](33)“忽然想到陶渊明辞官归故里,归去来兮,载欣载奔,有点不理解。没了官一家人就没了生计,他怎么那样高兴?”[11](116)“那些天我整天就想着钱的事情,钱,钱,钱。生活动不动就要钱。……这种状态让我害怕,一个知识分子,他怎能这样去想钱呢?说到底,自己的心中还有着一种景仰,那些让自己景仰的人,孔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杜甫、曹雪芹,中国文化史上任何正面的人物,每一个人物都是反功利的,并在这一点上确立了自身的形象。如果钱大于一切,中国文化就是个零。”[11](32-33)好在,在为企业家代写传记、在论文评优、在职称晋升和评比等关乎个人切身利益的问题上,聂致远最终舍利而选取了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反功利思想确实是伟大文化人物共同的信念。《论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4](73),这是以“君子”和“小人”来给“义”“利”做区分。当面临聂致远这样的难题时,传统文化所强调的是“义大于利”,也就是人的道德自觉要优先于本能欲望诉求。《孟子》云:“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12](332)与之相对应的道德评判标准则是《荀子》所云:“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13](卷二)汉代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更进一步提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样近乎绝对的“反功利”思想,并成为指导相当一部分士人义利选择的基本道德标准。
《活着之上》所构筑的“新道统”几乎全盘吸收了传统思想“反功利”的一面,“反功利”在小说中因而被提到一个特别突出的地位。小说在开篇部分屡次提及《红楼梦》和曹雪芹,并称许道:“这样一个曾经存在的生命,在某个历史瞬间,在某个寂寞的角落,过着贫窘的日子,却干着一件伟大不求回报的事情。”[11](8)由此,作者由衷赞叹曹雪芹虽然在现实物质生活中渺小、卑微、凄清、贫窘,但他的精神生活从容、淡定、优雅、高贵。与传统文化中“反功利”多存在于思想领域的研讨相比,《活着之上》把这种“反功利”思想具象化了,具体地落实到现实生活,变成赤裸裸的残酷的生存抉择。小说写到,在申报课题的时候,出现了蒙天舒“搞到了就是搞到了”的论调。所谓“搞到了”就是放弃“义”而得到的课题,而“没搞到”的“反功利”则意味着失去这一利益——“总之,别人有的一切你都没有。”“搞到”与否依靠的是“沟通”:“一个学者,除非他真正才华横溢,谁也压不住,不然不沟通就很难出头。沟通,现在叫作公关,从前叫拜码头。公关就是攻关,攻下那道关,这就是目标,目标就是一切,公平正义和人格清高都没办法讲。”[11](68)小说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有时更进一步地直接将“功利”简化为钱,“反功利”就意味着不要钱,没有钱。这些粗粝的具象词句和场景,让传统的“反功利”思想变得具有很强的震撼力。
至于支撑“反功利”思想的,在小说中所构筑的理由主要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小说写到聂致远求职异常艰难的时候,就忆及宋儒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并说:“这是我的使命、我的道路、我的信仰。”[11](70)关于传统知识分子的天下家国情怀,历代论述者甚多,可谓胜义纷披、精彩叠见,最显著地体现在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在这种宏大叙事的精神感召下,人们很容易受此激励而建立崇高的、为理想献身的“反功利”信念。但现实生活常常特别的冷酷,由这样的反功利思想出发,知识分子势必要在现实中遭遇不少的挫折。在这种挫折背后,知识分子首先表现的是某种犹疑:“钱和权,这是时代的巨型话语,他们不动声色,但都坚定地展示着自身那巨轮般的力量。我能螳臂当车吗?我忽然想到,自己心目中的圣人,都是螳臂当车的人,他们因此都遭遇了凄凉的人生。哎,司马迁、曹雪芹,他们是来给人瞻仰的,而不是来给人效仿的啊!”[11](224)显然,这番感慨不仅仅是主人公聂致远的个人感悟,而更像是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发出的群体拷问。那么,如何在现实生活中,解决因“反功利”思想而带来的挫折和困难问题,就显得比较重要了。
在此,《活着之上》再次将视线转向传统文化,顺理成章地借鉴了“安贫乐道”这一思想命题。
小说借用苏东坡的遭遇作了一种自我宽慰:“欲望无边无际,就意味着痛苦无边无际。苏东坡当年在京城当大学士,说贬就贬到黄州惠州海南岛去了,那是什么境地?他也没有失去旷达。”[11](297)旷达,不计较个人的成败得失,因而内心能够获得安宁。当然,任何一种思想的选择与转折,以及最后的定型,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安贫乐道的思想同样不能一步达成,否则小说就写不出人物性格的变化了。事实上,安贫乐道正是无数次因“道”而遭遇挫折后习得的一种人生智慧。在许多次面对钱的时候,面对权力的时候,面对精神与物质的冲突的时候,选择反功利常常意味着在世俗生活中的失败。普通人是无法承受这种痛苦的,因而传统文化的解决之道显得颇为可贵。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4](77)颜渊有所谓“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4](87)。至于小说中写到的其他人物,如陶渊明有“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李白称“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苏东坡吟“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等等,这样一些脍炙人口的句子,反映的恰好是这样一种道德智慧和道德情怀。
由于有了精神信仰的支撑,对于穷困,传统文化的安贫乐道不失为一条有效的解决之道,而底线则是不能悖离“道统”,也不能破坏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所以《论语》又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4](161)
三、余论:“新道统”与当代知识分子的反思
借助“反功利”和“安贫乐道”两大传统文化资源构筑起“新道统”,《活着之上》较为完整地展现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焦虑和自我省思的历程。在这场关乎传统文化的大检验中,《活着之上》最终给予主人公聂致远一个较为美好的结局。然而从小说具体的描写看来,作者应该是在暗示:虽然聂致远得以保全其理想,但屈服于现实功利的知识分子数量恐怕更为庞大。捍卫“新道统”的群体,遭遇和前景似乎颇为不妙。由检验的最终结果看,我们不能不对这样一种结果有些失望。但这种失望和失败,既不能归因于作者,也不能完全归罪于传统文化。实际上,正是通过传统文化这根探针,才烛照出当今知识分子的诸多问题。
至于针对这一问题的药方,作者似乎并没有给出较为完善的答案。其实,在小说文本中,作者就借助曹雪芹等文化巨人直接表达了他的这种困惑,尽管这种困惑始终都以致敬的方式体现出来:“曹雪芹太骄傲了,内心也太强大了。他是生活在别处的人,世俗的眼光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他选择了背向主流社会,背向荣华富贵,背向人们所仰慕和渴求的一切。他改变了世界吗?没有。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吗?也没有。既然没有,他的选择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理由?唯一的理由,就是心灵的理由。唉,心灵的理由是不是能够成为充分的理由呢?清高和骄傲摧毁了他的现实生活,却成就了他的历史形象。这其实也是中国所有文化名人的共同选择和共同命运,孔子、司马迁、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曹雪芹,也是如此。我是聂致远,我不是他们。这让我感到惭愧,却也感到幸运。”[11](55-56)心灵的理由就是内心的强大与骄傲,这种强大与骄傲在缺失了传统精神信仰资源的当代,无疑显得有些尴尬和无措,“惭愧”与“幸运”就是这种面对纯粹精神世界时表现出来的复杂心态的真实体现。
小说反复强调中国文化传统,很容易使人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作者为精神沦陷所开出的全副药方。但是显然,要重新构建知识分子的精神信仰世界,仅有中国传统文化或许还不够。此外,小说主人公聂致远对于世俗功利,仅仅从反抗和妥协的角度去处理,这也有些一厢情愿了。即便不论借鉴西方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不乏其他应对功利诉求过度的制衡措施,比如庄子的逍遥坐忘、理学思想对欲望膨胀的制约,等等。这些在小说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展示,由此给一般读者造成坚持理想、道德和原则,便要穷困乃至于被社会边缘化的印象,这恐怕是小说的一点遗憾。实际上,道德原则和利益原则在任何一种文化中均同生共长,差别仅在侧重点不同而已。二者发生冲突时,一味强调一方而压抑另一方,单独标榜“义”或者“利”,今天看来都有欠妥帖,但未必不是作者有意为之,以此为竞相追逐功利风气而下的针砭之剂。
事实上,尽管存在这些缺憾,小说在呈现传统文化的价值和理想方面,在揭示传统文化的贡献和局限方面,在呼唤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方面,仍有着非常独特的意义。正如作者再三致意的那样:“曹雪芹们,这是真实而强大的存在,无论有什么理由,我都不能说他是他,我是我,更不能把他们指为虚幻。”“曹雪芹他做出了既不为现世功利,也不为千古流芳的牺牲,无人见证,也无需见证。也许,认为他受了天大的委屈,那是我用一双俗眼去看他,完全不合他的心意。高山仰止。曹雪芹最有资格接受这种景仰,虽然他自己对此毫不在意。”[11](309)我们这个时代,同样需要如曹雪芹们这样的文化巨人,化解弥漫着的焦虑情绪,支撑起文化信仰的天空。尤其是小说发出的“活着之上”的提问,与传统精神一脉相沿,而这一提问背后的传统文化资源,仍然值得研究者和创作者不断开掘。
注释:
① 此一概念借鉴了祝尚书《论宋代理学家的“新文统”》一文的观点,见《文学遗产》2006年第三期。文章认为韩愈的道统、文统观念到朱熹那里,发生变化,朱熹“在‘道之文’的框架中,构建起符合理学文学观的诗文统绪。”但祝先生所着重讨论的是文章统绪,本文侧重的则是文学与道学融合而成的文化统绪。
[1] 赵勇. 知识分子的底线意识,或聂致远的书生气——重读《活着之上》[J]. 南方文坛,2015(4): 96-100.
[2] 谢文芳. 绝望反抗招魂——关于阎真的《活着之上》[J]. 名作欣赏,2015(33): 80-82.
[3] 冯翔. 保证我们做人还有一个底线: 从《沧浪之水》到《活着之上》,[EB/OL]. http://www.infzm.com/ content/108060/html,2015-03-06.
[4] 孔子. 论语[C]∥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北京: 中华书局,1995.
[5] 司马迁. 太史公自序[C]// 史记. 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6] 韩愈. 送浮屠文畅师序[C]// 韩愈集. 长沙: 岳麓书社,2000.
[7] 朱熹. 中庸章句序[C]// 四书章句集注. 北京: 中华书局,1995.
[8] 苏轼. 潮州韩文公庙碑[C]// 苏文忠公全集. 明成化刻本.
[9] 王湘华,连丹虹. 论古典长篇小说中的“榜”艺术[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133-137.
[10] 欧阳友权. 超越活着与活法的重量——评阎真长篇新作《活着之上》,南方文坛,2015(4): 100-104.
[11] 阎真. 活着之上[M].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
[12] 孟子. 孟子[C]//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 北京: 中华书局,1995.
[13] 荀子. 荀子[M]. 清抱经堂丛书本.
[编辑: 胡兴华]
Construction of new Confucian orthodoxy in Beyond Living seen from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YAN Xuanjun,YAO Yufe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3,China)
By referring to and absorbing the concepts of the Confucian orthodoxy and the literary orthodoxy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Beyond Living has successfully constructed the new Confucian orthodoxy from within. In this value system and spirit direction of new Confucian orthodoxy,the traditional thoughts of anti-utility and being contented with poverty of a humble yet virtuous life matter a lot. The interaction of the two thoughts forms the basic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novel,which also attempts to respond to the spiritual anxiety of the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s.
new Confucian orthodoxy; Beyond Living; anti-utility; being contented with poverty of a humble yet virtuous life
I207.42
A
1672-3104(2016)04-0162-05
2016-03-20;
2016-06-12
晏选军(1974-),男,湖南醴陵人,文学博士,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古典文献学;尧育飞(1987-),男,江西广昌人,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