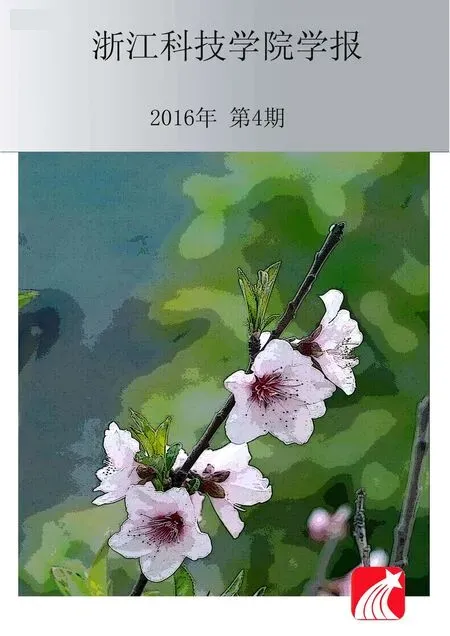《地铁通达之处》:英国现代版的“情感教育”
石雅芳,程 娅
(杭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杭州 311121)
《地铁通达之处》:英国现代版的“情感教育”
石雅芳,程娅
(杭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杭州 311121)
当代英国著名作家朱利安·巴恩斯的处女作《地铁通达之处》出版后曾获毛姆奖,但它在中国的受关注程度却远不及作者的其他作品。从“情感教育”、戏仿、现代英国性这三个视角,解读生活于英国伦敦郊区、地铁沿线及曾一度旅居巴黎的主要人物,从少年到青年再到中年的情感困扰、生活追求与成年迷茫,探索这部带着浓郁戏仿色彩的英国现代版的“情感教育”,试图揭示作者对生命、时代及空间的独特理解与思索。
《地铁通达之处》;“情感教育”;戏仿;现代英国性
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 1946—)是颇受关注与欢迎的当代英国作家,中国社科院的陆建德研究员在为巴恩斯的曼布克获奖作品《终结的感觉》的中译本作序时赞叹道:“巴恩斯是当今世界上最优秀的作家之一”[1]。巴恩斯的不少作品都受到中国文学研究者们颇多的关注,或有译本,或有研究评论。但是,他的处女作《地铁通达之处》[2]虽曾荣获英国的毛姆奖,并在出版时被评论界誉为“久违了的最出色的现代小说之一”,然而在中国却鲜有关注。
研究者们把研究目光较多地投向了巴恩斯的曼布克奖提名与获奖作品,如《福楼拜的鹦鹉》《10 1/2章世界史》《英格兰,英格兰》《终结的感觉》。确实,这些作品体现了作者较高的文学成就,它们都在某种程度拓展了英国小说创作的可能性空间。中国巴恩斯研究大都围绕着这些提名与获奖作品,就实验性、自反性、新历史主义、历史编纂元小说、后现代叙事等关键词所展开的研究,取得不少可喜的成就。但是若想要寻找一些对《地铁通达之处》的中文评论,却不容易。不过,综述性的英语文学研究给予了它相对公平的研究关注,如《当代英国小说史》[3]319在谈及巴恩斯时,相对公平地对待了他的所有小说,没有厚此薄彼,其中还对《地铁通达之处》作了较详细的介绍与点评。庆幸的是,近年对巴恩斯作品的研究视角似乎更趋于包容与公正,如王一平2015年相继发表的2篇相关论文都正面关注了《地铁通达之处》。他在文献[4]中详细解读了巴恩斯小说中的历史与新历史主义的关系,指出了巴恩斯在60多岁出版的《终结的感觉》是他34岁时出版的小说《地铁通达之处》的续篇,并将2部作品进行了对照研究,令人耳目一新。国外的巴恩斯研究及英国文学研究,同样较公平地对待巴恩斯的小说创作。Bradbury[5]在对每位涉及的作家及其作品都给予了应有的公平与公正的同时,对《地铁通达之处》的点评精到而富有启发性。在《朱利安·巴恩斯:当代批评视野》[6]一书中,第一章就是一篇关于《地铁通达之处》的研究文章,即“游荡者与资产者:朱利安·巴恩斯的《地铁通达之处》中的巴黎与伦敦”,它抓住都市与郊区两个关键词,将伦敦郊区与巴黎的价值观与生活风格进行了对比研究。又如《朱利安·巴恩斯谈话录》[7]的主编,在选编的18篇谈话录中,同样按作者发表作品的时间顺序,首先选择了有关巴恩斯的处女作《地铁通达之处》的谈话内容。
赶潮流,追热点,或许是人性使然,但对待文学研究,尤其是想了解一个作者的创作脉络,却是不可取的,甚至略显势利。
虽然《地铁通达之处》在中国评论界受到的关注尚且不多,但此书在英国出版时受到评论界的欢迎,根据《当代英国小说史》的资料,尼娜·鲍登在《每日电讯》上评论道:“我想不起何时欣赏过更佳的处女作”[3]319。《新政治家》的评语是:“如果每一部小说处女作都是如此深思熟虑、感觉敏锐、诙谐有趣,那么再也不会有人谈论小说的死亡了”[3]319。
可见,这部作品所遇到的冷遇、热赞及授奖,形成了不小的反差,这激发了笔者开卷拜读,一探巴恩斯在他这部带着浓郁戏仿色彩的英国现代版的“情感教育”所展示的艺术魅力。
1 叙事线索
巴恩斯的这部小说是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的,主人公是克里斯托弗(昵称:克里斯),由他给读者讲述他的少年、青年及中年时期的3个人生片段:1963年,主人公16岁,住在伦敦郊区;1968年,20岁的主人公到巴黎进行半年的研修;1977年,30岁时,他安居于伦敦郊区。这3个片段构成了小说的3个组成部分。小说的叙述视角是第一人称单数与复数,因为小说的主人公除了克里斯以外,还有他的好朋友托尼。小说中的“我们”,通常就是指克里斯与托尼。
第一部分,即少年部分,是三部分中最长的一部分,其篇幅几乎占了全书的一半。这部分是在引用法国诗人兰波的诗《元音》中的“A黑、E白、I红、U绿、O蓝”诗行中开始的,在接下来冠以不同标题的13个章节中,读者读到了克里斯与好朋友托尼在成长过程中所遇到的情感问题、对成人世界的反抗、对郊区生活的思考等。这2个少年充满着对艺术的热爱,对生活真谛的追求,对成人世界虚伪的强烈不满与冷嘲热讽。如他们带着望远镜与笔记本去逛艺术馆,观察参观艺术馆的人们的行为举止并进行记录;他们初次被人尊称为“先生”的经过与感受;老师与家长竭力回避书中少年所感兴趣的性话题,突显了成人世界的谎言与虚伪的特征;他们在伦敦街头“有意义地闲逛”,去“寻找情感”,讨论着妓女是否是“小资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意识到“艺术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寻找有助于世界了解自身”的动力,“追求更简单、更真实、更深刻、更基本的东西”[2]30;从伦敦市中心坐地铁到他们郊区的家的过程中,了解了地铁曾给人们带来的无限希望与希望落空的失望;享受并追求住在郊区的那种“无根”的生活;哥哥将女朋友带回家而引出了少年克里斯对女性话题的几个维度。
在小说的第二部分中,主人公克里斯已经是21岁的青年大学生,不再是懵懂的少年,这时不只是与朋友托尼谈论性与情感话题,而是直接开始了对情感与性的生活体验。克里斯因一个研究课题来到法国巴黎,认识了一个叫安妮克的法国姑娘,不久便与这个率真的姑娘住在了一起。后来在一个艺术家故居里结识了3个英国来的年轻人——两男一女,后来这个女孩便成了克里斯的妻子。在这一部分中,主人公追溯了自己的情感经历,同时思考了自己在巴黎生活了一段时间后,英法2种文化对自己的影响与改变。最关键的是他与好朋友托尼之间的分歧开始变得明显起来,特别是他们对政治与艺术出现了不同的追求。
在小说的第三部分中,主人公已经是30岁的中年人,已经在伦敦郊区结婚生子,安家乐业,似乎已经开始享受如他少年时所反抗的父母的那种生活了:那种都市郊区的中产阶级所享受的保守、安稳的生活。
同时,这部小说有一个非常巧妙的平行线:那就是主人公的3个成长阶段与时代发展的平行线。1963年,西方世界自由主义思潮泛滥,反抗与叛逆精神弥漫于一切角落,这似乎与处于反抗期的16岁少年的性情非常吻合。1968年,法国巴黎的校园抗议激情似火,而21岁的主人公也正处在激情似火的年龄阶段。1977年,英国社会处于相对保守的时期,如30岁的克里斯一样,保守与满足就是他生活的现状。
2 对《情感教育》的戏仿
说起“情感教育”,人们自然会想到福楼拜的同名小说《情感教育》[8]。而巴恩斯小说中恰恰又与福楼拜的《情感教育》存在着诸多的相仿之处,难怪乎,Brandbury称《地铁通达之处》“几乎是一部现代的情感教育”[5]487!如果对两部小说都较为熟悉,便不难感觉到巴恩斯的这部小说中浓郁的戏仿色彩。
戏仿,又有称为戏拟,“非专业的定义和字典中一般意义上的定义都是贬义的,或者至少是颇不以为然的”[9]41。但萨莫瓦约却认为,其实戏拟的目的或是出于玩味和逆反,或是出于欣赏[9]42,而萨莫瓦约的观点似乎更符合巴恩斯对福楼拜艺术的戏仿。
2部小说都是以一个年轻人的视角,讲述着年轻人的情感经历。福楼拜的《情感教育》讲述了一个怀着艺术梦想与追求而无心其他事业的弗雷德里克·莫洛的情感历程。《地铁通达之处》中的克里斯与托尼也同样少年时怀着追求艺术的梦想。弗雷德里克是一个巴黎外省的青年,最后来到巴黎寻找到了他对异性的情感:他被画商阿尔努的夫人玛丽的美貌与仪态深深吸引。克里斯也是都市郊区的年轻人,同样到了巴黎,开始了他与女性的情感经历。
最有意思的是,2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有一个好朋友:克里斯有托尼,而弗雷德里克有戴洛立叶。像弗雷德里克一样,克里斯出身于相对殷实的中产阶级,而托尼则与戴洛立叶一样,家境相对贫困。2对朋友中,一个是资产者,另一个则是无产者。这多少又与他们未来的人生道路与人生态度密切相关。如克里斯在激情似火的年龄来到了激情似火的1968年5月的巴黎,但他的激情投入到了他自己的情感世界中。正如《情感教育》中的弗雷德里克好不容易有了与他心爱的玛丽约会的机会,而约会那晚,法国正处于1848年的革命风暴中,朋友劝他参加到如火如荼的革命行动中去,但他如何能听从他的朋友,投身于革命风暴而放得下他心仪的女人?《地铁通达之处》中的托尼虽人在英国却心系当时的巴黎学潮,他一方面希望从克里斯那里更多地了解到学潮的情况,另一方面又对克里斯投身于他的情感世界而置当时的学潮于不顾充满鄙视与不满。是投入自己的感情世界,还是像对政治充满着热切的托尼那样投身于现实的革命风暴中?这样的分歧到了他们中年时更为显著。巴恩斯小说在对《情感教育》的戏仿不知是有意为之的还是纯属巧合?至少这部分的戏仿成分特别浓郁,是不是也多少体现出了作者对人生的态度与立场的选择与思考?或者,想表达他对福楼拜对待政治运动的态度与思考?
巴恩斯对福楼拜远不止是怀着崇敬之情,他对后者的小说及人生的熟悉程度在他的第三部作品《福楼拜的鹦鹉》里就一目了然了。事实上,作者以“在我的口袋里装着我刚开始阅读的《情感教育》”[2]130来结束《地铁通达之处》第二部分,这是不是所谓的“露痕”?或者作者有意为他的小说《地铁通达之处》与福楼拜的小说《情感教育》之间的联系给读者提供一点线索?
3 一部“情感教育”
说巴恩斯的这部处女作是一部“情感教育”,首先是因为贯穿全书的主要内容是人物的情感发展,小说追溯了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对情感从懵懂、好奇到体验,再到对婚姻家庭的情感维护3个阶段。此处的“情感教育”并非是社会学或心理学的意义。
当然,小说里的情感既是狭义的,专门指男女之间的感情,也是广义的,指主人公体验的各种爱恨情仇,特别在第一部分里,巴恩斯较广义地展示了2个中学生的心理反抗期的多种情绪。
在心理反抗期的少年眼里,成人世界是不可靠的,是充满矛盾与虚伪的。相比较,只有艺术才是真之所在,于是他们的梦想与理想从文学艺术开始,因为克里斯与托尼都认为“艺术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2]29。小说一开始就透过2个少年的望远镜看到那些来到国家艺术馆欣赏艺术的人们的那种假模假样,“一个戴着男人眼镜的年轻修女”站在充满着情爱暗示的画作《阿诺菲尼的婚礼》前“多愁善感地微笑着”[2]11,另一个中年女人在凡·代克的《骑马的查理一世》前安静下来,直到眼睛闭合了起来,“她的闭眼可以作两种解释:要么她欣赏得愉悦无比;要么她睡着了。”[2]12
家庭与学校是孩子成长过程中2个重要的知识源头,那么小说中的2个少年,是否能从这2个源头获得他们渴望获得的与性相关的知识呢?题为“兔子,人类”一章告诉你,不论是父母还是老师在这一点上都是靠不住的。
克里斯在读《圣经》时读到了“太监(eunuch)”一词时,问其父母,“什么是太监?”由于克里斯不熟悉“eunuch(太监)”,因此发音不准确。他母亲一方面说她不清楚,一方面用标准的发音纠正了克里斯,并让克里斯的父亲来回答。所以克里斯暗底里在想,“戏演得妙极了,纠正了发音,却又佯装无知。”正当克里斯的父亲要开口解释时,其母亲又立马抢过话题,用一本正经的口吻说:“……是一个阿比西亚佣人,对不对,亲爱的?”[2]22
学校生物课的教学计划里包括了“繁殖”一章,其主要内容是“植物、兔子、人类,”在学期临近结束时,“整个教学计划里只剩下两个词——兔子、人类——没有讲授,而课时也只剩下两节了。”[2]23
“下周,”洛松(生物老师)在剩下的最后两节课开头说,“我将开始复习……”
……全班同学都失望地低语开了。
“……但今天我将讲哺乳动物的繁殖。”寂静无声;同学中有一二人想到繁殖就会勃起……于是大家笔记记得异常勤快。他给我们讲了兔子的繁殖,部分是用拉丁语讲的。说实话,用拉丁语讲的效果完全不同……我们开始意识到,洛松将以此种方式敷衍我们了。我们越来越不满了。最后,只剩下一分钟时,他说:
“好,还有问题吗?”
“先生,我们什么时候上教学计划上写的人类繁殖?”
“啊,”他答道(口气中有一丝得意?),“人类繁殖与其他哺乳动物的繁殖原理是一样的。”说完,他趾高气昂地走出了教室[2]23。
不难看出,克里斯与他的同学们对“人类繁殖”的话题期待了一个学期,结果却是如此这般结束了!除了家里的父母与学校的老师外,相关信息与知识,特别是少年感兴趣的话题,“是很难通过正规渠道获得的,”[2] 23这应该是书中少年的成长烦恼吧?但谁又能说,这不是所有少年普遍存在的烦恼呢?当然,成长的烦恼远不止这些,还有当克里斯的哥哥初次带回女朋友的时候,他恨这个女朋友的一切,包括她的名字,但“最主要的,恨她是她。一个女孩,一种异样的存在物。”[2]64
少年有少年的烦恼,当这种烦恼到了青年时期也许就不一样了。克里斯在1968年21岁时,开始了与这种令他憎恨的“异样的存在物”进行交往。第二部分的第二章是全书中最长的一章,它详细讲述了克里斯如何闲荡在充满文学艺术气息的巴黎,又如何在法国国家图书馆里开始认识法国女孩安妮克,与她一起去喝酒、看电影,最后他竟然“亲吻了她!嗨,我亲吻了一个法国女孩!她喜欢我!”[2]93他反思着与安妮克的关系,比较着他正体验的情爱与以前在学校里时书本(如《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上读到的内容,深感书本中存在着很多误导信息。最后,他与安妮克的关系结束是因为3个英国朋友,特别是其中的女孩玛利安的出现。一次与玛利安的单独约会时,玛利安的几个问题引发了克里斯对自己感情生活的未来的思考。当他想把这些思考敞开在同居的法国女孩安妮克面前时,发现自己不知道如何开口表达,最后在“我喜欢你”一章里,克里斯面对安妮克既不敢公然提及英国女孩玛利安,而是用无性别指代的“一个英国朋友”,又不想让安妮克伤心,可又说不出“我爱你”,最后听他勉强挤出了“我喜欢你”几个字后,安妮克离他而去。玛利安的出现,预示着安妮克的离开成了必然与必需。当然小说很巧妙与含蓄地交待了克里斯与玛利安的心心相应:当克里斯准备离开巴黎时,他的3个英国朋友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在巴黎之行即将结束的时候,玛利安与克里斯已经有很好的默契:“玛利安笑了。我笑了。……我赞同地笑了。玛利安用笑回应着我。”[2]127
小说的第三部分主要关注的是婚姻,关注婚后的夫妻感情。30岁的克里斯已是个有妻儿的中年人,他作为一个“健康的英国白人,”满足于那种住在都市郊区的中产阶级生活。在他看来,“成人,总体就是一个舒适。”[2]133甚至,他觉得与妻子做爱后,是他“人生最幸福的时候。”[2]134当然,他的这种婚姻观与满足感并没有得到他的好朋友托尼的赞同。虽然少年时期,克里斯与托尼几乎形影不离,而且他们同样对虚伪与充满谎言的成人世界进行叛逆与嘲讽。而青年时两人便表现出了不同的追求。再到中年时,他们的婚恋观与人生观则更是大相径庭。
4 现代英国性
虽然巴恩斯戏仿了福楼拜的小说,但他讲述的是20世纪60到70年代的现代英国人的故事,因而贯穿于整个文本的是对现代英国人的生存状态、思想意识与生活态度的反思。
都市的地铁,几乎可以称为现代化过程中英国伦敦的象征。伦敦的地铁是世界上率先发展起来的,而伦敦地铁的四通八达反映了中产阶级的生活追求,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小说的书名“Metroland(地铁通达之处)”一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地产商与铁路公司采用的,他们用它将一些郊区地方,串连成了一个虚假的整体[2]34。小说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个“虚假的整体”区域里,而如同大多数居住在这条大都会铁路沿线的人们“……似乎都来自别的什么地方。大家被结实的房子、可靠的铁路设施及较好的花园泥土吸引过来。”[2]34可见,“地铁通达之处”一语充满着现代化过程中的英国中产阶级的生活追求!这些吸引着人们生活到地铁沿线的是结实的房子、便捷的交通及带着花园的宽敞的郊区住房,好一幅英国中产阶级的生活图景!当然,从“虚假的整体”一词就不难读出作者对这种生活图景的温和的批评。
作者的批评还透过2个少年的追求得以巧妙的传达。应该说,这种舒适的郊区生活景象并不是少年主人公与他的好朋友托尼所追求的,那是他们父母的追求。而这2个少年却喜欢人们都“来自别的什么地方”的那种“无根”状态,还深为这种“无根”状态骄傲,因为在这2个少年心中,这种“无根”与他们所推崇的现代派法国文学与艺术中的“游荡”意义相仿。克里斯曾说,“我们喜欢法国文学,主要是它充满着斗争精神。”[2]16为了具有这种“斗争精神”,克里斯“游荡”于伦敦的街头与艺术馆,后来还“游荡”于巴黎街头与艺术馆。克里斯最爱波德莱尔,被他哥哥在向他女朋友介绍时戏称为“克里斯·波德莱尔”,他在夏日度假时“带着波德莱尔的诗集到海滩上读。”[2]14本杰明在他的《波德莱尔》里看到波德莱尔的“诗里,中心形象就是一个永远不停下来的游荡者,”[3] 13少年克里斯与托尼会学着波德莱尔那样,甘愿做一名游荡者,甘愿选择波德莱尔式的现代人“游荡”的生存状态。
这种现代人“无根”与“游荡”与生活于“地铁通达之处”这个“虚假的整体”里的生活是完全不同的,故而形成鲜明的对比。然而,生活在英国较为保守的20世纪70年代的中年克里斯,却不得不为了家庭与妻儿,为了婚姻,做出妥协。于是,克里斯沾沾自喜地过起了一种让他青少年时所不屑的生活。对于少年的反叛与中年的妥协,作者巴恩斯不无机智而诙谐地说,“妥协就是成熟……我怀疑成熟的概念是靠不反抗这样的阴谋来维持的。”[2]134他接着写道:“成长难道不就是骑在反讽之虎的背上,而不至于被它掀翻在地?”[2]135
尽管妥协,主人公虽不再“无根”地“游荡”,却还是觉得那是一种充满“令人气愤的单调”的生活!克里斯看到,他的有些中学同学似乎很出色,也很成功,与他一样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但他感叹朋友们的成功故事都不过是“平庸的富足的老生常谈”[2]153!真是一语道出了一个人群——英国现代的中产阶级的真实生活境况!
有评论认为,巴恩斯的小说代言了英国中产阶级[10],笔者不能完全赞同。虽然巴恩斯写出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追求,正如主人公最后从巴黎返回到“地铁通达之处”安家、结婚生子、有了安稳的工作与富足的生活,一副“十足”的中产阶级的样子!但是,从“虚假的整体”到“平庸的富足”,从为“无根”而骄傲到追求“游荡”的状态,都感觉不出他在为这个阶层作代言,代言必须为其说话,为其辩护,而巴恩斯并没有为英国中产阶级的“平庸的富足”辩护,而是站在旁观的立场试图揭示出这个阶层的纠结与迷茫。
5 结 语
巴恩斯试图用他那支挥洒自如、收放有度、幽默诙谐、反讽与讽喻信手拈来的精妙之笔,戏仿福楼拜,借用兰波与波德莱尔,书写着主人公的少年叛逆,青年炽热,中年妥协,书写了“地铁通达之处”的“虚假的整体”中现代英国人的生活追求与追求后的迷茫,简言之,在对人生、时代与空间互动关系的思索与探寻中,书写出了一部现代英国版的“情感教育”。最后,借用作者本人对生命与艺术关系的思索来结束本文:“我梦想着找到融合艺术与生命的钥匙……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在哪里?它们是否如我们假定的那样可区分?一个生命可否是一个艺术作品;或者说,一个艺术作品是否是一种更高的生命形态?”[2]128
[1]陆建德.回忆中的“新乐音”[M]∥朱利安·巴恩斯.终结的感觉. 郭国良,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12:3.
[2]BARNES J. Metroland[M]. 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 1980.
[3]瞿世镜,任一鸣. 当代英国小说史[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4]王一平. 朱利安·巴恩斯小说与新历史主义:兼论曼布克奖获奖小说《终结的感觉》[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5(1): 94.
[5]BRADBURY M. 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1878-2001[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6]CHILDS P, GROSE S. Julian Barnes: Contemporary Critical Perspectives[M]. London: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11.
[7]GUIGNERY V, ROBERTS R. Conversation with Julian Barnes[M].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9.
[8]居斯塔夫·福楼拜. 情感教育[M].李健吾,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9]蒂费纳·萨莫瓦约. 互文性研究[M].邵炜,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10] 王一平. 朱利安·巴恩斯小说的当代“英国性”建构与书写模式[J].国外文学,2015(1):75.
Metroland: A modern English “sentimental education”
SHI Yafang, CHENG Y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Well accepted as it was after its publication in Britain, the first novelMetroland, by the acclaimed British writer Julian Barnes, is paid far less attention to than his other works in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in China. The authors of this thesis try to make a study of this modern British “sentimental education” through the perspectives of “sentimental education”, parodic structure and modern Englishness so as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Julian Barnes’s unique contempl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life, time and space in the novel.
Metroland; parodic structure; “sentimental education”; modern Englishness
10.3969/j.issn.1671-8798.2016.04.003
2016-02-26
石雅芳(1958—),女,江苏省昆山人,教授,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I106; I561.074
A
1671-8798(2016)04-026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