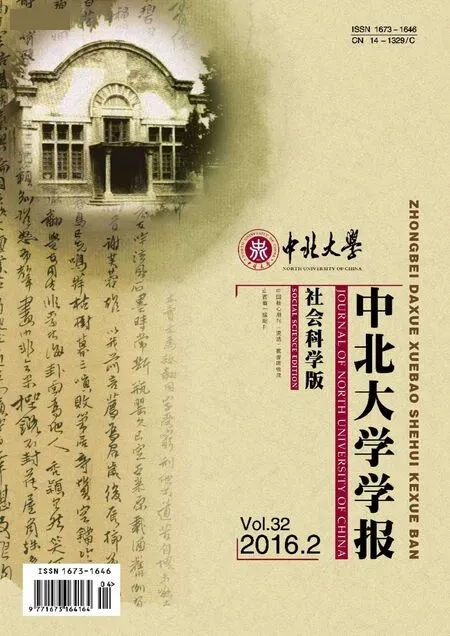莫言小说《生死疲劳》叙述技巧探析
李艳云
(大同大学 文学学院, 山西 大同 037009)
莫言小说《生死疲劳》叙述技巧探析
李艳云
(大同大学 文学学院, 山西 大同 037009)
小说《生死疲劳》叙述手法娴熟, 叙述技巧高超。 本文运用现代叙事学相关理论, 分析《生死疲劳》所运用的叙述技巧, 探求小说之所以取得较高艺术成就的内在原因。 在小说《生死疲劳》的叙述中, 轮回策略下叙述向度的呈现增强了小说的魔幻色彩, 拓展了小说的主题内蕴; 对话、 复调式的叙述结构增强了叙述的厚度与张力, 延伸了小说的叙述魅力; 视角越界现象的频繁出现又使得叙述话语不断延宕与伸展, 从而使得小说的解读充满了更多的可能性。
莫言; 《生死疲劳》; 叙述向度; 隐性越界
长篇小说《生死疲劳》创作于2005年, 是莫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小说一经发表, 评论界众声喧哗, 褒贬不一, 但是莫言在小说文本叙述方面的自我突破性, 是有目共睹的。 最终《生死疲劳》拿下了第二届“红楼梦奖”与第一届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 两个奖项的获得无疑是对《生死疲劳》创作成就的最好褒奖。 正如有的评论家所言:“莫言的《生死疲劳》肯定是一部非同凡响的作品, 莫言的叙述比以往作品更为自由, 无拘无束。”[1]可以说, 高超的叙述技巧是这部小说取得如此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文主要从叙述向度的选择, 对话、 复调式叙述方法的运用以及在小说中大量存在的叙述越界现象三方面探析《生死疲劳》的叙述技巧。
1 叙述向度——轮回策略下乡土历史经验的重构
乡土历史经验叙述是莫言叙述话语中重要的叙述向度, 与作者其他作品不同, 《生死疲劳》中乡土历史经验的传达, 主要通过佛家六道轮回的思想, 借助了动物视角进行传达。 这使得《生死疲劳》带上了浓郁的魔幻主义色彩。 从时间跨度来说, 《生死疲劳》主要依托于“土地改革” “大跃进时期”“文化大革命”“改革开发”这四个历史阶段进行线性时间建构, 文本时间横跨半个世纪。 不同时间阶段相应的文化语境, 赋予了小说中主人公们行动的原动力。
在线性逻辑叙述中, 主人公西门闹经过六世劫难的游历, 从一个血性的汉子退化为一个以女人头发为食、 脑袋奇大、 身材瘦小的大头儿, 凭着记忆, 借助人类的语言, 讲述着自己作为诸种动物眼中的那段历史。 在这段历史叙述中, 相对于各种动物, 人类形象是扁平、 暗淡的, 支配人类行动的除了生存本能, 更多的是各种政治口号的能指, 这种口号进而演绎为一种理想精神, 使每一位为之奋斗的西门金龙、 洪泰岳等人身上涂饰了一层崇高悲壮的色彩。 在物质稀缺的“土地改革”“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三个历史阶段, 形而下层面的吃喝拉撒、 生存与欲望却又挤压着“理想精神”, 因此作品中人类行动除了形而下层面的生存显得真诚、 真实以外, 其他的所有活动皆呈现为可笑的小丑式的表演。 倒是转世投胎的驴、 牛、 猪、 狗、 猴按照自己的本能生存, 依靠着骨子里西门闹式的倔强,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鲜活地演绎了自己——驴的倔强勇敢、 牛的坚守执着、 猪的酣畅与忠义、 狗的忠诚与机巧。 莫言这种叙述态度具有鲜明的批判立场——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 人何以为人, 又何以成其为人。 在这里, 佛家六道轮回思想的借用, 使得《生死疲劳》中动物视角叙述沿着叙述逻辑展开, 一方面小说文本因佛家思想增添了浓郁的东方美学气息, 高密东北乡的民间资源因动物拟人化的讲述更带有了原始的神秘气息; 另一方面跳脱出人类思维限制, 从动物视角审视人类, 人类生存的盲目性、 荒诞性尽得显现, 历史所谓的“庄严”与“神圣” 统统解构。
六道轮回思想本是佛教用来宣扬道德规训, 进行善恶劝诫的一种理论思想, 指的是生命体依据其前世善恶之行在天道、 人道、 阿修罗道、 畜牲道、 饿鬼道、 地狱这六道中进行生命的循环流转, 前三道为善道, 后三道为恶道。 其实质即“因果”的循环, 善因即善果, 恶因即恶果。 《生死疲劳》中西门闹虽经历了六次轮回, 但却只是在“畜牲道”的轮回。 小说文本中, 这种轮回策略的运用不仅为动物视角叙述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论说辞, 而且这一贯穿全篇的思想为我们进一步解读小说内蕴提供了可能性。 结构主义叙述学认为叙述性文学作品结构可以分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 表层结构按照作品的线性时间演绎人物及事件的存在义, 深层结构则从共时向度传达文本深层文化义。 历时向度上, 《生死疲劳》讲述了从1950年~2000年发生在以大栏镇为中心的高密东北乡的诸多历史事件, 以及在这些事件推动下蓝脸、 洪泰岳、 西门金龙、 蓝解放等人命运的发展, 揭示土改到改革开放后半个世纪间中国农村物质形态以及价值观、 伦理观等精神文化层面的变化, 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处在历史变动中人的精神样貌与心理流变过程。 作者在叙述中要传达的主题是: 历史向前发展, 农村整体经济社会结构也在向前发展, 但是相应的文化机制、 人的社会心理并未随之适应性的得以发展, 千百年来农耕文化的固有惰性得以展现。 西门闹一次次的转世, 由忠义的驴到供人娱乐取笑的猴子, 逐渐丧失主体性, 而最终失去话语权。 这样降序式的转世安排是别有用心的——农耕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的碰撞中, 人在物质欲望的追求中最终丧失自我。 小说安排了几乎所有重要人物的死亡, 留下蓝千岁与蓝解放似乎也只是出于需要借助两者完成叙述任务。 蓝千岁作为这个家族唯一的血脉, 且生于新世纪之初, 本应作为家族的未来与希望而存活的, 但在小说中, 蓝千岁更多是作为历史、 作为过去事件的亲历者而存在的。 故事时间终止在 2000年, 2000年之后发生了什么, 那就是大头儿在他五岁时讲了一个故事, 一切又回到小说开篇的1950年。 在这里莫言传达给我们一种历史的怪诞感: 一切发生过了的似乎又在重新开始。 正如有的研究者分析:“这部历史小说中, 存在着一种复合型叙事间形态 , 一是直线的历史时间, 一是循环的民间时间, 前者显, 后者隐, 但两者并非总是受到相同的强调。 后者是对前者的有力颠覆和消解, 颠覆了前者的持续进步的、 合目的性的、 不可逆转的发展的现代时间观念, 把前者的不可逆转的特性融入和消解到宇宙的永恒轮回之中, 使融合之后的时间感更加充实、 强劲。”[2]
这一叙述意义的传达, 可从文本的深层结构再作解读。 小说开篇莫言即语:“佛说: 生死疲劳, 从贪欲起。 少欲无为, 身心自在。”从共时角度来看, 小说主要介绍了西门闹死后的几度轮回, 这些轮回过程共有的特征就是生的轰轰烈烈与死的不甘、 沉寂与顺从。 反复的生与死之后, 西门闹内心的仇恨逐渐得以消解, 最终以大头儿云淡风清地似乎讲着别人的故事结尾。 很明显作家本欲要讲的是生命个体对生与死的无法选择, 无法规避。 欲要内心自由, 只能“少欲无为”。 小说中的人物与动物各自或主动或被动地承受着自己生存场域诸种欲望的调度与指挥, 忙碌地生存着, 又各自或不甘或顺从地死去。 这种忙乱的生死之中, 土地沉默地接纳着逝去的生命(一切来自土地的都将回归土地), 时间有条不紊循环式地映照着每个生命的生存(轮回叙述搭建的叙述主框架), 在这时空永恒之下, 个体生命的挣扎与抗争显得如此渺小、 可笑。 这种“存在主义”式的对生命存在的思考, 使得莫言的《生死疲劳》超越了其之前像《红高粱》《丰乳肥臀》这样的同样的对乡土历史经验传达的作品, 带有了更多的宗教色彩与哲理意味。 而这一叙述效果的实现, 无疑是得益于佛教六道轮回思想的运用。 在这里轮回策略已经自觉内化为小说的一种文体形式, 由此, “莫言在现世和轮回之间建立了互为注解的关系”[3]。
2 对话、 复调式叙述——叙述的厚度与张力
前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指出:“在艺术中, 意义完全不能脱离体现它的物体的一切细节。 文艺作品毫无例外都具有意义。 物质、 符号创造的本身, 在这里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4]15《生死疲劳》中的话语形式作为结构全文、 呈现意义的物质形式, 其存在样貌亦指向文本意义的传达。 小说内容共分为“驴折腾”“牛犟劲”“猪撒欢”“狗精神”“结局与开端”五部分, 由三位叙述者叙述完成。 其中, 主要叙述者为蓝千岁和蓝解放, 小说人物莫言为次要叙述者。 三位叙述者在叙述事件过程中, 叙述语言相互交叉、 补充甚至对立、 冲突, 从不同视角传达着各自对叙述内容的认知与评判, 并且在自我叙述与对方叙述语言中各自完成自我形象的建构。 不同叙述者对叙述事件的参与, 使得小说意义的多向度解读成为可能。
小说整体上呈现为一种对话结构——由蓝千岁与蓝解放看似一场无心的交谈完成。 在交谈过程中蓝千岁完成“驴折腾”“猪撒欢”的全部篇目和“狗精神”部分篇目内容的叙述, 蓝解放则完成“牛犟劲”的全部篇目和“狗精神”的另部分篇目的叙述。 在对话过程中, 由于人物内视角所限, 出于故事最终的完整性的考虑, 故事的“结局开端”部分, 作者安排由小说人物莫言完成。 在故事叙述过程中, 三位叙述者的声音是同时呈现的。 在蓝千岁的叙述中, 他常常停顿下来征询蓝解放对事件的认识、 评论, 或提及在事件过程中蓝解放的态度或转述蓝解放的话语; 而在蓝解放的叙述过程中, 他常常从自己的视角巧妙穿插蓝千岁为驴、 为牛、 为狗的前身的诸种表现, 补充映证式地完成西门闹死后的轮回形象; 而在两者交谈、 回忆的过程中又始终夹杂着另一位叙述者莫言的声音, 莫言的文学作品《黑驴记》《养猪记》《杏花烂漫》《撑杆跳月》等以知识分子语言模式嵌入到前两者的交谈回忆之中, 因此可以说小说人物莫言也是从始至终参与叙述的。 三位叙述者在叙述过程中, 各自依据对方的话语佐证自己话语的真实性, 却又在佐证过程中不断消解对方叙述的可靠性。 例如, 在蓝千岁的叙述中反复提及他为驴的日子里, 莫言的剧本《黑驴记》中的唱词和描述性语言与自己为驴经历的契合, 以及他为驴的神勇事迹被莫言写进了小说里的事实。 在讲述他轮回为猪、 狗经历了种种奇幻遭遇时, 他也常常以莫言的散文《养猪记》、 小说《撑杆挑月》《圆月》等来佐证自己的讲述与经历的真实性。 但在运用莫言文学作品佐证过程中, 他又反复强调莫言这个人物的圆滑与不可靠以及他文学作品对事实的偏离与虚构, 从而消解了叙述人之一莫言叙述的可靠性。 同时, 在叙述过程中, 蓝千岁又指出蓝解放因为年龄小对亲历事件没有留下深刻记忆, 或因为不在场没有亲自见证事件的发生, 因而对于这段时间此地发生的事件没有叙述权, 从而确立了自己在这两个篇目叙述中的绝对话语权。 正如在“猪撒欢”部分, 蓝千岁所说:“所以我是唯一的权威讲述者, 我说的就是历史, 我否认的就是伪历史。”
蓝解放对于“牛犟劲”的叙述则是完全从自己的视角以旁观者身份补叙蓝千岁为牛前身的经历, 对于“西门牛”外聚焦式的叙述, 客观印证了“西门牛”经历的真实性, 蓝解放指出蓝千岁因为多次轮回人世记忆丧失的事实, 从而确立起自己在这次叙述过程中叙述话语的真实性与权威性。 由此可见, 在整个叙述过程中, 三位叙述者的叙述都有其视角偏差, 都不能做到完全真实而客观。 主要叙述者蓝千岁的叙述, 因为借用动物视角完成, 因此主观色彩、 奇幻色彩强烈, 用人类思维难以判断其言说真伪。 蓝解放在整场叙述过程中, 所述内容有限, 且多作为不在场人物存在, 其叙述不足以支撑整场叙述的真实性。 而作为热衷于生活事件提炼加工的、 职业为作家的小说人物莫言, 其文学作品以及他在小说中的言行固然能够一定程度上佐证蓝千岁叙述话语的真实性, 但是鉴于其在蓝千岁、 蓝解放叙述中被描述的形象, 其叙述内容的真实性同样被大打折扣的。 而我们知道, 小说人物莫言实则指涉小说创作者本人莫言的, 在第五部分, 小说人物莫言以一个创作者的形象, 运用“读者诸君”的口吻, 交代了整部小说故事的结局与开端, 俨然一副整场叙述操纵者的样貌出现在读者面前。 特别是从小说的一个细节——小说人物莫言为蓝脸编撰的墓碑碑文“一切来自土地的都将回归土地”中, 我们甚至可以直接看到潜藏在其背后的作家本人。 莫言在小说中设置一个与自己同名且职业为作家的人物, 并将人物刻意打造成圆滑、 世故颇讨人嫌的形象, 有意让他的言行指涉自己, 其用意很显然是在引导读者对小说本身的阅读做出几分谨慎的质疑。
从故事本身的讲述到整场叙述的完成再到小说文本的创作, 莫言成功实现了自我解构, 完成了自己的叙述任务。 正如研究者指出《生死疲劳》一方面设置生死轮回架构以盛载历史命定的进程, 另一方面又反复对此架构进行深度的反讽, 正是为了显现出历史荒诞吊诡的本质。[5]对历史的解构通过对叙述的自我解构实现, 而叙述的解构依托的正是创作者在小说文本中设置的对话、 复调式话语结构。 “让每个人物展现出他的真实存在中的自我, 发出自己的声音……使主体和主体以生存、 生命的权利与名义发出话语, 使主体和主体之间形成生命的对话, 从而使作品进入复调的艺术境地。”[6]驴、 牛、 猪、 狗走出历史深处, 从自己的视角观察着人类的言行举止, 参与着人类历史的叙述构建, 这与小说人物莫言的诸多文学作品对同一事件的描述之间产生了奇妙关系——互相佐证又互相消解。 然而, 这些看似嘈杂的话语, 以及蓝千岁的统辖, 因着蓝千岁与蓝解放问答式、 倾听式的沟通又实现了某种统一性, 这种对峙与统一使得小说叙述充满了张力与多样解读性的审美魅力。
3 视角越界——叙述的展开、 延宕与回收
叙述性作品中, 叙述者总要站在一定立场、 位置进行讲述, 叙述者就叙述内容讲述、 观察的角度, 称为叙述视角。 叙述视角可分为“第一人称经验视角、 有限全知叙述、 摄像式外叙述、 全知叙述”[7]245-249, 前三种称为限制视角。 限制视角对叙述没有完全的操控权, 叙述过程中有其视角难以触及的叙述空间。 全知叙述则叙述者只要愿意, 完全可以对叙述进行全盘操控, 可以说没有叙述者不知道的事情, 除非其故意隐蔽。 在故事讲述过程中, 叙述者为了充分利用不同叙述视角的叙述优势, 高质量地完成一场叙述, 会不自觉地从限制视角跳脱到全知视角, 或从全知叙述转为限制叙述, 这就出现了视角越界现象。
《生死疲劳》叙述过程始终是跳脱的, 这不光表现为叙述者的反复转换, 还表现为叙述过程中, 视角越界现象的大量出现。
《生死疲劳》主要有三位叙述者——蓝千岁、 蓝解放、 莫言。 其中由蓝千岁叙述的部分又可裂变为以驴、 猪、 狗为叙述者的三部分独立叙述板块。 整体看来蓝千岁、 莫言叙述部分都兼有全知叙述与限制叙述两种叙述视角。 可以说蓝千岁作为一个单独叙述人进行叙述时, 叙述视角主要体现为全知视角。 而在这个经验主体以轮回方式进行裂变产生的以动物为叙述者的叙述板块中, 叙述视角又都是限制视角。 蓝解放叙述部分也属限制视角。
全知叙述的优越性在于其能够控制叙述进程, 保证叙述的流畅与完整, 能够轻易窥探人物内心, 详细交代事件的发展及原委。 一般来说, 叙述线索复杂, 人物角色众多, 篇幅较长的作品多采用此种叙述视角。 限制视角则侧重从某一角色或非角色人物视角进行叙述, 叙述者仅仅叙述自己所知道的与故事相关的部分。 此种叙述视角, 容易使读者对于人物角色产生认同感或者产生间离效果, 容易造成叙述空白, 引起读者的阅读快感。 《生死疲劳》文本时间跨度为半个世纪, 设计的人物角色有三十多个, 这样五十多万字的著作, 全知叙述模式才能保证其叙述的顺畅与完整, 这也是为什么小说选择以蓝千岁为主要叙述人, 而小说最后一部分又选择小说人物莫言以全知叙述模式对作品中主要的人物的结局展开讲述。 这一部分中开篇第一段写道:
“亲爱的读者诸君, 小说写到此处, 本该见好就收, 但书中的许多人物, 尚无最终结局, 而希望看到最终结局, 又是大多数读者的愿望。 那么, 就让我们的叙事主人公——蓝解放和大头儿——休息休息, 由我——他们的朋友莫言, 接着他们的话茬儿, 在这个堪称漫长的故事上, 再续上一个尾巴。”[8]513
讲述者以控制话语权的全知叙事模式出现, 并且在文中比较详尽地以第三人称的方式交代了人物在故事中的最终结局。 但是, 叙事过程中, 叙事者又反复以“我的朋友”“我们的开放”这种具有内聚集限制视角的叙事特征来称呼指称人物, 由此可见在这部分叙述过程中始终是伴随着视角越界现象的, 叙述者为了避免自己作为全知叙述者出现, 在叙述过程中还反复用“我猜想”等词语, 力图掩饰自己对故事的把控、 操纵。 但是对在私密空间中人物语言的直接引用, 对人物心理的猜想, 故事结局的最终安排又都暴露了叙述者实则是以“第一人称经验视角”进行全知视角叙述的。
大头儿的叙述主要是借用动物视角叙述完成的, 大头儿作为带着前世记忆且有超人记忆力的特殊个体, 其转世记忆为其成为全知叙述者提供了可能, 这种转世记忆使得不同动物视角下讲述的历史故事具有了衔接性, 而各种动物在感官上的各自优越性, 又使其能够讲述作为人类凭借外在感官无法触及的讲述空间, 而这部分空间在全知叙述模式下可以通过直接进入人物心理的方式获得, 但是在经验外限制叙述的模式下, 则无法展开。 如猪十六与狗小四凭借嗅觉的优势对主人内心情欲骚动的敏感探知, 从而在叙述中直达叙述对象的情欲空间展开探究, 而这一私密的空间, 从经验外限制视角讲述是无法深入触及的。 《生死疲劳》通过从动物视角展开的轮回记忆, 巧妙地实现了限制叙述模式下的全知叙述, 同时, 动物视角以及动物视角之后“西门闹”的人物视角, 使得被叙述人物及被讲述历史事件实现了双重聚焦, 历史呈现出别样的意味。
《生死疲劳》中还存在着不是源于叙述视角跳脱产生的视角越界现象, 在这里借用当代学者申丹在其论著《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中提到的“隐性越界”来指称这种现象。 申丹认为虽然小说人物未超出其叙述模式的视角所限, 但是其言论、 态度与其叙述身份相异时, 便可视为“隐性越界”[7]269-270。 小说中“大头儿”蓝千岁担当主要叙述人。 虽然小说叙述语言整体呈现为粗放式的非精英知识分子精细打磨的语言, 但是小说特定情景的安排, 人物心理的揣测, 主题内蕴的挖掘拓展, 依然能够见出蓝千岁这个主要叙述者借用的实际上依然是莫言这个以写作为生的知识分子的语言模式。 小说叙述者跳脱出自己的话语模式采用一种与自己身份相异的话语模式进行叙述, 很明显这正属于视角“隐性越界”现象。 特别是在小说“猪撒欢”部分中, 猪十六或时不时跳脱出以猪的身份叙述, 对作品中其他人物及其行为进行长篇大论, 刻意营造出狂欢与反讽的叙述效果; 或反复剖析自己的内心, 渲染自己为猪的身与为人的心之间的无奈与悲凉; 或全凭猪的本能欲望, 依靠掌控在自己手里的话语权, 刻意营造描绘出一个理想的猪类世界, 从而使得小说文本既充满了瑰丽想象, 多了几分浪漫主义色彩, 又直指现实, 具有了强烈的现实批判力度。 这样在小说作品语言的粗砺与文学内蕴的精细之间形成强大的审美张力, 而这种大气魄的叙述调度能力不可能由一个经过六世轮回磨砺了内心诸种仇恨, 且只有五岁的孩子完成, 很明显在其背后站着一位精于叙述的叙述人, 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小说人物莫言, 因为是他最后完成了小说叙述, 且在小说最后提到蓝千岁对蓝解放讲述自己的故事——“我的故事, 从1950年1月1日那天讲起……”, 而这句话又正好是小说开篇的第一句话, 也就是说小说人物莫言实则是见证了整场叙述过程的, 也是操控着整场叙述的。 莫言这个小说人物的安排是饶有意味的, 表面看来作者设置他的主要目的是借用“他”来完成一定的叙述任务, 但是细细品味小说, 又会发现小说人物莫言与作者本人和读者都形成了一定的对话关系, 他与作者之间建构与解构的关系, 他与读者解构与建构的关系, 作者通过他实现了自己叙述对读者的引导, 最终完成自己的叙述目的。 因为他对叙述的操控意味带有了创作者的性质, 小说也因为这样一个人物的安排意蕴更加深邃, 文本有了更多的解读空间。
法国学者罗兰·巴特指出:“一般作家写的是某种东西, 真正的作家就只是写, 区别全在于此。 真正的作家不是把我们带向他的作品之外, 而是为了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写作活动本身。”[9]115莫言的小说创作正是如此, 我们一方面看到了小说文本, 同时通过叙述技巧我们更清晰地看到叙述本身。 莫言在《生死疲劳》叙述技巧上新的探索, 使得其再次成为作家带有鲜明创作个性的又一部力作。
[1]陈晓明. 《生死疲劳》: 乡土中国的寓言化叙事[N]. 文学报, 2006-03-14(08).
[2]苗变丽. 论循环时间叙事的精神文化特质——解读莫言的《生死疲劳》[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4): 106-108.
[3]关峰. 《生死疲劳》: 莫言讲故事的民间写作[J].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2): 128-132.
[4][苏]巴赫金.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M]. 李辉凡, 张捷, 译.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89.
[5]吴耀宗. 轮回·暴力·反讽: 论莫言《生死疲劳》的荒涎叙事[J]. 东岳论丛, 2010(11): 73-78.
[6]张灵. 莫言小说中的“复调”与“对话”——莫言小说的肌理与结构特征研究[J]. 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0(3): 35-41.
[7]申丹.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8]莫言. 生死疲劳[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9][英]特伦斯·霍克斯. 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 瞿铁鹏,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On Narrative Skills ofFatigueLifeandDeathWritten by Mo Yan
LI Yanyun
(Institute of Literary, Datong University, Datong 037009, China)
The narrative skills of the novelFatigueLifeandDeathis superb and excellent. This paper uses the modern narrative theory to explore the internal reason why the novel gets high artistic achievement. In the novelFatigueLifeandDeath, the narrative dimension of reincarnation has strengthened the magical atmosphere and expanded the connotation of the theme. Narrative structure with polyphonic dialogue has enhanced the thickness and tension of narrative, and extended the narrative charm. Frequent cross-border perspectives also make discourse constantly delayed and extended, so that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novel is full of possibilities.
Mo Yan;FatigueLifeandDeath; narrative dimension; implicit cross-border perspectives
2015-10-20
李艳云(1979-), 女, 助教, 硕士, 从事专业: 文学理论与批评。
1673-1646(2016)02-0097-05
I207.42
A
10.3969/j.issn.1673-1646.2016.0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