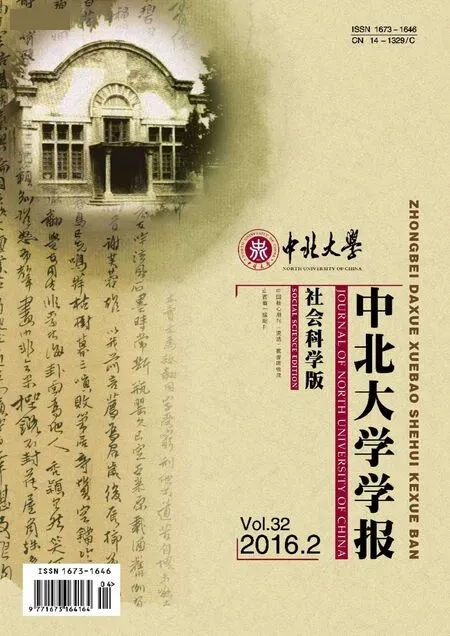墨子“非乐”思想新论
田宝祥
(首都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 北京 100048)
墨子“非乐”思想新论
田宝祥
(首都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 北京 100048)
作为百家争鸣时代的“世之显学”, 墨子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不可谓不深远。 梁启超说, 墨子是小基督, 也是大马克思。 墨子思想伟大的地方在于, 既被赋予了“天志”的道德律, 又有充分的形式逻辑可凭依, 这种二元一体的结构看似类宗教, 实则更靠近哲学之本, 也最能代表先秦诸子的理性气质。 在名实关系上, 墨子主张“名实合一”, 且认为实为第一性, 名为第二性, 无论抽象的知识还是审美的艺术, 都随客体之变化而变化, 具有充分的相对性。 墨子“非乐”, 正是建立在这种认识论的基础之上。 而今, 再论其“非乐”之思想, 不仅于先秦哲学之研究有意义, 于当下文艺形态之重构也有意义。
墨子; 《非乐上》; “风雅”之乐; “三表法”
1 官方之乐与私人之乐
知识分子对“乐”向来是极为敏感的。 《论语·述而》有云:“子在齐闻韶, 三月不知肉味, 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按照儒家的说法, 音乐作为一种精神层面的存在, 最大作用在于培养人的心智。 某种意义上讲, 孔子极力推崇“乐”, 乃是希望以个人的超越式审美对官方立场施加影响。 作为知识分子的儒者, 对于“乐”存有强烈的情感共鸣, 并无不妥; 可若是视听的对象换作百官, 那事态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 在墨子看来, 一官如此, 就有可能官官皆如此, 任此趋势发展下去, 国家昏乱不是不可能。
与孔子闻韶乐的痴迷状态不同, 庄子驾驭音乐的方式有些异常, 也有些超越。 《庄子·至乐》中载:“庄子妻死, 惠子吊之, 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以儒家的立场来看, 庄子的行为方式必然有违人伦。 可若从墨家的立场看, 则不然。 “鼓盆而歌”虽不合儒家之孝义体统, 却也减少了形式上的虚张声势。 庄子将对逝者的情感内化为生者的力量, 恰与西北农村吹唢呐吊唁亡亲的传统一样, 不铺陈、 不做作, 悲戚且令人动容。 可以说, 庄子的行为方式是对儒家纲常的一种挑战, “击缶而歌”也具有私人之乐的倾向性。
孔子编《诗》三百, 影响虽大, 但个人倾向明显, 不能代表周朝官方音乐的选择。 《诗经》中所呈现的诗, 按照现在的理解, 就是所谓的唱本、 歌词。 《诗经》中所对应的宫廷之“乐”, 名曰“雅”, 与之对应的民间音乐, 乃谓之“风”。 从篇目上讲, “风”多于“雅”, 占了《诗经》的一半以上, 但实质上, 作为“风”之受众的“农与工肆”, 并不具备编曲和记谱的能力, 民间之“风”也不得不以“雅”的演奏形式来表现。 而且, “雅”乐在音乐风格和表演曲目上, 对民间之“风”大力改造, 使之融于官方音乐的系统。 总之, 即使在百家争鸣的文化活跃期, 官方之乐作为君王意志的主要传播方式, 对整个社会仍具有恐怖的辐射作用。 墨子“非乐”, 可谓洞悉了浑噩表象下的这一真相。
2 《墨子·非乐上》的思想主题
关于音乐的社会功能, 《荀子·乐论》有云:“乐者, 圣人之所乐也, 而可以善民心, 其感人深, 其移风易俗, 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音乐, 不仅为圣人所推崇, 也为民众所喜爱, 一方面具有至情至性的道德之“善”, 另一方面具有改良社会、 净化风气之审美功能。 《乐论》篇还说道:“乐行而志清, 礼修而行成, 耳目聪明, 血气平和, 移风易俗, 天下皆宁。”荀子向来主张“人性本恶”, 在他看来, 音乐作为一剂情感传递的良药, 恰可以起到使民向善之作用。 继而通过“礼”的教化, 促使人的情感有效地发生变化, 最终影响和改善整个民族的性格和气质。
邢兆良先生在《墨子评传》中, 对“非乐”思想持基本否定的态度。 他认为:“人际关系的精神、 心态的平衡、 调节问题亦是人生存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音乐、 艺术等人类活动形式的产生和发展就是为了适应人类精神生产和心理调适的需要。 墨子‘非乐’, 只看到乐之不能实用生利, 并以音乐能移人性情、 荒废生产为由而非之, 而没有看到音乐是人情调试之必需。”[1]221所谓“非乐”, 不仅是批判, 更是反思。 探究“非乐”这一命题的思想性, 前提是准确地把握墨子所“非”之对象。 若是“非”的对象存在偏差, 那么结论的合理性就要大打折扣。 墨子“非乐”, 可能本质上并非反对音乐, 而是反对声色犬马的快乐主义, 反对纵欲主义和奢靡之风。 对此, 下文将从不同角度予以论证。
在思想主题上, 墨子的“非乐”论与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是异曲同工的, 它们都把矛头对准了统治意志强烈的官方音乐。 不同的是, 嵇康在于发明, 而墨子在于批评。 嵇康主观上认为, 情感之“哀”本身就构成了音乐, 它隐藏于人们的内心, 只是没有形成完整的旋律, 没有在恰当的时机生发出来。 而一旦那些外在的、 已然成熟的音乐传播进来, 造成一种听觉上的刺激, 人们的情感马上会被勾起, 达成一种情感上的共鸣。 换言之, 音乐乃人的一种天赋, 无论贫富贵贱, 生来素有, 后天也不该受意识形态左右。
墨子“非乐”不是基于个体, 而是立足现实。 他既反对意识形态化的官方音乐, 也漠视因情感需要而自由抒发的民间音乐, 更不愿为大众提供一种精神层面的抒发方式。 在对“乐”的评价上, 墨子是严苛的、 深切的, 尤其对于奢靡的宫廷雅乐, 墨子的态度十分坚决, 那就是零容忍、 拒不接受。 音乐不被提倡, 原因有二: 从“上”的角度而论, 无圣王的事迹可考; 从“下”的角度考虑, 不符合民众的利益。
墨子并非觉得琴瑟竽笙这样的乐器没用, 也并未说过大钟、 响鼓所发之声会毒害人心。 墨子“非乐”的直接动力, 来自于上流人物享于“乐”与劳苦大众忧于“生”的这一社会反差。 “非乐”的主要意义也在于反对快乐主义, 重建严肃、 智性的生活方式。 墨子认为, 音乐对人而言, 益处甚少, 应该克制, 而不是发扬。 人的价值更应该体现在思考和行动上, 哪怕其过程是艰辛而痛苦的, 也应该选择独自承受, 而非消极逃避, 追求一时欢愉和世俗乐趣。
3 《墨子·非乐上》的主要概念
《墨子·非乐上》开篇写道:“仁之事者, 必务求兴天下之利, 除天下之害, 将以为法乎天下, 利人乎即为, 不利人乎即止。”“仁之事者”一句, 文法上没问题, 但理解上有争议。 俞樾认为, 当作“仁人之所以为事者”之解较妥。 孙诒让大致认同, 但认为还不够清楚, 于是在《墨子间诂》里给出了“仁者之事”的明确解释。 这样, 在对《非乐上》一篇的论证上, 就有了第一个直接的对象, 即“仁者”。
孔子谈“仁”, 墨子也谈“仁”, 但二者在内涵上颇有差异。 孔子的“仁”, 更强调主体的德性和精神性, 在儒家看来, “仁”的基石是“亲亲”, 内容上对应的是“孝悌”。 墨子的“仁”, 更强调主体的智性和实践性, 内容上对应的是“义”。 在墨家那里, “仁”的根本是“兼爱”, 恰与儒家的“别爱”相对。 墨家从不排斥“亲亲”之爱, 它将父母兄弟之爱纳入到一个平行的空间系统里, 在这个系统里, 每一个对象都与自己构成一对“爱”的关系, 这一系统的最大特点就是平等性、 无等差性。 反之, 儒家的社会关系基本上呈现“金字塔状”“同心圆状”, 血亲关系始终处于系统的顶端和核心位置。 如果说孔子“爱有等差”的结构更有秩序性, 那么墨子“爱无等差”的观念则更有兼容性。 譬如, 一个陌路之人在孔子那里, 得到的第一道德反馈只能是“亲亲”二字, 而在墨子那里, 他可以获得“兼爱”的补偿, 也就是说, 无论他在世界的哪个角落, 都可以得到等同于其他人的极大幸福与满足。
孔子从不给“仁”一个准确的定义, 他在不同的场合、 针对不同的对象赋予“仁”不同的道德内涵。 而在墨子的思想系统里, 无论大家、 小家, 抑或君王、 百姓, 都有十分合理而有效的言行标准, 那就是“三表法”。 《墨子·非乐上》也有依据:“上考之, 不中圣王之事; 下度之, 不中万民之利。”此外, 墨子还直截了当地提出“是非与否”的根本准则, 那就是:“利人乎, 即为; 不利人乎, 即止。”可以说, “为乐, 非也”这一客观命题完全是基于该标准而提出的。
墨子思想有一组对立统一的核心范畴, 即“利”与“害”。 墨子用了一组实例, 来论证谁“利”谁“害”的问题。
其一, 从王公大人的角度, 欲得“大钟、 鸣鼓、 琴瑟、 竽笙之声”, 必先有大规模的精良乐器, 而乐器制作需要大量的物力和人力, 乐器运输需要船只和车辆, 完全就是一项“事乎国家、 敛乎万民”的浩大工程。 在墨子看来, 耗费如此大的精力, 只为满足少数人的一时欢愉, 很显然, 与“兴天下之利、 除天下之害”的要旨是背离的。 因而, “非乐”命题的提出, 既符合道德, 又合乎正义。
其二, 从百姓生计的角度, 心智聪颖、 体力充沛的成年人在君王意志的支配下, “击鸣鼓、 弹琴瑟、 吹竽笙而扬干戚”, 造成的负面影响有二: 一方面, 大量的青壮劳动力参与音乐表演, 而放弃社会劳动, 作为物质性的人, 连基本的饮食生活都得不到保证, 还谈什么个人价值、 人生理想。 另一方面, 宫廷之乐兴盛, 必然助长奢靡享乐之风, 整个国家若是沉浸在快乐、 自足的氛围而长久不能自拔, 一旦出现战争, 势必无丝毫还手之力。 到那时, “强劫弱、 众暴寡、 诈欺愚、 贵傲贱、 寇乱盗贼”之乱象丛生, 则不可禁止。
其三, 从心智养成的角度, 墨子从来都不是感性主义的颂扬者, 在先秦诸子中, 他是唯一一位主张“自苦”的大家。 这种“自苦”, 不仅是行为上的, 也是精神上的。 墨子认为, 人作为高级动物, 与“禽兽、 麋鹿、 蜚鸟、 贞虫”之类的区别在于, 兼有物质性与社会性。 《非乐上》有云:“赖其力者生, 不赖其力者不生。”“力”是墨子哲学的重要概念, 它的对立范畴并不是孟子的“气”, 从概念表达的准确性上, “君子不器”四字更为合适。 墨子认为, 个体不应该贪图享乐, 寻找生活体验的愉悦性, 而要依靠自己的“力”, 不断迎接生活的苦难, 最终完成生存的使命, 只有这样, 才配称为道德至上的“真君子”。
墨子对“力”的崇尚, 实质上是沿袭了夏禹的传统。 在墨子眼中, “力”所催生的一切社会生产, 才是人类绵延不绝的内因。 而诸如音乐、 舞蹈之类的艺术形式, 尤其是歌功颂德、 附庸君统的宫廷雅乐, 很大程度上是对带有神圣性的社会劳动的一种妨碍和伤害。
4 《墨子·非乐上》的“神道设教”
“神道设教”一语, 首见于《易·观》:“观天之神道, 而四时不忒, 圣人以神道设教, 而天下服矣。”关于“神道”二字, 《周易正义》的解释是:“微妙无方, 理不可知, 目不可见, 不知所以然而然。”简而言之, “神道设教”就是圣人以一种神秘主义的方式教化民众。
《非乐上》的逻辑结构十分清晰, 论证方式也十分合理。 最特别之处, 恰恰在于“神道设教”的部分。 首先, 墨子自设问题: 为什么“非乐”是一种合理的必然呢?然后遵循“三表法”中“上本之古者圣王之事”一则, 给出了先王之书《官刑》中的证例, “其恒舞于宫, 是谓巫风”。 在墨子看来, 对于违背圣王传统的行为, 要加以“君子出丝二卫, 小人否, 似二伯”的惩罚。 在经济上, 罚君子缴纳“二卫”, 小人加倍, 追罚二匹帛。 然后, 墨子又以《黄径》当中“舞佯佯”则“上帝不顺, 降之百殃, 其家必坏丧”一例, 树立起其“非乐”命题的权威性, 强调了这一原则的不可违逆。
墨子以“神道设教”的方式反对音乐, 并不表现为宗教意义上的有神信仰, 而是试图站在先代“圣人”的立场, 普及墨家的人文精神和道德情怀。 墨子“非乐”, 并不意味着墨子本人失去了审美的旨趣。 《非乐上》有云:“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 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竿笙之事, 以为不乐也; 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 以为不美也, 非以惨豢煎炙之味, 以为不甘也; 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 以为不安也。”可见, 墨子排斥一切纵情肆意、 附庸风雅的宫廷之乐, 对于流行于民间的“十五国风”, 墨子并不完全反对。
墨子“非乐”, 可以理解为是对孔子礼乐思想的一种反动, 但这绝不是“非乐”的终极目标。 受时局的影响, 人的物质欲望被无限放大的同时, 精神空虚也成为一种流行病, 在个体的意识当中蔓延开来。 在长期的鬼神崇拜之后, 音乐“娱乐”的对象也由神过渡到了人。 至此, 完全有理由断定, 墨子真正要反对的, 是冲动而世俗的快乐主义和个人享乐主义, 而非作为艺术审美的音乐本身。
5 墨子“非乐”论的价值导向
任继愈先生认为:“墨子未把批评的矛头指向王公贵族利用音乐艺术加重人民的负担上面, 而是指责音乐艺术本身, 这就本末倒置了。 照墨子的推论, 王公大人如果放弃他们对音乐艺术的享受, 就会留出更多的时间来, 把国家治理好, 这是没有依据的。”[2]47任继愈先生还说:“由于墨子不懂得音乐艺术的价值和作用, 不懂得音乐艺术的产生和创造是由于劳动和生活体验, 所以他对音乐艺术的观点是片面的。 他为了反对王公大人过分奢侈的生活, 连老百姓正当的艺术生活也要一并取消, 这未免因噎废食了。”[2]48然而事实恐不如此。 据《吕氏春秋·贵因》记载:“墨子见荆王, 锦衣吹笙, 因也。”《艺文类聚》卷四十四曾引《尸子》一语:“墨子吹笙, 墨子非乐, 而于乐有是也。”《礼记·祭统》中则明示:“墨翟者, 乐吏之贱者也。”以上史料充分说明, 墨子是懂音乐的, 即便不十分热爱, 也绝不至于断然诋毁。
墨子虽出生贫贱, 但凭借后天的习得, 不仅在学问知识上强于素人, 在音乐艺术上也颇有造诣。 至于“非乐”, 并不是盲目反对一切精神性的艺术创造, 而是一种有选择、 有针对的社会性批判。 对此, 杨俊光的观点则颇为中肯:“非乐是一种有原则的思想, 从墨子消费思想的总原则推衍而出的, 绝不是‘有激而发’或出于‘一时之所感触’。”[3]136薛柏成也认为:“若将其思想的合理性和局限性放在一个较为宽阔的视野中加以审视, 无疑具有丰富的内涵, 它是对社会功能的深层次思考。”[4]138
就狭义的文本而论, 墨子在《非乐》篇中没有展开对音乐的深层讨论是遗憾的, 也可以说是不足。[5]89-97但从史学的宏观角度来看, 墨子所推行的那种高于个体精神之上的群体行动主义, 显然要超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 既是激进的, 也是先进的。 虽然墨子“非乐”论所激发的思想浪花, 对于处于礼乐桎梏下的周朝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冲击, 但它隔空回应了当下这个时代的诸多文化乱象。 相信一旦生发, 足以发动一场拒绝靡靡之音的艺术革命, 对我们今日的文化建设反倒十分有益。
[1]邢兆良. 墨子评传[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2]任继愈. 墨子与墨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
[3]杨俊光. 墨子新论[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2.
[4]薛柏成. 墨子讲读[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5]曾繁仁. 评墨子“非乐论”美学思想[G]∥墨子研究论丛(4). 济南: 齐鲁出版社, 1998.
A New Argument for Mo-tse’s Anti-Music Thought
TIAN Baoxiang
(College of Political and Law,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As a famous school in the era of “letting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 Mo-tse’s thought has profound influences o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s Liang Qichao said, Mo-tse is Christian and also Marxian. The greatness of Mo-tse’s thought is not only endowed the moral law of the will of heaven, but also follows the formal logic adequately. This whole binary cultural structure seems to be religious, but in reality, it is closer to the soul of philosophy, and it best represents pre-Qin thinkers’ rational temperamen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istence and consciousness, Mo-tse advocates the unity of existence and consciousness, and he believes the existence is the primary qualities, and the consciousness is secondary. Both the abstract knowledge and aesthetic arts change with the variation of object. Mo-tse’s “anti-music” thought is built on the base of this epistemology. Nowadays, the research on Mo-tse’s “anti-music” thought is not only meaningful for the study of pre-Qin philosophy, but also significant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current literary form.
Mo-tse;Anti-MusicI; the music of “classic elegance”; “three meter method”
2015-10-16
2015年度首都师范大学学术创新与优秀学位论文培育计划项目: 墨子思想之源出研究
田宝祥(1989-), 男, 硕士生, 从事专业: 中国哲学。
1673-1646(2016)02-0026-04
B224
A
10.3969/j.issn.1673-1646.2016.02.006
——以《修身》篇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