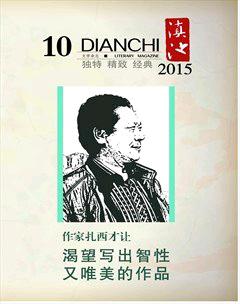作为画家的诗人
查尔斯·汤姆林森+文+马永波+译



查尔斯·汤姆林森(CharlesTomlinson),1927年生于英国特伦特河畔斯托克,他一开始想做画家,而不是诗人。但是诗歌占了上风,他的书名恰切的诗集《看见就是相信》问世于 1960年。实际上,它是与最初 1958年在美国出版的同一诗集略有不同的版本。汤姆林森对美国事物有种一直压抑着的兴趣,尤其是美国西南部的文化,他的选集《美国场景》(1960)和回忆录《一些美国人》(1980)就是证明。他忠诚以待的还有其他对象,他一直在作画、搞拼贴:它们带有各种影响的印记,如马克斯·恩斯特、乔治亚·奥基弗和赫克勒斯·塞格尔斯。他曾经写道,“1970年 6月18日对我是个发现的日子。”长久迷恋于奥斯卡·多明格兹的贴花法 1以及对建筑蔓藤图案的记忆,汤姆林森开始用贴花法制作一系列想象的风景。其中许多被收集在《黑与白:查尔斯·汤姆林森的图形艺术》(1976),诗人帕斯为这位用两种媒介工作的诗人写了评论。在思考一种艺术家关于另一种艺术家所写的评论时,汤姆林森说:“里尔克曾这样说到塞尚,‘在这些画中我辨认出了危机,因为我在自己的工作中也遇到了同样的危机。一些诗人与一些画家的联系引起了类似的挑战和认同感。他们的反应可能是准确的,也可能是极其片面的,就像布莱克之于雷诺兹,尼采之于德拉克罗瓦,罗森堡之于漩涡主义者。但是准确和片面都证明了这些关联的绝对必要性:他们现在都发誓要作出回应和解释,而历史不会等待。”
对于我今晚所要谈论的东西来说,“作为画家的诗人”不是一个完全恰当的题目。尽管我可以给你们读我的诗,我却不能给你们看我的画。我惟一能做的就是提醒大家,我的一本图画书《黑与白》问世了,由奥克塔维奥·帕斯作序,卡卡尼特出版社出版。也许你们中有人在今年早些时候甚至出席过我在剑桥诗歌节的展览。我将要谈论的主要是诗人和画家共同拥有的媒介。华莱士 ·斯蒂文斯说:“我们生活在一种有形诗歌的核心。”这当然是基本的事实,这个事实会促使一个诗人想要去画画,或者是如果他不能画画,他就会去领会画家对待他们共同拥有的有形诗歌的方式。正是因为“生活在一种有形诗歌的核心”这个同样的基本事实,塞缪·帕尔默的追随者,爱德华·卡尔弗特,能够写出“一首好诗,无论是写的还是画的”。斯蒂文斯说:“在很大程度上,诗人的问题就是画家的问题,诗人必须经常地转向绘画的文学,来讨论他们自己的问题。 ”你可以对斯蒂文斯的这句话加以补充,诗人不仅转向绘画的文学,而且帮助创造了那种文学。斯蒂文斯《遗作》的题词采用了格雷汉姆·贝尔论塞尚的完整的一段话,斯蒂文斯曾经令人难忘地对这位画家做过不止一次的评论。除了斯蒂文斯之外,里尔克、D.H.劳伦斯、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都写过有关塞尚的富于洞察的文章。这些人都发现,当他们在自己的艺术中与先入之见和主观性作斗争的时候,这位画家身上反映
了他们自己作为作家所存在的问题。里尔克说:“在这些画中我辨认出了危机,因为我在自己的工作中也遇到了同样的危机。”D.H.劳伦斯说:“在找苹果的时候,塞尚在颜料中感觉到了它。他突然感觉到了思想的暴政,处于它自我绘制的蓝色天堂里的封闭的自我。”而威廉斯说:“塞尚——艺术中惟一的现实主义是想象。只有这样,作品才能逃脱对自然的抄袭而成为一种创造。”就这样,塞尚巨人般地赫然出现在文学和绘画之上,成了一种新感性和新发明的先驱。确实,塞尚从另一个方向穿越了诗人和画家之间的公共领域——他自己写了很多的诗歌。在他年轻的时候,他这样写到:
一棵树,被狂风摇撼, 在空气中摇摆,像一个巨大的尸体, 干冷的西北风摇晃着它赤裸的枝条。
在老年的时候,他在一幅惊人的水彩画中成功地实现了这个想象,画的标题为《风的愤怒中的裸树》。无论最后的产品是什么,出发点都是一样的:“我们生活在一种有形诗歌的核心。”
我将返回到塞尚和他对诗歌的意义上来。但是,首先,让我给我的演讲增加个题目,一个副标题,这能让我探索斯蒂文斯所说的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有形诗歌的核心。我的副标题是“四元素”,而我所探索的地方,是我的出生地波特里斯 2。能最为持久地触动一个正在成长为艺术家的孩子的想象的元素,是水。那个烟雾腾腾、房屋黝黑、熔渣成堆、矿渣铺路、井口密布、钢厂林立的地区,拥有一整套运河网络作为它的动脉。运河把用于洗礼的元素带回了白天是炼狱、晚上是地狱的风景之中。运河不仅把水引进了那个地方,根据阿诺德·伯内特的说法,那里的大气层黑如污泥。一定不要忘记那些挖掘做瓷器用的泥灰土所留下的巨大池塘:当这些坑塘逐渐被废弃的时候,自然重新侵入进来,绿色出现在水边,坑里还出现了鱼。鱼!正是它们的存在,不仅仅是在泥灰土池塘中,而且在运河里,有助于把沉思带回在矿山和工厂的喧嚣中消磨的生活。钓鱼俱乐部,星期天比赛,长时间地观察涟漪和水的变化,从这一切中产生了某种既明智又神秘的东西。为什么是神秘的?因为钓鱼者如果不仅仅是偶尔涉猎,他就必须获得有关鱼和水的直觉知识,在他的静止中,在他等待和沉思的能力中,
存在着一种准备在精确时刻发出一击的感觉,这种感觉甚至会知道,如何把他全神贯注的水面下甚至看不见的生物引诱到它的精神轨道上去。正如沃尔顿 3所知,捕鱼者是艺术家。他保持自律,从自身向外注视,同时他内在的能力保持着高度清醒,如果他有潜能,这些就能把他造就成诗人或画家。
关于水就说这些。在同样的童年中,土和火又是什么角色呢?伯内特说:“波特里斯地区包括了火与纯净、贫瘠土地的神秘传统。”他的意思当然是指火对制陶黏土的作用。我自己想得最多的有关火的有形诗歌的经验更多地与炼钢有关,胜过了制陶。那主要是夜晚的火的经验。夜晚当炉子被拍响,或是当熔化的金属被倾进炼钢厂巨大的敞篷屋,巨大炫目的火柱喷射出来,反射在附近运河的水面上。所以,我记忆中的经验也是与水有关的火,不是作为水的对立面的火,而是与水混合在一起的火,它在那种元素和观者的心里点燃了沉思与回忆。去看也就是从内部去看。
这种经验是你沿着乔赛亚·韦奇伍德 18世纪所建工厂外面的运河而行时得到的,他把这个地方命名为埃特鲁里亚。你继续沿运河而行,直到运河穿过谢尔顿钢铁厂的中心。你是夜里去的,这样就不会被人发现,因为那里是特别不欢迎孩子的。埃特鲁里亚,全名是埃特鲁里亚山谷,久已失去了与这个名字相关的水泽仙女的踪影。但是红色的喷射物和火焰在熔化的钢铁、倒映在运河里的炉子中闪耀着,使你遭遇到一种原始而基本的感觉,与水泽仙女在与风景的关联中被作为象征相类似。而且,关键在于,一旦你的眼睛被这更为强烈的赤裸性所打开,树神就仅仅成了你和一棵树之间的面纱。因为,随着煤烟穿过黑暗向你的头发飘落,你会将火体验为水的本质。
土,和空气一样,在这个地区十分稀少。“它的大气层黑如污泥”:这是伯内特的判断。土,和空气一样,染上了黑色调。土地越发贫瘠,不仅仅因为制陶,还有熔渣堆和煤渣路。于是,园丁们从满是煤烟的命运中压榨出奇迹,给曾经繁茂葱绿的埃特鲁里亚的山坡戴上了冠冕。至于空气——空气是类似笑话的东西。本地明信片上画着瓶形的炉子和工厂烟囱,都在同时冒着烟,还有黑色的房子,也许还有一座黄褐色的教堂塔楼。这些明信片带有斯多葛式的标题,如“来自波特里斯的清新空气”。在学校,当波特里斯的炉子燃起的时候,有时很难看清操场的另一边。那个时代的一个熟悉的意象就是黑烟从工厂烟囱里升起来,被风捉住,穿过空气慢慢消散。在那里,空气是必须被创造出来的一个元素。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空气和水的追寻,吸引那些钓鱼俱乐部成员跑到周围的乡村,沿着那些运河而行,仿佛它们是返回伊甸园的道路一样。
所以,在四元素中,是水捉住了正在成长为艺术家的儿童的想象——带有火的色调的水,许诺着一个清洁、想象的洗礼,摇荡着、旋转着,充满了变化。
我在 20年代初期离开了那里,随后在许多风景中居住过,有城市的也有乡村的——伦敦、意大利、新墨西哥、美国北方、科茨沃尔德。我认为是意大利的利吉里亚区和托斯卡纳区以及后来的格洛斯特郡教会了我一个男人如何以一种风景为家。为了安置好那些更早的都市经验,这种看待事物的不同视域有多么必要。那些都市经验威胁着要把你封闭,把你和一个更为宽广更为明亮的世界隔开,与直觉隔开,埃兹拉·庞德称这种直觉为“灿烂的世界,其中一个思想以清晰的边缘切入另一个思想,一个移动着的能量世界,取得形式的磁力世界……”我想在诗歌中发现那个“灿烂的世界”,这么做使我似乎失去了与英格兰中部地区的联系。但是英格兰中部地区始终作为一种辩证逻辑而存在,作为一种对完美的要求而存在,这种完美在潜意识中逼迫着一个人的艺术形式,甚至要求着两种艺术,以便使可见世界的天堂一面能够得到拯救,得到赞美。
几乎在三十年后我才回到了波特里斯,我明白了我的诗歌世界有多么依赖于这个地方,尽管事实上它们企图发现一个清晰的世界,一个没有雾蒙蒙感觉的世界,一种伊甸园式的清新直觉和清晰知觉。我试图把这全部的历史浓缩在一首题为《泥灰土坑》的短诗中:
我寻求水、光和空气的语言
来谈论摆脱了一个世界的我自己
它坦然的昏睡似乎是一种回答
回答那堵塞了的地平线和街道
在单调的烟气中,在一朵灰色之花
中。 我发现了我的语言。岁月返回 告诉我所有被风干和被囚禁的事物: 我呼吸着熟悉的、有沉积物的空气 从一片被掏去内脏的风景, 黏土中未被发掘出的地下世界。 挖掘灰泥,他们挖掘出第二个自然 而水,渗上来充满了他们的矿坑, 把它们弥漫成闪烁明灭的湖泊 在尖顶和尖塔,街道和垃圾之间 在缓慢的驯服中,微光闪耀,平衡, 仿佛燃烧的伊甸园收回了它的损失 而词语和水来自那同样的源泉。
我的“水的精神分析”(借用加斯东
·巴什拉的术语),能够表明一种激励人心的洞察吗?将诗人和画家的态度联合起来的知觉和直觉的幸福结合吗?沉思着这个问题,我回想起一首早期的诗,《海的变化》,它试图以一系列形象捕捉住水的本质——这一次是海——“不安的大理石”,“绿色的丝绸”,“蓝色的泥浆”,然后被迫承认它们是不恰当不胜任的:它们就像
白酒
漂浮在毛玻璃的托盘中
在一个雕花玻璃的基座上:
一个静态的瞬间,因此不真实。
很久以后——二十年之后——在形式上复杂得多的《在杰纳哥湖游泳》一诗中,我观察到一个泳者在观察水。这里是从开头部分截取的片段:
冬天不久将阻止这个游泳者。 他阅读着水的秋天的犹豫 许许多多的方式:它被震动, 它已经波动起来,尽管平稳, 那里,最初的树叶 在晨风最初的颤抖中落下 先于他,把它们的印痕 以重叠的同心圆向外扩散。 存在着一种水的几何学,因为它 把云彩多余的部分划分成方格 让它们漂进下面的大气层中 所有的角和延长线:每一棵树 都像是柏树,在那里展开 每一丛展示出季节的灌木 都是一束火焰。它是一种几何学 不是扭曲的形式的幻想曲, 每次清澈的变化都对主题负责 在演奏之前,它匆忙离开: 它是一种坚持,搏动之流的谷粒……
我沉思着这个片段,还有更早的那首《海的变化》,为了发现支配我作为诗歌和画家的态度的常量。以此为基础的诗歌——比如我所写的众多风景诗——是对瞬息即逝的视觉印象的揭示和观察;它们竭力捕捉这种短暂的清新感,并把它统一成稳定的形式,以便其他人分享;这样的诗歌把目光从纯粹的个人移开。绘画也是如此,那里,外部世界的存在被强烈地感觉到,那里,画家关心的是(引用里尔克论塞尚的话)“将世界化身为有说服力的物,通过他对客体的经验,让一种对真实的描绘变得不朽”。为了使水的真实变得不朽!画家必须获得巨大的形式能力才能达到:因
为他观察的是水,是水所代表的变动不居的感知世界,是时间的心脏。
塞尚自己对画家的这个问题十分清楚——如何调和感觉和形式,而又不使你的画被迫成为一种故意的统一,以牺牲真实为代价的个性对关系的胜利:“没有任何一种关联是过于松散的,”乔基姆·加斯奎特这样汇报过塞尚的话,“也没有一个裂缝能让情感、光、真实从中逃逸……我们所看见的一切都在消散和消失;不是这样吗?自然还是同一个自然,但它什么都没有留下,没有什么显现在我们眼前。我们的艺术应该把持久的光亮赋予众元素,它所有变化的外观。它应该让我们永远地领略到它……我的画布与双手联合……但如果我感到有些微的分心,些微的软弱,尤其是如果有一天我解释得太多……如果我去进行干预,那就是一切消失的原因。”
早在我读到塞尚与加斯奎特的那个对话之前,我写了一首题为《塞尚在艾克斯》,一种我想要我的诗歌接受塞尚的知觉伦理的宣言,这种伦理不相信浪漫主义艺术中泛滥的个性的戏剧,按照这种伦理,凭借信任感觉,我们能进入存在,经验到它原始的完美:
而山:每一天
都像果实一样静止。又不像
——因为不能缩减,因为
既没有一个成分
因为珍贵而可疑,
也没有(像模特一样)
因自己的姿势而分心,并因此, 受到加倍的怀疑:它的姿势
不是摆好的。它本来如此。天然
不可改变,一个石头的桥头堡
对于它是实在的
因为以前没有感觉到。
在它风吹雨打的重量中
在它的寂静中,沉默着一个
没有表现自身的存在。
塞尚打动我的地方,也是我在更为卑微的层次上要求于诗歌的,是对自我关注的彻底消除。D.H.劳伦斯说:“塞尚的苹果是使苹果在自己独立的实体中存在的一种真正的尝试,没有用个人感情来渗透它。”塞尚一定感觉到了劳伦斯这里所指的“个人感情”的那种狭隘化的诱惑。塞尚自己受到了误解、忽略、疾病和忧郁的威胁。如果他选择了忽略自然,或仅仅是将自我戏剧化并强加给自然,他的绘画将缺乏我们所发现的地中海的自由与灿烂。甚至他的自画像也会缺乏内省。里尔克再一次提供了经典的评论。他写信给自己的妻子说:“……他目光的客观性是多么伟大和诚实,它被周围环境以一种几乎感人的方式所证实,没有分析,也没有从一个优越的立场出发,最为疏远地对待他的表达,他以如此谦卑的客观复制了自己,以一条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的狗的轻信、外在兴趣和专注,他在想:哦,那里有另一条狗。”
在谈到塞尚诚实的客观性时,很清楚,里尔克不是在思考 19世纪实证科学纯想象的、过时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假定观察者和观察对象之间是完全分开的。里尔克归结到塞尚身上的客观性意味着一种向外的目光,它将把感官世界拉近内在的人,它将缩小抽象和感觉、智力和事物之间的缝隙。正如梅洛·庞蒂在他杰出的论文《眼和脑》中所沉思的,这篇文章以引用加斯奎特论塞尚的书中的句子开头:“品质、光、色彩、深度摆在我们面前,它们存在的惟一理由是它们在我们的身体里唤醒了一种回声,因为身体欢迎它们……事物在我的内部有一种内在对应;它们在我内部激起了有关其存在的一种尘世的公式。”
梅洛·庞蒂就说到这里。我想获得把塞尚的艺术伦理用做诗歌基础的权利,我相信这能让我从自然风景转向城市风景。对我来说,它似乎是一种宗教,把事物引领到原始的光中,甚至是一种方式,用来衡量我们的城市从丰富的悲剧性堕落。但是让我做一个表白。作为画家,我无法发现使用这笔遗产的直接方式。我面临四个元素,而我惟一可以在绘画中解决它们的方式是强行将其结合起来,去干预它们,以焦虑的黑色轮廓为形式,把个人压力施加到我的形式上。有时,我会接近某种实现,但却用黑色损害了它。我找不到办法摆脱现成建议,避免过于自觉的头脑和手的先入之见,恰似我童年时工厂烟囱的变黑的自然使它变黑。黑色成了困扰我的东西。尽管我继续画画,但我一点点地与绘画疏远了,部分原因是这种无法解决的困境的压力,部分是因为到了想办法谋生的时候了。十五年来我几乎就是在写诗,然后,到了 1970年,在一段复苏的、集中绘画时期之后,一种解决办法几乎是偶然出现了。
我再一次想起华莱士·斯蒂文斯,他的一则《箴言》所说的:“对大地各方面的关注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是偶然的,就像光、色彩或形象。 ”这里的“偶然”我认为他指的是艺术的偶然性——你有可能在一个沉闷的街角、一双旧鞋、完全没有预期和表面上没有关联的偶然联系中发现最深的意义。事物突然紧密结合起来——用塞尚的话说,画布与手联合起来了。引用斯蒂文斯的另一句箴言来讲,你不再强加什么,而是去发现。而你的发现表面上是偶然的。但何为偶然?如果你接受了它,它难道就不再是偶然的了吗?
有助于我解决作为画家的问题的偶然因素是被称为贴花法的超现实主义手法。简单地说,这个药方是奥斯卡·多明格兹于 1936年开出来的:“使用一把粗刷子,把或多或少稀释过的黑色水粉颜料涂在一张平滑白纸上,马上用另一张纸盖上,施加平均的压力。然后毫不犹豫地把盖上的这张纸揭起来。”这个过程的结果是把颜料分离成随机的图案,有时可能会浪费很多纸,偶尔会得到非常美的完整形象,有时是有趣的片段,能激发你的想象将之组合进一幅图画。你可以用画刷改变所得到的东西,也可以用剪刀和糨糊来改变和重组你的形象,制作成一个拼贴。这种技术的弱点在于它会导致对想象的动物的一种松散幻想,或者是正在变成自行车的狮子。它的力量潜藏在它对心理定势构成的挑战中,在于材料提供给你的、你必须对之作出回应的那种非个人性。一种非常塞尚化的任务,也是我所谓的塞尚的伦理——服从给定的一切,努力打破先入为主的形象,捕捉并固定瞬间的显现——这种伦理一旦实施,就能引导你的贴花法远离幻想的随心所欲,朝向新知觉的门槛。
我忠实地遵循多明格兹的做法:敷涂黑色的水粉颜料。马克斯·恩斯特把这种技术用做他最好的一些绘画的基础,清晰地使用若干种色彩。几乎是盲目地,我求助于我的宿敌——黑色。我继续使用它,并且仅仅使用那一种颜色。第一步是把黑色涂在潮湿的纸上,你最先看见的是一笔笔颜料消散在水中,就像童年时代的烟雾消散在空气中一样。这两种经验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奇异的对应。当我把纸一张张揭开,改变,擦去,用画刷涂抹,用指尖刮,把片段串起来,切开和重新组合,我看见黑色变得令人目眩;我看见了水的微弱闪光,纯粹是偶然形成的光和空气;我明白了我现在又是同时作为诗人和画家在工作了。
“纯粹的”偶然!两者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偶然”(chance)和“舞蹈”(dance)押韵的事实对于诗人或画家都是一个有营养的思想。就像另一个偶然事件一样,在英格兰南部,它们的发音是“darnce”和“charnce”,这一直让中部的人惊奇,而对于南方人却属平常。为什么这两个词应该有很大关联,似乎没有内在的原因。同样,用刷子敷涂的颜料,沾上颜料的手指的指指戳戳,潦草的一笔,画出的线和点,为什么会与一张面孔、一片风景、一块石头或颅骨有很大关联,这里面似乎也不存在内在的原因。透纳留了一副很长的鹰爪样的指甲,为了在他的水彩画中挠搔出光的效果来。对水彩画纸表面的这些刺戳最后会代表光,这似乎是奇怪的偶然。
“偶然”与“舞蹈”确凿无疑的押韵以及对此事实的沉思激发了这样的思想:偶然的事件、偶然的遇合侵入了我们日常的一切,将它们拖入一种模式之中,当它们与我们对自身的感觉交叉,当它们使我们想起其他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强化我们对未来可能性的感觉。诗歌也与此非常相似。诗歌的发生仿佛是非常偶然的——比如说,一个标题,出乎意料地要求有一首诗与之伴随,一个“押韵的偶然”这样的题目,而你发现自己在信封的背面写下了这样的句子:
押韵的偶然就像相遇的偶然——
在偶然中寻找着,可一旦发现,就连接起来……
就这样,你已经开始把那些偶然紧密编织起来,用“寻找”和“连接”强化了模式,先于押韵的偶然变成思想的连续性之前,你继续写到:
接受偶然,就像押韵一样 是人性的,但是在偶然和顽固者之间 (一个半韵)出现了舞蹈,警觉 和环境……
是的,那是有意义的。那意义似乎源自什么地方:词语中的模式,思想中的模式,每句诗大多设置四个重读的模式,有时发展到五个重读,又大多会跳回到四个。处理这样的韵律似乎是一件合乎人性的事情:你的重复从来不会恰当熟练到纯粹像机械一样,你的派生也从不会芜杂到纯粹像植物的蔓延一样。一种人的尺度,被意外、费解和不可知的事物所环绕,但总是重申着自己的权威,这可能是一个有益的目标——在其中韵律和声调结合在一起——像我们那样经常要面临夸大和过高估价自我主张的诱惑:
押韵的偶然
押韵的偶然就像相遇的偶然——
在偶然中寻找着,可一旦发现,就连接起来:
它们说,它们示意,它们继续,而继续
并不意味着成功,而是向前的一条道
路即便地图上没有,也是一种如实而非
庄严的连续;尽管庄严(也许)是形容词或者一个
地区我们,自然的特权阶层,被引入其
中。是的。我们被引领,尽管我们似乎是
主动 穿过一片美丽的树林,一片阿登高地 (它和伊甸押韵)——野兽的繁殖地 它没有自然野蛮,而且比自然更忠诚 更有传奇性。可为什么我们要谈论 艺术,生活,仿佛艺术是形式 而生活是风云变幻?我还认为, 我们应该局限于克鲁或者莫乔普地区, 所有那些把艺术的偶然性 混同于仅仅在四肢末端 遇见的东西的人,会把韵脚 缩减成绳子的末端,一根草 被我们纵身经过时瞥见和抓住—— 为了一个被延误的希望而充满乡愁。 接受偶然,就像押韵一样 是人性的,但是在偶然和顽固者之间 (一个半韵)出现了舞蹈,警觉 和环境(指的是当你在那里时, 你之外存在的一切)。 而在安歇和悬崖之间, 惯性和错乱之间,出现了多样性增加,出租,释放(在两种意义
上); 还有惰性物质的浸入,转变, 那就是,变成与混乱对抗的能量。
让韵律成为我的结论。
如果你喜欢的话,绘画会唤醒你的手,带动你肌肉的协调感,你身体的感觉。诗歌也是如此,当它围绕着它的重音旋转,当它越过行末向前,或者是在行中逐渐休止,诗歌也把整个人带进游戏之中,和他自身的身体感觉之中。但是在绘画中,不存在近似的、实际的对等物,对等于由句子的长度、句中和句末停顿所调节的声调和节奏。没有任何近似对等物的原因在于媒介是如此不同。你可以用铅笔写作,可一旦你用它来画画,它所留下的痕迹所服务的目的就是多么不同。但是偶然因素仍然存在——遇见你没有预想到的事物、不是你自身的事物。而一旦你专心于它,你看见的一切都开始对它自己松弛的自满构成一种有趣的挑战。例如,你非常偶然地发现,在一片海滩上,有一只海鸟的颅骨。你可以把它放在橱里,或是把它忘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可是相反,你把它画了下来。当眼睛和铅笔试图彼此跟上,你开始对那特殊的颅骨结构了解得更多了。
但是,还有很多你无法知道的东西——它内部的神秘黑暗,有趣的不能通过的洞和沟槽,什么东西烂掉后留下的干净的空洞。颅骨的干净和自然的几何学提示你用自己的几何学把它围绕起来——用仔细控制的线条把颅骨送入、扩展、镶嵌在一个力的对比线条的宇宙中。正如与思想共舞的韵律引领你穿过一个人的价值世界,颅骨和线条也建立并向外进入一个包容的宇宙。
现在,有关这个颅骨存在某种非常顽固的东西,你觉得可以在上面刻一首小诗,它也许叫做《刻在鸬鹚的颅骨上》。这么做你就必须既粗暴又小心地对待它 ——
……锐利得像大海一样
将这个头颅
掏空和剥皮,并保留了
它脆弱的尖锐。
于是你继续写了一首完整的诗:
穿过薄薄的
正面,这布满
薄膜的脑袋:
狭窄,接受
分隔目光的
斜坡,那里
刚刚出现的鸟嘴
准备飞行
在一种依然
完美的突出中:
这里,你的镜子
必须保持稳定
你粗大的针
沉默着再次倾斜
但却锐利得像大海一样
将这个头颅
掏空和剥皮,并保留了
它脆弱的尖锐。
于是,一首诗就这样从这发现中诞生,绘画也是如此。但是那内部的黑暗仍继续困扰着你。你想想,我怎么能把它和我的句子围绕它编织起的小宇宙联系起来?
这个特殊问题的解决是凭借遗忘。或者是凭借表面上的遗忘和从事其他事情。画完《长嘴的颅骨》的三年后,我做了贴花法拼贴《动物的睡眠》:两只颅骨梦见一个有鸟兽正在穿越的风景。这个梦明确表现了黑暗。我试图让每个颅骨都暗示一个完整的世界。它暗示着这种睡眠也许就是死亡,其中脑袋和自然是一体的。
在写诗的时候,你有时搁浅在沉默上,有时需要数月或数年时间你才能明白你希望说些什么。同时,你半清醒地把问题翻了过去,同时加强你对媒介的认识。在《长嘴的颅骨》和《动物的睡眠》当中我所使用的技巧,是我上面描述过的拼贴和贴花法。我突然看见某种很像(尽管不是非常像)两只颅骨的东西融入了我的贴花法风景中,我乱糟糟碾碎的漂浮在水中的颜料中。纸干透以后,我不是继续画下去,而是用剪子把颅骨剪下来,把新的形状和它们粘在一起,然后置入一个非常严密的设计中,由仔细控制的线条串在一起,并称之为《动物的睡眠》。我意识到我已经发现了对最初那只鸟的颅骨那黑暗、不可进入的内部的一种回应。我的回应似乎是瞬间达到的,但是——这里又和诗歌的情况相同——正规形式吸收了偶然因素,它是意识和下意识过程的结果,是陌生的、统一的识别运动的结果,在我去拿剪子的时候,我发现的东西变成了我选择的东西,“偶然”再一次与“舞蹈”押韵了。
为什么,作为艺术家,一个人会这么着迷于颅骨的形状,无论是动物的还是人的?我不相信一个人回到它仅仅是出于纪念——尽管那个因素也是存在的。同样重要的是,颅骨被看成了一座建筑。它类似于一座房子,有着明亮的正面和阴影重重的内部。无论它的结局多么悲惨,它总是使人卷入对内与外的迷恋之中,那人类心灵寻求超越自身的主要诱惑,牢牢抓住世界那或令人愉快或充满威胁的表面,因为藏在那些表面后面或下面的意义而变得焦虑和丰富。我试图在许多绘画中表达这种认识,尤其是动物颅骨的画。我也试图清楚地用词语来表达这个认识,以一首题为《颅骨的形
状》的散文诗的形式。
颅骨。结局。它们从下层灌木中涌现,进入新的开始。随着石头、化石、燧石、轮辐,随着碗底印着制造者标记的白黏土的碗,出现的是孩子们带回家来的乡村牛颅骨的残渣。它们染上了苔藓,被泥土弄脏了。洗去它们上面的斑驳,手逐渐感到了重量,因参差不齐而变得尖锐的重量。把它们悬挂在一根钉子上,你感觉骨头的笨拙:在它们对钉子的垂直下拉中依然有重量存在,但是也有一种悬挂的易碎性。两种性质混合在一起,刷子把这种混合转换成机智,那里腿状的附器决定了颅骨的悬垂物。
阴影探索着它们。它把眼窝衬上黑色。它像手指伸进你看不见的地方。颅骨是这种可见的双重性的深刻例证:它形成了眼睛无法看清的事物的界限,它超越自己,暗示着那里存在的一切,除了眼睛所占有的东西:它无法被占有。充盈着光芒,这颅骨马上成了清楚的表面和壁凹的迷宫。阴影从头盔状空腔的世界向下延伸,宣告它的存在。
一个人看见了。可不仅仅是视网膜马赛克的被动反射——也不像罗斯金的盲人突然被幻觉袭击,没有记忆也没有观念。感官,被其他景象唤醒,慢慢忍受,想象着它们形象的模式;它们为其他赤裸和无家可归的印象提供观点和位置。这是头脑在看。但是它看见的不仅仅是由它所遭遇的东西、在它所记忆的光中捕捉住的东西所组成。它看见了可能性。
鸟的颅骨,摸着硬,看着脆。颅骨本身圆如卵形,仿佛这球形是吹玻璃泡一样吹出来的,它们用嘴喙的刀片抵抗着眼睛的想象,没有任何抒情的赞赏能使之脆弱。
自然的颅骨是壁凹和体积。艺术的可能性的颅骨是壁凹、体积,也是线条——包容的线条,延长的线条。在观看之中,一个人彻底即时地延伸了视网膜印象。画刷和笔将探索延伸,超出瞬间,揭示出一个未来。体积,被一根挑战的线条穿过,凹凸不平的薄骨头被有序的三角形晶面所反击,一个牛头骨打开了一片幻觉的田野,一出普遍性的戏剧。
在图形艺术和诗歌艺术中,我喜欢被神秘包围着的东西。我把诗歌和绘画看成文明化的识别能力和对本质的原初感觉互相强化的地方。有时,我会重新回到有关一幅海景的思想——
有着难以读懂的深奥
和明白易懂的段落,
石头的动物寓言集,
没有书页的书……
而一首能够自我成型的诗也同样能够成为一幅画,或几幅画:
在水上
“犁沟”是不准确的:
任何船都不能
被变成犁
沿着这玻璃的乌木而行:
把它封在海中洞穴
你不能让它静止:
形象弯身在形象上
半明半暗的灯光把它充满
有着难以读懂的深奥
和明白易懂的段落,
石头的动物寓言集,
没有书页的书:
然而它同样给予
又同样拒绝:
我们是孤儿和父亲
因为这坚固的空缺
当词语显得过于抽象的时候,我发现 自己用组成海的东西——水,来画海,让它使颜料稀薄、分开,揭示出一个形象的本质。我先前说过,把事物带入原始的光中。当你用水来画画,并且画着水的形象,你返回到它,仿佛返回所有原始的事物,带着一种认同感——水!我们从此出发。“人的眼泪,”科学家说,“是原始海洋的再创造,在进化的最初阶段,是海洋沐浴了最初的眼睛。”也许对水的沉思在我们内心唤醒了尘世的回声,越过那久远的时间鸣响。如果那思想过于幻想化,当我发现自己从乱糟糟的皱褶和黑颜料中悖论般地创造出一个水、光和空气的世界,也许同样的偶然就在这行为中存在,引领一个男孩在一个变黑的城市,在夜里沿漆黑的运河而行,并向他显示了水中不可熄灭的火焰。
注:1 贴花法(decalcomania),一种把图像从一个表面传送到另一个表面以复制图画的技法。由西班牙超现实主义者奥斯卡·多明格兹于 1935年发明于巴黎。采用含树胶不透明的水彩颜料敷涂纸张,再将纸压到帆布或另一张纸上,然后揭去,这样颜料就能随机地从一个表面流向另一个表面,产生出类似海绵状的特异图案。布勒东赞赏这种技法,因为这样形成的图画没有任何主题或形式方面的先入之见。超现实主义画家恩斯特就曾在自己的绘画中应用这种技法,他的画有时以这种方法开始,最后再以常规手段完成。
2 波特里斯(Potteries),英格兰斯塔福德郡北部的一个行政区。为英国主要陶瓷器产地。包括原来的坦斯特尔、伯斯勒姆、汉利、特伦特河畔斯托克、朗顿和芬顿六个城镇。韦奇伍德和明顿是两个与该区陶瓷业密切相关的著名家族。
3 沃尔顿(1593-1683),英国作家,以其描写钓鱼之乐和技巧的《高明的垂钓者》一书最为著名。
责任编辑 段爱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