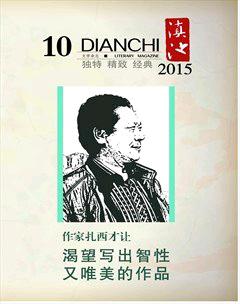燃烧的雪(短篇小说)
周远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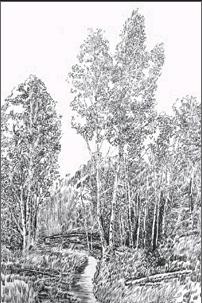
1
啪啪,荞花脸上挨了两巴掌,鼻血哗哗哗地流了出来,她正想掏出手帕抹鼻血,又被人一脚踢在大腿上,站立不住一屁股跌在地上。
那个凶恶的女人愤怒得脸几乎变了形,五官错了位,鼻孔大张着,朝着天,让人感到十分恐怖:“我儿子要是留下残疾,我就撕了你这个小骚货。”
朝天鼻打骂了人,随即问小男孩:“哎哟,我的宝宝啊,伤在哪里,快给妈妈说?”
小男孩被女人揽到怀里,睁着一双惊恐的大眼睛望望这个,看看那个,只是摇摇头,并不说话。
一会儿,小男孩的父亲、爷爷、奶奶都来了。奶奶的手在荞花脑门上戳了一下说:“你这个冒失鬼,骑车咋个不看路,那么大的一个人看不见,我孙子有个三长两短,你看我不撕了你。”说着从朝天鼻手里一把抱过男孩子亲了又亲,眼泪簌簌地落了下来。
围观的人很多,他们叹息着、议论着。一个中年妇女小声说:“出了这种事,还是请交警来解决比较恰当。”
那妇女声音虽小,朝天鼻还是听到了,就说:“那倒没必要,你们也不必多事,我们自己就能了结。”
朝天鼻果然了得,指挥男人把荞花的摩托推进身后那道大门里去了,她还从荞花身上搜走了驾驶证,然后叫荞花到市医院等着付钱,一家人骂骂咧咧地走了。
荞花抹了一下鼻血,使了几下力终于站了起来,眼泪啪啪直往下掉。刚才说话的那个中年妇女又说:“姑娘,我看你也是乡下来的,你还是找交警来解决,孩子好像也没有伤着。”
一个骑三轮车的汉子说:“现在咋个找,人不见了,车被收起来了,现场也被破坏了,谁来
管你?等着挨一刀吧。”
荞花身上就七十块钱,是准备给母亲买药的,拿什么付医药费?不去肯定不行,摩托和证件还在人家手里。她谢过那些关心她的人,出了两块钱坐电三轮到了医院,正巧医生正在为孩子检查,家属们全围住医生,她想靠拢去,却又不敢。听医生说,孩子没伤到骨头,就是臀部和手肘碰破了点皮,开点药带回去抹抹就行了。这时,众人发现荞花来了,医生也看到她鼻子上有血迹,就再一次问了当时的情况。朝天鼻说:“还是拍个片子看看,我们大人才放心。”
医生说:“拍片?我看就没有那个必要。”
朝天鼻又说:“有后遗症咋办?”
医生很不耐烦地说:“你应该相信我们的检查结果,如果你不相信,可以到另一家医院去查。”
朝天鼻看着医生如此态度,眉毛一挑,就要发火,她男人拉了她一下说:“走了,到处都一样。”
她觉得无趣,拉着一张长脸回过身来,把处方一把塞到荞花手里说:“你别高兴得太早,我们还没完。”
荞花急忙跛着腿去算钱,拿药,七十块钱所剩无几。
灰蒙蒙的天空一直愁眉苦脸,云始终凝重,深秋的风无休无止凛冽地刮着,刀子一般锋利,柏油路上落满了黄叶,在地上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人们都在厚重而透骨的寒冷中瑟瑟发抖,荞花身上有一种凉嗖嗖的感觉。她一路抹着泪往回走,那个朝天鼻女人的话还在耳边响起:没有三千块休想拿走摩托和证件。她当时听到那句话差点晕过去,她哪里去找三千块钱?早上起床时右眼皮跳个不停,想起来今天就要走霉运。天气一凉,妈的肺心病又加重了,在床上高一声低一声地哼着,哼得荞花心里铅块一样的压着。她只好请了一天的假,到城里帮母亲买药。想不到,药还没有买到,摩托把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推倒了,她知道闯大祸了。那时,她有个念头,那是一条小巷,人也不多,至少周围还没有人,跑掉还来得及。但那个念
头仅只是一瞬间的事,她还是决定等小男孩的大人来,偷偷跑掉很不道德。
荞花住的村子叫落雁村,一个很好听的名字,村子离城里也就是三十多公里,父亲还在的时候,她曾问父亲为什么叫落雁村,父亲说大概是北宋靖康时,金人与宋皇帝交恶,金兵见人就杀,徽钦二帝被捉,一时生灵涂炭,血染汴梁,老辈人为躲战乱,就从河南来到这里,发现成群的大雁在这里落脚,就取名为落雁村。父亲是小学教师,知道的事情还真多,她读到高二时,父亲为救落水学生一撒手走了,丢下她和患病的母亲,书也就读到头了。读不了书的荞花闲了就坐在门口看远处的大山,看村子里上学放学的学生,一坐就是半天。母亲说:“荞花,那山,那些学生,有什么好看的。”
她木木的,母亲的话像风吹过一样,半天没有反应。
母亲的病情稍有好转,有一天,她告诉母亲,她要去打工!母亲死活不同意,说世道乱得很,你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不怕被人家拐去卖了?
她就说:“那金凤、喜妹她们也不见得就被人拐卖了?”
母亲一副地主婆的嘴脸,大声说:“那两个鬼丫头精灵古怪,你死木头一根,能和人家比?你死了那个心吧。”
她的话是少,但也不是像母亲说的那样,真的是根木头。实际上,她知道母亲不准她出去的原因。一是她长得漂亮,虽说是农村女子,但皮肤白白的,眼睛大而深陷,眉毛弯弯的,眼角微翘着,瓜子脸型下巴尖尖的,母亲说这块脸有点狐媚相,容易惹祸。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村子东头的二秀,前几年出去说给老板当秘书,村里的人都知道她初中都没有毕业,那点水平当得了秘书,哄鬼去吧。二秀在城里实际做的是“那个”,不出力不出汗,不晒太阳不淋雨,钱来的却很容易,她爹张斜眼用女儿挣来的钱盖上了大房子,家里电器样样齐全,日子倒是滋润着呢。但背后村里的人就指着张斜眼的背脊骂,说那钱不干净,狗日的拿女儿卖肉的钱,也不羞得慌。张斜眼也不知道是不是装聋作哑,只是见了熟人眼光躲躲闪闪,像做贼似的。荞花也见不得二秀,觉得她是一个贱骨头,每次遇见了都仰着头,转过身还要往地下吐口水,那样的钱有多肮脏,她才不齿呢。
这样过了一年,荞花几天不说一句话,脸上清汤寡水的不受看。荞花的舅舅说:“再憋下去,要整出病来,还是让她出去找点事吧,这是潮流。”
母亲也真的怕她出事,经不住亲友们在耳朵边聒噪,就放了她的生。
舅母家比较富裕,买了帕萨特偷偷跑运输,一车运四个人,到省城每人收一百六十八元,简称“168”,逢年过节价钱还要上浮。舅舅和表哥一人一辆车,钞票大把大把地捞进来。一辆摩托刚买来没几个月摆着没人用,舅舅的意思是叫荞花拿去骑,挣着钱给半价就行了,执照找人帮她办。荞花知道半价就是三千块,说起来也不吃亏,她是知道那辆摩托价格的。舅舅抵得上半个父亲,人家不要现钱,啥时有钱啥时还,这就多大的情分了,荞花脸上终于漾开了笑容。舅舅有能耐,没出两个月,证就真的办下来了,但办证的钱荞花还是得欠着。那两个月,她也学会了骑摩托。打工苦是苦了点,但一群男女青年在一起做起来猛做,休息时又说些笑话,一天的光阴也就捱过去了。
想不到才出去打工不到半年,就出了事,舅舅的摩托钱还没有苦着,挣着的钱有一半为母亲买了药。现在,摩托被人家扣下了,怎么向舅舅交代。她的事很快母亲就知道了,急得坐立不安,不停地陪荞花抹眼泪。舅母当然也知道了,骂荞花冒冒失失的不好好看路,城里人刁钻古怪,你惹得起?
金凤来了,她说,我有办法,我男朋友的一个铁哥,是做矿石生意的,什么事都玩得转,他叫安南,与前联合国秘书长名字相同,一个电话就解决问题。金凤随即打了一个电话,那头说找政府办的鲁秘书就行,他马上给他电话。金凤到底是自己人的好姐妹,借钱给荞花买了两条极品云烟、一盒铁观音,来到城里,找到鲁秘书。那时,已经六点过了,办公大楼里的人大概都早走了,只有鲁秘书还在电脑上打游戏。她们进去,鲁秘书很客气,说美女,安哥给我说了你们的事。说着就张罗给她们泡茶。金凤喝着茶,把荞花的事作了介绍后,就说:“鲁秘书,荞花的事就靠你了!”
鲁秘书笑笑说:“这事也不是很大,我已经找了派出所问过,你说的那家人特别难缠,那个小男孩的母亲叫鲁再兰,说起来还与我沾亲带故的,只是脾气暴躁,不好对付。不过,弟妹你说了,我还能推卸?但有一点,荞花既然伤了人,总是要补偿一点的。”
荞花说:“补偿点应该,我知道。”
那晚上,金凤请鲁秘书吃了饭,喝了酒。鲁秘书喝了不少,眼睛红红的,舌头都有点卷了,看着荞花说:“就冲是安哥介绍来的,还有你那么朴实本分,我也要帮你的,下周你来看结果吧。”
荞花说:“那就感谢鲁秘书了,我不会忘记你的大恩大德。”荞花庆幸自己遇上了好人。舅舅好,金凤好,鲁秘书也好,有鲁秘书帮忙,还怕那个朝天鼻鲁再兰?
金凤自然不会再陪她去了,人家在上班呢。到了周一早上,她一个人就去鲁秘书的办公室。鲁秘书很高兴地接待了她,给她倒了一杯水,让她慢慢喝着,说他有事要去办,如果坐不住,可以先去街上逛逛。说完,鲁秘书就出去了。荞花坐了好长时间,见不着人,真的就上街去逛商店,看那些花花绿绿的衣服,看到一个书店,就进去翻书看,她读书时,最喜欢看文摘类书刊,看一会觉得还不错,就买了一本《读者》,等回到秘书办公室,差不多到了下班吃中饭的时候了,鲁秘书也办完事回来了,正在低着头写材料呢。鲁秘书说:“荞花,我们吃饭去!”
荞花说:“不了,不了,不晓得那件事怎么样了?”
鲁秘书说:“那事不忙,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我说过,那个鲁再兰难缠得很。”
荞花急了,想起那个女人的凶恶霸道,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经不住鲁秘书再三邀请,他们就到街上小馆子里吃饭。吃了饭,荞花总觉得麻烦人家还要人家掏钱请客,就十分过意不去,就去给饭钱。鲁秘书哪里要她付钱,两人争了好一会,最后还是鲁秘书付了钱。
摩托和驾驶证还没有要回来,一晃过去了一个月,工地上是去不成了,几十里路没有摩托那肯定不行。
日子像水一样慢慢流淌着,百无聊赖的她又开始窝在家里看山、看上学放学的学生了。
落雁村风硬,风从山垭口吹来,到了村子就不想走,使着性子,又缠又绵,早早晚晚把人吹得畏畏缩缩的,没有一点生气。荞花站在门口,风像刀子刺来,仿佛是木头人一般,脸上虽然有些青紫,但不知道冷。那天,她在门口看山的时候,一辆黑色轿车在她面前停了下来,金凤和一个男人从车上走下来,金凤和她打招呼,并指着那个人介绍说:“他叫郝强,是我的男朋友,在商场里当经理。”
那个叫郝强的男人有些秃顶,张口一笑,一口白牙亮亮的很是招眼。金凤见她憔悴不堪的模样,看了一眼郝强说:“你也去那个商场,请郝强给你安排点事做,工资虽说不高,比在家里好多了。”
郝强也说:“去吧,混口饭吃还可以。”
荞花推辞说:“谢谢你们的好意,以后吧,现在还不想去。”
金凤也不勉强,说你什么时候想去就吱一声。
村里人十分羡慕金凤,金凤是她初中的同学,又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姐妹。金凤家离她家没几步,黑色轿车就停在家门口,村里人都围着观看,孩子们在车边追逐打闹,嘻嘻哈哈,像过节一样兴奋。舅母过来对荞花妈说:“看看,人家金凤有本事,找了那么好一个老公,有车有钱,还是个当官的。”
荞花妈摇摇头,看了一眼死木头似的荞花没说话。
郝强拿着极品云烟发给那些乡邻抽,金凤她爹金大牙笑容满面地招呼大家到家里坐。荞花母亲和舅母也过去看热闹,回来就说金凤那丫头哪辈子修来的阴功,还没我家荞花长得秀气,怎么就有那么好的福气。荞花听不得母亲的絮叨,站起身就出门去了。她来到村背后小河边,看着瘦瘦的河水缓缓流去,眼泪汪汪地一坐就是半天。
金凤叫她再去找鲁秘书,说人家又没有拒绝。舅母也催她好几次,说你天天坐在家里,摩托莫非就会回到你手里不成?她没办法,只得硬着头皮去找鲁秘书。鲁秘书胖胖的脸堆满了笑容,依然对她很客气,说你不来我都要打电话找你了,已经有眉目了,我找派出所的人做了很多工作,那个鲁再兰口气缓了下来。荞花高兴地说:“真的,她怎么说?”
鲁秘书说:“看把你高兴的。她说少点当然可以,但你必须要拿出两千块,少一个子儿也不行。”
荞花刚刚有点兴奋的心情又被一瓢水浇灭了,不要说两千块,就是叫她现在拿两百块也实在困难,她家徒四壁,又没有出去打工,母亲病恹恹的,哪里来一分钱的收入?
鲁秘书说:“荞花,我们到外边说话,里边人杂。你先出去!”
荞花有些犹豫,她有点害怕,没有说话,政府大楼里人来人往,也确实混杂,随时有人来找鲁秘书问事情。
荞花走出政府大门,鲁秘书也跟了上来。在他的带领下,两人来到一个小巷,他打开一道门,是一个小套间。他说是办公地点离家远,租了这间房子中午不回家休息用的。
荞花心里突突地跳,不敢进屋。
鲁秘书说:“荞花妹子,难道我会把你吃了,你还不相信我?”
鲁秘书话说到这里,荞花已经没了退路,就随鲁秘书进屋。屋子逼仄,有一个长沙发,一张床和一个写字台。她坐到沙发上,鲁秘书站在她面前说:“荞花,到这一步,我就给你直说了,如果你真的感谢我,我就把你那两千块付了。”鲁秘书说着,就坐到荞花身边,荞花赶紧往角落里让了让。
鲁秘书笑了笑说:“你真的那么怕我?”
荞花低着头说:“鲁秘书,你帮我付了钱,我记你一辈子的好,一有钱我就立马还你。”
鲁秘书说:“我既然帮你付了钱,就不要你还。”
荞花慌了,忙说:“不行,不行,你对我那么好,我一定会把钱还给你的。”
鲁秘书哈哈笑了起来,说:“荞花,我的心思你明白,我会给你带来很多好处的。但我不会逼你。”
荞花心口咚咚咚地跳个不停:“鲁秘书,你说的话我听不懂。”
鲁秘书说:“你会懂的,你走吧!”
这时候落雁村出了一件大事,表哥的帕萨特轿车翻在路上,乘客一死一伤,万幸的是表哥只受了点轻伤,但车已损坏了。表哥是非法营运,本地暂时没人过问,但在省城被发现就会把车没收掉。所以,出了这种事是见不得天的,只能私了。死者和伤者家属抓住表哥这个软肋,要价高得惊人,巨额赔偿压得表哥一家喘不过起来。人死了多要点无可非议,但活着的也狮子大开口就过分了。舅舅、舅母把房子卖了,到处借钱赔偿,苦不堪言。荞花过去想安慰一下,看到表哥一家遭受如此灾难,心里别提有多难过,只恨自己不争气,不仅帮不上一点忙,反而欠了那一笔钱,话是找不着说的,只是陪着叹气流泪。舅舅对荞花欠摩托钱的事只字不提,叫荞花不要放在心上,过了这一劫就好了。可舅母脸色很不好看,说的话就有些夹枪带棒的。舅舅一边眨眼睛叫荞花快走,一边就去拉他老婆说:“你这是什么话?”
舅母甩开舅舅拉她的手说:“我们遇到这样大的灾祸,外人都出看不过,亲朋好友应该搭把手,我说错了吗?”
舅舅说:“你当然没有错,慢慢会有办法的。”
舅母火了,直接对荞花说:“荞花,听说你认识一个政府的领导,听说他跟派出所的人很熟悉,那个大腿骨折的人住在西门,正是西门派出所管着,你请那个大领导从中周旋一下,给他打个招呼,死的那个人陪了好几十万,伤一条腿八万块就算把我们卖了也给不起,能不能减掉一半?这个忙你帮帮我们,不难吧?”
舅舅说:“荞花,不到万不得已,你舅母也不会这样让你为难,我们真的是山穷水尽了,你就跑一趟吧,啊!”
荞花那时只差没个地缝钻进去,她看看舅舅哀求的模样,又看看舅母期待的目光,她已被逼迫到了悬崖上了,机械地点了点头。
荞花这一点头,其实是把自个儿全交给了鲁秘书。
2
今年的雪特别大,天气预报说有强降雪。
落雁村的冬天是雪带来的。雪是冬天的精灵,有了雪,冬天就丰满起来了,屋顶上、草垛上、水井上、田野里,全是白茫茫一片。喜妹结婚的日子遇着下大雪,雪花飘飘荡荡,迷迷茫茫,整个村子银装素裹,分外妖娆。大家都说喜庆,瑞雪兆丰年,来年抱个胖小子。荞花自然接到了请柬。她和金凤、喜妹从小一块儿长大,一块儿读书,是最要好的朋友。只是这几年,外出挣钱和喜妹就聚少离多,后来喜妹就在乡政府办的褐煤厂里当会计,也还轻松。再说了,喜妹的对象恰恰是荞花的表哥,这简直就更加外不开了。所以,无论如何,荞花都要去捧这个场。她对韩北斗说:“我的朋友喜妹结婚,我得回去一趟。”
韩北斗说:“我跟你一块去,也拜见一下岳母!”
荞花说:“你不能去,等我们下个月结了婚,再去不迟。”
韩北斗说:“天气预报说有强降雪,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去!”
荞花说:“怕什么,农村人见惯了雪,我还会被雪埋了?”
韩北斗说:“那,也行。”就把五千块钱给她,代表他顺便看看岳母大人。
韩北斗何许人也?这还得啰嗦几句。
前年荞花被她舅母逼着去见鲁秘书后,鲁秘书果然没有食言,当荞花从他床上爬起来后的第二天,摩托和证件就到了手中,那个一条腿骨折的男人,也不再盯着表哥要八万块了,答应减掉四万,也不知是鲁秘书找了什么人,用了什么办法说服了那个难缠的鸟人。荞花还把舅母的摩托钱也还了,尽管舅母再三说不急不急,但在荞花的一再坚持下,她还是把钱接在手里。舅母一家人对荞花感激万分,夸荞花劳苦功高,在城里玩得转,帮全家人渡过了难关。
鲁秘书帮了荞花这样大的忙,让荞花在村里很有面子,都说她有本事,人缘好,在城里吃得开。鲁秘书出手也大方,给荞花买了衣服、化妆品、首饰,给了她一个手机,说是联系起来方便。当然,项链那些东西荞花不敢用,悄悄放在箱子底下藏着,反正有用得着的时候。荞花投桃报李,只要鲁秘书的电话一响,她就要去找他。鲁秘书的老婆早就离了,孩子跟妈,他一个人过了好几年,他承诺适当的时候给她一个名分,让她名正言顺地做秘书夫人。后来他才知道,鲁秘书其实是政府里分管后勤的科长,确实在很多方面有办法,给她介绍在一个家电商场当收银员,工作也不苦,轻松干净,鲁秘书说先干着,以后有好工作再调换。既然有了工作,荞花没有住处,也就住进了鲁秘书租的那间小房子里。鲁秘书说过,本来要安排她直接住进家里,但考虑到还没有结婚,怕影响不好,所以暂时住在外边。
鲁秘书曾带她回去住过一晚上。大房子多宽敞啊,鲁秘书说:“你今后就是房子的女主人了。”
看着漂亮的大屏幕液晶电视、名牌大冰箱和舒适的红木家具,荞花多高兴啊,这三室一厅的房子很快就会是她的了。她双手挂在鲁秘书的脖子上,给鲁秘书一个热辣辣的亲吻,说:“鲁哥,你对我真好。”
鲁秘书回敬她的是,把她放翻到宽大的席梦
林间(线描) 桑子
思床上,整个身子压了上去。
荞花回村里去都不再骑摩托了,鲁秘书用大众车送她,当然没有送进村里,只送到村口那个石拱桥上。荞花要返城去,一个电话,鲁秘书的大众车又会在石拱桥上等她。即便鲁秘书有事来不了,他也会叫她搭车来,车票照报,不需签字。这当然是一句玩笑话,她也不好意思当真叫司机撕票给她去报销,鲁秘书给她的够多了,人应该知足。
仅仅几个月时间,荞花摇身一变换了一个人,白白净净丰满标致十分惹眼,麻花辫子烫卷曲后又拉成披肩发,活脱脱一个城里人。回到家里,大包小包地提着,孩子们来玩,都能得到水果糖啊、饼干之类的东西吃。村里好多人都有点不习惯,说不看吃的看穿的,荞花一定苦着大钱了,那衣服,那鞋子,那发型,啧啧,那脸嫩得一掐一包水。她母亲拉着女儿左看右看说:“我们荞花出息了,比金凤有出息。”
那段时间,舅母家吃着好的东西就要把母亲接过去吃,直夸母亲养了一个好女儿,比以前漂亮还能干,良心好,有奔头,是前世修来的福。母以女贵,看着村里人和亲朋好友都夸奖荞花,母亲的心情比任何时候都好,病也好得多了,脸上常常溢满了笑容,吃完饭还喜欢在村里溜达,与大伯大娘说说笑话,偶尔还会哼几句小曲儿呢。
虽然鲁秘书比荞花大十三岁,说起了也不算大。十三岁算什么大呢?父亲就比母亲大十八岁,母亲也从没有嫌父亲大,那时两个老人你敬我爱,举案齐眉,多幸福啊。遗憾的是父亲提前走了,丢下母亲孤苦度日,好不让人心酸。现在好了,苦尽甘来,和鲁秘书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母亲高兴,女儿满意,村民羡慕,其乐融融。
生活如果按这个轨迹走下去,那多好啊。
可是,上帝总是喜欢捉弄人。
有一天荞花调休,中午吃了饭,荞花在她那个蜗居里看书,突然有两个女人推门进去,一个三十七八岁左右,一个十岁左右。三十七八岁左右那个大嘴女人问:“你就是荞花?”
她说:“是啊,荞花就是我。”
大嘴女人眼睛一瞪说:“你这个小骚货,终于逮着你了,我告诉你,鲁松年是我男人,敢抢走我男人,打死你!”
荞花被那个女人扯着头发拖出门来,掀翻在地上就是一顿拳脚,差点要了命。还好有人路过,看着荞花满脸是血,忙劝说:“别打了,出了人命可不是好玩的。”
那个年龄小的说:“妈,快别打了,找我爹算账去。”
大嘴女人指着地下的荞花说:“记好了,再让我看着你,有你好瞧的。”
可怜荞花被那一番毒打,整整睡了半个月。那半个月,她除了吃饭喝水上卫生间外,连床都没下过。她夜间常常被噩梦缠绕,先是朝天鼻女人迎着她心口一脚踢来,接着就是大嘴女人拿着刀在她脸上划口子。她一宿一宿地醒着,眼泪哗啦哗啦地落,把黑黑的夜打湿了。大嘴女人这一闹腾,她的人生计划全乱套了,梦想中的美好日子瞬间化为乌有。鲁秘书来过一次,给她买了很多营养品,陪了许多不是,希望荞花原谅他。荞花当然不理他,她最恨的是欺骗她,把她当做一个傻瓜打整。她把那些花花绿绿的营养品狠狠地甩出门去,叫他滚远点,今生再也不要见到他。
那次变故的结果是荞花下水了,拉她下水的是二秀。
伤好以后,荞花家电商场也不愿意去了,想起鲁秘书那狗东西,心里就疼得受不了。
商场的胡琼认识二秀,两人曾在一起打过工,一次见面说起荞花被打一事,二秀就找来了。当初在家的时候,荞花见不得二秀,骂二秀是贱骨头,见面还吐过她口水。实际上她和二秀是初中同届不同班的同学,二秀毕竟是家乡人,现在,二秀就坐在面前,她这个样子,五十步不敢再笑百步,乌鸦岂能再骂猪黑?无论如何也放不下那个脸来,眼泪还不争气地簌簌直往下掉。两人说了很多话,后来,荞花就和二秀到洗脚城当服务生去了。自己身子已不干净了,做什么事当然无所谓。
在她给顾客洗脚做按摩时,发现有一个叫韩北斗的人每半个月来一次,每次都点四十六号,四十六号是荞花的工号。韩北斗这人很规矩,完全是一个正人君子,每次都老老实实地让她按摩,从来没有像有的男人那样嬉皮笑脸,不摸屁股就捏乳房。韩北斗话不多,偶尔看看荞花一眼,眼神里没有一点淫邪。一来二去,两人就熟了,话就多了几句。荞花知道他是建材城的老板,老家是浙江的,他随时来照顾自己的业务。荞花也把自己的遭遇说给韩北斗听,韩北斗也把如何从浙江来做生意的情况讲了出来,还说最让他痛心的是爱人患绝症去年离开了他。说起爱人,韩北斗声泪俱下,说此生再也找不到像她那样漂亮温柔的女人了。荞花看他那样子,心里想,韩北斗还是一个重情重义的男人,如今这世道这样的人可不多了。
他还说,之所以喜欢荞花,第一次来洗脚就发现荞花长得极像他爱人,特别是那个弯弯的眉毛、深陷的大眼睛和瓜子型的脸,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后来,还发现,连性格也居然有些相像。韩北斗说:“荞花,如果你愿意,我接你出去,就在我的建材城里做事,工资不比这里低。”
荞花被蛇咬过,见井绳就怕,就说:“不去,在这里最好。”
韩北斗见荞花有顾虑,也不勉强,继续来找他洗脚按摩。只是韩北斗来的次数更勤了,由原来半个月一次变成十天,后来是一周一次。
一次洗浴后,韩北斗约荞花出去吃夜宵,再一次提出让他去建材城,甚至愿意同她喜结连理。荞花睁着惊讶的眼睛说:“算了吧,你们男人最会哄女人,等在一起,哪天老婆就打上门来了。”
提到老婆,韩北斗眼圈就又红了,他从包里把医院为他爱人开具的死亡鉴定书拿出来,还把他妻子的一张照片也拿给她看。荞花心里想:“那是一个多美的女人啊,那鼻子、那眼睛,真的像自己啊,如果让不知情的人看,那绝对就是另一个荞花啊。”
韩北斗知道了荞花的遭遇后,同情并深深地爱上了荞花。后来,荞花还是相信了韩北斗,她怕在洗浴城时间长了,碰着熟人不好,就真的到建材城做事。几个月后,她见到韩北斗出入其它商谈会应酬、平时生活都十分检点,就与韩北斗住到了一起。荞花看着客厅里韩北斗妻子的遗像,心里难免有些凄然,叫他收了起来,要尽快从阴影里走出来。韩北斗把妻子的遗像放到箱子的底部锁好,默默地祈祷了好一阵。
他对荞花很好,就像大哥哥对小妹妹那样细心呵护。那段时间,她觉得小草也欢笑石头也唱歌,世界真美好,爱情真美好。荞花要回落雁村,韩北斗就开车送她,当然还是像当初鲁秘书那样送到村口石拱桥上。荞花指着村子说:“北斗哥,你看,到村子向左拐五十米,见着一棵大槐树就是我家。”
3
落雁村里,喜妹和表哥的婚礼开始了。果然是强降雪,漫天一片雪白,老天还在无休止地下着大雪。雪天有雪天的乐趣,人们最喜欢打雪仗、堆雪人。表哥把喜妹接来还没进家门,一对新人就被那些细妹子和青皮后生雨点般的雪团打得嗷嗷叫。老辈人出来干涉,说别打了,大喜的日子着凉感冒可不是闹着玩的。众人嘻嘻哈哈不依不饶,表哥脖子里早丢进几个雪团,喜妹的脸上也有人抓雪去抹。在打雪团时,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小胡子男子站在一边看热闹,眼睛直往荞花这边看。荞花也觉得面熟,但一时也想不起来,到底在哪里见过。那个小胡子过来说:“美女妹子,我好像见过你?”
荞花说:“你认错人了吧,我可没有见过你。”
小胡子说:“我是喜妹在城里打工时认识的朋友,留个电话,以后好联系?”
荞花说:“我没电话,以后吧。”
那个小胡子顿觉无趣,尴尬地笑笑说:“好的,好的。”
俗话说,打架莫上前,吃酒别落后。前边吃席主要是干净,吃了好做事。疯够了,大家都上桌吃饭,荞花和母亲坐一桌。城里有大酒店,一次就摆几十桌,农村的酒席只能在小院子里几桌几桌地摆,要吃好长时间,叫做流水席。荞花她们吃的是头一巡,舅母过来说:“天气冷,先喝点酒暖暖身子。”
桌子上的人都说这强降雪天气真的贼冷,喝酒热乎,于是就举杯。舅母对众人说这两年又翻过身来了,日子还过得下去,儿子也才娶得起媳妇,夸奖荞花帮了她家的大忙,各位亲朋好友一定要吃好喝好。大家都朝荞花投去羡慕的目光,说养姑娘争气,比儿子还有出息。母亲兴奋得脸孔红红的,说我家荞花听话,还特别孝顺。
表哥和喜妹来敬酒了,伴郎的开场白还没有说,荞花发现邻桌的那个小胡子男人突然端着酒杯向她走了过来,说:“我,我想起来了,美女妹子,你是四十六号,你给我洗过脚,按摩过,我,我敬你一口。”小胡子男人明显有点醉了,说话已有些结巴,一口就把杯中的酒喝了。
荞花心里一惊说:“你胡说,什么四十六号,你看错人了。”
小胡子男人争辩说:“没有,绝对没、没有,你就是四十六号。”
伴郎不耐烦了,对小胡子男人说:“老哥,有话等下说,新人在敬酒!”
小胡子不理睬伴郎,大着舌头说:“哈哈,你在洗脚城做按摩,你的工号是四十六号,还,还陪我兄弟睡,睡过觉呢,给了你 500块钱,说你的皮肤好白。你,你,记不得啦?”
小胡子那句话无疑在人堆丢了一颗炸弹,强劲的冲击波把人们击晕了。
瞬间,空气稠得像泥浆,凝固得瘆人。
新郎新娘呆了,荞花母亲木了,亲朋们痴了。
荞花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她站起来就往家里跑,一下倒在床上,用被子蒙住头,嚎啕不已,万箭穿心。母亲也回来了,那饭她吃不下去,她走到荞花床边,看着被子一耸一耸的抖动,知道此时多说无益,就坐在堂屋里抹眼泪。荞花哭够了,眼泪也流干了,拿出手机给韩北斗发了一个信息:北斗哥,谢谢你对我那么好,今生我的日子已到了尽头,我们来生再做夫妻吧。
韩北斗收到那个信息,预感到事情不妙,急忙拨电话,对方已经关机了。他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心急火燎,坐上了办公室小邵的三菱越野车全速直奔落雁村。
荞花掀开被子,坐了起来。母亲红着眼睛进来说:“你走吧,别回来了,我没有脸再见村里人了。”母亲说完就出去了。
荞花整整睡了一天,不吃不喝。
第二天,她坐了起来,虽心如死灰,面似霜打,但此时心里比任何时候都清醒,她找出梳子开始梳头,梳好头,把身上的钱全部拿出来放在小桌子上,然后找出一本影集,那上边是她从小学到高中照的照片,除了同学、老师,还有她的好朋友金凤、喜妹,她把那些照片一张一张地撕碎。据喜妹说金凤与那个郝强经理闹了别扭,郝强与另一个女人被她堵在床上,两个女人大打出手,金凤破了相,婚宴也不敢来参加,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喜妹当了新娘子,好幸福,表哥一定会对她好的。她想给她们两个发一个信息,但这个念头只是一闪现就没了。她站起身,从抽屉里拿出小刀,在床上躺下,对着自己的手腕狠狠割下去……
雪花依然飘飘荡荡,漫天狂舞,韩北斗的大众车发了疯,碾着厚厚的积雪一路呼啸着,直向落雁村飞奔。
韩北斗冲进屋里,把荞花眼角那颗泪轻轻抹掉,抱起已经逐渐僵硬的荞花出了门。她母亲流着眼泪拦住说:“这是她的家,你把她抱到哪里去?”
韩北斗表情木木的,没有任何反应,嘴里絮絮叨叨:“回家,回家,荞花,我们回家。”
落雁村的天黑了,表哥家人声鼎沸,闹房开始了,嬉笑声传得很远,门口拉起几盏大灯泡,光芒四射,夜如白昼。雪还在下,而且更猛,铺张而恣肆,灯光落在白皑皑的房上、树上、草垛上,似在燃烧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