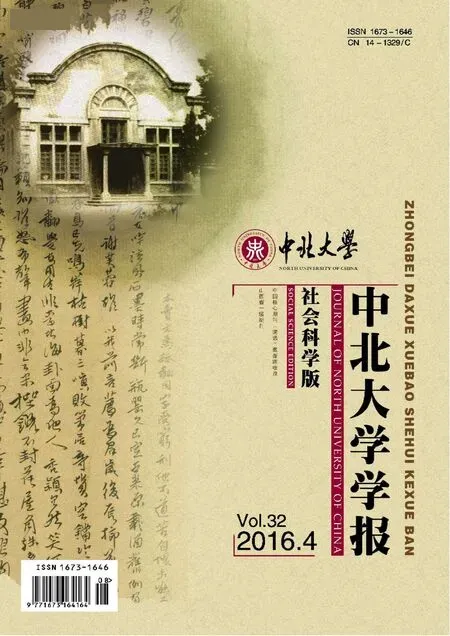北宋后期的陶潜热与宋诗学转向
王 苑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北宋后期的陶潜热与宋诗学转向
王苑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摘要:熙宁元年,宋神宗登基变法,北宋历史进入后期阶段。在诗歌领域,已经显露自家面目的宋调也在追求新变。继韩愈、杜甫之后,宋人上承中晚唐人,找到了新的诗学典范——陶渊明。故本文通过从唐代到北宋,官方民间日渐兴起的靖节祠修建与祭祀活动,从中可以窥知当时的时代精神,发现尊崇陶渊明的社会潮流及其诗学意义。尤其是宋人别具只眼地从陶诗中挖掘出的“反常合道”的奇趣诗论,更俨然成为宋人标举陶诗的最高境界与北宋后期诗学的终极目标。
关键词:北宋后期;陶渊明;奇趣;宋诗学转变
宋人言:“渊明诗,唐人绝无知其奥者,惟韦苏州白乐天,尝有效其体之作。……然薛能郑谷乃皆自言师渊明。”[1]380-381据钱锺书论,此语“近似而未得实”,唐五代爱陶学陶者犹有多人,大历诗人钱起始称及陶诗,自中唐而后,学陶诗者渐多,至两宋而极盛。[2]88-93又论以文为诗,“唐以前惟陶渊明通文于诗,稍引厥绪,朴茂流转,别开风格”,“夫昌黎五古句法,本有得自渊明者”,“渊明《止酒》一首,更已开昌黎以文为戏笔调矣”[2]73。可见,发轫于中唐,大盛于北宋,陶渊明奠立的诗学典范意义愈益突出,时至今日,依旧值得予以学术观照。
1元丰崇陶与宋调自赎
从元丰年间(1078年~1085年)开始,宋人对陶渊明的尊崇形成热潮。
首先,表现在苏轼的尊陶学陶言行上。苏轼是北宋后期文化的杰出代表,无论是他的追随者还是敌对者都受到其言论的影响,他对陶渊明的解读在陶渊明接受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而其崇陶起点则在元丰年间。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次年,欲字号“鏖糟陂里陶靖节”,此后的日常生活和读书写作多见与陶渊明相关者。[3]508王水照先生早已指出,从黄州时起,苏轼就在作品中大量地咏赞陶渊明,每逢身体不适,即取陶氏诗集阅读,反复强调陶渊明的真率自然,第一个对陶诗艺术作出正确精到的评赏,又在创作和生活中将陶潜精神的主要方面“作了引人注目的深化和突出”[4]278-300。这实在是中肯的评价。
其次,从元丰开始形成的靖节祠祭祀,也体现出北宋后期的陶渊明崇拜。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宋人的崇陶、学陶言行已探讨甚多,但往往缺乏知识社会学的视野,只关注知识精英的言论,忽视国家、社会和普通民众之间的互动机制。中国自古以来即重视祭祀,逐渐形成了丰富而系统的祭祀制度与文化。《左传》早已记载了古人的认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5]1911作为古代礼制总汇的《礼记》则指出:“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6]1602祭祀被认为是人类精神活动的首要内容,起着寄托精神信仰、传承历史传统、调节天人关系、控制社会秩序、构筑文化认同等重要作用。正如胡适所言:“一时代的精神,只有一时代的祠祀,可以代表。因某时之所尊奉者,列为祠祀,即可觇某时代民意的趋向。”北宋后期对陶渊明的祭祀即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的时代精神,从中可以发现尊崇陶渊明的社会潮流及其诗学意义。
据此,就陶渊明祭祀而言,一方面,国家通过地方政府主导祭祀,贯彻了官方对陶渊明文化魅力的解读,加强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促进了全社会对陶渊明文化的尊崇;另一方面,各地士人和地方民众的信仰得到了官方的承认,在持续的拜谒、阅读过程中加深了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的理解和推崇。由此可见,在北宋后期,国家权力、知识精英和普通民众在对陶渊明的认识上达成了一致,对陶渊明的崇拜现象折射出当时社会思想的普遍性与共通性,可以代表“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7]10-26,对陶渊明的尊崇在全社会达到高潮,从而,陶渊明对北宋后期的思想和诗歌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元丰以降,靖节祠纳入国家祀典,几经修葺,陶渊明祭祀成为国家祭祀与仪式惯例,地方政府、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纷纷拜谒靖节祠,祭祀陶渊明,陶潜热达到了高潮。这种具有外在的物质凭借与观感形式的社会现象内部,充填着人们反思历史事件、针对现实情势、遵循内心体验、因应权力控制而创造出来的意义与本质。陶潜热包含着自然、经济和社会各种要素,指涉历史与现实、儒林与文苑、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精英与庶众等诸多关系。就此而言,靖节祠,以及相应的陶渊明崇拜,是北宋后期社会关系的一种展现和依据,是文化创造的一个媒介和动力,是精神信仰的一个场所和寄托,体现时代精神,充满社会意义。靖节祠是陶渊明崇拜的产物,又反过来极大地强化了这种崇拜,推动了陶潜热。钱锺书先生曾指出:“渊明文名,至宋而极。”[2]88综上所述,渊明之名,至北宋后期而达到极盛。借助尊陶学陶,宋诗展开了自我调适与折衷,宋诗学理论也日益完善,迈向更高境界。
2杜、陶嬗代与宋诗学演变
在持续而隆重的陶渊明祭祀文化氛围中,北宋后期人普遍视陶渊明为达道的典范,把陶渊明信仰推向顶峰。中国诸家思想流派都讲求“道”,“道”是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和终极路径,宋人尤其致力于此,宋代的新儒学即为“道学”。对宋人而言,最高的评价就是“闻道”“知道”“达道”,即使是诗人,其最高境界也不是圣于诗,而是达于道。
祭祀陶潜带来了陶潜的圣贤化,其诗被奉为至尊,其人被尊为圣贤。在陶渊明与道的关系上,杜甫有个著名的论断:“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宋人尊杜甫为诗圣,但并不同意这个论断。曾巩《过彭泽》诗云:
渊明昔抱道,为贫仕兹邑。幡然复谢去,肯受一官絷?予观长者忧,慷慨在遗集。
岂同孤蒙人,剪剪慕原隰。遭时乃肥遯,兹理固可执。独有田庐归,嗟我未能及。[8]42
曾巩说陶渊明“抱道”,即是赞扬他持守正道。并认为其慷慨忧乐就表现在作品里。
北宋后期人更是直接反驳杜甫。刘攽《续董子温咏陶潜诗八首》其六云:“道术既分裂,人人得其偏。丹青照千载,始觉真检全。尔时扬仁风,到今犹栗然。”其七又云:“神释乃超然,道真于此得。”[9]7079他赞扬陶潜得到了真道。专门拜谒过靖节祠的郭祥正也推崇陶渊明,以“达道”为最高圭臬。如《夏日游环碧亭》:“微吟百忧散,达道千古同。”《颖叔招饮吴圃》:“达道齐生死,笔端真有神。” 其《读陶渊明传二首》其二反驳杜甫说:“陶潜真达道,何以避俗翁。寂寥千载事,抚卷思冲融。使遇宣尼圣,故应颜子同。”不仅指出陶渊明真正抵达了大道,而且认为他达到了孔门贤人颜回的境界。颜回是孔子最喜爱的学生,不幸早亡。古人追求的“三不朽”,他几乎全无:既无显赫功烈,也无言论著作,只在“立德”方面稍见突出,但也只是穷居陋巷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换言之,他仅仅由于能安于贫穷并乐在其中而被尊为“亚圣”“先师”,这体现出儒家“内圣”的境界。陶渊明在自传《五柳先生传》里说自己“箪瓢屡空,晏如也”,就是用颜回的典故。这说明他辞官归隐、甘于贫贱是出于效仿颜回,背后自有儒家信念在。但其《饮酒二十首》其十一又说:“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10]觉得颜子虽然身后留名,但活着时挨饿短命,一生穷困潦倒。杜甫对此评论道:“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 杜甫认为陶渊明既然觉得颜回那样的生活未免枯槁,那么陶渊明本人就没有达道。而郭祥正指出,杜甫所说有误,陶潜和颜回一样都是能耐得住贫穷寂寞并乐在其中的人,是真正达于大道的圣贤。李邦彦之弟李邦献类比说:“陶渊明无功德及人,而名节与古忠臣、义士等。何耶?岂颜氏子以退为进、宁武子愚不可及之徒欤?”(《省心杂言》) 他也把陶潜比作颜回。郭、李二人都是指出内在精神追求与得道入圣的关系。体现出北宋后期士大夫“转向内在”的思想趋向,也是当时理学家们探求“孔颜乐处”的学理组成部分。郭祥正在当时诗名甚隆,李廌甚至尊他为诗坛盟主,他以颜回比陶渊明很有代表意义。而作为儒学思想家的李邦献对陶潜的评价则意味着儒学对陶氏的尊崇。
被在野士人视作文化领袖的苏轼也认为陶渊明“知道”。其《书渊明饮酒诗后》云:“《饮酒》诗云:‘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宝不过躯,躯化则宝已矣。人言靖节不知道,吾不信也。”[11]2112这是从生死观的角度反驳杜甫。《韵语阳秋》记载得更详:
东坡拈出渊明谈理之诗,前后有三:一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二曰“笑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三曰“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皆以为知道之言。盖摛章绘句,嘲弄风月,虽工亦何补。若覩道者,出语自然超诣,非常人能蹈其轨辙也。[12]507
在苏轼看来,陶潜是“知道”之士,后者彻悟的道就体现在相关的诗句中。葛立方根据苏轼的意见,把陶渊明称作“覩道者”,是符合苏轼本意的。苏轼诗云:“渊明初亦仕,弦歌本诚言。不乐乃径归,视世羞独贤。”[11]2138又指出:“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13]15靖节之道的真谛,不在以退为高,而在破除仕或隐各执一端的执著,率性而为,绝对自由。这种自然真率,正是北宋后期人的人格理想。苏轼此论融合了儒释道的要义,新人耳目,故范温许为“发明如此”[14]316。哲宗元符三年正月,苏轼在儋州贬所,作《自书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诗并跋》,末云:“陶公此诗,日诵一过,去道不远矣。”晚年苏轼进道日深,对于陶诗所含之道体味尤深。
江西派宗主黄庭坚的态度则同中有异。他元丰三年途经江州,作《宿旧彭泽怀陶令》诗,认为陶潜能担当大道,“欲招千载魂,斯文或宜当”。他又在《题意可诗后》推尊陶诗:“至于渊明,则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并指出:“巧于斧斤者,多疑其拙;窘于检括者,辄病其放。孔子曰:‘宁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渊明之拙与放,岂可为不知者道哉?”与李邦献一样,黄庭坚也将陶渊明与古之圣贤宁武子相比拟,视陶潜为得道之圣人。他既同意陶渊明达道的观点,又不愿看到人们责难杜甫,故设法为杜甫评陶公案作辩解。针对当时人对杜氏论断的反驳,黄庭坚说:“杜子美困穷于三蜀,盖为不知者诟病,以为拙于生事,又往往讥议宗文、宗武失学,故聊托之渊明以解嘲耳。其诗名曰《遣兴》,可解也,俗人不领,便为讥病渊明,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15]49表面上,在因尊陶潜而贬杜甫的时代大潮中,黄庭坚始终坚持陶杜并举:“拾遗句中有眼,彭泽意在无弦。”指出杜甫的锤炼法度和陶潜的自然平淡都值得学习,不可偏废。但据研究,黄庭坚句法理论的最高蕲向是“无意为文”,杜甫“句中有眼”只是艺术技巧层面的相对自由,与陶潜“意在无弦”的主体精神层面的绝对自由,尚隔一关。陶诗“不烦绳削”的直截自由,使其成为了超越于杜甫之上的最高诗学典范。
在郭祥正、苏轼、黄庭坚这些文化名流的影响下,陶渊明成为宋人心目中公认的诗、道双至的楷模。谢薖《陶渊明写真图》说:“此公闻道穷亦乐。”“穷亦乐”是将陶潜与颜回比拟,“闻道”是直接赞扬。又有《亦爱轩》云:“漆园游濠梁,得意鯈鱼乐。渊明爱吾庐,感彼众鸟托。两贤俱达道,妙处要商略。夫子谁与归,潜也如可作。” 谢氏以庄子比陶潜,认为两人皆已达道,但陶潜更胜一筹,倘若能学陶氏,就不愿跟从庄子。特别是徽宗朝的政治形势,世路艰险,更要铭记归去之志。与惠洪交往的许顗称:“陶彭泽《归去来辞》云:‘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是此老悟道处。若人能用此两句,出处有馀裕也。”[16]401这是陶渊明觉悟大道的典型例证。程俱为了“叙出处之意”而作诗称颂陶渊明,说“靖节直有道,高怀俯黄园”,也是在强调出仕归隐之道。
需要指出的是,苏黄等“元祐党人”以渊明为“达道”,并没有遭到政治反对派的反对。蔡京之子蔡绦《西清诗话》说:“陶渊明意趣真古,清淡之宗。诗家视渊明,犹孔门视伯夷也。”[17]179以孔子尊崇的大圣人伯夷来比陶潜,不亚于郭祥正等人视陶渊明为亚圣颜回。有论者以为《西清诗话》所论与“熙宁党人”不同,但据张伯伟先生研究,《西清诗话》是在蔡京授意下撰成,虽多载元祐诸公语,其实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伺机攻讦对手。因此,此处对陶潜的好评无疑代表了新党的意见。在综合评价陶渊明时,旧党与新党都认同他已经“绝类离伦,优入圣域”,这充分说明,在北宋后期,全社会的知识精英在对陶潜的崇拜、信仰方面达成了共识。
北宋后期的这场陶潜热,体现出士大夫心态和诗学的转变。北宋中期,以范仲淹为首的庆历士大夫满怀忧患意识,以杜甫为诗学典范,以良相为事功追求,充满以天下为己任的“外向”精神。至北宋后期,形格势禁,许多士大夫纵使身处魏阙之下,也心在江湖之上。乌台诗案、车盖亭诗案、政和文忌等文字狱不断,引发了诗人的不满和疑惧。特别是徽宗一朝,新党在政治上占据绝对优势,旧党子弟长期被迫在野,难有作为。“元亮惟知隐是真”,遗世退隐、坚持真我成为新的时代风尚。在诗学领域,一味追求干预现实、过度讲求锤炼句法,也导致宋诗缺乏温柔敦厚之气,丧失自然平淡之趣。[18]333-346有鉴于此,士大夫遂从“外向”的淑世关怀,转向“内在”的精神超越,诗学以平淡自然的陶潜为宗,思想以箪食瓢饮的颜回为圣。北宋中期,海内尚称苟安,如文同所感“也待将身学归去,圣时争奈正升平”(《丹渊集》),知识人肯定陶潜,但仍期待有所作为。南渡初期,国难当头,张元幹感慨“古木寒藤挽我住,身非靖节谁能留”[19]289,陈与义疾呼“中兴天子要人才,当使生擒颉利来。正待吾曹红抹额,不须辛苦学颜回”[20]477,陶潜、颜回无助于抗敌救亡。历史留给陶渊明其人其诗产生最大影响的时空,只在北宋后期。起初,正如苏轼同年进士黄履所说,“少陵怀北阙,靖节傲东皋”[9]7484,前者济世,后者自适;又如曾巩所论,“少陵雅健材孤出,彭泽清闲兴最长”[8]118,前者富于才学法度,后者美在天性兴趣:要之,陶潜与杜甫本各擅胜场,适可互补。但最后,在浓烈的崇拜氛围中,苏轼告诉苏辙“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21]1110,范温评论“古今诗人,惟渊明最高”[14]374,陶潜被尊为诗中至尊、人中圣贤,跨越儒林和文苑的领域,身兼杜甫与颜回的角色,独领风骚。北宋后期人圣化陶潜,引领道学关注内在心性,诗学也展开自赎的反思与调适折衷的策略,宋调在曲折中进一步演变,呈现出“奇趣”。整个宋代的学术文化形态由此发生重大转向。
3北宋后期的“奇趣”诗学
从天圣到庆历、嘉祐时期,北宋人师和法韩愈、杜甫,在诗中探索人与自然、社会和自我的关系,以文为诗,穷理尽意,力求绪密而思深,催生出成熟的宋调。然而,对现实政治的过分介入容易使诗等同于文,北宋后期的政治运作方式也难以容忍诗的讽谏教化,过分的语言锤炼也使得理性之斧凿破混沌七窍,诗作缺乏自然浑融之美。北宋后期,在陶潜崇拜的文化氛围中,诗人们展开调适、矫正与反思,以尊陶学陶为契机,发掘出新的诗歌审美范畴——奇趣,从而使宋诗学再次得以发展、演进与更新。
以“奇趣”论诗始于中唐。释皎然《杼山集》卷十《四言讲古文联句》载潘述句:“灵运山水,实多奇趣。” 皎然称谢灵运山水诗多奇趣,但具体涵义不明。白居易《读谢灵运诗》有“谢公才廓落,与世不相遇。壮志郁不用,须有所滞处。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指谢灵运怀才不遇,发而为诗,其山水诗包含奇趣,即使在即事写景时也不忘比兴讽谕。
明确给诗歌奇趣作出定义的是北宋后期的苏轼。元丰四年,苏轼谪居黄州,作《书唐氏六家书后》,首云:
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返造疏淡。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覆不已,乃识其奇趣。[11]2206
苏轼首次在陶渊明诗里发现“奇趣”,表现为初读起来似乎散缓不已,反复多遍后乃体味到其诗的至境。这是以陶潜为奇趣的典范。释惠洪《冷斋夜话》载:“东坡尝曰: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 惠洪当是从上述题跋转述。“句”或乃“趣”之讹,南宋《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竹庄诗话》等著作转引惠洪记述时皆作“奇趣”。《冷斋夜话》卷五又载:
柳子厚诗曰:“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然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东坡云:“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熟味此诗,有奇趣。然其尾两句虽不必亦可。”[22]50-51
苏轼先提出诗的根本是奇趣,评价标准是反常合道,再评定柳宗元《渔翁》诗符合此标准。全诗通过在山水中独来独往、自遣自歌的渔翁形象,表现出寄情山水、任运自然的深刻哲理,语浅而道深,似奇而合理,这就是“奇趣”。综合苏轼的题跋和惠洪的转述,可知苏轼作诗的本旨是表现奇趣,而陶诗则是奇趣的典范,柳宗元某些诗亦具奇趣;奇趣的表现方法和评价标准是反常而合道。
苏轼因“乌台诗案”而遭贬黄州以后,对社会、人生的态度都发生了重大转变,对陶潜仰慕不已,作诗也初露淡远风格;贬谪惠州、儋州后,更是以陶渊明为作诗圭臬,正有得于对陶诗“奇趣”的发现。元丰六年,他作《王定国诗集叙》,犹称“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但只是从政治上肯定:“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11]318苏轼晚年则从艺术上认为杜诗于陶诗的“高风绝尘”有所不及,并进而强调“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李杜等一切诗人皆不如陶渊明。至于赞赏柳宗元《渔翁》诗有奇趣,则是由于他深感柳宗元诗有陶诗之味:“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11]2109李杜虽凌跨百代,但缺少陶渊明等魏晋诗人的“高风绝尘”,“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馀子所及也”[11]2124。“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这些赞语都与“初若散缓不收,反覆不已,乃识其奇趣”一脉相承,涵义相近。
苏轼的奇趣说以陶诗为最高境界,其标准则受到禅宗思想“反常合道”的启示。据周裕锴先生研究,“反常”亦作“返常”,尽管“反常合道”的思想出现很早,但“作为固定的语言搭配或术语,它却常常出现在禅宗语录中”,后来成为禅宗常见的话头之一,苏轼借此宗门语来说明诗歌的创作原则和批评标准,“反常合道”即“超乎常规,合于常理”[23]112-114。“奇趣”即指“诗歌超越常情识解而合于义理大道的艺术趣味”[18]317。清吴乔阐发奇趣说:
子瞻云:“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此语最善。无奇趣何以为诗?反常而不合道,是谓乱谈;不反常而合道,则文章也。[24]475
不反常而合道,是文章,不是诗,也就是说,没有奇趣便称不上诗。正如有的学者指出,苏轼的奇趣说“抓住了诗的‘诗性’,即审美本性”,是江西派“活法”说的先声。[25]520-523正如苏轼称扬陈师道诗时提出,“凡诗,须做到众人不爱、可恶处,方为工”,所论也是反常合道之意。
王安石是苏轼的政敌,但对陶诗奇趣的认识却与苏轼一致。陈正敏《遯斋闲览》在评述欧阳修、黄庭坚、苏轼推崇陶潜后,又称赞王安石:
荆公在金陵,作诗多用渊明诗中事,至有四韵诗全使渊明诗者。又尝言其诗有奇绝不可及之语,如“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由诗人以来,无此句也。然则渊明趣向不群,词彩精拔,晋、宋之间,一人而已。[13]18
陈正敏所谓“趣向不群”,正可与王安石所论“有奇绝不可及之语”互释,则安石所称,亦指向陶诗的奇趣。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其五首四句,居住在人来人往的环境中,却没有车马的喧闹,此谓“反常”;超脱于世俗利害、荣辱得失,疏远了车马喧闹所象征的上层官僚社会,居处故能僻静,此谓“合道”。另一方面,这四句看上去如同口语,实质结构异常严密,看不到生硬的雕琢痕迹而意趣高远,与王安石赞赏张籍的“看似寻常最奇崛”甚为契合。这与苏轼说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初若散缓不收,反覆不已,乃识其奇趣”“反常合道为趣”等言论如出一辙。
黄庭坚也赞赏陶诗的反常合道。他在《题意可诗后》曰:
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语俗:此庾开府之所长也。然有意于为诗也。至于渊明,则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虽然,巧于斧斤者,多疑其拙;窘于检括者,辄病其放。孔子曰:“宁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渊明之拙与放,其可为不知者道哉?……以法眼观,无俗不真。以世眼观,无真不俗。渊明之诗,要当与一邱一壑者共之耳。[26]1427
在黄庭坚看来,陶诗的拙与放正是其高不可及之处。“谢康乐、庾义城之于诗,炉锤之功不遗力也。然陶彭泽之墙数仞,谢、庾未能窥者,何哉?盖二子有意于俗人赞毁其工拙,渊明直寄焉耳。”[26]1428“不烦绳削而自合”、愚拙、无意于俗人赞毁,就是苏轼“初若散缓、实有奇趣”。黄庭坚的创作也是以此为终极追求。需要指出的是,在禅宗语言里,“反常合道”又作“反俗合真”。因此,黄庭坚此处所论“无俗不真”,实际就是苏轼所论“反常合道”。
陈师道对陶诗的奇趣也深有体会。众所周知,陈师道作诗师法黄庭坚、杜甫。但据他晚年自述:“此生精力尽于诗,岁末心存力已疲。不共卢王争出手,却思陶谢与同时。”[27]153-154陶谢在唐代被人并称,但在宋代,对二人的评价已大有轩轾,前引黄庭坚语即抑谢尊陶,陈师道此诗亦偏指陶渊明,并用陶谢只是为了与卢照邻、王勃形成对仗。可见陈师道暮年倾慕的诗学典范乃是陶潜,遂有“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诗文皆然”[28]311的朴拙、反俗的创作告诫语。以此观照其以下言论,则见其独具深意:
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退之于诗,本无解处,以才高而好尔。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尔。学杜无成,不失为功。无韩之才与陶之妙,而学其诗,终为乐天尔。[28]304
这段话可视为对中唐到北宋诗学楷式与典范嬗替关系的简要论述。白居易到此时,评价已偏低,韩愈以才学为诗,不易学,陶诗无法无痕,不可学,可学者乃杜诗。表面上,陈师道主张学诗要以杜甫为师,其实只是因为其诗有法度规矩,容易入手,并非最高境界。最高境界非陶诗莫属,无意于专门作诗,而自然表现出胸中之妙。妙者,奇趣也。陈师道最终举起以朴拙、无法、反俗达到奇妙的理论旌旗,而以陶渊明为具体指向,与苏轼、黄庭坚后期的诗学取向是一致的。
北宋末期,祖述苏黄诗学的是僧惠洪大力推广苏轼的奇趣说。其《冷斋夜话》卷一载:
东坡尝曰: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如“日暮巾柴车,路暗光已夕。归人望烟火,稚子候檐隙。”又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又曰:“霭霭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造语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不知者疲精力,至死不知悟,而俗人亦谓之佳。如曰:“一千里色中秋月,十万军声半夜潮。”…… 皆如寒乞相,一览便尽。初如秀整,熟视无神气,以其字露也。东坡作对则不然,如曰“山中老宿依然在,桉上《楞严》已不看”之类,更无龃龉之态。细味对甚的而字不露,此其得渊明遗意耳。[22]52
“日暮”四句出江淹拟陶诗,即《杂体三十首·陶徵君田居》,“采菊”二句出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其五,“霭霭”四句出陶潜《归园田居》其一。惠洪评此数首均无斧凿之痕,而寓意远妙,正合于苏轼对奇趣的解说。说苏诗得到陶诗的遗韵,即是说苏轼亦具有奇趣。惠洪《天厨禁脔》又云:
诗分三种趣:奇趣、天趣、胜趣。《田家》:“高原耕种罢,牵犊负薪归。深夜一炉火,浑家身上衣。” 江淹《效渊明体》:“ 日暮巾柴车,路暗光已夕。归人望烟火,稚子候檐隙。”此二诗脱去翰墨痕迹,读之令人想见其处,此谓之奇趣也。[29]126
赞扬诗歌“脱去翰墨痕迹”,亦即无斧凿痕迹而具深意远韵。以奇趣论诗贯穿惠洪的一生,他多次直接借用苏轼评陶诗语,如《送觉海大师还庐陵省亲》云:“此诗语散缓,细读有奇趣。”又常常直接以奇趣作为诗歌评鉴的最高标准,如《次韵游方广》:“临高赋新诗,妙语发奇趣。”其《冷斋夜话》指出:
众人之诗,例无精彩,其气夺也。夫气之夺人,百种禁忌,诗亦如之。富贵中不得言贫贱事,少壮中不得言衰老事,康强中不得言疾病死亡事。脱或犯之,谓之诗谶,谓之无气,是大不然。诗者,妙观逸想之所寓也,岂可限以绳墨哉?如王维作《画雪中芭蕉》,诗眼见之,知其神情寄寓于物,俗论则讥以为不知寒暑。荆公方大拜,贺客盈门,忽点墨书其壁曰:“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欤寄此生。”坡在儋耳作诗曰:“平生万事足,所欠惟一死。”岂可与世俗论哉!予尝与客论至此,而客不然吾论。予作诗自志,其略曰:“东坡醉墨浩琳琅,千首空馀万丈光。雪里芭蕉失寒暑,眼中骐骥略玄黄。”[22]42-43
作诗就要以“妙观逸想”冲破世俗的各种禁忌,世俗所不通的、所讥笑的,正是诗的真气所在。“诗眼”指诗歌独具的审美本质,“俗论”相当于日常生活及其逻辑。惠洪以二者相对立,可谓直探诗心,亦近于苏轼所谓反常合道。
4结语
北宋后期,王安石的“荆公新学”是在朝显学,苏轼是朝野一致推崇的大诗人,黄庭坚、陈师道是在野诗人们的代表。此外,黄庭坚是站在诗学、理学和禅学交界处的杰出人物,惠洪是在朝野均有影响的诗人和佛学家。以上诸家对陶诗奇趣的推崇、反常合道诗法的提倡,在全社会影响巨大,诗人们或引用,或实践,将之引向深入。如李复《读陶渊明诗》:“渊明才力高,诗语最萧散。矫首捐末事,阔
步探幽远。初若不相属,再味意方见。旷然闲寂中,奇趣高蹇嵼。”[9]12407陈渊《越州道中杂诗十三首》其八:“渊明已黄壤,诗语馀奇趣。我行田野间,举目辄相遇。”均从苏轼之说。可见,以陶渊明为典范的奇趣说俨然成了北宋后期诗学的终极目标和典型标识。
参考文献
[1]蔡启.蔡宽夫诗话[M].宋诗话辑佚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
[2]钱锺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孔凡礼.苏轼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98.
[4]王水照.苏轼创作的发展阶段——苏、辛退居时期的心态评议[G]∥王水照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5][春秋]左丘明.左传[G]∥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6][西汉]戴圣.礼记[G]∥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7]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8][宋]曾巩.曾巩集[M].陈杏珍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
[9]傅璇琮,倪其心.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10]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3.
[11][宋]苏轼.苏轼文集[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12][宋]葛立方.韵语阳秋[G]∥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
[13]胡仔.苕溪渔隐丛话[M].廖德明,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14]范温.潜溪诗眼[G]∥宋诗话辑佚.北京:中华书局,1980.
[15]王直方.王直方诗话[G]∥宋诗话辑佚.北京:中华书局,1980.
[16]许顗.彦周诗话[G]∥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
[17]蔡绦.西清诗话[G]∥张伯伟,编校.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18]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9]曾季貍.艇斋诗话[G]∥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2006.
[20]陈与义.陈与义集校笺[M].白敦仁,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21]苏辙.苏辙集[M].陈宏天,高秀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
[22]惠洪.冷斋夜话[G]∥张伯伟,编校.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23]周裕锴.文字禅与宋代诗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24]吴乔.围炉诗话[G]∥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5]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6]黄庭坚.黄庭坚全集[M].刘琳,校点.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
[27]陈师道.后山诗注补笺[M].冒广生,补笺.北京:中华书局,1995.
[28]陈师道.后山诗话[M].历代诗话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
[29]惠洪.天厨禁脔[G]∥日本宽文版.张伯伟,编校.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The Fashion of Worship TaoQian in Late Northern-Song Dynasty and the Change of Song Dynasty Poetics
WANG Yuan
(College of Literature,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Abstract:The first year of Xining period,Emperor Shenzong of Song began to hold the reign of song dynasty political reform,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history in late stage.In the field of poetry,has revealed the face of their own age also changes in the pursuit of new.After Han Yu,Du Fu,poets begin to find a new poetics model,Tao Yuanming.So in this paper,from the Tang dynasty to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the official and the folk were surging to build Jingjie temple and hold ritual activities.We can know the spirits of the Times ,find that the social trends of exalting Tao Yuanming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poetry.Particularly,the Song dynasty people did have an original view to excavated the connotative meaning from the Tao’s poem ,such as the fabulous poetics,“abnormal but reasonable”,which has become the highest standard for the creation of poetry of the Song,at the same time,the aesthetics of Tao’s poetry has become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 late Northern Song dynasty poetics.
Key words:the lat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ao Yuanming; Abnormal but Reasonable; the change of song dynasty poetics
文章编号:1673-1646(2016)04-0016-06
* 收稿日期:2016-03-18
作者简介:王苑(1989-),女,博士生,从事专业:唐宋文学与文论。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3-1646.2016.04.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