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乡
熊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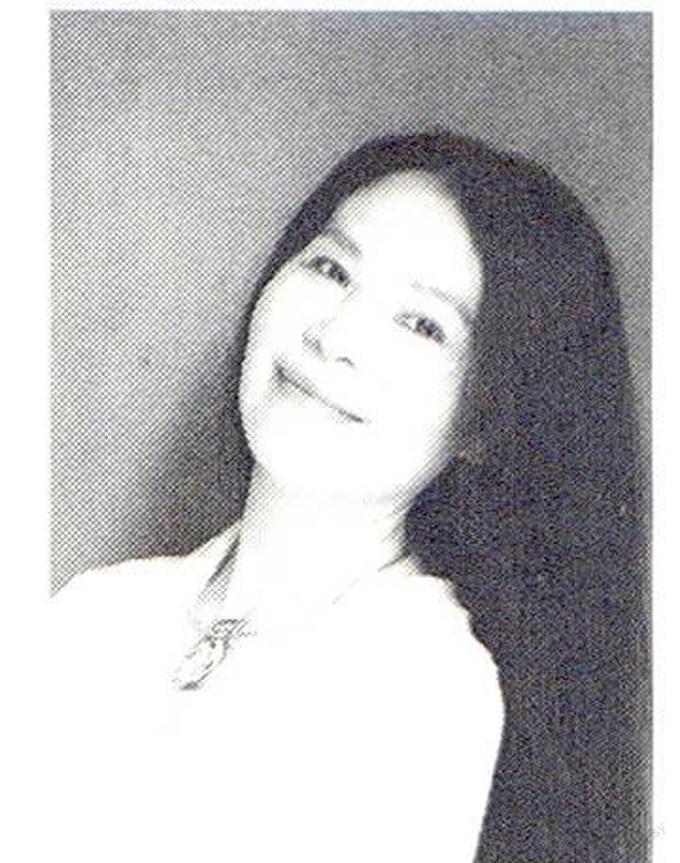
一
“前世,我是做了什么坏事吗?”老人蒋淳英看着我。她立在门侧,身后以及周遭的泥墙,将屋内的光线吮吸殆尽。“不然,我的命咋会这么苦?”她问。
华发满头,她将发丝熨熨帖帖梳在脑后。发梢处,束成两团元宵般的小鬏。
因为瘦小,恍然间,你总以为,是一位小女生在暗处絮絮呢哝。
我将满眼泪花的老人淳英揽过来,“我们去屋外坐下来慢慢说,好吗?”
于是,金秋,在秦巴山南麓的群峦之中,四川广元苍溪县月山乡的这座小山村,在一排“尺子拐”土坯泥屋半围的晒坝里,我倾听——
1950年出生的淳英只念到小学二年级,因为家里替生产队养牛,母亲需要帮手,一对弟弟妹妹需要照顾,她辍学了。
从河坝那边的小山村嫁到这山中来,那年,淳英十八岁。
夫家人口薄少,丈夫是独子,也是这户朴素人家的养子。土屋,老灶,门前有树,有狗,不远处有粮田,有菜地。她与她的公公、婆婆、丈夫,还有之后来到人世的她的三个孝顺女儿,一家人就这样平平静静在这里度着时光。
她很满足于这样的平淡日子。一只狗莫名地一声叫,感应似地,整个山坳里的狗,都次第叫开来。大欢大愉地叫。日子很慢,天亮披衣下床,照料家禽,照料人,然后出坡,打理田地。
那些田里地里水库里的家禽,白天孩子似地跑出去,天色渐晚,又一只只牵着线似地往家回。
这个小家庭的平静,是从六年前被打破的。
深秋地里点麦子时,淳英发现丈夫新奎老捂着肚。汗珠缀满额头。他陪丈夫去乡上检查,医生回,慢性胃炎。
每天一服中药,如山里不疾不徐的日子,人就这样将息着。
新奎的疼痛在加剧。后来,山塆里,谁家都能听见新奎在床榻上的呻吟声。三个女儿分别在上海和四川的广元、巴中打工,淳英给远在上海做工的大女儿玉琼打去电话。
后来,新奎被送往县城医院复查,诊断结果,肝硬化。
经过长长一年多的治疗,新奎最终还是走了。走在第三个年头的初春。
这个小家如果没有那些个病魔作祟,土屋里的日子当是如意吉祥的。但是淳英的家遇上了,他年迈的公公和婆婆,彼时,都因病抱憾而去。
给新奎烧“三七”那日,那个黄昏,淳英独自一人上山。是不是心事重重,新奎葬在高高的山腰上,烧完纸下山的路上,一截树枝拦路,她被拌了一下,竟一头栽在了地上。
人如中魔咒,她就那样倚靠着湿漉漉山石树丛而坐,动弹不得。
她八十三岁的娘家母亲第二天叫来了医生上门,她被告之,肋骨多处骨折。
一年后,淳英在上海做工的大女儿玉琼又被查出肝病。
所有的劫难对于这个只剩下女人的家庭而言,仿佛来得太急太快。
玉琼做手术那日,从广元和巴中赶去上海的玉琼的两个妹妹,扑通一下,径直跪在了那位手术医生面前。但医生打开玉琼的腹腔后,未敢去触碰那个“瘤”,最终缝合上了。
在四川,在秦巴山脉深处的这一处农舍里,那些日子里,淳英泪如雨下。她的娘家母亲那日再度从河坝那边上山来,老母叹,“我都八十多岁人了,老天爷要带就把我带走吧,把我的孙女,留下!”
回家后的头一天,淳英记得,母亲下田割了谷子。那个上午,母亲晒好谷子,做好午饭,手起手落端碗吃饭的刹那,她倒在了地上。
突发脑溢血。老母从发病到离世,仅十五天。
但老天爷并未顺遂这位八旬老妇的心意,她的孙女依旧病着,孙女与病魔拉锯抗争如今已三四年。上海打工十年攒下钱在广元置下的房,卖了。前后八次手术引流腹水,如今,她的孙女玉琼的腹部,伤痕满布。
避世而居,不谙人间事,晚年的淳英如今仿佛大梦方醒,淳英没有购买“农保”。而一户一个名额的“低保”资格,她又让位给了急需用钱、病中的玉琼。也就是说,每个月,走过一个多甲子的淳英不似其他山村里的老人,她没有分文现金收入。
老伴走了,两个小女远嫁户口被迁走,淳英、玉琼,以及玉琼丈夫和女儿,一家四口人的几亩田地,是老人淳英晚年每日每时生活意义的全部。
此外老人所养的一头猪,五只老鸭,还有十五只小鸭,这些,成了这位山里母亲经济来源的全部依托。
淳英不愿跟孩子们去城里度日,倒是几个孩子 在城里吃的米和油,差不多都源自淳英之手,源自那几亩良田。淳英悉心侍弄着那些土地,那是一位山里母亲的另一种“盼头”。我去的头一天,据说淳英正好托镇上的长途车司机,给她在广元治病的女儿玉琼捎去了二十斤米、一壶油,还有一百个鸭蛋和一只老鸭。
山里人过日子,地里有嘴里就有,钱,孩子们可以自己去想办法,这位个子不足一米五高的母亲所愁的是:可还有回天之药,可救她的玉琼的命?
“我这一世,连蚂蚁都不踩的人……”
晒坝里,穿得整整洁洁的淳英,用生满老茧的一只手去拭泪,而另一只眼里的泪滴,又盈出眼帘。
二
每人六元钱,村里几十个人包下了一辆解放牌敞篷汽车。早春晓风刺骨,但挤在人丛中的少年勇益,他并不觉得冷。
从白驿镇,过苍溪,到广元,少年乘了大半日的车。车到广元后他与兄长方知,开往河北的列车,所有车次的票早已售罄。三个少年——勇益、勇益的哥哥,还有勇益的一位同学,所带干粮悉数吃完,他们索性睡觉,展开行李,躺在露天的站台上睡。
被困三天,第四天他们终于上了车。购得站票的他们,选择了厕所旁的过道而坐。他们需要卫生间里的那一股涓涓细水,维持生命。
饿了整整六日,到达河北那晚,砖厂的伙计做了一大锅面片,须臾之间他们给吃了个精光。三个少年一直睡到次日日落时分才醒来。
那时的勇益想到的是他于十二岁时写下的一篇作文,“我的妈妈”。老师念给全班同学听——妈妈在他七岁时过世了,九岁的他,那年终于有了人生的第一双鞋。那是他的奶奶找本队的人要来的一双鞋……记事起,妈妈总是病恹恹……
是什么因缘让勇益迈出了打工这一步?继母?担心父亲两头为难?还是家穷,只想跟着哥哥走出去?
那一年,1990年,白驿镇岫云村辍学的少年陈勇益,十六岁。
“童工”陈勇益,在这家民营砖厂所做的工作是运砖。用手推车运送砖。四五百米不等的一段路,他来回运送。每趟5分钱。
这工作,少年最没有把握的事,是初春那半尺深的雪,车轮碾在上面,梦幻般缠绵,使不上劲。
少年年末回到家,他带回了现金200多元。
此后的岁月少年一路打工,从少年打到了中年。前后二十余载。文化不高,漂泊异乡的勇益最难忘的是那一回。
“人进砖厂,牛进磨房”。那年出门前,他的哥哥与他商量,听说煤矿挣钱多,一起去山西挖煤吧。他们买下了去山西的车票。
煤矿在山里,山上没有生活用水,得由毛驴运水上去。初来乍到,那晚兄弟俩站在煤窑洞口,没走几步路,再也不敢前行了。“尺八煤”,即最高处约八十厘米高的煤窑,从里出来的人,除了眼与牙雪一样白,浑身漆黑。
夜半,兄弟俩起身逃跑。跑出约两里地时,后面有人追来了。他们翻山越岭,往人迹罕至的地方跑,往深山沟里藏,颠沛了三天三夜,方才脱险。
最后一次打工,是2014年在新疆。勇益独自乘火车去。一下火车,四下戒严。后来知道,他们的车次与新疆乌鲁木齐火车站“暴恐案”,从时间来看,擦身而过。
被囿于工地,不能出入,四十一岁的勇益那时躺在工棚里反复自问:为什么要出来?如今在外,活难找,薪难讨,背井离乡,流离……流离……不出来,真的,不行吗?
为什么要出来?!
三
八零后大学生李君,从2008年开始,就思考着他的小舅舅陈勇益六年后才开始问天的问题。
苍溪距地震极重灾区广元青川县不远,2008年“5·12”地震那天,李君从那一刻开始到晚上,一直给家里拨电话。无法接通。夜里,终于联系上母亲,母亲的第一句话是,“要死,我们一家人,一定要死在一起!”
以志愿者的身份,李君从成都星夜兼程往家乡往大山里赶。这一趟回家,他至今未“返”。
大山里出一名大学生不易。
上世纪的90年代初,山里的孩子,仍旧在为着每学年并不多的几元学杂费烦恼。交不上学费,老师会让那些学生站着听课。小李君就那样,常常孤零零站在自己的课桌前。
上学放学路上,大眼睛圆脸的男孩李君总一边走一边哭。那时节,他听见妈妈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等卖了猪,妈给你交学费。”
男孩的妈妈后来去集市上摆地摊。逢场,他的妈妈把从县里进来的针头线脑日用百货,列在街头。那日,李君看中了别家地摊上的一件夹克,八块钱。他去找妈妈。妈妈自是不舍得钱。李君从场头哭到场尾,那天他的妈妈也来了气,追打他,从场头打到场尾。
更小时,家里修房子,请来人烧窑,两斤肉要待两天的客。是不是知道无望,小李君站在院子里抽噎跌足,“老子要吃肉,老子要吃肉……”
愤怒的“老子”没能如愿。
去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报到那天,他的母亲也是第一次上成都。大学在成都建设路附近,母子俩站在建设路边问道“建设路”,一位三轮车夫走过来,拉着他母子跑了一会又回到了原地不远处。李君的母亲下车后哭了。不仅仅是为了那三元钱的人力车费。
那时的李君只有一个想法,留在城里,成为这座大城市的主人。
与李君当年一起打拼的大学同学舒义,如今已是一家即将上市的公司的老板。2008年,李君辞别好友舒义,回到了家乡岫云村。那天他径直去找到村主任侯俊益。他问侯叔,我怎样才能留下来,同时,能够为家乡做点事。
他侯叔使出一计,先做村主任助理,然后参加一年后的村支书选举。
全国最小的“官”,而且是这个小“官”的助理,拿
着这张“令牌”,年轻人李君自费出发了。
他去名噪一时的彭州市宝山村取经,村支书贾正方慷慨捐资10万元,以资助岫云村的道路建设。苍溪县慈善家地产商冯文忠后又捐助了20万元。至此,遥远的小山村岫云村,有了那条如锦似帛缭绕丛山中的水泥路。
再之后,村民小组的“组”级公路,也先后贯通。
岫云村村党支部换届那日,25岁奶气未脱的李君站在台上,全村27名党员,他得24票。
2010年后,静心下来的村支书李君开始和“班子”成员思考另一个大问题。农村如今最严峻的问题是乡里没有人,劳动力大量外出,家里留下老人、孩子和妇女,他们怎么办?农村经济怎样突围?
那日一位看着他长大的老人取笑他,“你们干部让我们去做的,我们偏偏不会去做”,有本事,把我家养的鸡呀鸭呀猪肉呀,给我变成钱!
“乡村经济”的个体性、它的“小”,小到费孝通时代,费母当年出嫁时,他母亲的母亲陪嫁给女儿的是一台织布机。以个体以家庭为单位,小农经济小规模经营,点点滴滴的家庭细小经济补给,构成了上世纪一辈又一辈人,乡村自然经济的基础。
岫云村与中国大多数的乡村一样,“规模化”种植过各种果树,经济作物,但最终这些规模化效应给乡村酿成苦果。曾经有村民把一种叫 “脆香甜”的柑子,一背一背给村主任侯俊益家门前垒了一地。
李君悄悄回到了成都,他念大学的地方。他从成都请回来了摄影师,给村里的每一个老幼拍照。他要给城里人在乡下找个“亲戚”——让城里人吃到最放心,最天然的绿色食品。同时,给他家乡的父老乡亲——那些老人和妇女,给暮气沉沉的山村觅一条出路。
几十个笑靥如花的老人、妇女,还有留守于家的孩子们的彩色照片,印刷在了一张鲜艳瑰丽的宣传单上。李君记得拍照那天,山里的人们奔走相告,许多老人一世没出过大山,过世时,在子女们返家合影的照片上“挖”出一个头像,了事。摄影师进山了,有讲究的老人蘸清水梳头,梳了又梳。衣角整了又整。
李君拿着这些宣传单开始去成都为他们寻“亲”。
机关单位是进不去的,他去民营公司。公司一般设四道岗,第一道岗是大门,第二道是办公楼门,第三道是部门经理门,最后一道,才是他要找的“寻亲”对象,总经理的门。但是每一道门,都不是为他而开的,无论机关还是民营公司,所有的大门外都贴着纸条,“推销人员禁止入内”。
李君站在门口佯装等人,员工刷卡进门的刹那,他瞄准机会,尾随而入。一道一道“防线”,他就这样突破。
好几次,总经理靠在老板椅上,斜睨他。李君跟对方说,“我不是乞丐,我的父老乡亲们也不是,我是村支书。”
许多时候,话说不下去了,他垂目端详宣传单上面的那一张张他熟悉的脸。
苍溪,国家级贫困县,境内的岫云村,耕地659亩,荒地占240亩。全村944人,400多强劳动力外出,村里如今剩下,老人300多人,儿童70多人,妇女几十人……这是这个村庄的现状,也是大多数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
他抬起头来继续迎战另一道“防线”,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彼此信任。
2013年4月,“合村并校”关张多年,杂草丛生的岫云村小学的大门再度被打开。全村老少都来了。他们来到这里欢迎来自成都、重庆、绵阳还有乐山的两大车“亲人”。这一天,远方亲人们一下子在这里签订了约53万元、由村里的老人和妇女们 “生产”的订单。
农妇郑慧家用粮食和青菜青草饲养的生态猪,那时当地市场价行情1000多元一头,远方亲人“以购代捐”,给出了每头3000元的爱心价。村民一组小组长李雪云老人家的生态猪,也以同样价格成交。
村主任侯俊益算过一笔账,53万元的订单,按岫云村留守在家、尚有“生产”能力的186个老人和几十个妇女计,可实现年人均增收2000多元。
“省亲”现场,28岁的李君,记得自己只对他的父老乡亲说了一句话,“贫穷不是别人‘施舍我们的理由,我们有手有脚,我们要有尊严地,活着!”
四
大山里,每一位耄耋老人,每一位背着重担蹒跚行走的妇女,都是“远山结亲”计划里的生产主体,一个独立“生产作坊”的有价值的工人。
“作坊”大了,对接每一个“作坊”的端口,变成了岫云村“农村合作社”。如今,有了民间资本的进入,“合作社”升级成了 “电商”,由公司化运作。
电商的末梢,一端在乡村,一端接都市。城市客户如今直逼5000家,签约生产合同的乡村“作坊”,目前已上千户。
今年30岁的李君未曾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办起如此规模庞大的“养殖场”,在没有半寸工厂厂房的前提下。
李君爱发微信,他的“朋友圈”里,转发有这样的内容:《农业资本化威胁中国》。
文章讲述香港理工大学学者严海蓉和四名青年学者在三农问题上,发出的与“主流”不同的声音。中国农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迁,学者们认为,城市工业资本大举进入农村,是与广大农民争夺利益,而不是形成互补,这是当前三农问题面临的新挑战。
在这群年轻的学者们看来,小农经济,小规模经营,仍旧是我国当前农村的经济主体。
他爱在“朋友圈”里发感慨: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晒家乡风光)。
九十岁的老人(一老人田间劳作背影)
老了就回农村吧!(点评转发文章《揭示4600 万老年农民工生存现状,夹缝中的苦与累》)
……
李君的语速不算快,但在交谈中,信息量大亮点多。那晚在他家乡小镇的一家客栈里聊天,我不得不收起笔帽开启录音:
“跟Uber经济一样,利用互联网来解决市场刚需。Uber是将民间闲余的私家车辆,分享于社会。我们现在做的,正是在利用这种‘分享经济模式,来解决生态农产品的卖出难问题,继而解决生态农业的刚需问题。”
“互联网的出现,不是‘消灭农民,而是保障最末端农民利益,让农民利益更大化……”
“互联网只是工具……”
落在实处,我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淳英老人,公司数月前签约的这位乡村“工人”的利益。
公司目前给老人签订的“合同”,事关今年和明年。今年淳英家愿意出售的只有3只老鸭,每只按80元计,如果立即出售,老人足不出户,能收成240元。
明年,老人在喂养自家“年猪”的同时,完成“合同”里一头生态猪的生产任务。合同价,这笔收入2000元。除去现金成本购买猪仔420元,十个月需要喂养玉米500斤、黄豆50斤、糠500斤,以及田间地头的草料等,因这些粮食都是自产,如不纳入现金成本核算,按村主任侯俊益的计算“公式”,淳英的纯收入,可在1580元。
侯主任的算盘也敲过另一笔账,如喂养饲料猪,生长周期虽短,一年理论上可出栏两槽,但除去饲料费用以及市场销售价格因素,两槽猪收益相加,与一头生态猪的价,相差无几。
年收入1580元,平均每月约130元,这差不多是一个农村老人一个月的“农保”,加上一个月“低保”的津贴。也是一位平凡老农人的“底气”,家底。
五
白云深处的岫云村,于梁上俯瞰,童话般旖旎。山影依稀,鱼塘恬静。农舍,灰瓦白墙,如玉似佩般点染。李君说,“可别看表面,其实,他们比任何一个地方的农民更贫困。灾后重建,国家补助建房款,这是好事,可相互攀比家家盖起了小楼房,几辈人的钱都用进去了,因此,他们负债更多。”
农村劳动力“回流”,岫云村,任重道远!
“远山结亲”“让留守的人们有尊严地生活”,幻若一盏“灯”。
这“灯”的意义,我理解——
老有所为。
倦鸟知返。年逾不惑的李君的小舅舅陈勇益,去年已返乡就业。如今他是“远山结亲”计划团队的一员,月薪2000元。每天,他穿戴如都市“白领”,走村串户,与他熟悉的土地上的人们用乡音交谈,签订“生产”合同。“远山结亲”创意在乡间生根,如今这一模式已在岫云村以外的几个村庄拓展。
三位应届毕业大学生来乡下“打工”:
李军之:毕业于四川理工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向文科:毕业于西南科技大学,工程力学专业;
李钉生:毕业于四川理工学院,生物技术与应用专业。
农业问题,中国的现实问题,谁能说学子们又不是在困厄之中击石取火,推进乡村文明进程的薪火传递者?
那日,勇益去回访他的签约农户、月山村的淳英,他带上了我。淳英是勇益及同事上门去签订的第475单生产合同,如今公司签约农户已1100多户。
水塘边,我、李君、勇益,我们站在那里。淳英早上给鸭子用半熟的米饭拌的糠食还在那里。我目睹,淳英家几只已一岁半的老鸭在水面,破冰似倏地游出了几缕,银丝。
山光日影,天地,静得入冥。
六
去白驿镇赶集,那日,白驿镇邮政局支局长胡泽勇,带我去看位于小镇老街深处的老邮政局旧址。他讲,八九十年代,这个镇,在外打工的人邮回来的钱,全年二三十万元。那时候5000元,就算大额存款。而去年(2014年),镇邮政局收到的款额,已达一个多亿。
数字改变着乡村,改变着乡土中国,而这些惊人的数字,又消融在了乡村的哪里?建房、还贷、婚丧嫁娶、医疗救急、孩子教育、人情支应、创业投资,还是别的什么地方?
中国乡村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以城市资本为主导的农业规模化,可是乡村的最佳出路?资本化农业,谁是利益主体?
如何摒弃化工农业?
劳动力外流,当前农村“结构性”力量,在哪里?
打工者“回流”,他们能做什么?
留守老人,留守儿童问题,老无所养,少无所教(家庭教育),他们的权益谁来维护?
“换工互助”时代的乡村良风美德,可有溯回的那一天?
无数空村,谁是它们未来的主人?
……
差不多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我在我热爱的土地上进行着精神行走,我总去问我所见到的老人、妇女、孩子、村主任,老支书,以及路边、田间地里的百灵,哪怕乞丐。今天,我也问眼前、不时站在扶贫励志领奖台上,趑趑趄趄跌跌撞撞探出一条“小生产+大合作”路子的李君。
因为一时无答,我如弃婴,合目蜷缩着。
——李君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