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公民
张羊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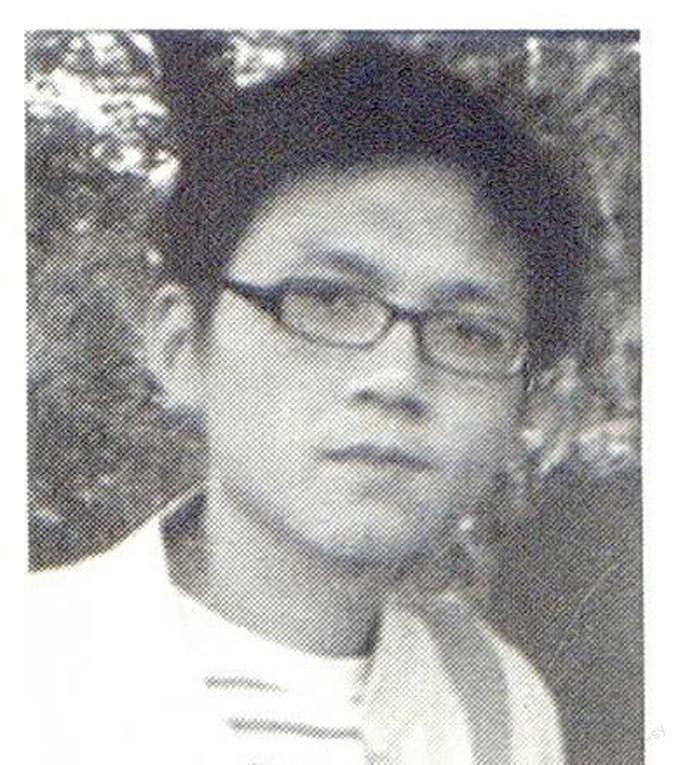
狐狸
狐狸是在小王子因为发现自己并不是拥有宇宙间独一无二的花朵而趴在草地上痛哭的时候出现的。这是一只生活很单调的狐狸,它去捉鸡,然后人来捉它,对它而言,所有的母鸡都相像,所有的猎人也差不多。它希望小王子驯养它,这样它就能听出一种脚步声和别的脚步声不一样,别的脚步声只能让它钻进地洞,小王子的脚步声却像音乐一样把它从地洞里召唤出来。这只可爱的狐狸,给小王子讲了一个彼此需要的道理:唯一性。
我们似乎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概念,狐狸就是偷鸡的坏东西,其实它也捕捉田鼠的。即便它偶尔捉了只鸡,也是出于饥饿,这种本能是纯洁的,它远没有我们这种坏东西贪婪。小的时候,我们就从课本上学了狐假虎威的故事,长大了又有可能被指责交上了狐朋狗友,反正在汉语长河里我没发觉与“狐”这个字眼相关联时是关于赞美的话。我现在只想简单想想,成语这种结构形式有时像个固执的老头儿,过于偏颇了,就没有了胸怀也有点不讲理了。狐狸敢不敢在老虎身边出现是个问题,小王子有狐狸这样的新朋、我们有狗那么忠诚的老友,有什么不好呢?
而这已经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有人说连孩子看到杀狐狸都不哭闹了。当我瞄了一眼那些图片,慌忙转身,大批狐狸皮晒在树干上,就像老农晒着一根根柴火。在狐狸因为皮毛而毫无尊严地死去时我们把人类的尊严也扫得一干二净。
我平生见过一次狐狸,三四只的样子,它们毛色黯淡,杂乱,蜷缩在一只铁丝笼里,眼神有点捉摸不透,与我想象中的优雅和神秘沾不上一点边。如果我的判断没错的话,他是一个山民,捕猎为生,来自哪座山村无从知晓,他双臂交叉,耐心地搜集着来往人群中可能性的主顾。但我能确定,在我生活的这座平原上的小镇,他是不可能卖出这几只狐狸的,许久无人问津他可能百思不得其解,靠山吃山的人杀只狐狸和我们这些靠水吃水的人杀条鲫鱼一般习以为常。
多年前我的奶奶曾从堆柴火的老屋惊叫着跑出来,一阵踉跄,脸色苍白,手拍打着胸口嘀嘀咕咕。母亲问她出什么事了,是不是看见了蛇?半晌过后,她才吐出了两个字“狐狸”,母亲听后也吓了一跳,是不是看错了?猫吧?奶奶一个劲地摇头,“尖嘴,大尾巴,怎么可能是猫呢”。母亲拉着她壮胆再进去看看,奶奶却只是一个劲往后退。那刻,我的少年英雄气概顿时布满全身,我说我进去看看。母亲连忙伸出的手没能拉住我细幼的胳膊。我在老屋里仔细搜寻了一遍,除了一只老鼠外没有任何动物的踪影。母亲和奶奶才又提心吊胆进屋子看了看。
其实谈不上英雄气概,在我眼里,狐狸不过是一种可爱的小动物。至于有关狐狸的邪乎传说我是向来不相信的。比如那次某厂原址翻建,老房子里逮住了两只白狐狸,一个胆子大的工人两铁锹就把它们铲死了,一个月不到,这人就得绝症死了。类似的故事经口口相传更把狐狸的传奇色彩渲染得越来越悬乎,我只是觉得某种巧合而已。我不反驳奶奶是不是眼花看错了,即便真有狐狸出现也不是奇怪的事。当家园丧失,狐狸也有流浪的时候。《武进县志》记载: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芳茂山猛虎伤人。康熙三十年,迎春乡民于山中捕杀虎六只……然后人口增长迅猛,土地开发加紧,捕猎增多,野生动物锐减,然至民国时期,仍见水獭、狐出没,兔、刺猬、獾、黄鼠狼、野猫、喜鹊、黄莺、啄木鸟甚多。芳茂山离我居住过的村庄不过几十里而已,山不高,三百多年前居然也有老虎生活。时至今日,这片土地上能常见的可能也就喜鹊、麻雀了。但狐狸肯定还有的,过着躲躲藏藏的生活,一旦迷路了,穿乡过野,也就串门到了我家的那间老屋。
曾看过一则晚报新闻,说长顺街一家店铺打起了吃“狐肉煲”的招牌,店内张贴了大量的宣传画报,画上了红烧狐肉、炒狐心、炒狐肝、狐肉煲等菜品。看这菜单有点“全狐宴”的味道,只是没人敢轻易品尝。那么多可爱、温顺的动物都难以幸免于人类这张嘴巴,狐狸为什么就不能吃呢?说这话并不是我赞成人们吃野生动物,实在是感谢狐狸,终于让食物链的终端者懂得了禁忌。
“农场住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如此场景适合鬼狐登场,《聊斋志异》一书中甚多,却也是蒲松龄真实的宿处。荒野孤寂,蒲松龄难免想入非非,这本书因此也成了我辈青春期时部分幻想的源头或依据。
试想一幅盛夏的情景:一只狐狸站在缀满沉甸甸的紫亮葡萄串下,它试了几次弹跳动作,始终没能摘下一串几乎触手可及的葡萄,它咽了几下口水,自言自语了一句“这葡萄是酸的”。我觉得这是一幅挺美妙的画面,闪烁着童话里的温情,这样的土地上,真有几只狐狸的身影时隐时现,倒也陡添了几分灵气。
可以时常翻翻那本哲性好书圣艾克絮佩里的《小王子》,再温习一部暖心的老电影吕克·雅克的《孩子和狐狸》,让我们,让我们所有的大人们坐下来,静静地看一看想一想,为什么在孩子眼里,我们这些大人总是喜欢数字,为什么孩子对我们的宽容远远超过我们对他们的宽容……我们这些大人真的有点像大人了。
草狗
它识得时间的形状:当钟表上的时针与分针成150度角时,教授的身影就会出现在它眼前。它总会提前几分钟,乖静地坐在广场的花坛上等候他……车站的管理员老了,车站旁卖热狗的人也老了,日落日出的弧线从教授的墓碑上划过了十个年头,它还在等候着一张熟悉的脸,它如何晓得那个人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呢?
那只名字叫“小八”的秋田犬,让我想起和我相处过美好时光的“小嘿”,它们的模样那么相似,它们把逝去的岁月欢跃得那么诗意。这个世间上有一种动物,一旦说起它我就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比如《忠犬八公》里的秋田犬,比如《零度寒冷》、《最后的猎人》里拉着雪橇狂奔的爱斯基摩犬,比如我的老伙计中华田园犬:一条叫“小嘿”的草狗。
我曾经写过《关于一条狗》,还写过《关于另外一条狗》。我担心还会有第三条狗、第四条狗……的故事碰触我的神经,使得我不停地写下去。于是,到这篇文章为止,我决定不再写狗了。而且,当我看到那些穿着各种颜色和款式的毛衣、剪了奇怪发型人模人样地在城市过冬的狗,我顿生厌恶之感。我找不到一丁点记忆中的狗所拥有的性格和温情,它们各有国籍、各有血统,却被取上了同一个名字:宠物。它们与这个国度里“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各司其职的古老秩序没甚关系。
有天我看到妻子接完电话就哭了,问其原因,她啜泣着告诉我“妞妞”不见了。岳母说这两天有个人老在门前门后转悠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得手的。我脑子里冒出之前和一个朋友聊天时的情景,他给另一个朋友打电话,乐呵呵地让对方想办法去乡下弄条狗,他说想念狗肉的味道了,但饭店里卖的不知道来处不敢吃,万一是毒死的狗那可有点得不偿失。看他挂电话时满意的神情我可以想象电话另一头那种拍着胸脯“小事一桩”的心领神会,只是不知道哪户农家的狗要倒霉了。不仅是狗丢了命的事,养狗的人家还要伤心难过老长一阵子。在乡下,人和狗的感情是很深的,狗不像其他家畜,就是家庭的一员,一户人家一般会把狗养到终老。在我家乡,如果碰到用猎枪或药物偷狗的二流子,全村的人都会拿着农具、砖头什么的去追赶打狗的混蛋,我记得有人回忆此类事时曾写到“村委会本来用于公布账目的黑板上多数写着‘打狗者拿着打死这样充满了战斗的话”,可见人与狗的感情了。
岳娘家养的“妞妞”是条温顺的黄金猎犬,已经有了身孕。那狗壮实,我第一次去岳母家它就摇头晃脑地迎上来,突然直起两脚搭上我的肩膀,我虽然吓了一大跳,却被这狗的友善和热情感染了。“妞妞”不见了,妻子这一哭哭得我也很难过。可一会儿妻子又破涕笑了起来,小孩子性格弄得我莫名其妙。她说,“妞妞”是黄金猎犬,偷狗的人肯定是去卖给想养狗的人的,他不会舍得杀,那么小狗狗也就没事了。妻子非常善良,她如此自我安慰,我连忙说对啊,怎么一开始没想到呢。过了两天,我担心岳母老俩口伤心,两个女儿都出嫁了,养条狗也热闹些,就问有养狗场的朋友给我弄条狗过来,要黄金猎犬。本想给岳母一个惊喜的,她却说算了,不想养了,免得再难过一次。我想想也是,冬天对狗来说是个不祥的季节,这个不祥的季节每年都会来的,我已经碰到过好几个这样的冬日,一场雪下到心里就积在了那儿。
我还听到过一个悲情的故事:有一年某某回苏北老家,带了不少苏南土特产回去,回来时老家人送他一个礼物——一只怀孕的母狗。邻居开玩笑,这狗还不宰了下酒?某某说,那起码等狗生下狗崽再说。母狗生了四只小狗。三四天后,那只母狗就不见在某某家门口晃悠了,邻居问,你不会真把狗宰了吧?某某笑笑,指指肚子,早就在这里了。邻居听了打了个激灵,从此对某某避而远之。至于故事里我感兴趣的部分并没有听到,那四只小狗有没有养大?养大了的命运何去何从?时空切换到十九世纪的西方,母亲乘迈纳尔(加拿大博物学家、鸟类学家、自然保护工作者,《我与飞鸟》一书的作者)和哥哥特德不在家的时候,请人把两只衰老的狗永远麻醉过去。那两只狗并排躺在一只木箱子里,葬在老宅一棵树的树阴下。麻醉、木箱、墓地以及迈纳尔和特德兄弟俩的热泪盈眶,已不亚于二十一世纪一次文明的葬礼。据考古发现,即便是四千年前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分明可见先人已为狗留有一个进出的门、墓葬里尚有狗的骨骸,四千年后的东方文明还能出现以上的寒心一幕。
据说狗和狼有一共性,双耳向后贴、尾巴摇摆的时候,对人是没有攻击性的。当狗表达这样一番情感的时候,作为拥有养狗十多年经历的我来说,总想起一种远古的朴素味道:夕阳西下,一个农人扛着锄头走在归家的方向,一条老黄狗尾随其后,它在那条乡间小路上,左闻闻右嗅嗅,偶尔停下来翘起一只后腿,进行必要的生理排泄。农人好像察觉到了一丝动静,止步、回首,叫唤一声,黄狗立即跟了上来,不紧不慢地在他身后摇晃着。其间默契的节奏,兼含着两个物种间的依附与信任。这种微妙关系的保持,一晃已是数千年的时光……而今,人们逐渐爱上了那些名字洋气的宠物狗,它们出门很少自己走路了,要么被捧在怀里,要么如富家少爷般坐着豪华“轿子”,主人对它们比主人的父母还好。我所见的还在边走边觅食的狗,大多一副流浪汉的样子,其实这些草狗才是我们的亲人,它们也有着那么好听的名字:中华田园犬。
“小八”还在等它的教授吧,它把自己等成了一座关于忠诚的永恒的雕塑。它等候的姿势让我浮现起那些年的状景,一个孩子坐在门槛上,等待他的“小嘿”从暮色里归来,他也等过了许多个漫长的冬日。
麻雀
当我想写下“一只黄雀说着蓝蓝的话”时,一只青花瓷盘子端到了面前:用鸭肠系好的百叶卷。好客的主人说,这是黄雀,不用吐骨头。我原本是喜欢吃百叶的,一下子感觉那是张裹尸布。“男孩们会撕麻雀、点燃天牛角、捉青蛙打得胀得老大,拉住野猫的尾巴甩得飞快然后一松手让猫飞出去,这样的事他撞见就发抖,脸煞白,浑身冷汗,人家就笑他”,如果我也有一个顾乡这样的姐姐,她也会如此描述我这个“没有多大出息”的弟弟。
在小镇破旧的粮管所附近,我驻足停留了很久,我在看一群麻雀,路过的人在打量我这个如此认真看麻雀的人。我眼睛的余光发现了他们脸上的惊奇。我在看一群麻雀,我发觉麻雀也居然如此美丽,造物主给了它们与其他物种不同的独特样貌,而每一种具体的生命形式原本就是美丽的。
“太湖平原上银色的水稻田/平稳闪烁的月光……/候鸟沿着清晰的树叶/飞向独立命名的南方/唯有麻雀,俨然如/双手背握的老村长/在谷子地搜寻/粗心农民遗漏的口粮”(《单行道》)。麻雀将是我汉语写作使用的基本词汇:它和人类纤维交织、镶嵌,象征着中国古老土地的命运。
它们落叶般从窗边滑落,又猛地翻飞,提醒我更认真地阅读这个不察觉间业已来到的冬日,以及江南四季不再分明的命运的无常。数日前,几百只麻雀集聚在池塘边的几棵柳树上,我听不懂它们在吵些什么,在小雨夹雪的阴郁、湿冷天气,我只能听出一种不安,一丝冰凉与凄苦。像天气放晴后,它们欢聚在那片荒地上,从枯黄的藤藤蔓蔓中找寻杂草和野生禾本科植物的种子,它们吵些什么我依然听不懂,但我听出了一种欢快。
我曾仔细观察过三种常见的鸟在这片土地上与人类相处的生活方式:在我眼里,麻雀就像活泼、好奇的孩子一样,在人们身边跳来跳去;而喜鹊却像有了经验的青年,与人类保持一定的距离,在屋前屋后数十米处的大树上居家过日子,并以其吉祥之鸟的身份纳入人们欢迎之列;与喜鹊享受同等待遇的夏候鸟家燕更是接近了一步,在农家的屋檐下营巢育雏。
我越来越喜欢麻雀这种小动物了,因为在之前的感情基础上,我又知道了它另一个名字:家雀。很多时候,我更乐意把耐心细致的李时珍看作一位写实的民间诗人,“栖宿簷瓦之间……故曰瓦雀”,以瓦与雀之间的某种联系而命名远比用外表色彩命名的“麻雀”要来得蕴义悠长(瓦,用泥土烧成,有拱、平或半个圆筒等形状,是江南民居铺屋顶时普遍使用的建筑材料,今时几近在某些怀旧味道的仿古建筑中偶尔露面。瓦,数百年来被雨点打磨成寒青的光泽,被江南散落了的一个名词,意味着瓦楞的流畅线条或一株屋檐草的失踪,也意味着一种鸟的别名成为记忆中沉睡的符号)。
麻雀作为和人类伴生的中国最庞大的留鸟家族,却因其杂食的生活习性而被人类收敛住该有的慷慨。在人们眼里,只看见夏、秋之际偷窃着他们辛勤种植的禾本科植物种子,对它们起伏于田野间捕食鳞翅目害虫的一幕却视而不见。于是,五十年前的一个大悲剧开始上演,人类与相伴了数万年的鸟儿反目成仇,把被它们列为与苍蝇、蚊子、老鼠为伍的四害之一,政府动员全国城乡居民,在规定的日期和时间内,掏窝、捕打、敲锣、打鼓、放鞭炮……把它们轰赶得既无处藏身之处,又得不到喘息的机会,最后活活累死。麻雀的委屈无处倾诉。一年以后,当各地陆续发现园林植物出现虫灾,有些甚至是毁灭性的时,人们开始为麻雀“平反”。四害之一的麻雀终于先后被臭虫、蟑螂替换。
此刻,许多只褐黄色的麻雀在草坪上小幅度地跳跃,觅食,像风掀动着一枚枚落叶。数十只麻雀在我生活的领地起起落落,那么地舒心,并感化了我。它们孩子般顽皮,像为这步入暮年的世界增添几分希望和生机。我每看到一只麻雀双爪拘谨地向前拎着、“扑棱扑棱”地飞起时,我就想笑,我就想“哦呦哦呦”地喊几声,它一分神,节奏慢了一拍,就停落了下来。然后天真地责怪我几句,再次飞起。
如果五十只麻雀飞进清时,飞进袁枚的《随园食单》,就成了“煨麻雀”:“取麻雀五十只,以清酱、甜酒煨之,熟后取爪脚,单取雀胸、头肉,连汤放盘中,甘鲜异常。其他鸟鹊俱可类推。但鲜者一时难得。薛白生常劝人,‘勿食人间豢养之物。以野禽味鲜,且易消化”(“薛白生”注:我读的《随园食单》这个版本将名医薛生白误作薛白生,当时我还责怪地写下“只关注麻雀味美的袁枚,和名医薛生白相交甚久、诗酒流连,居然把友人的名字记错,由此可见还是沈归愚与薛生白感情要好些”,原来错怪了袁枚。此处与本文无多大关系,说一说只是如实记录我的阅读经历)。
如果一百只麻雀飞进二十一世纪,飞过祥和的乡间傍晚飞进农家乐,就成了一道“五彩雀肫”。一只麻雀的个头实在小得可怜,去头去爪的尚需三五十只凑成一盘,一只麻雀一个肫(胃),按比例想想,可约莫猜出一盘雀肫所用去的麻雀数量了(我每次都要阻止做东者点这道菜,少上一盘,上百只麻雀就可逃脱厄运,餬餬嘴的事,还是少干些张口就灭一个群落的事)。
打量着周围微笑的面庞,肌肉的伸缩间正悄悄洗却中国乡村慈母般温和的遗容,我似乎听到了夕阳失去一个个伙伴的孤独叹息——它变得沉默而犹豫。好吃,好吃。于是,我看着他们吃掉声音,吃掉形状。顷刻间,一只只青花瓷露出原来的面貌,我们以及曾经制造这些瓷器的祖先吞咽下了这片古老土地上最古老的民族音乐。
蛇
河水到了汛期,秧田到了灌溉的日子,加上雨季来临,苏南平原水汪汪的,让北方人看上一眼都觉得可以解渴了。在满满的秧田中,镶嵌着大大小小的沟塘,水面已经和秧田几乎连成了一片。鱼儿们纷纷跃入水渠、田沟,养鱼人拦也拦不住,顶多沿着自家的沟塘围上一道简易的网。这样的日子,跑出来的各种鱼儿成了大伙共有的好食物,会捉鱼的和手拙的,他们之间收获的差距可大了。我只能乘着暮色,等伙伴们满载而归后,在田野间捡漏,以免被他们耻笑(其实,相对被称为野孩子的那群从小的生活就远远比我丰富,到现在他们还在乡村延续着富有的野趣的生活)。记得有一年吧,天暗下来了,我在水田里捉到了两三条小鲫鱼。原本打算回去了,又看见秧苗一动一动的,以为还可以多捉一条,我弯腰,双手一合上去,一拎,手感完全不对……随手甩了出去,撒腿往家的方向奔跑。以后,我再也没有去捉鱼了。
那条没看清的蛇,留给了我永久的阴影,像那年雨季的傍晚一般灰暗。其实,我并不是很怕蛇,除了大人们从小告诫的巨毒的土鬼蛇(蝮蛇),还有一种就是毒性不大但通体颜色醒目、斑纹耀眼的火赤链。我有时也像其他孩子一样,勇敢地抓起一条水蛇的尾巴,抖上几抖,以免被它缠住,然后甩几下就往远处扔了出去。家乡流传一句谚语“蛇吃黄鳝——并死”,这个并有共同的意思,也有动作“拼”的意思。我跟小伙伴们钓过黄鳝,用一根木棒,系上一根莳秧线,线的另一头系上针(缝衣服的大号针),针上穿好肥硕的蚯蚓。傍晚时分,木棒插在田埂和沟塘边上,饵抛远点。半夜或清早去收线,如果一拉沉沉的吃了力,那就有收获了。有时收起来后直接扔掉,就是那种恶心的火赤链,不是蛇吃了蚯蚓,而是黄鳝上钩后,蛇去吃黄鳝,从尾巴向头部吞,整条黄鳝吞下后,体形又相仿,黄鳝在蛇的身体里挣扎,使劲蠕动,蛇也就直挺挺地被“并”死了。
我们这的蛇种类不多。有毒的除土鬼蛇外,还有一种竹叶青。但这种蛇在我父亲辈时已经罕见,我从未见过,所以只在传说中想象它的模样。此外,只有乌风梢、黄风梢和菜花蛇。其实,乌风梢和黄风梢也只是同一种蛇,叫乌梢蛇,因为背部有一条黄色的纵纹,体背由绿褐、棕褐到棕黑的变化,所以还有地方叫它青风梢。我觉得它们名字的来由,大概是爬行速度极快,在麦田间甚至发出“嗖嗖”之声。乌梢蛇经常树息,它的食谱中有蛙类、鼠类,还有鸟类。我曾有次在谷树下钓鱼,听见鸟的一阵慌叫,“扑通”一声掉了下来一条硕大的乌风梢,把我着实吓了一跳。
至于菜花蛇,我的记忆颇为深刻。某年某月某日午后,我和同村伙伴赵东去学校路上,一条菜花蛇在菜花地爬行,我俩追过去,它听到动静,开始狂蹿起来往旁边的水沟钻。菜花蛇体形大,有两米多长,捉那条蛇花了我俩很大力气,简直可以用个动词“拔”了。捉住后,一个高年级的调皮鬼硬是把那蛇抢了过去,据说卖了三块钱。三块钱,在我们十来岁的时候,可是个大数字了,所以我们非常恨他。等我们长大了,那个人因为经常偷别人家的鱼坐牢了,想想也是,连蛇也要从小孩手里抢去卖掉,免不了会再做些其他坏事吧。
我舅妈那里仿佛生产蛇的故事,都是很久很久以前了:三舅妈睡觉时,掀开被子,一条蛇蜷缩在被窝里,她受了惊吓,精神上恍惚了很久才好了起来;二舅妈说,她看见老屋里的墙壁上伸出半条蛇,还有半条在屋子外,她觉得有灾祸,就去给祖宗上香烧纸了;最离奇的是大舅妈,因为家境殷实,老跟人家说,她掀开米藤能看见有一条苍龙在缸里不停地吐米,永远也吃不完。我以前信,现在不信了,既然吃不完,大舅妈你为什么还种田呢?而且种得比别人家还多。表哥一染上赌习,多少条苍龙都来不及给你吐米了。后来听说,苍龙也是一种家蛇,究竟叫什么蛇我也不知道,有人说是乌梢蛇。
近日对散曲有点兴趣,翻得无名氏一首《虚名》“蜂针儿尖尖的做不得绣,萤火儿亮亮的点不得油,蛛丝儿密密的上不得簆……”感觉那比喻确实巧妙,有没有关于蛇的呢?翻来找去,也没见把蛇写多美的,仅什么“蛇缠胡芦”之类的。在我有限的阅读里,就一个叫乔梦符的元人写的《卖花声·悟世》还有点意思:“肝肠百炼炉间铁,富贵三更枕上蝶,功名两字酒中蛇。尖风薄雪,残杯冷炙,掩清灯竹离茅舍”,用了个杯弓蛇影的典故,初看还以为用蛇泡了杯药酒——若真是蛇泡的药酒,我也还是不敢喝的。秋分一到,老伙伴们常打电话来说,蛇肥了,回来尝尝。我说,好好好,其实,蛇肉我也不想吃了。我想的是看看他们的身手还有没有当年敏捷,跟着他们过过以前满是野趣的生活。
以前,看到蛇就会梦见它,多半受了惊,就像小时候走过田埂冷不防地踩到一条水蛇。写这些文字时,我还时不时地看看书桌下有没有蛇游出来,晚上会不会又要做梦呢?明天印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