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颖:“无能”背后是“有情”
现实情况是,文学在社会变动中非常没有力量。不过,我这个话要反过来说,越是没有力量,越要认识到力量。
“有自己的一块园地,是好的,看得轻一点,可以闲情逸致;重一些,甚至能够在这上面安身立命。”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曾这样自述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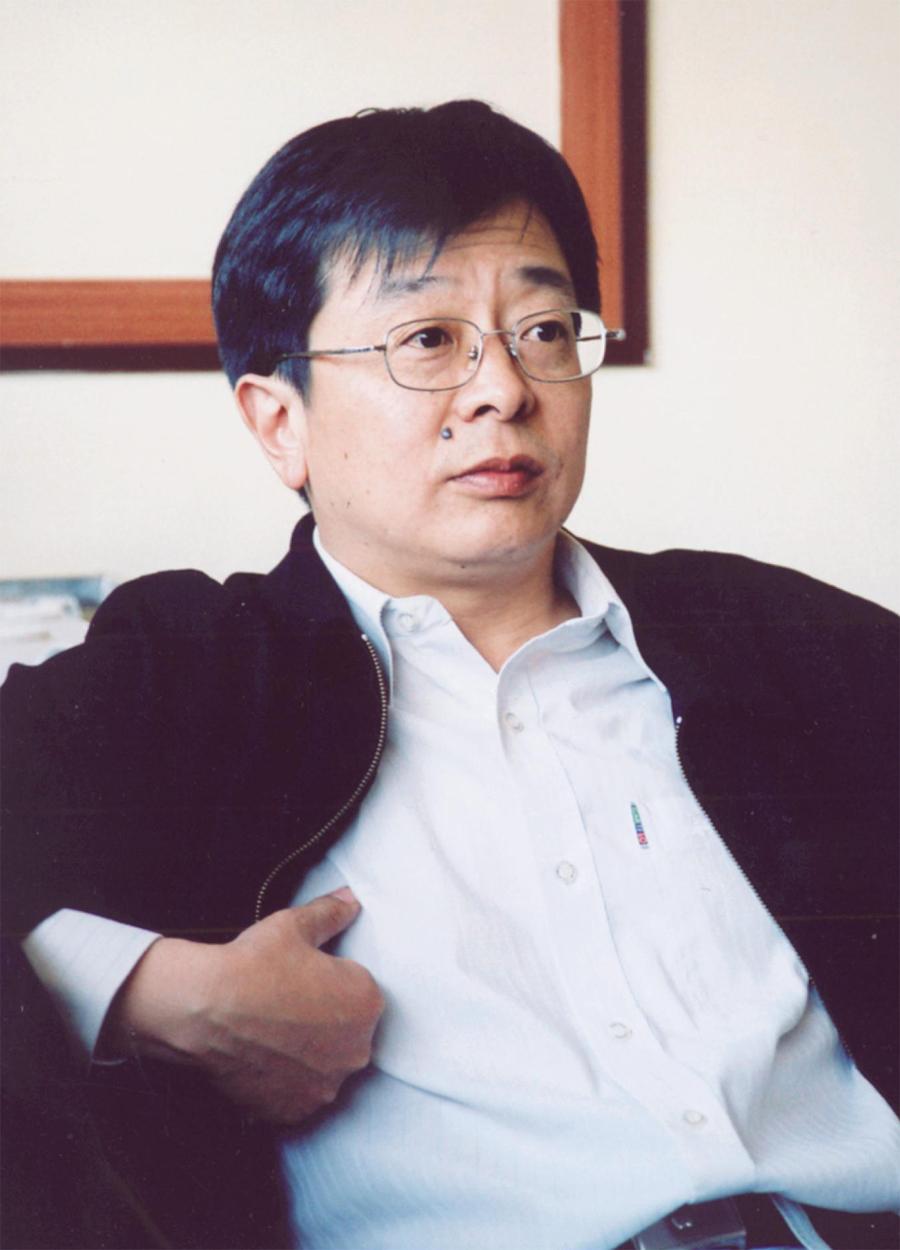
从1985年在大学里懵懵懂懂地阅读沈从文,到1997年写下第一篇有关沈从文的文章,再到2004年开设“沈从文精读”课程,连推了几本沈从文研究的图书……这些年,张新颖一直在沈从文的世界里低回流连、感触生发。很显然,沈从文研究是他长久耕耘的一块园地,也是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成果最为丰硕的领域。
《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在2014年的各种年度好书榜中名列前茅,被誉为当年度大众阅读领域的标杆。
尽管32卷本的《沈从文全集》达一千多万字,但张新颖读来从不觉枯燥、倦怠。深入解读沈从文的后半生,他发现这个世界敞开着各个朝向的窗子,隐现着通达四方也通向自己的道路。这更像是自己跟前人的灵魂的一场对话,进而完成对自己的人生困惑的解析和超越。
张新颖谈论沈从文的“有情”,担忧现实生活中的爱无能,又感受到,透过沈从文的后半生,他其实更想讲的是爱的故事。在文学写作中,沈从文把满腔的文学热情投射到了绵延如长河的普通人的生死哀乐上;而1949年正式开始杂文物研究,也是因为爱这些在漫长时光里由劳动者创作留下的物质存在,爱这段由大众喜怒哀乐构成的历史。
一个人不论在怎样变化的时代里,都可以坚持按自己的本心来做事情。其实理想的时代永远不会来,做事情就是在很多条件不理想的时候去做,这样才可以真的做成事情。这便是沈从文给张新颖的教育,同样也是留给希望有所作为的当代读者的启示。
谈现代传统:
当代作家都是现代文脉的承受者
卢欢:大家都知道,您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现代文学。有个背景是,您从少年时代就开始读“新时期文学”,一路读下去,几乎是当代文学发展过程的见证者。我相信,1980年代以来文学的巨变会深刻影响到您。与仅就现代文学本身做研究的学者不一样,您的视角和研究重心会更多受当代的因素左右?
张新颖:你这个观察是蛮对的,但是我也说不清楚自己是研究现代文学还是研究当代文学的。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方面,现代文学加当代文学一共也就一百年的时间,放到文学史上看是很短的。百年的历史中有统一性,都是现代汉语的文学,假设把语言当成工具,使用的工具基本是一样的东西。另一方面,其实我们如今大概还处于现代以来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不是说我们跳出来,不是现代了,我们还是生活在现代,还是在这个大的历史过程里面。
在这一百年的文学研究中,我不太刻意地区划现代和当代。还有一个实际情况,我在复旦大学读书教学,这里从来都是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放在一起,没分两个教研室。我大概也受这样的小环境的影响。但像你说的,与大家认为的现代文学研究不同,我确实会受到我关注的当代文学的影响。具体来说,不管是现代,还是当代,没有被当作跟我们没关系的东西。一个当代的人,深处当代的社会和文学,自然会觉得自己跟当代联系紧密。与此同时,现代文学也跟我联系紧密。研究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实际上都是研究我们自身的问题。
卢欢:也就是说,像陈思和老师那样,您也主张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应该是一个整体,在此基础上研究?
张新颖:陈思和老师、钱理群老师、陈平原老师、黄子平老师等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当作一个整体来观察和研究,是很具突破性的。他们感觉现代和当代的划分,学科上的阻隔很严重,提出这个,需要很大的力量;我进入这个学科比较晚,也是他们的学生辈,接受起来相对要容易得多。在我看来,很多事情是很自然地发生的,不一定非要受什么理论、思想来影响自己做这个事情。
卢欢:您提到,“期望与当代生活息息相通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具体到个人,便是发挥“无能的力量”,我们得清醒地意识到各种方式对理解和把握当代生活的无能、无力,同时也要积极而智慧地发现这种无能的力量。为何会如此强调“无能的力量”?
张新颖:在今天,把文学夸大到一个特别有意义的程度也不符合现实。现实情况是,文学在社会变动中非常没有力量。不过,我这个话要反过来说,越是没有力量,越要认识到力量。要有清醒的认识,有个限度,但也不应该否定、菲薄了这个力量。这才是一个踏实的态度。文学和现实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吧。
“无能”,指的是相对来讲的“弱”,微弱的,柔软的,不强大的。我特别强调“无能”, 强调看上去很弱的力量,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都在强调有能力,强调强大、有力量。那么,我觉得,被这样的社会所压抑、牵制的,没有力量的、柔弱的东西,应该反过来强调。文学本身就是弱的,它更应该关注这些东西,否则变成跟社会各种潮流一样的东西,并不是特别好的存在方式。之所以会弱,会无能,这背后的东西才是重要的。“无能”背后是一个有情的问题,爱的问题。只是,现实中,爱的力量是很无能的。
卢欢:对,您在研究现代中国的人、文、事上也谈过“有情”。我们接下来还会聊到这个话题。您还说过,很想做的是为当代文学找到和自己的传统接起来的东西和方式,只有和根接起来,才可能生生不息。对沈从文的研究,其实是您描述现代和当代文学之间密切联系的一条脉络?
张新颖:沈从文这样的作家,一生的经历贯穿了整个20世纪,对他的文学研究本身就没有现代和当代之分。除了尝试对沈从文的文学进行重新理解之外,我还想探究他这类比较特殊的知识分子和21世纪中国社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特别是1949年以后,他和这个时代是怎么相处的。他怎么在这样一个时代中确立他自己的事业,确立他在这个时代中的位置。
卢欢:当代文学不了解自己的现代汉语的传统,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却没有很好地解决?这其中是否有些僵化、落后的观念或模式需要打破?
张新颖:对。当代文学不了解自己的传统,不了解它自己的现代汉语传统。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现代汉语天天在说,就像空气一样,大家好像觉得它是天生的。其实不是,它的存在历史才不过一百年。那么,它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呢?对于普通人来说,他可以不关心这个问题,但是对于一个以语言文字为生的人,研究当代文学的人来说,当然要了解这个传统。你用现代汉语写作,却不知道就在你眼前的现代汉语的历史,这是很遗憾的事情。
这背后,还不是什么僵化、落后的观念需要打破的问题。就是没有意识,还谈不上观念。我们往往没有想到过这个事情,没有去思考一个作家为什么这样写作,而不会像屈原那样写作之类的问题。
卢欢:对于当代作家来说,需要重新去重视现代汉语传统?
张新颖:这个说了也没用,反正还是要从个体产生自觉的意识上去讨论。仅仅是其他人在说,而自己没意识到这个问题,还是没有用。举个例子吧,白先勇那一代台湾作家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才二十几岁。他们的老师夏济安告诉他们:你们一定要去读中国的现代文学,不应该只读胡适鲁迅,哪怕是左翼的胡风也要读啊。因为我们用的语言都是从他们那儿来的。他们用现代汉语进行创作遇到了很多语言上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同样你们也会遇到,你们要看看在遇到这些问题时,在你们之前的人是如何做的。文学最基本的根基就是语言。如果不了解语言,你们的写作怎么进行下去啊,怎么产生自觉的意识啊?这个例子已经过时,但现在重提还是很有意思。
对于我们当代作家来说,传统首先是现代以来的、离得最近的传统。不论我们承认不承认,意识没意识到,我们都是一个现代文学传统,或者说是现代文脉的承受者。我们不知道这个,就像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父亲、自己的来历一样。这个有点遗憾。
卢欢:我记得,您在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的论文《中国当代文学中沈从文传统的回响——〈活着〉、〈秦腔〉、〈天香〉和这个传统的不同部分的对话》中提到了“沈从文传统”的概念。除此之外,现代以来的文学传统还有哪些?
张新颖:沈从文只是现代以来的文学传统里面的一支。这个表面上不强大的传统一直没有断过,以至于我们后来可以在侯孝贤、贾樟柯的电影和贾平凹、王安忆等人的创作中看到这样的传统,一直在流动、延续。至于还有哪些传统,我说不好。为什么呢?你一旦总结出来,就真的变成僵化的了,变成一条一条的了,而且这个对创作没有益处。创作还是要作家自己去体悟。哪怕是那些他说不出、道不明的东西,可能对他的写作更有实在的用处。
卢欢:再说远一点。有人说,当今中国社会急需“三个对接”,即把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学者与大众对接起来。您觉得,相比而言,哪方面的“对接”更重要,哪方面当今知识分子又做得比较欠缺?
张新颖:没有哪个更重要,都重要。但是这样说呢,也都没用。在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东方和西方、传统和现代、高雅和大众的对接。今天的中国需要这样的,再过一百年的中国也还是需要。问题是怎么做。如果变成一个口号的话是没有用的,其实这个口号已经喊了很多年了。我觉得,相对来说,更重要的是每一个人做一些这方面的具体工作。深入具体工作的内部,哪怕看起来不一定伟大,只要有一点点贡献就好。你找到自己的方式,做具体的事情就好了。
谈文学批评:
文学应有能力向辽阔的生活世界敞开
卢欢:“我总是有这样的疑惑,觉得人的感悟力是天生的。因为我看到一些杰出的人,他们并没有深长的生活阅历,就能对艺术做出深刻的把握。张新颖就是这一类人。”作家张炜曾这样评价您。关于文学的感悟力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培养的,您怎么看?
张新颖:我的回答可能比较平庸。我认为,文学的感悟力既是天生的,也是需要后天培养的。一个人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有文学才能的。哪怕是天才,他也不是具有自觉意识的,而需要后天的努力来帮助他发现这种天才。我感觉自己没有文学创作的才能,走上文学批评这条道路,好像不是刻意发展出来的,不知道怎么就到了这一步。
卢欢:最初您对文学的感情是以文学批评的形式表达的。现在,文学批评对您而言不仅是一种学术工作,还是一种生活方式?
张新颖:我从1987年开始写文学评论,那时候还很年轻,至今也有近三十年了。这么长的一个时期中,文学批评一直伴随着你,肯定和你有一个比较密切的关系,算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吧。也可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这是我爱文学的一个形式,参与当代文学的一个形式。
卢欢: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阅历的扩充,您对文学批评的理解,以及文学批评活动都发生过变化吧?您自己有意识地分过阶段么?
张新颖:当然有变化。人的想法都会发生变化。我自己并没有分过什么阶段。我好像做的也不像文学批评,也没有特别有意识的变化,而是顺着这么走吧。
比如我在高校当老师,不做文学批评,可以吗?当然可以啊,不会损失什么。从世俗意义来说,我把科研工作和教学工作做好就可以了。除此之外,文学到底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呢?虽然说如今文学在大众中声誉很差,但是你还是得做点什么吧,那么就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做。我在文学批评上没有一个什么规划,说一定要怎么做,也没有说这个一定要给我带来什么。往往是,有话多说两句,没话就少说或者不说。
有人会说,我是一个批评家,应该有一个责任,批评家的责任就该如何如何。有这种责任也挺好的。但是我确实没有这种责任意识,也不需要对当代文学负责任。我没有这么大的抱负。我只是会对自己喜欢的东西投入更大的关注度和精力而已。
卢欢:说到您的兴趣爱好,我了解到您在同辈人中有点“另类”,您对新音乐十分着迷,“架子鼓打得不错”。崔健、张楚这些曾经的摇滚青年都曾进入您的批评文字里,跟北岛、王朔等作家相提并论。
张新颖:我现在也不关心这些东西了。喜欢摇滚乐,那是二十几岁的时候。我感觉,我当时的关注、喜欢,和今天一个二十几岁年轻人对摇滚乐的喜爱还是不太一样。因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崔健等人的意义与今天的摇滚歌手的意义是很不同的。我对于崔健的兴趣,不仅仅是音乐上的兴趣,而是对一种文化的兴趣。
卢欢:这与您当时对先锋文学的研究看似触类旁通。您关注的问题“文化反抗的代言人”以及“隐而不现的时代精神”是如何被揭示出来的?
张新颖:对了,如果要将我的文学批评分个阶段的话,就有关注先锋文学的这个阶段。我1985年进大学,当时正是先锋文学兴起的时候。到1989年之间,我的主要兴趣就在先锋文学上。但这个也不特殊,像我这个年龄的文学青年大概在那个阶段都会关心先锋文学。
先锋文学有一点很吸引人。当社会发生变化时,文学也会有更深的变化出来,这时候先锋文学登场。包括先锋文学作家在内的年轻人会更敏感地感受到社会生活的变化。他对一个新的世界的向往和追求,或者说他对表达世界的新方式的渴望,都投射在他的文学里面了。
卢欢:您后来对贾平凹、王安忆、张炜等这些文坛长跑健将式的作家关注得较多,对他们在文学创新上的努力和贡献怎么看?之所以问这个,是因为很多评论家热衷于谈作家创新、超越的话题,但王安忆在接受我采访时直言自己是一个创新性不强的人,她觉得,我们回过头去看一二百年前的文学史,会发现真正的革命性的阶段是很少的,要积累很多很多年,才会有一次革命爆发。一个人一生里面是不可能有几次创新的。
张新颖:我们一直都在创新啊,不断创新啊。好像每一代的文学都是从头再来。好像文学本身是没有积累似的。好像从我开始,都是新的。回过头来看,这些是成问题的。我想王安忆说的是对的,文学是需要积累的,需要长久的时间来促成的。
现在好些了,有贾平凹、王安忆这样的作家,写作时间超过三十年,创作了那么多作品。从世界文学史来看,这个并不特殊,国外好多作家七八十岁都还在写,还写出好作品。而就现代文学发展的情况来说,就比较特殊了。我们讲文学史,这个十年讲这一拨作家,下一个十年讲另一拨作家,讲的又都是他们在青年时代创作的文学。这样老是讲青年文学史,并不是很健康的状态。一个成熟的文学状态是需要不同年龄、不同经历的人构成的状态。比如我们讲今天的文学,就不能绕开那些六十多岁的作家,像贾平凹。当然,你光讲贾平凹也不行,也还有四十多岁的作家。同一个阶段,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的,都有作品被关注到,这才是正常的状态。
至于个人创作的创新,长时间的写作中肯定也会发生些变化,但不必把创新当成强迫症。问题是,不是我要创新就能创新出来的。一天到晚都在喊创新,这是比较可疑的。
卢欢:就您自己而言,各个年龄层的文学创作中,您更关注与自己同一代的作家么?
张新颖:我不考虑作家的年龄,不管一代一代的。我也不是那种很有责任感的批评家。我只关心我喜欢的作家。贾平凹、莫言、王安忆等,是比我长一辈的;余华、苏童,差不多跟我同一代,但比我年长;也有跟我年纪差不多的,或者比我年轻的。当然,我喜欢的作家也不会一成不变。我也在变,文坛也在变,有新的人进来,也有旧的人出去。
卢欢:我想反过来冒昧地问一句,您批评过自己不喜欢的知名作家么?
张新颖:其实,我很少批评某一个作家。我不喜欢的,就不说嘛。很多人讲文学批评就应该是批评嘛,要勇敢。我觉得这不是勇不勇敢的问题。说别人坏,不需要多么勇敢。反倒是说别人好,才需要勇敢。因为我们现在不太会说别人好,把我们当代创作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揭示出来。直言批评的批评家也有做得很好的,但这不是我的方式。在我看来,空洞地说好,跟空洞地说坏是一样的,是语言的浪费,没有任何意义。而真正揭示出这里面值得赞美的东西,说出自己感受到的东西,才是有意义的。
卢欢:您评论林白《妇女闲聊录》的文章让我印象深刻。您说林白尝试把“上升”的艺术改变为“下降”的艺术,从个人性的文学高度“下降”到辽阔的生活世界之中去。有的作家就偏好这种低姿态的写作,这意味着他们更有雅俗共赏的追求?
张新颖:我说这个,是因为作家和批评家,从事文学写作和研究的时间长了,不管用什么语言,脑子里一定会形成某些固化的文学观念,比如对什么是好的文学,文学应该是怎样的,会有相对偏执或者说一成不变的认识。这会带来新的问题,我对此是有疑问的。文学是需要不断重新发现的概念。但是我们的文学教育长期形成的观念,就是把文学变成越来越狭隘的东西,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文学应该有能力向辽阔的生活世界敞开,对文学之外的东西敞开,让外面的东西进来。
所谓“下降的艺术”、“低姿态的写作”,这些还不仅仅是雅俗共赏的问题。外面可能不会承认这是文学,更不要说欣赏了。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文学的观念总是在变化。我们不必把它变成排斥性的观念。如果文学把什么东西都排斥了,这也不能写,那也不能写,那么它把自己当成什么呢?当然,你可以说是纯文学。但是,把什么东西都排斥掉了的纯文学还存在吗?
卢欢: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应该是没有那么严重的分野吧?
张新颖:比如说,斯蒂芬·金的作品是严肃文学还是不严肃文学?我们只知道,他比我们很多纯文学作家写得好。严肃不能构成判断标准。严肃文学中也有很多糟糕的作品嘛。至于什么是好文学的标准,我想肯定是有标准的,我说不出来。很多人说不出来,但是心里会有标准。而且,这个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敞开的。
谈沈从文研究:他有一个自我,
在任何时候不会轻易放弃和改变
卢欢:您对沈从文的阅读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之前就出过专著《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而新著《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据说是“十六年磨一剑”。长期研究这位作家,更多是基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教学传统,还是自己的需要?
张新颖:这些说法太夸张了,我开始读沈从文的时候只是个学生,没多少深的体会,更谈不上研究。要说研究大概可以从1997年算起,但期间也不是全部心思都在沈从文,还做了许多别的事。不过对沈从文的阅读和思考倒是没有断过,这十几年每年有一个学期要讲一门“沈从文精读”的课,客观上也促进了阅读和思考的深入。教学的需要和自己的需要常常分不大开,因为我上课就是讲自己想讲的东西,这二者在我这里不那么矛盾。
卢欢:作为读者,您如何做到常读常新呢?
张新颖:要是你在一个较长的时段里读一个作家,一定要常读常新才行。这要求你选择读的作家要有足够的丰富性,沈从文就是这样一个作家。特别是从沈从文的后半生,你可以看出他的丰富程度,远远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范围之外。我特别不认同简单化、标签化、概念化、理论化地理解沈从文,那样是不可能常读常新的;还有就是,你自己也在不断变化,三十岁的人和四十岁的人不一样,三十岁没有读出来的东西,也许四十岁就读出来了。
卢欢:关于沈从文前半生的传记已出版过多种。这部传记则着力于呈现他后半生的经历,相比之下这部分是不大广为人知的。这种写作体验是不是跟写1949年以前的他很不一样?笔调也要压抑一些?
张新颖:一般我们会说沈从文的一生,以1949年为界突然被劈成两部分,前面一部分是文学家,后面一部分是文物研究者。写1949年以前的他可以写得多彩多姿,甚至可以写出传奇性来。后半生基本是一个调子的不断发展,一路压抑下来。
卢欢:从1949年的“精神失常”中恢复过来,到主动调去博物馆当讲解员,到长子被划成“右派”,自己常在“斗争”呼声来复中如临深履薄,到下放湖北咸宁的干校……沈从文是怎么对待和转化痛苦、磨难,从而“好好活在人间”的?
张新颖:简单说,是忍受,逆转——沈从文自己说是“反报之以爱”,就是这个“反报”,很了不起。我在书中写过,从1949年的“精神失常”中恢复过来,没过几个月就进入革命大学改造思想,沈从文当然明白自己正处在生命的一个大转折过程中。他回顾此前的人生,总结出自己的存在方式:把苦痛挣扎转化为悲悯的爱。“一生受社会或个人任何种糟蹋挫折,都经过一种挣扎苦痛过程,反报之以爱。”《边城》和《湘行散记》,及大部分写农村若干短篇,如《丈夫》、《三三》都如此完成。所谓生动背后,实在都有个个人孤寂和苦痛转化的记号。……工作全部清算,还是一种生活上的凡事逆来顺受,而经过一段时日,通过自己的痛苦,通过自己的笔,转而报之以爱。”“现在又轮到我一个转折点,要努力把身受的一切,转化为对时代的爱。”
卢欢:1952年沈从文在川南小山村土改时谈及自己正遭遇的思想和文学上的困境说:“对人生‘有情’,就常和在社会中‘事功’相背斥,易顾此失彼。”您说,他确曾抱着将“单独”的生命融合到“一个群”的意愿,但最终,还是投向了“有情”的传统。这个传统具体指的是什么?
张新颖:这个传统指的是更长时段的历史——比现代以来的历史更长的历史——中,一些杰出的文化创造者遭受困厄而创造文化的伟大传统。当沈从文深陷困境的时候,他自觉地将自己的文学遭遇和人的现实遭遇放进这个更为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之中,可以找到解释,找到安慰,更能从中获得对于命运的接受和对于自我的确认,寻求支撑的力量。
卢欢:现在回过头看沈从文三十岁写的《从文自传》,您会认为这些早年的文字其实为他后来的人生埋下了惊人的大伏笔。也就是说,无论是之前创作文学还是后来从事历史文物研究,都是因为他生命中有一脉相承的东西在起作用?
张新颖:他有一个自我,在任何时候不会轻易放弃和改变这个自我,所以才有一脉相承的东西。他为什么做文物研究而不是做别的呢?这里面有一个生命发展的连续的过程,只不过在这个生命发展的过程当中,这样一条脉络是潜伏在下面的,潜伏到什么程度?潜伏到作者自己也不知道的程度。他的这个传记写的是他二十岁以前的生活,也就是说他到北京以前在湘西的童年,在湘西部队里面的少年和青年的样子。他写出了一个少年到青年的人对于中国历史、对于文物的热爱,以及它们和自己生命的关系。比如他在湘西部队里面当兵,一个月大概三块钱的补贴,但是他随身的小背包里面的一本字帖就会值六块钱,另外一本字帖可能值五块钱,还有一本字帖值一块钱,你想象不到一个小兵的背包里面有这样丰富的财产。他在军人陈渠珍身边保管书画、青铜器、古书,闲着没事时就帮着晒书和清点文物。他做文物研究的那个种子,其实从他的少年时代就已经埋下了,不过这个种子发芽长出来的时间非常长,经过二十年或者三十年这样漫长的时间。
卢欢:瑞典汉学家马悦然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看成是一部非常有刺激性的长篇小说。这是不是也侧面说明了他的文物研究与文学创作其实是有着紧密的关系?
张新颖: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当成小说来读,对于文物研究的“外行”,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也不失为一种有趣的读法。你可以把服饰当成小说的主人公,看它在不同时代的形态和变化。沈从文自己还曾说过这是一部长篇散文,用了分章叙述的结构。
沈从文的文物研究和文学相通,怎么个相通呢?第一是,你看他感兴趣、下功夫的东西,很杂,所以他把他的研究叫做杂文物研究;但这些很杂的东西有个共同的地方,大多是民间的、日常的、生活中的,不但与庙堂里的东西不同,与文人雅士兴趣集中的东西也很不一样,你也可以说,他的杂文物,大多不登大雅之堂。这些杂文物,和他的文学书写兴发的对象,在性质上是统一的、通联的。沈从文钟情的是与百姓日用密切相关的工艺器物,他自己更喜欢把他的研究叫做物质文化史研究,以强调他的物质文化史所关注的与一般文物研究关注的不同,他关注的是千百年来普通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劳动、智慧和创造。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不正是民间的、普通人的、生活的世界?
第二,沈从文对文物的爱好和研究,关心文物背后的人。年复一年地在历史博物馆灰扑扑的库房中与文物为伴,很多人以为是和“无生命”的东西打交道,枯燥无味;其实每一件文物,都保存着丰富的信息,打开这些信息,就有可能看到生动活泼的生命之态。汪曾祺说他搞的文物工作,是“抒情考古学”,也就是说,物通人,从林林总总的“杂文物”里看到了普通平凡的人,通于他的文学里的人。
第三,关于历史。文物和文物,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东西,它们各自蕴藏的信息打开之后能够连接、交流、沟通、融会,最终汇合成历史文化的长河,显现人类劳动、智慧和创造能量的生生不息。工艺器物所构成的物质文化史,正是由一代又一代普普通通的无名者相接相续而成。而在沈从文看来,这样的历史,才是“真的历史”。
在沈从文那里,历史学者和文学家,学术研究和文学叙述,并非壁垒森严,截然分明。一身二任,总还是一身。
卢欢:我注意到,每个章节后面都会补充当时港台地区和海外对沈从文及其作品的研究进展情况。而且提到,很多人认为如果他在世,肯定是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最有力的候选人。这其实印证了他是一个世界性的作家。
张新颖:我很高兴你注意到这一点,就是在叙述沈从文的经历之外,我还特别写了另外一条线索,即1950年代以来国外的沈从文作品翻译、介绍和研究,这个和他的经历形成一种对照,用的文字不多,但确实是一条连续的、隐现的线索。
卢欢:书中还收录了几幅沈从文画的速写,封面上那幅,画的是挤满五一节游行人群的桥,以及江面一叶小舟。这用来做书封有何寓意?
张新颖:我很喜欢沈从文的这几幅速写,也很喜欢这本书的封面设计。我在书里写了我对这些速写的简单解读,相信有心的读者也会有自己的体会。这个封面大致上可以解释沈从文和他所处的这个时代之间的关系。他在1957年上海出差时,住在黄埔江边上的一个酒店,5月1日的早晨画了三幅速写。当时他从窗口看出去,看到外滩白渡桥上正在通过游行的人群,“红旗的海,歌声的海,锣鼓的海”……歌声、锣鼓、红旗是当年典型的形象,可是沈从文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从这样一个时代潮流的中心,眼睛能够偏开去,看到那最不起眼的角落里有一些船。等到六点钟的时候,渔船上睡觉的人醒了,拿来一个小的网兜在捞鱼虾。那么小的网兜能拉上什么样的鱼虾?可他好像自己也不知道,就是在那很固执地做自己的事情。这个所谓的捞鱼虾对沈从文来说就是永远也做不完的杂物文物研究。当然,现在我们站在时间的后面,时间过去了,时间没有过去很长,只三五十年过去了,那个强大的潮流消退了,当年看不见的、弱小的个人站起来了,存在的时间会比这个潮流更长远,在历史上占据的地位更重要。
责任编辑 向 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