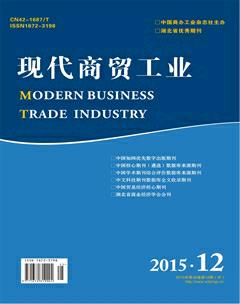延安时期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探索
刘远柱
摘 要:在抗战时期的“中国化”思潮支配下,作为西方文化支流之一的马克思主义,其中国化毫无疑问带有历史的印迹。延安时期知识分子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一种自觉选择,这种选择付诸实践后又强化了他们的主体意识。延安知识分子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探索,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并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理论探讨和历史贡献。
关键词:延安时期;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25-0221-02
在延安时期,从理论上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知识分子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产党人实现了历史性的融合。学界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得到的启示,另一部分则是从艾思奇、陈伯达等延安知识分子那里借鉴而来。那么毛泽东同志从延安知识分子那里获取了哪些思想资源?这一问题虽然难以量化,但遵循历史的线索还是可以对这一问题作一逻辑的推演。
1 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当时在延安,“中国化”已成延安学者的一种共识。从知识分子提出文化的中国化、哲学的中国化,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这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显得符合历史逻辑。首先提出了文化运动必须中国化和大众化,比如在1937年11月,《解放》周刊上发表为署名为“从贤”的文章——《现阶段的文化工作》,从贤在文中指出,我们当下的文化运动必须具有民族性和大众性。这不仅是对具有浓重外国味的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反思,也是对我们的文化运动如何做到传承传统文化和接近并融入人民大众的理性解读,要让我们的文化接地气体现人民性,如此就“要使我们的文化运动充分中国化”。其次,提出哲学研究的中国化。比如艾思奇在1938年4月发表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就提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而且指出这一运动“不是书斋课堂里的运动,不是滥用公式的运动,是要从各部门的抗战动员的经验中吸取哲学的养料,发展哲学的理论。然后才把这发展的哲学理论拿来应用,指示我们的思想行动,我们要根据每一时期的经验,不断地来丰富和发展我们的理论,而不是把固定了的哲学理论,当作支配一切的死公式”。哲学的中国化、现实化是基础和前提,它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做了理论准备。再次,新启蒙运动的发起者陈伯达在延安还对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提出了自己的许多重要见解。经过多年研究,陈伯达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之间存在契合点,只有将二者结合统一起来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因为若不如此马克思主义将成为空中楼阁、海市蜃楼,就不能接地气、融民意,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哲学和历史中汲取营养和力量,也就是必须体现民族性。
在延安,无论是艾思奇,还是陈伯达,都与毛泽东交往甚密。他们对中国化的提倡绝非偶然。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深受教条主义之害的毛泽东也容易从心理上接受中国化的见解,深感中国化的必要。于是在总结党内马克思主义者和延安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做的报告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名论断,这是我党历史上首次提出这一命题,意义重大,为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了方向。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解决的问题。”从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同志强调要解决当前中国的各种问题唯有运用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同时必须和中国的实际和国情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此外,这个命题还包含“民族形式”和“中国特性”的要求。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必须注重理论形态的文化环境及其表现形式,使原本诞生于西方资本主义氛围和欧洲话语系统下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和东方文化相结合、相融通。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阐述不仅结合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理论探索,而且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他不仅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而且传承了中华文化的血脉和基因,是一次文化重构,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华文化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
2 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内涵
在党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探索成果显著。比如张闻天不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民族化,还提出了组织工作中国化的概念,他强调,虽然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方法具有国际性,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忽略自己的国情和特殊性,在中国做组织工作必须有中国特点和中国气派,必须结合我们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民族习惯,一切照搬照抄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张在延安知识界反响强烈。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和理论界进步人士就相关问题的中国化展开热烈讨论,有人提出了学术中国化问题,比如潘梓年的《新阶段学术运动的任务》,社会上也引起很大反响,对学术中国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1939年10月,嵇文甫写成《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一文,他从比较的角度揭示了中国化的含义:首先它不同于顽固的国粹论。中国化是说把外来文化经过加工变成中国的、变成自己的。其次,它不同于糊涂的中体西用论。中国化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彻底的融合、化合、汇通。再次,也不同于中国本位文化论。中国本位文化论是非世界性和非现实性的。而“中国化”就是把世界性的文化“中国化”,就是要把世界性的文化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它必须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
在党内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和带动下,思想文化界关注学术中国化的声音愈演愈烈,更多的学者参与其中,围绕马克思主义等如何中国化的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比如1939年向林冰发表了一篇意在否认辩证法法则是科学方法的文章,认为辩证法运用的前提是对于所把握的对象要有具体的科学认识。对此,艾思奇等人纷纷撰文抨击向林冰的观点,双方围绕“辩证法法则是否是研究客观事物的科学方法”展开讨论,艾思奇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他认为,辩证法和人们认识、研究客观事物的科学方法是一致的,而唯物辩证法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方法,这无疑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普遍指导意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在胡风和向林冰等人之间围绕着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也展开了一场大讨论,使文艺具有民族性的观点得以弘扬并得到多数知识分子的赞同,这无疑也助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深化。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潮也不绝于耳。张君励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中写道:“窃以为目前阶段中,先生等既努力于对外民族战争,不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使国人思想走上彼此是非黑白分明一涂,而不必出以灰色与掩饰之辞。诚能如此,国中各派思想,同以救民族救国家为出发点,而其接近也自易易矣。”还有《论学术中国化》、《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等文章的作者叶青等文人主张取消共产党、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取消社会主义、取消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面对各种攻击,延安理论文化工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理论分析和论证。论证者中既有留学苏联的陈伯达、张如心、张仲实、杨松,又有留学日本的艾思奇,还有土生土长的和培元等。他们的论证主要集中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什么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怎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问题上。在论证者中艾思奇最为突出。早在1938年艾思奇就撰写了《哲学的现状和任务》,提出了哲学中国化现实化的主张。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艾思奇等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在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立场和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这里不仅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必须结合中国实际、中国历史和中国国情,以便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学者们认为,在中国革命的早期,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不足、对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把握不深,还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致使革命遭受巨大损失,这一深刻教训要求我们必须加快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从一开始我们党就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具有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再加上不断发展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海纳百川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品质,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可能。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知识分子们认为,要想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须坚持以下几个原则:其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理论、观点和方法。也就是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中国化,而绝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
其二,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不是空洞的理论家。其三,必须坚持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的原则,在实践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正如艾思奇所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而同时是指要能在一定的具体环境之下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一定国家的特殊条件之下来进行创造马克思主义的事业”。
(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路径。学者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可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包括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第二阶段,对在革命实践中遇到的现实问题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叫理论联系实际;第三阶段,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运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问题。
此外,张如心的《论布尔赛维克的教育家》、杨松的《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陈伯达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若干辨证》以及和培元的遗著《论新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等文章,都从不同角度支持和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由于立论的视角不同,他们的论证又呈现出一定的个性差异。从论证的出发点看,艾思奇、杨松的论证主要针对叶青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诋毁而展开;和培元的论述,则直接指向了中共党内的教条主义。从论证的有关内容来看,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论证者都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性,同时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环境具有包容汇通优秀品质,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条件。
延安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和历史探索虽然是在毛泽东同志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指导下展开的,但他们并没有局限于此,而是有了一些新的创新与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熟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认识水平是相对应的。中共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并作出理论论证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已日趋成熟。
参考文献
[1]从贤.现阶段的文化运动[J].解放,1937-11-13,(23).
[2]艾思奇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87-388.
[3]毛泽东.论新阶段[J].解放,1938-11-25,(57).
[4]张君劢.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J].再生,1938-12-16,(10).